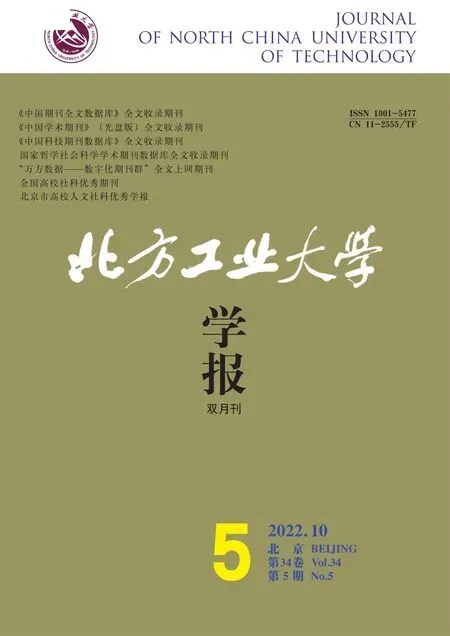秦代《春秋》經傳之學存續考略*
劉 偉
(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73165,曲阜)
對于秦代的《春秋》經傳之學,學者往往語焉不詳,在已出版的《春秋》學史著作中也罕有論述。沈玉成、劉寧所撰《春秋左傳學史稿》為國內同類著作中較早系統研究者,然其所述始于西漢劉歆,沒有提及秦代《春秋》學。[1]趙伯雄先生在《春秋學史》中說:“秦始皇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和愚民政策,幾乎禁止了一切學術活動……戰國以來諸子百家競相講學論道的風氣不復存在。 ……假如秦的統治照這樣再維持個五六十年,包括儒學在內的先秦文化傳統就將大部滅絕。”[2]其書闡述《春秋》學史也從先秦直接越過秦代而至兩漢。 然秦祚雖短,國策雖嚴,戰國時期的學術文化余脈尚存,對這一時期經學的面貌,實有進一步認識的必要。 以下試通過對相關史料的整理與解讀,對秦代《春秋》經傳之學的基本情況進行初步探討,希望能稍微彌補相關研究的不足。
1 秦代經學并未中斷
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帝國。 總的來說,秦帝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社會、文化等方面所推行的各項制度,都是以戰國時期的秦國制度為基礎的,并體現出濃厚的法家影響。 《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李斯的一段話,非常清晰地展現出秦朝統一后國家統治政策與治國思想的變化。 李斯認為“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3]亦即戰國時期列國并立戰亂頻仍、百家爭鳴的情況,在秦剛統一之初,對諸子百家的政策并沒有馬上調整,博士的設置、私學的延續都是明證。[4]
而隨著以皇帝制度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各項制度的完善,局面也發生了變化。 “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李斯認為國家應該改變思想文化領域的政策,“以吏為師”,焚毀“詩、書、百家語”,只保留“醫藥卜筮種樹之書”。[5]在這一方針指導之下,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家文獻均遭到嚴重破壞,《春秋》經傳當然也未能躲過此劫。 但正如鄭樵《秦不絕儒學論》所言,“陳勝起山東,二世召博士三十余人問故,皆用《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 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余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6]歷代有不少學者也曾指出這一點。 王子今先生也曾以稷下學為例進行深入討論,認為“以焚書坑儒為標志的極端的文化專制的舉措并沒有宣布稷下學的終結。因‘不中用'導致的冷落和迫害,并未能摧毀稷下學繼承者的文化自信,他們仍頑強堅持自己的學術風格。”[7]田君先生也曾指出:“作為秦朝官學代表的博士,職掌官方所藏儒學典籍以及諸子百家語的研習、整理與教授,尤其在秦朝制度建設方面,儒學有著廣泛的影響。 秦始皇焚書并沒有阻斷儒家經典流傳,在這一傳承過程中,秦代儒學還呈現出官學與私學并存的局面。”[8]可以看出,盡管儒家學說及其經典文獻在秦朝命運多舛,但可以肯定的是,儒家思想對秦朝政權和社會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消除,儒家經典的傳承也沒有完全斷絕,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士人也以自己的方式頑強生存下來。 因此,在秦代的文化荒漠之中,仍然可以看到一抹抹綠色。 對此,當代學人李景明先生認為可以從不同層面來簡單認識:“從空間范圍看,經學活動遍及朝野;從時間跨度看,貫串秦朝始終;從經學家看,居處不同,學派各異,或專一經,或通六藝;從經典看,六經都有人研習傳授;從經學作用看,經學成為統治思想體系構成因素、議政工具,干預了秦政治與現實生活。”[9]就《春秋》經傳來說,戰國以來已經非常成熟的傳承方式和具有強烈使命感的學人也給后人留下了來日復興的火種。
概而言之,盡管出現過“焚書坑儒”這樣的事件,并推行“以吏為師”等相關舉措,秦代的國家政策并沒有完全阻斷儒家經學。 《春秋》經傳之學在這一時期的延續,既源自戰國以降學術傳承的歷史慣性,也有賴于儒家后學與孔門后裔的文化自覺,以下試分別論之。
2 秦代諸儒與《春秋》經傳之存續
由于秦祚短暫,這一時期的《春秋》經傳之學,實際上以能延續不絕為最大成果。 秦代熟稔《春秋》經傳并能將其保存、運用和傳播者,能留下姓名事跡的甚少,其中對后世貢獻最大者當是張蒼。 作為荀子晚年的入門弟子,張蒼在秦統一天下之后才進入生命中最具活力的階段。 《史記·張丞相列傳》云:“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好書律歷。 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有罪,亡歸。”裴骃《集解》引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 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 或曰四方文書。”司馬貞《索隱》亦謂:“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 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為周柱下史。 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 方書者,如淳以為方板,謂小事書之于方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 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是也。”[10]而《史記》老子本傳云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11]由御史、柱下史、守藏室之史的職掌來看,三者確實非常接近,歷代學者也贊同柱下史即御史之說,然董平玉女史認為老子之“守藏室之史”與張蒼之“柱下史”職責存在差異,兩者當是前后相繼的關系,是周秦之間官制衍變的結果,[12]其說也可參考。 張蒼擔任掌管圖書文獻的御史一職,顯然與其學識淵博密切相關,至于是不是有其同門學兄李斯的作用,則難以考證。 張蒼掌管的圖書不在焚燒之列,而本人又長于《春秋》經傳,故《左傳》《國語》等書在秦時得以保存當不是問題。
秦時長于《春秋》經傳之學的儒生,還有名浮丘伯者。 《漢書·楚元王傳》載:“楚元王交,字游,髙祖同父少弟也。 好書,多材藝。 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 伯者,孫卿門人也。 及秦焚書,各別去。”[13]浮丘伯,楚人,曾與李斯一起在荀子門下求學,但二人志趣差別極大,《鹽鐵論·毀學》篇載桑弘羊之言曰:“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切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丘子不免于甕牖蒿廬,如潦歲之蛙,口非不眾也,卒死于溝壑而已。”又載文學之言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睹其罹不測之禍也。 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于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14]對于桑弘羊和賢良文學都提到的“包丘子”,陳立《公羊義疏》卷九云:“秦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 而《鹽鐵論》作‘包丘子',蓋古音通也。 按‘浮'‘包'古韻同部,故從‘孚'從‘包'字,經多相通。”[15]《四庫全書考證》卷二十亦云:“古浮、包字同。 《公羊傳》‘盟于包來',《左氏》作‘浮來'。浮丘伯見《漢·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丘子',是浮丘公與上所引苞丘先生同為一人也。”[16]則浮丘伯、包丘子、苞丘先生是同一人,歷代均無異議。 從《鹽鐵論》所載可知,李斯雖然問學于荀子,但志在仕途,故辭荀子而入秦,一度位極人臣,然終未能善終;而浮丘伯則安貧樂道,講學收徒,繼承荀子之學,并得以善終,且影響及于漢代。 上引《漢書·楚元王傳》提到浮丘伯是《魯詩》一系的重要傳承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五“詩序二卷”曾概述其師承系統云:“蓋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 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 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為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17]由此可見,荀子在《春秋》經傳與《詩經》學的傳承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只此二者,皮錫瑞還指出大小戴《禮》與《易》等經的傳承也離不開荀子,“是荀子能傳《易》《詩》《禮》《樂》《春秋》,漢初傳其學者極盛。”因此其“傳經之功甚巨”。[18]荀子是儒家學說與儒家經典傳承中最關鍵的人物之一,特別是放在戰國末期、秦亡漢興的大背景之下來看的話,荀子的地位與貢獻尤其顯得重要。 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沒有荀子,漢代以后的經學會是什么面貌實在難以想象。 基于此,后世學者糾結于其學派歸屬就顯得沒有意義了。
在經學史上,浮丘伯除了是《詩經》的重要傳承人之外,對《春秋》經傳之學的傳承也是貢獻卓著。 上引皮錫瑞之文已經提到《儒林傳》有“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之說,而申公正是浮丘伯的學生,可見《榖梁傳》也是由荀子通過浮丘伯傳入漢代的。 對此傳承關系,閻若璩在《尚書古文疏證》卷四曾提出懷疑:“《疏》稱荀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 申傳江見《儒林傳》,申受于荀尚不足信。 《楚元王傳》:‘少時與申公等受《詩》浮丘伯。'伯,荀卿門人。 申于《詩》為再傳,何獨于《春秋》而親受業乎? 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余,計其生當在秦初并天下日,荀卒已久。 疏凡此等俱訛謬不勝辯,聊發憤一道,以為舉隅云爾。”[19]閻若璩提出的疑問在于,若據孔疏的說法,《詩經》的傳承是荀子經浮丘伯至申公,而《春秋》經傳的傳承則是申公“親受業”于荀子,但荀子去世時申公還未出生,故孔疏所稱“荀卿傳魯人申公”之說“訛謬不勝辯”。 楊士勛《榖梁疏》也說《榖梁傳》傳自子夏,后榖梁氏傳于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江公。 孔、楊二疏所說荀子傳《榖梁傳》于申公,中間當遺漏了浮丘伯這一環節。
閻若璩之疑問是針對孔疏而發,而若將上引各種資料綜合分析,便可知孔、楊二疏之失。 在《榖梁傳》傳承中,荀子肯定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浮丘伯無疑也有貢獻。 吳濤先生根據漢初陸賈、賈誼等人著作引用《榖梁傳》以及《榖梁傳》自身引書的情況推測《榖梁傳》出于荀子之門,又根據浮丘伯本人治學風格推測《榖梁傳》作者很可能就是浮丘伯。[20]其說雖難稱定論,但肯定荀子、浮丘伯在《榖梁傳》傳承中的作用,這是沒有問題的。 荀子博通諸經,又不拘于一家、一經之學,其門徒如李斯、韓非、張蒼、浮丘伯等等都體現了這一風格,對秦漢以后經學發展居功甚偉。
3 孔鮒與《春秋》經傳之傳承
在秦代《春秋》經傳傳承序列中,孔鮒也是不得不提的人物。 關于其本人的生平經歷,《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21]《孔叢子·獨治》說:“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22]孔鮒為孔子八世孫,其父孔慎(順)曾任魏國相。 《史記·儒林列傳》又云:“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 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23]秦始皇焚書后,孔鮒“隱居嵩陽,授弟子常百余人”。[24]陳勝首倡反秦,孔鮒受邀為博士,后死于軍中。 孔鮒其人的治學經歷、言行事跡,主要保存在《孔叢子》一書中。 盡管學界對《孔叢子》的真偽與編纂時代尚有爭議,但其中所載孔鮒之史料大體可信。 《孔叢子·獨治》篇載其治學經歷,云其“生于戰國之世,長于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 在他看來,“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基于此種考慮,“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 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25]
孔鮒之學以家族相傳為主,金朝時衍圣公孔元措所撰《孔氏祖庭廣記》卷一《世次》說“子魚好習經史,該通六藝,秦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召為魯國文通君,拜為少傅。”[26]若此說可信,則孔鮒在秦始皇時期已經應召出仕。 那么,上引《孔叢子》所說孔鮒“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以“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為人生理想,當是在秦始皇焚書之后。 但陳勝舉兵反秦時,孔鮒沒能拒絕陳勝的邀請,在陳余的勸說下出任博士,《孔叢子·獨治》載此事云:“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 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 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咨度焉。”[27]據《孔叢子》所言,孔鮒擔任陳勝博士期間,曾多次與陳勝談論治國之道,深得陳勝賞識。 只是局勢變化太快,孔鮒未能幸免于難,殊為憾事。 對于他改變治學收徒之志、轉而輔佐陳勝以致死于戰亂之事,《史記·儒林列傳》曾評價說:“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28]其論可謂一語中的。 孔鮒對秦朝焚書黜儒政策非常不滿,故選擇投奔陳勝,希望儒學再興,也顯示出作為孔門傳人的責任感。 除此之外,對于秦始皇的焚書舉措,孔鮒還曾采取藏書的方式保存了部分儒家經典文獻,《孔叢子·獨治》篇載其事云:
陳余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為有用之學。 知吾者、惟友。 秦非吾友,吾何危哉? 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 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29]
據《秦始皇本紀》,秦始皇采納李斯的建議,焚毀民間所藏經史諸子之書,但也有少數知識分子冒險藏匿,孔鮒就是一個例子。 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卷一《世次》也說“鮒知秦將滅,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安于祖堂舊壁中。”[30]至于有哪些經典藏于壁中,歷來說法不一,《漢書·藝文志》提到“《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可見數量頗多。[31]這與孔鮒的身份也相符合。
孔鮒藏書除了《尚書》《禮記》《論語》《孝經》之外,有沒有《春秋》經傳? 《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均未明說,唯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五上敘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32]筆者以為,孔氏家人世代相傳之書,《詩》《書》《禮》《樂》《易》《春秋》皆應在內,孔鮒自幼所學,也當以六藝為主。 《孔叢子·論書》篇云:“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圣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33]以理推之,其藏書也當涵蓋六藝之學。
孔鮒自云其曾讀過《春秋》,除上引《論書》篇之言外,《孔叢子·公孫龍》篇也有一個很好的例證:
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 《春秋》記六鶂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鶂。 鶂猶馬也,六猶白也。 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 色以名別,內由外顯。 謂之白馬,名實當矣。[34]
孔鮒所說《春秋》六鶂退飛之事,載僖公十六年《春秋》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鹢退飛,過宋都。”[35]孔鮒引此與公孫龍之白馬非馬說進行辯論,足見其學養之深。 除了《春秋》經文外,在《孔叢子》中也能看到運用《左傳》《公羊傳》的痕跡。 如《記義》篇載子貢之言說:“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 盡置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36]據《左傳》,孫文子即衛卿孫林父,因得罪于衛殤公而以其封地叛晉。 《左傳·成公十四年》說衛定公死時之事云:“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置諸戚,而甚善晉大夫。”[37]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孔叢子》所述來自《左傳》。 再如《記問》篇載“西狩獲麟”事云: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鋤商樵于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 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 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 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 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 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38]
“西狩獲麟”之事,初見于哀公十四年之《春秋》經。 《左傳》釋此事說:“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后取之。”[39]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左傳》述此事較為簡略,其中“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的說法與《記問》中“子鋤商樵于野而獲獸焉”一句相似。 《記問》接下來的說法則與《公羊傳》比較接近:“麟者,仁獸也。 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 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40]《公羊傳》至遲在戰國中期便已經出現,早期之傳承以師徒之間口耳相傳為主要形式,到漢景帝時始“著于竹帛”,趙伯雄先生言之甚詳,[41]此處不贅。 《記問》關于麟獸“有麇而肉角”的形象描述,以及孔子見此而哭泣并感嘆“吾道窮矣”的描述,都與《公羊傳》有明顯的引述關系。 由此可見,《記問》篇關于“西狩獲麟”的言論,當是綜合采用了《左傳》和《公羊傳》的敘述,而以《公羊傳》為主闡發己意。
除了利用《左傳》《公羊傳》之外,《孔叢子》也曾引用《國語》中的事例,而《國語》本身便與《左傳》密切相關,其傳承與流布也是早期《春秋》學的組成部分。 《孔叢子·記義》載魯大夫公父文伯死后,有兩妾欲陪葬,其母堅決反對,并闡述了自己的理由:“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于魯,退而去。 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 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 若此于長者薄,于婦人厚也。”[42]《國語·魯語下》述其母之言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 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 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搯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 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聽說此事后,對公父文伯之母給予高度評價:“公父氏之婦智也夫! 欲明其子之令德。”[43]《孔叢子》與《國語》盡管具體言辭有所不同,但有相承關系還是非常明確的。
還要特別指出的是,《孔叢子》書中不僅有引用《國語》的例子,還出現了最早對《國語》史事的評論分析。 《孔叢子·答問》篇云: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余信圣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 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亂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 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 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 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 故使予并疑于圣人也。”博士曰:“不然也。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 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后世。 善以為式,惡以為戒。 廢而不記,史失其官。 故凡若晉侯驪姬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 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 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圣人之后也。 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44]
如果《孔叢子》的基本內容確定形成于孔鮒時期,則這段記載是目前所見文獻典籍中“《國語》”書名的最早記錄。 陳勝在戰爭時期還能讀《國語》,也從另一個側面驗證了《國語》為興衰成敗提供鑒戒的功能。 陳勝所讀之申生故事,見《晉語一》。 陳勝讀《國語》所載晉獻公寵幸驪姬而迫使太子申生自殺、改立太子之事,見書中有“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之語,認為夫妻夜話這樣的隱私,外人無從得知,應該是“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由此出發,陳勝認為所謂典籍所載“圣人”“圣賢之道”不可盡信。孔鮒則從史官職責和史書編纂角度進行了解釋,認為“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并打消了陳勝的疑慮。 可以看出,《孔叢子》這段解說已經不僅僅運用《國語》所載史事闡述自己的思想主張了,而是以“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這一記載出發,探討了周代的史官設置與職能,以及史書的教化和鑒戒作用。 可以認為,《孔叢子》此論是有據可查的《國語》學史的開端。
4 余論
秦代的文化政策造成大量先秦典籍散佚不存,很多知識精英湮沒無聞。 受這一大環境制約,戰國時期非常活躍的儒家經學與諸子之學此時基本處于隱忍或蟄伏狀態,但知識精英們傳承文化之心未泯,遇到稍微合適一點的土壤,孕育已久的種子便會破土萌發,魯壁藏書之舉便寄托著他們不滅的希望。 而孔鮒放棄隱居山林,以孔氏之禮器往歸陳勝,以博士之職為其宣講儒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本是滿懷期待,然時局變換,不久便身死軍中,剛剛燃起的希望之火頃刻之間便被傾盆之水澆滅。 即便如此,直到楚漢戰爭之時,仍有不少儒生堅守理想,“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45]他們所等待的,只是一個機會。 斗轉星移之間,劉邦建立了西漢帝國,天下重歸一統。 盡管劉邦不好儒家,但畢竟不能在馬上治理天下,于是“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46]困境迷茫之中的百家之學迎來了轉機。儒家學說盡管沒能占據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但形勢已經大有改觀,“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 就連劉邦本人也意識到叔孫通所言“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之理,用其制禮,然后“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47]在此背景之下,漢初的經學得以恢復與發展。
在戰國末年經秦至漢初的《春秋》學存續過程中,張蒼無疑是繼荀子之后最重要的傳承人之一。 據前文所引《史記·張丞相列傳》所述,張蒼在秦時曾任柱下史,掌管“圖書計籍”,后有罪亡歸。 到劉項反秦戰爭時,張蒼跟隨劉邦入武關。劉邦稱帝建漢后,張蒼被封為北平侯,又曾任計相、淮南王相、御史大夫等職,是西漢初期的朝廷重臣。[48]張蒼學識淵博,于儒家經典、黃老之術、天文歷算等皆有成就。 對于張蒼在《左傳》學方面的貢獻,可以大略包括兩方面。 一是獻書,《說文解字》卷十五上敘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49]劉師培《左氏學行于西漢考》一文以為:“此西漢秘府有《春秋》古經及《左傳》之始,蓋在高帝之時。 故高祖之詔引其文,叔孫通之倫并才其說以制禮,下迨文帝詔書、武帝制令、哀帝封冊,咸述其文。 漢廷有司,亦持以議禮。 此即張蒼所獻之書,亦即劉歆所謂‘《左氏春秋》,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者'也。 及成帝之世,陳發秘藏,以考學官所傳經,欲立三傳博士,胥君安以《左傳》不祖圣人相駁,然成封孔子后,仍推跡古文,以《左氏》相明。 此均歆、莽以前《左氏》 行于漢廷之征也。”[50]漢高祖、叔孫通等人言論中所引《左傳》之文,劉師培也有說明,可以參考。 二是著述,《十二諸侯年表序》在歷數孟子、荀子、公孫固和韓非之后有一句簡單的描述:“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51]《漢書·藝文志》有《張氏微》十篇,列于《春秋》家,有學者認為即張蒼的作品。 又有《張蒼》十六篇,列在道家類,當即司馬遷所謂“歷譜五德”之作,實際也與《春秋》經傳有密切關系。
與張蒼有學術淵源的賈誼,是漢初治《春秋》經傳之學的另一代表人物。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言“蒼傳洛陽賈誼”,[52]后世學者基本認同此說。 然《史記》本傳說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又說:“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 文帝召以為博士。”[53]《漢書》本傳沿襲《史記》,都沒提到賈誼師事張蒼,而是曾在吳廷尉(吳公)門下,且其入仕途也是得到吳廷尉的提攜與引薦。 又,趙伯雄先生曾指出,張蒼和賈誼二人在漢為水德或土德問題上意見并不一致,“倘張蒼與賈誼真有師生之誼,似乎主張不應如此相左。”[54]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 《漢書·儒林傳》說“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 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55]未把張蒼和賈誼列為師承關系,而是并列敘述。 《史記》本傳又云:“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征為廷尉。”[56]則吳公之學傳自李斯,而李斯與張蒼同出于荀子之門,可見賈誼之師承雖然不是直接來自張蒼,其學術淵源仍出荀子。《漢書·儒林傳》 又云賈誼“為《左氏傳》 訓故”,[57]則是《左傳》學史上較早的訓釋之作,可惜其著不存,無法見其詳情。
簡而言之,戰國到秦朝時期的經學傳授,主要存在兩條線索。 一條是儒家各派之師承授受,如《七錄》《經典釋文·敘錄》所載《左傳》傳承系統。 另一條則是孔子與歷代孔氏之家學傳承,由孔子始經子思乃至于孔鮒,對于儒家經典文獻的保存以及經學的傳承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春秋》經傳之學,其源肇于孔子,在戰國時期出現了分化,但各派之間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共同開發”先輩們流傳下來的文化遺產,成為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各家皆可利用的思想資源。 秦代的《春秋》經傳之學雖然受到文化政策的極大影響,但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張蒼、浮丘伯、孔鮒等人均為傳承與傳播《春秋》經傳之學做出了重要貢獻,并為代秦而立的漢代經學復興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