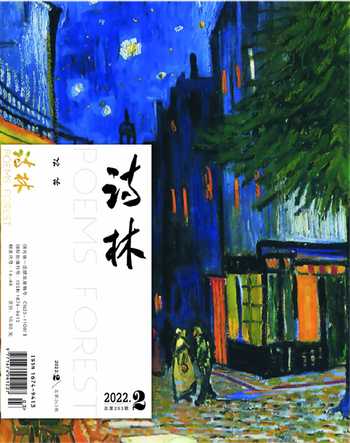楊川慶:喚醒他找到的詞語的靈魂
三姑石
走進一首詩,就如走進一個熟悉或陌生的地方,而促使你走進的,就是一首詩的力量。
楊川慶的詩《綏化》,于我同時營造了熟悉與陌生兩種狀況。這個地方所呈現的力量似抱緊了我的身體,讓我有大熟悉的開闊,也有小陌生的吸引。我不能拒絕這里景色的魅力,不能不駐足欣賞,不能不讓舌頭獲取管轄的力量。
詩中有一處堪稱金句——
故鄉在胃里,這種感覺仿佛天賜
我們對于喂養我們童年、少年或者中年艱苦生活的故鄉,不管走多遠多久,都會在心中為其留有最溫柔的部分。而這一部分仿佛休眠的火山,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被喚醒,就會呈噴發之勢。
詩人借胃設喻,很容易就找到了讀者的共鳴點,喚醒了我們熱愛家鄉的胃口,也喚起了讀詩的興趣。
我們生于斯、長于斯,有時不免有麻木感,甚至她的地名都因為太熟悉,而被我們忽略了其間的粗獷和唯美的寓意,又何談她的那些“吉祥”美麗的懷想。
詩人起句就喚醒了沉睡的我們——
黑土之上,一個吉祥的地名
是的,吉祥而樸素,樸素而親切
詩人猶如有經驗的導引者,把讀者變成他的同謀,與詩中他所要主導的聲音、所要呈現的另一個世界牢牢地捆綁在一起——
還有話語,猶如黑土,一點都不空洞
還有生活,更靠近植物,離汽車的喇叭
一步之遙
身邊的人,他們的笑容,讓我想起葵花
好看,籽粒的芳香在召喚,讓人愛不釋
手
詩人以有節奏的預期和流動推進一首詩,在和讀者反復確認:這就是我們可愛的家鄉——家鄉的聲名美、家鄉的話語親、家鄉的生活近、家鄉的人們好。
簡潔而飽滿的語句,恰如秋天金黃的老玉米,光鮮醉人。可以說,詩人是高高地舉起了一瓶甜美的汁液,讓我們的胃咕咕地叫起來。
詩人的高妙還在于,絕不就此罷筆。
二人轉的唱腔浸入骨髓,如此自然
剪紙的夢想低微,像成熟的糧食
糧食,真實而炫目,鋪滿原野
他用二人轉、剪紙和糧食進一步調整我們的胃口,反復強調它們的功用,最后歸結到“糧食,真實而炫目,鋪滿原野”。我們好像瞬間就興奮起來了,以致于不能自持,非大快朵頤不行,非一飲而盡不痛快,非放聲歌唱不足以表達心中的豪情。
讀到這里,我們只是看見詩人在用心用情用力表達對家鄉深沉磅礴的情感,似乎感覺還有些壓抑,有些透不過氣來,似還差一口氣沒有吐出來。一個成熟的詩人絕不會給讀者這樣的瘀結——
她們氣息獨特,喂養平凡的胃口
故鄉在胃里,這種感覺仿佛天賜
是的,天賜黑土,天賜黑土之上的綏化
這首詩的高潮因此到來。詩人仿佛斟滿了酒,舉起了酒杯,在黎明,在月夜,在夢中,仰天高歌對家鄉的贊美,對“天賜黑土之上的綏化”的無限祝福。
而這贊美,這祝福,停不下來。
謝有順認為,作家“寫作根據地”不一定是偏遠蠻荒的山坳,而更是凝結作家記憶和情感的地方。無疑,楊川慶已經把工作地綏化作為他寫作精神扎根的地方,他所熟悉的地域、物態、人情,源源不斷地為他提供寫作的真材實料。
同時,這首詩也是時代之詩,深深地鐫刻著歲月的痕跡。詩人在此間鮮明地亮出了“精神還鄉”的憑借與依靠。在社會轉型期凸顯的矛盾與沖突中,在人們對城市文明追逐的喧嘩與騷動、分裂與扭曲中,詩人以其對鄉風與農耕的歌頌與吟詠,達成了對承載純樸與自然、自由與美好的精神棲居地的最終皈依。
可以說,在綏化這個地方,楊川慶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陌生化表達,這種表達喚醒了他找到的詞語的靈魂;而本已屬于這里的我們,又一次發現著,并在詩中驚異地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