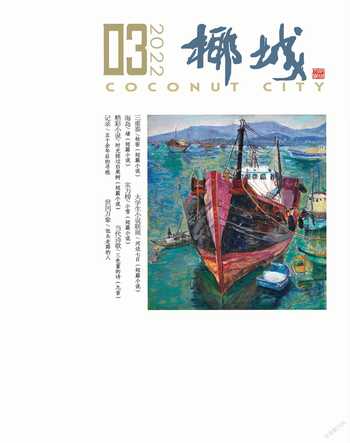符號的天差與地別
2022-04-04 12:16:45蕭然
椰城
2022年3期
蕭然
文字成為供人觀看的文本以后,作者本人的闡釋便成為眾多闡釋中的一種。作者的闡釋,甚至已失去對文本的掌控。這種關系好比里爾克《圣母憐子像》一詩中所說的:“母親,你再也生不出我來。”懷中原本小的存在,所忍受的巨苦,已遠超你的理解。作者與作品的關系,就好比過時但宅心仁厚的母親,費解地望著自己的誕物。《河邊七日》是布滿隱喻的文本,寫創作談,我亦為第一次,作為作者,我只能頗有信心地指出刻意布下的隱喻。那些不自覺生成的部分,或那些不可言說但真切地被稿紙上排列的文字隱藏著的部分,永遠迎候別樣的闡釋。
早在2015年,我腦中便有這篇小說的雛形。那時只想寫一篇人與花的故事,人愛上一朵花,并堅信它有所回應,在樹下對它講述自己的一生,直至它枯萎。這篇故事的要義在于物種之間壽命的天差,主體則是男人的獨白。后來,我知曉這種手法叫作意識流。此前,我是個缺乏文學寫作訓練的孩子,高中學數學競賽,本科學經管,只顧悶頭寫詩,發現這種手法早被用過后(意識流鼻祖迪雅丹的〈月桂樹已砍盡〉甚至同樣是與植物有關的意象)興致大損,終究是沒有寫出。這番失落好比幼時發現兩數和差與平方的關系,老師卻告知你:這是平方差公式,早已提出。
直至2019年,我才打定主意寫下這篇小說。此時我傾向黃鐘大呂般的文字,于是砍去男人的獨白與世俗生活,寫出僅有兩千字的寓言式故事。由于對一朵花貪圖,他譫妄地進入重復,第七日的他總算劃走第一日他的筏子。……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幼兒園(2021年6期)2021-07-28 07:42:14
小學生學習指導(低年級)(2019年11期)2019-11-25 07:31:48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小學生導刊(2017年13期)2017-06-15 20:29:38
哈爾濱師范大學自然科學學報(2015年1期)2015-04-19 06:55:26
天津科技大學學報(2015年4期)2015-04-16 04:55:11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