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情感?如何認知?
鄧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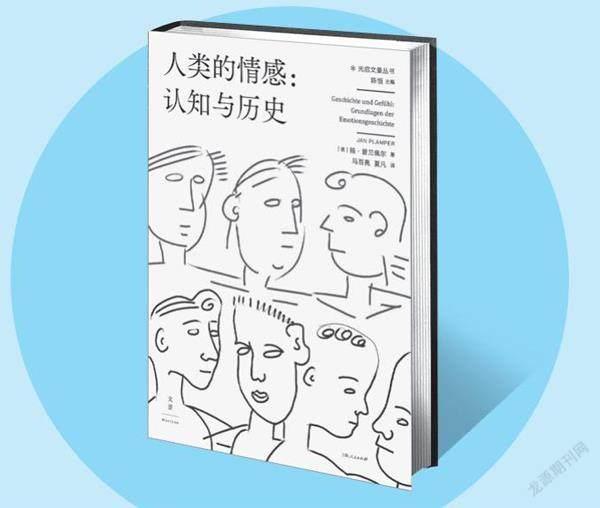
人類是情感的動物。對人類而言,情感無比重要,但人類對情感問題的認知,從來就沒有統一過。德國歷史學家普蘭佩爾在其著作《人類的情感:認知與歷史》的“導言”中就提到,在西方,從古希臘時代開始,哲學家們就開始思考“情感是什么”這樣的問題,從哲學、醫學、倫理學、文學、美學到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神經科學,人類幾乎動用了所有的知識領域來思考情感問題,試圖找到人類情感的本質。但是,關于人類情感的研究,并不容易找到確定答案。
在情感研究中,歷來存在著普遍主義和建構主義的二元對立。普蘭佩爾在這本著作的第二、第三章,分別介紹了這兩種立場的情感研究。普遍主義以生命科學為主,認為人類的情感固定不變,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涵蓋了所有物種,超越了時間,它既是生物學概念,也是生理學概念,它是本質主義的,與生俱來的;而建構主義以人類學為主,認為人類的情感是靈活的,反本質主義的,反決定論的,社會建構主義的,具有文化的相對性和獨特性。
在建構主義看來,從古至今,人類的情感是變動不居的。中國明代戲劇家湯顯祖曾經記錄過一樁逸事,“婁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詞,未有所適。酷嗜《牡丹亭》傳奇,蠅頭細字,批注其側。幽思苦韻,有痛于本詞者。十七惋憤而終”,他后來還為此寫了悼亡詩《哭婁江女子二首》以表哀思。湯顯祖的《牡丹亭》講述了杜麗娘為情而死又為情而生的傳奇故事。而現實生活中竟然也有閨閣女子在讀了《牡丹亭》之后,心有戚戚焉而郁郁而終。這件事放在今天來看,顯然是天方夜譚,但在湯顯祖的時代卻并不為怪。漢學家史華羅在《中國歷史中的情感文化》中就認為,明朝后期是一個“情感至上”的時代。而如今,我們則處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稱之為后現代主義的時代,其特征之一就是“情感的消逝”—“主體已經從一切情感中解放出來了”“今天一切的情感都是‘非個人的’,是飄忽忽而無所主的”。讀者因為與劇中人共情而殞命,這樣的事在當代再也不可能發生了。
從“情感至上”到“情感的消逝”,隨著社會歷史變遷,人類的情感狀態在發生著變化,不同時代對情感有著不同態度。大致說來,從前現代到現代再到后現代,人類經歷了對情感從不重視到重視又到不重視的變化。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就認為:歐洲在十八世紀后半葉之前,無論宗教還是哲學,大多否定感性(感覺/感情)的價值;但到了十八世紀后半葉,隨著工商業的興隆,自然科學的發展,現代哲學開始重視情感的價值,以情感為標志的文學也隨之興盛起來。在這個“情感轉向”的過程中,新型的經濟倫理起著關鍵作用,比如亞當·斯密倡導的“同情”。斯密所說的“同情”不是宗教的憐憫、慈悲,而是設身處地代入他人的“想象力”。“想象力”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個人主義,其根源是現代的市場經濟。“同情”是通過破壞前現代的共同體并高揚個人主義而產生的。因此,“同情”是一種全新的感情。由于高揚“同情”的價值,感情本身也開始被重新估價。
相比于文學和哲學,史學對社會情感變化的反應可以說不無滯后。強調史料的嚴格考訂和寫作中以可信的事實為據的蘭克史學幾乎籠罩了整個十九世紀的西方史學界,無怪乎美國情感史專家芭芭拉·羅森宛恩抱怨說,“作為一個學術分支,歷史學最早研究政治的變遷。盡管社會史和文化史已經開展了有一代之久,但歷史研究仍然專注硬邦邦的、理性的東西。對于歷史研究而言,情感是無關重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這種狀況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法國年鑒學派的“心態史”研究崛起后,才得以改變。實際上,普蘭佩爾在其著作的第一章追溯西方情感史的歷史時,就把它的開創者定為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費弗爾呼吁分析不同時期文字和圖像中的情感表達。這就意味著我們今天所說的情感的概念史,它描述了情感這一概念的意義在數十年乃至數百年間的變化。費弗爾是第一個勾勒出這個研究領域輪廓的人”。
可以說,西方史學領域同樣經歷了一場“情感轉向”,而普蘭佩爾自己,則一直是史學“情感轉向論”的重要推手。二○一○年,他通過《歷史和理論》雜志采訪情感史三位先驅人物威廉·雷迪、芭芭拉·羅森宛恩和彼得·斯特恩斯時,詢問他們歷史研究是否已經出現了某種“情感轉向”,結果大家都作出了肯定的答復。在追溯西方史學“情感轉向”的發生時,普蘭佩爾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認為它是“9·11”事件推動的結果。在他看來,西方史學“情感轉向”的發生既與生命科學的興起有關,也與“9·11”事件對史學的語言學模式的沖擊有關。在“9·11”之前,歷史學流行的是話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但是在“9·11”發生之后,人們開始追問,后結構主義歷史學能夠解釋恐怖分子操縱載滿乘客的飛機撞毀摩天大樓這種赤裸裸的暴力嗎?歷史學的話語分析能夠解釋極端主義的狂熱和仇恨嗎?正是在這種追問下,歷史學轉向了對人類情感的研究。
歷史學又是如何研究情感的呢?它主要研究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歷史的情感性,即情感在歷史學中的地位以及情感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一是情感的歷史性,即情感的歷史變化以及情感在特定社會歷史中的表現。與關注人類情感多樣性的情感人類學、關注人類情感制度性的情感社會學不同,情感歷史學(即情感史)關注人類情感的變化性。
與一般情感史理論著作不同,普蘭佩爾的這本《人類的情感:認知與歷史》有一個顯著優點。它雖然是站在情感史的立場上,但是對情感普遍主義持一種比較開放的借鑒態度,其用意在于建立“一種超越普遍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二分法的情感研究”。與很多情感建構主義者對情感普遍主義的漠視和敵意不同,普蘭佩爾在書中花了很大篇幅來介紹當代“生命科學”的普遍主義情感觀。比如,他在書中談到了當代的神經政治學。對這方面了解不多的讀者也許很難意識到,當代社會的政治已經下沉到了情感和神經的維度。簡單說,意識形態不再“曉之以理”,而是“動之以情”,在你還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就已經發揮作用了。這就是神經政治學為我們描繪的當代政治場景。因此,當普蘭佩爾把《帝國》的作者哈特和奈格里也歸到生命科學和情感普遍主義里來介紹時,讀者大可不必驚訝。因為后者的確相信“情感是抵抗的源泉”,“我們要不斷地把行動和激情之間的關系、理性和情感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問題。我們事先不知道身體能做什么、心智能想什么、情感能做什么。它需要我們對這些尚不可知的力量進行探索”。
當然,普蘭佩爾也意識到了,目前西方的情感史研究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限制”:“情感史探討的基本上是歐洲和北美的歷史”,在對情感史進行理論概述時,“我們還需要考慮到非西方世界對于情感的思考”,但他本人對這方面的關注顯然不夠,甚至沒有提到史華羅對中國情感歷史的研究。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章“情感史的視角”部分,普蘭佩爾展望了未來情感史研究各種可能領域,其中尤其談到了歷史學家的情感問題。他在書中對人類學家們帶有個人情感色彩的田野調查和民族志寫作(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郁的熱帶》無疑是這方面的典范)極其推崇:“如果歷史研究能夠像人類學一樣多一些研究者的反思,這將是非常有益的。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不是來自真空,他們的研究也不是‘不帶任何感情’。為什么歷史學家不像人類學家寫作田野調查日記那樣記錄自己的感受呢?”對歐美的史學家們來說,蘭克史學雖然早已是過去式,但其嚴肅枯燥的幽靈似乎仍然在糾纏他們的史筆。在十九世紀后期,西方年輕的歷史學家尚能接受“共情”方法的訓練,以期在歷史編撰者與歷史參與者之間建立“感情之橋”。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歷史寫作中越來越多的客觀性逐漸取代了共情觀念,共情不再是歷史訓練的一部分。而到了二十世紀,雖然情感史研究在西方史學界方興未艾,但歷史學家的情感問題早已無人問津了。但是,如果對中國的史學界多少有所了解的話,普蘭佩爾或許會驚奇地發現,中國史學可以勾勒出一個情感傳統來,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史學家陳寅恪所提出的,在歷史研究中對古人應該“有了解之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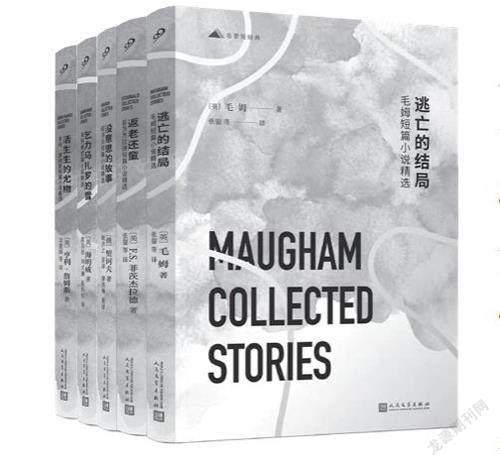
[美] 亨利·詹姆斯 等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1月版
短篇小說,讀這五個人就夠了: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說”這一文學體裁的開創者之一;契訶夫,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之一,名副其實的短篇小說之王;菲茨杰拉德,張愛玲最推崇的美國作家,《了不起的蓋茨比》奠定了他在現代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被嚴重低估的短篇小說圣手;海明威,極簡主義短篇小說之父;毛姆,以《月亮和六便士》聞名于世,也是技藝爐火純青的短篇巨匠。
《活生生的尤物: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說精選》《沒意思的故事:契訶夫短篇小說精選》《返老還童: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說精選》《乞力馬扎羅的雪:海明威短篇小說精選》《逃亡的結局:毛姆短篇小說精選》……這里的每一篇都展示了這些作家在短篇小說創作領域的非凡創造力,是進入他們的文學宇宙的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