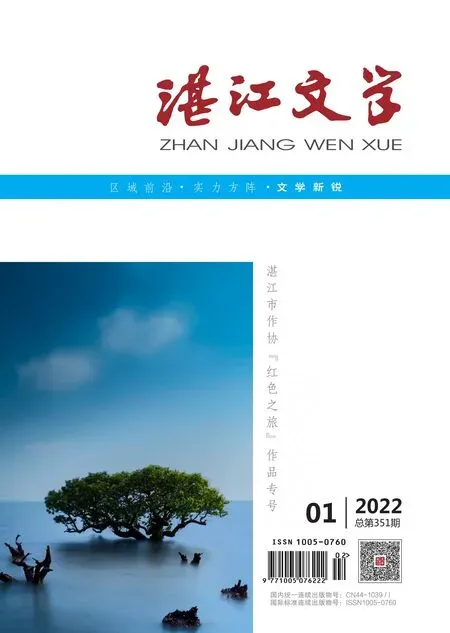文秀嶺的秋
◎ 周有德
十月初二,辛丑年秋天最盡頭的一天。
老祖宗創(chuàng)造的節(jié)氣該是踏遍青山的巧遇吧,雖沒了空氣發(fā)酵一樣的納悶,也沒了頭發(fā)梢燃燒一樣的焦慮,但雙腳呢,還踏在又明又滅的炎熱里。
那火的星星就抖動著小尾巴,直往文秀嶺的腦門上撞。嘭嘭,嘭嘭——,一撥撥正確的思想與不太正確的想象,夾雜著一些歪的事、斜的物,卷入時間螺旋柱子的慣性里,急劇地旋轉(zhuǎn)。
那墨綠的意識流就膨脹起來,發(fā)散而去,突破天的界線了,繼而洶涌,繼而澎湃,又一葉輕盈,搖啊搖啊!
誰能說得清、道得明呢?在這南方的南方,在沒有季節(jié)之界的季節(jié)里。
文秀嶺依然如故,進(jìn)行著廣闊的有條不紊的光合反應(yīng)。一片隨風(fēng)起伏的葉子,就是一個能量無窮的反應(yīng)堆,瑣碎繁雜,但蜂巢格子一樣的程序一個都不能少,都微縮在枝椏里。
記得今年夏天第一次到文秀嶺,漫山遍野的荔枝紅了。那妃子笑,黑葉,桂味,糯米糍,白糖罌,披著掛著,將五月的枝頭壓彎了。
一抹輕輕的笑,從緊抿的小嘴里泌了出來,那乳白的心思怎能抵抗?就顫著抖著打翻了一只糖罐子。
我急切切地剝開一個,往嘴里塞,太成熟了,甜的盡頭就是酸,更是醉人的味道。滿樹的妃子笑,笑了。
這一樹是桂味,三個一串,四個一簇,掛在高高的枝丫上,掩在綠葉里,又大又紅又豐盛。我拉開架勢,往上一跳,卻跌進(jìn)了一個落葉與牧草掩護(hù)的坑。
誰稀罕你這狼狽的樣子呢?一個鮮艷的花裙子的老太太,一邊推輪椅,一邊拉開嗓門唱:
“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老翁呢呢喃喃,是說又到了文秀嶺?大步流星的日子雖被塵封在輪椅上,但還在山路上。
文秀嶺農(nóng)牧場的路很開闊,還不是鐵絲網(wǎng)限制了荔枝樹的肆意生長?可仍有一些枝條不受約束,從鐵絲網(wǎng)的上空伸出來,捧出飽滿的夢。可我一跳再跳,還是夠不上。
這可不是尋常的愛。
當(dāng)收獲與觀賞并重的季節(jié)可以拉得更長的時候,掃蕩式的采摘就是一種錯誤,甚至是一種掠奪。
又如人生的風(fēng)景,一步登天的奇峰式的完美,無論如何也比不上一村又一店的希望,那是攜手前行,一路芬芳。
所以,文秀嶺所有的果樹,包括荔枝、木瓜、檸檬、橙子、樹菠蘿,都不是為了單純意義上的采摘。而那肥美的黑山羊、獅頭鵝,也不是為了現(xiàn)代肉類加工廠的奉獻(xiàn)。
文秀嶺的初心是給黑山羊圈一塊土地,修建遮風(fēng)擋雨的羊舍,播種茂盛的牧草。而荔枝樹就是無拘無束的牧羊人,那伸展的枝條就是綠色的長鞭,盡情地?fù)]動,呵護(hù)著一片藍(lán)天。
這是何等的愜意!咩咩——,午后三點(diǎn)的牧草最嫩最香。咩咩——,新朋友、老朋友都到了。
甫哥愛交朋友。規(guī)整的平頭,透著山水的熱情與瀟灑,但說話輕聲細(xì)氣。
他是文秀嶺農(nóng)牧場的主人,1995年得了一場大病,無法堅持公安派出所所長繁重的工作,就到了父親承包經(jīng)營的文秀嶺。
年復(fù)一年,他成了地道的山民,血液都融進(jìn)了這山、這水、這貧瘠的砂礫與土地。
“山頂上有幾棵桂味,又大又甜,等著你們來摘呢。”
砂礫路的盡頭處,山坡緩緩,天高云淡,沒有圍欄的限制,更顯寬廣。遠(yuǎn)處還有一幅湖水,如白色的、細(xì)長的流水線。
那一棵一棵的荔枝樹,可是一葉一葉的輕舟了,托著金色的陽光,嫣然一笑,又嫣然一笑,在藍(lán)色的安逸的大海中蕩槳。
猛烈的山風(fēng)到哪里去了?我想起了一行文字:宇宙很謙虛,明明擁著一切,卻叫太空。
這就是文秀嶺的最高境界!
但斜坡拐彎處的一棵荔枝樹,卻被攔腰一斬,那是什么風(fēng)的橫行霸道?它生命的斷裂處又長出繁茂堅韌的枝條,掛滿紅色的果子,仍與枯枝擁抱在一起。
都說山高風(fēng)大,但文秀嶺山頂上的風(fēng)是徒有虛表的空殼,是欺軟怕硬的兩面人。你頂天立地,舉重若輕,萬物不絮于懷地瞪它一眼,它就繞道走了。而斜坡拐彎處的生長,正好撞上它壯膽的冷槍,就遭遇惡運(yùn)了。
看來自然界的規(guī)矩是可以修改的,或者根本上就沒有,而是人們憑空的想像,說風(fēng)不見風(fēng),說雨不下雨。而當(dāng)你高枕無憂的時候,風(fēng)雨卻來了。
我異想天開,將文秀嶺大的風(fēng)、小的風(fēng)、橫行霸道的風(fēng),以及沒有風(fēng)的風(fēng),全都扯下來,裝進(jìn)薄膜袋子里,連同那棵重獲生命的荔枝樹。
我提著沉甸甸的豐收,回到文秀嶺農(nóng)牧場的場部,那座兩面采光、三面透風(fēng)的吊腳樓式的簡易建筑。
甫哥的妻子捧來一大扎的鮮花,插在花瓶里,這吊腳樓立刻多了一份家的溫馨。
我問甫哥,承包文秀嶺的經(jīng)營權(quán)還有多少年?五年。可以突破這個界限嗎?比如說再延長經(jīng)營權(quán)三十年。甫哥不作聲。
我知道,這個問題應(yīng)該由他的兒子來回答,但年輕人正忙著給我們安排午餐。

文秀嶺早已是甫哥一家子的家了。
它和所有的山林地一樣,都是所有權(quán)、承包權(quán)、經(jīng)營權(quán)三分設(shè),但依然是一塊土地,孕育著無數(shù)生物的家,創(chuàng)造著色彩斑斕的世界。
甫哥說,文秀嶺的水電設(shè)施已經(jīng)完善,道路已經(jīng)暢通。你看,又來了一隊鄉(xiāng)村游的小汽車。你們要經(jīng)常來。
是的,我們又來了,還將“湛江市作家協(xié)會文學(xué)創(chuàng)作基地”的牌子掛上了。
吊腳樓什么時候改建呢?該是一座山雨欲來風(fēng)滿樓的現(xiàn)代氣派。
甫哥滿蘸美好的心愿,在一張白紙上飛龍走筆:
福氣,文秀嶺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