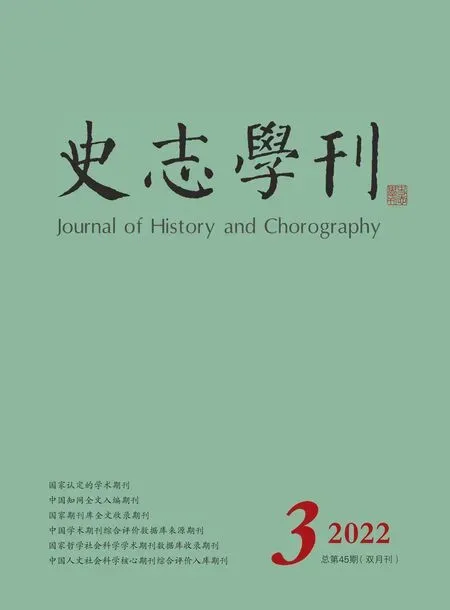全球史觀對絲綢之路研究的啟示
王永平 王思雯
(1.首都師范大學,北京 100089;2.清華大學,北京 100084)
全球史(global history)興起以后,對傳統歷史學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隨著全球史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這種影響已經開始傳導到中國史研究領域[1]王永平.面對全球史的中國史研究[J].歷史研究,2013,(1);劉新成.全球史觀在中國[J].歷史研究,2011,(6).。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已經有學者開始自覺嘗試與運用全球史觀開展研究,尤其是在絲綢之路的研究中,運用全球史觀開展研究更是大有作為。然而,對于大多數國內的中國史研究者而言,全球史對他們還是一種相對陌生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之所以會形成這種局面,其原因是非常復雜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全球史的理解以及對中國史與全球史關系的定位上。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更好地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史研究者關注全球史,并自覺地引進和應用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展開研究。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中國史與全球史的關系?全球史對中國史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何在?中國史在全球史研究中應該如何定位?在絲綢之路研究中應該如何運用全球史觀?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值得學術界深思的。
一、絲綢之路是一部人類文明發展的全球史
中國史是全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但是,全球史強調超越國家和民族本位,而以“社會空間”作為審視歷史的基本單位(人們的生活圈),因此全球史絕不只是簡單地在原來的世界史中增加了中國史的內容而已。這樣說,并不是像有的學者所擔心的那樣,在全球史的潮流中,國別史的研究會失去意義[1]葛兆光.在全球史潮流中國別史還有意義嗎[J].中國文化,2012,(2).。相反,他們中許多人的研究專題仍然是地區史和國別史,只是他們的研究范式、研究視角和研究內容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即在“全球史觀”的指導下,重新審視地區史和國別史。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區-國別史的藩籬,也不能繼續作為地區-國別史的堆積。但迄今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層級、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單位,仍然應當是‘國家’(nation-state,包括多民族的國家和單一民族國家)。”[2]董正華.論全球史的多層級結構[J].貴州社會科學,2011,(11).可見,在全球史的研究中,國別史和地區史的研究仍然非常重要。全球史并不能完全取代舊的國別史,“但它的確豐富了傳統世界史(包括中國史在內——筆者按)的視角和方法,擴展了我們的歷史視野,使我們注意到跨越民族、國家和文化區域間的人口遷移、帝國的擴張、技術轉移、環境變遷、文化宗教和思想的傳播、經濟的波動等等對全球歷史的影響和意義”[3]何平.全球史對世界史編纂理論和方法的發展[J].世界歷史,2006,(4).。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全球史的研究中,是不能缺少中國史的。
全球史家在進行歷史研究時都非常重視對中國歷史的考察,近年來,“在全球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把中國史納入世界史的宏觀體系,并逐漸成了一種新的學術趨向”[4]張廣智.中國史學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國年鑒學派走向世界說開去[J].江海學刊,2007,(1).。許多全球史家都以獨特的視角和方法對中國史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和重新解讀,如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和本特利、齊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等,都將中國史的研究納入全球范圍內去考察,強調跨國界、跨地域范圍的比較與借鑒、互動與關聯,使中國史研究具有了新的廣度與深度。也有學者吸收了全球史的觀念與方法,用以研究中國歷史,產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區域史研究中,濱下武志在《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等論著中,把中國放在東亞或整個亞洲的空間范圍內進行審視,從新的角度對歷史上的中國以及亞洲與歐洲關系進行了闡釋[5](日)濱下武志;朱茹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在社會經濟史領域,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經濟的發展》[6](美)彭慕蘭;史建云譯.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王國斌的《轉變中國:歷史變化和歐洲經驗之局限》[7](美)王國斌;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和歐洲經驗之局限[M].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8](德)貢德?弗蘭克;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等論著,以全球視野為參照系,交互比較中西發展道路的歧異,將中國置于世界歷史的發展之中,強調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國歷史獨特的發展邏輯。在環境史研究中,龐廷的《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1](英)克萊夫?龐廷;王毅,張學廣譯.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2](美)賈雷德?戴蒙德;謝延光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3](美)威廉?H.麥克尼爾;余新忠,畢會成譯.瘟疫與人[M].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0.等論著,將中國歷史發展放在世界環境變遷中考察,從環境因素、人類活動和環境意識的角度發現中國環境的變遷與世界的許多共性與特性。
在中國的歷史學研究領域中,由于中國史與世界史是兩個分立的學科,囿于學術訓練和知識結構,很少有學者真正把中國史當成全球史的一部分來進行研究。近年來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和探索借鑒全球史的理念與方法來研究歷史,在傳統研究范式中取得了創新和突破,然而,方興未艾的全球史在我國主要還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學理論研究者的青睞和歡迎,與他們熱烈談論和傾心引介全球史的熱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國史研究者中卻顯得相對比較冷清,鮮有回應[4]蔣竹山.探尋世界的關聯:全球史研究趨勢與實踐[J].歷史研究,2013,(1).。這種情況的出現固然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復雜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的認識問題。傳統觀點認為,“‘世界史’等同于‘外國史’,凡是一切不包括中國史在內的歷史,都可以叫‘世界史’”[5]錢乘旦.評麥克尼爾《世界史》[J].世界歷史,2008,(2).;而中國史則主要是以歷代王朝興衰和社會變遷為線索的斷代史和各種專題史的分解與整合。這種劃分既有歷史學科本身發展的原因,也有現實需要的考慮,但它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卻產生了諸多弊端。正如德國學者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所指出的,盡管中國的大學中很早就設置了外國史與世界史專業,但其世界史研究實際上集中于一些選定的重點地區,從拉美到南亞的世界其他地區在大部分時間里都缺乏關注;中國歷史編纂學與其他地區性研究的嚴重分離從20世紀上半葉持續至今,很多重要的世界史教材甚至完全沒有提及中國史[6]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Cambridge,2011;董欣潔.變動世界中的全球史及其多樣性——讀《全球史的全球觀點:連通世界中的理論與方法》[J].史學理論研究,2012,(2).。因此,在我國的中國史研究領域中,如何引進和運用全球史的理念與方法,將中國史當作全球史的一部分來進行研究,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話題。
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對絲綢之路的開辟、發展以及由此帶動的多元文明的互動與交流一直是學術界非常關注的重要課題。絲綢之路的開辟正是超越了傳統的民族與國家的界限,關注絲路沿線不同人群之間的相互接觸、交流與碰撞。通過對古代絲綢之路的考察,可以看出來往于東西方之間的各色人員以及頻繁流動與遷徙的人口,將技術、物種、風俗、宗教、文化思想甚至是瘟疫和疾病傳播到世界各地,以此引發世界范圍內不斷地技術革新、觀念變化、文化與思想的進步以及環境變遷、經濟與政治的波動、帝國的消長等等,從而對全球歷史產生深刻的影響,將人類的發展由各地相對分散與隔絕的狀態逐漸帶入到相互聯系與持續交融的全球化時代。絲綢之路文明交流強調互鑒與融通,因此從本質上來講,絲綢之路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文明傳承與融合的全球史。
二、全球史對絲綢之路研究的啟示
隨著全球史的影響越來越擴大、研究的領域越來越深入,它的一些思維與理念逐漸波及到中國史研究領域,對絲綢之路的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非常有益的啟示:
1.破除“歐洲中心論”對絲綢之路研究的啟示。“全球史觀”旨在突破傳統歷史研究中的“歐洲中心論”,建立一種超越狹隘民族和國家界限,公正地評價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區的一切民族建樹的整體歷史觀。首倡“全球史觀”的英國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Geoffery Barraclough)說:“世界上每個地區的各個民族和各個文明都處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權利要求對自己進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許將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經歷只當作邊緣的無意義的東西加以排斥。”[1](英)巴勒克拉夫;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P158)在絲綢之路的研究中,“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幾乎沒有市場。絲綢之路的研究強調的是多元文明的互動、交流與傳播,形形色色的“文明中心觀”自然也會受到學者的自覺摒棄。但是,由于從近代以來中國就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與蹂躪,所以當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和民族的自豪感空前高漲,反映在學術研究中,就是在否定“歐洲中心論”和批判“中國文化外(西)來說”的同時,又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非常濃厚的“中國中心觀”。反映到我們的中國史研究中,通常也會在不經意間貫徹這種歷史觀。如在絲綢之路文明交往中,過分強調中華文明的獨立發展道路和在東亞文明的中心地位,陶醉于中國古代的各種發明創造和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領先地位,動輒就以“我們古已有之”來回應從絲路傳入的世界各地的新生事物和新興潮流的誕生與出現,而忽視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響,結果導致盲目排外與妄自尊大情結在社會上時有泛濫。這樣就很容易形成一種“中華文明優越論”的感覺。所以有的學者就明確指出:“‘中國中心論’也不對。”[2]林甘泉.“中國中心論”也不對[N].北京日報,2007-1-22.第19版.其實,無論是“歐洲中心論”,還是“中國中心觀”,都是一種失之偏頗的狹隘歷史觀。我們只有在歷史研究中,尤其是在絲綢之路研究中,將中國真正放在全球大背景下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時期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和世界其他地區歷史進程的相互聯系和區別,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2.互動理念對絲綢之路研究的啟示。全球史家認為互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社會發展源自變化,而變化的起點是接觸外來新事物。對新事物的取舍過程就是傳統的蛻變過程,盡管社會對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歡迎態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結果同樣會導致社會發生變化[3]劉新成.互動:全球史觀的核心理念[J].全球史評論(第2輯),2009.(P3-12)。從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互動始終貫穿其中。互動不僅體現在民族與國家之間,而且還體現在不同地域與人群之間、不同階層之間、不同信仰和黨派之間、不同性別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等許多方面。互動包括政治交往、經貿往來、文化交流、自然抉擇等多種形式;互動強調互動者互為主體。通過互動,達到彼此了解和認知,并由此帶來社會發生變化,形成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局面。當然,認知有時也會發生偏差和誤讀;另外,互動也并不總是通過和平的方式來進行的,有時也會發生激烈的沖突,甚至訴諸武力、導致戰爭。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互動”也是中國社會發生變化與進步的動力。在中國歷史上,中國與外國、中央與地方、漢族與少數民族、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村之間,互動幾乎無處不在。尤其是在絲綢之路開辟以后,佛教、景教-基督教-天主教、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甚至猶太教、東正教、婆羅門教等多種宗教的入華,技術、物種、風俗的東傳,瘟疫與疾病的傳播,多民族的融合以及由此引發的王朝的興衰更迭、社會階層的升降變動、唐宋變革、近代社會的變遷、現代化道路的選擇等,都與絲綢之路多元文明的互動與交流有一定的關系。可以說,絲綢之路多元文明的互動使中國社會充滿了活力,促進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3.中心-邊緣(center and periphery)視角對絲綢之路研究的啟示。中心-邊緣視角來自于經濟學理論,它已經成為世界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模式。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建構他的“世界體系”理論時,就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由中心區、半邊緣區和邊緣區三部分聯結而成[1](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羅榮渠等譯.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P194)。全球史觀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中,每一種文化都將自身視為當然的中心地帶和文明所在。從中心到邊緣的地理構架反映到文化觀念上就是發達文明與欠發達文明,但歷史事實表明,所謂“中心”與“邊緣”是變動不居的概念,“中心”與“邊緣”之間常有互動、雜混的現象發生。比如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一直自稱為天下的中心,而將周邊民族視作蠻夷。而古代印度也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天地之中也”[2](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一·河水[M].中華書局,2007.(P7),他們將恒河中流一帶的中印度稱為“中國”(Madhya-desa),而將遠方之地當作“邊地”(Mleccha-desa)。東晉僧人法顯沿絲綢之路遠赴天竺求法,當他到達南亞,被自稱為“中國”的印度人稱作“邊人”和“邊地之人”時,原來固有的“中國”觀念受到強烈沖擊,很快就表現出來了極大的心理落差,產生了“中心—邊緣”時空置換的心理變化,以至他后來撰寫的《佛國記》中處處將天竺當作他心目中的“中國”來描寫[3](東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M].中華書局,2008.。另外,從中心—邊緣視角審視我們的傳統史學敘述也會得到新穎的啟示。如南北朝時,南朝與北朝互為“中心”與“邊緣”。原來處于邊緣地帶的蠻族拓跋鮮卑部進入中原(尤其是遷都洛陽)后,建立了北魏王朝,一躍而成為中國北方的中心,而將南方政權視作邊緣,蔑稱為“島夷”;而原來處于中心地帶的晉室南渡后,建立東晉政權,歷經宋齊梁陳諸朝,成為中國南方的中心,而將北方政權當作邊緣,反唇相譏為“胡虜”。從中心—邊緣視角重新審視這種傳統敘述,對我們更好地處理歷史上曾被作為邊緣的蠻族的歷史地位,重新看待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還有從中心—邊緣視角重新審視鴉片戰爭,將會看到大英帝國與清帝國這兩個文化中心的激烈碰撞,雙方敵對的同時仍不忘將對方看作蠻族甚至非人的東西,追溯這種文化碰撞的過程及雙方中心—邊緣觀念的轉變,就是一種很好的全球史取向。中心—邊緣視角是全球史研究的一個有益嘗試,它會給絲綢之路的研究帶來嶄新的面貌。
4.關注人與自然甚至宇宙的關系對絲綢之路研究的啟示。全球史是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劇的產物,其實質是史學界對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的學術反思與回應,它反映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史學發展的新趨勢。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類的交往與互動更加密切與頻繁,人類的生存環境面臨著更大的壓力,過去常常將“杞人憂天”當作笑談,如今人類社會能否可持續發展卻成為嚴肅地擺在全體地球人面前的共同話題,如環境問題、生態問題、氣候變化問題、能源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疾病傳播與擴散、物種的入侵與傳播、信息與技術革命、戰略安全等,而這些問題也正是傳統歷史學所忽視的問題。全球史的學術取向,在于“把全球化歷史化,把歷史學全球化”,這也正是其魅力所在。所謂“把全球化歷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發展歷程;“把歷史學全球化”,則是要體現全球史的學術立場,即貫徹“互動”理念[1]劉新成.《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M]//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著;魏鳳蓮等譯.新全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Ⅴ頁.。傳統歷史學傾向于把世界各民族分為不同類型,并孤立地考察各自發生、發展的過程,因此研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其關注的重點。全球史則更傾向于關注那些影響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全球性問題,這樣研究人與自然甚至宇宙的歷史,就理所應當地進入全球史家的視野。在傳統的絲綢之路研究中,學者們多關注絲路沿線各帝國的興衰和社會變遷,以考察這些帝國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為重點。全球史的興起,已經或正在對絲綢之路的研究產生著越來越大的輻射和傳感力,那些以往為史家所忽視的絲路沿線的環境變遷、生態變化、瘟疫與疾病的擴散、物種和技術的交流、風俗與宗教、思想文化的傳播等領域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絲綢之路研究者的關注。
5.宏大敘事與微觀視角的結合對絲綢之路研究的啟示。全球史從本質上來說,屬于宏觀史學[2]劉新成.文明互動:從文明史到全球史[J].歷史研究,2013,(1).。宏觀史學屬于歷史哲學的范疇,它關注的是人類的整體命運。從這一點上來說,它和具有整體史觀的全球史有相通之處。但是,從“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到后現代史學宏大敘事備受質疑,微觀史卻獨領風騷,史學的“碎片化”傾向越來越嚴重。在中國史研究領域,由于長期受教條主義的束縛,按照僵化的理論模式演繹的所謂宏大敘事已經顯得陳腐與過時,史學研究的微觀化傾向越來越嚴重,表現在研究課題瑣碎雜亂,缺乏整體關懷和全面聯系與貫通,輕視理論思考,對歷史現象不能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全球史和傳統意義上的宏觀史學有所不同,它雖然致力于通過跨學科、長時段、大范圍、全方位地探討和關注人類生活層面的相互聯系與互動,尤其是以關注跨越地域和種族的互動與交流為特色,但是它并不排斥微觀史學,它已經跳出了以往建構宏大體系與理論的框架,將宏大敘事與微觀視角相結合[3]蔣竹山.超越民族與國家的歷史書寫——試論晚近西方史學研究中的“全球轉向”[J].新史學,2012,(3).,開辟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類似于史學研究中的“以小見大”。有學者提出“全球微觀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主張,如安德雷德的《一個中國農民、兩個非洲男孩和一個軍閥:一種全球微觀史的研究趨向》一文,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即如何從全球視野來書寫個人歷史[1]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Two African Boys,and a Warlord: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21, no.4,2010,(P573-591)。又如羅斯?鄧恩的《伊本?巴圖塔的冒險經歷:一個14世紀的穆斯林旅行家》[2]Ross E.Dunn,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則是將一個曾到過中國的穆斯林旅行家置于廣闊的情境中,探討其流動的全球性意義。因此,“全球史不僅只有宏觀,其實仍可兼顧微觀”[3]蔣竹山.探尋世界的關聯:全球史研究趨勢與實踐[J].歷史研究,2013,(1).。當然,“宏觀和微觀都是相對的,取決于研究者的界定和聚焦”[4]張偉偉.全球史中的中國史.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第2輯)[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P25-46)。但是,宏觀與微觀的結合,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強調在宏觀研究指導下進行微觀研究,或在微觀研究支撐下開展宏觀研究,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微觀史的細碎化和宏觀敘事的空洞化。而絲綢之路的研究非常契合跨學科、長時段、大范圍、全方位地探討和關注各地人類生活層面的相互聯系與互動,尤其是關注跨越地域和種族的互動與交流,因此在絲綢之路的研究中自覺運用全球史觀將大有作為。
當然,全球史的研究特色對絲綢之路的啟示遠非以上諸點所能囊括得了。由于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還正處于不斷探索與實踐當中,因此在絲綢之路研究中如何體現全球史觀還面臨著一些困惑。如在學科設置上,全球史一般歸于世界史學科,而絲綢之路的研究一般隸屬于中國史,這樣就與全球史的結合還面臨著身份認同上的尷尬局面;又如在絲綢之路研究中的全球史取向應如何避免落入中外關系史的老套路,同時還要避免那種將全球史觀簡單地理解成只要在絲綢之路的研究中引入世界史背景的“偽全球史”。而實際上還是“兩張皮”的現象;另外,在當前的絲綢之路研究中所體現出來的往往還是站在“我者”的角度看待“他者”的觀念,也非常不利于貫徹全球史觀的理念。因此,全球史觀在給絲綢之路研究帶來啟發與思考的同時,也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它不僅給絲綢之路研究帶來了一種新視角,而且還為觀察中國歷史和社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方法。在全球史視野下考察絲綢之路,可以對以往的許多問題做出重新解釋,從而進一步拓展對中國歷史的理解與認識。因此,在絲綢之路的研究中,引進全球史觀的理念與方法,或許將會給我們的研究開辟出一片嶄新的史學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