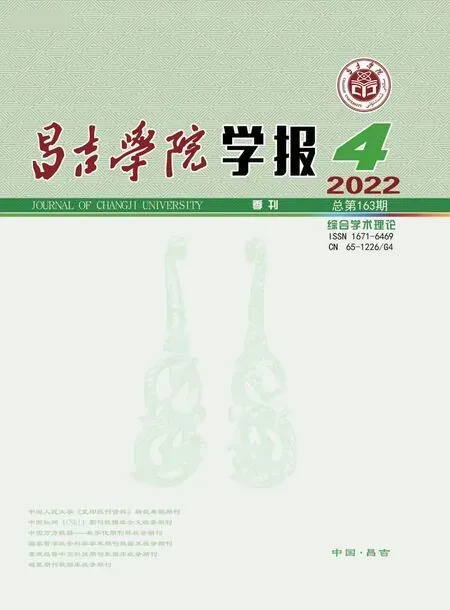悲劇愉悅:跨學科討論語境中的多元視角
果 玉
(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 山東 濟南 250100)
引言
數(shù)據(jù)時代與生物技術改變了我們傳統(tǒng)的認知模式與感知方式,在圍繞審美機制與審美活動的探討中,辯證的立場包括了對既有美學研究方向的批判和呼吁科學與人文的共融。劉旭光在《審美人文主義及其敵人》中以審美價值、思維方式與意義來闡釋審美人文主義立場對校正美學研究方向的必要性。他認為神經(jīng)美學研究將“審美”裁減為形式美感,將“美學”簡化為愉悅的快感,將審美看作是神經(jīng)性反應或是身體反應,不僅無視審美的人文性,還違背了審美活動的精神性,并將這種研究稱為“本質(zhì)主義與科學主義對人文活動的入侵”。[1]胡俊在回應的文章中呼吁科學與人文的交融貫通,在她看來審美活動是一般腦區(qū)與核心腦區(qū)共同加工的復雜的聯(lián)動過程,而美感是集感性、理性與情感的智性愉悅,這種智性愉悅是結(jié)合自下而上的感覺體驗與自上而下的意義調(diào)節(jié)所形成的綜合機制。[2]斯諾提出彌補人文與科學“交流鴻溝”的解決之道已偏離其最初設想,實現(xiàn)二者之間有效對話的期許尚未實現(xiàn)。喬納·萊勒結(jié)合當下語境認為,雙方描述世界的語言仍舊是不對等或不通用的,萊勒嘗試結(jié)合現(xiàn)象學與生物學建立“第三種文化”,這種文化會“自由地移植科學與人文,會專注于將科學簡化的事實與我們真實的經(jīng)歷連接起來。”[3]234認知和闡釋人類身心是人文探索與科學研究的共同分母,對這一問題的理論研究架起了二者溝通的橋梁,那我們不禁要思考結(jié)合人文與科學的神經(jīng)美學領域能否實現(xiàn)兩種文化之間有效的對話。
構(gòu)建范疇是人類本性使然,可以被視同主體做出判斷和剖析意義的根基。在哲學與神經(jīng)科學的視域下,始于審美活動的悲劇是在腦部各區(qū)域高效互動中認識人類與世界的邏輯思維及表達方式。悲劇愉悅不再僅僅依賴人文學科的視角來描繪自己的輪廓,科學性的發(fā)現(xiàn)也充盈著悲劇研究的理論景觀,在“悲劇”這一審美范疇的照耀下,深描悲劇愉悅可以為我們探究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借鑒提供范例。因此,更好的研究思路應是在人文與科學的交相輝映中,探索并詮釋悲劇愉悅研究新路徑的可能及其價值。
一、悲劇愉悅問題的哲學源考
悲劇展示并追問了人的此在與現(xiàn)實存在的哲學意涵。以雅思貝爾斯的話來說,即研究個人體驗的“臨界境況”達人之存在的“基本境況”。“悲劇愉悅”作為悲劇范疇的核心議題,照亮了哲學與神經(jīng)科學之間一個重要的哲學鏈接點——“我們是如何從人類再現(xiàn)痛苦中獲得愉悅?”圍繞其所形成的思辨方式、基本設問與解決路徑在不同學者的闡釋中逐漸形成。
古典悲劇誕生于宗教與理性的沖突之中,“命運與自由之間的沖突反映了秘索斯(mythos)和邏各斯(logos)之間強大的張力。”[4]6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經(jīng)過‘裝飾’的語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別被用于劇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動,而不是敘述,通過引發(fā)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疏泄。”[5]63凈化說使人作為一個親歷者投入悲劇之中去接受客觀實在,但是卡塔西斯的原意,何謂凈化歷來是莫衷一是。卡塔西斯作為悲劇悖論的關鍵節(jié)點,對前者的把握可謂是理解后者的必要條件,穆爾從不同方面(宗教、醫(yī)學、道德寓意、心理治療等)闡釋卡塔西斯的內(nèi)涵,結(jié)合穆爾對卡塔西斯的分析及厄爾·沃瑟曼對悲劇悖論的梳理,我們可以從宏觀層面把握悲劇悖論的歸屬問題,從微觀層面提煉悲劇愉悅的情感轉(zhuǎn)換機理。
第一,從起源來看,源于宗教的悲劇與酒神崇拜聯(lián)系在一起,與神契合欣喜若狂,在此意義上的卡塔西斯是指醉酒后的一種能夠緩解恐懼與悲傷的迷狂狀態(tài)。從宗教的角度來說卡塔西斯還可以被譯為“凈化”,指的是對含有罪惡之事的救贖。不同文化中都包含著本體論差異(如人/神,男/女)與規(guī)范性差異(如善/惡,真/假),當其中的界限含混不清時則被視為污染,以宗教中的儀式或獻祭來“清除”污染,恢復宇宙秩序。
第二,治療學意義上的卡塔西斯被譯為“清潔衛(wèi)生”,如類病類治的醫(yī)學治療原則,“強烈的感情可以通過用一種情感的調(diào)節(jié)性的管理而獲得凈化,之后就喚起一種愉悅的慰藉。”[4]138
第三,受柏拉圖影響的基督教傳統(tǒng)傾向于卡塔西斯的道德寓意——同情。在同情學說的擁護者們看來,即使在悲劇中傳達出的情感是令人悲痛的,但也會因同情的運作及其社會效用,使人自然而然地感到愉悅。[6]417如奧古斯丁認為愉悅來自對悲劇英雄受難的憐憫,與別人分享英雄磨難以此獲得愉悅體驗。叔本華將憐憫與同情理解為一種積極的能力,同情喚起人類惻隱之心,“能夠?qū)λ说哪ルy展開移情與調(diào)試”。[7]艾德蒙·伯克認為真實的悲劇相比模仿的悲劇更為有趣,原因在于作為人類社會本能之同情才是真實目的,他建議劇作家的任務是接近現(xiàn)實,進而強化同情和愉悅。[7]道德哲學將悲劇愉悅放置在道德價值的運作之中,主體的道德滿足感才是悲劇愉悅的根本原因,“將所有的激情都指向自我滿足的欲望來決定這種情感是愉悅的還是痛苦的”。[7]最后,在心理學論域中的卡塔西斯經(jīng)由笛卡爾的激情學說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雅各布·伯奈斯那里被視為“精神磨難的凈化”,悲劇引起的強烈情感經(jīng)由觀眾“宣泄”終獲鎮(zhèn)靜與愉悅。在悲劇悖論的哲學解釋中,從悲傷之情到愉悅之感必定是經(jīng)歷了某種推動和轉(zhuǎn)換,這一推手則是卡塔西斯的“調(diào)節(jié)性管理”。卡塔西斯猶如意義集合體,肉體與精神的凈化、清潔、救贖、解放、同情、利己、疏泄、模仿、實踐等都被涵蓋其中,正是在卡塔西斯的調(diào)節(jié)運轉(zhuǎn)中,主體的悲劇體驗實現(xiàn)了從悲傷到愉悅的轉(zhuǎn)換。總體來看,上述學者們分別從客觀認知和主觀情感各有側(cè)重的建構(gòu)了自己的學說,悲劇愉悅問題使我們看到了這一議題立足點的多樣和基本問題的開放未決。
“最豐富的審美體驗來自與使人感到痛苦的藝術的接觸,因為一個人很少像在藝術面前經(jīng)歷痛苦的情感反應那樣,在智力、知覺和情感上完全投入。”[8]人們在悲劇藝術作品中獲得豐富的審美體驗,在此過程中人的智力、知覺和情感高度投入,愉悅則是這種高度投入的產(chǎn)物。對于悲劇審美體驗中的愉悅,我們需要聯(lián)合認知與情感使得此項研究更具系統(tǒng)性與深度性。對于悲劇愉悅議題,經(jīng)典的哲學思辨與現(xiàn)代的美學論證為其在人文學科的更新帶來了動力,也為神經(jīng)科學理論框架提供了立論依據(jù)。朱光潛對哲學家們研究悲劇的方式頗有微詞,他認為哲學家是將悲劇作為例證來證明先驗演繹,缺少對作品歸納析解后的經(jīng)驗闡釋,“哲學家有特權(quán)抽象地處理事物,但是把純分析方法應用于精神活動往往有歪曲精神活動本質(zhì)的危險。”[9]6隨著歷史進程的變遷,傳統(tǒng)哲學對悲劇愉悅的析解已然不夠充分,因此探尋一種更加貼合現(xiàn)實感的研究方法,不僅有助于充盈美學研究空間,還能夠?qū)劢刮膶W藝術、理解審美體驗、塑造大腦認知提供思路。如今神經(jīng)科學研究的認知積累已輻射至人文社會科學,由此誕生的神經(jīng)美學一方面深化人類對自我生物基礎的理解,另一方面將更多具有啟發(fā)式的美學理論和洞察式的經(jīng)驗現(xiàn)象融入到自身理論的建構(gòu)與驗證之中。[10]6
二、悲劇愉悅問題的科學省思
正如加布里埃爾·斯塔爾所言,“審美體驗之效果既可以是科學的精準詳細,也可以是詩學的漫無邊際。”[11]124神經(jīng)美學是傳統(tǒng)藝術哲學與美學之間的紐帶,它為闡釋文藝創(chuàng)造者和接受者的大腦結(jié)構(gòu)與功能搭建背景,對哲學描繪下的審美體驗提供了補充。[12]探索悲劇審美體驗的神經(jīng)基礎,既有助于闡明悲劇愉悅的機理,又可以發(fā)掘哲學與美學中重要概念對神經(jīng)科學研究的中介作用,“哲學美學的概念中介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這一研究領域比前面所述的更加復雜:一個給定的美學對象往往為不同技能、不同背景、不同時間的不同人服務于多種目的。”[13]科學為美學理論補充客觀性,認知科學為把握審美價值提供實驗數(shù)據(jù),在神經(jīng)美學研究意義上得以拓展的悲劇愉悅開啟了神經(jīng)科學與美學關聯(lián)路徑的多樣性,使對悲劇愉悅的探討獲得了綜合的,跨學科的維度。
基于國外神經(jīng)美學研究成果,胡俊對悲劇愉悅的闡釋開拓了我們的視野,她主要以如下三條路徑展開。首先,神經(jīng)美學家瓦塔尼安的審美快樂理論認為,基本的核心感情作為審美中認識與情感的理論連接點,上承主體與客體利害關系的認知,與此同時激活了其后的情感體驗機制。胡俊由此基礎上思考悲劇愉悅的審美過程,在審美活動中主體先是產(chǎn)生并確定了悲傷這一核心感情,經(jīng)由審美主體情感的流溢,主體經(jīng)歷、記憶、想象、意義的再加工,結(jié)合后天有關世界、社會與文化的情感而形成的綜合審美判斷,隨之而來的則是更具高峰體驗的審美愉悅。但是,胡俊對瓦塔尼安的理論構(gòu)架有所保留,是因為他是依據(jù)已有的理論成果,還需接受神經(jīng)美學實證檢驗。其次,神經(jīng)美學家通過觀測神經(jīng)遞質(zhì)的方法來研究審美體驗,在欣賞文藝作品時,人腦在激活獎賞機制的同時也會分泌多種神經(jīng)遞質(zhì),如內(nèi)啡肽、多巴胺、五羥色胺等,進而產(chǎn)生愉悅感。胡俊借此理解悲劇愉悅,在她看來當我們在欣賞悲劇時,悲傷、痛苦、難過等消極情感體驗會激活自我情緒免疫能力,釋放人腦中如內(nèi)啡肽等快樂神經(jīng)遞質(zhì),GABA抑制多巴胺,內(nèi)啡肽的產(chǎn)生可以抑制GABA進而增加多巴胺引起興奮,隨后釋放血清素歸于安寧的愉悅。[14]最后,胡俊根據(jù)澤基教授的實驗來闡釋悲劇愉悅的發(fā)生機制,根據(jù)實驗發(fā)現(xiàn),悲傷在激活內(nèi)側(cè)眶額葉皮層時也激活了背外側(cè)前額葉。我們知道內(nèi)側(cè)眶額葉皮層即美感體驗區(qū),而背外側(cè)前額葉則是有關推理反思和意義判斷的高級認知區(qū)域。“雖然最初從悲劇中感受到痛苦、恐懼、悲傷的不快感,但隨著我們從悲劇中進一步體會到崇高的意義,我們通過消極共情也可激發(fā)審美愉悅體驗。”[15]
綜上所述,我們在審美體驗中生發(fā)出的混合情感并非是大腦對某一刺激的歷時性加工,而是源于大腦的智性運轉(zhuǎn),促使運轉(zhuǎn)成功的則是數(shù)量龐大的神經(jīng)結(jié)構(gòu)與不同腦區(qū)的互動協(xié)作。悲劇愉悅是感覺知覺、情緒情感、動作想象、記憶加工、審美判斷和獎賞機制等腦部各區(qū)域協(xié)調(diào),動態(tài)交互的產(chǎn)物。在審美語境中,被稱為是消極情緒的悲傷常常和積極情緒的愉悅聯(lián)系在一起,目前神經(jīng)美學主要以音樂和視覺藝術作為研究對象,對文學作品的研究亟需關注。美學中的一些概念于不同時期經(jīng)由西方正典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已然發(fā)生改變,而與之相伴的對于審美體驗與審美愉悅的詮釋也在歷史演化與文化演變中移宮換羽,神經(jīng)美學需要結(jié)合當下語境提煉抽象的美學原理,更需要豐富的文學作品樣本與詳實的實驗數(shù)據(jù),只有這樣才能夠為美學和文藝理論批評提供更好的實證支撐。
三、認知與情感:悲劇愉悅的雙向運作機制
加布里埃爾·斯塔爾以繪畫、文學與音樂中的形象化為切入點搭建審美體驗的神經(jīng)科學模型,即結(jié)合神經(jīng)科學的框架與文學藝術的批評理論,探索審美愉悅的體驗過程與運作機制,重塑美學認知。愉悅作為悲劇審美體驗的終端,本文試圖結(jié)合斯塔爾建構(gòu)的神經(jīng)美學模型與西方的移情學說,從審美愉悅的發(fā)生機制入手來梳理并完善悲劇愉悅的認知與情感雙向運作機制。
第一,多項研究表明相較于日常情感,審美情感更受認知的控制。在情感反應實驗中,視覺藝術的情感反應與其他行為的情感反應有所區(qū)別。在審美體驗中,被稱為積極情緒的愉悅和消極情緒的不愉悅都表現(xiàn)出了大腦左半球的單側(cè)性活躍。斯塔爾認為這項研究也許印證了“審美反應之情感只是名義上的‘消極’(例如,我們一般將悲傷冠之為消極)這一說法,那些被我們稱之為‘消極’的情感在一種積極的審美反應語境中其神經(jīng)評估或許會發(fā)生改變。”[11]38人類審美體驗與審美反應是大腦運作機制與人類主觀活動動態(tài)交互的產(chǎn)物,“深度審美體驗使我們回到了靜察的狀態(tài),守候核心意識特征的出現(xiàn),我們還會在對某個對象的觀照中產(chǎn)生一種愉悅的覺知,并對它的價值進行思忖與評估,或許深度審美體驗綜合了我們總是在期待的以及我們無法預料的東西。”[11]57深度審美體驗能夠產(chǎn)生新的神經(jīng)評估與價值評價,其中包含著大量神經(jīng)元的默認神經(jīng)網(wǎng)絡涉及到自我意識與經(jīng)驗、社會環(huán)境、他人心理等更為全面的認知與評估。我們在欣賞悲劇時多項通道參與其中,比如不愉悅的感覺、悲傷的情緒、對以往經(jīng)歷的聯(lián)想、對悲劇情境的回憶和對人物的想象等,它們均參與了大腦的獎賞加工機制形成審美認知。參與深度審美體驗的默認模式網(wǎng)絡在悲傷情緒中,在不同腦區(qū)的動態(tài)交互下,結(jié)合高級的認知神經(jīng)評估機制與積極的審美情感反應,將內(nèi)在與外在、自我與社會、感知與評價整合為愉悅感,在悲傷的體驗中發(fā)現(xiàn)悲劇本質(zhì)、悲劇精神、世界秩序、人類存在等更為宏偉的意義。第二,形象化是通達審美愉悅的關鍵樞紐,我們是以感性的形象化理解不同的藝術形式與美,主體的審美體驗既是視覺的又是具體化的動作,動作想象以具身模擬的方式體驗他人行為。語言藝術中動作想象是核心,作者以文字實現(xiàn)形象化使審美主體獲得生動的形象體驗,我們能夠緊跟悲劇主人公感官景象在形象化的感知中體驗悲傷之情,文字所表現(xiàn)出來的動態(tài)跨感官想象讓審美主體產(chǎn)生聯(lián)覺、移情、共鳴等體驗,“動作的發(fā)生不僅是作為一種暗示或描述,而是一種感受,是我們的思維或肢體或聲帶中所伴隨的一種合法的節(jié)奏韻律。這種聯(lián)結(jié)所產(chǎn)生的愉悅感被編碼進了動作想象之中,并分布于一系列形象之中,最終,我們是通過多種方式或感知模式將它們再次形象化、生發(fā)愉悅感。”[11]83作為人類有意識知覺體驗,它是以具體的形象和象征來被讀者理解,這個過程也是有“時間序列和意外的瞬間”,時間性是闡釋悲劇精神意蘊的關鍵因素,我們能夠緊跟悲劇主人公感官景象在形象化的感知中體驗悲傷之情,文字所表現(xiàn)出來的動態(tài)跨感官想象讓審美主體產(chǎn)生聯(lián)覺、移情、共鳴等體驗,也正是形象化將悲劇中我們所感受到的信息,情感體驗與語義認識聯(lián)合在一起生發(fā)愉悅之感。
雅思貝爾斯認為一部作品被稱為真正悲劇的條件是主人公與觀眾都投入悲劇知識(悲劇性)當中,當二者雙方融為一體,個人體驗進入了主人公的“臨界狀況”,產(chǎn)生“自我置身于其中的存在的意義上的同情。”[16]49今道友信則將悲劇中的感動視作是同情,這種感動或同情使觀眾在悲劇中獲得解脫與超越。[17]178正如前文所述,同情常常與道德聯(lián)系在一起,而移情則掌握了道德與情感雙重維度,迪薩納亞克認為以移情闡釋審美經(jīng)驗的身體現(xiàn)象是合理的,重要的是這種闡釋要建立在以自然審美傾向為基點的心理生物學之上,“藝術作品在感知者的身上書寫自身:即電化地寫在由大腦皮層圖譜構(gòu)成的活動的信號模式中,它們也具有伴生的生理效果和動覺效果。”[18]259康德奠定了共通感的先天機制,如今我們能夠依托大腦神經(jīng)科學推進康德所謂的共通感,將悲傷與愉悅的共通感歸因于人類的移情能力,分布在額下回布洛卡區(qū)、杏仁核及穎上回等結(jié)構(gòu)中的神經(jīng)鏡像元使我們能夠推斷和理解他人的情感狀態(tài)。“首先,移情關系到我們掌握他人思想內(nèi)容的能力,以及預測和解釋他們想法、感受和行為的能力。其次,移情與我們在道德上對他人做出反應的能力有關——使我們不僅能了解他人的痛苦,而且能以適當?shù)牡赖路绞阶饕曰貞!保?9]IX移情是一個復雜的模擬過程,在品讀悲劇作品的過程中,審美主體可以模擬字里行間關于主人公的描述,將他人情境移入自我,體會人物生活與情感,可以模仿作者的創(chuàng)作過程與其產(chǎn)生共鳴。在自我與他者的分離,悲傷與愉悅的交織中傾聽、理解、回應他人苦痛,沉思自我概念與社會價值,深思人類命運,這恰恰是悲劇藝術重要性之所在。
從神經(jīng)美學角度來研究美學內(nèi)部歷來存在的經(jīng)典性議題,不僅展現(xiàn)美學理論的延續(xù)性,也可以使我們梳理出這一經(jīng)典議題在時間變遷中是如何被論證的。神經(jīng)美學是備具現(xiàn)實價值的實證智慧,但其對文化性、個體性,多層意義的解讀上略顯不足。安簡·查特吉認為感覺,情緒與意義作為審美體驗的三大要素,只有前兩者可以為神經(jīng)美學所研究,要以科學的研究方法對蘊含作品文化意義的概念藝術進行研究是困難的。[20]143文學作品、視覺藝術、聽覺藝術以不同的方式觸動我們,通達文學藝術中的意義層面是需要審美主體去體驗、欣賞、感受、理解和品鑒,在其背后牽涉到更為廣闊的個人知識背景與社會文化價值。再其次,索爾索在分析藝術與語言的結(jié)構(gòu)性質(zhì)時提出的“第三水平的藝術”即匯聚藝術智慧的悟(感覺認知的“道”),這也被視為是一個人對藝術的更為高級的自我回應,從這個層面來說很難用神經(jīng)科學的方式來研究。最后,神經(jīng)美學的研究對象應更加多元。在迪薩納亞克看來“神經(jīng)美學領域的更好的目標是發(fā)展出一種綜合的、高級的審美反應理論,該理論適用于所有被評價的對象,而不僅是藝術品(就這點來說,可以是風景或同伴)。”[21]44在神經(jīng)美學視域中探討悲劇愉悅充分展示了人文與科學的相互支撐與互相論證,但如萊勒所言,分割簡化法與實驗只能夠?qū)植康膯栴}做出闡釋,人文學科對現(xiàn)實感知與現(xiàn)象闡釋此種“最深層積淀”為科學的雄辯力提供了媒介,人文學科在闡述關于人類意識的獨特性,主觀體驗的差異性與自我感受的私人性時則更為全面。
結(jié)語
人類深度審美體驗發(fā)生于多感官的臨界之處,沃爾夫?qū)ろf爾施在《重構(gòu)美學》中認為,美學應該吸納不同學科領域的成果,“范圍擴大到涵蓋‘感知’所有領域的超越美學的美學,不僅對于完全把握審美來說是勢在必然,而且對于充分理解藝術也有著特殊的意義。”[22]137我們應該關注人文學科與科學之間的演變發(fā)展,聯(lián)結(jié)神經(jīng)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多重論點,關注差異與區(qū)分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他們的交界之域,結(jié)合理論與實踐來理解悲劇精神及其價值,以跨學科的視野研究美學中的悲劇議題,為人類審美認知提供廣闊圖景。悲劇向我們傳達出悲痛之感,在人類認知與情感雙重作用下主體終獲審美愉悅,結(jié)束對悲劇核心問題的探討我們不禁要追問悲劇的意義,李澤厚將悲劇的實質(zhì)引向創(chuàng)造崇高和激發(fā)人們倫理精神的高揚。區(qū)別于表象的美感,悲劇為我們提供的是一種引導式與啟發(fā)性的審美,這歸因于它用人類獨具一格的感知力與想象力將人性囊括于形象之中,彌散于動作想象之中。宇宙秩序與人類本質(zhì)在悲劇中得到了呈現(xiàn)與表達,宏大歷史敘事總是在沖擊著我們的記憶,諾拉認為能保留下來的只有所謂的“記憶之場”,能否將悲劇看作是懸置的“時間的島嶼”,視作并未因時過境遷而消逝的記憶場域,它以獨特的意象系統(tǒng)表達宣泄與凈化,以文本系統(tǒng)書寫文化記憶與社會價值,這種書寫融合認知與情感,表達倫理與道德,抒發(fā)記憶與創(chuàng)傷,其背后一切關于人類對生的向往和對美的憧憬被娓娓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