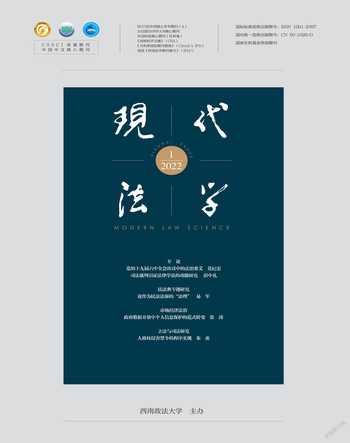論“飯圈”的法律規制
摘 要:當下“飯圈”呈現出頻繁投訴與舉報、非理性消費、數據造假以及組織性的行為失范現象。“飯圈”負面行為的產生與資方控制及平臺打榜的主導、藝人與“飯圈”組織者的推動、粉絲的參與及沉浸密切相關。“飯圈”的負面行為違背公序良俗,須進行綜合治理。應合理設置平臺的內容管理義務、調整刑法對巨額逃稅的處罰規則、完善網絡舉報制度、明確藝人及經紀公司或工作室對粉絲的引導義務。此外,應區分“飯圈”組織者雇主責任、教唆及幫助侵權規則的適用、賦予粉絲組織民事主體身份、家庭內部弘揚優良家風。
關鍵詞:“飯圈”;公序良俗;平臺責任
中圖分類號:DF920.0?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2.01.05
引言
“飯圈”是對圍繞某個明星建構的粉絲圈子的簡稱,它是由追星粉絲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助力,形成的以符號、文本為表現,由觀念、行為、態度構成的自成一體的娛樂群體。這一群體的主要成員集中在青少年等低年齡人群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組織性。“飯圈”中的“飯”來自“fan”(粉絲)的音譯,“圈”則體現了群體的邊界和區隔。而“粉絲”一詞,最早見于19世紀末的體育報道中,用以描述專業體育隊的追隨者。后來這個詞被廣泛地用在體育活動或商業娛樂的忠實追隨者身上,但這個詞在詞源上附著的狂熱的引申義,卻一直未與這一詞劃清界限。①
國內“追星”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雛形期”,始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先于內地發展的港臺大眾文化作品大量輸入,在內地掀起一股追星熱。崇拜和追逐影視明星、歌星的年輕人被賦予了“追星族”的稱謂。②這一階段,因時空阻隔追星活動大多是“追星族”自發的個人行為,相對缺乏組織性和統一性,粉絲群體的選擇與偏好主要通過購買或不購買偶像相關產品等經濟行為反饋,對偶像生產不產生直接的影響。第二階段為發展期,從2005年開始,湖南衛視選秀節目《超級女聲》的熱播為“追星族”重置了名稱——“粉絲”,他們不僅到節目現場高舉燈牌、高喊口號表達對選手的支持,還有組織地制作大量宣傳材料,向他人推廣自己的偶像,號召更多人為其支持的偶像投票。這一階段,粉絲群體主動自覺地完成內部集結和圈層話語建構,如李宇春的粉絲自命“玉米”并利用專有團體名稱區隔,實現人際交往領域的強關系集結。這一階段“粉絲”團隊的作用得以初顯,話語權開始增強,組織化程度也得到提升。[參見胡岑岑:《從“追星族”到“飯圈”——我國粉絲組織的“變”與“不變”》,載《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3頁。]第三階段為鼎盛期,伴隨著社交媒體平臺的廣泛使用,“流量明星”[流量明星,亦稱流量藝人,是指粉絲眾多且號召力極強,卻沒有知名作品的明星。流量明星通常擁有好看的外表、極高的人氣,常年占據微博熱搜和娛樂頭條,在互聯網上具有極高的話題度。]走紅。2018年,偶像養成類綜藝節目熱播,粉絲與偶像之間借由傳播技術帶來的便利,構建出一種情感上更熱切、行為上更主動、心理上更親密的關系模式,通過投入大量時間、精力、金錢助力偶像出道,陪同偶像從默默無聞到炙手可熱,追星與造星漸趨融合,大量藝人步入偶像養成時代。[參見韓傳喜、黃慧:《雙重驅力:偶像養成時代粉絲行為動機研究——基于周杰倫和蔡徐坤雙方粉絲打榜事件》,載《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110頁。]這一階段,粉絲成為高黏性的興趣與情感共同體,他們通過為偶像積極發聲、消費等方式影響輿論、影響娛樂業對明星的選擇,粉絲介入到打造明星的運作中形成具有組織性的活動方式。[參見張頤武:《“飯圈文化”反思》,載《中國文藝評論》2021年第10期,第7頁。]粉絲圈層內部的精密明確分工與多樣化、規模化的應援手段也使粉絲迎來“我的偶像我做主”式的群體狂歡,文化圈層特質更為鮮明。[參見王敏芝、李珍:《媒介文化視域中的粉絲話語權增強機制及文化反思》,載《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1月,第109頁。]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粉絲對偶像的追捧現象一直存在,這種現象與社會歷史發展、人的思維能力發展相關,是各個民族都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現象。[參見廉思:《中國青年發展(1978—20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18頁。]年輕人對偶像的迷戀本無口厚非,但近幾年,粉絲語言暴力、線上線下行為越界引發的文化發展失序、盲目偶像崇拜導致的社會道德規范錯位以及粉絲集體非理性等問題不斷涌現。[參見姜明:《大眾文化視域下的中國粉絲文化研究》,吉林大學2016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12-118頁。]
“飯圈”問題的研究涉及多個學科,已有的文獻呈現出多學科并進的態勢。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粉絲經濟的形成機制、發展趨勢上;心理學研究關注的重點是粉絲偶像崇拜的心理認同與行為機制;傳播學的研究主要著眼于“飯圈”的組織結構、動員機制、集體行動的邏輯上;社會學的研究主要關注組織維度、文化維度中偶像崇拜的行為失范現象及不良影響等方面。然而,遺憾的是,法學領域至今未對“飯圈”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飯圈”治理的核心是法律問題,本文試分析“飯圈”行為的典型表現、“飯圈”行為的產生原因及社會危害,以期促成解決問題的方案。
一、“飯圈”負面行為的典型表現
人們本以為,互聯網時代的青少年會更自由、更寬容,但未曾想,“飯圈”青少年的行為愈發的非理性。操控評論、數據造假、以自己的好惡為標準頻繁舉報、漠視他人權利、人肉搜索、非理性消費等不良行為時常見諸報端。
(一)投訴與舉報的工具化
在“飯圈”內部,粉絲常常在“飯圈”組織者的帶領下,有組織地搜索各平臺上偶像的負面信息,發現后要求發帖者刪帖或向平臺投訴,并向有關部門舉報,壓制或者消除關于偶像的負面信息。另外,不同“飯圈”群體之間,也會利用或制造具有競爭關系的對立方藝人的負面言行,依托公開的網絡平臺向有關部門舉報。[參見秦璇、陳曦:《偶像失格、群體非理性和道德恐慌:粉絲群體互相攻擊中的舉報策略與誘因》,載《新聞記者》2021年第10期,第52頁。]包容與多元的理念在“飯圈”漸被邊緣化。粉絲的投訴與舉報并非偶發,已成為“飯圈”的常態。“飯圈”慣常的操作是由“飯圈”組織者把投訴及舉報的方法及鏈接編輯成博文,便于廣大粉絲們反復操作。大多數互聯網平臺都設立了投訴機制,這使得粉絲在平臺內的投訴操作變得極為便利。粉絲不僅向平臺投訴,還會向中央網信辦、掃黃打非辦等公權力機構舉報,并將“危害青少年網友身心健康”“低俗涉黃”“維護網絡治安環境”等作為舉報理由。隨著投訴與舉報的常態化與擴大化,“飯圈”的生態變得復雜與混亂。[參見張世超、胡岑岑:《粉絲、平臺、資本與國家:多元互動視角下的飯圈反黑及其治理》,載《學習與實踐》2021年第7期,第134頁。] “飯圈”成員的舉報與刑事領域、經濟領域涉腐敗問題的舉報都不同。“飯圈”舉報常常缺乏事實與法律理據,有的是出于惡意、憤怒或為了報復,有的是為了增加自身偶像或降低對手的商業資源。這類爭斗行為常常外溢到公共空間,不利于公共討論。頻繁出現的舉報行為,不僅突破了文藝評論的界限,也大大增加了公權力機關不必要的審查負擔與社會治理成本。
(二)粉絲的非理性消費
粉絲追星的活動常圍繞對商品的消費和明星的營銷產生。[參見陳璐:《情感勞動與收編——關于百度貼吧K-POP粉絲集資應援的研究》,載《文化研究》第34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頁。] “粉絲經濟”的基本邏輯是情感經濟,即因情感聯結而產生的消費現象。[參見蔡騏:《社會化網絡時代的粉絲經濟模式》,載《中國青年研究》2015年第11期,第11頁。]在粉絲群體撬動的“粉絲經濟”中,粉絲的能動性、參與性和影響力不斷增強。[同上注,第10頁。]2021年4月,愛奇藝自制選秀綜藝《青春有你3》被一則網傳視頻推向風口浪尖,眾人傾倒牛奶飲品,只為獲取節目組指定飲品奶蓋內的二維碼給偶像打榜。[參見蒲俊杰、胡恩紅:《從“粉絲倒牛奶打投”看“后文化工業”現象》,載《青年記者》2021年第15期,第49頁。]因粉絲購買飲品只為瓶蓋,于是牛奶經銷商組織人力拆箱,倒奶,再將瓶蓋打包賣給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粉絲們省掉中間環節,直接購買瓶蓋。各方出于最大化效率和收益考慮,形成了一條完整但畸形的產業鏈。
這當中流量明星與粉絲力量相容共生。流量明星的粉絲群體基數大、活躍度高,流量明星崛起的背后,往往有著“飯圈”強大的應援消費實力。金錢與時間的投入成為粉絲參與應援的基本要求。[參見馬志浩、林仲軒:《粉絲社群的集體行動邏輯及其階層形成—以SNH48 Group粉絲應援會為例》,載《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第13頁。]粉絲在為偶像消費的實際行動中獲得身份認同和群體歸屬感,“飯圈”文化在消費領域呈現出群體性、狂熱性的特點。這一消費主義摒棄深度理性思考,以充滿視覺沖擊和感官刺激的偶像“人設”符號設定激發受眾消費欲望。[參見[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劉精明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頁。]“飯圈”的偶像已由傳統的精神信仰象征淪為消費的符號、空洞的形象和娛樂的工具。[參見李志雄、侯麗杰:《后現代偶像的建構與解構—以“鹿晗事件”反思當下偶像崇拜現象》,載《傳媒觀察》2018年第2期,第33頁。] “飯圈經濟”呈現出組織化、專業化、規模化、商業化的特質。[參見張亞光:《“飯圈經濟”的概念、理論與批判》,載《中國文藝評論》2021年第10期,第20頁。]
(三)“數據女工”的誕生
當下,流量已成為互聯網注意力經濟的通用貨幣。“流量”不僅是技術邏輯的關鍵,也是“粉絲經濟”商業邏輯的核心。流量源自用戶在網絡平臺的活躍度,它既代表著用戶閱讀和訪問數量,也代表著能夠被量化和轉換為生產資料的數據內容集合。隨著技術的發展與大數據算法的引入,藝人的網絡熱度完全能夠通過技術手段被量化,數據成為反映藝人流量高低的直觀依據。因此,粉絲也日益介入到偶像的出道、宣傳、營銷推廣等各環節的數據實踐中,“做數據”成為粉絲追星的常態。粉絲通過給偶像在各類平臺帶話題、投票等方式,使得與偶像相關信息的轉發、評論、閱讀、排名等量化數據上升。在追星的過程中,微博成為刺激和催生粉絲數據意識和勞動的“工廠”。由于大量粉絲為女性,粉絲也常被稱為“數據女工”。粉絲將自己對偶像的情感轉化為數據勞動,通過在微博上長時間不斷地點贊、轉載、發帖等方式生產數據,數據積聚成流量,而流量為偶像及其所屬團隊帶來經濟效益與資源。
巨量粉絲互動帶來的數據熱度以及“飯圈”超高消費能力帶來的商業價值變現使得資方趨之若鶩。[參見童祁:《飯圈女孩的流量戰爭:數據勞動、情感消費與新自由主義》,載《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第72頁。]“流量為王”的粉絲經濟崛起,使得數據與流量成為評判藝人的顯性指標。原本偶像背后映射的“認同—奮斗—夢想”的邏輯已被扭曲為“喜愛—數據—熱度”的利益模式。流量不僅成為主宰“飯圈”文化和粉絲經濟的法則,也改變了粉絲行為和這一群體的運作機制。
(四) 組織性的行為失范
互聯網的便捷性與傳導性,使各地有共同興趣愛好的個體在網上集結。以應援為紐帶,粉絲們組建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開展應援活動。他們目標明確,建立了一定的組織行為規則。但除了少量明確且可以公之于眾的規則以外,內部還存在著大量隱形規則,如粉絲應投入金錢助力偶像出道,投入時間維護偶像聲譽,投票、做數據,保持明星熱度等。“飯圈”成員還會使用特殊的語言符號和圈內行話,構成了這一組織的身份標志。從文化維度看,“飯圈”已形成內部專屬的話語體系與組織、運作規則。[參見呂鵬、張原:《青少年飯圈文化的社會學視角解讀》,載《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第64頁。]
“飯圈文化”是粉絲群體以網絡社交平臺為主要空間,圍繞偶像所展開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它有特定的傳播模式與群體內部的運作機制。[參見王敏芝、李珍:《媒介文化視域中的粉絲話語權增強機制及文化反思》,載《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111頁。 ]其中,較大規模的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常常衍生出組織分工明確、流程完整嚴密的應援體系,主要分為三類:一是數據類,為偶像炒話題、刷微博、刷排行榜名次,支持偶像新作品的各類排行榜名次;二是維穩類,成立“輿情組”監控對偶像的負面評價,成立“反黑組”為偶像洗刷負面新聞;三是消費類,為偶像斥巨資慶生、購買偶像代言的產品等。[參見胡泳、劉純懿:《現實之鏡:飯圈文化背后的社會癥候》,載《新聞大學》2021年第8期,第67頁。]依據不同的分工,粉絲被定為前線粉、數據粉、氪金(花錢)粉等。[參見童祁:《飯圈女孩的流量戰爭:數據勞動、情感消費與新自由主義》,載《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第74頁。]“粉頭”常常有計劃地號召粉絲通過長時間不斷地發帖、點贊、轉發、評論等方式生產內容,擴大言論的作用與影響范圍。粉絲在“粉頭”的組織下,有組織地對涉及偶像信息的評論進行審查,并不斷對偶像的負面內容進行匯總,通過“反黑”操作壓制或消除負面內容。[參見張世超、胡岑岑:《粉絲、平臺、資本與國家:多元互動視角下的飯圈反黑及其治理》,載《學習與實踐》2021年第7期,第134頁。]這一操作會在自由的社交平臺中對持有不同意見者造成群體性壓力。微博上,即使有些網友愿意針對某位明星發表不同于粉絲主流意見的個人觀點,有時也不得不用明星人名拼音縮寫的方式進行指代,以避免粉絲的搜索以及與之相伴的網絡暴力。粉絲們常常將個人好惡凌駕于事實和法律之上,在“粉頭”的帶領下“人肉搜索”侵害他人隱私;言語越界損害他人名譽;頻繁投訴與舉報,突破文藝評論的界限;而多元化的評論往往淹沒在粉絲為做數據形成的組織化、模板化的刷屏中。在外界看來,粉絲們重復的復制粘貼模板、機械的打卡是集體無意識的非理性行為,但這樣的操作符合商業社會中的流量邏輯,是粉絲群體在數據審查與生產中滲透著的“理性”考量。[同上注,第137頁。]
二、“飯圈”負面行為的產生原因
(一) 資方控制與平臺打榜的主導
“飯圈”存在一種獨特的控制結構,核心決策層往往由打造藝人的出資方,即藝人的經紀公司(工作室)掌控,資方控制力強且隱蔽。他們向“飯圈”開放文化運作的邏輯,而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在傳播鏈條中,常作為管理層、推廣層而存在。打造明星的資方往往與“飯圈”中的“粉頭”聯系密切,有些直接是明星團隊成員,他們會參與到明星行動策劃創意之中,消息靈通,在粉絲群體內部發揮類似意見領袖的作用。“飯圈”內部,資方常能控制或影響意見領袖,意見領袖控制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控制“飯圈”成員,“飯圈”成員影響媒介事件,媒介事件影響算法、流量,算法、流量把控社會關注。[參見孟威:《“飯圈”文化的成長與省思》,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19期,第55頁。]這一過程中,明星公司(工作室)常進行專門的數據統計,在特定時間推出顯示明星排名的統計數據鞭策粉絲打榜。建立明星流量的監測體系,實時衡量明星的商業價值。對于經紀公司(工作室)而言,基于熱度、流量和數據的明星號召力和粉絲購買力是資方獲益的重要來源。[同上注,第55-56頁。]
除了資方對“飯圈”的控制外,社交平臺也是主要獲益者。以新浪微博為例, 2016年微博推出的“微博超話榜”“明星勢力榜”,增強了微博用戶的互動活躍度,活躍度與流量直接掛鉤。作為主要的社交平臺,粉絲們在微博上幫助偶像反黑、做數據、刷流量,偶像也相應地對粉絲的行動進行回應,形成雙向互動關系。[參加姜雯嘉:《傳播視域下的“飯圈文化”探析》,載《東南傳播》2019年第6期,第52頁。]微博的產品機制和平臺邏輯給予粉絲巨大的操作空間。[參見胡泳、劉純懿:《現實之鏡:飯圈文化背后的社會癥候》,載《新聞大學》2021年第8期,第69頁。]
近幾年,除新浪微博以外,各大互聯網頭部企業與平臺也參與到粉絲經濟中,競相推出各類打榜榜單,涉及社交媒體類、音樂播放類、視頻播放類、專門追星類、綜藝節目類。這類榜單絕大部分是簡單的人氣、財力比拼,缺乏對作品質量、專業水平內容的鑒別。打榜形式主要是增加粉絲在平臺內的活躍度,如完成簽到、發帖、點贊、評論等任務以及花錢購買應援物、助力值等方式,幫助偶像提升排名。大量榜單都涉及粉絲“花錢買投票”的環節,平臺或節目組通過規則制定,引導、鼓勵網民采取購物、充會員等物質化手段為選手投票助力,而打榜的福利體現在平臺為上榜偶像提供廣告展位、流量曝光、資源推廣的機會方面。由此,平臺通過較多的用戶數與較高的活躍度,獲得更多的廣告和營銷收入,而代表用戶活躍程度的流量,有助于偶像的出道或保持已出道偶像的熱度。這是粉絲們為偶像打榜投票、操控評論、非理性消費的誘因。為追求經濟利益,各平臺將榜單分為周榜、月榜、年榜等,不斷刺激粉絲打榜,進行數據勞動與情感消費,粉絲情感被數據量化,成為供給資本和流量的源泉。
非理性的打榜、消費是商業、媒介共同運作與構建的結果。資方控制與平臺打榜的主導促進了“粉絲經濟”的發展,使其呈現出生產者對消費者情感、認同的收編和商品化。[參見楊玲:《粉絲經濟的三重面向》,載《中國青年研究》2015年第11期,第13頁。]非理性的消費與數據至上的追星價值觀加劇了“飯圈”的混亂與無序,這背后的商業利益正是偶像得以大量制造、迅速發展,平臺廣泛參與的動因。
(二)藝人與“飯圈”組織者的推動
流量與數據是衡量明星商業價值的指標。為取得廣告代言、影視歌曲資源,賺取“粉絲經濟”的紅利,藝人需要流量與數據,而流量與數據熱度需要粉絲應援支持。粉絲的熱情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工具。在藝人經紀公司(工作室)、“飯圈”組織者的鞭策下,粉絲自愿花費時間、精力、金錢為偶像應援,迎合了藝人及其團隊的需求,藝人自身缺乏正面引導“飯圈”成員行為的動力。“偶像”這種符號應當承載的精神引領或先進性的價值要素被忽視。[參見王敏芝、李珍:《媒介文化視域中的粉絲話語權增強機制及文化反思》,載《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114頁。]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不少藝人偷稅漏稅,簽訂陰陽合同,進一步助推了文娛行業的混亂。
“飯圈”組織者不僅擅長組織溝通、媒介使用、社會公關等技能,也是“飯圈”規范的制定者、行動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參見趙麗瑾:《粉絲社群的組織結構與動員機制研究》,載《現代傳播》2020年第8期,第155頁。] “飯圈”行為受組織者直接影響,也為組織者帶來經濟收益。他們常常發起“飯圈行動”,號召粉絲進行數據勞動、情感消費、應援集資、公益參與。有時還會蓄意挑唆不同“飯圈”間的對立,故意制造流量與明星熱度,擾亂公共秩序。“飯圈文化”呈現出盲目、排他、打壓異己、索取奉獻的特征。組織者往往要求粉絲對偶像絕對崇拜,不允許對偶像的任何批評、質疑;引導粉絲人肉、控評、舉報;要求粉絲出錢出力,否則就是不愛偶像。其中,粉絲常被要求購買多份相同的唱片、消費同一影視歌作品,以證明他們對偶像的愛與奉獻。[參見倪弋:《治理“飯圈”亂象,凈化網絡環境》,載《人民日報》2021年5月13日,第19版。]
當辨識力較弱的低齡人群加入追星群體時,持續聽取這些意見,不僅容易相信這些立場,也難免極為在意群體中其他個體或肯定或批評的態度。在組織者的宣傳與控制下,“飯圈”內部呈現出“粉頭”“大粉”負責發布任務、組織指揮,粉絲不辨是非、負責執行的現象。
(三)粉絲的參與及沉浸
“飯圈”作為一個具有共同情感聯系的網絡共同體,它的形成源于粉絲對偶像身體、心靈的認同。在認同中,有些粉絲在偶像身上看到自己已有或想要擁有的素質、特征,把偶像看作是想要成為的自己,形成一種自我投射;或將個人對父母、配偶等的情感和態度轉移到偶像身上,自我移情;或者作為一種心靈空虛、情感缺失的自我補償。[參見曾慶香:《“飯圈”的認同邏輯:從個人到共同體》,載《學術前沿》2020年第19期,第16頁。]在自我投射、自我移情和自我補償的心理機制下,實現從偶像認同到群體認同的發展。一方面,隨著社交平臺的廣泛運用,“飯圈”與“偶像”之間有了互動空間,粉絲有了接近“偶像”的可能性,追星方式呈現出“參與感”與“沉浸式”的特點;另一方面,粉絲們常常通過各種媒體內容不斷加深自己對所喜愛偶像的情感。她們將自己制作的與偶像相關的文字、圖片、視頻稱為“物料”,豐富的“物料”可以幫助她們構建起內心對偶像全方位的幻想。這些“物料”一定程度上充當了粉絲和偶像之間的橋梁,物料越豐富,想象越真實,粉絲也越沉浸,情感隨之也越深厚。粉絲們通過匯集偶像的信息,交換意見、分享和構建彼此的創造性工作,建立起一種對明星角色的解讀并達成接近于共識的理解。在認同機制的影響下,粉絲不惜花費時間、勞動力與金錢、保持或提高偶像人氣,在消費主義中做出了權衡并獲得自己所渴望的媒體體驗、產品與對偶像情感的滿足。
“飯圈”行為的產生不僅是粉絲和偶像的雙向互動,也包含著資方控制與平臺打榜的主導,明星經紀公司、“飯圈”組織者的推動,粉絲自身的參與及沉浸。而媒介技術的進步與發展,也賦予了粉絲文化表達的話語權力與傳播渠道,激發出粉絲的數據生產能力、文化消費能力與文本生產熱情。[參見張建敏:《媒介技術驅動與粉絲文化表達變遷》,載《現代傳播》2019年第4期,第34頁。]“飯圈”行為的產生呈現出多方因素參與交織與相互聯結的影響。
三、“飯圈”負面行為的危害性
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的獨特方式表達對偶像的崇拜。以打榜、控評、舉報、狂熱消費、“做數據”等非理性方式追星的流量“飯圈文化”,成為當代青少年追星的主要方式,而這一系列行為不僅損害了公共秩序,也有悖善良風俗。公共秩序,不僅指政治的公序,也包括經濟、文化領域的基本秩序與根本理念,與國家、社會整體利益密切相關。[參見黃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總則編·物權編),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頁。]善良風俗是基于社會主流道德觀念的習俗,是作為社會、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是特定社會所應尊重的起碼的倫理要求。[參見王軼:《論民法諸項基本原則及其關系》,載《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第96頁。]
(一)違背公序
1. 擾亂公共傳播秩序
首先,粉絲們的追星行為會影響公共傳播秩序。粉絲們通過“蹭熱點”、制造話題等形式干擾輿論,通過雇傭網絡“水軍”“養號”形式刷量控評。這不僅違背了誠信原則,不利于營造健康的評論生態,也有礙社會公眾的信息獲取。2018年8月,藝人蔡徐坤發布一條微博,10天內微博累計轉發量達1.04億次。當時,微博月活用戶4.46億,如此異常的數據引發社會對藝人流量數據真實性的質疑。粉絲不斷制造的明星話題、閱讀與收視奇跡與流量數據,讓演藝市場數據造假、重流量、輕質量的風氣盛行。僅以流量作為衡量偶像與作品的標準,不僅扭曲了行業環境與生態,也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了藝術標準。過度娛樂化、同質化甚至低俗化的作品充斥市場,劣幣驅逐良幣。其次,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移動互聯的興起,平臺與網絡新媒體對信息、資訊的報道、推送也呈現出狹隘性特征,引發“信息繭房”效應。在“泛娛樂化”的輿論環境里,出于商業考慮,平臺和網絡媒體積極向用戶推送明星八卦、隱私和緋聞。除此之外,根據人氣、用戶搜索歷史、興趣偏好分析的移動端個性化智能算法推送應用廣泛。算法推薦機制在個性化的旗號下,背離了多元信息傳播的初衷,會將用戶裹挾在基于自身屬性、興趣、社交關系的“過濾泡”中,沉浸在相似觀點與意見的信息流中,對外部世界愈發不敏感。[參見方師師:《算法如何重塑新聞業:現狀、問題與規制》,載《新聞與寫作》2018年第9期,第17頁。]公眾常常關注的是自己感興趣的內容與使自己愉悅的領域,這種信息選擇與基于算法的信息推送會將用戶桎梏于“信息繭房”[參見[美]凱斯·R.桑斯坦:《信息烏托邦: 眾人如何生產知識》,畢競悅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頁。]。長此以往,多元觀點的傳播會受到影響,用戶信息接收與觀念表達也易窄化。一旦設計開發者在算法中加入過度的商業追求、價值偏好,那錯誤的信息將不斷得到傳播,憑借算法侵蝕大眾權益的情況就會變得日益普遍。[參見馬長山:《人工智能的社會風險及其法律規制》,載《法律科學》2018年第6期,第51頁。]對青少年而言,這一影響尤甚。大量青少年以追星為目的在網絡空間聚集,明星話題的過度推送,平臺基于算法對其它內容的協同過濾,會導致青少年接收的信息愈發的同質與窄化,缺乏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與思考,造成信息結構的失衡。平臺從自身商業利益出發基于算法的信息推送,操縱了大眾對輿論的關注、審美情趣與消費心理。單邊化的算法權力需要合理制衡與限制。
2.網絡暴力與隱私侵害
只要存在資源爭奪,不同“飯圈”間就易于互相敵對,而群體內則往往同仇敵愾,呈現出極強的凝聚力與排他性。粉絲們往往容不下任何對偶像的批評與對競爭對手的表揚,盲從地發表不當言論,貶低與其偶像有競爭關系的其他明星的名譽。不同“飯圈”的粉絲們常常相互攻擊,人肉搜索、侵害名譽、侵犯隱私等行為頻頻出現。
以青少年為涉嫌侵權主體的網絡侵害名譽權行為,集中出現于從事演藝工作的公眾人物名譽權侵權案件中,青少年作為其中的參與主體常常主張“飯圈”文化已形成共識,應放寬法律評價標準;主張轉發內容并非原創,無需擔責;認為發布的言論在網絡上已經傳播,法不責眾等。這類案件立案后,涉訴被告常常受到同一“飯圈”的聲援;結案后,有的被告繼續在網絡空間發表不當言論,持續受到粉絲追捧。更有甚者,在訴訟期間,所屬粉絲群體為其發起“打賞”活動,組織粉絲為其籌款。這些認知,反映出行為主體法律意識的淡薄。
雖然“人肉搜索”客觀上能對違法行為產生震懾作用,但“人肉搜索”也必然帶來網絡暴力,名譽、隱私被侵犯等問題。[參見戴激濤:《從“人肉搜索”看隱私權和言論自由的平衡保護》,載《法學》2008年第11期,第40頁。]表達自由雖然來源于憲法確認和保障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但當言論的理性程度和真實性降低,呈現出情緒宣泄性的非理性表達時,它們不僅不是達成共識的基礎,反而成為導致社會分裂和沖突的催化劑。[參見張燕、徐繼強:《論網絡表達自由的規制——以國家與社會治理為視角》,載《法學論壇》2015年第6期,第79頁。]名譽侵害、隱私侵害、人肉搜索等網絡攻擊行為無益于任何理性的討論,帶來的是對個體人格權益的侵害,促成的是輿論場的撕裂,而這種撕裂還會向圈外公共生活蔓延。
(二)妨礙公序良俗
首先,飯圈內部消費主義、拜金主義盛行。“飯圈”中不乏粉絲攀比炫富、奢靡享樂的行為。明星偶像作為粉絲崇拜、認同、模仿的對象,粉絲們不僅易模仿他們的妝容、服飾,還易模仿他們的生活方式。偶像崇尚享樂主義、奢侈消費的拜金行為會給粉絲帶來錯誤的示范效應。粉絲的行為,除了受到來自偶像的影響,還容易受到平臺、“飯圈”內部成員的鼓動。在“飯圈”人眼里,沒有消費的崇拜與追星會被看作是一種廉價和不堪,會被扣上“你沒資格粉他”之類的帽子。[參見馬赫:《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與重構路徑研究》,吉林大學2020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31頁。]對物質消費的重視使得消費主義充斥在追星活動中,更有甚者將粉絲打榜與金融捆綁。例如,微博旗下網貸產品“微博借錢”曾以提升點贊倍數的方式誘導微博用戶開通并使用其產品。[2019年“微博借錢”發起的“好物紅榜”中,每個用戶可選擇上傳自己想分享的商品,集贊、使用“微博借錢”都會幫助用戶提升打榜名次。使用“微博借錢”金額越高,獲得的點贊數越高。這一活動吸引了眾多粉絲的參與,粉絲們希望借此提升偶像及其商業代言產品的人氣。]青少年在網絡平臺借錢后,給明星集資、送“粉絲應援禮”“借貸追星”現象蔓延。
其次,群體最廣泛的互動塑造了“飯圈”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參與性,但“飯圈”并未形成以對話、傾聽為特征的環境。絕大多數粉絲可以自由參與、配合群體活動,但卻無法參與群體的決策過程,絕大多數“飯圈”成員通過開放的途徑卷入“造星”運動,增加或減少明星的流量,他們的時間、精力、金錢與投入其中的智力創造被無條件占用,所享有的僅僅是平等參與的幻象。與此同時,“飯圈”內部,粉絲針對偶像的勞動付出與購買消費不再遵循自愿的原則,成為帶有束縛性的義務。付出時間的長短與金錢的多少會和“你究竟有多愛他”掛鉤,給粉絲帶來沉重的精神與經濟負擔。
最后,“飯圈”成員的行動邏輯與處事規則也可能損害和諧、誠信、友善的社會環境。“飯圈”的爭斗,看似僅是內部爭執、無關大局,但實際上 “飯圈”裹挾青少年開展的每一次爭斗,都是對良善價值觀念的背離,有違誠懇待人的道德傳承與互相尊重、和睦友好的社會理念。“飯圈”的運作模式,越是高效可復制,對社會越有害。當下,“飯圈”青少年成為明星背后娛樂資本爭搶注意力資源的利器,其思維、行動、價值觀都深受影響。
四、“飯圈”治理的法律實現路徑
2021年6月,中央網信辦開展為期2個月的“清朗·‘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采取了清理負面有害信息、處置違規賬號、關閉問題群組等措施。2021年8月25日,《中央網信辦秘書局關于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中提出了取消明星榜單比拼、嚴管明星經紀公司、清理違規群組板塊、嚴控未成年人參與等舉措。2021年9月2日,中宣部針對流量至上、“飯圈”亂象、違法失德等問題印發了《關于開展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提出應堅持核心價值觀引領、規范市場秩序、強化行業管理、探索完善制度保障、推進依法治理等要求。 “飯圈”治理,需長效機制依法展開,其核心是通過法律的治理,這將有利于形成穩定的規則與良好的治理效果。
(一)合理確定平臺的公共責任
平臺由私人設立并運營,追求商業利潤無可厚非,但隨著移動互聯的高速發展,平臺在事實上已成為大眾參與公共活動的重要場所,具有了公共屬性。[參見高薇:《互聯網時代的公共承運人規制》,載《政法論壇》2016年第4期,第89頁。]影響力巨大的平臺并非普通的市場經營者,也不是純粹的提供信息的居間服務者。[參見劉權:《網絡平臺的公共性及其實現——以電商平臺的法律規制為視角》,載《法學研究》2020年第2期,第43頁。]它們不僅通過產品開發和功能設計,吸引著大眾的關注,引導著輿論的走向與人們的行為,還通過制定大量規則,管理著用戶,對用戶間的紛爭進行處理,行使著準立法權、準執法權、準司法權。[參見許可:《網絡平臺規制的雙重邏輯及其反思》,載《網絡信息法學研究》第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118頁。]平臺在自己搭建的網絡空間里,履行著相應的管理職能,但作為追求商業利潤最大化的市場主體,平臺也易濫用自己的權力。平臺有責任維護公序良俗,將私領域的利益訴求與公領域的社會公序相融合,承擔起維護網絡市場秩序,保障用戶權益的公共職能。
1. 優化算法
當下,通信技術的發展與變遷呈現出通信技術本身的不透明性,用戶信息接觸的封閉性等特點。這一過程會涉及互聯網公司的排序算法、網頁內容生產、基于用戶使用習慣的個性化推薦,其中必然存在對用戶喜好的利用、迎合自身商業利益的考慮。在信息獲取民主化的表象下,商業對知識、信息的控制從明處走向暗處,變得難以察覺。這種誤導加劇了信息的非均衡分發,推動著錯誤信息的傳播。[參見[美]伊萊·帕里澤:《過濾泡:互聯網對我們的隱秘操縱》,方師師、楊媛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導讀。]信息資訊類平臺不應為泛娛樂化推波助瀾,基于算法的信息分發應當為大眾提供各類有益信息,在提高生產、生活效率的同時,促進視野開闊、思想進步。基于此,避免明星話題、明星緋聞、低俗信息的過度推送,是當前追星治理中需面對的重要議題。應對此類行為進行嚴格規制,避免個體陷入算法的信息宰制。對算法應采取場景化的規制路徑。[參見丁曉東:《論算法的法律規制》,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第138頁。]平臺應抵制暗箱操作的沖動,接受公眾一定程度的參與和監督。對采用個性化算法推薦技術推送信息的平臺應貫徹用戶自主選擇機制,互聯網平臺運營商有責任說明其對信息聚合、篩選、排序后,進行個性化推送的機制和效果,用戶有權自主選擇是否接受個性化信息的推送。互聯網公司有義務也有能力將公共利益納入自身的考慮范圍,推動算法的成熟。對算法分發可能存在的信息偏向的糾正,不僅是保障用戶參與權、社會公眾知情權的先決條件,也是平臺獲取公眾信任的重要途徑。
2. 從“通知—取下”規則到平臺的內容管理義務
“通知—取下”規則最初規定在美國《千禧年數字版權法》中,經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借鑒和移植后,于2009年制定侵權責任法時第一次在民法中確立,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1195條中予以保留。[參見黃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侵權責任編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頁。]這一制度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在接到侵權通知后,根據情況采取移除或屏蔽等措施,違反此義務,應承擔侵權責任。法律制度的這一安排設計體現出對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商業運營規制的寬容。隨著自動化過濾技術的發展,網絡平臺介入用戶信息的成本被大大降低。通過技術措施實現對不良內容的自動過濾、識別和攔截,成為提高互聯網內容治理能力的重要舉措。考慮到平臺的公共屬性與所擁有的技術能力,平臺應負擔內容管理義務。既有的“通知—取下”規則并不排斥法律對平臺內容規制能力的合理利用。平臺應采取“技術過濾+人工復審”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復制、發布含有炒作明星緋聞、丑聞、劣跡與宣揚低俗、庸俗、媚俗的內容,及時識別流量異常的操作與宣揚仇恨、網絡暴力、人肉搜索、操縱賬號等違法活動。豐富干預、懲治違法行為的具體舉措,破除平臺主導的唯流量論,抑制資方主導的過度營銷。合理的平臺義務設置需平衡互聯網內容合法、商業自由與創新和用戶權利保護間的價值。當然,法律應做出符合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非不計成本的追求一種正義。[參見熊秉元:《正義的成本:當法律遇上經濟》,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194頁。]在價值平衡間,平臺的內容治理應全面透明并滿足正當程序的要求。自動過濾技術只應適用于能通過機器和算法做出準確判定的違法內容。“技術過濾+人工復審”是保證算法過濾正確率的必要程序,而“通知—取下”規則中,侵權嫌疑人發出“反向通知”進行申辯的權利也依然適用。“反向通知”制度是編纂《民法典》中新增加的內容,規定在第1196條中。無論是技術抑或人工干預,都需要法律設置相應的監管反饋機制以確保權力不被濫用。[參見魏露露:《互聯網創新視角下社交平臺內容規制責任》,載《東方法學》2020年第1期,第27-28頁。]這當中不僅包含“反向通知”制度,也應包含平臺為刪除“飯圈”不當言論內容、采取屏蔽、封號等操作設立的申訴程序。平臺應創制透明、可實現的正當程序來維持刪除“飯圈”不當言論與保護表達權利間的平衡。這一責任的法理基礎既源自平臺是公共參與的重要場所、公共話語的組成部分,也源于平臺對用戶、社會負有的倫理責任。
(二)明確參與各方義務
1. 對藝人與經紀公司(工作室)的規制
(1)調整稅收優惠政策與巨額逃稅的刑事處罰
2018年國家稅務總局開展了規范影視行業稅收秩序的工作,但演藝領域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款等問題仍然存在。一些高收入的藝人通過拆分合同、將個人報酬轉為企業收入等方式隱瞞真實收入,偷逃稅款。不少藝人成立個人工作室,適用核定征收方式規避高額個稅。一些地方為吸引企業入駐,制定免稅、退稅、返還、補貼等稅收優惠政策。藝人在“稅收洼地”注冊工作室或企業,可以享受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稅收優惠。
應進一步加強文娛領域從業人員的稅收管理,藝人公司、工作室應依法履行納稅及代扣代繳稅款的義務,稅收征收應采用查賬征收方式。地方政府不應設置不恰當的稅收優惠政策,擅自向明星經紀公司(工作室)提供“先征后返”“等額獎勵”“即征即退”等稅收優惠,這不僅會形成對稅基的侵蝕,也會被刻意規避納稅義務的藝人與企業利用。此等舉措無法發揮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破壞稅負的公平性。再者,應加大對藝人偷漏稅刑事處罰的力度。我國《刑法》第201條第4款規定,五年內納稅人首次因逃稅接受行政處罰,且已補繳稅款、滯納金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這使得藝人巨額稅款偷逃的違法成本過低,難以形成有效威懾。需加大對藝人巨額稅款偷逃的處罰,可考慮劃定一個標準,對巨額稅款的偷逃,不再設置五年內首次因逃稅被行政處罰者,補繳稅款后免于刑罰的規定。
(2) 明確藝人、經紀公司(工作室)對粉絲的引導義務
首先,明星與經紀公司或工作室應嚴格約束自身的言行。近年來,明星吸毒、偷稅、酒駕、緋聞、代孕棄養、性侵等新聞,時常見諸報端。對于動輒擁有百千萬粉絲,對社會意見形成、所屬群體成員的言行有重大影響力的明星藝人,應以良好的藝德、優質的作品維護行業及個人形象,引領社會風尚。其自身不僅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自覺遵守社會公德,在職業倫理、個人品德上也應對自己嚴格要求。2021年2月5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演出行業演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法》,以行業自律懲戒的形式,規定協會有權在行業范圍內對“劣跡藝人”進行行業聯合抵制。除開行業自律,主管機構也應加強管理,構建起分級、分類常態化、制度化劣跡藝人的管理、處罰措施。另外,經紀公司(工作室)不應組織、策劃、號召粉絲刷量控評,這一行為不僅擾亂公共傳播秩序,也擾亂市場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構成不正當競爭。因這一行為引發的侵權責任,應由組織這一行為且具有經營者身份的經紀公司(工作室)承擔。
其次,明星對社會評價負有一定的容忍義務。作為公眾人物,明星隱私權是被限縮的,限縮部分與公共利益相關。以演藝明星為例,那些可能影響其社會形象的成長經歷、家庭背景、藝術成就等不應成其隱私。[參見李新天、鄭鳴:《論中國公眾人物隱私權的構建》,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5期,第98頁。]對社會評論,尤其是涉及對其業務能力、工作成果及自身不當言行的評論,即使出現了令人不快的用語,但表達內容若未明顯偏離公知事實,演藝工作者應當容忍。
最后,明星與經紀公司(工作室)對“飯圈”應負引導義務。由于“飯圈”低齡化現象的存在,明星與粉絲之間的獨特粘性,導致明星能對粉絲能產生顯著的垂范效應。雖經紀公司(工作室)對“飯圈”的組織、運作通常不同于具有嚴密組織架構的法人的管理和運營活動,但“飯圈”組織者往往與經紀公司(工作室)往來密切,新浪微博確立的官方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的認證,必需經明星及其經紀公司(工作室)的授權,強化了明星、經紀公司(工作室)對“飯圈”的控制力。明星與經紀公司(工作室)應禁止義務教育階段未成年人參加公司策劃、組織的偶像團組和應援活動;若粉絲群體出現拉踩引戰、惡意攻擊等非理性行為,應及時發聲,正面引導;對經其授權,在微博注冊的官方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的活動進行指引與約束;對有惡意行為的非官方粉絲組織和非理性行為,應及時與平臺溝通,配合平臺管理。明星與經紀公司對粉絲群體的非理性行為,若視而不見,任由事態發展,產生不良社會影響,需承擔引導不力的法律責任。
立法者應在公共利益、比例原則的引導下,以成文的規則,規定明星藝人與經紀公司(工作室)的義務,明確其引導青少年理智追星的義務;放任粉絲群體非理性,不加干預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時的責任;以及明星自身德不配名,產生惡劣示范效應時應面臨的處罰,減少粉絲群體擾亂社會公序不良行為的發生,以法律強制力的形式敦促公眾人物與經紀公司(工作室)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承擔法律責任。
2. 對“飯圈”組織者的規制
(1)雇主責任與教唆責任的適用
“飯圈”對圈外第三人實施的典型侵權行為,主要是侵害他人人格權益的行為,包括侵害他人名譽權,隱私權與信息權益以及肖像權等行為。“飯圈”中發揮策劃、引領作用的核心粉絲應被認定為組織者,其應當對侵權行為承擔責任,核心成員之間應承擔連帶責任。若經紀公司或工作室實際參與到“飯圈”行為的組織、策劃中,發揮重要作用、提供支持,亦可將其認定為組織者。當組織者與“飯圈”成員間存在支配關系時,組織者應承擔雇主責任;當不存在支配關系,但“飯圈”成員在組織者號召、說服、慫恿、幫助下實施侵權行為時,組織者應當承擔教唆或幫助侵權的責任。
雇主責任的適用,以組織者對“飯圈”成員具有一定的支配力與控制力為前提,不以雇傭為必要條件。“飯圈”的組織者往往可從組織活動中直接或間接獲益,“飯圈”組織者承擔雇主責任符合報償理論。考慮到“飯圈”組織在當下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不屬于《民法典》第1191條第1款所規定的“用人單位”,“飯圈”組織與其成員間不存在用工關系,“飯圈”組織者雇主責任的認定應類推適用1192條第1款關于接受勞務一方侵權責任的規定,不應適用《民法典》第1191條第1款的規定。
教唆或幫助侵權責任的適用,以“飯圈”組織者與“飯圈”成員之間不存在支配關系,但“飯圈”成員依然在組織者引導下實施與“飯圈”存在目的相適應的侵權行為為前提。如果被教唆的行為人是成年人,應適用《民法典》第1169條第1款的規定,教唆者與行為人一同承擔連帶責任。在舉證責任上,受害人只需證明教唆、幫助行為與受害人所受損害存在部分因果關系,無需證明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條件或完全原因。讓并未直接實施侵權行為的教唆人承擔連帶責任,強化了受害人獲得賠償的擔保。[參見鄒海林、朱廣新主編:《民法典評注·侵權責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9頁。]如果教唆的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應適用《民法典》第1169條第2款的規定,由教唆者承擔侵權責任。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未盡到監護之責任,承擔相應的責任。相應責任不是代替或免除教唆者、幫助者的責任,而只是承擔與自身失職程度相適應的責任,分配的通常是小部分而不是大部分。[參見張新寶:《中國民法典釋評·侵權責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頁。]這樣的安排,既有轉換部分因果關系為完全因果關系的功效,又可實現對未成年粉絲的保護。在監護人有過錯時令其承擔相應責任,不僅有利于督促監護人有效履行監護義務,也有利于受害人獲得損害賠償。
(2)行政制裁與刑事處罰的配套
僅追究組織者的侵權責任,并不充分,還需考慮行政處罰措施的配套。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應根據情況及時采取暫停發布、關閉群組等處置措施,主管機關應加強懲戒,視行為的影響程度,采取罰款、拘留等行政處罰措施。“飯圈”成員在“粉頭”的號召下,為發表不當言論的涉訴被告籌款、打賞的收入,應視為違法所得予以收繳。對“粉頭”“大粉”虛構應援活動項目,吸引粉絲參與,集資后卷款潛逃或者揮霍款項,致使款項無法歸還的,應追究其詐騙罪或侵占罪的刑事責任。對向粉絲下達的任務、指令涉及虛構或篡改關注度、瀏覽量、點贊量、交易量等數據的行為,不僅違背了公序良俗,也有違正當競爭;不僅擾亂正常經營秩序,也背棄了數據信用。2019年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確認了虛假流量的違法性,制造虛假流量可被評價為虛假宣傳行為,進而施以相應處罰。當流量造假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窮盡一般規制手段,仍不足以營造安全、有序、公平的網絡流量運營環境時,應考慮對組織者科以刑事責任。刑法上有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等罪名。刑法作為應對流量造假的最后手段,有助于構筑起流量造假的最后防線,對組織者的行為形成威懾。
(三)完善網絡舉報制度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舉報制度隨之興起。網絡舉報具有方便快捷、暢通高效、成本低廉、不受時空限制的優勢,有利于網民行使監督權。從個人層面看,舉報權[舉報權與檢舉權有差異。《憲法》第41條將檢舉權規定為一項憲法權利,強調公民對公權力行使的監督。舉報權沒有被納入憲法權利,其是指任何人將發現的違法違規、危險或不正確的信息和行為向組織內外進行披露的行為。《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大多使用“舉報”一詞,未對檢舉與舉報作區分。]制度的核心在保護公民毫無畏懼地行使言論自由權、監督權,披露關乎公共利益的信息,進而保護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從社會層面觀察,其有利于強化企業責任,維護社會公共安全和利益;從國家層面觀察,有助于加強政府監管,預防和打擊腐敗。[參見彭成義:《國外吹哨人保護制度及啟示》,載《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4期,第42頁。]然而,“飯圈”舉報頻頻發生,“飯圈”成員有組織地對網站、相關內容進行舉報的行為,已與公正監督無關,超出了維護偶像形象的合理限度與范圍,侵蝕了公共領域。
舉報制度的運用,并非毫無邊界。從國際公約與國外相關立法例來看,往往要求受保護的舉報人在舉報時主觀上是善意、客觀上有合理的理由,不允許誣告陷害。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理事會關于發展合作行動者以管理腐敗風險的建議》中強調,舉報應基于善意并具有合理理由。[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ctors on Managing the Risk of Corruption, art 7(i), (16 November), https://www.oecd.org/corruption/anti-bribery/Recommendation-Development-Cooperation-Corruption.pdf.]《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33條也規定,所保護的舉報人應是基于善意和合理理由進行舉報的人。[參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33條。]觀察舉報行為的動機會發現,有的舉報行為可能出于惡意或憤怒,為了報復;有的舉報行為源自做正義之事的崇高。從我國憲法和相關法律規定來看,未對舉報人主觀善意進行要求,僅在《刑法》第243條規定舉報人“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而錯告和檢舉不實不適用“誣告陷害”的規定。但如何區分誣告陷害與錯告及檢舉不實,尚缺乏具體的細化規定。
清晰的權利邊界對于公民舉報權實現機制的良性運轉不可或缺。對受保護的信息披露和受法律保護的舉報人的范圍應進行精確的界定。網絡舉報可以報告和保存舉報事件信息,以其匿名性減少舉報風險,但面對“飯圈”舉報蔚然成風的現狀,應考慮建立和實施誠信化網絡舉報制度,對惡意舉報人作出標記,記入個人誠信檔案。以此規范舉報者的行為,督促其謹慎行使舉報權利。除此之外,為避免舉報權利被濫用,還應有清晰的程序性指引、正當程序的保障、對舉報制度效用的定期評估。公民舉報、檢舉權實現機制的運行基礎,不僅應包含合格的公民,還應包含對公民監督權、知情權的保障和實現。一套完善的舉報制度,還應包括對惡意舉報、誣告陷害行為的懲戒與有效制約。
(四)賦予粉絲組織民事主體身份
新浪微博上的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常常表現為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兩種形式。一個熱度較高的藝人,常常存在官方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用以連接國內外各地的分支機構。體系化的官方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往往作為唯一對接明星經紀公司的粉絲機構,在粉絲應援消費、集資、做數據、控評、做公益等方面都擁有龐大的流量控制力,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力。這一基于互聯網形成的自發組織,已進入精細化運營的階段,其內部組織架構清晰、運作高效、動輒擁有百千萬成員,但這一組織在民法典民事主體的制度安排中卻找不到對應的主體地位。現行制度安排,無法對這一組織進行有效引導與有序治理。
為了更好地宣傳與支持偶像,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常組織粉絲為偶像捐款,由于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不具有民事主體的資格,應援款往往最終都匯入發起人賬戶中。現實中,發起人不按預設目的使用錢款、錢款流向不明、發起人攜款潛逃等事件層出不窮。應援集資法律關系中,粉絲自愿出資行為屬附條件捐贈,具有委托代理的特征,這一行為本身并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但應援資金的用途應遵循社會公序,未成年人的應援捐款更應受限制。現實中任何一個粉絲都可發起集資應援,絕大多數應援集資項目都帶有盲目性與沖動性,缺乏具體用款計劃和對資金實際用途的監管。通過平臺募集資金,平臺可從中獲利,卻通過免責條款的設置規避責任,要求粉絲自行對項目風險進行判斷,而缺乏對發起人的審查機制。這種全靠集資發起人自律的模式,潛藏著道德與法律風險。
明星粉絲團或后援會可獲得民事主體資格后,可名正言順地參與民事活動,捐款人可將資金打入組織體賬戶,組織體嚴格按捐款目的合法使用捐款資金,內部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定期進行財務公示。若出現組織成員變更,也不會影響錢款的歸屬。捐款的粉絲對組織體是否履行捐款所附特定義務享有知情權與監督權,當其不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未按照應援目的使用集資款項時,不僅可撤銷贈與,還可追究其法律責任。
自民政部《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2000年)頒布后,民間組織、經營組織的設立需要經過批準、登記的程序,若沒有經過批準、登記,國家采取的是禁止、取締的態度。[參見肖海軍:《民法典編纂中非法人組織主體定位的技術進路》,載《法學》2016年第5期,第31-32頁。]《民法典》第103條規定,非法人組織的設立,應當經過登記,一些特殊的非法人組織的設立還需要經過有關機關批準。因此,如果立法安排考慮將粉絲組織納入非法人組織的類別,唯有通過登記、批準,方能解決主體資格問題。當然,立法安排還可以將粉絲組織納入社會團體法人序列。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3條的規定,成立社會團體,除應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并依照本條例規定進行登記外,社會團體還應具備法人條件。這一規定排除了非法人社會團體的存在可能。[參見陳甦主編:《民法總則評注(上冊)》,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54頁。]相較于將粉絲組織歸入非法人組織的類別,將其歸入社會團體法人的類別更能激發設立人的設立熱情,因為設立人在組織體的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無須承擔無限責任。但當下,不論社團領袖想將粉絲組織登記為社團法人或是非法人組織,都不可行。這一組織的主管單位與登記機構是不明確的,現實中其無法取得民事主體資格。立法需要為現實多樣性保留足夠的空間,粉絲社團民事主體身份的缺位,擋住了對其進行有序治理的進路。賦予粉絲組織民事主體的資格,這不僅有利于國家對這類組織進行有序引導與治理,也將有利于這類組織內部信息的充分公示與對社會交往的保護。否定這類組織民事主體的地位,將無法解決此類組織的財產歸屬、對外代表、對外責任承擔、成員發生變動時組織穩定性等問題。
(五)遵循《民法典》優良家風條款
公民素養的培育及獨立精神的塑造須從家庭生活中生根、制度保障中發芽。但長期以來,孩子的選擇傾向與偏好往往被父母權威所壓制與超越。家庭內部的控制、壓制會直接或間接影響被監護人健康、獨立人格的養成。《民法典》在1043條增加了“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的倡導性規定,并在此條中進一步強調,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關系”, 將包括優良家風和家庭美德在內的家庭文明建設上升為《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倡導性規范,是法律與道德共同作用于家庭建設,促進家庭關系和諧發展的體現,也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民法典立法的具體實踐。[參見薛寧蘭、謝鴻飛主編:《民法典評注·婚姻家庭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頁。]
親屬關系具有濃厚的人倫色彩,優良家風條款的入法為改變家庭內部的教養方式奠定了制度基礎。孩子們的獨立思考和某些決策的能力往往與其依賴性并存,父母應認識到他們在依賴成年人的同時有能力為自己做出一些決定。有實證研究也支持兒童具有相應決策能力的主張。[Elizabeth S. Scott, Judgment and Reasoning in Adolescent Decision Making, 37 Villanova Law Review 1607,1627 (1992).]家庭內部應遵循民法典優良家風條款的指引,盡量給予孩子尊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5條也鼓勵父母以符合兒童不同階段接受能力的方式適當指引兒童行使公約規定的權利。應重視孩子們在父母引導下為自己決策的價值。那些在重視控制、強調服從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飯圈”成員,不僅易對組織者惟命是從,也更易在偶像身上追逐虛假的親密關系,出現對偶像的直接性模仿、全盤性接受、沉湎式依戀。[參見岳曉東:《追星與粉絲:青少年偶像崇拜探析》,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頁。]
父母對未成人的控制應轉化為一種出于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引導。父母作為監護人,在民法典優良家風原則的指引下,應將重學、仁愛、謙讓、友善等優良品格傳承給孩子,培養他們健全的人格與人文關懷的精神,避免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癡迷地投入到一場場無盡的偶像追逐中,難辨是非、難以自拔。
家庭是人生的起點,也是傳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起點。家事領域的制度安排應反映出對孩子依賴性和自主性共存的尊重以及對他們身體及精神漸進發展的認知,對成人權威施以限制,培育孩子的獨立精神與明辨是非的能力。
結語
“飯圈”既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中立、開放的環境,將有助于粉絲走出“飯圈”的禁錮,逐漸成為獨立、自主、成熟的個體。平臺內容治理的目標之一應是更多基于事實的講話,當經紀公司(工作室)、藝人能以身作則,“飯圈”組織者依法行為,網絡舉報回歸法治化軌道,粉絲組織能被有序引導與有效治理,大量青少年可以成長為理性公民時,“飯圈文化”則鮮有生存土壤。
制度的供給,應通過創造一個為青少年探索性學習與成長提供機會的環境來引導他們的發展。家庭、社會、國家應各自承擔責任,共同增強青少年的人文、法律與數字素養,促進他們的人格發展,提升他們交流、傾聽、表達、協作、參與社會的能力,更好地豐富、促進青少年當下與未來的生活,降低他們對偶像的虛榮欲望與浪漫幻想。希望通過制度的配套與社會整體的配合,青少年可以對自我的人生規劃充滿激情,靠自己的努力開創美好的人生。
On the Regulation of Fandom: a Legal Perspective
LI Yua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chaos such as the frequent complaints and reports to suppress dissidents, fanatic consumption, data fraud, disordere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merged frequently in fandom. The caus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irrational supporting behaviors include capital control, the dominance of platform rankings, the promotion of celebrities and fandom organizers, and the involvement and indulgence of fans. Its consequences erode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social customs, which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regulated. We must reasonably set platforms content governance obligation, adjust criminal penalties for celebrity’s huge tax evasion, clarify the celebrity’s duty to guide fans, distinguish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organizer’s infringement rules, improve the online reporting system, carry forward the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values, and give fans organizations a civil subject status.
Key Words: fandom; public orders and bonus mores;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本文責任編輯:董彥斌
青年學術編輯:任世丹
收稿日期:2021-12-01
作者簡介:李媛(1985),女,四川雅安人,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