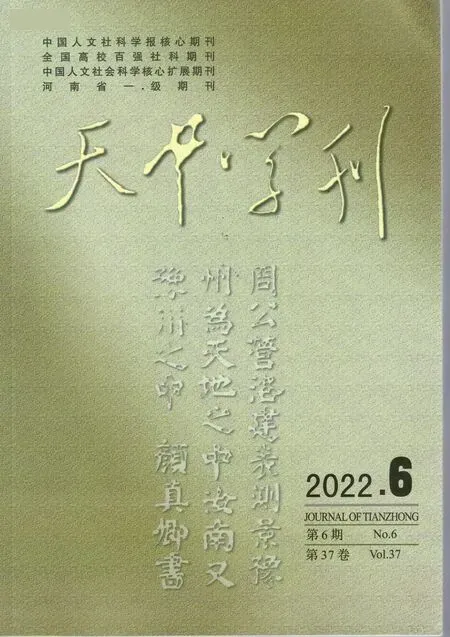近20年國內文化研究若干熱點問題研究述評
呂若玫
近20年國內文化研究若干熱點問題研究述評
呂若玫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0)
文化研究在我國登陸后,旋即引起了人文學者的關注,它對既往文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徹底反叛也引發了學界熱議。2000年以來,國內學者就文化研究的學科屬性、大眾文化等問題展開激烈辯論,后者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持續數年。文化研究不能滿足于譯介抑或因襲西方理論,而要以一種關懷當下的眼光反察并超越自身,進而形成對人文社科領域的廣泛影響。
文化研究;學科屬性;“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中國經驗
1999年8月,《南方文壇》第71期刊登了《關于今日批評的答問》一文。該文設置了關于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的4個問題,收到了54份回答,有20位相關人士參與,包括童慶炳、謝冕、陳思和等高校教授以及謝有順、賀紹俊等報紙編輯。可見“文化研究”是當時學術界的熱點話題之一。文化研究的草創者是以雷蒙·威廉斯、斯圖亞特·霍爾等人為代表的20世紀50年代英國伯明翰大學的一批學者,他們普遍認為“權力”這一概念居于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因此,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題圍繞著階級、性別、種族等方面展開,并引申出有關通俗文學、大眾傳播、性別與種族沖突、文化身份認同等問題的思考[1]。在文化研究關注的幾大領域,如大眾文化、性別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研究、文化產業、傳媒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等,多位學者已發表出版了成果扎實的相關文章和專著,各類“概論”“導論”類教材中也有詳細的專題介紹。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在梳理和概括的基礎上,從2000―2020年間國內發表的文化研究論文中選出具有典型意義的論題,以期反映近20年國內文化研究的發展歷程。
一、文化研究的學科問題
(一)文化研究自身的學科屬性之爭
在探討學科屬性之前,需要對文化研究的形態予以闡述:同大多數文學概念一樣,“文化研究”并無一個準確而統一的定義,研究者大多采取一種模糊化的描述策略。例如,羅鋼和劉象愚認為:從研究對象上看,文化研究并不涉獵那些經過歷史沉淀、具有“精英”屬性的經典著作,而更注重以影視為媒介的當代大眾文化、非主流的“邊緣文化和亞文化”,尤其“關注文化中蘊含的權力關系及其運作機制”[2]1。金元浦將文化研究的要點歸結于“對‘關系’的深度關注”:“由‘關系’尋求‘聯結’、‘協同’或‘共識’”,保持自身多元獨立性和更大發展的可能[3]。以上說法大致勾畫出了文化研究的概貌,如果進一步對它做一個學科屬性的劃分,不難發現,文化研究的核心思想,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后結構主義等學說之上,概念之龐雜,注定使文化研究不容易獲得一個清晰的學科定位。因此,文化研究具備跨學科,甚至反學科的屬性。正如詹姆遜在《論“文化研究”》一文中所說,文化研究最好被當作“一項促成‘歷史大聯合’的事業,而不是理論化地將它視為某種新學科的規劃圖”[4]。
從《學科化:文化研究的必然選擇》《文化研究學科化即末途之旅?》《文化研究:學科抑或策略?》《文化研究:在體制與學科之間游走》《文化研究與反學科的知識實踐》等文章標題可以看出,文化研究無法歸入任何一種既有的學科建制,它的出現顛覆了傳統的學科理念,在“學科化”這一問題上甚至出現了截然對立的兩種態度。文化研究的學科屬性之爭,深層原因在于學科體制和文化研究兩者內部固有屬性的矛盾。華勒斯坦等學者指出,學科“是以一定的措辭建構起來的歷史產物”“代表了知識和權力兩方面的結合”[5]。僅這一點就違背了文化研究的初衷。質疑權威、拒斥規范、貼近大眾、對抗權力,是構成文化研究的底色;而學科化所要求的學術標準、學術規范以及大學學科建立起來之后的學院制度化運作,讓人有理由對文化研究的未來產生疑慮:學科化的文化研究是否會逐漸走向封閉化和經院化,參與和批判現實的功能大大弱化乃至喪失,進而與象牙塔里的文學研究一般無二?
盡管如此,西方和中國共同面對的情況是,反體制化、反學科化的文化研究正逐漸走上體制化、學科化的道路。陶東風坦言,文化研究可以不被視作一門學科,但是在當前的學術生態和文化研究機構生存狀況下,研究者的“學術背景及體制化身份”、研究場所“都建立在高校或官方研究機構內部”,使得“非學科化”的自我標榜成為一句空談[6]。其實這也不足為奇。事實上,文化研究的相關機構和中心,以及牽涉著科研各環節的管理、評價、職稱、經費等體制[6]4–10,都是通過學科化、體制化運作起來的。早在2001年,上海大學就成立了大陸第一所文化研究機構——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又設立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心主任王曉明表示,雖然反體制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場之一,但為了培養能夠有效參與文化研究的年輕人,大學必須“開辟自己的教學空間”,所以“不得不硬著頭皮擠入現行大學體制”[7]。
另有一些學者對文化研究學科化的態度是復雜的。周憲傾向于開辟出一條與現有的文學研究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策略,希望文化研究者能夠“擺脫制度的限制和文化資本的誘惑,進入真正的文化批判”[8]。趙勇引用了霍爾等人關于文化研究“非學科性”的論述,并以西方國家體制化了的文化研究陷入困境為佐證,最終落腳于中國的文化研究和文藝學應該相互融合[9]。也就是說,在“是否應當為文化研究設立一門學科”的問題上,相當一部分人采取了一種回避的態度,更多將其視為一種能夠打破目前文藝學僵化的新的方法論,認為文化研究反學科的知識實踐可以轉化為文藝學可資借鑒的有益啟示,從而建立一個新的研究范式。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糾結文化研究的學科屬性、一味制造與體制的對立,是既沒有現實意義,也沒有必要的。文化研究如何既占有開展研究必需的資源(經費、場所、資料庫、人才儲備等),又最大程度的保留自身話語權?絕大多數研究者都明白,向體制借力并不等于做政治的傀儡,追求烏托邦式的研究畢竟只是一種幻想。要想辦法利用體制提供的資源,努力爭取更多話語權以促進研究的深入,至于尺度的把握和策略的運用,就是另外的問題了。
(二)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
文化研究自身對學科化的抵制,反而使其成為一塊能吸引任何理論的磁石。這種復雜性造成了學界對它有一定了解后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間的關系。趙勇在分析了兩者各自的缺陷后,倡導“在文學研究中增加文化研究的維度,在文化研究中增加文學研究的維度”,最終得到一種同時兼顧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美學分析和意識形態癥候分析的研究范式[10]。與這種“謀共存”的溫和態度相比,童慶炳對文化研究“完全不以文學為研究對象”[11]的批評則尖銳得多。但這種說法有將“文學”的涵蓋面大大縮小的嫌疑,后者所指應該是所謂的“文學經典”,但并不是只有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才有資格稱為“文學”。文化研究對文學經典的研究不在少數,但文化研究所作的不是繼續為經典“加冕”,而是秉持知識社會學的立場,“解構經典的神話”[12]。陶東風舉了一個例子——英國的莎士比亞研究,在文化研究產生以前,這些問題幾乎沒有人討論過:劇院在伊麗莎白時代居于何種社會地位?戲劇在16―17世紀是如何被創作和生產出來的?這些戲劇面向的受眾群體和接受過程是怎樣的?結果表明:“對莎士比亞的解釋是一個權力問題。”[12]基于這一研究,為文學經典“去神圣化”成為文化研究的顯著特征。文化研究要做的是“質詢經典化過程背后的權力關系,包括所謂普遍的‘審美價值’、‘文學價值’的非普遍性、歷史性、地方性。文化研究感興趣的問題不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經典?’而是:‘誰之經典?’、‘誰之(經典)標準?’等帶有解構意味的問題”[12]。還有人用“可疑”一詞概括了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轉向,并對文化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當下語境中的有效性以及“‘偽平民主義’姿態”提出了質疑[13]。
二、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
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中,霍爾將文化研究的文化主義范式理解為以“經驗”為基礎的主導范式;而結構主義則更看重“實踐”,否認“經驗”在文化框架中的基礎地位[2]。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彼此之間的張力為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了多樣化選擇。隨著20世紀90年代傳媒技術日益進步,物質世界的輪廓逐漸變得清晰,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強烈吸引著大眾,與現代日常生活問題聯系密切的大眾文化也逐漸成為新世紀以來文化研究的熱點話題。
從現代化理論出發是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一種典型范式。李澤厚、王蒙、陶東風等人肯定大眾文化的“進步政治意義(而不是審美價值)”[14]。戴錦華則以帶有新左翼色彩的批判眼光,將其置于全球化語境下分析,認為大眾文化的生產能夠給作者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但介入這一過程也同時“意味著經典意義上的文學藝術的無疾而終”[15]。陸揚看到了大眾文化的兩面性:一方面它是“統治階級和資本合謀”的產物,另一方面大眾文化也未嘗不可“顯示為一種民主力量”[16]。
凡言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必然離不開文化工業、消費主義、電視媒體、跨國資本和“通俗”“流行”等字眼。正如王一川所下的操作性定義:大眾文化是以傳統和電子媒介為手段、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運作、讓接受者(大眾)獲得愉悅體驗的日常文化形態[17]。今天我們用“文化產業”將通俗小說、暢銷書、流行音樂、影視劇等大眾文化的各種存在形態統統囊括,但它剛剛崛起時對日常生活方式的改造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在現代傳媒的推動下,審美活動不再局限于美術館、音樂廳等專門場所,媒體不間斷地推銷著“審美的”生活方式,點燃了人們的文化需求和消費熱情,一時間掀起了“一場深刻的生活革命”[18]。2002年前后,“日常生活審美化”一詞被首次提出,隨即引發熱烈討論。然而,學者們爭論的并非僅僅是空前繁榮的大眾文化本身,而是把它放置在文藝學研究呈現出衰微之勢的背景下。也就是說,要理清文化研究如何從理論和方法的引進過渡到“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不能不提當時文藝理論研究面臨的危機。關于這一點,2002年1月《浙江社會科學》編者說得很清楚:“(文藝學研究)已顯危機跡象……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轉型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文藝活動的存在方式、生產、傳播與消費方式,對于原先的許多文藝理論觀念提出了挑戰。”[19]
除了審美泛化對傳統文藝學研究造成的沖擊,一批對經典有著堅定信仰的學者,將具有濃厚“商品拜物教”色彩的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審美化,視為人類精神的極大墮落。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陶東風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以下簡稱《反思》)受到如此多的質疑和批判,進而發展為“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的緣起,影響之大,“席卷全國,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20]。《反思》認為,文化的商業化和大眾傳媒的普及帶動了日常生活的審美化,進而“導致了文學藝術以及整個文化領域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的變化”[21]。將審美泛化趨勢視為反面教材者有之,為其辯護正名者亦有之。諸如朱朝暉《看上去很美——對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的思考》、姜文振《誰的‘日常生活’?怎樣的‘審美化’?》、童慶炳《“日常生活中審美化”與文藝學的“越界”》等文均對“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命題持否定和批判態度。值得注意的是陶東風與魯樞元、趙勇之間的一系列爭鳴文章。《反思》一文發表后,魯、趙分別作《評所謂“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審美日常生活化”的價值取向析疑》(以下簡稱《析疑》)和《誰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怎樣做“文化研究”?——與陶東風教授商榷》,陶以《大眾消費文化研究的三種范式及其西方資源——兼答魯樞元先生》(以下簡稱《答魯樞元》)和《研究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的三種范式及其西方資源——兼談“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并答趙勇博士》(以下簡稱《答趙勇》)作為回應,魯又作《再談“日常生活審美化”——對陶東風先生一文的簡短回應》。《析疑》中指出,“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審美的日常生活化”二者雖然有密切的聯系,但在審美和價值取向上都是相當不同的:后者是“精神生活對物質生活的依附”,而前者則是“物質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華”[22]。趙勇也是從價值判斷的角度出發,對“日常生活審美化”提出了相當尖銳的批評:“日常生活審美化”是對現實的虛假美化,不僅割裂了人與現實的聯系,而且給人一種虛假而膚淺的審美幻覺[23]。在回應文章中,陶東風并未對各方發難逐一作出解釋,而是回顧了中國大眾消費文化的研究歷史。在他看來,從價值判斷的層面上批判日常生活審美化仍然是抽象的,令人擔憂的是“與消費主義相伴隨的大眾的政治冷漠”——只是滿足于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毫不關心政治權利、公共領域的重大問題等議題[14]。《答趙勇》文末提出的憂慮,表明他對消費主義、消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審美化是帶著反思和批判的。
王德勝等人指出,當前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的焦點有二:一是美學、文藝理論界內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角度不同,評價出現兩極化;二是隨著論爭的展開,現有的文藝學、美學在介入和闡釋“日常生活審美化”時感到“力不從心”,學者們對文藝學“邊界”問題意見不一。關于第一點談到的“認識角度不同”,筆者以為主要是指論爭雙方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問題上存在分歧。以王德勝為例,他認為《析疑》一文“最具理論上誤讀、誤解的典型性”,理由是在解讀何謂“日常生活審美化”時,魯樞元將其置換為“審美的日常生活化”,并把后者作為批判對象[24]。桑農也站在為“日常生活審美化”辯護的立場,指出魯樞元并非“無意間混淆了概念”,這恰恰是一種話語策略:“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駁論者有意回避審美現象,而去檢查它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倫理意義[25]。更多學者從各種角度出發的意見茲不一一列舉。總之,“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背后折射出了學界的一個巨大分歧:技術進步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文化研究?倡導者認為“日常生活審美化”改變了有關文學與藝術的定義;反方則指出,“日常生活審美化”表面上解放了人的感性,深層則是“工具理性對于人的更為嚴酷的操控”;人的自由被局限為消費能力的自由,理性對于人類存在和社會發展的意義顯然被大大遮蔽了[26]。
通過對上述文章觀點的梳理不難看出,這些文章文字犀利火辣,用大量篇幅、甚至逐句逐段地進行反駁。如湯擁華所說,“爭論常常始于誤解而終于分歧”[20],各方對于“日常生活審美化”議題下涉及的消費與消費主義、消費文化與文化消費主義等概念的理解見仁見智、各執一詞,最終也沒能得出相對一致的觀點。也有人從旁觀者的角度認為,“日常生活審美化”是否需要作為一個新問題被提出還值得反復考量,參與者們只不過是借此機會表達自己“對文藝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看法[27]。
盡管在很多問題上都未能達成共識,但認同“日常生活審美化”的一方可以說大獲全勝。受惠于資本運作的強大力量和市場經濟化、文化多元化的國家戰略,大眾文化被納入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框架,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然而不能忽視的是,無論是用伯明翰學派主張為己方助威吶喊,還是高踞法蘭克福學派的精英主義陣地,大陸文化研究對西方理論的歡迎和欣賞都暴露出自身理論生產的惰性和理論運用的慣性。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場論爭的發起距離全國大范圍“下崗潮”過去不過三四年,普通民眾遭受的深刻創痛尚未撫平,“沉默的大多數”仍然是構成更大社會背景的灰暗底色,此時就“中國在多大程度上已經日常生活審美化”等問題筆戰,未免有些不合時宜——僅從這一點來看,論爭的合法性值得商榷。檢索1995―2005年的文化研究成果,幾乎沒有一篇是與城市工人下崗有關的論述(將搜索范圍擴大到2020年也是如此)。一向“以描述、解釋當代文化與社會實踐為目的”[28]的文化研究對如此重大的社會事件“選擇性失明”,與其說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文化研究理想與現實的脫節,毋寧說文化研究的邊緣品格和底層關懷并不像它宣稱的那樣切實可行(這也是大部分社會批判理論一貫為人詬病之處),知識分子走下象牙塔路途依然漫長。
三、文化研究的中國經驗與未來
美國學者格羅斯伯格認為,“激進的語境主義構成了文化研究的核心”[29],這意味著文化研究需要根據場域的變化做出調整和適應,從引進理論、消費理論發展為生產理論。在知識本土化和理論生產的問題上,國內學者引入了“中國經驗”“中國問題”等概念。周憲指出,作為后進的現代化國家,中國在提出理論方面具有一定滯后性,但文化研究討論的種種文化現象“必然帶有本土文化實踐的獨特性”,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它們“正是實現西方理論向中國理論范式轉換的契機”[30]。基于此,“中國的獨特問題和經驗資源”需要被關注和發掘,研究不能止步于中西文化的某些表面相似之處,甚或是對西方理論不加修正改造便直接移植至本土語境。近幾年對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實踐投以極大熱情的青年學者顏桂堤在一系列相關論文中,多次提出文化研究進入中國場域“便進入了另一個闡釋結構——‘中國問題’”[31],文化研究理論“提供了介入中國本土實踐的一種可能”[32]。借助“中國經驗”這一概念,他提出了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兩個維度:介入當代中國的歷史空間、在其中占據獨特位置。對“中國經驗”做出有效闡釋,需要借助包括新的方法論、研究路徑、研究視域、造成的理論誤讀和自我調適等在內的多種理論。“中國經驗”是文化研究諸多層面下共同的隱藏內核,它既是對“中國問題”的理論闡釋,又是能夠有效介入其中的批判性實踐[33]。
文化研究介入中國文化場域的過程啟發并推動了“中國問題”的闡釋與理解,形成了大陸學界對文化研究接受的“復調”。諸多學者在這種“接受的復調”的影響下對“中國問題”產生了多角度的理解,這些觀點比較全面地概括了當前中國文化研究的發展狀況,反映了文化研究在中國的接受與本土化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多元性。那么,如何找到一套適合中國本土的文化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因其高度語境化、地方化,從而與“民族志”形成了某種同頻震動,民族志文本或可成為文化研究中國化一個新的挖掘點,“民族志書寫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寬泛的‘地方’語言,它在介入日常生活的過程中體現了一種公共話語(來自底層),同時又能夠聯系不同的語境(包括各種理論與精英文化)”[34]。上海大學推出的《熱風學術》輯刊以及“熱風書系”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開創性成果,但從總體來看,以民族志視角進行文化研究還比較薄弱。陸揚在考察了英美兩國文化研究的發展路徑后認為,文化研究屬于人文科學,它與社會學融合不僅可能,而且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16]。民族志視角和與社會學結合分別從內部和外部為文化研究的發展設計了藍圖,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文化研究并非將文學研究比附于物質現象和社會階級的庸俗社會學的體現,文化研究是一種具有強烈批判反思色彩的研究方式,正因如此,對于自身的反省和檢討也是其突破固有思維,使理論得以創新的重要途徑。
四、問題與反思
“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熱潮退去后,文化研究越來越呈現出廣義的“泛文化研究”趨勢。梳理近20年國內文化研究的成果,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關注。
第一,不得不遺憾地指出,目前大陸還沒有“中國文化研究”,而只有“都市文化研究”,甚至可以將定語縮小至“發達地區的都市文化研究”。除了鄒贊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一特殊群體的文化研究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廣大中西部地區在文化研究面前仍處于一種失語狀態。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促進社會和一般文化狀況的良性改革”[7]。良性改革的動力來源一般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城市里的中等收入階層;另一種則認為來自城鄉的底層民眾。鄉村的務農及留守人員,城市里的進城務工人員、流動小商販、個體經營者等,文化研究與上述群體的隔膜是不可否認的。這種現象也絕非近幾年才產生,2009年就有學者批評文化研究已“逐漸背離初衷,愈發遮蔽底層民眾和邊緣群體的聲音”[35]。10余年過去,文化研究距離它的理想品格依然十分遙遠,這與對所謂“底層”的忽視不無關系。
第二,中國也幾乎沒有政治批判性濃厚的文化研究。國內目前有兩種“文化研究”:一種是研究“文化研究”,聚焦于文化研究之歐美傳統以及后現代后殖民等各種理論研究;另一種是做“文化研究”,對文化產業和網絡新媒體甚為關心。20世紀90年代戴錦華、李陀等對文化背后權力和資本的操縱運作尚有所揭示,之后的批判力度則大不如前,甚至幾近銷聲匿跡。有學者意味深長地指出:“在需要文化研究者表明價值立場、顯示批判力量的時刻,越來越多的文化研究者放棄真正的問題導向,沒有將公共領域的重大問題納入視野……對權力介入市場、資本購買權力,對體制造就的知識霸權、知識霸權獲取的體制收益等種種嚴峻問題保持緘默。”文化研究脫胎于“對公共―政治領域的關切”,然而“其研究目標、研究領域卻日益局限于消費―娛樂領域”[36]。文化研究最棘手、最難以突破的困境就在于此。
第三,文化研究的文學研究范式尚處于摸索階段,差強人意之作少之又少。文學性文本即便被提起,“也只能是用作某個文化理論論點的資證”[37]。殊不知,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對文學文本進行再解讀——讀出不以文化研究為切入點就不能讀出的內涵——無疑是推動學術創新、回應“文學研究衰落”論的有效工具。對于如何回歸文學本體,最近有學者提出重建“本文詩學”,“以回歸文本的原則重返文學自身,找尋作家的創作規律與個性特點,并試圖以‘博采東西,并覽古今’的姿態,攜手文化詩學和詩文評共同參與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38]。這一構想十分有嘗試的價值和必要。文化研究能否煥發新的生機,能夠打破“理論與實踐脫節”的魔咒,能夠直言時弊、切中要害,對此,我們充滿期待。
[1] 戴錦華.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錄[M].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217.
[2] 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56-62.
[3] 金元浦.文化研究:學科大聯合的事業[J].社會科學戰線,2005(1):246–253.
[4] 詹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M].王逢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399.
[5] 羅鋼,孟登迎.文化研究與反學科的知識實踐[J].文藝研究,2002(4):14–19.
[6] 陶東風.文化研究:在體制與學科之間游走[J].當代文壇,2015(2):4–10.
[7] 王曉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難題:以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為例[J].上海大學學報,2010(1):5–17.
[8] 周憲.文化研究:學科抑或策略?[J].文藝研究,2002(4):26–32.
[9] 趙勇.關于文化研究的歷史考察及其反思[J].中國社會科學,2005(2):168–176.
[10] 趙勇.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對一種新研究范式的期待[J].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5):25–29+38.
[11] 童慶炳.文藝學邊界三題[J].文學評論,2004(6):54–59.
[12] 陶東風.文學經典與文化權力(上):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經典問題[J].中國比較文學,2004(3):61–77.
[13] 鄭崇選.可疑的轉向:對當下文化研究熱的幾點反思[J].學術論壇,2003(4):131–134.
[14] 陶東風.研究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的三種范式及其西方資源:兼談“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并答趙勇博士[J].河北學刊,2004(5):86–92.
[15] 戴錦華.文學備忘錄:質疑“全球化”[J].山花,2000(3):85–89.
[16] 陸揚.對文化研究發展歷程的反思[J].探索與爭鳴,2011(3):55–58.
[17] 王一川.當代大眾文化與中國大眾文化學[J].藝術廣角,2001(2):4–10.
[18] 陶東風.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新文化媒介人的興起[J].文藝爭鳴,2003(6):9–12.
[19] 編者的話[J].浙江社會科學,2002(1):165.
[20] 湯擁華.日常生活審美化:一個意識形態問題[J].山花,2005(6):123–130.
[21] 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J].浙江社會科學,2002(1).
[22] 魯樞元.評所謂“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審美日常生活化”的價值取向析疑[J].文藝爭鳴,2004(3):6–12.
[23] 趙勇.誰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怎樣做“文化研究”?——與陶東風教授商榷[J].河北學刊,2004(5):81–85.
[24] 王德勝.為“新的美學原則”辯護:答魯樞元教授[J].文藝爭鳴,2004(5):6–10.
[25] 桑農.“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中的價值問題:兼為“新的美學原則”辯護[J].文藝爭鳴,2006(3):10–14.
[26] 陸揚.論日常生活“審美化”[J].理論與現代化,2004(3):70–72.
[27] 艾秀梅.“日常生活審美化”爭論述評[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2):81–86.
[28] 陶東風,和磊.文化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1.
[29] 格羅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來[M].莊鵬濤,等譯.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19.
[30] 周憲.文化研究:為何并如何?[J].文藝研究,2007(6):21–26+166.
[31] 顏桂堤.文化研究對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的挑戰與重構[J].文學評論,2019(3):46–54.
[32] 顏桂堤.闡釋“中國經驗”的當代文化研究[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09-25(4).
[33] 顏桂堤.近三十年中國“文化研究”:開放的話語場域與中國經驗[J].文學與文化,2019(4):101–110.
[34] 費中正,孫秋云.文化研究內卷化的探索路徑:一種民族志的視角[J].學習與實踐,2011(5):102–107.
[35] 范玉剛.文化研究的局限與發展前景[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9(6):101–106.
[36] 邢曉飛.“文化研究”:中國語境下的理論再思[J].浙江學刊,2014(4):102–108.
[37] 金永兵.“文化研究”的價值與虛妄[J].湖南社會科學,2008(2):137–141.
[38] 胡友峰.重建本文詩學:中國文論走出去的路徑與方法[J].中國文學批評,2020(2):42–51+158.
A Review of Some Hot Issues in Domestic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LYU Ruome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00, China)
Cultural studies have aroused the concern of humanists immediately after their landing in China, and their complete rebellion against the previous objects and methods of literary studies has also aroused heated debate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2000, domestic scholars have launched a fierce debate on the subject attribute of cultural studies, popular culture and other issues, and the latter's debate on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daily life” has lasted for several years. The study of culture cannot be satisfied with translating or introducing or following western theories, but needs to reflect and transcend itself with a concern for the moment, forming a broad influence o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research; discipline attribute; debate on “aestheticization of daily life”; Chinese experience
I206
A
1006–5261(2022)06–0135–08
2022-07-26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1&ZD256)
呂若玫(1998―),女,遼寧大連人,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劉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