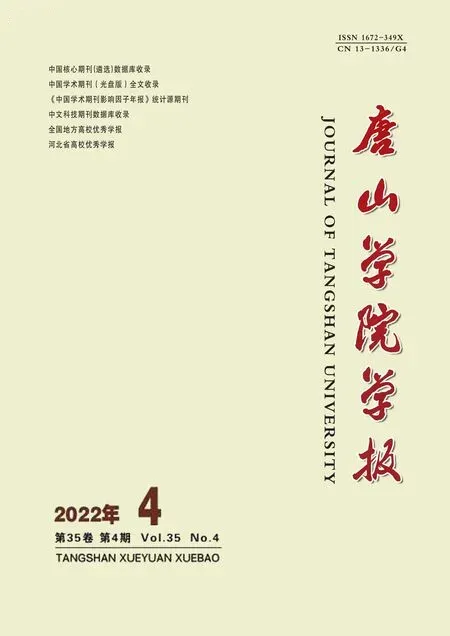中共湖北地區鄉村早期組織的創建與發展
——以鄉村人口流動為中心
丁君濤,張雨尉
(湖北經濟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武漢 430200)
中共湖北地區早期組織的創建與發展作為中共黨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來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1-4],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探析了中共湖北地區早期組織創建的原因、發展壯大的背景、活動狀況等。中共早期組織首先在上海、武漢等主要城市創建并很快成長為全國性組織,且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系,究其原因,除了革命理論的引領外,還與我國近代社會大量的人口流動密切相關,但學術界對此卻鮮有研究。以社會學理論解讀我國近代鄉村人口的流動,為研究中共早期組織的創建與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而通過探究鄉村人口流動與中共湖北地區早期組織創建與發展的關系,不僅可以填補相關研究空白,還能為探索地區革命史提供新的思路。
一、人口流動為中共湖北鄉村早期組織的創建與發展創造條件
(一)人口流動與思想傳播
我國近代人口流動異常活躍,特別是大量鄉村人口涌入城市,還有一些境外人口也進入國內部分主要城市,武漢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成為人口遷移的重要目的地。葉調元《漢口竹枝詞》中“茶庵直上通橋口,后市前街屋似鱗。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說的就是武漢外來人口的繁盛。可見,近代武漢人口的迅速增長有相當一部分是依賴外來移民,截至1930年武漢城市人口已突破10萬大關[5]。
在遷入武漢的人口中,有農民、商人、學生等,其中學生占據相當大的比重。據統計,1916-1918年間,武漢僅專門大學(含公立、私立,但不包括教會學校)的學生人數已達到1 592人,占全國大學生總人數的9%,僅次于直隸,居全國第二位[6]。與周邊的長沙、南昌等城市相比較,武漢在教育方面遙遙領先,在高校數量、教育投入等方面都占據優勢,因此周邊地區的學生大量入讀武漢高校。“新式學校的存在讓青年人有了一個較為固定的公共活動場所,同齡人之間的切磋熏染容易產生共鳴,有助于群體意識的形成……新式學校的出現,實際上為中國社會的重新組織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動力”[2]。可以說,匯聚武漢的青年學生為湖北地區先進思想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成為早期黨團組織的骨干成員。
在武漢的流動人口中,數量最多的還是農民。“鄉民因農村生活艱苦,羨慕都市繁榮,離村外出者,亦日漸加多,所去之處,以漢口為多。”[7]流入武漢的農民大多從事社會底層工作,主要職業有傭工、碼頭夫、小藝、苦力、木工、使役、車夫以及各種實業工人等[8]。這些遍布武漢三鎮、從事艱苦勞作并往返于城鄉間的農民,必然會將城市中的新興思想帶回鄉村并廣泛傳播,這種傳播方式為中共湖北地區鄉村早期組織的創建與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此外,在遷入武漢的人口中,來自海外的人口數量也顯著增加。據統計,1905年在武漢的外國人已有2 142人(1)參見水野幸吉《漢口》第11頁,光緒三十四年(1908)刊行。,其中日本人居多,占40%以上。這些外國人在武漢地區創辦了大量報刊,如《漢報》《益文月報》等,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漢報》。《漢報》的辦報方針是“抑制舊黨,援助新黨,以助長維新之氣運”,標榜“發中國之風氣,鼓舞中國之士民,振作政治教育,勸興農工商務,使中國四萬萬之民,脫歐人將吞之虎門,以欲全同文同種同洲之義務天職”[9]。這些報刊在當時確實宣傳了一些進步思想,也為武漢革命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必要的輿論基礎。俄國革命勝利后,武漢更成為革命思想傳播的重要地帶。維經斯基在其1920年的一封書信中提到:“現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系,雖然他們在漢口、廣州、南京等地尚未設代表處,但我們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過一些朋友即當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在漢口,我們有可能吸收一位編外副教授參加我們的工作,此人在中國生活好幾年,通曉中文,是柏偉烈教授推薦的。”[10]25從這封書信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共產國際已有意識地借助“當地的革命者”在武漢宣傳革命思想。不僅如此,共產國際還有意識地推動武漢黨組織的創建,將當地的“益群書店作為一個核心把這些革命團體團結在它的周圍”[10]25,“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共產國際代表在武漢的活動為中共湖北地區鄉村早期組織的創建與發展發揮了指導作用。
(二)人口流動與鄉村真空
學術界對近代中國鄉村人口流動、鄉村真空形成及其與中共早期鄉村組織創建和發展的關系鮮有研究,從人口流動與鄉村真空形成的角度探討中共早期鄉村組織的創建與發展,對于解讀中共在鄉村站穩腳跟并取得全國勝利的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國近代鄉村人口的流動對鄉村的沖擊較大。遷移者的選擇理論認為,遷移者并不是原居住地的一個隨機樣本,它與遷移者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相關[11]106。因此,在鄉村,只有青年人與綜合素質較高的人才擁有較低的遷移成本和較高的預期收益,換句話說,從鄉村遷往主要城市的除了大量迫于生計的農民,還有一些手握社會資源的鄉村精英。鄉村精英人口的流失、農民階層的邊緣化、宗法制度的瓦解,使近代的中國鄉村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都處于一種真空狀態,迫切需要外來力量引導鄉村實現再整合,以改變鄉村面貌。
在經濟方面,一些鄉村精英的遷出伴隨大量資金從鄉村流入城市,導致鄉村融資成本進一步提高,借貸利率不斷增長,特別是短期借貸增長更加迅猛:“二十二省八百七十一縣之報告二千四百零八件中,六個月以內者占12.6%,六個月至十二個月以內者占64.7%。”[12]一部分投機者也趁機從中漁利,“以不到一分的利息,向金融機關借得款項,又把他們所借的款項以三分至七分的利息,借給貧苦的農民,無孔不入地發揮了高利貸的作用”[13],使農民本已困頓的生活雪上加霜,大量農民對這種經濟沖擊根本無力抵御,不得不放棄農耕到城市打工謀生,鄉村土地兼并也因此日益嚴重。
在政治方面,隨著近代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城市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的資源也較多地流向主要城市,國家政策凸顯“馬太效應”。原有的鄉村治理體系不斷坍塌,而現代治理手段又銜接不上,加之“農村中比較有志力的分子不斷地向城市跑,外縣的向省會跑,外省的向首都與通商大埠跑”[14],故而,鄉村的政治權力通常都被在鄉的土豪劣紳直接把持,這些人“莫不藉執村事從中漁利,且往往霸公產為己產,肥己身家”[15]。因此,近代鄉村在政治上已陷入混亂,農民階層與鄉村社會在政治生活中不斷被邊緣化,鄉村及農民急需在政治上獲得相應的地位與建立良性的秩序。
在思想方面,隨著鄉村傳統知識分子不斷遷入城市,在新文化難以傳入的鄉村,舊有的文化傳統也難以為繼。“頻年的革命只是幾個城市,內地仍然在換湯不換藥的境況中。然而只這換湯式的政府嚴令下,已是使舊有的思想習慣日在破壞損毀,新的思想生活方式又不曾用‘換湯’的政策建立起來,是以鄉間問題比城市來得更復雜可怕”[16]。近代鄉村已經在文化上喪失了原有的自我調節機制,迫切需要新思想的傳入以推動自身進步。
在湖北地區,大革命失敗后的反動統治進一步加強了對武漢等中心城市的控制,而在廣袤的鄉村則存在大量的權力真空。這種真空狀態為中共早期組織在湖北鄉村的創建與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一些貧苦農民和鄉村知識分子在革命思想影響下,懷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義無反顧地投身于革命事業,成為革命事業發展重要的力量源泉。
(三)人口流動與“弱關系”
中國“城市文化的近代轉型主要是在外力的推引下,通過通商、建租界、傳教等途徑輸入外來文化而進行的”[17],正如魯迅先生所描繪的:“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就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槍,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18]而大量鄉村人口的遷入則使這個轉型過程變得更加復雜。
農民入城大多具有群聚性。社會學遷移者網絡理論認為:“遷移者并非僅僅是年輕人和高素質的人口,而是與遷入地人口有某些聯系的人,他們與遷入地已有移民的聯系構成的網絡成為一種社會資本,起著降低遷移成本、增加收益和減少風險的作用。”[11]106因此,武漢的很多產業工人都呈現出明顯的地域聚集性。如紗廠工人主要來自武漢三鎮及周邊的青山、蔡甸、黃陂、沔陽、鄂城和黃岡等地,還有一部分來自下江一帶,另有少部分來自粵、湘地區[19]。入城的同鄉農民間保持著緊密聯系,并有意識地復刻原有的生活環境與文化,這種狀況在當時是比較普遍的。同鄉集群生活有利于文化適應,并逐步轉化為一種“弱關系”,“通過弱關系可以獲得更多的非常重復的或非多余的信息”[20]322。這種以“弱關系”為通道的傳播格局對中共早期的思想宣傳和組織發動非常有利,也是中共早期組織在武漢等主要城市和廣袤的湖北鄉村能夠獲得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熟人社會與革命落地
近代中國的鄉村社會是一種以宗族關系為紐帶的熟人社會。鄉村運動的最大意義就是“宣傳農民”[21]。中共湖北地區鄉村早期組織的創建與發展,就是充分利用廣大鄉村熟人社會的特點,借助組織成員特別是青年學生在鄉村的社交網絡,動員宗族成員、熟人等加入組織以壯大力量,同時在鄉村廣泛建立農會、開展演講、印刷刊物等以加強思想宣傳。如林育南等人在黃岡成立平民教育社,“在年假期間,各學生回鄉……鼓吹平民教育,作農村運動的先導”(2)參見中央檔案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群團文件1922-1924)》,1983年第113頁。;惲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在黃岡成立了共存社[22];還有一些學生在羅田、麻城成立了羅麻青年協會(3)參見中央檔案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群團文件1925-1926)》,1983年第287頁。。特別是農民協會工作在這一時期取得了顯著成果,以農運工作做得較好的棗陽地區為例,這區農協1925年底成立,“加入組織的有三十余莊,人數在千人以上……幾次反抗官紳的大運動,均得勝利”(4)同②,第286頁。。
中共早期開展農民運動非常倚重回鄉學生。武漢的黨員有三分之二為學生,相當一部分學生黨員、團員在城市接受訓練后被派回故鄉開展工作。如棗陽地區黨組織領導人程祖武即為棗陽當地人。中共早期的發展網絡“基本都是利用傳統的同鄉關系、師徒關系、同宗關系等由復雜歷史積淀而成的傳統社會資本構件來推展的”[23],“正是通過……這些方式,涵蓋黨、政、軍、群等各方面的龐大的中共組織體系在較短的時間內得以建立起來,關于中國革命的種種設想和計劃也初步實現了不同程度的落地”[2]。總之,中共先進的理論宣傳與傳統的熟人社會相結合,使其早期組織短時間內在湖北鄉村得到了快速發展。
然而,成果的背后是過程的艱辛,實現中共先進理論宣傳與傳統熟人社會相結合既要解決理論問題,又要解決策略問題。成立組織、開展集會宣傳等城市化的傳播手段無法迅速適應鄉村現實,對農民的吸引力極為有限,對農民的宣傳也就難以取得明顯效果。對此武漢地委曾批評道:“武漢的同志三分之二為學生……而學生同志又多在城市,所以更加和農民隔絕。”(5)同②,第286頁。“在韋伯看來,傳統中國人之間存在著普遍的不信任,傳統中國的社會信任是缺失的。”[20]281由于“中國社會的信任半徑常常局限于家庭和有血緣關系的群體內”[20]280,因此中共早期鄉村組織吸納的人員主要是回鄉黨員、團員的宗族親戚及一些較有影響力的鄉村知識分子。雖然這種方式使中共早期組織在鄉村的發展較快,截至1927年4月,“除武漢三鎮外,湖北省各地黨支部增至400多個,黨的組織遍及50多個縣、市,黨員逐月銳增”[24],但由于返鄉黨員、團員大多出身于鄉村上層社會,并非貧苦農民,在其以傳統熟人社會同心圓模式吸納成員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傳統社會網絡滲入組織之中,“如公安縣之四十一個同志中,竟然有三十九人為土豪劣紳及與土豪劣紳利害一致的成份”(6)參見中央檔案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6-1927)》,1983年第274頁。。傳統社會網絡與中共組織之間互相滲透,必然會擾亂中共早期組織的內部溝通,導致機會主義在組織內部比較活躍。
中共早期這種借助鄉村傳統網絡建立起來的組織很難長久穩固,原因有三。首先,對于鄉村而言,從城市返鄉的黨員、團員在文化屬性上已屬外來者。傳統鄉村社會屬于典型的機械團結社會,需要強大的集體意識維系社會秩序及成員間的聯系,故此以中共的革命理論替代傳統鄉村的集體意識,必然是一個艱難且持久的過程。其次,傳統鄉村是一種典型的命運共同體,無論個體在形式上如何分割,成員間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由于從城市返鄉的黨員、團員在文化屬性上已屬外來者,因此在宣傳黨的理論、主張的過程中,仍要面臨身份認同的問題。如“隨、襄同志……是本地人,顧慮身家,工作方面有許多顧慮”(7)同上,第270頁。,“各區同志均各行其是,完全不執行省委決定的策略,甚且與此策略背道而馳”(8)同上,第273頁。。再次,這種組織發展方式導致占鄉村多數的農民難以進入領導核心。據中共黨史研究室相關資料記載,“1925年以后……指導機關仍然沒有群眾化……從上至下的指導機關,無形中逐漸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化”[25]。這也是導致機會主義錯誤的重大隱患。此外,大革命失敗后,原已逃離鄉村的土豪劣紳又紛紛回鄉,借助宗族、地緣等傳統社會網絡擴大力量,打擊中共鄉村組織。據中央檔案館資料記載,沔陽地區“土劣活動甚烈,紛紛下鄉,并組織暗殺隊三十隊,欲乘機屠殺黨部工運農運人員”(9)同上,第218頁。;漢川地區“土劣以軍隊為護符,除告狀外并在各處捕人,打房子、封房子”(10)同上,第219頁。等。鄉村反動勢力利用傳統社會網絡對中共組織的反撲,使中共鄉村組織工作一度陷入被動。大革命的失敗進一步證明,完全依賴傳統社會網絡發展組織并不現實。此后,中共逐步調整政策,使黨的組織建設更加完善、戰斗力不斷提升。
三、中共早期的組織再造與黨員流動
大革命失敗后,鄉村成為中共早期組織發展的重心,大批黨員流動到鄉村。同時,大革命的失敗也使中共內部產生劇烈震蕩,黨內各種分歧、矛盾復雜,組織結構受到沖擊。因此,中共面臨著更加復雜的黨內與黨外環境,不得不加強組織紀律性與純潔性建設。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共對于鄉村黨組織的管控也顯著加強,黨內人員的調動與處理也愈加頻繁,特別是中共善于通過黨員的調動不斷完善民主集中制,提高黨內純潔性,保持組織戰斗力。
1927年中共出臺《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其中提出中央要督促和幫助湖北省委進行改組并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省委以下各級黨部委員會之成分[26]。中共湖北省委也按照中央精神強化了組織紀律建設。如中共湖北省委通告(第6號)即要求下屬各級黨組織將秋收暴動以來犯錯誤同志的詳細信息、犯錯情況、處理狀況等報告給省委,并強調如有延遲不報、敷衍從事,將以黨的紀律制裁(11)參見中央檔案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6-1927)》,1983年第447頁。。這一時期的黨員發展工作也更加規范,保證了黨員的忠誠度。提高鄉村組織純潔性的工作,則通過派遣可靠黨員下鄉來完成,并建立了完善的組織制度。羅亦農被派往長江局工作時就指出:“我在此間的工作,是按照中央指示湖北革命的前途這一觀察上,積極改造湖北的工農運動與黨的組織。”(12)同上,第388頁。中共湖北省委主要領導也認識到干部下鄉的重要性:“(鄉村)黨的力量太弱,尤其是同志政治觀點太薄弱,能夠了解黨的策略的簡直是少到了極點,為使黨能領導鄉村的革命起見,省委應加派得力同志下鄉,尤其是要加重巡視員的工作。”(13)同上,第400頁。這一時期有200多名黨員干部被派往湖北地區廣大鄉村,幫助鄉村開展組織建設。中共還建立了巡視員制度,這種制度對基層黨組織建設一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通過派遣可靠黨員下鄉和建立巡視制度,不僅推動了鄉村早期黨組織建設,保證了黨內的純潔性,而且確保了中共對于基層黨組織的把控。
“八七”會議后,中共通過大力批判黨內機會主義及對前一階段工作的反思,對基層組織建設存在的問題有了深刻認識,更加注重對工農黨員的培養,在基層黨組織建設方面也強化了理論及策略指導,“改造支部領導,建立支部生活……改造各級指導機關……積極培養和引進工人干部”[27]。經過大力整頓,黨內的純潔性更強了,黨組織建設更加嚴密、規范,中央對于基層黨組織的把控力顯著增強。為了進一步加強組織建設,中共還派遣黨員赴蘇聯學習,提高其理論水平;同時又有大量留蘇學生黨員回國,深入基層開展工作。無論是派黨員下鄉改進組織,還是派黨員赴蘇聯學習,其目的都是加強組織內部思想的同一性,使組織在應對復雜環境時能夠做到中央與基層之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最終達成組織的穩固化。通過總結中共湖北地區鄉村早期組織創建與發展的歷程可以發現,中共組織建設一直是在發展中摸索、在挫折中成長并逐步走向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