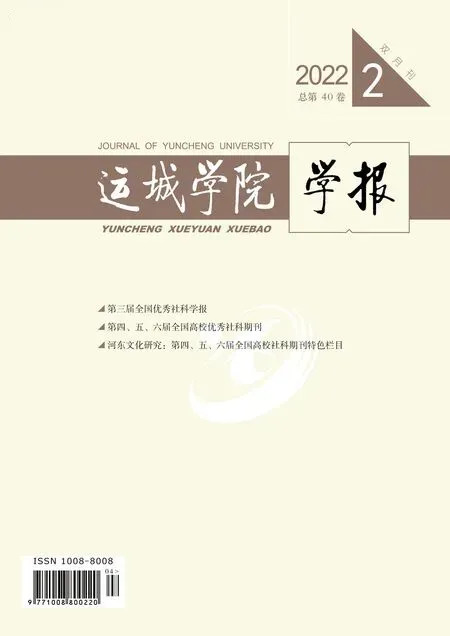《金瓶梅》中“嗑瓜子”的意蘊(yùn)及作用
任 若 嘉
(寶雞文理學(xué)院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陜西 寶雞 721013)
《金瓶梅》一書將視野聚焦于市井生活,它以西門慶及其妻妾、同僚、朋友為中心,以網(wǎng)狀結(jié)構(gòu)輻射到整個(gè)社會(huì)階層,小到走街串巷賣果子的鄆哥,大到權(quán)傾朝野的蔡太師乃至最高統(tǒng)治者宋徽宗,其所涉及描寫的人物無(wú)不極具個(gè)性、形象鮮明。書中圍繞形形色色的人物,展開了各式各樣的場(chǎng)面描寫,其中對(duì)飲食、服飾描寫十分詳盡,較為全面地反映了明代后期的社會(huì)生活。在《金瓶梅》中,作者不厭其煩地對(duì)飲食場(chǎng)面進(jìn)行細(xì)致地描寫,無(wú)論是西門慶與妻妾的日常飲食,還是與官場(chǎng)中人、友人的往來(lái)宴請(qǐng),其中許多場(chǎng)面往往都與情欲密切相關(guān)。而瓜子作為日常食用的零食,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人物的生活之中,“嗑瓜子”作為一處多次出現(xiàn)的細(xì)節(jié),在書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從“嗑瓜子”這一細(xì)節(jié)描寫入手,分析其在《金瓶梅》中的含義以及作用。
一、明清文學(xué)中的“瓜子”書寫
明清文學(xué)中的“瓜子”多指西瓜、南瓜等蔬果的籽粒,而非今日所常食的葵花籽。向日葵雖在明代中期便已傳入中國(guó),但是最初的作用僅僅在于觀賞,直至清末的吳其浚《植物名實(shí)圖考》方才明確記載向日葵用作零食[1]。瓜子作為一種零食小吃,在宋元時(shí)期便已進(jìn)入民間日常,成為世俗生活的重要裝點(diǎn)。如宋代蘇軾在與妻弟王箴的書信中寫道:“與君對(duì)莊門吃瓜子炒豆,不知當(dāng)復(fù)有此日否?”(《與王元直二首其一》)[2]121又如元雜劇《百花亭》中,正末提著查梨條一連叫賣了許多瓜果名,其中便有“魏郡收來(lái)的指頂大的瓜子”[3]231。可見宋元時(shí)期,瓜子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常見的吃食。至明清時(shí)期,食用瓜子更加普遍,在文學(xué)作品中多有提及。在馮夢(mèng)龍《醒世恒言·賣油郎獨(dú)占花魁》中,劉四媽一見杜美娘的豐富積蓄,心中驚想,自家所養(yǎng)粉頭與美娘相比,不過(guò)有幾文錢在荷包里,“閑時(shí)買瓜子嗑。”[4]41明時(shí)人胡文煥《群音類選·補(bǔ)卷二》收錄鄭墟泉【點(diǎn)絳唇·賀節(jié)】套曲,其中【寄生草】一支寫道,衣冠濟(jì)楚、花費(fèi)銀錢一逞風(fēng)流的浪蕩游子“將瓜子兒嗑著排門兒混”[5]2518-2519。瓜子成為粉頭浪子們喜愛的休閑零食,其在明代世俗生活中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嗑瓜子作為一種大眾化的飲食活動(dòng),在明清文學(xué)的描寫中多有著一定的意蘊(yùn)指向和功能。首先,嗑瓜子在明清文學(xué)中往往與女性描寫相關(guān),文學(xué)作品中,嗑瓜子常作為女性打發(fā)時(shí)間的一種方式。元代《燕青博魚》雜劇中,燕和之妻王臘梅與楊衙內(nèi)有奸,在燕和離家之后,王臘梅等待楊衙內(nèi)到來(lái)時(shí),說(shuō)白云“嗑些瓜子兒,等著他者”[3]1434,嗑瓜子成為她在等待奸夫到來(lái)時(shí)的一種消遣。
文學(xué)作品中的嗑瓜子不僅是女性打發(fā)時(shí)間的方式,也是一種特別的細(xì)節(jié)呈現(xiàn),展現(xiàn)出女性獨(dú)特的心理狀態(tài)和外貌神情。如明代詩(shī)人湯尹賓《南中春詞》云:“衫薰石葉宿香凝,滿檻鶯花一袖憑。掩將一袖雙齒縫,費(fèi)來(lái)瓜子日三升。”[6]406其中便以佳人憑欄觀賞春景、掩袖而嗑瓜子的細(xì)節(jié)刻畫,展現(xiàn)出佳人百無(wú)聊賴、令人心傾的風(fēng)采。又如《紅樓夢(mèng)》第八回寫寶玉見寶釵勸說(shuō)吃冷酒不好,“便放下冷的,命人暖來(lái)方飲”,黛玉便“嗑著瓜子兒,只抿著嘴笑”[7]121,活畫出黛玉一副含嗔帶笑的神情。第六十六回寫尤二姐見三姐回護(hù)寶玉為人行事,便問(wèn)“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此時(shí)三姐見有興兒在旁,不好多說(shuō),便“只低了頭嗑著瓜子”[8]854。三姐此時(shí)的顧慮正在無(wú)言之中借嗑瓜子的描寫展現(xiàn)了出來(lái)。
其次,嗑瓜子這一飲食活動(dòng)在男女兩性的交往之中體現(xiàn)出獨(dú)特的交際功能。首先,瓜子被用作傳達(dá)對(duì)異性的傾慕與愛意的一種媒介,情人之間時(shí)有擲瓜子以示愛的親昵活動(dòng)。袁宏道《迎春歌和江進(jìn)之》云:“青蓮衫子藕荷裳,透額垂髻淡淡裝。拾得春條夸姊妹,袖來(lái)瓜子擲兒郎。”[9]153在美好的春季,少女們身著春裝,柔婉動(dòng)人,將瓜子擲向中意的少年,表達(dá)自己的愛意。明代胡文煥《群音類選·清腔卷六》載傅玄泉【南步步嬌·男相思】套曲,寫男子對(duì)情人的思念,其中【北雁兒落帶得勝令】一支云:“俺也曾偎著肩把手腕掐,俺也曾隔著人使瓜子打。”[5]2363主人公回憶起與情人的相處,曾經(jīng)向她擲瓜子打情罵俏。這種愛意的傳達(dá)還通過(guò)贈(zèng)送給情人嗑好的瓜子來(lái)實(shí)現(xiàn)。清代項(xiàng)鴻祚《鵲橋仙·即席戲詠瓜子》詞云:“相思一點(diǎn),合歡雙剖,擲向檀奴衫里,十三剛是破瓜時(shí),怕里許、人還未有。”[10]51(《憶云詞·丙稿》)“破瓜”雙關(guān)兩意,意謂在破身時(shí)節(jié),將嗑好的瓜子贈(zèng)予情人,其中多有鄭重之意。又如清末詩(shī)人樊增祥《憶飲》詩(shī)云:“閣盞時(shí)時(shí)破瓜子,贈(zèng)郎猶帶口脂香。”[11]1476(《樊山續(xù)集卷二十六》)也是以嗑好的瓜子作為一種情愛的表達(dá)。
其次,贈(zèng)送嗑好的瓜子被用作安慰情人相思之情、寄托希望的一種方式。《憶飲》詩(shī)中“贈(zèng)郎猶帶口脂香”一句,尚且含蓄,但已然有著身體相親的隱喻與暗示。清代華廣生所輯《白雪遺音·卷二》中收有《瓜子嗑了》《瓜子仁》兩支俗曲,寫女子將自己親口嗑好的瓜子仁兒包好,送給情郎。兩支曲子都在強(qiáng)調(diào),瓜子是女子親口所嗑,上面有著自己的唾液。“一顆敵十顆,一顆顆都在奴的舌尖兒上過(guò)。”(《瓜子仁》)[12]29“個(gè)個(gè)都是奴家親口嗑。紅的是胭脂,濕的是吐沫。”(《瓜子嗑》)前者是希望情人吃下自己所嗑的瓜子仁兒之后“切莫忘了我”,后者是為了“保管他的相思病全好卻”[12]42。
再次,嗑瓜子在文學(xué)書寫中成為一種情欲的暗示。《白雪遺音·卷四》所載《玉蜻蜓·彈詞》申貴升游庵,尋訪心上人尼姑志貞,向志貞說(shuō)道:“昨日山塘同看戲,你秋波頻轉(zhuǎn)為誰(shuí)來(lái)。一把多情瓜子殼,分明召我赴陽(yáng)臺(tái)。”[13]44-45前引項(xiàng)鴻祚《鵲橋仙》詞著意寫道嗑瓜子的女子的手指是“春蔥細(xì)擘玉纖纖”[10]51,此處云“你秋波頻轉(zhuǎn)為誰(shuí)來(lái)”,由于女性嗑瓜子時(shí)在指尖、眼中所呈現(xiàn)出的風(fēng)情,使得嗑瓜子這一簡(jiǎn)單動(dòng)作具有性感的意味,從而成為了一種情欲的象征。
可見,明清文學(xué)中的瓜子飲食活動(dòng),在女性書寫與兩性關(guān)系書寫中具有多向的意蘊(yùn),它本身即是紛繁的世俗生活畫面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生動(dòng)呈現(xiàn)。《金瓶梅》作為明清文學(xué)中杰出的世情小說(shuō),多有嗑瓜子的場(chǎng)景描寫,更成為這一文學(xué)性呈現(xiàn)的上國(guó)大觀。欣欣子在《金瓶梅詞話序》中指出:“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寄意于時(shí)俗,蓋有謂也。”[14]1《金瓶梅》雖然以市井生活為主要描寫對(duì)象,但是卻以小見大,反映出整個(gè)明代社會(huì)的風(fēng)貌。《酌中志》載,明神宗好食瓜子,“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15]181,上行下效,這種宮廷的飲食偏好影響到了明代民間的食俗。統(tǒng)計(jì)《金瓶梅》全書,關(guān)于瓜子的描寫多達(dá)26處,其中對(duì)“嗑瓜子”進(jìn)行細(xì)致描寫的有12處。這些“嗑瓜子”的場(chǎng)景細(xì)節(jié)刻畫都有著特定的內(nèi)在意蘊(yùn)與藝術(shù)功能。
二、《金瓶梅》中“嗑瓜子”的內(nèi)在意蘊(yùn)
(一)身份地位的間接呈現(xiàn)
食用瓜子在明朝雖然已經(jīng)十分普遍,但是對(duì)于忙于生計(jì)的下層普通民眾來(lái)說(shuō),平時(shí)是很少有閑暇的時(shí)間坐下來(lái)嗑瓜子的,只有在過(guò)年過(guò)節(jié)時(shí),才得以有時(shí)間消遣。這一點(diǎn),在書中有明顯的體現(xiàn),例如第四十六回中,在元夜時(shí),玉簫和書童二人在一處嬉笑打鬧搶著瓜子嗑;小玉也和玳安也在一處嗑著瓜子。又如在第七十八回中,元旦時(shí),玳安與王經(jīng)換上新衣,放爆竹,嗑瓜子。總觀全書一百回,提到下人們嗑瓜子,都是在元旦和元宵節(jié),這便說(shuō)明,即使在瓜子已經(jīng)風(fēng)靡一時(shí)的宋代,處于底層的人應(yīng)很少有時(shí)間享受用來(lái)消磨時(shí)間的零食。故而作者才不惜筆墨加以敘寫。
在書中,還有多次賞賜瓜子的情節(jié)。如在第十六回之中,西門慶于元宵夜與李瓶?jī)核綍?huì),李瓶?jī)簽榇鹬x玳安的掩護(hù),便賞與他二錢銀子買瓜子。又如在第二十四回中,另一個(gè)元宵之夜,李瓶?jī)嘿p給賁四娘子的女兒一方汗巾,又賞了一錢銀子讓其買瓜子,賁四娘子歡喜地連忙道謝。在第七十七回中,西門慶差玳安給鄭月兒送銀子過(guò)節(jié),鄭管家便給了玳安四錢銀子買瓜子。盡管這幾處并未直接刻畫嗑瓜子的動(dòng)作,但是從這些互動(dòng)之中,可以明顯看出上下地位之區(qū)別。同時(shí)也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賞賜或贈(zèng)予也都發(fā)生在元旦與元宵這兩個(gè)節(jié)日之中,而平常的賞賜僅是銀子或是方巾,并不會(huì)特意說(shuō)明是讓受惠者買瓜子。以此,也從側(cè)面說(shuō)明這些身份地位低下的人也只有在年節(jié)時(shí)才有空閑的時(shí)間和閑錢買瓜子。
閑時(shí)和閑錢往往與嗑瓜子之人的身份與地位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可知,書中“嗑瓜子”次數(shù)最多的是潘金蓮,文本多處描寫了她在嫁給西門慶后嗑瓜子的場(chǎng)景。剛?cè)腴T的潘金蓮備受西門慶寵愛,又盡力討得大娘子吳月娘的歡心,風(fēng)頭正盛的她或是在元宵節(jié)夜于樓上露出春蔥般的手指嗑著瓜子,一邊把嗑下的瓜子皮吐落在行人頭上,或是在李瓶?jī)悍块T外一邊偷聽,一邊嗑著瓜子(第二十回),又或是在門首嗑著瓜子等西門慶回來(lái)(第二十一回)。潘金蓮雖然不像李瓶?jī)骸⒚嫌駱悄菢幼陨砭蛽碛写蠊P的財(cái)富,但是憑借西門慶的寵愛仍然有閑錢和閑時(shí)選擇瓜子這一零食作為消遣解悶的方式。與潘金蓮相似,書中有一個(gè)名號(hào)“小金蓮”的人物——宋惠蓮。宋惠蓮原本只是西門慶家的一個(gè)下人,身份低賤,但是自從和西門慶通奸之后,從西門慶處得到了不少的銀錢和首飾。在西門慶巧言欺騙下,宋惠蓮便自認(rèn)為與其他下人不同,開始以“主人”的身份自居,“常在門首成兩價(jià)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jìn)去,教與各房丫鬟并眾人吃”[14]268(第二十三回),開始炫耀自己與眾丫鬟小廝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此外,在元宵夜宴時(shí),其他人都忙的不可開交時(shí),宋惠蓮卻坐在那里嗑著瓜子,把瓜子皮扔的滿地,并且讓畫童幫她打掃(第二十四回)。此外,潘金蓮差人叫她做最拿手的燒豬頭時(shí),她也只是嗑著瓜子,推說(shuō)沒空。西門慶不過(guò)只是把宋惠蓮當(dāng)作解悶的工具,但宋惠蓮卻開始恃寵而驕,迫不及待地彰顯自己所處的新階層,不僅以主子的身份恩惠、指使下人,甚至連真正主子的差遣都敢抗拒不從。從這個(gè)方面來(lái)看,是因?yàn)樗位萆彴炎约寒?dāng)作西門慶的妻妾,隨著身份的提高,行事做派自然都應(yīng)該改變,宋惠蓮的這種心理便可以通過(guò)“嗑瓜子”這一細(xì)節(jié)體現(xiàn)出來(lái),同時(shí)也刻畫出了一個(gè)出身低微卻心高氣傲、不甘屈服于命運(yùn)的下層女性形象。
(二)性暗示與爭(zhēng)寵的外在表現(xiàn)
《金瓶梅》中有關(guān)飲食的描寫十分豐富,而關(guān)于宴飲的場(chǎng)景,往往食色摻雜、相互勾連。比如在第六回中武大郎死后,西門慶、潘金蓮二人一番云雨過(guò)后,西門慶便以潘金蓮的鞋為酒杯。三寸金蓮在以小腳為美的時(shí)代,已然成為女性的“第二性器官”,同時(shí)也成為了一種性欲的象征。正如潘金蓮初時(shí)經(jīng)常在門簾下坐著,有意露出自己的小腳,以引起門外浪子的注意。而套在小腳上的鞋,也成為了一種極具情欲象征的器皿,這就將肉體與飲食相結(jié)合,即食與色的結(jié)合。除了直接的飲食描寫,書中人物在平常生活對(duì)話之中也經(jīng)常使用與食物有關(guān)的俗語(yǔ)。比如在第二十三回中,宋惠蓮與西門慶暗中通奸,被平安兒知曉,便出言諷刺:“我聽見五娘教你腌螃蟹——說(shuō)你會(huì)劈的好腿兒。”[14]265這句話也是隱指性交,諸如此類的俗語(yǔ)在書中尚多,食物與情欲相連之密切于此可見。食物此時(shí)已經(jīng)不僅僅是單純滿足人口腹之欲的東西,更是潛入人物的內(nèi)心深處、勾出情欲的引子[16]。
瓜仁是西門慶家的常見干果,經(jīng)常一碟一碟的出現(xiàn)在餐桌上,和其他食物一樣,被賦予了情欲的含義。鄭愛月就曾親口嗑了瓜子,并親手揀了泡螺兒,差人給西門慶送去(第六十七回)。以此可見鄭愛月的心思:其一,借嗑好的瓜子仁以表對(duì)西門慶的相思之情;其二,借泡螺兒告訴西門慶,并非只有死去的李瓶?jī)簳?huì)做,由此引起西門慶對(duì)李瓶?jī)旱乃寄钪椋M(jìn)一步希望西門慶把對(duì)愛妾的情感轉(zhuǎn)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無(wú)論是鄭愛月親口嗑出的瓜子仁,還是泡螺兒,目的都是為了爭(zhēng)取西門慶的寵愛,這兩樣信物都成了鄭愛月爭(zhēng)寵的方式和手段。最終西門慶也成功地被鄭愛月的“真情實(shí)感”所打動(dòng),帶著一眾人等來(lái)到鄭愛月家進(jìn)行消費(fèi)。以此,便可確定,瓜仁也確實(shí)超出了食用的范圍,而成為一種性暗示的工具。
“嗑瓜子”的這一動(dòng)作,有意無(wú)意間唇齒的觸碰與發(fā)出的聲音,在書中所刻畫的這群沉迷于酒色財(cái)氣的人看來(lái),無(wú)疑是一種性感的流露。從年節(jié)時(shí)玳安與小玉、書童與玉簫來(lái)看,兩兩一對(duì)湊在一起嗑瓜子,但他們之間的動(dòng)作不僅僅限于嗑瓜子,更有許多肢體上的接觸。小廝與婢女尚且如此,那么便可以小見大,作為一家之主的西門慶只會(huì)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在第七十二回中,西門慶進(jìn)到潘金蓮房里時(shí),潘金蓮正踩著爐臺(tái),悠閑地嗑著瓜子等著西門慶,見西門慶回來(lái),趕忙取了盞子,用纖手抹去盞邊的水漬,親自點(diǎn)了一盞“濃濃艷艷,芝麻、鹽筍、栗絲、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瑰六安雀舌芽茶”[14]951,哄得西門慶“滿心欣喜”,便迫不及待地與婦人上床交歡,期間潘金蓮還不忘把嗑下的瓜子仁一口一口地送與西門慶吃。潘金蓮借瓜子滿足自己的情欲,在文中表現(xiàn)的十分明顯,先是點(diǎn)一盞含有瓜仁的濃茶,而這瓜仁,可能是閑時(shí)親口所嗑,這就先讓西門慶在味覺上享受一番,心情大悅,再加上佳人在旁,西門慶自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于是潘金蓮滿足自己性欲的想法也成功達(dá)成。書中多次出現(xiàn)“風(fēng)流茶說(shuō)合,酒是色媒人”,食色相通,食欲得到了滿足,色欲就被激發(fā)出來(lái)。作者對(duì)潘金蓮這一嗑瓜子的描寫,無(wú)疑是食色相通的最好證明。嗑瓜子盡顯潘金蓮之風(fēng)流,所點(diǎn)的濃艷瓜仁泡茶則盡顯潘金蓮之奉承,以口送瓜子則盡顯潘金蓮之情欲,小小的一個(gè)動(dòng)作便可看出潘金蓮為爭(zhēng)取寵愛、滿足性欲的急切心理。
《金瓶梅》被稱為“天下第一奇書”的同時(shí),也被稱為“淫書”,書中充斥著大量淫穢的性描寫,但作者對(duì)于“淫”的態(tài)度,無(wú)疑是否定的、批判的。體現(xiàn)在對(duì)人物命運(yùn)的設(shè)計(jì)上,好淫之人最終走向滅亡,比如西門慶、李瓶?jī)骸⑴私鹕彙嫶好罚际亲髡吲械膶?duì)象。西門慶因?yàn)槭秤眠^(guò)多胡僧藥而“遺精溺血”;李瓶?jī)阂蛭鏖T慶而死于“崩漏之疾”;潘金蓮為貪圖西門慶而毒殺武大郎,最終被武松報(bào)仇而殺死;龐春梅也因“貪淫不已”,而死于非命。縱觀全書,作者對(duì)潘金蓮嗑瓜子場(chǎng)景的刻畫次數(shù)最多,而這些場(chǎng)面描寫部分與她的淫欲活動(dòng)緊密聯(lián)系。
作者往往將淫欲與貪欲相聯(lián),而不僅僅是單純地寫淫,正如上文所闡述的“嗑瓜子”這一細(xì)節(jié)動(dòng)作的特殊含義,借瓜子傳情的鄭愛月,她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借此“拉客”,獲得西門慶的錢財(cái);又如韓道國(guó)的老婆王六兒,更是赤裸裸地將與西門慶的性交作為獲取利益的方式。
三、《金瓶梅》中“嗑瓜子”的藝術(shù)功能
(一)以場(chǎng)面促情節(jié)
《金瓶梅》中有大大小小幾百場(chǎng)宴飲場(chǎng)面的描寫,有些宴飲場(chǎng)面在情節(jié)發(fā)展過(gu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dòng)作用[17]。如第三回,王婆為西門慶與潘金蓮牽線,為了增進(jìn)二人的了解,王婆便整治了一桌的肥鵝、燒鴨、熟肉鮮鲊、細(xì)巧果子以及一壺酒。在酒席中,西門慶便按照王婆所說(shuō)的方法,借機(jī)試探潘金蓮的心意。從此二人便互通心意,時(shí)常來(lái)往。而武大郎知道西門慶、潘金蓮二人奸情的起因,也是因?yàn)槎苏诜績(jī)?nèi)飲酒作樂(lè),王婆攔住了找西門慶做生意的鄆哥,并與鄆哥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鄆哥一氣之下將西門慶潘金蓮私通一事告訴了武大郎,后來(lái)才有武大郎捉奸、潘金蓮毒死武大郎的情節(jié)。可以說(shuō)西門慶潘金蓮的第一次宴飲,決定了潘金蓮今后的命運(yùn),也是因?yàn)橐淮窝顼嫞Y(jié)束了武大郎的生命。宴飲場(chǎng)面的描寫與故事情節(jié)息息相關(guān),由于人物宴飲目的的不同,便導(dǎo)致了人物的走向和結(jié)局不同。
“嗑瓜子”作為書中出現(xiàn)次數(shù)較多的小的飲食場(chǎng)面的描寫,同樣也為情節(jié)的發(fā)展埋下了伏筆。如第四十六回,元宵夜西門慶宴請(qǐng)親朋好友,玉簫和書童便在一起搶著瓜子嗑,過(guò)程中還碰倒了一壺酒,被春梅斥責(zé)了幾句,二人便悻悻地分開了。此時(shí)便已暗伏玉簫與書童早有私情,但因二人感情不堅(jiān),終會(huì)離散的結(jié)局。在第六十四回中,玉簫與書童的私情被潘金蓮撞破,書童害怕被潘金蓮責(zé)罰,在不知道后果的情況下,便丟下了玉簫,自己一個(gè)人逃回老家,留下玉簫一個(gè)人,這一場(chǎng)景正與嗑瓜子一回中二人剛被春梅呵斥兩句就立刻分開的情節(jié)吻合。
同樣“嗑瓜子”的情節(jié)也發(fā)生在小玉與玳安身上,在第四十六回中,同一個(gè)元宵夜,小玉與玳安不僅一邊嗑著瓜子,還一邊家常聊著天,甚至篩酒吃肉。二人處于一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且安靜的環(huán)境中,相比于玉簫、書童嗑瓜子時(shí)的嘈雜環(huán)境,且被春梅打散的情節(jié),更襯托出小玉與玳安二人情感的穩(wěn)定與和平。在第九十五回中,月娘撞破小玉與玳安的私情,便將小玉許給玳安,二人順理成章地結(jié)為夫妻。而二人元宵夜私下相見的場(chǎng)景,儼然像一對(duì)成婚已久的夫妻,即使被琴童撞破,也只是淡然地招呼琴童喝酒,不似玉簫、書童相會(huì)場(chǎng)面一般混亂,絲毫沒有被撞破私情的窘態(tài),可見此處便已經(jīng)為玳安、小玉二人順利成婚埋下了伏筆。
這兩處嗑瓜子的情節(jié)同時(shí)也說(shuō)明了西門慶治家不嚴(yán),張竹坡就認(rèn)為西門慶家無(wú)家法,就連一直以貞潔為重的大娘子吳月娘身邊的兩個(gè)丫鬟都與小廝有染,遑論西門慶家中的其他人,在這樣的家庭之中,情欲色欲摻雜,充分體現(xiàn)了人性欲望貪婪的一面。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人們都被酒色財(cái)氣的欲望遮蔽,那么這個(gè)家庭只能一步步地走向沒落和消亡,體現(xiàn)出書中所揭露批判的意旨。
(二)以動(dòng)作塑性格
《金瓶梅》善寫人物,寫潘金蓮,又寫宋惠蓮,又寫李桂姐;既寫李瓶?jī)海謱懭缫鈨海謱憛倾y兒,善用犯筆而不犯,每個(gè)人物既有相同之處卻又個(gè)性鮮明,可見作者的藝術(shù)功力之深厚。此外,作者也通常將人物置于飲食活動(dòng)之下,通過(guò)人物的動(dòng)作、語(yǔ)言,真實(shí)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色。
書中“嗑瓜子”的描寫也是如此,潘金蓮作為一個(gè)愛嗑瓜子的人,許多嗑瓜子的情節(jié)都生動(dòng)形象地體現(xiàn)出了潘金蓮的性格。如在第十五回中,元宵節(jié)夜晚,西門慶一家妻妾都在李瓶?jī)邯{子街的房子里賞花燈,只有潘金蓮一人吵鬧,在窗口摟著衣服袖子,露出她帶滿戒指的手,嗑著瓜子,故意把瓜子皮吐落在下面行人的身上,引得不少浮浪子弟議論,直至月娘看到圍觀的人多了,才將潘金蓮叫至身邊坐著。潘金蓮這一連串的動(dòng)作,一是為引起人的注意,炫耀自己如今的富貴與地位,二是有意無(wú)意的情欲的展露。與月娘的保守、潔身自好相比,更加襯托出潘金蓮性格的張揚(yáng)與風(fēng)流成性。
書中也描寫了潘金蓮兩次在李瓶?jī)洪T口嗑瓜子的場(chǎng)景,在第二十回,西門慶娶回李瓶?jī)海瑓s因?yàn)橹袄钇績(jī)喝胭樖Y竹山之事生氣,在房?jī)?nèi)鞭打李瓶?jī)骸4藭r(shí)的潘金蓮正與孟玉樓在李瓶?jī)洪T口嗑著瓜子,聊著天,等著春梅從房?jī)?nèi)出來(lái)問(wèn)話,打聽房?jī)?nèi)的情況;同樣的場(chǎng)景出現(xiàn)在第三十回,李瓶?jī)杭磳⑸a(chǎn),家中其他人都在忙碌,就連孫雪娥都急忙趕來(lái)詢問(wèn)關(guān)切,潘金蓮卻“扶著庭柱兒,一只腳跐著門檻兒,口里嗑著瓜子”[14]349,不忘對(duì)孫雪娥冷嘲熱諷一場(chǎng)。自李瓶?jī)喝敫詠?lái),潘金蓮就把李瓶?jī)鹤鳛樽约旱臄橙耍瑤状稳魮軈窃履锱c李瓶?jī)旱年P(guān)系,不僅對(duì)李瓶?jī)哼M(jìn)行冷嘲熱諷,之后更是使用惡毒的手段使官哥兒受驚離世,讓李瓶?jī)和词圩樱蔀槔钇績(jī)核劳龅闹匾颉_@兩處潘金蓮“嗑瓜子”的場(chǎng)景,都是在李瓶?jī)菏芸嘀畷r(shí),此時(shí)的潘金蓮卻擺著一副悠閑的姿態(tài)嗑著瓜子,若說(shuō)潘金蓮的心理,第一次只是好奇房?jī)?nèi)的場(chǎng)景,且對(duì)李瓶?jī)罕淮蚝翢o(wú)憐憫之情;第二次對(duì)李瓶?jī)焊嗟氖羌刀屎驮{咒,在官哥兒呱呱墜地之時(shí),潘金蓮便生氣回房哭了起來(lái),可見潘金蓮的由嫉妒至仇恨的內(nèi)心變化。同樣是在李瓶?jī)洪T口“嗑瓜子”,但是前后兩次潘金蓮的心理卻是有所發(fā)展變化,由此可見潘金蓮善妒與無(wú)情的性格。
《金瓶梅》中關(guān)于人物活動(dòng)的描寫,以飲食場(chǎng)面為多,或是鋪張而精致,或是溫馨而平淡,真實(shí)地展現(xiàn)出明代社會(huì)的市井風(fēng)貌。“嗑瓜子”不僅成為《金瓶梅》中人物身份地位的象征與爭(zhēng)寵的方式和手段,也是在其所蘊(yùn)含的食色關(guān)系中,表現(xiàn)出作者寄寓時(shí)俗、對(duì)“淫”與“欲”的批判與譴責(zé),同時(shí)也起著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表現(xiàn)人物性格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