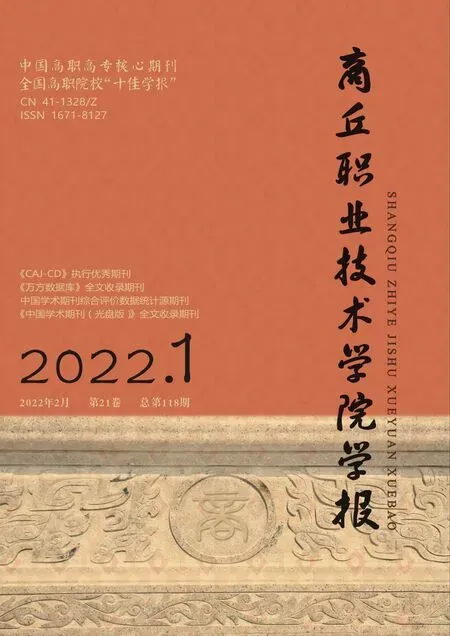《平原客》
——現代化進程下城鄉關系的新思考
韓 優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李佩甫是一位有著明確寫作對象的作家。他的作品從《紅螞蚱 綠螞蚱》到“平原三部曲”,始終圍繞著他所熟悉和熱愛的豫東平原,李佩甫也因此成為“文學豫軍”的主要人物之一。繼“平原三部曲”之后的《平原客》,是李佩甫根據轟動一時的真實社會事件“省長殺妻案”改編而成的。這部作品既是李佩甫對于自己鄉土寫作的一種延續,也是其在新情況下新的嘗試。
一、以小麥作為核心意象
植物書寫是李佩甫重要的寫作方式之一。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描寫植物,并通過這些植物來表達他對于人物的理解與情感,形成了具有鮮明個人風格的“植物書寫”。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一直在研究‘土壤’,‘平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也是我的寫作領地。在一些時間里我的寫作方向一直著力于‘人與土地’的對話,或者說是寫‘土壤與植物’的關系。”[1]李佩甫筆下的植物,既是小說敘事的切入點,更是小說中人物的歸途。
《平原客》中主要有兩種植物意象,分別是小麥和古樁梅花,其中小麥意象值得讀者關注。如果說“小說首先是建立在幾個根本性詞語上的”[2]105,那么《平原客》也可以看作是建立在植物意象上的。在《生命冊》的開始部分,作者用史詩般的語調,描述了平原眾多常見的野草和樹木。如同書中的蕓蕓眾生,這些野草和樹木既不起眼,可能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場,但卻有著頑強又驚人的生存能力。而具有這樣特點的植物和作者想要展示給讀者的人物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就像《生命冊》中的蟲嫂一樣,雖然卑微如草芥,但卻具有讓人無法忘懷的生命活力。
《平原客》舍棄了之前作品中常用的野草類的植物意象,而改用小麥這個意象是有著作者的深切思考的。盡管小麥的原產地并非中國,但根據資料顯示,隨著栽培和加工技術的逐步成熟,小麥逐漸成為我國的主要農作物之一。食物是人們的基本需求之一,對于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農耕民族來說,小麥可以說是養育我們民族世世代代生存和發展下來的根基。北方人,尤其是農民,對于小麥的情感,是潛藏在民族記憶中的,是對于饑餓的恐懼和生命的敬畏的自覺和不自覺的體現。
李佩甫之所以選擇小麥作為《平原客》的主要植物意象,原因是:首先,小麥對于中國北方人民有著特殊意義。小麥是農民的主要作物,也是人們的主要食物。小麥之于中國北方人民,正像農村之于城市。其次,小麥是主人公李德林改變命運的重要道具。李德林地位不斷提升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小麥培育上做出的貢獻。在學生時代,他因為在小麥研究中獲得了優秀成果才能夠留校任職,后來又因為小麥專家的身份才轉型為官員。“他自小是在麥田邊上長大的,是小麥給了他夢想。他是先有小麥,后有人生的。”[3]224最后,李德林自身就是一株失敗了的雙穗小麥。李德林出生在農村,是其他人口中的“黃土小兒”,但是他又憑借著自己的努力在都市中獲得了不錯的成就和地位。同時,他也出過國留過學,接受過國外的教育,所以,他的身份是多層的、復雜的,是多種文化影響下的結果。正如雙穗小麥在小說中沒有被研究出成果一樣,李德林的婚姻和事業都以失敗告終,不論是他自己的努力還是國家對于他的培養,都因他的初心不在而付之東流。
以小麥作為主要意象的還有詩人海子。海子將自己對生命的思考融入小麥與麥地,小麥是延續肉體生命的物質需要,也是詩人甚至人類的精神旨歸,它和海子詩中的其他意象一起代表著海子對人生終極問題的思考與回答。海子的“‘麥子’不僅僅是一種普通的農作物,而是一種圖騰。‘麥地’是大地的隱喻,粗糲、廣袤、充滿生命力,是勞動、創造和生存的統一。大地不僅為人類提供永恒的棲居之地,還具有龐大的接納和承擔的含義,同時是人類不能割舍的精神之鄉。麥地之于海子不是一般的收獲之地,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歸宿之地。麥地充滿了溫柔與親切,同時又是焦慮和充滿危機的”[4]。與海子詩歌中象征著人類群體的小麥意象相比,《平原客》中的小麥則更多的是對于個體生命軌跡的投射,是對更加具體化的問題的思索。與海子詩歌中頗具有神秘性的小麥意象相比,李佩甫小說中的小麥更堅實也更有泥土氣息,它是李德林喜歡的燴面,也是牽動李德林思想情緒的面葉子,也是李德林對自己的一種比喻。李德林將他的小麥理論引申到他個人的情感問題上,李佩甫則是將其對小麥的情感延續到他對于以小說主人公為代表的群體的身上,來思考這些平原客們如何尋到自己的價值所在。總體來說,李佩甫更多的是將小麥意象作為他表現人物和表達主體的突破口,使讀者能通過小麥迅速進入他所展開的問題域。
二、無法回避的鄉村
《平原客》仍舊講述的是豫東平原上這批努力扎根平原的平原客們,尤其是主人公李德林。李德林和《羊的門》中的呼國慶一樣,都是農村出身的官員,甚至二人的結局也有著微妙的相似,都以腐化墮落的結局告終。在《平原客》中,既繼承著作者對于其在前作中關于城鄉之間呈現的矛盾的思考,也體現出作者對于因為時代發展而產生的城鄉新問題的思考。
從結構上我們可以看到,李佩甫以前的長篇小說多采用雙線并行的結構:“鄉土和城市、昨日與今天、一群人的故事和一個人的命運彼此交替運行,努力讓時間呈現空間的圖形,造就一種結構上的歷史現實。”[5]而在《平原客》中,李佩甫更多地將視線放在了城市,尤其是官場的爭斗之中,農村雖是幾位主人公的出生地,但并沒有花費作者太多的筆墨。李德林回鄉在小說中被重點描寫的有兩次:第一次是在第一次結婚后和妻子羅秋旖一起回去,但因妻子無法忍受農村的婚嫁習俗匆匆離開;第二次則是在中秋,李德林在劉金鼎的陪伴下回去,但差點沒有認出回家的路。兩次回鄉體現了主人公的變化,暗示了李德林隨后將被欲望逐漸吞沒。表面上,李德林同家鄉的聯系已經非常微弱,但實際上,鄉村在小說中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留白,始終圍繞在故事的情節和人物周圍。《平原客》并非典型的官場小說,也是因為它的這一特點,雖然在小說的表層我們看到的是各級官員之間的對抗和博弈,以及巨大又復雜的人際網絡,但是作為背景的鄉村,卻又作為一種民族特有的文化,關系著這一人際網絡的建構和破裂。就像小說中的謝之長,他通過送花一步一步“跑”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成為“黑白兩道通吃的人物”。謝之長之所以能夠成功,跟他能夠迅速選擇出能夠滿足自己利益的對象,并不惜一切成本來與對方搭上關系有關。這種關系學,跟鄉土文化是分不開的。農耕生活所帶來的對于土地的依戀,使得人們之間的關系不僅是在空間上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也產生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人際關系,正是這種人際關系使得《平原客》中幾個主人公得到了足以改變人生的機遇。
成也關系學,敗也關系學。因為鄉村特有的文化而產生的人情規則在人數較少、關系也較簡單的鄉村可以很好地運行。但是,當主人公們越來越深入城市文明之中時,這種相處模式顯然無法與其相匹配。李德林出生于農村,當他成為精英人物后,他通過不斷提拔鄉村里的青年,在為城市輸送人才的同時也在回饋著鄉里。但是,李德林僅僅采用直接幫助村內人升官發財的做法,以致最后危害社會的同時也自食惡果。與李德林相比,謝之長的做法更加明顯,他通過勾連起省長、資助鄉里青年構建起一個人際關系網,并迅速財勢通天。但是,不管是省長,還是鄉里青年或者花農,他們仍舊受著其所生長的鄉村的磁石般的影響,盡管有了知識、眼界、權力和財富,仍舊無法擺脫土地,也無法改變土地。
正像趙旭東所說:“對于中國的城鄉關系而言,二者之間從來都不是完全分離開來的,很多時候二者恰恰相互聯系在一起,是作為城鄉連續的一體而存在著的。而所有城鄉關系的討論也都離不開這個城鄉連續體的存在。”[6]《平原客》也是如此。盡管同之前作品相比,《平原客》較少涉及有關鄉村的生活部分,書中的主要人物盡管出生于鄉村,作者的筆觸也主要放在他們的城市生活,但鄉村一直作為一個巨大又不可忽視的背景始終圍繞著整部小說。米蘭·昆德拉曾說:“主題是不間斷地在小說故事中并通過小說故事而展開的。一旦小說放棄它的那些主題而滿足于講述故事,它就變得平淡了。”[2]104《平原客》的可貴之處,正是它不滿足于講述一個官員如何落馬的故事,而是將這個官員作為一位典型人物,去剖析他的內心困境和思考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危機。
三、平原客將何去何從
李佩甫在書中這樣表述:“在平原,‘客’是一種尊稱。上至僚謀、術士、東床、西席,下至親朋、好友,以至于走街賣漿之流,進了門統稱為‘客’。是啊,人海茫茫,車流滾滾,誰又不是‘客’呢?”[3]352要知道,李佩甫的作品始終關注的都是平原地區生活的人們,這些人在這片土地上發展出自己特有的文化。但是,李佩甫卻將他們稱之為客而并非主人,這是很值得人們思索的。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尤其是現代性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城鄉之間原有的平衡狀態被打破,“鄉村自身的可以自我循環的水土資源也遭到了一種蛀蝕性的侵害,水土流失不僅表現在土地養分的流失上,鄉村日常建設的人才資源因此而漸漸地被吸引到了吸附力極強的城市空間中去,鄉村也就再難看到所謂真實落地的人才的會聚和功能發揮,他們成了‘回不了家的鄉村子弟’”[6]。所以,李佩甫使用“客”來形容這些來自農村且試圖融入城市的人物,既有其為鄉村不斷失去話語權的心痛,也有其對于鄉村尤其是鄉村中的人如何順應新的時代發展趨勢找到自己位置的憂思。
當然,作者不僅關注著鄉村,也同樣關注著那些在新的時代中相對老一輩的力量。與《河洛圖》一樣,作者總是“能夠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對我們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我們的靈魂狀況進行非常有洞察力的追問,他始終關注在時間范疇中個人如何能夠存在于其中”[7]。在《平原客》中,作者塑造了一個被人稱作“天下第一審”的預審員赫連東山,他有能力又有氣節,是破獲殺妻案的重要人物,也是將李德林這個人物層層剝離開來的線索人物。李佩甫在書中特意為他設置了一個支線情節,來講述他與自己兒子赫連西楚之間的代際沖突。赫連西楚和書中其他人物的奮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通過網絡游戲來賺得自己的第一桶金,并通過游戲獲得了成功。對于這樣的結果,赫連東山是五味雜陳的,他無法理解兒子“玩”出了個年薪30萬,更無法理解他認為會使人玩物喪志的游戲可以給兒子帶來財富和成功。赫連東山作為老一輩的代表是迷茫和尷尬的,同時,“東”與“西”的取名似乎也有著對立的意思,赫連東山與赫連西楚的對立不僅是前浪與后浪,也是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與西方傳播轉化過來的新的文化的對立和沖擊。正如李佩甫在結語中所說:“社會生活單一的年代,我們渴望多元;在多元化時期,我們又懷念純粹。……總之,對于人類社會來說,所謂的永恒,就是一個字:變。”[3]354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階段,變化不僅出現在空間上的城鄉之間,時間方面的代際關系之間也產生了很大的差距。因此,李佩甫對于社會巨變下人類的困境的思考,也從農民擴展到城市。在城市化進程的急遽發展中,不僅是處于相對弱勢的農村,城市中的人們也在尋求落腳點。
“在這樣的一個否定性時代,我們正在否定我們的一切,否定我們曾經有過的情感方式、生活經驗和文化方式,那些曾經慰藉過我們心靈的東西正在遠去,這些都存在于中原大地深處。作為一個中原作家,或者有責任把這種否定性思維對中國生活的影響給傳達出來。不是懷舊,而是挽救,甚至也不是挽救,而是重新尋找自我,具有真正主體性的民族自我。”[8]這也正是李佩甫作品的可貴之處和價值所在。盡管李佩甫在其作品中并沒有給我們一個答案,但是,從其各部作品中對執著于名利和欲望的人的批判和對堅守理性與正義的人的頌揚來看,李佩甫始終堅守他的道德觀念,并且也始終相信道德觀念的力量。從“平原三部曲”到《平原客》,李佩甫始終懷著一種深沉又熱愛的目光注視著這片平原,試圖去展現因時代發展而產生的困境,來喚起人們的注意。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原文化在面對新的文化沖擊下如何浴火重生,既是李佩甫所關注的,也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