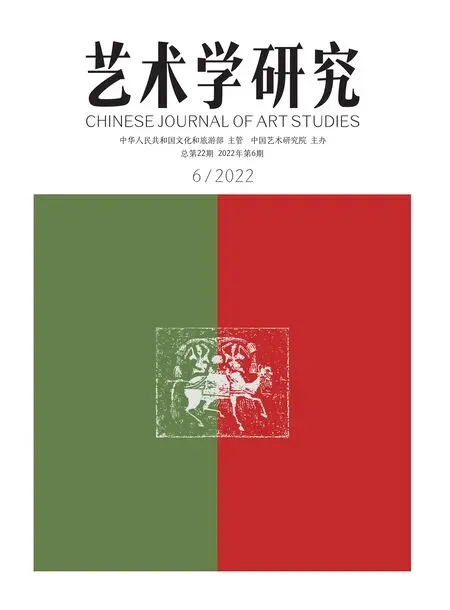“人民戲曲”與“戲改”初期的“身體”塑造
——以川劇為中心的考察
張志全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
在傳統主體哲學中,“身體”長期處于靈魂(意識)的對立面,總是受到貶抑和漠視,直到尼采開創性地提出“以身體為引線”,認為身體是比“陳舊的‘靈魂’更令人驚訝的思想”[1][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權力意志》,孫周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頁。,“身體”在哲學中的地位才得以確立。自此以降,“身體”正式出場,進而在西方現代哲學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身體”的轉向及身體理論的多元拓展,為我們考察審美活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理論架構。審美活動的主體既然是身體而不是心靈,那么回歸到身體的維度,或許是探究藝術活動所不能忽視的支點。戲曲作為借助身體表演的藝術,其“身體”的內涵包含多個層面。就舞臺表演而言,可分為戲曲藝人的身體、行當的身體、角色的身體等;就歷史演進與功能界分而言,可分為世俗的身體、革命的身體和藝術的身體等。戲曲之身體既指向藝人所依存的庶民群體與生活世界,也指向戲曲自身的藝術走向與身份定位。轉向身體的視角,為我們觀照戲曲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戲改”運動,提供了全新的解讀空間。“戲改”中的“改人”“改戲”“改制”,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身體”的規約,以及對傳統身體審美范式的修正乃至重塑。在創建“人民戲曲”的呼聲下,作為表演載體的“身體”被賦予更多的符號意義。“世俗的身體”經由革命化實踐,在向“藝術的身體”蛻變之中,呈現出多重面相,地方戲的表演生態也在這一過程中得以重構,從而推動了傳統戲曲的現代轉身。
川劇是形成較早的幾大地方劇種之一,其輻射范圍一度遍及整個西南地區。川劇在形成過程中,長期浸淫于民間的迎神賽會之中,致使其帶有明顯的世俗趣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創建“人民戲曲”的號召之下,川劇藝人順時而動,積極參與并推進戲曲改革工作,在20世紀50年代的“戲改”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為此,本文將以川劇為中心,考察“戲改”初期的“身體”塑造。
一、“世俗的身體”與戲曲表演的民間性
民間性,是地方戲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民間”孕育了地方戲,賦予地方戲獨特的民俗風貌和審美特質。有別于高雅藝術與日常生活的距離感,“民間藝術和民眾的日常生活可謂須臾不離,始終處于民眾的生活之中,是一種生活化的藝術形式”[1]季中揚:《民間藝術的審美經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頁。。民間藝術一開始并不具備藝術的身份,也難以用藝術的標準去繩墨其價值。民間藝術的產生與表演,不以審美為旨歸,或者嚴格地說,至少審美不是它的首要目的。在傳統社會中,“民間藝術”是民眾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川劇這樣的地方戲,在傳統的表演中首先強調的仍然是其現實功用——祈福禳災。因而,作為民間表演藝術,地方戲有其獨特的審美范式——如果我們可以稱之為審美范式的話,“俗”就是這一審美范式之內核。“俗”的文化品格,形構了地方戲的審美形態。就其核心層面而言,地方戲的演出是庶民群體“生命精神”的直觀體現,“藝術是人的藝術,表現的是人對宇宙的認識、感覺和體驗,所以表現生命是中國藝術理論的最高準則”[2]朱良志:《中國藝術的生命精神》,安徽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7頁。。它不注重個體的美學表達,而側重于群體的生命體悟,對“生存”“命運”的關懷貫穿于地方戲演出的始終。就外在形態而言,以“俗”為內核的地方戲,顯然迥異于文人士夫的審美表達,滲透著濃濃的泥土氣息。它似乎并不注重嚴肅而完整地演繹故事,而是要將閾限中的“狂歡”與“喜樂”進行到底。與今天的藝術觀念不太契合的“插科打諢”,乃至張揚世俗情欲的動作程式等,皆為傳統地方戲演出的日常。因而,傳統地方戲演出表現為一種“鬧熱”的狀態:在聽覺上震耳欲聾,在視覺上宏大壯觀;同時,“觀”與“演”相呼應,民眾廣泛參與,萬人空巷,激情涌動,形成特定場域的全民“狂歡”。鑼鼓震天、音聲高亢、場面驚險,是為傳統地方戲演出的常態,川劇則更是其中之“典范”。無怪乎明清方志對民間迎神賽戲的描述,幾乎都少不了“舉國若狂”這一看似夸張的字眼。
費孝通認為,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人們靠欲望行事,“欲望——緊張——動作——滿足——愉快,那是人類行為的過程”[3]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頁。。“鬧熱”是一種生存的欲望。從儀式功能而言,民眾借助“鬧熱”的場景實現對鬼疫的驅逐,也借此消除內心的恐懼。李永平認為,“從發生學的視角,祭祀儀式劇中,大鬧除祟儀式是熱鬧的原編碼”[4]李永平:《“大鬧”:“熱鬧”的內在結構與文化編碼》,《民族藝術》2019年第1期。。“鬧熱”是祭祀儀式的功能性特點,從原始的巫儺到后代的軍儺、宮廷儺儀乃至民間儺戲祭儀,無不體現出這一特點。可以說,“鬧熱”是地方戲的內在精神,是庶民社會對生命本質的體悟。從舞臺演出角度而言,“鬧熱”主要依托于演員之“身體”而展現。在傳統戲曲表演中,“身體”并未著力探尋形而上的超越之美,而慣于以感性之軀,去回應觀眾的“鬧熱”欲求,以川劇為例,其中眾多的噱頭化表演,如藏刀、吐火、變臉、下油鍋、上刀山、打叉、耍牙、擺扎(比姿式)、拉警報(唱戲時拼命拖長尾音)等舉不勝舉。當然,以上所列之噱頭,也可被視為一種超越性的表現,但這是一種形而下的超越,是對“肉身”生理性極限的超越,這種超越往往以強烈的感官刺激為目的。此類噱頭或是在恐怖血腥上下功夫,傳統川劇中以上內容比比皆是,如《盤腸戰》《鍘美案》《殺子報》《刺雍正》《半升米》等劇目中,表演“當場出彩”,出現血淋淋的鍘頭、盤腸等場面,以滿足部分觀眾的好奇心理;抑或在情欲表達上極盡夸張之能事,丟意子(飛眼)、耍舌頭、扭屁股、抖肩膀、咬手巾角等“性暗示”動作,充塞于1949年之前的戲曲舞臺,以此逗引觀眾的感官欲望,如川劇《南華堂》《別洞觀景》《園庭失巾》《傅琴斬考》《金蓮調叔》《馬寡婦開店》等,大多表現男女調情和思春等內容,其舞臺動作可謂露骨至極。
對感官刺激的追求,致使“身體”往往偏離敘事的軌跡,出離于角色功能之外。演員對角色的“身體”往往失去應有的掌控能力和凈化能力,“身體”受制于觀眾的世俗趣味,甚至淪為流俗的代言者。如舒斯特曼所言,“作為背景的身體習慣與特質感受,必然受制于環境,即身之所處及身體從中獲取能量及活動空間的地方”[1][美]理查德·舒斯特曼:《通過身體來思考:身體美學文集》,張寶貴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68頁。,傳統戲曲中演員的身體浸染著民間日常的世俗氣息,其在舞臺上表演的“身體”自然也受到這一身體的約束,必然具有世俗性。不過,如果將“世俗的身體”僅視為一種庶民群體的全部身體表達,就忽略了地方戲演出所隱含的藝術屬性。作為以歌舞演故事的舞臺表演形式,以“身體”演繹好故事終究是演員不能忽略的本分。因而,游曳于庶民空間的“世俗的身體”,始終存在著一種離心力,這力量源自“藝術”的召喚,也正因如此,才促成了近代地方戲舞臺藝術的現代轉變。
二、革命實踐與“身體”的革命化
“身體”是一切事物的起點,也是革命實踐的著力點。對于傳統的戲曲藝人而言,由“世俗的身體”向“藝術的身體”轉變,首先須經歷“身體”的規約,實現“身體”的革命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新政權即借用了“翻身”這一頗為形象的表述方式來闡釋當時的政治運動。可以說,這是從身體經驗出發,向民眾宣傳新社會的“人民性”。毋庸諱言,土地改革,以及“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運動,賦予“翻身”以生動的革命實踐,使普通民眾對“人民性”有了形象而直觀的理解。相較而言,戲曲藝人對“翻身”的體會,顯得更為直接。政治運動的深入推進,必須輔以能為民眾所接受的宣傳方式。戲曲——這一在傳統社會中為普通民眾所喜聞樂見的娛樂樣式,在經歷近半個世紀命運攸關的論爭之后,終于確立了自身在新社會的身份。戲曲藝人廣泛參與文藝宣傳活動,承擔著傳播新思想、新觀念的時代重任,因而他們既是“翻身”的受益者和親歷者,又是“翻身”故事的講述者和演繹者[2]張煉紅在《歷煉精魂:新中國戲曲改造考論》一書中也說道:“很難想象,在中國五六十年代特別是建國初期的社會政治文化的轉型過程中,假如沒有收編到這樣一支指揮自如、訓練有素、且能廣泛深入民間的群眾性‘宣教’隊伍,那么各項政策的上傳下達還能否進行得如此順利。而正是憑借著無與倫比的政治宣傳和教化功能,藝人們才獲得前所未有的‘新生’和‘榮耀’。”張煉紅:《歷煉精魂:新中國戲曲改造考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7—378頁。。“翻身”及其相應的政治實踐,在戲曲藝人身上不僅體現為作為“人民群眾”的“翻身”事實,還表現為對“翻身”歷史的“身體化”、儀式性演繹。就此而言,“翻身”本身寓含著另一層意義,那就是“身體”的革命化。革命化促使“身體”脫卻舊時代的世俗性,由外(動作、儀態、服飾等外部特征)而內(思想觀念)進行重塑,以此響應火熱的革命運動。
一般認為,“戲改”之中,加強政治理論學習與培訓,組織藝人工會和各種社會團體等,是促使藝人轉變思想觀念的核心舉措。也就是說,藝人主要是通過參加學習、接受教育等活動進行思想改造,提升思想境界——是“意識”而不是“身體”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然而,戲曲藝人群體的“意識”是否能在短時間內實現這一“革命性”轉化,他們是如何從一個文盲與半文盲的狀態迅速轉化為新社會的建設者的?其思想改造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細究起來,倘若依循傳統觀念,很難對以上問題作更明晰的解答。借助“身體理論”,我們發現戲曲藝人的“身體”經驗,或許是考察“戲改”不能忽略的一個重要環節。“身體是身份重塑的載體”[1][法]帕斯卡爾·迪雷、佩吉·魯塞爾:《身體及其社會學》,馬銳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頁。,“身體是我們身份認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維度。身體形成了我們感知這個世界的最初視角,或者說,它形成了我們與這個世界融合的模式。它經常以無意識的方式,塑造著我們的各種需要、種種習慣、種種興趣、種種愉悅,還塑造著那些目標和手段賴以實現的各種能力。所有這些,又決定了我們選擇不同目標和不同方式。當然,這也包括塑造我們的精神生活”[2][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程相占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3頁。。可見,身體是“身份重塑”與“身份認同”的核心要素。戲曲藝人理解“翻身”,最直觀的感受來自“身體”經驗。由此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對于戲曲藝人而言,或可理解為規約“身體”的儀式。政治身份的確立以及政治運動的開展,使戲曲藝人感受到迥異于過往的“身體”體驗。他們可以作為藝人代表出席會議;可以參加各類政治運動,擔負宣傳教育的職責;可以擁有自己的社團組織,并以“戲曲”作為畢生的事業。在身份上,他們不僅是新社會的“主人”,更是創建“人民戲曲”賴以依憑的“戲曲演員”“文藝工作者”“戲劇表演家”和“戲劇家”等。正如時任重慶市文聯副主席的沙汀在動員文藝工作者積極參加“三反”“五反”運動宣傳會議上所言,“文藝工作者只有從實際斗爭中,體驗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從而提高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才不致于在創作上犯錯誤”[3]耕心(沙汀):《配合宣傳“三反”“五反”運動 重慶文藝工作者五十人已深入運動并組織創作》,《觀眾報》1952年4月12日第1版。。可見,實際斗爭所獲得的“身體”感受,是思想改造最為可靠的方式。正是基于“身體”的革命實踐,促成了“舊藝人”迅速向“新演員”的身份轉變。
更為重要的是,戲曲藝人在參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以及義演賑災、勸募公債、提倡戒煙和宣傳婚姻法等活動的宣傳演出中,擔負著以舞臺形象宣傳“新思想”“新觀念”的重任。基于對“戲改”與創編新戲工作的配合,藝人往往需要在新編時事劇中,扮演革命運動中的角色,重返革命儀式的現場。因而,戲曲演出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宣傳與娛樂活動,而是實實在在的“身體”經驗。例如,為配合反霸運動,根據真實事件編寫的新川劇《槍斃連紹華》,其人物原型連紹華為臨江門一帶的惡霸,原系國民黨特務,于1950年5月14日經群眾公審后被槍決。此事件在短短數月后便被搬上舞臺,重演公開處決的過程,為反霸運動進行宣傳,其懲戒用意自不待言。對于藝人而言,這是身體革命化——“肉身”再度接受規約的儀式,是一次徹底的“身體”實踐。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戲曲界,為配合革命實踐,編演了很多時事劇。以川劇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在“戲改”最初的兩年里,新編或改編的時事劇有《槍斃連紹華》《一貫害人道》《槍斃馮丹書》《海底冤》《易定乾》《檢舉特務》《大惡霸龍腹謙》《紅杜鵑》《地主的花樣》《小二黑結婚》《白毛女》《九件衣》《人民的死敵》《唇亡齒寒》《人民功臣萬年紅》《土地回家》《為楊云清烈士報仇》《美軍獸行》《打美帝去》《復仇的怒火》《鴨綠江畔》《漢城烽火》《保家衛國》《援朝別家》《群丑哭宮》《臺灣夢》《參軍光榮》等代表性劇目。以上迥異于傳統劇目的新戲的上演,本身是依托“身體”而實現的。只是這一“身體”逐漸褪去“世俗的色彩”,被賦予革命化的符號意義。在演出以上劇目過程中,藝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角色”浸染,比如為了扮演地主、惡霸、特務與革命家、戰士等不同形象,他們不得不以“身體”去體驗不同角色的性格、動作與語言。因而,演出的過程,也是他們感知新社會氣息、觸摸革命新風的過程。過去演出時生旦凈丑的程式動作,顯然不再適應于這樣的舞臺。藝人對新“角色”的嘗試,盡管猶如幼童學步,然“身體”經驗,是藝人領悟“革命實踐”最便捷的方式。日本戲劇家鈴木忠志在《文化就是身體》中,談到日本能劇的“跺腳”動作有助于“讓演員感覺到身體內在的力量”,“可以創造出一個虛構空間,甚至是一個儀式空間,在這樣的一個空間里,演員的身體能完成從個人到普遍的轉化”[1][日]鈴木忠志:《文化就是身體》,李集慶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頁。。具身化的“跺腳”動作,可以在反復實踐中超越動作自身的“機械性”,進而激發出內心的“信仰力量”。在“戲改”初期,一系列配合政治運動所創編的新戲上演,事實上就是通過演員對“革命性”表演動作的不斷模仿與練習,創造出特定的信仰空間,而演員也借此發現身體內部的自我意識,使“身體”的實踐逐漸內化于心,并促成思想境界的革命性轉變。
三、“人民戲曲”與身體塑造的藝術尺度
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的《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對戲曲改革的“人民性”作了如下界定:“人民戲曲是以民主精神與愛國精神教育廣大人民的重要武器。……戲曲應以發揚人民新的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爭與生產勞動中的英雄主義為首要任務。凡宣傳反抗侵略、反抗壓迫、愛祖國、愛自由、愛勞動、表揚人民正義及其善良性格的戲曲應予以鼓勵和推廣,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隸道德、鼓吹野蠻恐怖或猥褻淫毒行為,丑化與侮辱勞動人民的戲曲應加以反對。”[2]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董健、胡星亮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大系》第三卷上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人民戲曲”將國家意志、民族精神貫注其間,賦予戲曲強烈的家國意識。“人民戲曲”的提出,隱含著對傳統“戲曲”概念的重新定義,從劇本到舞臺,從表現內容到表現形式,從外在形態到內在屬性等,都隨之發生根本改變。可以說,傳統戲曲向“人民戲曲”的轉向,是一次具有深刻意義的轉向,其中最核心的是身體審美的轉向——“人民戲曲”賦予“身體”更為豐富的內涵,在“人民藝術”的尺度下,“身體”理應凈化感性的過度欲望,轉化為藝術的載體,乃至成為藝術自身。
創建“人民戲曲”的革命化訴求,本質上是對身體的塑造。田漢在1950年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修改舊劇的步驟,首先是進行最必要的消毒,即拋棄其有害于人民的腐朽的、落后的部分,如鼓吹奴才思想的,殘酷、恐怖、野蠻、落后的部分,而保存和吸取其有利于人民的健康的、進步的部分,作為優秀傳統繼承下來,并在新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加以發展,這樣,舊的民族戲劇藝術就變成新的人民戲曲,成為新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1]田漢:《為愛國主義的人民新戲曲而奮斗——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在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摘要》,董健、胡星亮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大系》第三卷上冊,第108頁。。“消毒”就是要消除危害人民的、腐朽落后的成分,是“戲改”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消毒”涉及多個層面,就舞臺表演而言,其實是對身體作出具體要求。顯然,“人民戲曲”的舞臺不容許存留絲毫舊社會的痕跡。傳統戲曲舞臺上的蹺工、磕頭、行乞、辮子、酷刑兇殺以及鬼魂等表現內容,被列入“革除”的范圍。蹺工是展現女性小腳的技巧,因而被視為“集中地表現中國歷史上婦女被壓迫被屈辱以致生理殘廢的病態”[2]馬少波:《清除戲曲舞臺上的病態和丑惡形象》,董健、胡星亮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大系》第三卷上冊,第116頁。,是封建社會摧殘婦女的標志,與“人民性”背道而馳,有悖于身體的“革命化”進程;磕頭、行乞被視為舊社會下層民眾受壓迫的屈辱性動作,辮子則是清政府“剃發令”的痛苦記憶,酷刑與兇殺違背了藝術的本質,理應從舞臺上消失;同時,要破除封建迷信,象征因果報應的陰曹地府與鬼魂形象自然應被革除。本著革命化的宗旨,作為符號的身體,需要進行徹底的改變。身體“革命化”的目的,是為了更廣泛的“革命實踐”,以借助“身體”傳播新的價值觀念。
當然,“人民戲曲”本質上屬于藝術層面的界定。正如田漢所言,“戲改”就是“使中國戲曲脫胎換骨,成為真正人民需要的藝術”[3]田漢:《為愛國主義的人民新戲曲而奮斗——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在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摘要》,董健、胡星亮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大系》第三卷上冊,第112頁。。作為藝術的“人民戲曲”,就演出空間而言,將由神廟、廣場、院壩等場所轉向劇場,成為不折不扣的“劇場藝術”;就演出屬性而言,將由游戲性演出轉化為“人民藝術”的嚴肅表演;就審美層級而言,將由重感官的審美愉悅轉向重心意和精神人格的審美愉悅。戲曲是“身體”的表演,戲曲表演是依托被規約的“身體”,在功法與程式中演繹人生百態。以被規約的“身體”詮釋生命之精神,是新時代戲曲藝術的本質規定。對身體表演嚴肅性的要求,是“人民戲曲”確立自身藝術屬性的基礎環節。“戲改”消毒的對象,除上述所列之外,還包括丟意子(飛眼)、抖肩膀、咬手巾角、搖屁股等淫褻動作,以及打屁股、擤鼻涕、檢場、走尸、飲場、把場、抓哏逗笑等內容[4]馬少波:《清除戲曲舞臺上的病態和丑惡形象》,董健、胡星亮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大系》第三卷上冊,第116—124頁。《觀眾報》于1951年9月8日(第43期)、9月15日(第44期)、9月22日(第45期)連續轉載馬少波《關于澄清舞臺形象》一文,并由此開啟重慶戲曲界關于澄清舞臺形象的討論;該報自1951年12月22日(第58期)開始,連載羅健卿的《澄清川劇舞臺形象》,包括對“陰曹地府”“惡俗的噱頭”“抓哏逗笑”“不好的武功”“丑惡恐怖的死”“小腳”“淫蕩的動作”“侮辱勞動人民的戲”“磕頭乞討”“不合理的裝飾”“兇殘丑惡的道具”“當場出彩”等內容的討論。。如果說對前述蹺工一類的革除偏重于意識形態層面的界定,那么對這一類別行為的革除則回歸到藝術本位,側重于舞臺藝術自身的嚴肅性層面。其中,檢場、走尸、飲場、把場主要指的是舞臺表演中不合規范的陋習,與“身體”本身的關聯度不大,在此姑置不論;而淫蕩猥褻的動作,以及打屁股、擤鼻涕、抓哏逗笑等表演,是傳統社會民間戲曲表演中為迎合觀眾的低級趣味而采用的噱頭表演,這顯然與舞臺藝術的嚴肅性格格不入。以上表演,除淫蕩猥褻的動作在旦角身上也頗為常見外,其他表演大多發生在丑角身上。在傳統戲曲中,丑角多以插科打諢來調節氣氛,往往會雜以低俗的言行來逗引觀眾,這不僅偏離劇情,而且也偏離了藝術的軌道,甚至阻撓了故事的演繹。因而,對丑角及其插科打諢的規范,也是“戲改”的分內之事,“丑角在一定的場合打諢是可以的,但要照顧到劇情發展及所扮演的身份,要做到適可而止。過分的做作不但破壞了戲劇的嚴肅性,觀眾也會起反感的”[1]熊景萍:《談京劇中的丑角和配角》,《觀眾報》1951年8月19日第2版。。可見,嚴肅性作為規范“身體”的尺度,已然超越意識形態的畛域,轉而成為戲曲藝術的基本尺度。從表演層面而言,對那些民間表演陋習的抵制,也是在“人民藝術”觀念下強化身體意識的結果——“世俗身體”的表演徹底告別戲曲舞臺,從而為地方戲向“人民戲曲”的轉向奠定了基礎。
作為劇場藝術,嚴肅性不僅是對演員身體的規定,也是對觀演空間的“身體”規約。“人民戲曲”是服務于人民的藝術,其概念隱含著對觀眾群體的界定。其一,戲曲觀眾屬于社會主義新人,觀眾群體主要包括翻身的工人、農民,以及共產黨員、革命干部等[2]裴東籬:《戲曲要面向觀眾》,《觀眾報》1951年2月4日第1版。;其二,戲曲觀眾應當具備欣賞劇場藝術的能力。在傳統的觀演空間中,演員的“身體”是隨意的,觀眾的“身體”也是隨性的。觀眾在劇場之內,聊天、吸煙、喝酒、嗑瓜子、吃零食等皆習以為常,劇場儼然變成休閑場所。他們可以對演員的精彩表演喝彩叫好,也可以對演員無意間的失誤予以粗俗的懲罰,如以濃煙熏演員等。一旦臺上演員有向觀眾磕頭行乞等類似的表演,則毫無顧忌地向演員拋擲鈔票、果皮、香煙、石塊等,以致嚴重影響劇場秩序和舞臺表演。這種現象,在“戲改”早期仍然普遍存在。這是傳統觀演關系及觀演習俗的遺存,是傳統戲曲藝人作為“優伶”的低賤地位在劇場空間中的表現。因此,“戲改”其實也是對觀眾“身體”的一種規約。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據阿甲回憶,延安平劇研究院的舞臺態度相當認真嚴肅,演員為部隊演出,野地搭臺,不避酷暑嚴寒;而臺下的萬千戰士,席地而坐,巍然不動,秩序井然[3]阿甲:《你們是人民心目中喜愛的花神——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紀念發言》,《戲曲藝術》1983年第2期。。客觀地說,觀眾的“戰士”身份,為觀演空間的嚴肅性附加了籌碼。不過,對觀眾的嚴肅性要求,既與觀眾群體的“身份”變化相關,同時也是“人民戲曲”藝術定位的基本標準。觀眾理應擔負起相應的責任,為“人民戲曲”的創建而對自身行為予以約束,做新中國的“新觀眾”。時人意識到,“人民的新戲曲需要廣大觀眾來支持,需要觀眾對于好戲曲,好表演,好的演員給予適當的鼓勵;對于壞戲曲,壞表演,壞演員給予嚴肅的批評;需要觀眾正確的向戲曲界指出什么是應該提倡的和什么是應該反對的”,“新的觀眾的數量的增加,欣賞水平的提高,以及對于戲曲事業的熱切關心和對于演員的關系的改善,將是今后戲曲改革工作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4]謝代:《做新觀眾》,《觀眾報》1951年12月15日第2版。。在“人民戲曲”的創建過程中,觀眾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觀眾不僅要管好自己隨性的“身體”,更應當提升自我的藝術修養。
嚴肅性似乎只是地方戲藝術轉向的最低門檻,然而“戲改”初期由凈化舞臺而引出對“身體”表演的嚴肅性規范標準,其言外之意已然超出“凈化”的字面意義。“戲改”初期列為舞臺清除對象的“病態和丑惡形象”,相當一部分屬于滿足民間低級趣味的媚俗行為,因此對這部分“病態和丑惡形象”的革除,也是對一種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健康的、審美的舞臺藝術的呼吁,其本質上體現為一種身體審美的轉向。1951年,重慶戲曲界曾圍繞賈培之、周慕蓮、周企何等川劇名角聯袂演出的《柴市節》一劇進行討論,論者普遍主張刪減“哭頭”這場戲,認為在文天祥被斬首后,歐陽夫人抱著血淋淋的人頭哭訴其生平事跡,“就舞臺的形象來說是殘酷的,就藝術的完整性來說,它是破壞了《柴市節》的完美結構和劇情的發展,它是累贅的”[1]胡度、王向辰:《修改川劇〈柴市節〉劇本的經過》,《觀眾報》1951年8月5日第2版。。相反,時人對于幾位藝術家在劇中所展示的演技,皆給予充分肯定,認為他們“都是鉆研了多年的老手,對于劇中的性格,心理,把握得相當合適。賈培之演的文天祥正義不屈,偉大氣節,而又不失其人情味。周企何演的劉(留)夢炎,臉厚無恥,形容盡致,一眨眼,一彈指,一字輕重,可說是渾身是戲。周慕蓮演的歐陽夫人,表演悲痛到極點而又不便號啕痛哭的悲情,深刻細膩”[2]辛之:《記二次戲曲觀摩演出座談會》,《觀眾報》1951年7月8日第2版。。藝人不能再以夸張的噱頭取悅觀眾,而應在對角色的體驗中,促成身體動作的心理化、性格化與審美化。可以說,身體審美最終走向的是對“肉身”的否定,由具象的“身體”上升到理性的“身體”。“人民戲曲”指向的是超越世俗欲望的舞臺藝術,有著對“藝術身體”的本質規定。戲曲演員要在舞臺上綻放“藝術”的神韻,需要超越偏重感官的形而下之“術”,提高自身的藝術修養,領悟藝術之“道”,發掘身體固有的形而上之維度,實現“身體”的藝術化。“凈化”舞臺,無異于在一定程度上為藝人的舞臺表演設定了界線和禁區,使藝人從身體的角度感受到“人民藝術”的舞臺規定,領悟到“人民戲曲”的藝術標準,這在一定層面上為藝人“身體”的藝術化明確了方向。同時,從觀眾的角度視之,“凈化”舞臺作為一種審美導向,也促使觀眾審美趣味和審美習慣開始發生改變,從而重塑了戲曲觀演空間的法則。
綜上言之,“身體”早已超越生物學的范疇,被賦予廣泛而深刻的“背景”意義。重審“戲改”,“身體”不能缺位。“身體”是“戲改”的主體,也是“戲改”的客體。“戲改”的“革命化”與“藝術化”雙重目的,主要憑借“身體”而實現。通過“身體”,藝人確認自己的藝術家身份;通過“身體”,藝人重溫革命儀式;通過“身體”,藝人感知舞臺演出的禁區……盡管經歷了曲折和困境,但通過“戲改”,藝人的“身體”得到前所未有的革命化塑造,而肉身的體驗反哺于意識,使藝人對“藝術”“人民戲曲”等概念有了更為切身和清晰的認識,從而助推了“戲改”工作的進程。可以說,正是在對身體的規約中,重塑了戲曲的審美范式,從而推動了傳統戲曲的現代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