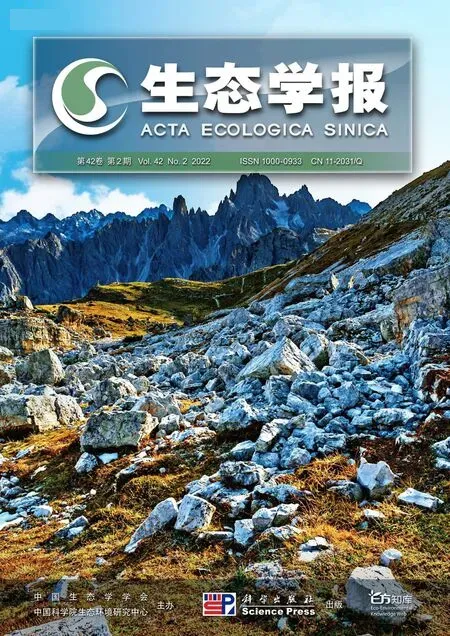魚類對海洋升溫與酸化的響應
王曉杰,謝金玲,袁一鑫
1上海海洋大學 海洋生物系統與神經科學研究所,上海 201306 2上海海洋大學 國家海洋生物科學國際聯合研究中心,上海 201306 3上海海洋大學 水產種質資源發掘與利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上海 201306
自工業革命以來,由于人類燃燒化石燃料,向大氣釋放了大量CO2,導致地球表面平均氣溫升高大約 0.7℃,并且以此 CO2排放速率計算,至 21 世紀末地表溫度將升高 2—4℃[1]。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約1℃已經改變了物種的地理分布,海洋變溫動物通過向兩極擴散來尋找溫度適宜的水域[2]。由于海-氣CO2交換,人為排放的CO2總量的四分之一進入海洋,引起海水化學改變,包括海水中溶解CO2的量增加,海水pH從工業革命前的8.2,至2100年將會降低到7.8,以及降低生物組織中碳酸鈣的溶解度[3—5]。
海洋魚類盡管具有較強的酸堿調節能力,但也可能受到酸化的不利影響[6—13]。并且,溫度是魚類生理和生態的主要非生物決定因子[14—15]。海洋升溫也將對海洋魚類產生廣泛影響,包括已有報道的向兩極擴散[16—17]和降低低緯度魚類的生長率[18]。目前,升溫和酸化雙重環境脅迫因子對海洋魚類影響的研究也開始引起關注[8, 19]。海水升溫和酸化不僅能夠直接影響魚類的生理和行為,也可能通過改變棲息地環境以及改變食物網結構而間接影響魚類[20]。而魚類同時也是海洋食物網的中心環節,海洋環境對魚類資源的影響必將影響全球漁業資源產量[21]。
為此,本文綜述了海洋酸化、海洋升溫以及兩者共同作用對魚類的影響,為預測魚類響應全球海洋環境變化的趨勢提供相關依據。
1 海洋升溫對魚類個體、種群及生態系統的影響
至21世紀末,全球海洋的平均溫度將升高2.6—4.8℃[22],這將對不同區域、不同魚類造成不同的影響。在赤道及兩極地區,海水水溫的日變化和季節變化較小[23—25],耐受溫度變化范圍較窄[26],溫度變化一旦超出其適宜范圍,海洋魚類將消耗更多能量用于維持日常代謝,因此會降低其生存適宜度[27]。這些魚類或者通過生理調節適應升溫,或者遷移到其他溫度適宜的緯度或水深度,也可能在局部地區徹底消失[16]。溫度變化會影響魚體內生物化學反應速度和代謝速率[28—29],進而影響生長、覓食和繁殖等生命過程中能量供給,這將間接影響魚類種群分布、群落結構及生態系統功能。
1.1 海洋升溫對魚類生理代謝影響

圖1 溫度對魚類有氧范圍的影響Fig.1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aerobic range of fish
不同種類、不同地理區域的魚類對溫度耐受范圍不同。經研究發現,有氧范圍是決定魚類溫度耐受能力的重要因素。有氧范圍即基礎氧氣攝取和最大氧氣攝取之間的間距(圖1)[30]。溫度升高對有氧范圍的影響是海洋升溫影響魚類存活最重要的生理機制。伴隨溫度升高,魚體合成代謝需氧量增加,然而水中溶解氧卻在下降,魚體血液循環和呼吸系統的能力不能滿足基礎代謝氧氣需求量的增加。氧氣需求量和氧氣供給量之間的不平衡將會限制有氧范圍,而有氧范圍的減少將會降低魚類生存適宜度[27, 31]。
熱帶海洋魚類生活在水溫相對恒定的環境中,他們對于海洋升溫更加敏感。當水溫升高至比夏季平均水溫高 2—4℃時,5種珊瑚礁魚類基礎代謝耗氧率升高,而最大氧氣攝取量并不增加,從而造成有氧范圍的下降[32]。對于絕大多數海洋魚類,在發育過程中首先經歷浮游生活階段,然后到近岸適宜棲息地定居,其中外海漂浮生活的仔魚最容易受到環境改變的影響,死亡率較高[33]。從1998年到2011年,從澳大利亞Lizard島共采集10批次剛定居的雀鯛(Pomacentrusmoluccensis),通過耳石微結構分析,推算仔魚漂浮階段的時間(pelagic larval duration, PLD)和仔魚的日生長率。研究發現隨著溫度升高,PLD逐漸下降而生長率不斷增加,而當海水溫度超過28℃后,溫度再升高,PLD趨向增加而生長率卻在下降[34]。實驗表明,魚類對水溫的耐受能力與水溫之間是呈傾斜的圓頂形的關系,在最適溫度范圍內,魚類的生長率會隨水溫升高增加,但是當水溫高于最適溫度后,其生長又會快速下降[26]。通常變溫動物在溫度升高時,會降低食物特殊動力系數,減少對食物消化、吸收和同化作用的能量消耗,以此維持日能量收支平衡[35]。但是,對出膜6—9d小丑魚(Amphiprionpercula)基礎代謝、餐后代謝反應的研究,發現升溫提高仔魚基礎代謝率,對餐后用于消化和吸收的能量消耗卻沒有影響,因此在海水溫度升高時,仔魚可能需要尋找更多食物才能維持正常生長速率[36]。而當食物不充足時,升溫增加能量消耗,用于生長和發育的能量相應地減少,導致仔魚生長速度下降,降低變態成功率[37]。并且,在野外長期的觀察也發現海洋升溫對魚類早期發育的潛在威脅。在長達58年對加利福尼亞州南部海區43種魚類幼魚的物候學研究中發現,在近十幾年,39%的種類(主要是外海漂浮性魚類)季節豐度最高值提前,19%的種類(主要是近岸底棲性魚類)延后。而浮游動物的物候學并沒有隨之提前,因此,那些物候學沒有與浮游動物同步改變的魚類將得不到充足的食物,最終減少漁業補充量[38]。
在溫度較高的環境中,生物個體趨向變小,因為這樣可以增加表面積與體積比,從而容易保持氧氣吸收和消耗平衡[39]。在40年間,伴隨著冬季水溫升高1—2℃,北海8種主要的經濟魚類中的6種,其漸近體型的大小隨之下降,從而使這些群體的單位補充漁獲量平均降低23%[40]。從全球角度,由于海洋升溫使得小個體魚種可能代替大個體魚種,據估計到2050年,魚類集合平均最大體重將會減少14%—24%[41]。
某些海區海面平均溫度的升高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氣溫的升高速度,等溫線在向兩極移動[42]。作為物種表型可塑性的一種方式,行為溫度調節可以降低環境溫度改變對物種和種群的不利影響。魚類是外溫動物,通過遷移活動來維持體內適宜溫度,而最適溫度理論上反映了魚類有氧運動能力的最適溫度。然而,目前許多熱帶魚類所在緯度的最高溫度已經接近它們的最適溫度[43]。因此,這些種群可能就會暫時性地遷移到更深水層或者高緯度等水溫更低的水域,以此降低基礎代謝消耗。最近的報道稱有80種熱帶和亞熱帶的草食性魚類的生活區域已經擴散到了溫帶珊瑚礁區[44]。
1.2 海洋升溫對魚類與其他物種間相互關系的影響
在以往研究全球氣候變化影響時主要關注全球升溫對單一物種直接的生理影響,然而最近通過對陸地和淡水系統的長期數據(>20年)的meta 分析發現,全球升溫對魚類分布區域改變,以及帶來新的種間關系的影響,更有可能改變整個生態群落的結構和功能[45]。
當小生境水溫不同時,魚類會通過遷移尋找適宜溫度的棲息地,尤其是當食物鏈頂端的捕食性魚類對溫度比較敏感,它遷移棲息地后,將會改變食物網結構和能量流動。例如,湖紅點鮭(Salvelinusnamaycush)是冷溫性魚類(適宜溫度10—12℃),對溫度敏感,是美國北部湖泊中頂級捕食者,是食物網中關鍵物種。夏季平均氣溫從15—20℃變化過程中,因為湖泊中有溫度分層,鮭魚會離開水溫較高的近岸,而游向水溫較低的深水區,與此相伴,它對來自近岸的小型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的捕食量將會下降,而更加依賴深水區的浮游植物的生產力,使得湖泊中食物網結構發生改變[46]。而這種基本食物網結構再造,會通過調節到捕食者的能量通量,改變生物量積累,在環境變化快速時期終將威脅到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
在全球,隨著海洋升溫和海流的向極化增強,許多熱帶魚類入侵至溫帶海域,由于物種入侵,海洋升溫將會間接影響魚類與其他物種間的關系,進而影響到群落結構和海洋生物多樣性。入侵物種主要是珊瑚礁關鍵草食性魚類,例如獨角魚(Nasounicornis)、鸚鵡魚、兔子魚(Siganusrivulatus)和刺尾魚屬(Acanthurussp.)的一些種類。其中,熱帶草食性兔子魚,因為海水升溫經蘇伊士運河拓殖到地中海,并建立了大量的種群。他們破壞了近岸大型海藻林,并阻止新藻場的建立,深刻改變了近岸巖礁系統[44]。澳大利亞東部地處熱帶-溫帶過渡地帶,有海藻森林這種關鍵棲息地。進行長期觀測發現,10年間水溫升高0.6℃,伴隨著入侵的草食性魚類種類增加以及高溫下這些魚類較高的啃食速率,海藻林逐漸減少,最后消失。同時,當地之前豐富的魚類群落也逐漸消失,取而代之以熱帶草食性魚類占優勢的群落[47]。在日本南部部分海區觀察到珊瑚已入侵至緯度較高的溫帶海區,珊瑚-海藻相互作用增強,這些區域正在以海藻為主慢慢轉變以珊瑚為主。如果大型海藻場消失而不是被替代,那么物種多樣性會急速下降,然而,若被珊瑚替代,那物種多樣性可能不受影響,甚至會增加。據估計到2100年,大范圍入侵將會導致多區域群落間的物種趨同化,從全球看局部物種豐富度凈增加,在入侵物種多的海域將會形成非相似群落[48]。
受全球升溫影響,海洋魚類分布區移向高緯度和深水區。利用捕撈平均氣溫指數,分析1970—2006年間的年漁業捕撈量,得知海洋漁業捕撈量受氣溫變化的顯著影響,在高緯度地區暖水性物種占捕撈優勢種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在熱帶海區亞熱帶物種捕撈量越來越少。這種捕撈組成的改變對沿岸地區漁業經濟發展有較大影響[41]。例如,金槍魚具有重要經濟價值,它們依賴于逆流熱交換系統維持體溫高于環境水溫,因而水溫是決定其分布的重要因素。熱帶金槍魚主要分布于水溫高于18℃的水域,然而1967—2011年間延繩釣捕撈量的數據顯示,在大西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亞熱帶水域中熱帶金槍魚的捕獲百分比呈上升趨勢。由此表明,伴隨全球變暖,熱帶金槍魚種群在向兩極移動[49]。
2 海洋酸化對魚類早期發育和行為影響
2.1 海洋酸化對魚類早期發育影響
研究表明海洋魚類對海洋酸化具有較強耐受性,因為成魚可以通過鰓和腎臟進行酸堿調節[9, 50],然而幼魚由于呼吸和離子交換模式與成體不同[51],并且與成魚相比具有較大的表面積和體積比[52—53],因此幼魚對海洋酸化比較敏感。酸化會影響一些魚類的胚胎發育[54]、仔稚魚的生長[6],破壞仔魚組織和器官結構[10],降低仔魚存活率[6]等。然而,也有研究發現,海水酸化并不影響精子和卵子的受精率[55]、受精卵的孵化率[56]、仔魚的生長和發育[7, 10—11, 56—57]以及游泳能力[58]等。盡管這些研究在海水中CO2分壓為700—900 μatm 時(以目前CO2排放速度,到21世紀末海水中CO2分壓),對魚類存活等并未造成直接的影響[59],但是,酸化對魚類造成的亞致死效應將可能是影響個體甚至種群最大的危險因素[60]。例如,酸化造成魚類生長緩慢,個體變小等,在自然種群中,這些個體將會增加被敵害捕食的幾率、降低獲得食物的能力,進而會增加死亡率[61]。
2.2 海洋酸化對魚類行為的影響及其機制
在以往的研究中高CO2的研究主要從 H+濃度升高帶來的酸性效應研究對魚類影響,大多研究發現魚類具有高效的酸堿調節方法,認為魚類可以耐受較高的CO2分壓。
直至2009年在對大堡礁魚類的研究中,發現酸化會影響珊瑚礁魚類的感覺和行為。Philip L. Munday 首先報道了酸化海水會干擾小丑魚幼魚嗅覺對不同氣味的辨別能力。在正常水體中(pH 8.15)小丑魚幼魚能夠識別一系列不同的氣味,正確識別這些氣味可以幫助他們找到適合成體生活的珊瑚礁棲息地。而在酸化(pH 7.8)處理剛剛產下的受精卵并繼續處理至孵化出膜11 d后,小丑魚幼魚會被正常情況下避讓的氣味所吸引,而在pH 7.6的酸化組,小丑魚幼魚對任何氣味都沒有反應[62]。隨后,通過越來越多的室內模擬及野外酸化實驗發現,酸化還能影響魚類聽覺敏感度[7]、視覺[63]、降低行為側向化[64]以及影響幼魚視覺識別捕食者的學習能力[65],表明酸化對魚類的整個神經系統都可能產生影響。
海洋酸化對魚類種群影響取決于該物種的適應潛能,而后者又取決于種群內個體間的遺傳變異度。研究發現,酸化對魚類種群內不同個體的行為影響程度不同[66—67],而且這種個體差異能夠跨代傳遞。將親代棘鯛(Acanthochromispolyacanthus)根據嗅覺行為分為CO2敏感個體和CO2耐受個體,然后再將它們的后代進行酸化處理。根據腦組織的基因組、轉錄組和蛋白質組學分析結果發現,高濃度CO2酸化處理后,耐受親代和敏感親代的后代的基因和蛋白表達均有差異,這種跨代分子特征表明個體間對CO2敏感度不同將為魚類種群適應海洋酸化提供可能[68]。
3 海洋酸化和升溫對魚類的復合效應
大氣中CO2濃度升高,給海洋帶來了雙重效應,即海洋升溫和海洋酸化[73—75]。然而,目前,同時研究海洋酸化和升溫兩種脅迫因子對魚類影響的報道很少,已有報道主要是研究它們對魚類生理和行為的影響。例如,在2種珊瑚魚類(Ostorhinchusdoederleini)和(O.cyanosoma)的研究中發現,升溫能夠降低這兩種魚的有氧范圍,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一致,更重要的是,酸化會加劇升溫的不良影響,使得有氧范圍進一步下降[28]。在研究這兩種脅迫因子對鰩魚(Leucorajaerinacea)胚胎發育影響中發現,升溫會影響胚胎發育、存活率和代謝率,但酸化會加劇升溫的影響,通過增加活動代謝消耗、延長發育時間和降低初孵仔魚體重面積比等影響胚胎發育[76]。在對冷水性、發育緩慢的南極龍魚(Gymnodracoacuticeps)的研究中,龍魚胚胎發育對升溫更加敏感,而只有在升溫和酸化同時處理時,酸化才會對胚胎發育產生不利影響。升溫和酸化協同累加效應,如降低孵化率、影響發育和代謝等會改變生物氣候學(如提早孵化),會對于季節分化非常明顯的極地生態系統帶來不利影響[77]。
海洋酸化和升溫還會影響珊瑚礁魚類的側向行為和覓食行為等。例如,對照組雀鯛(Pomacentruswardi)有明顯的向右轉彎的側向行為,酸化組表現出向左轉彎的行為,而酸化升溫組側向性則顯著降低[78]。捕食動態是一個關鍵的生態過程,在對海洋升溫和酸化對珊瑚礁群落中魚類的獵物-捕食者影響的研究中發現,升溫和酸化對于總體捕食率的影響是協同累加的,但對于捕食者對獵物選擇性的影響則是相互拮抗的[79]。雖然海洋酸化和海洋升溫只影響部分海洋魚類的生理及行為,但可能會通過物種間的競爭、捕食、繁殖、共生和寄生關系,從而對群落和生態系統產生深遠影響[80—81]。
4 研究展望
4.1 開展多重環境脅迫因子對魚類影響的研究
在許多近岸和外海生態系統中,海區低氧和酸化是緊密相關的。在低氧區CO2分壓會比預計21世紀末CO2分壓高出一個數量級[82]。伴隨著全球升溫,海洋中低氧且酸化的區域將會進一步擴大[83]。在某些海域,當海水升溫、缺氧與酸化三種環境脅迫因子同時存在時,它們共同作用對海洋生物的影響可能比單一因素的影響更為復雜[8, 83]。同時,海水升溫、酸化以及缺氧等海水理化性質的改變,也可能改變海洋中污染物的性質和毒性[84]。因此應更加關注多重環境脅迫因子對魚類的綜合影響。
4.2 研究環境變化對魚類及其生物間相互關系的影響
生物與環境以及不同物種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生物群落。競爭、捕食、繁殖、共生、疾病和寄生是種群和群落的關鍵組織力量[85]。目前,大部分研究是從個體水平研究環境變化對魚類直接生理影響,然而這些研究不可能提供全面了解魚類對復雜生態環境的響應。一個種群對環境變化的響應依賴于不同尺度的生態過程,比如行為改變、擴散和種群動態。這些生態過程依賴于棲息地和必需資源的可得性,后者又會受到環境因素的時空變化。因此,應該從目前單一物種的研究方式,逐漸轉向研究生物間的相互關系,從更高水平如群落、生態系統水平,了解環境變化對魚類以及全球漁業的影響。

圖2 環境變化從不同尺度上對魚類種群的影響[86]Fig.2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fish populations at different scales[86]
4.3 魚類對海洋環境變化的適應性進化
魚類在從仔魚、稚魚到成魚的不同的生活史階段,由于其生理特性的不同,如對鈣化生物需求量、自身酸堿等生理調節機能,對于海洋酸化和升溫等環境變化的生理響應(如行為等)不同(圖2)。目前絕大多數研究是通過短期、單世代實驗,研究海洋升溫、酸化對海洋生物的某一個生活史階段的影響,而生物對環境變化的長期適應及適應性進化等相關研究則相對較少,因此需要利用數量遺傳學和基因組學等方法廣泛研究魚類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