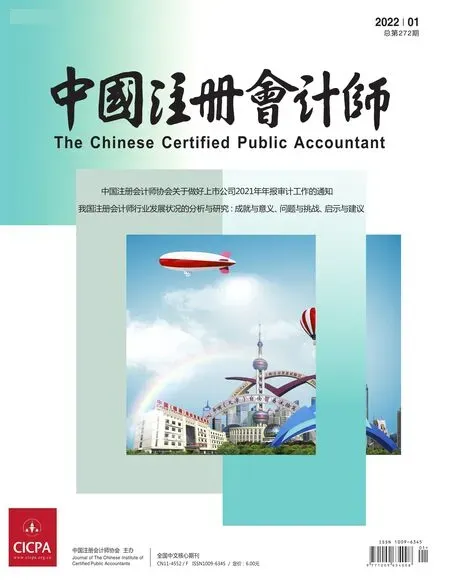企業金融化與違規行為的實證研究
| 司美玲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違規事件層出不窮,例如康尼機電、*ST天成、ST浩源等公司均因違規行為遭受了證監會處罰。根據上市公司相關違規數據統計可知,上市公司違規呈上升趨勢,截至2019年12月31日,15.3%的上市公司發生了違規行為,單個上市公司年度違規次數高達10次。上市公司違規行為會直接導致投資者的利益損失,是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絆腳石。研究表明,企業違規會導致長期代價高昂的聲譽損失,進而造成企業融資成本增加(Chava et al.,2018)、股票異常報酬降低(Firth et al.,2011)、資本市場運作效率降低(Ball,2009)。因此,深入考察影響企業違規行為的因素,能夠為監管部門強化監督提供參考依據。
從已有關于企業違規影響因素方面的文獻看,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從公司內部治理與其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層面加以探討。在公司內部治理層面,主要從管理層薪酬差距、CEO風險偏好、政治關聯、獨立董事比例及忙碌程度、股權結構、關系網絡、股權激勵、高管權力及影響力、內部審計經理監察能力、董事背景特征等方面進行了考察;在外部環境層面,既有研究主要從產品市場競爭程度、機構投資者調研、基金持股、制度情境、市場監管環境、市場分割、賣空威脅等方面展開。相比之下,在企業內部層面,對企業的投資決策作用于其違規行為的效果檢驗的考察相對匱乏。

企業過度擴大金融活動已成為全社會重點關注的結構性問題。就宏觀層面而言,過度投資于金融資產會增加虛擬經濟泡沫,使得依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良好初衷產生偏離,導致資源錯配問題。就微觀層面而言,實體企業擴大金融活動的動機,目前學者均認為“蓄水池”以及“投資替代”層面可以對此加以闡釋。根據“蓄水池”理論,公司在當期增加金融資產的配置比例是為了應對未來的經營不確定性,當未來經營面臨融資約束時,金融資產因具有變現能力強及投資收益高等特征,能夠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孫華妤等,2021)。投資替代理論認為,企業金融化的目的在于追逐短期利益,尤其是當金融資產投資收益高于實體投資收益時,公司更傾向于提高金融資產的持有比重,從而會擠出主營業務、制約企業的實體經營能力,對企業的長遠持續發展造成影響(鄧路等,2020)。
從企業違規的視角看,若企業金融化的動機是預防儲蓄功能,則增加金融資產是用于維持企業經營發展的戰略選擇,有助于降低企業違規概率;若企業金融化的動機是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那么增加金融資產配置是一種短視行為,會增加企業的違規行為。為此,本文以2007-201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考察了企業金融化及其期限結構對違規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金融化對違規行為的沖擊呈現“投資替代效應”,即企業增加金融資產投資不利于其穩定發展,增加了企業違規行為。從投資的期限結構看,與短期金融資產配置相比,長期金融資產配置對企業違規的影響效應更強烈。
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包含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從企業金融化的視角拓展了企業違規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鑒于鮮有研究從企業投資決策的角度考察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因素,本文從金融資產投資的視角出發,分析非金融企業金融化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為深入識別并監督企業違規行為提供了新的證據。第二,區分了企業持有金融資產的期限結構影響違規行為的差異,證實了長期金融資產的持有才是導致企業違規行為增加的深層次原因,該研究結論對于企業合理做出投資決策、優化金融資產結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第三,本文研究支持了企業金融化的投資替代功能,發現金融資產尤其是長期金融資產能夠增加企業的違規行為,有助于在當前雙循環背景下研究有效制約公司違規行為的具體思路,從而為監管部門監督和抑制企業違規提供新的視角。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宏觀經濟疲軟的背景下,金融資產投資收益往往高于實體投資利潤,大量企業為追逐短期超額回報而增加了其金融資產配置。基于企業金融化的預防儲蓄動機和投資替代動機的差異化作用機制,企業金融化對其違規行為的影響也存在異質性。
從公司金融化的預防儲蓄功能來看,公司金融化對于增強其未來的資產流動性水平大有裨益,當企業未來出現融資約束時,金融資產由于變現能力強,能夠及時為企業補充發展資金,發揮預防儲備功能。根據舞弊理論和代理理論,企業財務狀況惡化,管理層在業績壓力的影響下,會存在違規信息披露、業績操縱等違規動機。金融資產由于流動性較強,收益較高,能夠降低企業面臨的經營風險,緩解企業實體投資不足,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進而降低企業的違規動機。
然而大量學者研究發現,中國企業擴大金融活動的主要動機并非預防儲備,而在于追逐短期利益(杜勇等,2017;彭俞超等,2018)。按照投資替代理論可知,公司增加金融資產配置,會擠出部分原本用于實體投資的資金,使得企業主營業務方向發生偏離。實體經營肩負著企業長遠發展的重任,企業增加金融資產配置為其違規操作提供了動機和機會。首先,企業增加金融資產會弱化企業的治理水平,增加企業的代理沖突,其背后的邏輯在于以犧牲實體投資為代價的金融資產配置行為會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一旦金融市場呈現較大的波動,企業將面臨金融資產投資失敗的風險,主營業務經營也會受到強烈的負面影響。當企業投資回報率降低,財務狀況惡化時,管理層有動機從事財務舞弊等違規行為(李世輝等,2021)。其次,企業持有金融資產為其進行利潤操縱提供了便利條件。金融資產往往以公允價值進行計量,而公允價值計量的靈活性和復雜性特征會增加企業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提高公司的違規傾向,并導致其違規行為具有隱蔽性。根據動機理論,動機決定了個體的行為(Hambrick et al.,2015),企業違規行為是基于管理層能力的違規動機的外在表現。金融資產的高風險性增加了公司與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分離,當企業業績下滑時,企業有動機和機會操縱利潤、虛增股價、披露虛假信息等違規行為。
因此,企業金融化雖然能帶來一定的投資收益,但卻會損害企業的發展前景。持有較多的金融資產一方面增加了企業違規的動機,另一方面由于其計量的復雜性,為企業違規提供了機會,最終導致公司的違規行為增加。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一:
H1:限定其他條件,企業金融化程度越高,其違規行為越多。
企業金融資產包括多種不同的類型,其中交易性金融資產屬于期限結構較短的金融資產,相比之下,持有至到期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及金融衍生產品等均屬于期限結構較長的金融資產。與短期金融資產相比,長期金融資產變現相對困難,調整成本較大。企業配置較多的長期金融資產,會進一步弱化金融資產的預防儲備功能,強化其投資替代效應,表現為對實體投資的擠出效應更為明顯。當企業未來經營急需發展資金時,過多的長期金融資產由于變現能力較弱,而無法為企業提供相應的發展資金,可能導致企業產生財務危機。在此情境下,企業管理層迫于外界的業績壓力,而可能選擇通過一系列違規操作平滑公司業績的行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二:
H2:與持有短期金融資產相比,企業持有長期金融資產的比例越高,企業的違規行為相應會越多。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7-201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基于研究需要和慣例,對樣本采取了如下常規的處理方式:(1)刪除了金融保險行業的樣本;(2)剔除交易異常的樣本觀測值,如ST和PT類企業;(3)刪除數據缺失的樣本公司。經過上述處理后,本文最終獲得23735個企業年度樣本觀測值。為了避免異常值對回歸結果的可能影響,本文對相關的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進行了Winsorize處理。本文所用的相關數據主要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其中企業違規數據后續經過了手工整理。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為了探究公司金融化程度及持有金融資產的期限結構對違規行為的影響,本文參考江新峰等(2020)的研究,構建如下實證模型:


上述模型中,被解釋變量Viodmy和Vionum是企業違規變量。參考已有研究的做法,Viodmy是企業是否違規的虛擬變量,當企業當年發生了違規行為時取值為1,否則為0;Vionum代表企業當年違規次數,以企業每一年度發生違約行為的次數進行衡量。解釋變量Ftllo是企業金融化程度,等于金融資產除以總資產。Ftllo值與企業金融化程度呈正比,Ftllo越大,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越高。
為檢驗金融資產的期限結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差別化影響,本文根據金融資產的持有期限,進一步將其劃分為短期金融資產(SFtllo)和長期金融資產(LFtllo),并分別加入上述模型中進行回歸。其中,短期金融資產(SFtllo)等于交易性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長期金融資產(LFtllo)等于除交易性金融資產以外的其他金融資產除以總資產。
借鑒既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選取了以下控制變量:公司盈利能力(ROE)、公司成長性(Grow)、資產負債率(Lev)、股權集中度(Top1)、企業規模(Size)、獨立董事比例(Indratio)、兩職合一(Duality)、是否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Audit)、產權性質(SOE)。此外,本文還加入了年度和行業虛擬變量,以控制年度和行業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文主要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本文相關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企業是否違規變量(Viodmy)的均值是0.1532,表示每100家企業中平均約有15家發生了違規行為。企業違規次數(Vionum)的均值為0.2157,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0,說明樣本企業的平均違約次數為21.57%,且不同的企業之間違規次數具有明顯的差別。公司金融化程度(Ftllo)的均值是0.0219,中位數是0.0006,最大值是0.3613,說明樣本企業的金融化程度具有較為明顯的差異。從金融資產的期限結構看,短期金融資產(SFtllo)和長期金融資產(LFtllo)的均值分別為0.0021和0.0218,說明企業更傾向于持有長期金融資產,這為本文探討企業金融化及其期限結構對違規行為的影響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機會。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實證檢驗結果
1.企業金融化與違規行為。在開展企業金融化與其違規行為的回歸之前,利用樣本公司相關數據,對各變量之間進行了相關性檢驗(限于篇幅,表略),發現樣本公司的金融化程度(Ftllo)與違規行為(Viodmy和Vionum)的皮爾森相關系數分別為0.014和0.012,且在1%水平上顯著,初步證實金融化提高了公司的違規行為。
為進一步探究公司金融化程度對其違規行為的作用,根據模型(1)和模型(2),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前兩列顯示了未納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可知,公司金融化(Ftllo)與企業是否違規(Viodmy)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與違規次數(Vionum)正相關,且在5%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后兩列顯示了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可知,企業金融化(Ftllo)與企業是否違規(Viodmy)以及違規次數(Vionum)分別在1%和5%水平下正相關,說明企業金融資產配置在增加其違規行為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企業金融化程度越高,相應的違規傾向和違規次數越多,研究假設一獲得證實。

表3 企業金融化與違規行為
控制變量的結果顯示,股權集中度(Top1)、公司規模(Size)、獨立董事比例(Indratio)、盈利能力(ROE)、是否四大審計(Audit)、產權性質(SOE)均與企業違規行為顯著負相關,表明公司股權集中度越高、規模越大、獨立董事占比越高、盈利能力越強時,能夠抑制企業的違規行為;同時,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企業以及國有企業,其違規行為較少。此外,杠桿率(Lev)、兩職合一(Duality)與企業違規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負債率越高,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企業的違規行為越多。
2.金融資產期限結構的影響。表4列示了金融資產期限結構對企業違規行為影響的差異化結果。第(1)列和第(2)列是以企業是否違規(Viodmy)為因變量的結果,第(3)列和第(4)列是以企業違規次數(Vionum)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可見,短期金融資產(SFtllo)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長期金融資產(LFtllo)分別與企業違規傾向和違規次數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公司持有不同的金融資產期限結構對其違規行為產生了差別化的影響,與持有短期金融資產相比,企業持有長期金融資產能夠顯著增加企業的違規傾向和違規次數,本文的假設2得到驗證。

表4 金融資產期限結構的影響
(三)內生性問題
本文發現企業金融化提高了企業的違規行為,但是這可能是由于樣本自選擇引致的內生性問題,如某些違規行為較多的企業可能更愿意配置擴大金融活動。本文分別以是否配置了金融資產(Ynfin)、是否持有短期金融資產(Ynsf)以及是否持有長期金融資產(Ynlf)作為因變量,利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緩解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首先,選取企業規模、杠桿率、股權集中度、高管持股比例、同年度同行業其他企業金融資產均值、營業收入增長率、獨立董事比例、是否兩職合一、產權性質等變量對企業是否持有金融資產進行Probit回歸,計算企業是否持有金融資產的IMR;其次,將前一階段計算得到的IMR代入前述模型再次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顯示,在緩解了內生性問題后,企業金融化(Ftllo)和長期金融資產(LFtllo)依然與企業違規顯著正相關,短期金融資產(SFtllo)依舊對企業違規無顯著影響,說明企業金融化能夠增加企業的違規行為,且這種影響效應主要是由企業持有長期金融資產驅動的。本文的結論未發生改變。

表5 內生性檢驗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上述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進行了如下檢驗:
1.改變金融資產的計量方式。本文采用金融資產的自然對數衡量企業金融化重新回歸,結果見表6。第(1)列和第(2)列的結果顯示,企業金融化(Ftllo)依然在5%水平以上與企業違規顯著正相關;區分長短期金融資產后,結果顯示,短期金融資產(SFtllo)的估計系數依然不顯著,而長期金融資產(LFtllo)依舊在5%水平上與企業違規正相關。改變變量的衡量方式后,本文的結論未發生改變。

表6 改變金融資產的計量方式
2.剔除2007-2009年的樣本觀測值。考慮到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企業經營業績具有較大的負面沖擊,從而可能對企業金融化和違規動機產生影響。為減輕這部分樣本對本文結果的可能影響,在樣本中剔除這部分觀察值后重新回歸,結果見表7。結果顯示,企業金融化(Ftllo)和長期金融資產(LFtllo)依然與企業是否違規以及違規次數正相關,且均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短期金融資產(SFtllo)依舊對企業違規沒有顯著影響。剔除部分樣本觀測值后,本文的結論未發生改變。

表7 剔除2007-2009樣本觀測值
3.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檢驗。為避免個體層面不隨時間改變的相關因素對上述結果的干擾,本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重新檢驗,結果見表8。第(1)列和第(2)列中,企業金融化(Ftllo)依然與企業違規顯著正相關;第(3)列至第(6)列中,短期金融資產(SFtllo)的估計系數依然不顯著,長期金融資產(LFtllo)的估計系數依然為正且顯著。改變回歸方式后,本文的結論未發生改變。

表8 雙向固定效應回歸
4.進行公司聚類處理。為進一步增強回歸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進行了公司聚類處理,回歸結果見表9所示。結果顯示,企業金融化(Ftllo)和長期金融資產(LFtllo)的估計系數依舊顯著為正,而短期金融資產(SFtllo)的回歸系數依舊不顯著,說明企業金融化能夠增加企業違規的概率和次數,且這種效應主要是由企業持有長期金融資產驅動的。進行公司聚類處理后,本文的結論未發生改變。

表9 公司聚類處理
五、研究結論
本文以2007-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企業金融化與企業違規的關系以及企業持有金融資產的期限結構對企業違規的差別化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企業金融化顯著增加了企業違規行為,企業金融化程度越高,其違規傾向和違規次數越多,金融資產的投資替代效應得到支持;與持有短期金融資產相比,企業持有長期金融資產對企業違規的影響效應更大,說明企業金融化對其違規行為的影響主要是由長期金融資產驅動的。采用Heckman兩階段法處理內生性問題以及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本文的研究結論均保持一致。
研究結論表明,企業金融化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為企業帶來一定的投資收益,但從企業合規層面來看,企業金融化增加了其本身的經營風險,一旦投資收益下滑企業可能鋌而走險,依靠違規操作平滑公司業績。本文研究結論對于引導企業合理配置資產以及從資產持有的角度強化監管部門對企業的監督具有重要意義。(1)由于企業持有金融資產尤其是長期金融資產能夠顯著增加其違規行為,企業應適當減少對長期金融資產的配置,以強化金融投資對主營業務發展的支持作用,促進企業可持續健康發展。(2)對于監管部門而言,應重點關注企業金融資產的持有狀況,以便及時跟蹤、發現并阻止企業可能存在的違規行為,避免企業違規對投資者帶來利益損失,妨礙資本市場的良性發展。(3)對于投資者而言,應及時關注企業金融化程度,適當減少對金融化程度高的企業的投資,合理控制投資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