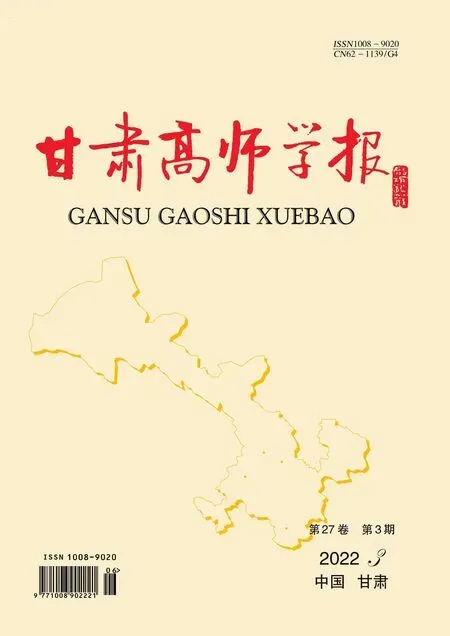隴南白馬藏人山歌的類型及語言特征
艾 麗,張淑萍
(蘭州城市學院 外國語學院,甘肅蘭州 730070)
白馬藏人聚居在隴南文縣、四川平武、九寨溝、松潘一帶的高山峽谷地帶,解放后被認定為白馬藏族,但是他們自己對這一族屬劃分持懷疑態度,自認為是氐人的后裔,學術界也多有討論。通過多方面的考察與追溯,最后基本達成共識,認同他們為白馬氐人,是古代氐人的后裔。白馬藏人有自己的語言,但沒有文字。由于自古以來常與漢族雜居,所以他們懂漢語,且能用漢語與漢人交流,但在白馬藏人內部使用白馬語。《三國志》卷30《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如是描述:“氐人…多知中國語,與中國雜居故。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1]858白馬藏族是歌舞民族,其歌謠的種類繁多,總體可分為三類:一是用白馬語演唱的各類儀式性民歌,如酒歌、祭祀歌、嫁娶歌等;第二類是小調,琵琶彈唱;第三類是山歌,無伴奏。后兩類多用漢語,即文縣當地漢語方言吟唱。
小調一般是每句七言,每四句組合成一段,每首小調的篇幅長短不定,從數段到數十段不等。小調是敘述性歌謠,大多有完整的故事情節,主題可大可小,從歷史性事件如《光緒逃西安》,到一個人的人生際遇如《南橋戲水》,乃至一個人的心理獨白如《皇姑哭五更》。山歌篇幅較為短小,以男女的即興對唱和獨唱為主。對唱歌的歌詞一般是八句,男女各四句,每句通常為七言;獨唱歌的歌詞以四句最為多見。比起隴南其他地域的山歌,白馬藏族山歌有較強的敘述性,三五句也能講一個簡明扼要的故事,出現一兩個卷入情節的人物。小調是“家曲”,在正式非正式場合都可以演唱;山歌是“野曲”,只能在野外唱,因其主題多為男歡女愛,也不乏野合式的愛情,故不符合婚姻和道德規范,不適宜在家里、村子里等社會規范較嚴格的場域演唱。小調和山歌的演唱場域反映出傳統的社會規范對人的監管是有彈性的,在對人性充分理解的基礎上,依照場域對人性的張弛作適度的規定。本文主要探討山歌的類型、語言特征及修辭手法。
一、白馬藏人山歌的類型
白馬藏人山歌從演唱方式來看,有男女對唱和獨唱兩類,從歌詞內容來看,有引歌、情歌、生活歌等類型。
(一)引歌
引歌是獨唱類山歌,也可以作為引子,引出對唱。演唱者用激將法,故意夸耀自己的山歌多或歌喉美,如“山歌子,子山歌,你歌哪有我歌多?前頭馱了十八馱,后頭還有九崖窩。”[2]169“馱”是量詞,表示騾馬負載之貨物的量,十八馱表示十八馱次的量。“崖窩”是在山崖上挖的供人居住的洞穴。這里的“十八”“九”是概數,“十八馱”“九崖窩”表示非常多,不可數。實際上,每個人會唱的山歌的數量無論是十幾首,幾十首還是幾百首,都是可數的,這里用不可數來指代可數,夸張的手法和語氣旨在逗引對方的注意,激起對方的不服氣甚至不滿情緒,從而對歌反駁。應戰者可以用同樣抑或更夸張的方式應對:“你的山歌沒我多,我的山歌牛毛多。唱了三年三個月,沒唱完一只牛耳朵。”[2]170“牛耳朵”是轉喻,與其所指“牛耳朵上的毛”是鄰接關系,表示自己會唱的山歌和牛毛一樣多,即使唱三年三個月,也沒有唱完一只牛耳朵上牛毛的數量,這也是用不可數的牛毛喻指可數的山歌。應戰者也可以這樣應戰:“熱頭出來紅刀背,你有山歌就來對。對得過了單對單,對不過了鉆炕眼。”[2]187“熱頭”即太陽,“紅”是動詞,映紅之意;“炕眼”即農村燒炕時往里面填柴火的柴道,“鉆炕眼”表示比賽輸了,羞于見人。以此賭咒發誓的方式把應戰反轉為挑戰。應戰者也可以直接接受挑戰:“說唱塊,就唱塊,莫非誰塊怕誰塊。唱了還要唱好的,不唱連毛帶草的。”[2]180“塊”是量詞,“個”之意,“唱塊”就是“唱個”,“誰塊”即“誰個”。“連毛帶草”即“拖泥帶水”,有雙重意指,一是表示歌詞不簡明準確,二來表示歌者態度含糊,不明朗。
應戰者也有出于禮貌,表面表示誠服的:“隔山隔嶺隔草坡,聽見小郎唱山歌。心想陪你唱兩句,聲氣不如小哥哥。”[2]177此時,挑戰者會勸勉對方繼續唱下去:“白面蒸饃蘸蜂蜜,山歌出在白馬夷。白馬夷的白馬寨,山歌越唱人越愛。”[2]170或者:“唱得不好也是歌,白馬下河也是鵝。黃牛配鞍也是馬,銅盆敲響也是鑼。”[2]188對唱便順利進行下去。對唱的歌詞可以是傳統唱詞,但大多數是歌者依據情境現編現唱。如果對唱中的任何一方編不上詞應對不上時,就會招致另一方的譏諷:“青石崖,銹石崖,你有山歌對到來。你無山歌退回去,明天叫你大嫂來。”[2]187甚至更激烈的挖苦:“棗紅馬,四蹄黃,你沒山歌問老娘。老娘給你教兩個,恐防你娃沒心顆。”[2]187“沒心顆”表示沒記性。另一方這時口氣往往會軟下來,溫婉地揶揄對方一下,以便對歌能持續下去:“你要唱了唱好的,甭唱連毛帶草的。唱歌甭唱罵人話,怪話叫人不快活。”[2]186這里的“連毛帶草”喻指不好的話,罵人的話。也可以是不卑不亢的解釋:“你有山歌唱到來,我沒山歌自安排。小小葫蘆裝菜籽,慢顆慢顆滾出來。”[2]187表示自己雖然應對速度慢一點,但知道的山歌還是不少。
(二)情歌
情歌,從試探歌、拒絕歌、贊美歌、熱戀歌、贈禮歌、起誓歌到離別歌、思念歌、抗爭歌,極其豐富。試探歌以男性試探女性為多:“高山種蕎桿桿紅,茄子開花像燈籠。心里想的把你纏,你家富來我家窮。”[2]206“纏”即“追”。如果女方也有此心意,便應和道:“梔子開花里面白,豌豆開花紫紅色。只要你的心腸好,賢妹從來不怕窮。”[2]206如果男方品行不好,女方看不上,便直接拒絕:“我愿拾柴愿挑水,也不跟你窮二鬼。好吃懶做都占全,誰塊跟你吃黃連。”[2]197也會嚇唬男方,以防他糾纏不休:“新修房子長九間,你纏奴家也枉然。你纏奴,奴不做,奴的屋里人不弱[2]94”或“巴山豆,豆巴山,你要纏我小心點。叫我男人知道了,打斷你的狗腰桿”[2]205等。也有婉言謝絕的,如:“叫聲小哥甭笑話,我是蜜蜂采過的花。你是高粱煮過的酒,我是豆腐濾過的渣。”[2]248女子用“蜜蜂采過的花”表示已經名花有主了。酒是陳的好,用高粱煮過的酒贊譽、抬高對方的身份或者品質;豆腐濾過的渣是謙辭,表示自己配不上男子。用這種委婉的方式謝絕男子的試探和追求。
如果雙方兩情相悅,就有了一唱一和的贊美歌和熱戀歌,這兩種歌經常相生相伴,因為熱戀,所以看到的都是對方的優點:“玉米地里苦苣菜,小哥心里把姐愛。一愛姐的心腸好,二愛姐的好人才。”[2]339“小哥長得筆桿端,好像磨輪沖天桿。把郎變個磨輪子,把妹變個閘水桿。”[2]339水磨靠閘水桿控制水量,從而控制磨輪的旋轉,以此比擬男女雙方的相互依存乃至相依為命。“小哥長得好人才,家里再窮妹也愛。真心不要定情物,葛條編個項圈戴。”[2]340葛條即當地生長的一種藤,質地柔韌。男女雙方信手拈來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自然物或家什取譬比興,恰如其分地表情達意。兩情相悅總伴隨著互換信物,男方多贈衣物布匹,女方多贈布鞋荷包,互表關心和思念。如:“大河壩里石頭高,我和小郎換系腰。這個系腰換的好,回去甭叫娘知道。”[2]338“系腰”即腰帶。“騾子馱到中壩場,給妹扯件花衣裳。一年四季都穿上,好像小哥在身旁。”[2]322
起誓歌較多,誓言的種類也不少,有單方面發誓非他不嫁或非她不娶的,如:“生要纏,死要纏,生死不離姐面前。死了變個圍腰子,纏在賢妹腰桿間。”[2]362也有猜疑對方有二心而發誓不再理睬的,如:“白布汗褂白如云,妹是桂花酒一瓶。外前有人摻了水,發誓不上你的門。”[2]233“外前”即“外面”,酒里摻水表示酒不再純,不再真了,喻指女子有了外心。也有兩人同時起誓互表忠心的,如:
男:白布腰帶丈二長,挽個疙瘩撂過墻。千年嫑叫疙瘩散,萬年嫑叫姐丟郎。
女:說不丟,就不丟,只等海干石頭朽。海不干,石不爛,只等公雞下雞蛋。[2]206女子用海干石爛、公雞下蛋之不可能比喻自己丟郎的不可能,回應男子對愛情持續千年、萬年的懇求。又如:
男:賢妹妹,我的人,你媽打你我心疼。如還二回再打你,包包背上出遠門。
女:小哥哥,我的肝,我的良心能見天。城隍廟里賭了咒,文縣城里見了官。[2]214
女子的母親不同意女兒和某男子交往,當女兒堅持要與該男子交往時,母親就會責打。男子心里過意不去,打算出遠門,不再與女子交往。女子表真情,表示自已在城隍面前發誓要與他交往,此心日月可鑒。
戀愛中的人恨不得整天黏在一起,但這在舊時代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了相思歌。有故事情節的相思歌如:
女:熱頭出來九架坡,想死人的小哥哥。賢妹得的相思病,給郎帶信吃副藥。
男:小郎聽得割心肝,手拿筆桿開藥方。一寫雄黃加桂香,二寫升麻對龍黃。甘草是個藥大王,擔上包袱進姐房。包袱放在桌子上,先揣賢妹熱么涼。
女:雙手扯上郎腰帶,閻王殿上去一場。
男:賢妹妹,我的妻,好好把你病將息。請上先生好好看,吃了藥錢算我的。[2]220
女子相思成病,捎信帶話,男子心急如焚,假托醫生來看望,其情也真,其意也切。相會是相思之情的最終釋放。但戀愛中的女方總是表現得比較被動,即使遭受相思的折磨,折磨到一病不起,也難以主動去看望相思對象。相較而言,男方則主動得多,從半真半假的玩笑話“我的賢妹我的人,今晚要上你的門”[2]234,到著實掉進愛的泥潭,實心實意去看望戀人,都表現出其主動性:
男:賢妹住在老山林,茅草房子籬笆門。拿上禮物來看她,假裝裝作腦殼疼。
女:叫聲小哥我的人,腦殼痛來是真情。明天上街請先生,后晚給我請個神。[2]221
“真情”即“真實情況”。“先生”即“醫生”。“給我”實為“我給”,這個詞的用法受白馬語影響,即母語負遷移。白馬語沒有動賓結構,只有賓動結構,如“正月采花無花采”,在白馬語中讀作“正月花采花無采”。這句話的意思是:“后晚我給(你)請個神。”“神”即師公,此句意為請神給他治病。女子明白男子佯裝頭疼,遂故意逗他,說幫他請醫生、請師公治病,實為逗他說出相思之情。也有去看望戀人而不遇的,如:
男:清早起來一上埡,關門閉鎖沒在家。揀個火鐮門上畫,門神老爺告訴他。
女:門神老爺活菩薩,咋不把我客留下。我在后園割韭菜,還說我在躲避他。[2]202
男子看望戀人而不遇,遂拿起火鐮在門上畫上暗號,表示自己來過了。女子看到暗號后失落之情難以承受,遂遷怒于他者,責怪門神沒有把戀人留下。女子的心理進一步延伸,推己及人:戀人一定會認為我在躲避他。
戀人相思總會被長輩察覺。家長,特別是母親,對于女兒的心思總是能夠明察秋毫,出于保護以及為女兒計深遠,總會橫加干涉,所以以女孩子為主角的相思歌總是與反抗歌相伴:
女:姐家門上一樹槐,手把槐樹望郎來。媽媽問娃望啥子,我望槐花幾時開。盡管女兒借口望槐花,但是母親作為過來人,從女兒的神情中看穿她的心思,所以警告:
母:扎你的花做你的鞋(hai),管它槐花幾時開。等你二天再來望,黃櫨條子有你挨。
“二天”表示“以后,下次”。母親最后警告女兒,要是心思還不收回來,就要挨打。此時女兒知道母親看穿了心思,所以惱羞成怒:
叫聲媽媽甭管閑,啊塊少年沒人纏。你是高山老廟子,才斷香火沒幾年。[3]:7
“啊塊”即“哪一個”。“老廟子”即“舊廟宇”。廟宇是個公共場合,人可以隨意出進。把母親比作香火才斷的老廟,喻指母親年輕時期情人不少。這句話分量重,意在揭短,旨在讓母親啞口無言,不再干涉女兒交友,把女子潑辣的性格和真性情表現得極其徹底,反襯其之前假托看槐花的溫婉是禮教教化的結果。當文化與自然、禮教與性情沖突時,女子的真性情壓倒性地占據上風,毫不顧忌地反抗權威。
幽怨歌也叫分手歌,但著重點不在分手這一行動,而在表達分手后心里的哀傷、怨恨、痛苦:
女:月亮出來太陽落,妹在屋里想小哥。小哥纏上別人了,賢妹難過受折磨。前思后想想不過,心想吊猴去跳河。”①“吊喉”即上吊自盡,把失戀之后的痛苦刻畫得入木三分。再如:
男:當初和妹親又親,燈草架橋妹愿跟。如今和妹緣分淡,石板架橋妹怕斷。
女:當初和哥恩愛深,一粒芝麻平半分。如今和哥恩情斷,碗大沙梨獨自吞。②
這首對唱歌極其形象地描寫了有愛與無愛時人的心理傾向:貧困、危險、苦難統統攔不住兩個相愛的人要義無反顧地走到一起;當愛情煙消云散,彼此間起碼的信任,同甘共苦的精神也隨之灰飛煙滅。
(三)生活歌
白馬藏人的生活中,有兩類極其有特色,即童養媳與出門歌。童養媳歌中,媳婦普遍年齡大,女婿年齡小,而且年齡差距比較大,如“十八姐,三歲郎”。童養媳歌以女性為敘述者,講述自己的婚姻生活,著重描述小女婿的孩童生活習性以及自己的無奈心理。如:“薸子開花一爪爪,男人是個小娃娃。鼻子掉到腔子上,蹴在院壩玩泥巴。”[2]283“薸子”即當地漢語方言中的野草莓;“鼻子”即鼻涕;“腔子”即胸前。又如:“十八姐,三歲郎,晚晚把郎抱上床。早上給郎穿褲子,黑了給郎脫衣裳。”[2]282女婿年齡太小,生活都不能自理,女子如同保姆,二者的關系或者如同母子。如:“十八姐,三歲郎,他當兒子我當娘。三歲小郎咋辦家,背起男人回娘家。”[2]283除了概述婚后生活,更有細節性生活場景的描述:“天上烏云遮太陽,把娃嫁到遠山上。奴家女婿三歲郎,晚晚都要抱上炕。抱上炕了要吃饃,剛吃兩口又睡著。睡到半夜尿炕了,奴家一說哭開了。”[2]284扭曲的童養媳婚姻制度使女性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她們除了逆來順受,別無他法,在無奈中或積極或消極地承受著命運的安排。如在“坐上花轎到婆家,奴家男子憨娃娃。幾時等到他長大,老了黃瓜謝了花”[2]283中,女子見到憨娃娃女婿時,悲戚感油然而生,變態的婚姻有違人性,而她只能在無奈、無助中被動接受。
無論如何,生活總得繼續。面對難以改變的命運,有些女性也明白,與其在悲戚中承受婚姻之苦,不如樂觀地勇敢面對,如上文中的“背起男人回娘家”中透露出女子在無可奈何之時選擇勇敢應對。而在“一碗面的燒圓饃,女婿小了人難活。睡到半夜沒見了,老鼠拉到窩去了。吸到去,磨到來,該得老娘不折財”[2]284中,一位幾近“沒心沒肺”的樂觀者形象栩栩如生。第一句講述事實:女婿小了人難活。第二句則用夸張手法戲謔女婿的小:小到能讓老鼠拉進鼠洞。第三句前半闋在承接第二句的基礎上,虛構幻境。其中,“到”是動態助詞,“著”之意。“磨”是動詞,意為“拉”。用鄉言土語生動地描畫女子與老鼠拉拉扯扯,爭奪女婿的動態畫面:老鼠吸著去,女子拉著來。后半闕是對前半闋的評論:老娘的財物沒有丟失。其中“老娘”有雙重意指,第一層表示夫妻關系類似于母子關系;其二,用“老娘”稱呼自己體現女子的一種豪氣,作為“家長”,怨天尤人沒有用,只好樂觀面對。一位笑中帶淚、獨當一面的潑辣女子形象被勾勒出來。
第二類是出門歌。如果說前面談到的相思歌主要表達戀人之間的相思之情,出門歌則更多地表現婚后丈夫迫于生計,出門經商,或者不得已當腳戶,由此產生的夫妻相思歌。出門歌有男歌也有女歌。男歌從男性的視角表達出門的見聞、經歷,以及出門之苦和想家之情。他們最初對出門充滿了憧憬:“世事到底有多大?我要出門經一下。”[2]248但是出門之后“一日三餐無飽飯,只愁一夜睡不安”[2]326,更有甚者,客店的“床上壩的爛氈片,虱子蟣子翻了天。小哥咬得睡不著,坐等天亮抽鍋煙”[2]320。再加上路途的辛苦:“馱腳小哥白汗衫,風里行來雨里穿。又翻山來又過河,一路吃的黑面饃。寒冬臘月雪花舞,馱腳哥哥好辛苦。”[2]322把他們對出門的好感打磨得煙消云散,于是感慨:“人家都說出門好,我把出門看淡了”[2]327,“難心難心實難心,難心不過出門人”[2]327。想家之情日漸濃厚起來:“毛毛雨,順梁飄,出門人兒好心焦。一想父母年事高,二想妻兒無依靠。”[2]328
女歌以女性為敘述者,表現主題從勸夫不要出門、為夫準備行囊、告誡出門注意事項到別后相思,她們用心丈量丈夫出門的歷程,并用山歌演繹出來。“世上能人比能人,我勸丈夫嫑出門。娘老子勸你支得硬,賢妹勸你你不聽。”[2]248“支”即“頂”。父母勸子不要出門,被兒子頂了回去,妻子勸夫不要出門,丈夫更不聽了,妻子只好為丈夫準備行囊:“下四川的小哥哥,帶上妹的火燒饃。啥時餓了啥時吃,千萬甭把你餓著。”[2]318臨行前,妻子想要說幾句知心話,但是“還沒張口淚流下”[2]318。妻子叮囑的注意事項從衣食住行到品德規范,無所不包:“殘湯剩飯少吃些,出門要防賊兒劫”[4]165“走路要走大路上,謹防路上棒客搶。看到天黑早住下,甭喝涼水甭貪花”[2]322“就說四川販辣醬,甭說四川找婆娘”[2]321。“棒客”即土匪。針對妻子“甭貪花”“甭說四川找婆娘”的告誡,丈夫也不忘勸勉妻子守貞操:“桂花不準亂人摘”[2]324“出門就是四十天,鑰匙不到不開門”[2]19“小哥出門三五天,賢妹甭叫外人纏。”[2]246也可以是試探式的:
男:叫聲賢妹我的人,小哥今年要出門。小哥回來無遲早,叫聲賢妹重嫁人。
女:叫聲小哥我的人,你大放寬心出遠門。賢妹是個鐵簧鎖,鑰匙不到不開門。[2]246
期待對方的否定回應,由此夫妻互表忠貞之心:
女:大雁南飛排成隊,小哥一去幾時回?勞動不怕長吃苦,就怕小哥忘了妹。
男:白云飄飄不離天,燕子高飛對對歡。筷子不離紅花碗,小妹常在哥心間。[2:247]
臨走時,妻子總是泣涕漣漣,丈夫一般勸勉有加:
女:郎說三聲就走哩,活拔心顆丟手哩。左手把郎扶上馬,右手就把眼淚擦。
男:叫聲賢妹你甭擦,來去三天回來家。③
“心顆”即“心”;“甭擦”字面意義是“不要擦”,是轉喻,表示“不要哭”;“三天”與上文“小哥出門三五天”中的“三五天”類似,是概數,表示少,語境意義即很快就回來了。
丈夫走后,妻子深沉的思念用多種方式體現在山歌中。其一是疑問式,想知道丈夫到哪里而不能:“我郎走到阿得了?晚上歇到哪店了?出門尋個好店家,才把妹的心放下。”[2]320“阿得”即“哪里”。其二是心跟著丈夫神游,換位體會丈夫的住行:“奴家小哥下四川,走到黑了歇腳店。床上壩的爛氈片,虱子蟣子翻了天。小哥咬得睡不著,坐等天亮抽鍋煙。”[2]320在想象中構建丈夫的處境。其三是單純傾訴相思之苦的:“小哥出門下四川,賢妹在家受熬煎。一天把郎望三遍,口吃冰糖不想咽。”[2]325相思使人茶飯無味。有一類歌男女均可唱,稱為男女間歌,表達男女思念之情:“一根竹子十二節,小哥出門十二月。十二月么十二年?賢妹床上草長嚴。”問號并不是歌者分不清十二月還是十二年,而是表達思念對方使得度月如年。“長嚴”即“長滿”。“草長嚴”本來表示莊稼無人鋤草而荒蕪了,這里隱喻丈夫迫于生計出門在外,妻子長期無人照顧。
男子出門在外的生活五花八門,有的是“又吃酒來又貪花”[2]327,有的“又燒洋煙又玩耍”[2]327,終于落得個“掙不下銀錢難回家”[2]327。有的雖然勤奮,但由于種種原因沒掙到錢。如有一首出門歌,表現一位去成都販花椒的商人,由于花椒價格太低,賣不出去,心情郁悶,思家更為心切,恨不得立馬回到妻子身邊,甚至想到把花椒倒掉,趕緊回家:“鐮刀刮的枰桿捎,郎在成都販花椒。初八十八二十八,花椒無價也無法。記起賢妹說的話,口袋提起倒了吧。”[2]321
掙到錢的,大買特買:“土黃騾子馱黨參,金洋鈴的好響聲。騾子馱到漢中縣,郎給賢妹扯鞋面。綢子一箱布一箱,小哥搖錢樹一樣。”[2]324掙得錢少的,也不忘給妻子買各種禮品:“中壩場上茶嶺子,給妹買把花扇子。有錢買把金洋傘,沒錢買把扇子扇”[2]323,“扯得三尺紅毛布,稱得四兩細花茶”[2]323,“洛陽場上好買賣,給妹買個水煙袋”[2]323。一路上歸心似箭,將至家,面對迎接他的妻子,縱有千般思萬般念,一時倒也難以出口,于是很含蓄地將問候對象轉至孩子:“馱子卸到十字街,先問娃兒乖不乖?”[2]325“乖”即身體好、未生病之意。妻子答:“自打你走娃不乖,上在脊背下在懷。”[2]325又滿懷歉意地說:“心想給你做雙鞋,娃兒吵得不落臺。”[2]325“落臺”即不停。丈夫寬慰妻子:“只要你把娃引乖,沒得鞋了買草鞋。”在相互理解和寬慰中,見面儀式完成。
二、白馬藏人山歌的語言特征
白馬藏人山歌的句式之基本構成單位是:興詞+應詞+敘事詞。興詞是第一句,起興、呼喚之意;應詞是第二句,有承上、啟下之雙重功能,承上即應和興詞的呼喚,啟下者開啟敘事。興詞與應詞之間的呼應有多種類型,包括語音呼應、語義呼應、情景呼應、比興呼應、性別呼應等[5]。各類呼應可以單獨出現,也可以重疊使用。語音呼應關系中興詞沒有實質性意義,或者說與應詞沒有意義上的關聯,如“茄子開的絳色花,賢妹上街賣豆芽。看見小哥身邊過,悄悄給他抓一把”[2]373中,興詞“茄子開的絳色花”起的是定調和定韻腳的功能,與應詞“賢妹上街賣豆芽”押尾韻,但語義不相關;在“黃裱紙,九十張,黃鷹落在柳樹上。黃鷹落樹有架哩,賢妹落難有啥哩”[2]376一句中,興詞“黃裱紙,九十張”和應詞“黃鷹落在柳樹上”既押頭韻,也押尾韻,但語義不相關。語義呼應不僅語音相呼應,語義也相關,如“白汗褂子搭襟斜,毛藍手巾腰里別。走路甭叫身材擺,看人甭叫眼睛斜”[2]372中,興詞“白汗褂子搭襟斜”描述衣著,應詞“毛藍手巾腰里別”描述衣著上的裝飾,二者不僅押尾韻,語義上也是承接、順應關系。
興詞和應詞也可以是情景呼應關系,即興詞描述景物或者事件發生的背景,為應詞的抒情或敘事營造一種氣氛,如“天上星多月光明,小哥約我墻外等。纏綿話語悄悄定,愛你到死不變心”。興詞和應詞還可以是比興關系,即興詞不僅起到語音呼應或情景呼應作用,還兼做比喻,如“滿架葡萄根連根,我和賢妹心貼心;葡萄架斷根還在,你我到死永同心”[2]378中,興詞以葡萄的“根連根”比喻戀愛雙方的“心連心”,把抽象的情感具象化。最有特色的是歌詞中的男女性別呼應,顯性的性別呼應以小哥、小郎或賢妹、奴家等為興詞,呼喚對應性別的回應,這種呼應最多,這與情歌“我給你唱”的心理機制以及“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的情感需要相關。隱性的性別呼應以自然成對的事物如“太陽/月亮”“天上/地下”“陽山/陰山”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對應物如上下磨盤等為興詞,是男/女這對最基本的二元對立概念的延伸,也由此反過來映射男/女,期待對應性別的呼應,如“磨盤石頭你為王,五色糧食你先嘗。你把上扇懸吊起,看你下扇忙不忙”。
白馬人的山歌有較強的敘述性,體現在敘事詞上。敘述的三要素是人物、情節和事件。山歌中少至兩句的敘事詞也在講述完整的故事情節,如“白楊樹,順溝栽,黃菊花兒九月開。到處朋友得罪了,實心只有我兩塊”[2]358。前兩句起語音興呼功能,與后兩句沒有語義關聯。敘事詞“到處朋友得罪了,實心只有我兩塊”講述歌者的戀愛歷程:處了不少朋友,都因不合拍而告吹,最終只和傾訴對象實心實意地相處。敘事完成,表白愛情的目的也達到了。中篇敘事山歌《難心不過出門人》[2]328,通篇共三十六句唱詞,以腳戶為敘述者,講述見聞:“小伙出門盤費多,老漢出門沒柰何。”描寫生意上的得失:“今年當歸跌了價,走在路上短精神。”描摹艱苦的住宿“熱肉爬到冷地下”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心理反應“有錢沒錢我回去家”,并設想回家之后的情景:“先問老子再問娘,再問夫妻小冤家。”至此,敘述者突然轉為腳戶之妻:“騾子馱的鈴來了,奴家丈夫回來了。”敘述從腳戶的心理活動突然轉換到妻子的聽覺上來,遠處傳來熟悉的鈴聲,轉喻丈夫的歸來。妻子的凝神傾聽將她的期盼、等待生動地刻畫出來。
注釋:
①調查資料:訪談對象:李雙全(男,39 歲,漢族,農民),訪談人:張淑萍、艾麗,訪談地點:甘肅省隴南市文縣鐵樓藏族自治鄉石門溝村,訪談時間:2015 年3 月5 日.
②調查資料:訪談對象:劉宗元(男,48 歲,漢族,農民),訪談人:張淑萍、艾麗,訪談地點:甘肅省隴南市文縣中寨鄉,訪談時間:2015 年3 月6 日.
③調查資料:訪談對象:余林機(男,56 歲,白馬藏族,農民),訪談人:張淑萍、艾麗,訪談地點:甘肅省隴南市文縣中寨鄉,訪談時間:2015 年5 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