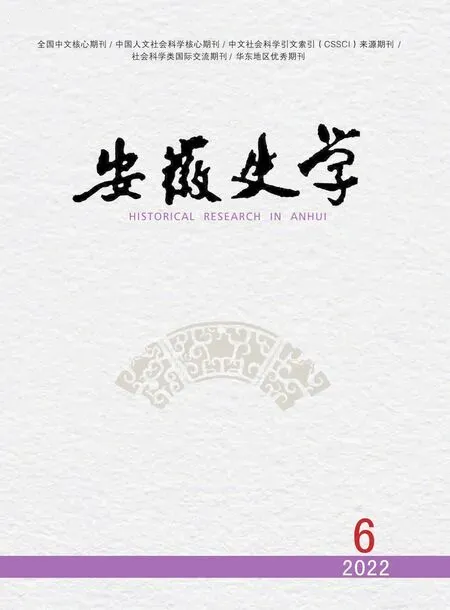《求己錄》與甲午戰后的和戰反思
楊雄威
(上海大學 歷史系,上海 200444)
抗戰前夕,周作人在給梁實秋的書信中自言與輿論氛圍的格格不入:“日前曾想寫一篇關于《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1)梁實秋:《憶周作人先生》,陳子善編:《梁實秋文學回憶錄》,岳麓書社1989年版,第249頁。《求己錄》是一部創作于甲午戰爭期間的反戰作品。作者陶葆廉是晚清著名疆臣陶模之子。他從甲午戰時開始匯集歷史反戰文字并加以論說,最終以《求己錄》之名面世,意在利用傳統思想資源敦促朝野反思和戰問題。
中國歷史文獻素以浩繁著稱,但匯集成卷的反戰文字卻十分罕見。進而言之,甲午戰敗之后變法聲浪日高,骎骎然成為時代潮流,陶葆廉及其所代表的部分晚清士大夫群體的和戰觀念與時代顯得格格不入。其后在20世紀流行的革命敘事、現代化敘事和民族主義敘事中更是無一例外地處在失語地位。(2)高拜石曾搜集各家論說,揄揚陶模、陶葆廉父子政績,且代為辯誣。參見高拜石:《新編古春風樓瑣記》第4集,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311頁。關曉紅教授的研究也對陶葆廉隨父從政等事有所關注。參見關曉紅:《陶模與清末新政》,《歷史研究》2003年第6期。二人的論述重點不約而同地放在陶氏父子對維新和革命的態度上。與此相應的是,《求己錄》至民國時期已近乎不聞,直至今日學界也罕有論及者。但這也正好提示書中有不同于上述話語體系的治國理路。新文化史主張借助陌生的歷史面相開啟“相異的意義體系”(3)參見羅志田:《不改原有之字以開啟“相異的意義體系”——舊文新解二則》,《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第4期。,本文即嘗試由此書切入考察甲午戰后朝野士大夫對和戰問題的反思。
一、《求己錄》的閱讀史
1967年周作人去世后,梁實秋為寫紀念文章向梁容若教授請教了《求己錄》的來歷,被告以卷冊、刊本、館藏和作者等信息。但梁教授也未讀過此書,只是據陶葆廉的身份和“久佐父幕”的閱歷推想:“陶模曾于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上書清廷請全廢宦官,聳動天下,主稿者當為其哲嗣。《求己錄》中如有此種思想,自當為豈明老人所傾倒也。”梁實秋也據此感慨道:“豈明先生想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當無疑問,惜不知《求己錄》內容究如何耳。”(4)梁實秋:《憶豈明老人》,陳子善編:《梁實秋文學回憶錄》,第242頁。可見此書在彼時已覓之不易。
但此書在晚清刊出之后曾風行一時。已知有蘭州官書局、求是書院、山東官書局、東河節署、江南制造總局等多個版本。《求己錄》刊布于1897年,面世不久,翁同龢即得讀之,并在日記中贊許作者“說時務,而引諸儒之說為根本,通才也”。(5)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7卷,1897年5月7日,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3043頁。此書主旨是反戰,翁同龢作為甲午戰爭中主戰派的領袖人物,尚且推許其為“通才”,可見其議論之動人。多年后,翰林惲毓鼎亦得緣一覽,自云“燈下看末卷,不忍釋手。夜深遂盡一冊”。(6)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第2冊,宣統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514頁。顯然也為此書所折服。
由當時讀者反饋可推知,《求己錄》展露了陶葆廉的才學。1902年夏,報界披露“有引見某員到京,以《求己錄》一書贈與某京堂”,而“某京堂得書大喜,以為是三百年來未有之文字,言于某邸,欲以是書進呈御覽,并擬奏保陶公子”,結果“為某相國所阻而止”。(7)《所聞錄》,《選報》第23期,1902年7月25日。此說今已難考,不過1908年春,疆吏錫良在薦舉陶葆廉時確曾專門提及此書。無獨有偶,1910年江西巡撫馮汝骙保薦陶葆廉為碩學通儒議員時,亦以此書為據,稱其“援古鑒今,通而不迂,平而不激,洵屬深識遠見,體用兼備之士。”(8)《本署司袁奉撫憲札準江西撫院咨陶紳保(葆)廉保為碩學通儒議員文》(宣統二年三月十六日),《浙江教育官報》1910年第21期。不僅有官場的揄揚,也有學者的推崇。譚獻即在日記中稱此書“以內治為本,不鶩外功。感時多沉痛之言,陳古刺今,折衷巨儒。少年賢哲之言可陳當寧”。(9)范旭侖、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廿七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頁。
不乏讀者希望將書中見解推而廣之。汪康年的一位友人提到:“拙存《求己錄》足以醒世,蘭州道黃觀察賞識之,囑寄閣下采擇傳播。”(10)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4),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1、3458頁。另有某君亦曾希望推薦給《時務報》以“使中外識時務者觀之”。(11)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4),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1、3458頁。除了向報館推薦,也有朋友間的轉贈。江瀚便“以拙存所著《辛卯侍行錄》及《求己錄》贈紫翱大令”。(12)鄭園整理:《江瀚日記》,1904年2月2日,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頁。杭州知府林啟還曾將《求己錄》與《明夷待訪錄》《天演論》及曾、胡文集指定為求是學堂的必讀書目。
陶葆廉在書成之后的幾年中,亦曾分贈各方士人。1900年冬,鄭孝胥日記載:“陶拙存來,遺所撰《求己錄》。”(13)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1900年12月25日,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778頁。1903年,江瀚日記載:“拙存來拜,撝謙過甚,并贈所刻書,惟《求己錄》已早讀之耳。”(14)鄭園整理:《江瀚日記》,1903年10月16日,第235頁。惲毓鼎得讀此書則是1910年,時陶葆廉在京任事,交游之中以書相贈。進入民國之后,《求己錄》已罕有人言及。但周作人偶得讀之便將其作者引為知己。陶葆廉究竟是何種人物,值得深究。
二、陶葆廉其人
陶葆廉(1862—1938),浙江嘉興人,字拙存,號蘆涇遁士,晚清疆臣陶模之子,副貢生。1891年隨父赴任新疆巡撫,其后又相繼隨赴陜甘和兩廣總督任。1902年,陶模去世,得蔭封為員外郎。1904年浙撫聶緝椝因其“品端學粹,名實相孚”奏請其代替勞乃宣任職為浙江高等學堂總理。(15)《浙江巡撫聶奏請遴員接辦大學堂片》,《申報》1904年3月25日,第11版。其后入浙撫張曾敭幕,1906年張撫任命其襄助辦理新政兼交涉商務、礦物、路政等事。(16)《遴員分科襄理政治》,《申報》1906年1月15日,第9版。1908年春,因端方屢屢相邀,由浙撫馮汝骙幕赴江督端方幕。(17)《陶部郎襄辦洋務》,《申報》1908年3月6日,第10版。同年經東督錫良力薦,蒙召對后擢為郎中,供職陸軍部。1910年經保薦入選咨政院碩學通儒議員。1911年任內閣法制院參議。鼎革之后定居滬上。其后仍參與嘉興乃至浙江地方社會活動,主要事跡是1919年擔任江浙兩省聯辦的太湖水利工程會辦,至1922年辭職。
陶模晚年在兩廣任上,父子二人以政見開明著稱,對革命黨人亦頗有包容。特別是曾將吳稚暉等人納為幕友,故其后在革命黨中口碑甚佳。吳稚暉即謂陶葆廉之“議論全與今之黨人契合”。(18)吳稚暉:《勤甫傳略》,《吳稚暉全集》卷13《雜著1》,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235、235、235頁。此外,陶葆廉亦與江浙的維新派士人交游密切。
陶葆廉是晚清士林公認的時務人才。鄭孝胥便“素聞其考論時務”。(19)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1900年12月20日,第777頁。與鄭氏一樣有外洋履歷的謝希傅頗欽佩陶葆廉的見識,向報人汪康年推薦說“偶檢行篋,得陶哲臣公子書一通,慷慨時局,與諸公為并世奇英”。(20)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3),第2814頁。陶葆廉的書信也折服過袁昶。其閱信后大喜道:“論新疆事具有識略,不惟保家之子,抑亦經世之才,難得難得!去宋賢高平范氏、藍田呂氏之子弟不遠,尤想見中丞公家法之嚴也。”(21)孫之梅整理:《袁昶日記》下,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979頁。吳稚暉后來亦許其為“名世才”。(22)吳稚暉:《勤甫傳略》,《吳稚暉全集》卷13《雜著1》,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235、235、235頁。錫良在上奏薦舉時則稱其“于新政多所贊畫,績學勵行,世罕其匹。京內外爭相薦引,并辭不就”。(23)《遵旨薦舉人才摺》(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奏稿》第2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63頁。薦舉的文體性質決定薦舉者必當為人說項,然而“世罕其匹”四字薦語畢竟分量不輕,可見錫良對他的格外認可。馮汝骙也以幕主身份親承“于新政外交治梟多用其策”。(24)《本署司袁奉撫憲札準江西撫院咨陶紳保(葆)廉保為碩學通儒議員文》(宣統二年三月十六日),《浙江教育官報》1910年第21期。
除《求己錄》外,陶葆廉有多部編著行世。其成名作《辛卯侍行記》可與《求己錄》并稱,此書考辨其1891和1892年間西行途中的地理風物,頗為時人推許。可以說,這兩部作品是陶葆廉生平代表作,體現了他的經世之才,同時也為他帶來廣泛聲譽。
歷史人物之性情最為微妙難察,但又不可不察。陶葆廉在陸軍部供職時的同事湯用彬曾在一部掌故書《新談往》中寫道:“其后父死,家貧窘,數入督幕,內任陸軍部郎。余前年與之同官戎署,見其趨奉鐵良,怡色柔聲,委瑣卑陋,英氣盡矣。甚矣,生計之困人也!”(25)湯用彬:《新談往》,國維報館1912年版,第14頁。但其后江庸《趨庭隨筆》則不以此說為然:“殊譏之太過,拙存為人卑以自牧則有之,何至若此?”江庸還舉例說明“《新談往》一書紀載頗多失實”。(26)江庸:《趨庭隨筆》,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9—30頁。江庸為江瀚之子,江瀚與陶葆廉會面時即覺其“撝謙過甚”。若說此時因失怙而氣短,何以1900年底鄭孝胥所見之陶葆廉亦“頗無貴介氣”?綜而觀之,則知湯用彬之不識人。其實,陶模父子二人性皆中和,岑春煊謂陶葆廉“持躬端謹,一如陶模”。(27)《署兩廣總督岑奏參道員招權納賄請旨懲辦片》,《申報》1904年2月25日,第10版。此固是岑春煊在參片中為陶葆廉辯護,但參照前后左右史料,可知用語甚確。朱宗良后來憶稱在求是書院執掌教鞭的陶葆廉“性溫和”(28)朱宗良:《浙大前身之回憶》,《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34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頁。,此印象亦屬可靠。
陶葆廉不惟謙卑,亦且淡泊,可稱安貧樂道。有論者謂:“陶拙存性行敦樸,居恒端坐一室,鎮日讀書無怠容。聲色貨利征逐游觀之樂去之若浼,布藝蔬食,怡然自得。”(29)陳贛一:《新語林》,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頁。其父病逝后,家境當不富裕。吳稚暉即稱其“至高隱于窮餓”。且輾轉聽說其“入民國曾一度以饑不舉火,隱姓名為官中傭書,得小胥值”,如此仍“夷然不為忤”。(30)吳稚暉:《勤甫傳略》,《吳稚暉全集》卷13《雜著1》,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235、235、235頁。沃丘仲子謂其“足跡不至權貴門”,“天性介潔”(31)沃丘仲子:《當代名人小傳》下,崇文書局1935年版,第204頁。,洵非過譽。1924年,陶葆廉有詩句云:“安定儒風欣未墜,跼身斗室道心寬。”(32)陶拙存:《樸安以消寒九集詩索和步原韻答之》,《民國日報·國學周刊》1924年3月6日,第4版。所云可視為夫子自道。
河流健康功能得到改善,有效修復了生態。在實施增效擴容改造時,重慶市對納入改造的非季節性河流電站均按規定完善了生態流量泄放措施,提高了水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有效改善和恢復了202條河流流域生態功能,保護了河流健康。通過改造新增了清潔能源供應量,每年可減少燃煤75萬t,減少排放二氧化碳191萬t、二氧化硫近3萬t和煙塵5萬余t。
在晚清與民國間,流傳四公子之說。湯用彬即謂:“戊戌維新人才,首推四公子。四公子者,譚嗣同復生,陳三立伯嚴,吳保初彥復,陶葆廉拙存……當時人士率以葆廉高尚,非時流所及。”(33)湯用彬:《新談往》,第13—14頁。民國之后,四公子具體所指為誰,其說不一。查湯用彬此書出自民元,可知晚清時即有四公子之說。在湯氏聽到的版本中,陶葆廉名列其中。從其生平行止來看,這一雅稱可謂名副其實。
三、《求己錄》中的和戰反思
關于《求己錄》一書的主旨,陶葆廉在甲午冬所作的敘目中自解其題云:“竊取孟子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名曰《求己錄》。”1896年,止園主人史夢蘭為其所作的序言則進一步闡發其義道:“法之當變,人人知之,特恐談變法者第震驚乎外國富強之說,舉古昔圣王經世大法,儒者之要道,一是芥棄,以為迂拙虛偽而不切于事,于是競務為功利,以窮兵黷武為能,甚且假孟子民重君輕之說以飾其奸而濟其詐。”(34)蘆涇遁士:《求己錄·序》,林慶彰等主編:《晚清四部叢刊》第2編,(臺灣)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頁。這一看法,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之旨相去不遠,反映的是晚清“變法”聲浪中的另一個源頭。(35)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陳寅格集·寒柳堂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67頁。
在陶葆廉乙未春所作的跋中,可知此書并不以康梁為對手方,而是針對另外兩個更為強大的對手。其跋先是交代說:“此編屬稿于平壤告捷之初,脫稿于鴨綠沉舟之后,以示友人,有病其多宋儒學究之語詳義理而略事功者。”繼而解釋說:“今天下言事功者不外變法與不變法兩途。余獨以為法可變而義理不可變。”進而又兩面出擊:“余嘗痛夫世之識時務者往往有才而無行,而迂夸之徒又復托名于儒以守舊為正,以主戰為高。紛呶叫囂,至于誤國而不之悟。雖名公巨卿,負中外重望,明知其說之必不可恃,猶必假此自重,以博一日之虛名。”(36)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69—270、1、62、3、157、5、19—20頁。結合甲午史事,可知所謂“識時務者”是指向得勢多年的洋務派,且或特指負有戰敗之責的李鴻章。而“以守舊為正”和“以主戰為高”的迂夸之徒,則又指向當時極力主戰的天下士人,所謂的“名公巨卿”或特指主戰派領袖翁同龢等人。
是書分上中下三卷,茲擇要摘錄并解讀如下:
上卷敘述或摘錄先秦至東漢六個時段的史例,并分別加以論說。其一為《左傳》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等事。陶葆廉開篇第一句評論即謂:“自來振衰起弱,必無速效。”(37)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69—270、1、62、3、157、5、19—20頁。這種觀點貫穿本書始終,如其后所謂“王道無近功”之說便是如此。(38)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69—270、1、62、3、157、5、19—20頁。陶葆廉借“通商惠工,衛文以之中興”之事,批評“今士大夫平居賤視工商,迨身任理財之責,惟以重稅商賈為計”。(39)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69—270、1、62、3、157、5、19—20頁。通商是此節論說的重點,陶葆廉列舉了歐洲列強因重商而致富強的例子。值得提及的是,在本書的前后論說中,歐洲列強皆以正面形象出現。如提到泰西預算制度便感慨“島族竟有古法”。(40)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69—270、1、62、3、157、5、19—20頁。
其二為《左傳》虢公敗戎事。虢以小國而欲張威于晉,遂向犬戎用兵,晉國的有識之士遂預言虢之將亡。陶葆廉據此論述道:“回天之力,宜培養根原,不宜尚虛驕之客氣。懾敵之方,恃有久長之政本,不恃有一日之武功。”(41)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69—270、1、62、3、157、5、19—20頁。這顯然是對當下戰事的回應。有論者曾暢想對日“一鼓作氣,戰勝取威”以“雪積恥而戢它族”。(42)《言有章致盛宣懷函》(1894年7月4日),陳旭麓等主編:《甲午戰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頁。其用意與虢公敗戎差相仿佛。
其三節錄《吳越春秋》越王勾踐事。陶葆廉強調的是其戰備過程,聲稱“自強本也,戰功末也”。在論說中,陶葆廉對五類潛在讀者提出警告:一是“肩大任柄國政者”,二是“不問根本肆口談兵者”,三是“不懼天災不顧民貧不聞鄰國非笑不量強敵才力而妄求一逞者”,四是“儒臣身居局外交章論戰者”,五是“驕將狃于前功鄙夷新法者”。(43)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69—270、1、62、3、157、5、19—20頁。通覽甲午戰爭前后的朝野言論,這五類人隨處可見。
其四述《漢書》匈奴事,借西漢和親等史事向主戰派發難。批評道:“老將談兵,多憑客氣以欺人,書生最易受欺,慎勿人云亦云。”(44)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老將談兵”之說似有所指。當時朝野士人皆以老將為柱石,號稱知兵的李鴻章在甲午戰前也有“劉省三不出,環顧諸將無可屬”之感。(45)張佩綸:《復鹿菘硯尚書》,《澗于集·書牘》卷6,《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5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總第598頁。事實證明,老將如劉坤一和吳大澂者,一試之后皆不堪用,劉銘傳則以老病得保晚節。陶葆廉屢次譏諷儒生不知戰而好戰。并指出:“北宋以上至漢唐,公卿吏民均不諱言和。”(46)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這一論斷在曾國藩等中興名臣的文集中多次出現。
其五述《后漢書》所載匈奴及西域事。此節重點談班超在西域的事功,陶葆廉指責其“動作孟浪,類亡命無賴者所為,蓋以傭書之苦,投筆之憤,日懸一封侯之想于心目間,不憚行險以僥幸”。(47)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班超經營西域事為歷代論者所推重,惟王夫之《讀通鑒論》自立異說,揭“其兄弟相獎,誣上徼幸以取功名”。(48)王夫之:《讀通鑒論》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65頁。陶葆廉當是借鑒其說而略作文字發揮。
其六述漢靈帝擊鮮卑事,提到靈帝未聽蔡邕勸阻用兵而兵敗。陶葆廉的結論是:“兩漢君臣但以慮匈奴鮮卑及西域各國為漢患,然亡前漢者外戚,亡東漢者閹寺。”(49)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并推及晉隋唐宋元諸代,認為亡國之因皆在蕭墻之內。
中卷摘錄兩宋儒家論和戰事,共十則。第一則錄丁度論契丹請絕夏元昊進貢事。陶葆廉以宋遼夏關系比附當下之中日韓,據此說明不當為朝鮮開戰,此說已跳出藩屬觀念框架。第二則錄司馬光乞戒邊城疏。陶葆廉由疏中論說談及當下邊吏“藐視外人,或于文牘寓譏訕,或于酬接示倨傲”。(50)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讀晚清對外交涉史,可證其說。第三則錄蘇軾上皇帝書,此書針對王安石變法而論道德風俗。陶葆廉據此批評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不能隱忍補苴,恐懼激發,受小屈以求大伸,盡人事以待天命,而大言不慚,遽構兵端,未有不受大禍者”。(51)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這一悲劇,在稍后的庚子年便不幸上演。無怪乎譚獻是年讀《求己錄》而感慨“乃至今日,則針砭痛切,更使人感涕盈襟也”。(52)譚獻:《復堂日記》,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廿七日,第409頁。
第四則節錄程氏遺書。二程主張治道的根本在于“格君心之非”。第五則節錄《程子易傳》的履卦傳。陶葆廉由“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之論出發(53)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闡發科舉、保薦、捐例之害,主張改科舉嚴保薦廢捐例。這一主張,亦出現在其父的奏折中,折中謂“人才之所以不振,皆由考試太濫,捐納太廣,保舉太多”。(5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折》第32輯《內政·賑濟》,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553頁。其余數則皆錄朱熹格君心和正人心的文字。陶葆廉指出人主不能正心,是源于宮室、嬪妾、閹寺三弊。(55)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庚子后,陶模上奏請廢除宦官,其旨即在于此。陶氏父子這一政見實有所指,陶葆廉致汪康年函便斷言“義和團之見信于王公,實由太監揄揚”。(56)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2),第1924—1925頁。
下卷為朱子語類節錄,又分三部分,分別為憂時之語、經世之語、論和戰及恢復之語。其下又按主題分成若干條目。每一主題摘錄朱子語類若干條不等。或于文中按語,或于文后論說,形式不拘一格。
憂時之語,包含因循釀患、上下隔膜、科舉無益、吏治茍且、財匱用侈、將多兵劣、舊制拘牽、變法未善、文學無憑、正學不明等十個主題。論上下隔膜時,陶葆廉說:“漢唐以來,人主崇高太過,上下懸絕,萬事蒙蔽,至尊之極,即以召至卑之禍。”(57)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晚清不少士人如宋恕、俞樾等談論時弊時都曾提到君位過尊之弊,皆是復古理路。論科舉無益時,陶葆廉引朱子之語反對“崇尚文辭”。(58)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是書反復表達過對文辭的不屑。論將多兵劣問題時,陶葆廉詳列當下十四項練兵問題。在文學無憑條目,陶葆廉痛陳“宋人奏疏,輒詬人為奸邪”。繼而又謂“言路壅塞固可憂,言路厖聒尤可患”。(59)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頁。晚清政治存在疆臣與言路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故而言路對疆臣的彈奏連篇累牘,而疆臣對言路的非議也屢見不鮮。
經世之語,包括君心、變法、政體、用人、裁冗官、通下情、勵臣節、興學校和為學本末諸條目。在用人條稱:“古來致治大率用一賢相,近今島族如意國用嘉富洱侯而強,德國用畢士麻克而興,得此道也。”(60)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頁。在裁冗官條,陶葆廉主張對中央與地方各機構的官員大加裁并,激進程度遠甚于戊戌變法。故有論者回應說“何職為贅,何職為要,應裁應并,可議者甚多,斷不能于一朝之間悉數改革”。(61)《裁道府增知縣各缺論》,《申報》1901年4月21日,第1版。其后陶模的奏折亦曾主張裁冗官,但方案已頗和緩。在興學校條,認為科舉“不足利國而轉以病國”。(62)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頁。標榜理學的士大夫竟主張廢科舉,折射了清末新政不易為人察覺的復古面向。實際上《求己錄》通篇有復古傾向,前述裁冗官條主張設黨正,便是從顧炎武封建論借鑒而來。
論和戰及恢復之語包括慎戰、浪戰、和議、失機、猜疑、敵情、復仇、恢復諸條目。在慎戰條,陶葆廉謂:“耳食者概以天幸為人力,幾若無敵于天下。余常論兵力遠不如外人,冀或警悟發憤,而聞者詬為狂。”(63)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頁。浪戰條指出:“世人第知安石以新法誤國,不知其新法非為求治安,特為揣摩上意,欲用兵而設。讀此乃知安石直以主戰誤國耳。”(64)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頁。又由朱子自謙不能帶兵打仗說起,嘲笑“膠庠小儒閭巷鄙夫時有平戎之策”。(65)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頁。和議條感嘆“吾讀漢文帝與外蕃諸書,語和而氣謙”。(66)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頁。在敵情條,陶葆廉對當下戰事多有批評。如謂“昨見某總兵上書謂敵軍一人持一械,我亦一人一械,何畏之有!豈知敵械十發九中,我械十不中一”。又力言報紙之謬,如“捏造某大將戰績,鋪張克敵之易,若惟恐中國士大夫之或醒而重投迷藥者”。(67)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頁。在復仇條,陶葆廉批評士大夫“嘩然以中華夷狄為詞”。在恢復條,陶葆廉指出:“近時談兵者,不思敗軍之恇怯由于積年之虛夸,第云勿懼即可制勝。”(68)蘆涇遁士:《求己錄》,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頁。戰爭勝負已見之際,光緒帝向劉坤一問以當和當戰,劉借舊典答以“三戰必克”(69)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上,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53頁。,實則所謂士氣、血氣及后世所謂意志等戰爭心理,都受制于相當苛刻的客觀條件。
四、甲午后的和戰反思
甲午戰敗之初,天下士論集矢于李鴻章。其婿張佩綸即謂“目擊我師四十年之勛名威望,一旦為倭約喪盡”。(70)《張佩綸致李鴻章》(1895年),姜鳴整理:《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6頁。此時和議未成,張佩綸原意在于勸阻。但李鴻章屈服于時勢不得不背負罵名。攻擊李鴻章誤國甚至賣國的奏折和報章難以計數,一是責其不當和而和,二是責其治軍而不能戰。但陳寶箴則另辟一徑,怒其不當戰而戰:“勛舊大臣如李公首當其難,極知不堪戰,當投闕瀝血自陳,爭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聽。今猥塞責望謗議,舉中國之大、宗社之重,懸孤注,戲付一擲。”(71)陳三立:《先府君行狀》,錢文忠標點:《散原精舍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頁。
其時主和的聲音本就微弱,陳寶箴這一批評顯得曲高和寡。但其后朝野痛定思痛,便難免有不當開戰的反思。于是便又有了“甲午之役,人皆謂戰之罪”的輿論轉向。(72)《答客問索地事》,《申報》1899年3月21日,第1版。其矛頭自然也指向主戰派。傳言恭親王奕訢臨終遺囑大罵翁同龢“是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73)《圣怒有由》,《申報》1898年6月27日,第1版。陳寶琛著名的《感春》詩暗諷“冒昧主戰,一敗涂地,實毫無把握”。(74)陳衍:《石遺室詩話》(1),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頁。士人梁濟私下品藻人物時則謂,孫毓汶當國十年,雖有可議,但“其見事明決,聽信合肥,能知敵情,不輕主戰,比較同朝諸老,如徐蔭軒之愚蒙,李高陽之沽譽,翁常熟之輕信人言,號稱忠義,而實懵于國情致誤大局者,相去天淵”。(75)梁濟:《梁巨川遺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頁。
甲午戰爭不僅造成了翁李雙輸的局面,更導致國事日非。1897年初,翁同龢拜訪李鴻章,二人“縱談時事,不覺流涕”。(76)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7卷,1897年2月9日,第3022頁。從傳統政治觀念看,此時國家已處在和戰兩無可恃的局面。庚子之后,清王朝并未亡于外戰,因此這一時段的和戰問題便淡出后世論者的視野。不過對于當時的行動者而言,外患是真實的存在,軍事上屢挫于列強的屈辱和恐懼一直相伴,這也意味著和戰是個無法逃避的問題。這個問題集中體現在練兵上。
1900年冬,陶模由陜甘調任兩廣途中,在武漢有數日逗留。在此期間與張之洞談及練兵問題。據鄭孝胥日記載:“南皮言:‘陶子方制軍、景月汀中丞皆稍諳時局之不可不和,而皆謂軍事之不必講,此未達也。’余曰:‘今地球列國謀國之宗旨,皆練兵而主和,宜陶、景之不解也。’南皮嗟訝久之曰:‘然。’”(77)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1900年12月16日,第777頁。景月汀即景星,此時是江西巡撫的身份。這三位疆臣一致主和,所不同的是,陶、景認為連軍備都沒有必要講求,而張之洞則以為二人不解和戰奧旨。其幕賓鄭孝胥自詡通達,笑陶、景不了解列強治術。
其實陶模父子對兵事有自己的理解。陶模作為地方督撫,練兵自是他的關注點。陶葆廉后來任職陸軍部,亦是緣于他在軍事上的知識。他在《求己錄》中專門列舉十四條具體問題,足證其了解并非泛泛。陶模并非不知歐洲國家以戰備為常態。只不過陶氏父子另有顧慮。1901年,陶模上疏論新政事,仍堅稱“舉行新政,兵事只可緩言”。(78)陶模:《變通政務宜務本原摺》(1901年5月22日),杜宏春補正:《陶模奏議遺稿補證》,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594頁。根據他的解釋,緩言兵事是因為用費太巨。后來,陶葆廉在給錫良的信中更是痛陳練兵之害,語氣十分激越:“國家推行新政,原欲扶危定傾,無如百事競興,胥資財力,未收寸效,已損本根。其立名最正、耗帑最巨而釀禍最不可測者,莫如添練新兵之策。”這一推論,也主要基于經費問題。他認為:“兵愈練,餉愈匱,終歲誅求,則輿情離散,一朝不給,則驕卒必嘩,是以揚威尚武之虛名賈瓦解土崩之實禍。”(79)《錫良收陶葆廉來函》,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輯第135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669—670頁。
這一見解在《求己錄》書中有充分發揮。在論及東漢和戰史事時,陶葆廉指出,耿秉說以戰去戰,班超說以夷攻夷,“后世策士奉此二語為至計”,但實際上“匈奴、西域仍屢次背畔,中國反因勞費激變”。(80)蘆涇遁士:《求己錄》,第86頁。陶葆廉擔心國家練兵耗帑將重蹈覆轍。
歷史證明這一見識可稱高遠。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正是始于新軍的發難,而從更深層次的角度看,新政帶來的財政壓力加速了王朝的瓦解。民國肇造,南北政府即陷入巨大的財政危機,而軍費正是最大最急迫的支出項目。袁世凱當政時,武人的地位有增無已。迨其死后,國人迎來一個漫長的軍閥混戰時期。
宋人蘇洵曾以極其冷峻的筆調寫道:“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教之以殺人之事。”(81)《蘇明允上韓樞密書》,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標校:《古文辭類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87頁。早年曾鼓吹富強的嚴復,日后深病“武人世界”之成,屢次借用蘇洵此說回顧和檢討清末以來的世變。其致鄭孝胥書說:“自鐵良、袁世凱席德、日之說,舉國練兵,至今使不義之人執殺人之器,禍在天下,始知不揣其本而務其末之為害也。”(82)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1920年9月25日,第1842頁。在與熊希齡信中語氣更為痛切:“吾國原是極好清平世界,外交失敗,其過亦不盡在兵。自光、宣間,當路目光不遠,亦不悟中西情勢大殊,僩然主張練兵,提倡尚武……此吾國今日所由賾賾大亂,而萬劫不復也。”(83)嚴復:《與熊純如書》(1921年),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14頁。
清廷因外侮而強兵,結果未亡于外侮反亡于所練之兵。北洋政府由練兵起家,最終又帶來連綿內戰。對比嚴復的事后反思,陶葆廉的事先預警更顯得難能可貴。但在強敵環伺之際而反對尚武,乍看近乎悖謬。1906年時嚴復尚且視強兵為理所當然,認為“國不詰戎,民不尚武,雖風俗溫良,終歸侮奪”。(84)嚴復:《有強權無公理此語信歟》(1906年),孫應祥、皮后鋒編:《嚴復集補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
晚清理學名臣倭仁“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之說在求富求強的時代氛圍下淪為笑柄。傳統治國理路在時代語境下越來越失語,故陶葆廉在標榜義理的同時不得不為此再三辯護。原本的“深謀遠慮之言”,如今的“談經濟者鮮有不以為迂”。(85)蘆涇遁士:《求己錄》,第87頁。無獨有偶,素守“隱居放言”之戒的俞樾在甲午戰后針對盛行的變法言論(86)俞樾:《致錢應溥》,張燕嬰整理:《俞樾函札輯證》上,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頁。,也忍不住向翁同龢、錢應溥等當道力陳孟子“反本”之言為“自強之上策”,其文即自名為《迂議》。(87)俞樾:《致翁同龢》,張燕嬰整理:《俞樾函札輯證》下,第442頁。此后一百多年時間,中國不僅未曾脫離富強話語,還與傳統義理漸行漸遠,《求己錄》不僅無力為義理招魂,還從迂腐之論走向失語。
結 語
《求己錄》是一部創作于甲午戰爭期間的反戰作品。作者陶葆廉意在利用傳統思想資源中的“義理”敦促朝野反思當下的“事功”。這無疑是傳統王霸之辯的延續。在晚清,事功主要表現為強烈的富強訴求,富強又進而分化出洋務與和戰兩個時代命題。二者特別是后者正是《求己錄》的對手方。這導致它與后世流行的現代化敘事和民族主義敘事頗多捍格,加之與另一流行的革命敘事亦甚抵牾,故而在歷史大潮中陷入失語境地。與歷史主流的背離致使《求己錄》這類宣揚義理的論著,或蒙受污名,或湮沒無聞,或失去聲光。但從嚴復、章士釗等一批近代人物由新向舊的心理軌跡來看,傳統治理自有其獨特魅力,這也正是《求己錄》一書在思想史上的價值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