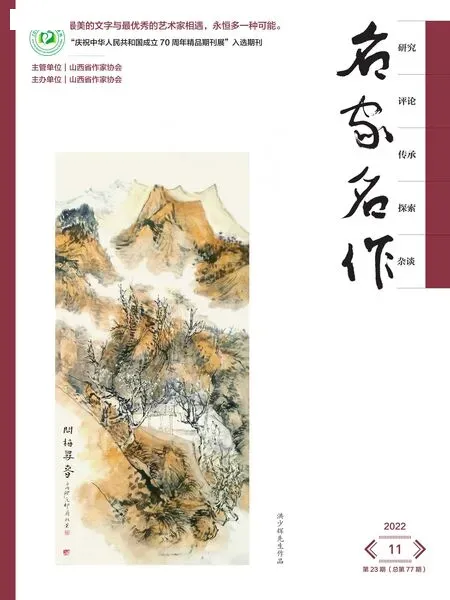對立與融合:從家庭三部曲看李安電影的文化沖突
邵亞璇
李安電影在跨文化傳播的語境下選擇從凌駕于東西方文化的高度去審視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在遭遇西方鮮明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念時的矛盾局面。李安電影在跨文化傳播的語境下審視中國傳統道德倫理,他考量了東西方觀眾的觀影趣味,在滿足本土中國觀眾、海外離散華人及其他非華人觀眾的基礎上,發力于客觀評價在價值觀念或者意識形態上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形態。李安試圖建構一條跨地區尋求文化、身份認同的道路。
一、李安電影中的家庭空間隱喻
李安在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以一種相對特殊的視野去審視兩種文化之間的矛盾。李安電影的主題中最重要的是探尋處于文化沖擊及轉型縫隙中的多元文化如何在相互角力中確認自身的主體位置。拋開文化形態、種族隔閡及美學訴求等因素來看,華語電影自我設定的全球化策略并未得到明確的體現,甚至是一再失利,在此基礎上,李安選擇了另一種創作策略成功進行了異域突圍。
東西方之間難以被調和的文化沖突被李安置換為象征著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規范的家庭沖突。影像與第三空間在多重維度發生勾連,從觀眾的觀影過程來看,影院作為與外部現實環境相對隔絕的真實空間,使得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暫時性擺脫了真實社交環境。而黑暗真實環境所建構出的游離于真實與虛幻間的虛實狀態可被歸為第三空間范疇。從影片的內容呈現來看,電影作為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又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生活的現實藝術,能夠敏銳地感知全球化語境下都市生活發展中的現實危機,并以電影語言的方式呈現給觀眾。李安無論是其“家庭三部曲”還是《臥虎藏龍》《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對此都有一定的現實闡釋。李安通過影像語言實踐所建構的“第三空間”,加深了身處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觀眾對于敘事文本內核的理解。
李安重視隱喻這種并非常規導演所鐘情的故事敘述技巧。作為世界范圍內離散華人的代表,李安在拍攝電影時,有意追尋電影中民族主體性的內在精神表達。他將西方的寫實主義傳統與中國的寫意化表達相結合,旨在創造出積極面向華語觀眾,同時也面向世界觀眾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他一直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協調原本南轅北轍的兩種文化形態之間的矛盾和差異。李安在影像文本的敘事中,東方文化成為其電影關于自身文化身份方面的鮮明旗幟。他將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法融入電影創作當中,創造出一種異域環境下東方文化的表現方式。影像所表現的并不僅僅是客觀事物本身的物理屬性,更多的情況下,影像也可以超越其事物所指的意義。《推手》中父親與兒媳婦之間矛盾的外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隸屬于不同文化形態的角色之間的矛盾。對于影像的理解與解讀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單一的畫面符號并不具有任何意義,符號只有通過一定規則的組接,才能使觀眾從成系統的符號文本中讀取導演所希望表達的含義。正如李安所說:“中國人將天人合一視為最高的精神境界,因此克制個人喜好,適應客觀環境是一種美德。”[1]而《推手》更是向觀眾呈現出導演所推崇的中庸之道。
二、李安電影中的中國形象
李安的華語電影并不是僅僅面對華語受眾群體,同時也積極面向全球范圍內的其他文化群體。這樣做就意味著,在電影中必須有效地協調好東西方價值觀念之間的矛盾。近幾年李安的影片已經不僅僅考慮離散華人觀眾及非中文地域的其他文化群體的觀影需要,他在文本內容的影像化呈現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去東方化做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很少有華人導演可以像李安一樣深入探索多元文化混雜中的交流與溝通狀態。相對于西方觀眾來說,中國形象作為“他者”本身就是陌生的。斯圖亞特·霍爾認為:關于“文化身份”,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把“文化身份”定位為一種共有的文化,集體的“一個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許多其他的、更加膚淺或人為地強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種歷史和祖先的人們也共享的這種“自我”。[2]命中注定,我這輩子都是做外人。這里面有中國結,有美國夢,但都沒有落實。李安在美國被貼上中國導演、華人導演之類的身份標簽,難以得到美國社會群體的接納,難以真正融入美國社會的文化政治環境中。同時,離散于中國地理主體的地域因素導致其難以真正完全回歸中華傳統文化主體。李安對家國的想象僅能存在于由域外文化與本體文化雙重兼容下的“第三空間”之中,而這種情感體驗呈現于電影中便是玉嬌龍這類既顛覆傳統文化又與傳統文化本體有著某種程度上契合的混雜人物形象中。玉嬌龍在與李慕白的對話中,承認了陰陽男女間的二元對立性,這可謂是對傳統文化的承認。而她對于女性陰性位置以及男性身處社會權利位置合法性的質疑,則可被看作其對性別身份改變的渴望以及自身所蘊含的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的影像化呈現。
人們之間的交流原本就是一個十分微妙和精巧的過程。在跨文化傳播中,因為有了不同文化的涉入,交流變得更加復雜。但是,跨文化傳播中縱然有著重重阻礙,充滿矛盾和沖突,卻依然很有吸引力。表面上看,這是因為人們需要不斷地理解他者,實現和他者的相處,以及在包括社會、經濟等領域更廣泛的交往;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說,這是源于文化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本能,源于人們本質上需要用不同于自己的視角來看待自身,看待周圍的世界,需要以融合了不同文化的方式來認識世界,從而提升認識自我的能力和認知外部事物以及規律的能力。[3]在臺灣長大,在美國接受正統電影教育的李安具有雙重文化身份。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優勢所造成的文化形態之間的優越感,或者是對于本民族文化一味地批判、抵制與拒絕。在感性認識與理性認知之間,李安站在東西文化、傳統與現代的交叉路口,展開了對東方文化在遭遇西方文化時所面臨的對抗、沖突的客觀描述。他基本沒有進行簡單的對錯劃分,而是期望在兩種不同文化形態的交流與碰撞中,找尋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式。
從李安對“文化中國”的建構來說,他所要建構起來的并不是具有特定地理坐標的區域,而是由語言、文化以及對于東方文化或是中國文化的認同和肯定。“文化中國”在李安的電影中可以被簡單理解為聯系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紐帶”,這條紐帶是超地域的,甚至是凌駕于歷史與文化元素之上的。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不同體制國家的發展,多元文化崛起,在文化產生中,生產特別的、有特點的產品變得異常重要。李安的電影中,夸張的行為以及與周圍環境相異的文化元素,恰恰是其進行文化想象的主要方式。書法、太極拳、飲食、推拿等正是李安作為中國人相對于西方文化的差異性而想象中國的具體表現。在《推手》中,李安就在不斷強調東西方之間的差異,展示雙方在飲食、教育等方面的不同。影片中,東西方文化和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差異、矛盾被李安以視覺對立的可見方式展示出來。在之后的《喜宴》中,雖然這部電影的矛盾點從表面上看只是探討伴侶性別的問題,但是在這個簡單的伴侶選擇問題背后,隱藏的是東西方文化沖突。這種對立依然是視覺化可見的。在偉同的父親即將來美國時,偉同和賽門在重新布置房間的同時,撤下許多意指同性戀的符號化物件,換上可以暗示異性戀身份的照片以及可以被中華傳統文化所認同的書法。對于差異的過分強調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對他者的排斥,但是在這里,筆者并不認為這是李安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一種排斥,恰恰相反,正是這種對于差異性的強調,才會使我們對于作為他者的西方文化傳統進行反思。
如果說,李安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簡稱《少年派》)之前創作的作品是將東西方文化間的差異性比較與角力場域的構建放置于中美之間的話,那么在《少年派》之后,他將東方的轄域進一步擴散至更遠的東方——印度。《少年派》中的東方不僅有印度文化、印度特定的地域性景觀呈現,還包括印度的文化以及宗教信仰。這里的“東方/東方文化”勢必是在面對不同地域、時間、社會政治文化語境影像下持續性地被西方語境轉譯且泛化的具有流變性的文化他者。
三、異化·歸化·同化
李安以“家庭三部曲”完美地闡釋了東西方文化在對立與沖突的過程中完成異化、歸化、同化的過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間文化的差異性在當下文化全球化語境下的呈現,促使我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即如何跨越文化間的鴻溝,從而達成跨文化的交互與融合。而李安正試圖借助電影完成這樣一種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整合。李安是一位可以將原本分隔兩端的東西方文化進行融合同化的導演。尤其是在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中,他將來自古老東方文化中的含蓄和傳統與來自西方文化中的激昂和浪漫分類放置又同化呈現在熒幕之上。從李安的電影作品中,觀眾不難發現東西方文化間共同的主題,即傳統家庭倫理問題中群體性與個體性之間的矛盾,同性之愛的社會接受程度等。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李安所渴望達成的一種中西文化共通的理想狀態。傳統的家庭倫理問題無論放置于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民族內部都是不得不去面對的永恒命題,但是鑒于不同地域的特殊與不同文化形態間的特殊,家庭內部的倫理問題也不相同。李安對于傳統家庭倫理問題的關注一直是其電影的主題,從《推手》里同堂三代的天倫之樂到《喜宴》中無論何種文化、地域環境下都客觀存在的傳宗接代的家庭責任,從《斷背山》中被傳統社會規范桎梏下的欲望到《制造伍德斯托克》中個體身心被家庭無情地束縛,從《飲食男女》中性取向以及兩性問題所造成的家庭內部矛盾到《冰風暴》里中產階級面臨淫亂家庭惡趣味的無奈困局,歷數李安的電影作品不難發現,他都以家庭倫理問題作為電影的敘事核心驅動力,他渴望通過電影去探討存在于東西方文化間共通性的家庭問題。李安希望通過電影中所闡發出的家庭倫理問題引發觀眾的思考,從而為受眾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具有相似性的問題和矛盾提供某種合理的解決方法。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依據現實生存環境的不同,受眾對于敘事文本中的倫理價值導向的建構有著不同的訴求,即差異化的生活方式勢必會帶來不同的現實問題。
四、結語
在李安的電影風格、電影結構甚至是電影內容的表現中,觀眾往往難以具體把握他的真實創作意圖。他的風格雖然不是多變的,但是每一部作品都會出現新的變化。李安的成功是對世界電影全球化的一種側面證明。早在20世紀中期,大衛·里恩的電影就已經初現跨國電影的雛形。跨文化傳播語境下,電影的全球化分工合作勢必會帶來不同意識形態的文化之間的交流、沖突,而如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成為擺在電影導演面前的重要問題。李安的華語電影能夠順利跨越文化、地理位置等各個方面的阻礙獲得成功,關鍵在于相對柔和的文化立場以及并不單一、呆板的編碼方式。他在審視兩種文化時,并不會以簡單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模式去評價,而是以一種相對客觀的、柔和的標準去看待這個宏大問題。僅僅就李安電影中的國家形象來說,他認為華語電影想要在西方觀眾觀影視野下生存,必須先滿足其觀影欲望,然后符合西方的語言和文化,以此為目標來改造東方文化。李安電影跨越了種族、文化以及性別,在經濟、社會全球化發展的今天,他以個人化制作電影的方式,描述了在跨文化、跨國語境下,在東西方文化傳播、交流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矛盾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