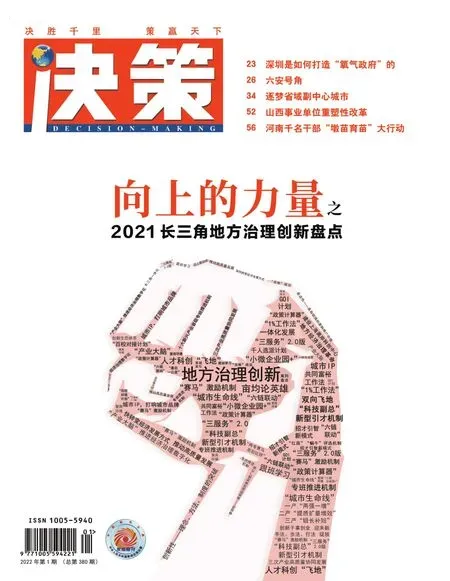堅決如鐵
黃榮才
羅則同在三望嶺停車,他以退休廳級干部的身份回到家鄉田背村擔任黨支部書記,遭到老婆羅蘇妍的強烈反對。羅蘇妍稍帶著也怪上西水縣縣委常委、副縣長陳一關。羅則同回鄉任職,和陳一關密切相關。
陳一關動了羅則同的心思,是因為田背村屢屢出事。陳一關發現田背村頻頻出現在公眾面前,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帶頭人,原來的村書記長病之后已經去世,村主任田河水這個人人不錯,就是容易一條筋,遇到事情根據自己理解簡單化處理,想用力有時候用不到點子上。村民也認可田河水是好人,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陳一關曾經和田河水說過:“如果你只會做好人,有一天你會發現自己是個壞人,因為你沒有帶著大家向前跑。”陳一關出身中醫世家,喜歡望聞問切。陳一關知道一名醫生,不僅僅要會看病,還要會治病,不會開藥方的醫生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不會出招的領導不是一個好領導。陳一關很清楚。
陳一關要給田背村找一個領頭人。陳一關會同田邊鎮黨委書記卓可和鎮長周見山把田背村比較“浮面”的人來回過了好幾遍,俗話說“過米篩”,但還是沒有發現合適的人。陳一關后來把目光瞄向羅則同。羅則同是田背村走出去的最高級別官員,其時還在省城某廳級單位當一把手,但他任期很快抵達終點,因為他距離六十周歲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用陳一關的話說,羅則同的職場生涯已經進入倒計時讀秒階段。陳一關找到羅則同,聊得熱乎。羅蘇妍以為羅則同僅僅是出于鄉情貢獻一點智慧,誰知道陳一關想要的不僅僅是羅則同的智慧,還是羅則同這個人。“我低估了陳一關的胃口。”后來羅蘇妍很是感慨。
喝著產自田背村高山上的田背茶,陳一關覺得自己是個釣魚高手,看著魚已經上鉤,不急切地把鉤扯了,而是慢慢遛魚,確保萬無一失。茶喝完,羅則同答應退休后回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縣委書記吳高仁高興地說:“陳常委不錯,挖了一個大坑,然后給這個坑找了一個大蘿卜,我相信這個蘿卜味道肯定很好。后續事情一定要跟緊,要落實好。別讓這個蘿卜跑了。”
羅則同的房子在村口處,他家前面有一塊平整的水田,被稱為大丘田。田背村夾在兩座大山中,左邊的山叫田墩山,右邊的是大坑山,到了盡頭橫切的山是田背山。有一條叫田坑的山澗從村莊中蜿蜒流下來。田背村和坑頭村、坑邊村是鄰村,被稱為田坑片。
羅則同順著田坑往上走,目光隨便一瞄,就看到郁郁蔥蔥的樹林。田背村的森林覆蓋率達到91%,每平方厘米的負氧離子達到2萬個以上,羅則同穿著短袖,感覺風都是濕潤的,有點豐滿、舒緩甚至粘稠的質感。羅則同把手伸直,看到微風吹過胳膊上的汗毛,有一種涼意輕柔撫摸過胳膊,羅則同舒服得好像皮膚要開始跳舞。
“ 陳一關哈哈大笑,看著車窗外茂密的樹林,搖下車窗,讓司機把空調關了,吹著自然風,揮了一下拳頭:“堅決如鐵。”
羅則同在和陳一關聊天的時候,說到年輕人不愿意留在村莊,兩個人都有共識:說家鄉回不去了,關鍵是找不到回去的理由,或者說留下來的理由。不能簡單一句要熱愛家鄉就要讓人回去或者留下來,要讓人看到盼頭,看到希望,否則就是某種程度上的道德綁架。很多人回憶家鄉,其實是留念當年的記憶,但骨子里又不愿意回到家鄉,家鄉已經今非昔比了。“殘缺是一種美,那是藝術家說的,對于老百姓,殘缺就是殘缺,就是不正常。”
羅則同的父母早亡,羅則同是吃著村里百家飯長大的,后來他上大學的錢都是村民里湊起來的,這也是羅則同義無反顧回到家鄉擔任黨支部書記的原因之一。
羅則同沒有看到田坑里有魚游來游去。田坑只剩下中間一條細細的水流,水面上各種垃圾漂浮。兩邊野草瘋長,河道兩旁,被開墾成菜園子。還零星散落著一些空農藥瓶子。
羅則同這幾天一直在村里轉來轉去,轉到山腳的時候,看到一個叫羅乙山的老人,他是村里有名的養蜜蜂的人。羅乙山正為蜂蜜賣不出去發愁,羅則同打電話叫來做電商的陳順意,讓他想辦法幫羅乙山賣蜂蜜。當天下午陳順意就和小伙伴們到了村里,答應第二天來做直播。次日,陳順意就開始“大山里的甜蜜事業”直播了,生意火爆。
當天晚上,羅則同一直琢磨田背村躲在深山無人知。對,直播。羅則同突然有個想法,他立刻打電話給陳一關。“直播村黨支部書記選舉過程?直播廳官如何當選村黨支部書記?”陳一關認可羅則同的思路,馬上向吳高仁匯報。吳高仁沉吟一會,拍板到:“干,這無非是把事后的熱點挪到事中,來個全過程公開。”
田背村黨員大會在眾多關注的目光中舉行,羅則同滿票當選田背村黨支部書記。對于選舉結果,網民沒有太多的意外,關鍵是羅則同 “廳官回鄉當村官”,是羅則同在當選后的表態發言。一時間,“廳官當村官”、“現代版的告老還鄉”、“新時期鄉紳文化的一種探索”等等成為網絡熱詞,田背村一下子就出名了,好像一個村姑突然間被推到公眾的面前。
“我們開始要做事了”羅則同召集召開支委會。“這次直播重點是選舉,鏡頭對著的是會議室。其他小視頻是提前準備的,都是挑好的說。現在村里出名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哪些上不得臺面。我覺得發展經濟要認真謀劃,村莊面貌要先改變,就像一個人,有沒有錢是一回事,穿名牌還是地攤貨是一回事,但首先要先把臉洗干凈,把衣服收拾整齊了。一個人,眼角有眼屎,嘴邊是口水的痕跡,頭發亂糟糟,衣服不是缺扣子就是扣錯扣子,或者這邊一塊污跡那邊沾點泥巴,人家一看就想站開一點。所以,第一個干的事就是田背村的‘凈臉工程’。把那些廢棄不用的豬圈、廁所給拆了,把路旁的垃圾堆,房前屋后的垃圾清理干凈,要讓人看到清清爽爽的田背村,而不是邋里邋遢。說好了,所有的豬圈、廁所都是無償拆除,誰家的孩子誰抱走,自己拆,其他的村民協助。廁所全村統一規劃,到時候建哪里,怎么建統一安排。趁這次換屆,不少外出的村民有回來,下午開村民大會,統一安排。”
田背村村民大會在村小學操場舉行,全村在家的人員都參加。羅則同在大會上掏心掏肺和村民交流。羅則同在村里的威信本來就很高,他掏心窩的話一說,就像一個火苗點到一堆柴火,轟地一下把村民的熱情給拉了起來。羅則同就“凈臉工程”做了安排,發動大家先把房前屋后收拾整齊,把雜物、垃圾清理干凈,把廢棄的豬圈、廁所全部拆了。說動手就動手,羅則同知道這股熱情一定不能讓它冷下來,旺火燒過了就會成小火,最后就是火灰。抓住時機很關鍵,羅則同太清楚這點。
五天過去,田背村所有的廢棄廁所、豬圈全部拆除到位,房前屋后也有了很大的改觀。“嗯,這村姑臉一洗,俊俏了不少。但還不夠,還要打扮打扮。”羅則同把目光盯住村里的小河田坑。羅則同把村干部都拉到河邊,讓大家好好看看。“我相信大家以前都在這水里游泳過。可現在呢?蹲下去連屁股都淹不了。還有河道上這些菜園子,這簡直就是好好一個女人,臉上長滿了雀斑。”田河水帶頭說 “沒說的,拔,現在馬上拔。村干部帶頭拔,現在馬上動手。村看村,戶看戶,村民看干部。廁所和豬圈都能說拆就拆,不就是一些菜嗎?”“這還真不一樣,那些廁所沒人用了,豬圈也不養豬了,拆了就拆了,但菜園子長菜啊,沒有菜,你天天用鹽配飯?還有啊,這羅了山在河道上種了許多南瓜,誰動他的南瓜他就要跟誰拼命,誰敢動他?他是赤腳的不怕穿鞋的。”大家正在說,羅了山扛著一把鋤頭走過來了。“誰說我不拔了,拔,我自己動手拔。”剛走到菜園子就自己動手,嘩啦啦地挖開了。
別人不知道,小魯可是知道羅則同提前去拜訪了羅了山。羅則同答應劃一片地讓羅了山種有造型的南瓜,把南瓜種成藝術品。羅了山痛快地答應鏟除河道里的南瓜。陳一關說羅則同屬于典型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做通羅了山的思想才去動河道清理的事情。”羅了山不阻攔,河道清理也就順暢推進。
羅則同跑了一趟省城,用陳一關的話說是回家述職。羅則同卻說這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項目。羅則同在省城家里住了幾天,就回到村里,忙乎招投標的事情。羅則同和陳一關說:“我可不是來當環衛工人,僅僅清理垃圾,清理河道。”他跑省城其中一個項目就是農村道路拼寬的事情。“以前官員退休告老還鄉,都還有個鳴鑼開道,帶些牌匾什么的回去,然后在縣志里留下那么幾行字。你現在可要充分發揮優勢,找一些項目回來落地。這些項目就是您的牌匾。”
羅則同回來的時候,田坑的河道已經清理得差不多了。“凈臉,不僅僅過過水,還要把眼屎擦干凈,把胡子刮干凈,鼻毛剪清楚。這臉才算凈。”羅則同在全村禁止隨意扔農藥瓶子,發動大家撿拾空農藥瓶子集中處理,半個月就拉走兩大車。“現在沒那么多經費,我只能管本村。我這也算是自掃家門雪。不過,如果大家都各掃門前雪這世界不就沒有雪了嗎。所以,下一步,要把各人房前屋后整理清楚。水稻不長稗子就長。”
羅則同找來侄輩羅建安,請他為村莊做規劃。羅建安在城里有公司,擅長規劃設計。“我們不能想到什么做什么,要么拆了建建了拆,重復建設浪費金錢;要么像一件衣服,補丁摞補丁,最后連底色是什么都不清楚。”
“我們再也不能走一步看一步,我們走一步要看好幾步,隨意走,撞墻了才要回頭,成本太大。”聞訊趕來的陳一關充分肯定羅則同的看法。“規劃要做,人心要聚攏,產業要清晰,但其中很關鍵的一點還要‘凈心’。現在凈臉工程是推進了,我還要推進凈心工程,我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但腳步不能停,要扎實推進,把步子走踏實了。”羅則同態度堅決。羅則同清楚,凈臉是面子,是有形工程,有形象進度。凈心是里子,是無形工程,看不到形象進度。清理村莊的垃圾容易,打掃心里的灰塵就沒那么簡單。
兩個人正聊得開心,小魯前來報告。羅建達的爺爺去世了。“一個考驗到了。”羅則同看著陳一關,念叨了一句。“這就像游戲打關,看看你這關是否能夠順利通過。”羅則同起身,前往羅建達家。
羅建達是田背村的“大腳”,在外辦了多家企業,是全村最有錢的人。羅建達的爺爺在九十五歲的高齡去世,屬于喜喪。但他這時候去世,剛好是羅則同要推出一條鄉規民約的節骨點,所以羅則同說是一個考驗,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羅則同不可能停下或者放緩腳步,要不然村民會說羅則同:“沒牙欺負軟。”
“煙花鞭炮的事情,只能你和建達商量。”村里退休教師羅科人看到羅則同,有點擔心的說。這對于長期牽頭處理喪事的羅科人來說,屬于首次出現焦慮情況。
羅則同推出的“凈心工程”一部分,就是解決煙花鞭炮的問題。田背村歷來有個習慣,誰家有人去世,辦理喪事期間,整個居民點除了喪家,其他都停辦伙食,不管有沒有在幫忙干活的,都在喪家吃飯,而且伙食越辦越好,食品豐富,酒也從家釀的米酒到啤酒、葡萄酒直到白酒,檔次越來越高,香煙滿足供應。不僅僅是吃,出殯那天,沿途燃放煙花鞭炮,很有陣勢。一個喪事下來,花費驚人。單單煙花鞭炮,最少的要燃放幾千元,多的數萬元,甚至上十萬元,造成極大浪費。
羅則同還在省城上班的時候,曾經和田河水他們商量如何解決喪事大辦的問題。在縣、鎮政府介入下,除了幫忙的,其他人基本不到場吃飯,伙食上也改變,全部改成吃面條,就是用大盆上香油拌面,上幾盤配菜,管吃飽但不奢華。不過這改革只到半路,就是解決了吃的問題,沒有解決燃放煙花鞭炮的問題。羅則同就任書記之后,和多人探討之后,尋求在這個問題上有實質性突破。其實村民對這習慣基本都是深惡痛絕,但“新例不設舊例不除”,沒有人愿意當這個“出頭鳥”,擔心引來非議。羅則同和村干部以及部分村民商量之后,決定適時推出禁止喪事大肆燃放煙花鞭炮的規定,規定上限不得超過一千元,這項約定得到村民代表大會通過,不過在哪天生效有了分歧。羅則同幾個人分析了村里老人的健康情況,推斷近期內身體健康狀況欠佳有可能去世的人,家屬應該不會有大的抵觸,就宣布即日生效。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羅建達的爺爺去世,他是否愿意當“出頭鳥?”
“這個比較麻煩,建達畢竟家大業大,不讓他燃放煙花鞭炮,他可能不愿意承擔‘埋不起’這個名聲,他又不差錢。再說了,他爺爺在望月嶺屬于有故事的人,這故事更是個大坎。”羅科人越想越擔憂。“我來和他談吧。他應該快到了吧?”羅則同深吸一口氣。羅建達住在城里,他爺爺平時也住城里,最近才回到望月嶺小住一段時間,沒想到就在老家去世了。羅建達接到消息就馬上往家里趕。
羅建達到家的時候,一下車跑著進了爺爺的房間,在爺爺的靈前下跪,哭得蕩氣回腸。羅則同和羅科人相互看看,心里更是忐忑。羅建達哭過之后,到了廳堂,謝過陳一關、羅則同和羅科人等人,不等羅則同說什么,他先開口:“爺爺對我很好,則同叔您知道我和爺爺的感情,您也知道我爺爺的結在哪里,他今天成仙了,我什么都不說。我知道村里剛剛出臺的規矩。”羅建達的眼淚又出來了,他擦了擦眼淚:“沒說的,我遵守,我來當這個‘出頭鳥’,我想這樣做,對村里推動這個規定會有一些幫助,爺爺會高興的。我爺爺知道路怎么走,我也要知道路怎么走。如果我堅持燃放煙花鞭炮,我爺爺肯定想拿拐杖打我。”羅則同和羅科人相互看看,放心地點了點頭。
“勢如破竹,事情出乎意料順利。”陳一關在回城路上,和羅則同通電話。“您回來,站在一個高點上,有些原來在普通村干部眼中的疑難雜癥已經不是問題。雖然不用驚堂木一拍滿場肅靜,但坐在那兒,氣場自然在。”“任重道遠,我發現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一串一串,不是一條線的問題,期間纏繞復雜,有些問題沒有那么簡單。”“那是當然,如果簡單,也就不用試驗,也就無需您出動。但現在既然已經上路,唯有往前走。地老天荒,堅決如鐵。”“停,停,聽下來好像牙要開始酸了,后面這些話,不知道的以為是小情侶的甜言蜜語。”陳一關哈哈大笑,看著車窗外茂密的樹林,搖下車窗,讓司機把空調關了,吹著自然風,揮了一下拳頭:“堅決如鐵。”
(原文刊載于《莆田文學》(季刊)2021年第三期,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