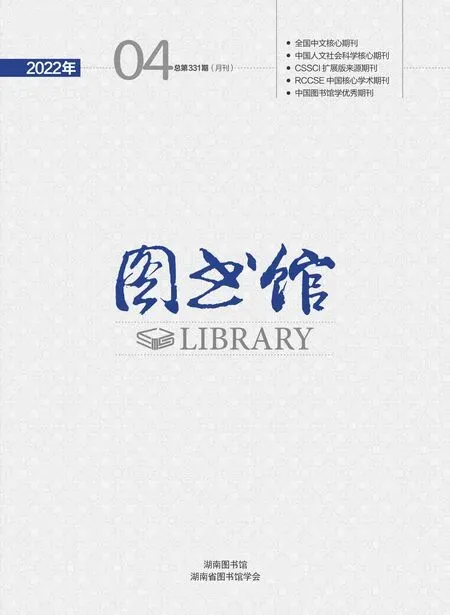古代江南私家藏書傳統對現代鄉村文化建設的啟示*
徐 雁 張思瑤 何雨琪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南京 210023)
在以“男耕女織”為基本生活和生產特征的傳統農業社會中,逐漸分離出若干以“晴耕雨讀”為文教追求的小康人家,以及以“詩書傳家”為榮耀的書香門第,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人文景觀。
追根溯源,陶淵明(365—427年)首次將“耕”“讀”并舉的田園生活場景展示于世,并深刻影響了后世文人學士的價值觀。他的《讀山海經》系列詩的開篇之作:“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如何?”,《歸園田居》詩中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以及《和郭主簿》詩中的“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莫不傳達出一種漁樵耕讀、書香琴韻的隱逸生活樂趣。隨著其詩作的流傳,其生活態度為文人學士所尊崇,并深刻影響到后世的崇文重教、樂讀慕學之風。
1 江南鄉村私家藏書的起源及讀書的傳統
藏書是一種綜合性的學術文化活動,對我國歷代典籍的搜集、保藏、復制、校勘、流傳有著重要貢獻。我國古代藏書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商代。據《尚書》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當時商王室設置有專門守藏典冊的文官。公元前551年,老子入周王室,任守藏室史。因公務時居宮中殿柱之下,又稱“柱下史”。春秋戰國之后,我國逐漸形成了皇家宮廷藏書、民間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及寺院、道觀藏書的藏書格局。其中私家藏書,自孔子及其弟子們開其先聲,在漢、唐盛世獲得較大發展,尤其是雕版印刷術在民間推廣應用以后,于宋、元、明三代接續繁盛,而又以“有清一代藏書,幾為江浙所獨占”[1]。
1.1 以蘇、杭為中心的江南私家藏書的起源
史載,孔門十哲之一的言偃(公元前506—前443年)晚年回歸常熟故里,傳播儒學于吳地,從而開啟了江南儒學文脈,尤其是“江南崇文藏書的歷史傳統”[2]3。
江南文化擁有蘇州、杭州兩個在歷史上同屬吳文化范疇的名城。就私家藏書來說,有史可稽的是吳郡錢塘(今浙江杭州)范家為最早。《晉書》卷九一《儒林傳》記載,范氏家世好學,有藏書7 000余卷。西晉太康年間,武帝司馬炎曾多次征召范平(218—284年)為官,皆辭謝不出,但他支持三子以儒學出仕,自己則居家以“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為務。范氏慷慨好客,據說“遠近來讀者恒有百余人”,由其孫子范蔚為辦衣食。后范蔚亦入仕,為關內侯,承繼了其祖藏書。
能與范平藏書媲美的,有稍后于范平的錢塘藏書家褚陶(244—300年)。他字季雅,少而聰慧,好學不倦。年十三時所作《鷗鳥》《水硙》二賦,見者奇之。晉滅吳國后,出任尚書郎。張華(232—300年)以之為人才,薦于陸機(261—303年)。褚陶平生酷愛藏書,數量多達8 000余卷,以古書自娛。其性清澹閑默,謂所親曰:“圣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陳頤道(字文述)于懷范子安、懷褚季雅先生之詩中云:“七錄香蕓新秘閣,百年黃葉舊江村。”“西京典籍同劉向,南國藏書匹范平。”
首開蘇州私家藏書風氣者,是南朝時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的陸家。據《南齊書》卷卅九列傳中記載:“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可見其祖、其父已有藏書,陸澄(425—494年)少小時就有博覽群書的家學環境,后以太學博士起家入仕,在朝歷任秘書監、領國子博士及度支尚書等職。其“家多墳籍,人所罕見”,多至萬余卷,時有“碩學”“書廚”之稱。他曾對以博聞多識自許的王儉(452—489年)夸耀說:“仆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覺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仆。”王儉不服,便約同學士何憲等一起會論,陸澄待王儉發表主旨言談方畢,就滔滔不絕地補充了其所未知的內容,眾人因此嘆服。陸溢去世之后,其所撰《地理書》《雜傳》等書200余卷,方為世人所知,然后皆亡佚。后其子少玄(生卒年不詳)繼承家藏之書,撰有《佛像雜銘》13卷,可惜在隋朝時就已亡佚。少玄好友張率(475—527年)能詩善文,盡讀其書,“遂通書籍”。
到唐代,蘇州又出現了一位萬卷藏書家,即大詩人陸龜蒙(?—約881年),字魯望,自號天隨子、江湖散人、甫里先生,生于長洲(今江蘇蘇州)一個官宦之家。陸龜蒙少聰悟,時舉進士不第,曾為湖州、蘇州刺史幕僚,后隱居松江甫里(今吳縣甪直),有地十萬畝,有屋三十楹,設有“著圖書所”,傳世有《唐甫里先生文集》。他生平好聚書,凡借他人之書,若篇帙壞舛,必為輯褫刊正。往往得一書,即誦讀至熟,然后抄錄副本。得另本則校之,故所藏之書皆精本。五代吳地文學家殷文圭(?—920年)在《題吳中陸龜蒙山齋》詩中有“萬卷圖書千戶貴,十洲煙草四時和”之句。
與陸龜蒙同時期的藏書世家徐修矩,字參卿,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家有湖田五萬畝,草堂十余間。據皮日休(約838—883年)《二游詩》序云:“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矩者,守世書萬卷,優游自適。余假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酣飫經史,或日晏忘飲食。”其詩中有句云:“昔之慕經史,有以傭筆札。何況遇斯文,借之不曾輟。”及 “念我曾苦心,相逢無間別。引之看秘室,任得窮披閱。軸間翠鈿剝,簽古紅牙折。帙解帶蕓香,卷開和桂屑”云云。陸龜蒙也有詩云:“倏來參卿處,遂得參卿憐。開懷展櫥簏,唯在性所便。”“因知遺孫謀,不在黃金錢。插架幾萬軸,森森若戈钅延 。風吹簽牌聲,滿室鏗鏘然。”[3]
上述范、褚、陸、徐諸家所藏的成千上萬卷書籍,都是十分難得的寫本紙卷。覓取原書,抄錄副本,加以校勘,裝幀成卷,護以縹帙,然后典藏于室,每一個環節都非常不易,因此,每一卷書在當時都無比珍貴。現代圖書館學家劉國鈞先生(1899—1980年)說:“把若干張紙粘連起來成一橫幅,用一根細木棒做中心,從左向右,圍繞著這木棒卷起來成為一束,這便是一卷。這根細木棒叫做‘軸’……你若看見了一軸這樣的書,一定以為它是一幅古畫,而不知一千多年以前我們所讀的書就正是這種形狀呢!”“隋唐時代是中國寫本書極盛時代,也是卷軸制度發達到高峰的時代。一切裝潢都非常考究。”[4]
隋、唐之后,“宋、元時期蘇州成為藏書家聚集地,明代蘇州私人藏書大發展,明末清初出現了以錢謙益為代表的具有輻射和影響力的虞山藏書流派,蘇州成為中國的私家藏書中心地”[2]3。至于清末民初,蘇州學人、藏書家潘圣一(1892—1972年)指出:“吳中文風,素稱極盛,俊士薈萃于茲,鴻儒碩彥,代不乏人。以故吳下舊家,每多經史子集四部書之儲藏,雖寒儉之家,亦往往有數百冊;至于富裕之室,更連櫝充棟,琳瑯滿目。故大江以南,藏書之富,首推吾吳。”[5]
至于杭州的藏書文化底蘊同樣精深厚實。顧志興先生指出,自北宋以來,杭州私家藏書的特色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士大夫藏書成為主流,藏書世家輩出”;二是“刻印抄校并重,增益藏書,提升藏書質量”;三是“藏書供學術研究,多學者型藏書家”;四是“重收藏宋元舊本、精本”;五是“關注地方文獻和其他專題典籍收藏”[6]。
明、清時期江南藏書家辛苦搜集、不斷積聚的古書舊籍,是近代書業市場的重要資源,更是現代公共圖書館藏書的重要來源。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紹興藏書家、鄉紳徐樹蘭(1837—1902年)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近代公共圖書館性質的“古越藏書樓”,此舉“推動了我國近代藏書樓向公共圖書館過渡”,被視為“我國學習西方圖書館技術和管理制度的開端”[7]。
1.2 “耕讀傳家”理念的形成、發展與嬗變
眾所周知,“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是我國古代流傳甚廣的一副對聯。《增廣賢文》中的“世間好事忠和孝,天下良圖讀與耕”“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等句,體現了往哲先賢的“耕讀傳家”觀。即使后來家居都市大邑,他們也會在院門上鐫刻“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舊聯,或將其改寫為“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耕讀傳家”在老百姓中可謂流傳甚廣,深入民心。耕田可以事稼穡,豐五谷,養家糊口,以立性命。讀書可以知詩書,達禮義,修身養性,以立高德。所以,“耕讀傳家”既學做人,又學謀生。這里所說的“讀”,當然是讀“圣賢書”,為的可不是做官,是學點“禮、義、廉、恥”的做人道理。因為在古人看來,做人第一,道德至上。在耕作之余,或念幾句《四書》,或讀幾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或聽老人講講歷史演義。人們就在這樣平平常常的生活中,潛移默化地接受著禮教的熏陶和圣哲先賢的教化。
“耕讀傳家”曾經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里南、北方小康農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種理想生活圖景”[8]。在江浙一帶,“耕讀傳家”的理念往往被寫入家訓族規之中,如象山黃埠潘氏家族家規中寫了“耕讀以務本業”;龍峰顧氏家族族譜云:“忠孝勤儉,耕讀傳家”;陳縊陳氏家族的祖訓中更明確要求:“訓子孫,課子弟當以耕讀為重。非耕無以厚生,非讀無以明理。”[9]
“耕讀傳家”在北方也被普遍接受。馮友蘭(1895—1990年),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人。他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回憶說:“我的父親行二,名臺異,字樹侯;伯父名云異,字鶴亭;叔父名漢異,字爽亭。父親后來成了清光緒戊戌(1898年)科進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們這一家就成為當地的書香之家,進入了‘耕讀傳家’的行列……母親深深知道這個功名的分量。她常對我們說,你父親聽某一個名人說過,不希望子孫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孫代代有一個秀才。”“一個人成了秀才,雖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進入士林,成為斯文中人,就是說成為知識分子了。以后他在社會中就有一種特殊的地位……一個人成了秀才,就成了‘儒’的繼承人。”[10]
這位“名人”,即在家書中諄諄告誡后人“愿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愿其為仕宦之家”的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1811—1872年)。他曾手書過一副由其父曾麟書(1790—1857年)撰文的廳堂聯:“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曾氏在寄往湖南湘鄉家中的書信里寫道:“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逸,繼而浪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愿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愿其為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為科第仕宦起見。”凡此足見閱世甚深的曾國藩,十分看重“耕讀傳家”的內涵,希望能保持其家族的可持續良性發展。
在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四,清廷明令自丙午科(1906年)始,一律停止所有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后,與科舉制度唇齒相依的“耕讀傳家”“讀書入仕”的傳統觀念似乎難以延續了。但在民間,人們很快就按新式學校的文憑在心中作比,既然縣城有小學,省城有高等學堂,都城有京師大學堂,那么,縣小畢業生不妨視同于科舉時代的“秀才”,省城高等學堂畢業生也就是“舉人”,而京師大學堂畢業生差不多也就與“進士”同地位了。
2 近代江南鄉村圖書館的發展
近代以來,由鄉村到城市乃至海外的商人、官紳、學者等,在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拓寬了眼界后,回到家鄉造福鄰里,培養后學,創建新式學校或圖書館,也就變得理所當然并更能為鄉民所接受了。
2.1 近現代圖書館學家的“鄉村圖書館”理念與愿景
20世紀20年代,杜威的平民教育思想在我國產生了極大影響,同時國民政府宣布進入“訓政時期”,期待通過“三民主義”思想加強地方、民眾與政府的聯系。到了30年代,社會教育和民眾教育的熱潮覆蓋更廣,教育界和圖書館界人士都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鄉村,圖書館界人士更是進一步認識到鄉村圖書館建設在提升鄉村教育水平、改善鄉村教育效果方面的重要作用[11]108-113。193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民眾教育館暫行規程》,民眾教育掀起了新一輪高潮:“鄉村民眾圖書館的建設,完全是在當時社會民眾教育、鄉村教育的氛圍中展開的。”[12]
1927年9月,李小緣(1897—1959年)在第四中山大學的講義《圖書館學》中指出:“鄉村圖書館必求保存一鄉之文獻,一鄉之教育。”[13]
1929年,在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上,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楊立誠(1888—1959年)在《設立鄉村圖書館以為鄉村社會之中心案》中提出建議,設立鄉村圖書館,以其作為鄉村生活的文化中心:“訓政期內,地方自治極為重要。然欲施行自治,非改造社會環境不可。圖書館為改良社會環境最適宜之機關,似不可不推行于鄉村,以期健全之發展。”[14]69-77
1931年,李鐘履(1906—1983年)著有《鄉村圖書館經營法之研究》一書,這是我國最早探討鄉村圖書館組織和運營的專著,書中構建了“以縣級圖書館為中心的總支館模型”[11]108-113。
1934年,王人駒發表《怎樣辦理鄉村圖書館》一文,認為可將整個鄉區分成幾片,在每一片都設一流通處,以使讀者能在1小時內到達。同時,各片之間的書籍也應時時輪轉流通[14]69-77。
1935年,趙建勛通過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鄉村巡回文庫經營法》,總結了河北定縣鄉村民眾教育館舉辦鄉村巡回文庫的經驗,認為巡回文庫是一種既經濟又便于與農民生活產生聯系的方法[12]108-113。
1936年,劉國鈞在面對前來金陵大學進修的農專學生進行演講時,表示可通過巡回圖書館、郵寄圖書館、代借處等形式,在農閑期間開展圖書館服務[15]。
近現代圖書館學家們對“鄉村圖書館”的理念與愿景,體現出我國圖書館界對于鄉村圖書館的重視以及鄉村圖書館在普及知識、推廣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如1916年2月6日在江寧韜園開放的“通俗圖書館”,據《新京備乘》記載,“館長以教育科一員兼充……圖書一部,自通俗書籍外,更取龍蟠里舊館通行本中之重出者,移而列之,為設特別閱覽室”,開放僅九個月,就吸引了10萬余人前往參觀和閱覽,后易名為“通俗教育館”[16]129。
2.2 近現代江南地區“鄉村圖書館”舉隅
由我國近代著名實業家榮宗敬(1873—1938年)、榮德生(1875—1952年)兄弟創辦的大公圖書館,位于江蘇省無錫市西郊的榮巷。少年時的經歷使他們了解到農民子弟求學的艱辛,因此二人在經營面粉企業取得初步成果后便相繼建立了8所小學,并在此基礎上萌生了創辦圖書館的念頭。榮德生在專家的指導下逐步訪求圖書,并選定地址進行建設,1916年10月10日大公圖書館正式開幕。開館后,榮德生重視本地文獻的搜集、圖書版本的精良,并用現代化的手段來運營圖書館,編制有《大公圖書館館藏目錄》《敘文匯編》等,還出版了《中國財政史輯要》《人道須知》等書[17]。
與大公圖書館同時期的“天上市村前圖書館”,于1916年10月15日正式開館,系由當地名士、教育家胡壹修(1865—1931年)、胡雨人(1867—1928年)兄弟創辦(天上曾為無錫惠山區的一個市鎮)。該館除開設普通閱覽室外,也開展巡回文庫的服務。胡氏兄弟意識到單純的學校教育并不能滿足提高民眾整體受教育水平的需求,應輔以社會教育,因此在創辦“胡氏公學”之后,二人創辦了“天上市村前圖書館”,胡雨人更是為圖書館的建設捐贈了自己的全部藏書。該館開辦之后,具有“民享”“民智”“民助”三大特點,旨在澤被鄉里、嘉惠桑梓[18]112-116。
李小緣在《圖書館學》一書中寫道:“近來國內公共圖書館事業,雖迭遭兵燹,然已漸見蓬勃之象”,除列舉了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及蘇州、九江等省、市立圖書館外,他還關注到新近開放的宜興圖書館、青浦圖書館及金山張堰圖書館。1928年5月28日,江蘇省教育行政部門明確通令全省,“每縣至少應設民眾圖書館1所”[19]35-38。在浙江,杭縣既有設在縣城苑寺巷的縣立流通圖書館,又有塘棲、七賢橋、丁橋、臨平等6所鄉村圖書館[16]143。
據統計,20世紀20年代初至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一些地方曾創辦有鄉鎮、鄉村圖書館。如1922年2月,教育部批準立案了浙江省嘉興縣新塍鎮公立通俗圖書館簡章;次年5月又批準立案了江西興國縣鄉立圖書館章程。1923年蔣顯增兄弟創辦了湖南“豐樂圖書館”。1924年,幾名自緬甸回到云南騰沖縣的青年,共同創辦了 “和順閱書報社”(后改名為“和順圖書館”)。同年7月,在東南大學舉行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3屆年會,議決通過了有關專家人士提出的“各省宜酌設農村圖書館案”[19]35-38。1931年,劉文伯(1893—1961年)創辦了陜西“私立敬業圖書館”等[20]54-56。
在此前后,江南地區創設的一些鄉村圖書館,在地方文獻的搜集和提升民眾知識水平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但1937年7月發生的日本侵華戰爭,致使中國城鄉圖書館事業蒙受重創,如上述的“天上市村前圖書館”就在當年11月為日寇摧毀[18]112-116。日寇侵占無錫后,大公圖書館的珍貴藏書被洗劫一空。在東北,日寇的“清村”政策也常常伴隨著對鄉村圖書館的毀壞,對“有關政治、中國文化、外交、抗戰與革命主題的文獻”的禁毀以及對文物的掠奪[17]。
3 鄉村圖書館傳承發揚江南文化的可能路徑
進入本世紀以后,鄉村圖書館建設作為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礎元素之一,開始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出臺了如“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2006),“盡快形成完備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2008),“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2011),“基本建成覆蓋城鄉、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2015),“完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2017)和“實現鄉村兩級公共文化服務全覆蓋”(2018)等一系列政策措施[21]。2018年1月2日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繁榮興盛農村文化,煥發鄉風文明新氣象”,強調了“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健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性[22]。2021年8月2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再次明確了要“努力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目的是“加快構建覆蓋城鄉、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努力讓人民享有更加充實、更為豐富、更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生活”[23]。
就客觀事實而言,當今城鄉差距的鴻溝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內地各級各類城市仍有眾多勞作機會吸引著農村人口,但越來越高的租、購房價,以及工作、生活壓力使得其中一部分人決定回返自己的家鄉,尋找新的經營方向;二是在城市中長久受到新高科技、時尚生活和城市文化影響的極少數群體,在收入有余、時間有閑、身體有力的前提下,回應來自內心深處“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晉陶淵明《歸園田居》)田園生活的呼喚,或農宿休假,或山村養老,甚至租借上一塊田地嘗試耕種和勞作。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認為鄉村圖書館推進鄉村文化振興存在三條可行的路徑。
第一,繼承、發展和弘揚江南鄉村歷史上存在的書籍藏傳、經典閱讀的傳統。私家藏書、累世遞藏、閱讀經典為中華民族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1927年10月23日,位于江蘇宜興縣和橋鎮的和橋圖書館揭幕開放。和橋是位于宜興北部的一座大鎮,近代以來人才輩出。據《和橋鎮志》編寫辦公室的統計,籍貫是和橋的海內外各領域的當代專家、學者、教授有600多人,其中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有4名。在和橋高級中學校史上,有“一校七院士、一門十教授”等人才佳話。筆者認為,鄉村圖書館應向讀者不斷傳遞讀書成才的理念,在做好自身資源建設的同時,也鼓勵讀者在家中設置書房,推出適合家庭閱讀和收藏的經典書目,并可尋找一些本村、本鄉的先進典型,發揮其表率作用,將“詩書繼世長”的理念重新傳輸到鄉民的思想中。
第二,下沉現代公共圖書館服務進鄉村、到農家,進一步明確以兒童閱讀接受為重點的導向。由于我國鄉村大多青壯年前往大城市謀生、求職,留守鄉村的多為老人和兒童,存在鄉村教育系統相對薄弱,鄉村圖書館文獻資源供給錯位的問題。因此,應特別重視鄉村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與學校教育補償功能,確立以兒童閱讀接受為重點的導向,傾聽需求,培養農村兒童的閱讀興趣與習慣,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與方法,重建鄉村文化認同感,彌合城鄉之間的教育水平差距[24]。有關部門還要鼓勵和吸納不同主體積極參與鄉村圖書館的建設和發展,如鼓勵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員、公益組織、村莊外溢的精英群體創辦和運營鄉村圖書館,適當打破有形的建筑局限,將鄉村圖書館融入鄉村生活的公共空間中[20]54-56。如創建于1928年的云南和順圖書館,就是在海外華人、華僑的大力幫助下建成的。該館以反帝反封建、救亡圖存、革新社會、傳播新文化知識為宗旨,依托當年全縣唯一的無線電收音機,創辦了油印的《和順圖書館無線電三日刊》(后改為《每日要訊》),無償分贈給縣城、本鄉和鄰近鄉村的各機關、學校、商店,并逐漸惠及鄰縣。它一方面成為了當地的局勢信息發布中心,另一方面也激起了當地民眾的抗日勇氣[25]。
在當代,立人鄉村圖書館以“讓鄉村青少年成長為健康、正常的現代公民”為使命,以人為核心,確立“以圖書為載體,以教育為內容,立足鄉村,連接城市,推廣國民閱讀,促進鄉村教育革新”的理念,將培育農村兒童的公民素質作為目標,成為區域性的文化教育中心[26]。中國圖書館學會原秘書長劉德元先生也曾自籌資金,在河北省保定市易縣固村莊村祖宅上開辦了“愛鄉圖書室”;浙江省衢州市云溪鄉云溪村的李丁富先生退休后,在家鄉辦起了“百姓書院”[20]57。
第三,在“促進全民閱讀,建設書香社會”的時代背景下,以活化江南文化資源為主導,重視對老村落改造中傳統書香底蘊(私塾、學校遺址、祠堂、藏書處、“敬惜字紙”爐等)的保護與復原,挖掘地方志中的文化線索,編寫新時期的地方志,最大程度發揮鄉村建設中書香文化設施的作用。鄉村中有許多承載著情感與記憶的歷史文化遺存、民俗活動與文化場景,雖然并不符合國家或地區政府所規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標準,但鄉村圖書館可以通過保藏并開發這些資源,使歷史記憶在新時代煥發新的面貌[27]。
從2003年起,江蘇省新聞出版局、省文物局、省全民閱讀辦在省域范圍內,聯合開展了以“閱讀遺存”為主題的專項調查,匯集了省內各地閱讀遺存12大類,共計636處。相關部門先是將資源匯編成《江蘇閱讀遺存名錄》,然后又在1949年之前的閱讀遺存中選擇了106處,編輯成《江蘇閱讀遺存》,內容涉及歷代讀書臺、讀書處、藏書樓、藏經閣、書局、書店、圖書館、文廟與府學、書院、學校及義學等,旨在引導人們加強對歷代書院、藏書樓、名人讀書處等閱讀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傳承江蘇書香文脈,使之與時俱進。如榜上有名的常熟古里圖書館,依托瞿氏鐵琴銅劍樓的文化記憶與資源,建在鐵琴銅劍樓的后院,收藏有“中華再造古籍善本”695種,以及多種適合當地人口文化、教育需求的新版圖書,這既可以向民眾宣揚瞿氏在藏書、刻書、抄書、護書、捐書等方面所做的貢獻,也展現了面向鄉村開展公共文化服務的特色,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