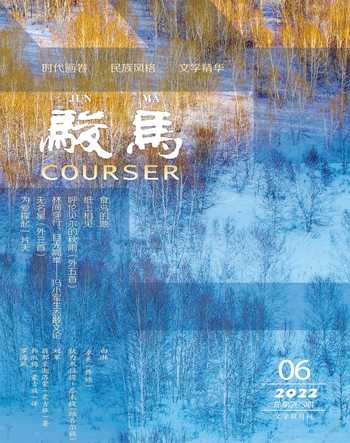痛
陳聯
1
“咕咕、咕咕”,肚子不停地催促李明俊,他急不可待地跨上摩托車,打著火就跑。
鏡片上如針尖般的雨水,像遠山薄薄的霧,他抬起左手抹一下,頓時一片光明。漫散、細瘦的雨即使長時間也難聚集成行,剛從單位了出來時沒有察覺,騎了幾公里后,頭盔的鏡片上才顯出蒙蒙的水。
李明俊跟在白色小車后面有一分鐘了,小車前方是一輛電動三輪車,不遠處是個小彎道,彎道前停著幾輛大貨車。小車磨磨蹭蹭的,他急了,等對面幾輛電動車駛過后,摁兩聲喇叭,給了點油門。與白色小車平行時,發現電動三輪車前面還有一輛小車。慢得像蝸牛,會開嗎?他抹了一下鏡片,又踩了踩油門。
剛修好不久的水泥路,被大貨車碾軋得坑洼不平,表面一層泥土與小雨充分地融合后,油光發亮。經驗告訴他這種路面滑,因此,不敢多給油門。濕滑的路面速度不能快,超三輛車有點難。
李明俊是平山礦業公司南山車間的一名大車司機,雖然特種車輛不準在馬路上行駛,但大車司機必須持有駕駛證才能上崗。他有二十多年駕齡了,平時偶爾借親朋的車出門,最多的還是騎摩托車。摩托車要速度有速度,又機動靈活。
摩托車與白色小車并行了兩三秒,他感覺不易超車,就想減速。念頭一閃時,前方拐彎處突然出現一輛飛馳的黑色桑塔納,他急忙右手松油門,左手捏剎車。踏板摩托車必需先后制動,再前制動,否則會摔倒。剛換摩托車那會兒,剎車性能還沒完全掌握,路遇險情,慌亂之中,他錯捏了前剎,結果摩托車像喝醉了酒,在馬路上扭了幾扭。驚出一身冷汗的他,暗自慶幸好在時速較慢,對面也沒有車輛,否則后果不堪設想。有了幾次教訓后,他習慣將左手的四根手指搭在剎車手柄上,這樣遇到突發狀況就可以及時減速或停車。
桑塔納沒有減速,像一匹脫韁的馬,一往無前。李明俊慌了,趕緊捏前剎,摩托車還是停不下來。
他感覺像一朵云在飄,慢悠悠,慢悠悠地飄,不知道飄了多久,最后落在草甸上。
李明俊清醒后,發覺自己是躺著的,桑塔納則像個龐然大物在十米開外瞪著他。躺在路邊成何體統。他想坐起來,身上到處痛,使不上勁。喘息兩口,動一下右胳膊,感覺右臂和胸部鉆心的痛。動一下左臂,除了胸部較痛,左臂是輕微的痛。他試著右手觸地,剎時,整個右臂和右胸疼痛難忍。這種痛,讓他覺得比死還難受,雖然沒死過,但這種痛是無法形容的,是前所未有的。莫不是右臂斷了?
騎電動車的,以及來往車輛里的人都勾著頭往這邊瞅。必須坐起來。
這時,一個下班的同事路過,停下電動車,關切地問:“怎么了?”說罷,伸手欲扶他。
他痛苦地搖一下頭,說:“不、不……”他奇怪自己聲音那么低那么慢,儼然與平時判若兩人。必須坐起來。他咬著牙,換左手撐地,一用力,坐起來了。瞬間,那種劇烈的痛又迫使他躺倒。
桑塔納的司機磨蹭半天才下車,猶猶豫豫走過來,紅著臉說:“你,你怎么騎到這邊來了。”此人五十多歲,黧黑色皮膚,身材魁梧。
李明俊沒說話,疼痛似千軍萬馬在身體里奔騰。他給自己打氣,起來,起來!左手撐地,一咬牙,一用力,又坐了起來。
下班的同事問桑塔納司機:“你是陶村的吧?我見過你。”
桑塔納司機說:“是的。但這事不怪我。”
李明俊看看腿,沒有流血,看看胳臂也沒出血。抬右胳膊,鉆心的痛,抬不起來。他把左手在褲子上擦了擦,解開頭盔,摸一下頭和臉,也沒血。沒出血就好。他有點慶幸。
他超車,全責,慶幸傷得不嚴重。
有三個騎電動車上班的同事停下來,其中有兩個人問桑塔納司機:“你們怎么撞上的?報警沒?”
“不報警,不報警。”桑塔納司機反復說。
必須站起來,坐在泥巴地里太丟人了。他用左手撐了幾次沒站起來,下班的同事又要扶他,他搖著頭拒絕。他用左臂卯足了力,終于顫巍巍地站起來了。能站起來證明雙腿也無大礙,只是左腿有點痛。
這時,一輛哈弗越野車停下來,是上小夜班的班長。他環顧四周,問要不要幫忙。
他感激地說:“不用。”看著小夜班的班長陰郁的臉,本來想多說幾句感謝的話,疼痛卻讓他說了兩個字,聲音微弱得只有自己能聽見。
他從包里掏出手機,準備告訴老婆他撞車了。
桑塔納司機走近兩步說:“不要報警,不要報警,我們去醫院。”
“對對對,趕緊去醫院。”幾個同事都贊同。
能站起來,也沒流血,只是身上痛,傷情應該不重,去醫院不浪費錢?不過,去醫院檢查一下也好,身體內部的問題只有醫院能檢查出來。看樣子明天不能上班了,或許好幾天都不能上班了。
李明俊在猶豫,沒說去,也沒說不去。一說話,身體就疼痛難忍。疼痛像春天的草,在他身體里繁衍生息。他回頭看一眼摩托車,心抽了一下。摩托車像一頭死豬,倒在滿是泥巴的路基上。
桑塔納司機說:“我有保險……不要報警,我帶你去醫院。”
不報警?他疑惑了。錯的一方是自己,他應該先報警啊,何況還有保險呢。
那三個騎電動車上班的同事說:“趕緊去醫院,耽誤了不好。”
“對對,不能耽誤,我帶你去醫院。”
李明俊看一眼下班的同事和小夜班的班長,兩個人也跟著點頭。小夜班的班長在來來回回地拍照,估計是準備發給段長的。
“他說,好吧,我打電話讓老婆來。”
“你倆去就行了,等你老婆來了又得耽誤一會兒。”一個騎電動車上班的同事說。
“嗯嗯,不能耽誤了。”桑塔納司機看他舉起手機,又朝他走近兩步。
桑塔納司機說話的時候,噴出濃厚的酒味。剎那間,他明白了。他說:“你們要給我證明,他喝酒了,是酒駕。”
2
細雨無聲無息地停了,天也無聲無息地黑了。
出租車上李明俊老婆責問桑塔納司機:“你不知道喝酒不能開車?你看你把人撞的!”
桑塔納司機說:“這也不能怪我,如果我不喝酒,都是你家他的責任。”
“你這是知法犯法,我要是報警,倒霉的肯定是你!”
“嘿嘿,朋友勸的,沒辦法,就喝了半杯。”
“酒味熏死人,就喝了半杯?你講給鬼聽鬼都不相信。”
“你們別報警,我負責醫療等一切費用,他們都認識我,我跑不掉的。”
李明俊坐在副駕駛,一言不發。疼痛讓他不想說話。剛才上車時,低頭、彎腰、下蹲,他都撕心裂肺的疼,是桑塔納司機扶著他,慢慢挪進來的。坐下后,背部一接觸到椅背,整個上半身都疼得厲害。只能微微前傾身體,不敢動彈,遇到顛簸,劇痛就輕而易舉將他吞噬。說話,痛。甚至,發動機的聲音也攛掇著痛。他覺得身體是別人的,痛才是自己的。
下車同樣困難,稍有動作,疼痛就從胸部向四周迅速擴散,是桑塔納司機小心翼翼把他挪出車的。他齜牙咧嘴,沒想到走路也一瘸一拐了。他努力克制著,終于挪進了急診室。
桑塔納司機搶著交費,為了減輕他走動的痛苦,還租了個輪椅。他小心謹慎地推著李明俊做X光和核磁共振,抱他上上下下。
這期間,桑塔納司機反復說:“我會對你負責到底的,你們別報警。”
只有他老婆偶爾搭理兩句:“萬一嚴重呢,不報警你能負得起責?”
“看他樣子不會嚴重的,能說話能走路,應該不嚴重。”
李明俊心里想,但愿不嚴重。
做完檢查,明亮的燈光已灑滿醫院的角角落落。
段長和班長來了。倆人說一接到小夜班班長的電話,沒顧上吃飯就趕來了,接著問報警了沒。他老婆說,看他人蠻好的,不報警了。兩個人咂著嘴,對望一眼。
他靠在輪椅上,想起身,但疼痛阻止了他的行動,只能感激地看著兩個人。
段長說:“你要想清楚,不報警就不能算工傷。”
他想,自己也有責任,如果報警,對方駕駛證肯定吊銷,甚至坐牢。與其這樣,不如不報警,看他積極負責的態度,應該是個值得信任的人。得饒人處且饒人吧。
班長走到他跟前,低聲說:“我們戴著口罩,還能聞到酒味,證明他喝了很多,你要考慮清楚,工傷對你以后有好處的。”
他略頓一下,愧疚地說:“算了,我答應他不報警了。”
“你考慮清楚,我們不好說什么的,你自己掂量掂量。”
“嗯,知道,還是不報警了。”
班長轉身走向段長。
桑塔納司機邊接電話邊往外走,片刻,他身后緊跟個與他年齡相仿的女人。
這個女人無意間看見李明俊老婆,走過來說:“你在平山礦文化宮練瑜伽吧?我見過你。”
李明俊老婆扭過臉,看了一眼說:“你也在那練瑜伽?”
“是啊,我身材不行,去的少。”
李明俊瞥見這女人果然五短三粗,一張肥胖的臉。
都在等片子出來,讓醫生看結果。
李明俊跟老婆商量:“既然不報警,就該談錢了,你看要八萬怎么樣?”
“八萬太多了吧?”
“六萬呢?”
“六萬也多了。”
“那就四萬吧,看樣子我要歇一段時間了,這四萬塊全當工資和營養費了。你把他喊過來。”
桑塔納司機搓著手走過來。李明俊對他說:“我們不報警,但你要答應我們的條件。”
“嗯嗯,好。”桑塔納司機彎腰,點頭。
“我幾個月不能上班,你給四萬塊,算是我的工資、護理費和摩托車修理費。”他聲音低得像從輪椅底下發出來的,說話稍大聲都能喚醒更深的痛。
“四萬……四萬多了。”桑塔納司機還是彎著腰。
“四萬一點都不多。”他不想說話了。這年頭四萬塊能干什么?這四萬塊能免你牢獄之災,能保證你駕駛證不被吊銷。
他老婆說:“那就兩萬吧。”
“好,兩萬。”桑塔納司機直起了腰。
他瞥老婆一眼,像看一個陌生人。
他老婆繼續說:“我們不訛人,我們是講良心的,你現在就拿兩萬塊來。”
聽到良心兩個字,他輕輕嘆一口氣,說:“兩萬不包括我后期治療和修摩托車的費用。”
桑塔納司機搓著手說:“我現在沒有這么多錢。”
“沒錢?”
“我微信里的幾千塊錢,剛才用得差不多了。”
怎么辦?老婆是指望不上,關鍵的時候不幫親人說話,卻同情外人。段長和班長背對著這邊,遠遠地,好像在告訴他,該交待的都交待了,剩下的就由你自己處理吧。
沉默是最好的拒絕。
燈紅酒綠的時分,急診室依然繁忙。為了不妨礙進出,李明俊的輪椅停在取片機對面的墻邊。因為痛,他始終保持一種姿勢——耷拉著頭,左手握著右腕。
桑塔納司機低頭耷腦站在李明俊面前,像個做錯事的小學生。
長時間的沉默令李明俊很難受。老婆低聲說:“要不讓他打欠條?”
“好吧。”他不假思索就脫口而出,說完,覷一眼像鐵塔似的桑塔納司機。但愿他沒聽見。可他聽見了,通過他期待的眼神,他知道他聽見了。
他無可奈何地說:“你打欠條給我吧。”他想,好人做到底吧,他跑前跑后也挺辛苦,一直小心翼翼地呵護,就不逼他了。兩萬塊錢不多,相信他不會賴賬的。
“我、我不識字,你寫好我簽名吧。”桑塔納司機又彎下腰。
李明俊覷他一眼。這年頭還有不識字的?但沒多想,他簽字是一樣的。
他接過老婆遞過來粘有泥巴的包,強忍著疼痛從包里掏出筆和記事本。記事本是以備萬一的,筆是上班簽到和寫交接班記錄的。
他問:“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陶振兵。振,振興的振,當兵的兵。”
“我陶振兵今欠李明俊誤工費、護理費等人民幣兩萬元整。李明俊的后期治療和摩托車修理費,均由我支付。兩萬元在十月底給李明俊。(因我是酒駕,所以選擇私了。)”
他哆哆嗦嗦地寫完,遞過去,陶振兵看都沒看,就在欠款人后面簽了名字。段長和班長站在自動取片機旁,邊等片子邊聊著什么。
等了幾十分鐘,片子出來了。診斷意見是:右側肩胛骨外側緣骨骨折可能,右胸部分肋骨皮質皮線自然,必要時進一步檢查。
醫生說后天做三維CT,住不住院都行,骨折就是要靜養。
陶振兵說:“我看還是在家靜養好,方便。”
李明俊和老婆認為有理,在醫院吃喝拉撒睡都不方便,還要有個人專門伺候。
病房里的呻吟和消毒水的味道,瞬間在李明俊腦海里涌動。
3
夜走到了深處,馬路顯得寬敞了,車燈如游動的大魚,車外風聲如水。
回家的途中,李明俊打電話叫修理部把摩托車拉走了。
躺不下去。稍有動作就疼痛難忍,只能讓老婆摟著,慢慢移到壘起的兩床棉被上,半靠半躺,不能側身,始終保持一種姿勢。疼痛像藤蔓纏著他,驅走了困意。幾個小時前發生的事,電影般在腦海里慢慢回放,虛汗在他的背部冒出來。他慶幸當時車速不快,如果再快一點,現在不是躺在家里,而是躺在醫院的某張病床上了。以后騎車一定千注意萬謹慎了,一次馬虎大意都能導致災難發生。
疼痛無時無刻不在,乃至于,坐和躺都困難重重——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會加劇疼痛。坐要如鐘,躺要如山,才能減輕疼痛。長時間的固定姿勢,蓄謀成酸脹痛,從腰間源源不斷地挑戰他。躺的時候想坐起來,坐的時候想躺下,但是疼痛讓他不能自主。要側身時,喊老婆的聲音,微弱得只有自己能聽見,必須等她進來查看,才能助他坐起或躺下。后來,老婆找來一個小孩子的玩具,輕輕一捏能發出“唧唧”怪叫,并閃七彩燈的皮球,讓他需要時,往地板上丟。
秋天還執著在高溫里,李明俊能聞到從肩背夾里散發出的汗酸味。有些事老婆只能幫助,不能代辦,比如:穿衣脫衣、上衛生間、洗漱、吃喝。有些事他要用左手完成,右胳膊失去了應有的功能。疼痛如影隨形。
早上九點多,他咳嗽了。往日咳嗽很正常,因為他是煙民,這次咳嗽卻令他疼痛難當。咳嗽制止不了,唯有捂著胸小心翼翼地咳,即便如此,疼痛還是一波一波地從胸部向四周蔓延。
疼痛像春天的草,生機勃勃地從胸部鉆出來,以雷霆萬鈞之勢,迫使他停止一切動作。咳嗽持續了十幾分鐘,仿佛從鬼門關走了一遭。必須戒煙了。以前戒煙是個難事,現在趁這個機會正好下定決心。
現在他才知道什么是痛,曾經的磕磕碰碰,小傷小口根本算不了什么,與現在比起來,那叫撓癢癢。他想,當年的英烈們所受的疼痛也不過如此,既然他們能經受得住,他李明俊也能經受得住。何況他們當中還有許多女性革命者呢。
翌日一早,陶振兵拎兩箱牛奶和水果來接李明俊去醫院。在車上,陶振兵說:“等你傷好了,去我那里釣魚,我自己養的。”
他嘴里“呵呵”著,沒說去,也沒說不去。不知道陶振兵從哪里知道他喜歡釣魚的。
陶振兵繼續說:“咱倆都倒霉。咱們是不打不相識啊,以后咱們就是朋友了。”
他說:“你是錢倒霉,我是身體倒霉。”通過這兩句話,他已經把他當朋友了。
三維CT排在兩天后的上午做,今天是預約。
回來的路上,桑塔納的水箱開鍋了,陶振兵說是他摩托車撞的。
摩托車能把小汽車撞壞,小汽車是紙糊的?他懷疑。
他和老婆只得打車回家。他們住礦山所在的小鎮上,離市人民醫院僅十幾公里。
兩天后,陶振兵打車來接李明俊去醫院。他說車子沒修好,還在修理廠。
三維CT的結果是:右側第3~7肋骨折(部分不全骨折);左側7、8、9肋前緣皮質線欠連續,考慮不全骨折。醫生建議,一個星期后來復查。
傷得這么重,難怪那么痛。
李明俊每天的任務是吃、喝、睡,除了身體疼痛之外,日子過得比退了休的還舒適。
時間在疼痛中慢慢逝去,疼痛也在時間里慢慢減輕。又過去一個禮拜,李明俊的右手能抓手機了,但還不能刷牙洗臉,更不能背到身后,只能輕輕地適度地抬。
去醫院復查時,在接近醫院的地方,桑塔納水箱又開鍋了。陶振兵說:“我去修理廠,你們自己拍片子吧,到時候我微信轉賬給你。”
李明俊恢復得越來越好,醫生告訴他,一個月后再來復查。
還未到家,陶振兵就把拍片子的200元轉到了他微信里。
4
樹葉一天比一天黃了,風也一天比一天涼了。
李明俊每天都心安理得地享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自出事后,床和電視成了不可離缺的一部分。現在能往左側翻身了,腰部酸痛得到了有效的緩解。疼痛正一點一點地遠離。
還是不能咳嗽,每一次咳嗽都地動山搖。他努力克制自己少抽煙,每天只抽三根,但是,常年的老痰已經在他肺里積淀成了火山,每天都要爆發兩次。他嘗試一根都不抽,卻屢屢被煙癮占了上風。
現在,不用老婆輔助,他勉強能坐下、蹲下、躺下,右胳膊也漸漸恢復了一點。每天無數次坐下,使他學會了“馬步”式站起和坐下——兩腿略分開,把需要腰部使的力全用在腿上,保持上半身不動,這樣就能減少一分疼痛。
這天下午,李明俊正在午睡,手機突然響了。摩托車修理部老板說:“配件到了,配件和人工費共3500元,你來付錢。”
他一愣:“不是說好是陶振兵付錢嗎?”
“我打他手機,他不接,只能找你啊。”
他心里一涼,說:“不會吧,我聯系他。”
他睡意全消,在手機聯系人里找到陶振兵的名字,點開。“嘟……”響了一會兒,手機提示暫時無人接聽。再打,還是無人接聽。再打……估計他在忙,手機不在身邊,也許等他空閑時看到未接電話,會打過來。
他打電話給修理部老板說:“我的摩托車一直在你那兒修,你放心,摩托車是我的,他不認我認。這兩天手頭緊,過幾天給你送去。”
修理部老板猶豫半天答應了。
他靠在床上發愣。
傍晚五六點鐘,李明俊又打陶振兵手機。這個點,是上下班的時候,手機都會帶在身上。無人接聽。他用老婆的手機打,依然無人接聽。他的心涼了半截。
夜牽著黃昏的手來了。李明俊和老婆的睡意全無,蟄伏的擔憂在倆人心中逐漸膨脹。
清晨,一絲微亮滲進窗簾,在眾鳥鳴唱中醒來的李明俊第一個反應是看手機,希望有陶振兵的微信留言,或者未接電話,結果讓他大失所望。他不假思索地撥通他的電話,“嘟、嘟、嘟……”一直持續到自動掛斷。中午還是無人接聽,晚上還是無人接聽。一個人忙得再焦頭爛額,總有空看手機吧,即使當時聽不到,等空閑時也能看到吧,難道是有意的?不敢細想。
第二天還是同樣的結果。他的心徹底涼了。
后天是復查期,必須要找到他。出事的第二天,他就打聽了陶振兵的住處,知道他在一個小選礦廠上班。
一大早,李明俊和老婆打車來到拆遷中的陶村。兩臺挖掘機的長臂前,塵煙彌漫,一幢二層小樓瞬間面目全非。
一扇緊閉的紅色大鐵門對著村路,安然無恙的院內是三間正房和兩間偏房。陶振兵說過,拆遷款少,他不愿意拆。隨著捶鐵門的“砰砰”聲,里面回應的是洪亮的“汪汪”聲,李明俊知道這是狼狗的聲音。接連捶了幾次,回應的只有狗吠聲。
老婆憤憤地說:“你托我趴在墻頭上看看他的車在不在。”
老婆雙手抓住墻沿,他用左臂摟住她的腿。咆哮的狗吠聲像一枚枚手榴彈,接二連三地從院內扔出來。
他嘆口氣說:“我們去小選廠吧,或許他在上班呢。”
昨夜零星小雨,已把白天留下的溫度驅趕漸盡。一股來自身體內部的冷突然襲擊了李明俊,他顫了一下,打了個噴嚏。
夫妻倆在小選廠轉了半天,才在拐角的房間里見到一個人。
老婆站在門口問:“請問師傅,陶振兵來上班了嗎?”
“誰?”聲音像毛糙的礦石。
“陶振兵。”
“沒這個人。”
老婆說:“他說他在這兒上班的。”
那人說:“我在這兒干十幾年了,沒聽說過這個人。”
“這……”他對老婆說:“走吧,回去再想辦法吧。”
垂頭喪氣的兩個人,還沒擰開家門,就被三個警察堵在門口。
一個微胖的警察說:“你是李明俊吧?我們需要你配合調查一起案件,請跟我們走!”
“我、我是李明俊,你們搞錯了吧?”他的腿在抖,長這么大,還是第一次被警察找上門。隨著身體的顫抖,他的胸部和右肩疼得他撇了一下嘴。
“你是李明俊就沒有錯,請跟我們去隊里配合調查!”
“我家他被人撞斷了八根肋骨都找不著人,不知道犯了哪門子法!”李明俊老婆像一只母老虎擋在前面。
三個警察對視一眼,還是微胖的警察說:“有個交通案的當事人說你碰瓷,既然你們說有傷,就把證據拿出來。”
“我碰瓷?笑話!咳咳咳……”李明俊一邊咳一邊用左手捂著胸。
三個警察又對視一眼,點著頭。
李明俊停止了咳嗽,說:“來家里吧。”他看見幾個鄰居手里拎著菜,走過來。他家是一樓。
李明俊講述了那天的經過,老婆遞煙泡茶,隨后,拿出所有診單和膠片。
三個警察傳在手上翻了翻,還是那個微胖的警察說:“陶振兵說你碰瓷,看你真的有傷,就不讓你跟我們去了,不過,我們需要證據。”隨即,掏出手機,把診單全拍下來。李明俊又讓老婆把欠條拿出來。警察問還有別的證據嗎?“照片行不行?”得到肯定后,他連忙打電話給同事,讓把事故現場的照片傳過來。
煙和茶在茶幾上沒動。微胖的警察在查看剛加微信好友的李明俊傳來的照片,一個警察說:“昨天陶振兵在另一起事故中供述了你,我們本著對群眾負責的態度找到你,你能積極配合,對你有幫助。”
“他又出事故了?”李明俊來回在三個人身上瞅,希望能得到肯定。三個人都不搭理他。
他繼續說:“我現在報警行嗎?”
“已過了報警期限,不受理了。”
“那他說我碰瓷,你們怎么就受理了呢?”
“他的是案中案,不同。”
“這、這……”
“我們把片子帶回去,找專家鑒定,你隨時等我們通知。”
“那他欠我的錢怎么辦?”
“你可以去派出所或法院,我們只處理交通事故。”
三個人站起來,面無表情地往外走,老婆隨后相送,李明俊卻站著不動,也不說話。回身后,老婆對怔在原地的李明俊,埋怨他不懂人情世故,“好歹他們是執法人員,一句話能頂我們十句,一百句。”
李明俊說:“他們讓找法院,我就找法院,還是得相信法律!”
責任編輯?烏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