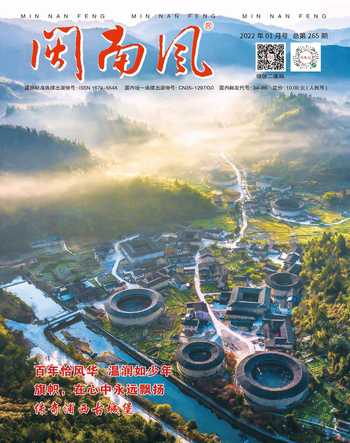杜甫與嚴武
沈淦
杜甫與嚴武不但是好朋友,而且是“世舊”之交——杜甫的祖父杜審言與嚴武的父親嚴挺之都是唐代名臣,他們想必也有過交往,或許也是好朋友呢。
杜、嚴二人還有個共同的朋友,叫房琯,一度官居宰相,與杜甫曾是“布衣交”,而嚴武的官職也有賴于房琯的推薦。可是,“安史之亂”爆發后,房琯率唐軍反擊叛軍,陳陶澤(今陜西咸陽市東)一戰,竟慘敗而歸,四萬唐軍幾乎全軍覆沒。杜甫的七律《悲陳陶》與五律《對雪》,記載的就是這場戰斗。在這種情況下,房琯罷相已是順理成章、早晚間的事了,可是官居右拾遺的杜甫卻偏偏要上疏替他辯護,說什么房琯“罪細,不宜免大臣”。唐肅宗李亨大怒,準備嚴厲地懲治杜甫。幸虧有人勸阻說:“杜甫如若因言獲罪,只怕要斷絕了言路。”肅宗皇帝這才不再追究。可是杜甫在向皇帝“謝罪”時,仍然喋喋不休地訴說房琯品德如何高尚,對皇帝如何忠心,希望“陛下棄細錄大”,繼續重用房琯。肅宗沒有再理睬他,只是將杜甫貶為華州司戶參軍,房琯則被貶為邠州刺史。
兵荒馬亂的年月,當一個窮官也不容易。由于關內大旱,華州一帶“谷食踴貴”,杜甫雖然親自“負薪采梠”,兒女仍然餓死了好幾個,他不得不棄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生活仍然困窘異常。幸虧過不多久老朋友嚴武再次擔任劍南節度使,坐鎮成都,便將杜甫收入幕下,并上奏朝廷,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后人稱他“杜工部”,即緣于此。
嚴武厚待杜甫,使杜甫的境況有了很大的改觀。然而嚴武性情暴虐,喜怒無常,可不是個好相處的主兒。據《新唐書·嚴武傳》所載:嚴武自幼豪爽。他父親嚴挺之并不喜歡自己的妻子——即嚴武的母親裴氏,卻特別寵愛小妾英娘。那一年嚴武才八歲,見母親整天愁眉苦臉的,問明了緣故后,便乘英娘熟睡時,拿著把鐵錘進入其臥室,砸碎了她的腦袋。左右婢仆大驚失色,急忙稟白嚴挺之道:“小郎戲殺了英娘。”所謂“戲殺”,就是在玩耍中不小心誤殺了,婢仆們怎會料到一個八歲的孩童會成為兇手、有意殺人呢?可是這個八歲的孩童不但挺身而出,而且理直氣壯地責備父親道:“哪有身為國家大臣卻厚妾而薄妻的呢?孩兒是故意殺掉她的,并非戲殺。”其父也驚駭異常,卻不無贊許地說:“這真是嚴挺之的兒子啊!”
嚴武長大后,歷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并兩度出任劍南節度使,鎮守四川。這期間,他曾大敗吐蕃七萬余眾,攻拔當狗城,收取鹽當城,因功進封檢校吏部尚書,賜爵鄭國公。敵軍聞其威名,不敢近境。可是,他在川中窮極奢侈,賦斂無度,將好端端一個天府之國折騰得“閭里為空”。作為一個土皇帝,他又專橫跋扈,恣行無忌。誰如果一句話使他高興了,就可以立即獲得上百萬的賞賜;倘若不小心惹怒了他,弄不好就會人頭落地。章彝,堂堂一個梓州刺史,也曾經照顧過杜甫,就因為一點“小忿”,被嚴武借故殺掉了。其時,推薦、提拔過嚴武的宰相房琯已經被貶為刺史,正在嚴武屬下。嚴武不但不念朋友情,不報往日恩,反而“慢倨不為禮”。李白的名詩《蜀道難》中有這么一段:“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據《新唐書》所云,李白一是指斥嚴武,二是為房琯與杜甫的生命安全擔憂,并勸喻他們早日離開蜀中這塊是非之地。倘若此論屬實,則李白筆下的嚴武,就不僅僅是獨霸四川的土皇帝了,簡直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毒蛇猛獸。
那么,居住于成都草堂中的杜甫,究竟有沒有生命危險呢?答案是肯定的。
《新唐書》說杜甫“性褊躁傲誕”,“曠放不自檢”;《舊唐書》更說他“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其依據有二:一是說杜甫在成都草堂種花植樹,縱酒嘯詠,與當地的莊稼漢、老農夫混在一起,“相狎蕩,無拘檢”,大概是指責他身為朝廷命官——工部員外郎,竟然混跡于“群氓”之中,成何體統!更不能令那些史官們容忍的是,當堂堂劍南節度使、蜀中最高長官嚴武念及朋友之情,攜帶著美酒佳肴,親自到他家屈尊拜訪時,杜甫見了,依然蓬頭散發,既不裹一塊頭巾,也不戴一頂帽子,一副自由散漫的架式——這不是輕視、怠慢于己有恩的貴客么?二是當嚴武將杜甫邀請至自己的官署中款待時,杜甫喝得醉醺醺的,竟然登上嚴武之床,兩眼直瞪瞪地盯著嚴武說:“想不到嚴挺之竟然有這樣一個兒子!”此時,《舊唐書》說“(嚴)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瞧,真是宰相肚里能撐船,多么寬宏大量啊;《新唐書》則說“(嚴)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比較接近實際了,表面上雖不露聲色,內心卻恨恨地記下了一筆賬;更有野史如《唐語林》則說,嚴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須耶?’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恚目久之”已經是非常惱怒了,接下來又威脅杜甫,并直呼其爺爺的名字,你杜審言的孫子竟然敢捋虎須么?如果此時有人火上澆油地再不冷不熱地挑唆幾句,只怕杜甫就性命難保了,幸虧那幫客人都比較厚道,笑著加以解勸,杜甫才化險為夷。平心而論,杜甫雖然有不少毛病,比如說過于偏激呀,不拘小節呀,卻更有一副古代知識分子的錚錚傲骨:即使你對我有恩,我也不會降低人格巴結你。然而,在這個獨霸一方而又專橫暴虐、喜怒無常的土皇帝面前,他能夠既保留著錚錚傲骨而又安然無恙,也堪稱奇跡了。嚴武雖然“最厚杜甫”,卻又“欲殺甫數矣”。據《新唐書》載:一天,嚴武要殺掉杜甫與章彝,已經命令將吏們都集合于轅門了。不巧,就在嚴武將要威嚴地出至中堂,傳下那令人生畏的殺人令時,頭上戴的官帽卻一連三次被掛在簾鉤上。就這么一耽擱,嚴武的侍從中有人急忙稟白其母裴氏,裴氏急奔而至,才救下了杜甫。唯獨章彝晦氣,無人相救,不幸遇難。
嚴武欲殺杜甫,在唐詩中亦可得到佐證。杜詩中有多首與嚴武唱和的詩,而《全唐詩》中所收嚴武的六首詩中,就有三首是贈酬杜甫的。且看嚴武寫給杜甫的一首七律《寄題杜拾遺錦江野亭》: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
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冠。
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后醫方靜處看。
興發會能馳駿馬,應須直到使君灘。”
此詩貌似平和,實質多處透露出殺機。如果說“何須不著鵕鸃冠”還只是委婉地責備杜甫不整冠見客是不知禮節的話,“莫倚善題鸚鵡賦”卻是直接了當地給予警告了,用的是東漢末年的典故:著名文士禰衡性格剛強傲慢,不為權貴所容。曹操欲召見,他謝病不往,被曹操強行罰作鼓吏。禰衡當眾裸身擊鼓,羞辱曹操。曹操大怒,將他遣送到劉表處,劉表又將他轉送江夏太守黃祖。黃祖的兒子黃射為章陵太守,尤其敬重禰衡。一次黃射大宴賓客,有人獻上一只鸚鵡,黃射舉起酒杯對禰衡說:“愿先生賦之,以娛嘉賓。”(《后漢書·文苑列傳·禰衡傳》)禰衡提起筆來,文不加點,當場寫下了著名的《鸚鵡賦》,辭采華美異常。不久,禰衡因語言冒犯了黃祖,黃祖要殺他。黃射聞訊,急得來不及穿鞋,光著腳板趕來相救,可惜還是遲了一步。可憐禰衡遇害時年僅二十六歲。嚴武的意思再明白不過:別倚仗著你能寫幾首詩,有點名氣,你看那才華橫溢的禰衡,縱然能寫出名滿天下的《鸚鵡賦》,不照樣成了一個小小江夏太守的刀下鬼!“使君灘”為四川江灘名,據《水經注》載:楊亮被授職為益州刺史,至此舟覆,溺水而亡。蜀人苦于該處波瀾險惡,稱之為“使君灘”。如此看來,“應須直到使君灘”,不正是赤祼裸地以死相脅么!
然而,杜甫并沒有被嚇倒,他當即回復了一首七律,題為《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
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
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疏。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這首詩的大意是:我杜甫官居拾遺時,面對著至高無上的皇帝也敢犯顏進諫,不為所屈——言下之意,你一個節度使就能使我閉嘴么?簡直是笑話!如今棲居蜀中,疏懶是我的天性,騎馬釣魚是我的常態。你看那魏晉時的名士,比如阮籍,比如謝安——阮籍蔑視禮法,縱酒佯狂以避世;謝安快意山水,風波險惡何所懼(據《晉書·謝安傳》載:謝安泛舟出海,陡遇風浪,他人驚恐失色,獨謝安神態如常)。如今我雖然白白承受著你節度使大人的恩澤,可是我存身于本來就沒有路徑的茅草之地,你卻叫我開辟一條循規蹈矩之路,叫我從何處入手?言外之意: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我杜甫雖無權無勢,卻寧愿像禰衡那樣死去,也絕不會向任何權勢者屈服!
詩圣杜甫,雖然也曾“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熱衷于功名富貴,比如安史之亂爆發不久,杜甫便歷經顛沛流離,風塵仆仆地趕到鳳翔,參拜新即位的唐肅宗李亨,求得了右拾遺一職。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杜甫之追求功名利祿,亦是為了實現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思想,亦是為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良好心愿;更可貴的是,詩人“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心中裝滿了普通老百姓,裝滿了民間疾苦。他兩次上疏唐肅宗替“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舊唐書·房琯傳》)的屢敗之將房琯辯護,雖然有迂腐的成份,不也充分體現了古代知識分子不計個人利害的執著追求嗎?
嚴武只活了四十歲(726~765),他病死的時候,其母裴氏尚健在,白發人送黑發人,這個做母親的痛哭一番后,又輕輕地舒了口氣,說:“而今而后,吾知免為官婢矣。”這一真情流露,反映了這樣一個客觀現實:鑒于兒子的暴虐與官場的險惡,她日日夜夜提心吊膽,一旦兒子受到“王法”制裁或失足于宦海,她也必然會受到誅連,不被沒入官府做婢女才怪;如今兒子已死,這個威脅總算解除,自己也不會于垂暮之年蒙受羞辱了。杜甫比嚴武大十四歲,享年五十九歲(712~770),嚴武死時,杜甫已經五十四歲了。由于失去了嚴武這個依靠,杜甫不得不東下夔州(今四川奉節縣),又輾轉漂泊于湖北、湖南,最后,病逝于耒陽湘江的一條小船上。
南宋朱翌在其《猗覺寮雜記》中感嘆地說:“倘若嚴武的帽子不被掛在簾鉤上,他的母親來得再遲一點,杜甫就被殺掉了。黃祖的兒子救禰衡遲了一步,禰衡遇難而死;嚴武的母親救杜甫來得快,杜甫僥幸活下來了。兩事雖相似,結果大不同,這就是命運啊!”
其實,杜甫的僥幸不也是我們民族的大幸么?倘若老杜當年被殺,后人便再也看不到《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登高》《登岳陽樓》《旅夜書懷》《江南逢李龜年》等老杜晚年的名篇了,更讀不到“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等名句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寶庫,將會損失多少瑰麗的珍寶啊!這,何嘗又不是嚴武的僥幸與大幸呢?專橫暴虐的嚴武,除了有點軍功外,最為后世稱道的,就是厚待過詩圣杜甫了。倘若他殺了杜甫,或許不會對其仕途產生任何影響——由一點“小忿”而殺掉梓州刺史章彝,也未遭到任何懲罰,何況殺一個曾被自己收于幕中的潦倒書生杜甫呢?然而,他卻不可避免地會留下千秋罵名。中國歷史上兇殘暴虐的皇帝固然不少,而散布于各地的、大大小小兇殘暴虐的土皇帝就更是如過江之鯽、不計其數了。僅僅兇殘暴虐,誰會特意記下一個區區嚴武?誰會特別痛恨一個區區嚴武?何況他還文武雙全,既能揮刀殺敵,又能提筆賦詩,一首《軍城早秋》“昨夜秋風入漢關,朔云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氣勢何等豪邁!然而,倘若他殺害了詩圣杜甫,那就臭名昭著,必將遭到萬人唾罵,永遠地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簡直與跪在岳墳前的奸相秦檜不相上下了。從這一點說,杜甫的僥幸不也正是嚴武的僥幸與大幸么?仔細想想,還是那生前雖無皇帝之名卻有皇帝之實、死后被追尊為“太祖武皇帝”的曹操最聰明,他說過一段特別耐人尋味的話:“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于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而劉表呢,一點兒也不笨,才不會上曹操的當呢。他雖然同樣不能容忍禰衡,也同樣不愿擔當殺害名士的惡名,卻“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引裴松之注》)。一介武夫的黃祖可沒那么多顧忌,怒氣一發,就斷送了一個年輕才子的性命。于是,聰明絕頂的曹操、一點兒也不笨的劉表等輩,必然會拈須微笑:妙極了!黃祖啊黃祖,你真不愧是老夫的一把快刀!于是,在形形色色的大皇帝、小皇帝、真皇帝、土皇帝們的眼中,捏死個把“雀鼠”,又何足道哉!倘若“雀鼠”般的禰衡地下有知,并能夠到閻羅天子面前鳴冤告狀的話,究竟該認定誰為真正的被告、真正的兇手呢?
杜甫確實僥幸,能夠“善終”于自家的小船上,免去了訴訟于陰曹地府的許多麻煩,比起連《鸚鵡賦》也未能流傳下來的青年才子禰衡,簡直太僥幸了!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備嘗艱辛的文士,既然誰也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既然誰也不能真正擺脫像“雀鼠”一樣任人宰割的命運,那就只有將自己的一生寄托給那渺茫的“僥幸”了。
嗚呼,這令人心酸的僥幸;嗚呼,這令人心痛的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