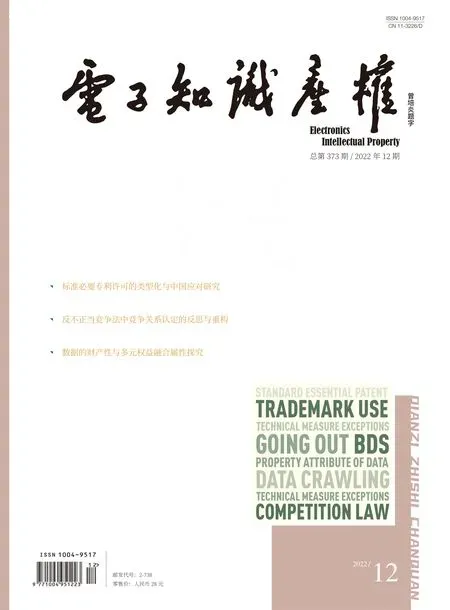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的類型化與中國應對研究
文 / 馬忠法 曾鑫坤
一、引言
在國際技術轉移持續增多和經濟全球化不斷加深的背景下,知識產權領域內的技術轉讓與許可早已呈現蔓延之勢,知識與技術的傳播交流不僅促進了高新技術成果轉化,豐富和提升了全人類的日常生活品質,而且也使得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帶動了全球經濟的橫向與縱深發展。在此背景下,人們對技術本身及其標準化要求也越來越高,并試圖建立一整套標準化體系來規制相關行業發展,達到互聯互通的無障礙適用目標1. 參見寧立志、龔濤:《標準必要專利全球費率裁判:實踐、爭議與對策》,載《北方法學》2022年第3 期,第38 頁。,從而為消費群體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但如此也帶來了牽涉不同地域國別的諸多訴訟糾紛。就中國而言,自從2001年12 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我國華為、中興通訊、小米等信息技術領域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竭力走向海外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取得了矚目成就;然而,由此使這些企業在國際上所牽涉的知識產權訴訟糾紛也日漸增多,反壟斷案件層出不窮,2. 參見袁嘉、王圣宇:《FRAND 原則在標準必要專利糾紛案中的適用——結合華為訴IDC 案進行分析》,載《競爭政策研究》2015年11 月,第49 頁。涉及的不同類型的產業范圍也在逐漸擴大,將與標準必要專利(SEP)相關的公平合理無歧視(英文“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縮寫為FRAND)原則的適用、政府干預限度、費率計算方法與標準、壟斷行為認定等相關法律問題推向深入,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尤其是在SEP 許可費率的全球裁判管轄權上,我國司法實踐實際上并無知識產權糾紛管轄的專門性規范,也始終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以所謂“適當聯系”或“更密切聯系”作為管轄依據3. 參見張鵬:《跨境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民事訴訟管轄規則研究》,載《知識產權》2022年第1 期,第14 頁。,理論界也是各執一詞,對相關問題的研究相對滯后于國外。這一現象對于我國司法主權和企業的國際化發展都構成了相當程度的挑戰,影響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建設。
當然,這與技術專利的“壟斷”特性相關,無論國內抑或國外,尤其是涉及高精尖技術和標準必要專利,“要么退出市場,要么接受合同”二選一的窘迫處境使得眾多技術受方企業不得不以犧牲自身權益的方式獲取技術供方的專利,向供方“合理合法”地退讓。但目前不同產業類型的涉SEP 案件,一則產業本身在技術難度、輻射范圍和發展狀況等方面的差異化特征對司法有一定影響,二則不同產業涉SEP 案件的發生頻率也有較大差距,其中信息技術產業占據較大比例,這也將吸引國家、各類司法機關以及企業自身更多的關注度,從而采取針對性應對舉措。具體而言,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例中,涉及SEP 的案例便有兩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華為終端有限公司、華為軟件技術有限公司與康文森無線許可有限公司確認不侵害專利權及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糾紛三案”4. 參見(2019)最高法知民終732、733、734 號民事裁定書。和“OPPO 廣東移動通信有限公司、OPPO 廣東移動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與夏普株式會社、賽恩倍吉日本株式會社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糾紛案”5. 參見(2020)粵03 民初689 號民事裁定書。,可以看到,盡管2020年全國知識產權案件所涉領域極其廣泛,汽車制造、飛機制造、藥品等支柱性產業領域案件都不少,但在十大知識產權典型案例中電信行業卻占了1/5 且都涉及SEP,足見最高司法機關對SEP 重視的程度。此外,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20年還專門設立課題組并發布了“標準必要專利訴訟案件法律問題與對策探析——基于通信領域訴訟案件的實證研究”(《問題與對策分析》)這一研究報告,副標題直接將研究范圍限制在“通信領域”,由此可見信息技術相關產業在SEP 案例中的重要性地位,并且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來看,除了信息技術領域和生物醫藥領域,其他領域涉及SEP 或者SEP 典型案例確實較為鮮見且影響較小。
因此,基于SEP 案件中信息技術等產業的類型化特征,本文將主要著眼于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的類型化分析,從SEP 基本概況出發,以類型化視角呈現國內外發展現狀,探討類型化產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
二、標準必要專利及其所涉案件的類型化分析
在對標準必要專利的許可進行類型化解讀之前,有必要對標準必要專利的基本概況進行前提性的說明,這一部分將從SEP 概念出發,厘清其基本運作方式,進而結合相關實證數據,主要呈現“標準必要專利”在國內外的總體發展現狀,展開標準必要專利所涉案例的產業類型化分析。總體上,SEP 雖然起源于國外,但隨著全球市場的不斷擴張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SEP 的許可搭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跨境貿易的橋梁,然而由于經濟狀況、科技水平、企業實力、法律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影響,SEP 許可費率所引發的糾紛近年來可謂愈演愈烈,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均呈現增長態勢。與此同時,SEP 許可的類型化取決于不同產業的特點,并非可以泛泛地適用于所有產業,而且,由于各產業本身的類型化特征和跨國發展進程中呈現出的特點,不同產業涉及SEP 糾紛的數量等具體情況也存在差異化現象,不能一概而論。
(一)標準必要專利之溯源
所謂“標準必要專利”(SEP)意指要達到某一行業標準的要求而必須使用的專利,并且無法規避和尋找替代專利,甚至每一個標準必要專利都構成一個單獨的相關技術市場,其初衷是為了使產品在必須滿足一定的性能、質量或安全等標準要求的前提下出現在市場中,達不到該標準則不允許進入該標準專利適用的產品市場,從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和提高消費者社會福利的目的,具有公益性特征6. 參見王曉嘩:《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對華為訴IDC 一案的看法》,載《人民司法》2014年4 月,第19 頁。。在世界各行業標準化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以歐洲電信標準化協會(簡稱ETSI)為代表的標準制定組織(簡稱SSO)為衡平公眾的標準化需求、保護合理競爭秩序和防止專利權人濫用許可之間的關系,致力于搭建全球性的技術標準化合作組織,因其專業性和權威性而被眾多行業采用實施;并且為避免SEP 權利人濫用專利形成壟斷,給予同等條件下的善意的被許可方以不同等的待遇,例如索要高價或者提出不公平、不合理的歧視化許可條件7. 參見譚袁:《論標準制定組織披露規則的完善》,載《北方法學》2017年第5 期,第91 頁。,SSO 也要求SEP 權利人在將自己的專利技術方案放入相應的技術標準中時,要么同意免費地讓別人使用,要么在許可SEP 時遵循FRAND 原則(即“公平、合理、無歧視”);8. See Common Patent Policy for ITU-T/ITU-R/ISO/IEC,http://www.itu.int/ITU-T/dbase/patent/patent-policy.html,最后訪問時間:2022年9 月13 日。雖然有部分權利人選擇免費許可他人使用其技術,9. 具體分析參見馬忠法:《技術標準與技術許可之關系探究》,載《電子知識產權》2007年第10 期,第10-15 頁。但多數權利人往往選擇FRAND原則。然而由于該原則作為相對抽象的概念,并無明確具體統一的定義和標準,其解釋權往往交由各國法律理論和司法實踐,具有極大靈活性10. 參見劉影:《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的計算:理念、原則與方法》,載《清華法學》2022年第4 期,第149 頁。,而不同國家在維護自身司法管轄權的基礎上,往往傾向于做出有利于本國企業的裁判,且部分國家并未將FRAND 原則寫入法律體系當中,從而在FRAND 原則適用以及管轄權合法性的問題上,極易產生爭議。
此外,FRAND 原則也隱含著對不同條件的被許可人可以給予差異化的許可費用,所以專利許可費用在實務當中的差異化本身并不違背該原則,真正產生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界定是否屬于“同等條件”,在何種程度上應該給予“同等待遇”,以及不同等的費用待遇是否超出了不同等條件的差異化界限并構成歧視。也正是基于此,世界范圍內目前關于標準必要專利的大多數糾紛,實際上都是圍繞著確認是否違背了FRAND 原則,以及確認相應的SEP 許可費率是否構成侵權、壟斷或破壞市場秩序等問題展開11. 參見張鵬:《跨境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民事訴訟管轄規則研究》,載《知識產權》2022年第1 期,第14 頁。,并且受到談判過程當中雙方是否就SEP 許可費率達成共識的影響。但這往往是一場拉鋸戰,最終會由于“管轄權”的爭奪而演變為多國不同法院之間的國際平行訴訟,這對于SEP 權利人而言或許只是時間成本的問題,但對于各國司法而言則是司法資源的浪費,以及不同法院作出不同裁判導致的司法權威受損12. 參見宋曉:《涉外標準必要專利糾紛禁訴令的司法方法》,載《法學》2021年第11 期,第176 頁。,對實體企業而言則不僅是陷入“奔走各國、疲于應訴”的消極狀態,而且可能因為判決得不到最終執行造成額外的重大經濟損失,錯失發展的重大機遇,企業的創造性和潛力也會受到沉重打擊。可以預見,隨著SEP 不斷融入到全球市場的各個行業領域,SEP 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影響也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司法作為保障合法利益的最終環節,需要在“戰爭”來臨前夕,做好一切準備。
(二)標準必要專利所涉案件的現狀及類型化
1. 中國的標準必要專利現狀及類型
針對標準必要專利之核心“FRAND 原則”,盡管我國司法當中并無明確規定,但其“公平、合理、無歧視”的理念卻見諸我國各部門法當中,例如,《民法通則》第五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合同法》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第六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反壟斷法》第十七條規定“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從事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價購買商品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并且《民法通則》第八條還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民事活動,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如此看來,在我國開展民事活動的商事主體理應遵循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也在應然層面需要認可我國司法的管轄。但問題在于,涉外SEP 糾紛更加復雜,前面也提到,正是因為我國尚無涉外知識產權糾紛管轄權的專門性規范,才導致當下對涉外問題停留在自下而上的摸索階段,演變為“禁訴令”與“反禁訴令”之間的戲劇化斗爭場面13. 一般而言,禁訴令制度是排除他國司法管轄權的一項法院命令,其目的在于阻止當事人在另一個國家提出訴訟或強迫當事人終止參加在他國已經開始的訴訟。若當事人無視該禁令而繼續進行他國的訴訟活動,則其將會受到諸如罰款、禁止從事特定的商業活動甚至拘禁等制裁措施。反禁訴令則是指法院通過頒布反禁訴令直接阻止一方當事人執行他國法院發布在先的禁令救濟裁判。參見祝建軍:《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與反禁訴令頒發的沖突及應對》,載《知識產權》2021年第6 期,第14-24 頁。,各國法院都試圖彰顯自身裁判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卻也否定了別國或異地法院的裁判結果14. 參見李宗輝:《標準必要專利跨國訴訟中禁訴令的適用標準研究》,載《法商研究》2022年第4 期,第187 頁。,這自然無益于當事雙方的談判順利進行,更不利于該領域諸多問題的高效解決,也會導致國際競爭環境走向惡化,不利于世界市場發展。因此,實際上并非只有我國會陷入這一窘境當中,別國法院同樣面臨這一難題,只是在這一過程中,哪一方將占據主導話語權,或者說能否形成世界范圍內的相對共識,從而采取互利共贏的可行性措施,仍然需要用更多時間去考察。
就中國涉SEP 案例來看,筆者通過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全文檢索“標準必要專利”,統計了2014年至2021年的含“標準必要專利”字樣的裁判文書數量,共92 份,制作圖1 如下:
從圖1 中可以看到,其一,我國2016年之前提及“標準必要專利”的裁判文書數量均為個位數,可見我國在標準必要專利上的司法實踐是相對滯后的,近年來各行業關于標準制定的增多一定程度上也佐證了這一點;其二,2014-2018年的文書數量呈現持續增多趨勢,2019年開始減少且相對穩定,所以審理該類案件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我國司法實務當中的常態,不過相比于其他類型案件,在總體數量的基數上仍然是少之又少,較為薄弱15. 需要說明的是,整體上與實際中發生的標準必要專利糾紛數量似乎并不相符,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中國裁判文書網數據上傳相對滯后導致的。。為了更詳細地考察我國涉SEP 案件的產業類型化特征,通過將以上92 份涉及的判決文書進行產業類型的劃分,即每份判決書當中所涉及的標準必要專利涉及何種產業,制作圖2 如上:

圖1 2014-2021年含“標準必要專利”字樣的裁判文書數量16. 數據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s://wenshu.court.gov.cn,最后訪問時間:2022年9 月13 日。

圖2 2014-2021年含“標準必要專利”字樣的裁判文書所涉產業類型
從圖2 中可以看到,我國2014-2021年涉標準必要專利案件的產業領域最多的是信息技術產業,比例達到74%,且大多數糾紛集中在信息通信技術的相關標準必要專利上17. 參見(2014)深中法知民初字第240 號、(2015)最高法知民終第4751 號、(2016)京民轄終303 號、(2018)蘇民轄終32 號等裁判文書。,主要圍繞許可費用及其定價、是否違反FRAND 原則、是否構成利用市場支配地位導致壟斷等問題,這與IPlytics 發布的標準必要專利糾紛集中在移動通信技術領域占比82%的數據是相契合的18. 參見秦樂、李紅陽:《美歐數字經濟知識產權治理趨勢研究》,載《信息通信技術與政策》2022年第6 期,第39頁。。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一方面是因為我國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相對較晚,大量的標準制定早已被歐美發達國家搶占先機,中國的SEP 依賴性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因而其中大部分為涉外案例,愛立信、高通、諾基亞、夏普、交互數字公司和康文森等頻頻出現,國內企業如華為、小米、OPPO、魅族等主要手機制造商更是高頻涉案主體;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近年來的信息技術產業發展迅猛,而相應的知識產權法治建設和社會氛圍仍然是相對滯后的,因而也極容易產生各類糾紛。僅次于信息技術產業,另一SEP 案例高發行業為藥品產業,占比13%,主要涉及藥品生產標準、檢測標準19. 參見(2015)呼民知初字第00130 號、(2017)京73 民初42 號、(2020)最高法知民終1564 號、(2017)魯06 民初195 號等裁判文書。。除此之外,汽車制造、建材、農業以及交通運輸等產業也存在較少SEP 訴訟類型,其中汽車制造業主要涉及了汽車配件標準、汽車制動系統標準20. 參見(2018)京73 民初62 號、(2021)最高法知民終12 號等裁判文書。,農業領域則涉及了土壤測定標準21. 參見(2019)最高法知民終382 號。,建材領域主要涉及了管樁、螺絲、鋼筋等建材工具的標準22. 參見(2018)鄂01 民初94 號、(2016)粵73 民初1926 號、(2020)最高法知民終551 號等裁判文書。,交通運輸領域則主要為交通裝置行業標準、集裝箱標準和制動系統標準等23. 參見(2017)魯民終99 號、(2019)最高法知民轄終92 號等裁判文書。,整體上多以技術含量不高的零部件或者材料為主。因此可以得出,SEP 對信息技術及藥品領域外的核心技術造成不了實質性的影響,置于整個知識產權領域當中則更是影響甚微。
反觀現實,我國涉標準必要專利案件主要圍繞是否違反FRAND 原則或是否構成侵權行為或壟斷行為進行裁判,而針對管轄權問題,其實大部分國內案件并不存在沖突,但仍然有部分公司會選擇不同SEP 在國內不同法院發起平行訴訟,例如華為與三星就曾在深圳中級人民法院、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西安中級人民法院形成“三陣對壘”的累訴局面。然而,由于SEP 糾紛案件具備證據材料眾多、法律關系復雜、專業技術問題要求高等特點,尤其是跨境信息技術產業類型糾紛,確實能夠給司法裁判帶來一定挑戰,而且部分非知識產權法院仍缺乏相關的專業法律人才,司法實務當中往往容易出現裁判結果不一乃至矛盾對立的情況,這不僅會消耗國內的司法資源,占用大量人力和時間,而且也嚴重威脅司法權威和影響當事人合法權益24. 參見胡志光、祝建軍:《標準必要專利平行訴訟的司法管轄權》,載《人民司法》2021年第13 期,第14 頁。。需要看到,國內SEP 平行訴訟實際上一定程度是我國司法體制本身的不完善導致的,因為各平行訴訟的案件所請求裁判的事項和內容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國內法院也理應具備形成管轄權協商合意的條件,所以我國的司法改革道路也可謂任重道遠。
2. 國外的標準必要專利現狀及類型
就國外的涉SEP 案件產生的主要領域而言,筆者通過檢索不同國家和地區涉及“標準必要專利/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的案件數量得到下表1:25. 數據來源:https://app.vlex.com,最后訪問時間:2022年9 月13 日。

表1 部分國家或地區涉SEP 的案件數量25. 數據來源:https://app.vlex.com,最后訪問時間:2022年9 月13 日。
從表1 中可以看到,美國在標準必要專利的涉案數量上可謂獨占鰲頭,達到27175 件,總體占據全球總量的近76%之多,而且在信息通信領域的標準必要專利的總體數量也是占據全球之首26. 參見賈文倩:《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標準必要專利侵權風險研究——從愛立信訴小米案切入》,山西大學2018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 頁。,這與美國在相關科技領域的強有力統治是分不開的,因而不管是從數量上還是從標準必要專利最早產生的時間上,美國都處在金字塔的頂端位置;而加拿大之所以數量也相對較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兩國在經濟往來上的關系極度關聯,從而產生的糾紛也并不少;英國的數量總體上也是較大的,比其他國家都更多,一方面是因為英國作為早期工業崛起的發源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底蘊深厚,因而在標準制定方面也是較多的,另一方面,近年來英國在標準必要專利的許可費用管轄權問題上的態度是相對堅決的,即主張英國法院具有全球管轄權,從而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該類案件的增長;對于印度而言,近年來隨著國際市場的制造業產地轉移,印度由于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地理位置優越、信息技術人才較多等優勢成為更多跨國企業的首選,因而在這一過程中也產生了較多標準必要專利案件;值得一提的是,涉及國際法的SEP 糾紛判例并不多,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跨境交易糾紛的商事主體往往更多傾向于在本國發起訴訟,從而攫取更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國際法對于知識產權領域SEP 糾紛的相關規定并不完善,從而很少被引用。最后,就單純涉案數量而言,相較于中國,其他國家就算在科技領域并不特別發達,涉案數量上也遠遠超過中國,當然,并不是說涉案發生數量越多就說明該國的相關領域越發達,但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可以反映出,中國在標準必要專利的市場上,仍然是處在初期發展階段的,還有很大的空間和潛力。
另外,具體到不同國家標準必要專利產生的糾紛主要集中在哪些產業領域,這里選取美國和英國作為主要考察對象,通過不完全統計,兩國2015年至今涉及的SEP 案件進行類型化分析,以“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汽車制造”“建筑建材”“交通運輸”“農業”和“其他”作為產業類型劃分標準,制作圖3 如下:27

圖3 英美兩國2015年至今涉標準必要專利的領域劃分27. 數據來源:https://app.vlex.com; https://heinonline.org,最后訪問時間:2022年9 月13 日。
從圖3 中可以看到,其一,英美兩國標準必要專利相關案件中,信息技術領域的占比與中國的情況一致,占比都是最高的,分別達到55%和49%,其中涉及LET 技術(4G)相關通信技術、無線網絡數據、電子、計算機技術等SEP 較多,這與當前世界市場中ICT(Intern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產業的迅猛發展密切相關,幾乎沒有人可以真正離開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者筆記本電腦這類產品,它們所涉及的SEP 則在糾紛當中占據了主要部分,前面提到的中國涉外糾紛中愛立信、高通、諾基亞、交互數字公司、康文森和摩托羅拉等廠商企業的身影同樣常見于英美國家;與此同時,在美國的諸多SEP 案件當中,涉及標準必要專利的軟硬件比例大致為6:4,而中國目前主要集中于軟件層面,硬件方面較少則得益于中國強大的制造業能力,但美國在軟硬件方面,至少在表面上看是相對均衡的,也足見美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絕對統治力和均衡發展的特點。其二,美國的涉生物醫藥SEP案件同樣比例較高,達到22%,而英國則為14%,強生、輝瑞、百健等國際知名公司赫然牽涉其中,涉及的產品包括護理、抗生素、檢測、醫療器材、疫苗以及各類疾病的藥物標準等;就美國而言,其生物醫藥科技確實是首屈一指的,在該領域的生物醫藥標準必要專利具有絕對的話語權,并且擁有全球最多的生物制藥公司和最高端的生物醫藥人才。其三,在汽車制造行業的比例上則是英國略高于美國,英國作為老牌的汽車制造強國,汽車行業發展較早,因而該領域的標準必要專利案件比例相對較高。其四,在建筑建材、交通運輸和農業等領域,二者相差并不顯著,不過在涉及農業的SEP 案件比例上,英國明顯少于美國,這與兩國的農業發展現狀息息相關,美國高度機械化和現代化的農業在全球市場當中占據了較大比重,其農業SEP 涵蓋了生產、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全流程各方面,這與現代農業的發展趨勢相契合。
整體上,就涉SEP 案件的產業類型特征而言,全球范圍內涉SEP 的糾紛中,中英美三者呈現出較為一致的產業類型化特征,即“信息技術產業”占據最大比例(分別為74%、55%及49%),其次則為生物醫藥產業(分別為13%、14%、22%),再次是汽車制造與建材(分別為8%、24%和20%),同時,前四類占比之和每個國家均在91%以上,而其他產業比例則相對較小,占比9%以下,這與國際上信息技術產業的重要地位及其全球擴張的迅速發展態勢密不可分。
三、標準必要專利類型化的原因及其影響
通過前文對國內外SEP 發展現狀及其類型化的分析,可以看到,信息技術產業的SEP 糾紛,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國外,都占據著最大比重,而不同產業之間往往具有不同的類型化特征,但產業類型化與司法二者之間如何產生相互關系和影響,目前學界內并無直接的相關論述。那么產業類型化的特征又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對司法產生影響呢?我國司法又應該作出何種程度上的適應性調整呢?這一部分將首先說明信息技術產業和藥品等領域SEP 使用頻繁的原因,進而探討產業類型化的影響,厘清對SEP 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
(一)標準必要專利類型化之原因
根據前面對產業類型化的分析可以看到,全球范圍內涉SEP 的糾紛中,信息技術產業占據最大比例,并且往往具有國際性,其次則為藥品產業,而汽車制造和農業等其他產業比例則相對較小,并且往往局限于國內,其產業類型特征對糾紛的影響也因其總體數量而有所折損。具體來看,信息技術產業和藥品領域之所以如此頻繁地使用SEP 許可,主要是受到這些領域本身的行業特征所影響,尤其是它們的技術或產品往往出現在軟件運用層面。如就信息產業而言,SEP 涉及的硬件產品或技術遠不如出現在軟件及運用層面多,主要原因是運用層面更新升級較快,硬件卻因取得重大技術突破較為困難而具有相對穩定性,且硬件持有專有技術本身意義不大;就藥品領域而言,由于需要獲得藥品監督管理機構的嚴格審查,以及化學藥品的成分、結構相對透明的特點,生物醫藥產業除了在工藝、溫度、濕度等領域有可能出現專有技術外,其他方面想以專有技術方式持有也相對困難。進一步,在涉及SEP 的領域,通過FRAND 原則許可的比率較高,原因在于想通過持有專有技術來控制被許可方,要么因升級更新速度太快而沒有必要,要么因技術相對穩定而比較困難。但需要注意的是,仍然有一類往往涉及高技術含量的硬件設備制造領域的技術專利標準,存在著權利人完全放棄收費和允許免費使用其專利的現象,而這種情況往往都潛藏著專有技術的許可,并以使用其SEP為由收取額外的高昂許可費用28. 有關這方面的詳細分析參見馬忠法:《技術標準與技術許可之關系探究》,載《電子知識產權》2007年第10 期,第10-15 頁;馬忠法:《標準與知識產權之關系——兼談在企業戰略中的應用》,載《知識產權》2007年第1 期,第37-41頁。。因此,在研究SEP 許可時,這一現象是不容忽視的,由此才有可能對SEP 許可有一個相對客觀、理性的清醒認知。要知道,在國際資本橫行的市場,任何時候都不能有“天上掉下餡餅”的想法,否則將面臨極其危險的困境。
(二)標準必要專利類型化之影響與認知態度
就類型化對司法的影響而言,相比于其他產業,信息技術產業的類型化特征對糾紛的影響則是較為明顯的,例如(1)技術專利族群龐大、技術難度和適用范圍各異導致全球許可費率標準不一,從而容易引發不同主體之間因待遇不同產生矛盾沖突,(2)跨國企業或組織資本雄厚一定程度上也讓這一群體毫不懼訴,甚至主動挑起訴訟以攫取更多利益,(3)信息通訊、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更新迭代迅速導致難以界定和估量各方侵權損失程度或者賠償額度,(4)產業跨境范圍廣往往容易導致國際平行訴訟,不僅引發管轄權爭奪和司法資源浪費,而且增加企業不必要的負擔,(5)涉及主體多樣導致利益糾紛關系復雜,司法裁判很難實現多方主體利益關系的平衡,(6)專業技術問題較為復雜高深則可能影響司法裁判的專業性和公正性,(7)證據材料繁多、法律關系復雜、跨國訴訟的語言障礙等同樣對此類產業糾紛產生實質性影響。進一步的,此類SEP 案件一旦涉及國際跨境糾紛當中的信息技術巨頭,類型化的特征則更加集中和明顯,并且該類企業同樣形成了較為明顯的集群化特征,通常在國際范圍內涉及多起SEP 訴訟,與之對應的SEP 持有者也早已孕育了歐洲電信標準化協會(ETSI)等各類標準制定組織(SSO),主動或被動地在全球范圍內發起各類SEP 侵權訴訟,因此其類型化特征對SEP 糾紛的影響已然不容忽視。反過來,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不斷交流的世界潮流背景之下,以及全球知識產權技術轉讓與許可的加持下,不同國家對知識產權的法律界定也將切實影響到信息技術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從而不可避免地影響產業類型化特征。所以,產業類型化與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之間,并非單向的影響關系,而是雙向的相互影響關系。
這里以SEP 案件管轄權問題為例,例如,美國法院裁判的“TCL 訴愛立信案”29. See TCL Comm. Tech. Holdings. Lad. v. 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on, 2017 WL. 6611635 (C. D. Cal. 2017)中,二者達成合意的情況下,美國仍然就愛立信這一涉SEP 案件作出了全球性的裁判30. 參見寧立志、龔濤:《標準必要專利全球費率裁判:實踐、爭議與對策》,載《北方法學》2022年第3 期,第40頁。,同時針對TCL在法國、巴西、德國等國對愛立信的起訴法院簽發了禁訴令(Anti-suit injunction),認為TCL在其他法院的重復訴訟是不必要的31. 參見宋曉:《涉外標準必要專利糾紛禁訴令的司法方法》,載《法學》2021年第11 期,第182 頁。,實際上這可以反映出,美國法院意在爭奪信息技術產業的司法裁判權威地位,這與美國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關鍵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是相映襯的。英國法院裁判的“無線星球訴華為案”32. See 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id.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ad. (2017) EWHC 711 (Pat).中,二者未達成管轄權合意,而英國法院對SEP 全球許可費率管轄權的立場卻極為強勢和明確,導致作為專利實施者和被許可方在這一訴訟中陷入極為被動的境況,極大壓縮了進一步談判的空間,對于SEP 持有人無線星球而言,則免去了大量不同司法管轄區進行侵權訴訟的額外損耗,并且優勢地位得到更強的彰顯,增加了抬高許可費的籌碼33. 參見宗倩倩:《標準必要專利的全球許可費率管轄權爭奪及其應對路徑研究》,載《科技與法律》2022年第1 期,第27-28 頁。。這一立場將直接影響到跨境交易中涉SEP 糾紛的當事方對法院的具體選擇,更多的SEP 持有者將傾向于選擇英國法院提起訴訟,試圖從中攫取更大程度的利益。再有,中國法院裁判的“OPPO 訴夏普案”34. 參見(2020)最高法知民轄終517 號民事裁定書。中,夏普在裁判過程中從4 個方面對中國法院提出了管轄權異議,認為其在中國并無住所和代表機構,中國法院也無權就夏普在全球范圍內的SEP 許可條件作出裁定,而我國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確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糾紛的管轄時,應考慮許可標的所在地、專利實施地、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雙方談判意愿、FRAND原則、最密切聯系原則等因素,因此,在中國的法律視閾之下,只要前述地點之一在中國境內,則可認為該案與中國存在“適當聯系”或“更密切聯系”35. 參見張鵬:《跨境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民事訴訟管轄規則研究》,載《知識產權》2022年第1 期,第15-16 頁。,從而具有管轄權。可以看到,中國法院并不拒斥對SEP的全球許可費率進行管轄36. 參見祝建軍:《標準必要專利全球許可條件的司法裁判研究》,載《知識產權》2022年第1 期,第36 頁。,對涉外的知識產權糾紛問題,同樣有著司法解決路徑和法律依據,并非完全無法可依。
然而,在一般法律意義上,司法制度與產業類型之間并無直接關系,因為一國的法律并不會針對特定的產業類型的裁判進行額外的規定,否則將背離法律本身的統一普適性,區別對待不同產業類型的糾紛也將導致新的問題。這一點固然無所爭議,筆者也并非認為需要從法律條款層面對涉及信息技術產業的SEP 糾紛作出新的規定。這里想要強調的是,基于產業類型化的特征,尤其是信息技術產業的類型化特征,各國針對此類糾紛的司法審判需要做出一定的適應性調整和整體應對,植根于現實狀況,齊心協力地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采取針對性措施,從而更好地解決FRAND 原則適用、政府干預限度、SEP 費率計算標準、壟斷行為認定等法律糾紛問題;并以此為契機,助推信息技術產業更加蓬勃發展,而且也能在將來為其他各領域的國際訴訟糾紛解決提供路徑參考和基本方法,最終做到惠及世界消費群體,推動人類文明共同發展和進步。
但需要警惕的是,我們不宜對標準必要專利的影響給予過度夸張或解讀。通過前面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到,SEP 主要集中在信息技術和藥品領域,其他領域并不多見;而且即使涉及這些領域,多是運用技術層面或大型制造業領域的零部件或配件等生產技術,涉及核心的底層技術或硬件技術的較少;此外便是通過專有技術保護模式難以有效保護核心技術的藥品領域等。這說明它不是一個涉及所有技術領域的普遍現象。倘若做過度解讀,反而容易誤導行業發展,誘使誤入歧途,不利于我國的創新產業和知識產權制度的健康發展。所以應當對SEP 形成客觀、理性的認知態度,不浪費資源于與投入回報不相匹配的問題上,將更多資源集中于創新產業領域,并完善公平、合理的知識產權制度。事實上,在英美、歐陸和其他發達國家,鮮少能夠見到像我國這樣對SEP 許可過度關注的現象,因為在它們那里,SEP 及其許可只不過是專利領域的一個普通問題,反觀我國,學界曾經或當下針對SEP 相關法律問題作出了過度討論,甚至有人提出在《專利法》修改草案中給予專門立法,37. 參見王震宇、江耀純:《對<專利法>修改的建議——有關標準必要專利》,載《專利代理》2015年,第21-28 頁。這其實并無太大必要。38. 2015年的《專利法》第四次修改草案中就有專門條款對標準必要專利進行了規定,所幸后來《專利法》第四次修改中沒有采納。相反,應該秉持的態度和理念是,立足于了解諸如技術標準及標準必要專利的某一制度本質,集中精力抓住其關鍵問題,不被假象迷惑,為中國的企業及相關創新主體營造更為合理、有利的環境,形成科學、符合規律的制度以切實確保它們創新能力的提升才是根本。
四、新時代中國應對SEP 主要法律問題的解決路徑
通過以上對標準必要專利的基本概況分析,筆者厘清了SEP 的概念和運作邏輯,并結合國內外的司法狀況簡要呈現了SEP 的發展現狀,展開了類型化分析,進而探討了信息技術產業和生物醫藥產業類型化特征顯著的背后原因以及相應的影響,并就較為核心的管轄權問題進行了實證分析,辯證地提出了對SEP 法律問題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那么,中國應該采取何種措施予以應對,這一部分將從五個主要方面,為新時代中國針對該領域問題的解決路徑和發展方向提供針對性意見與參考。
(一)禁訴令與反禁訴令的應對
相較于作為禁訴令源起的英美法系,目前我國對于禁訴令與反禁訴令的應用尚處于初期借鑒階段,直到2020年才有所實踐,而完善禁訴令制度并形成相應的配套體系是我國應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禁訴令的強有力反制措施,同時也將進一步保障我國法院作出的司法判決最大限度地得到他國承認39. 參見趙威:《論國際訴訟管轄權沖突中禁訴令制度——以標準必要專利訴訟案為例》,載《理論探索》2021年第4期,第117 頁。。對于信息技術產業而言,不管企業是否有較為充足的資本應訴,在國際平行訴訟中,無論是禁訴令還是反禁訴令的運用,都能夠極大地緩解企業應訴的壓力,避免和減少各類資源的盲目投入。不過需要注意,禁訴令制度在國際范圍內有著擴張發展的趨勢,其不確定性也在逐步增大,甚至被部分國家地區的法院純粹當作維護本國企業利益的“合法”工具,法官不當行使自由裁量權也將加劇這一趨勢40. 參見宋曉:《涉外標準必要專利糾紛禁訴令的司法方法》,載《法學》2021年第11 期,第177 頁。,例如美國法院在審理國際SEP 糾紛頻繁頒發禁訴令或反禁訴令,就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禁訴令減少司法資源消耗、促進裁判統一、維護司法權威的本質初衷。因此,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面臨國內企業涉外知識產權糾紛的問題時,需要保持足夠的理性與清醒認知,從公平公正的司法審判角度維護雙方合法權益,最大限度地促進和解,實現共贏。除此之外,有學者亦提出,隨著國際局勢的不斷深入發展,“國際仲裁”在跨境交易和糾紛解決當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因而理想狀態下,倘若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裁決SEP 許可費率的國際仲裁機構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平行訴訟的各類弊端41. 參見宗倩倩:《標準必要專利的全球許可費率管轄權爭奪及其應對路徑研究》,載《科技與法律》2022年第1 期,第31-33 頁。,不僅能夠節省全球司法審判資源,避免當事方陷入不必要的各類訴訟糾紛當中,而且還能夠確保仲裁結果得到各國的認可與貫徹執行,可謂是為標準必要專利的國際長遠發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鼓勵企業等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與國際合作
技術專利的無形性、許可的零邊際成本,“需求方規模經濟”這些特征導致知識產權領域面臨復雜挑戰42. 參見李展碩:《“無歧視”專利許可與反壟斷法釋義——華為訴IDC 案再思考》,載《法律適用》2019年第24 期,第40 頁。,世界各發達國家和主要發展中國家都共同面臨著知識產權專利技術糾紛的現實難題,因此這也是一場無法單打獨斗的戰爭。我國近年來國際地位的提升自然有助于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一定的有利地位,但我國在國際標準制定領域的話語權是極度缺乏的,無論是SEP 還是其他知識產權制度,都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所以,為了扭轉或者是緩解這一問題,我國仍需加強國際地位的提升,努力參與到國際標準許可費率的司法裁判和全球標準制定當中,鼓勵企業主動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加強標準學習和運用,尤其是信息技術產業的領軍企業,更應積極主動參與到這一過程當中,爭取發揮主導性作用和自身優勢,避免一直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與此同時,主動積極地開展國際合作與友好交流,在遵循國際禮讓原則的基礎上努力實現互利共贏,維護有序的國際司法環境。倘若能夠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統一的能夠裁決SEP 全球許可費率及其爭端的國際機構組織,將目前的單邊管轄轉變為多邊合作的共同管轄43. 參見宗倩倩:《標準必要專利的全球許可費率管轄權爭奪及其應對路徑研究》,載《科技與法律》2022年第1 期,第31 頁。,則可能真正地緩解國際SEP 糾紛,為知識產權的國際轉讓與許可提供更大發展空間,挖掘出跨國企業的更大潛力和創造力。
(三)加強企業自身建設與搭建侵權預警機制
雖然不能否認國外SEP 權利人確有違反FRAND 原則的不平等許可行為或通過支配地位壟斷市場的意圖,但前期“談判”的失敗往往是加劇矛盾和激化沖突的關鍵環節。因此,倘若企業能夠培養專門的國際談判人才,能夠“定紛止爭”,合理、合法地實現互利共贏,也能夠在極大的程度上緩解中國企業面臨的國際問題和窘境。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中國企業已然在國際化不斷深入發展的同時,加強了自身的反應能力和適應能力,采取主動適應國際規則和維護合法權益的積極姿態參與國際競爭44. 參見劉影: 《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的計算:理念、原則與方法》,載《清華法學》2022年第4 期,第167 頁。。但盡管如此,中國企業仍然需要加強自身建設,培養國際談判和跨境交易訴訟的復合型高端專業人才,具體而言,例如提前了解和學習各種費率計算標準方式、把握合理的侵權損失程度以及賠償額度、厘清涉案主體的復雜法律關系、掌握對關鍵技術問題SEP 許可的專業解釋,以及培養處理繁多證據材料的法律能力等,從而能夠在把握產業類型化的基礎上,運用類型化特征,幫助企業為國際訴訟糾紛做好充足準備,不致疲于應訴。進一步地,中國更需要加強企業自身技術的挖掘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激發自主的發展潛力,從而不斷開拓國際市場,同時建立知識產權的專門法務隊伍和侵權預警機制,避免被SEP 權利人突然“劫持”,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四)完善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及提升相關司法人員職業素養
針對國外企業與我國各方面交流的不斷深入,產生的糾紛也愈發多樣,尤其眾多案件當事方認為FRAND 原則并不內含于中國法律當中,盡管裁判過程中仍然能夠進行一定程度的說明,但這始終不能具有直接針對性,從而缺失了一定的司法公信力。因此,我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內的各方面法制都需要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建設,積極地回應社會現實所提出的問題與挑戰,適當地通過法定程序調整和完善法制,促進法治建設,例如加強反域外壟斷法的建設、將FRAND 原則融入到現行法當中、加大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和侵權懲罰力度、完善針對涉外的知識產權糾紛相關法律規范等。同時在國際友好交流與溝通的情況下,以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和全球消費者權益為目的,以司法裁判能夠得以落實為最終目標,有條件地建構更多的專門知識產權法院,為知識產權糾紛問題解決配備專業的司法審判隊伍。進一步的,加強培養專門的知識產權人才,提升法律工作者的職業倫理素養與認知水平,富有導向性地加強對信息技術等重要類型產業的技術性認識和特征把握,例如技術性較強、專利族群龐大繁多、涉及產品多、消費群體廣、跨域范圍大等產業類型化特征,需要綜合考慮到實際裁判過程當中,制定專業化、體系化、科學化的解決方案和配套措施,并在總結知識產權法院建立和發展的經驗基礎上,不斷推廣和建立更多的專門知識產權法院,從而更好解決涉外糾紛,為提升司法審判的效率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助力。
(五)提升信息技術等領域創新能力與培養高端人才
前面提到,我國企業涉外糾紛在全球范圍內都是較多的,其中信息技術產業占據最大比例,一方面這與中國企業融入世界市場的快速上升趨勢密切相關,且普遍缺乏對全球市場的前期考察,更不熟悉西方國家搭建起來的各種國際規則;另一方面需要看到,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技術的依賴性是非常大的,主體性缺失問題較為嚴重,從而極容易在利益相關問題上產生更大糾紛,并受制于國外。因此,為了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最根本的方法仍然是在國家層面貫徹科教興國戰略,不斷加大信息科技領域的資金、人力等全方位投入,提高中國各行業在國內和國際標準化領域的建設水平,尤其是當下堪稱全球經濟發展引擎的信息技術產業領域。中國目前仍然較缺乏高端的復合型人才,在國際競爭中容易處在劣勢地位,因此也急需完善高端人才的培養體系,搭建跨國的人才輸送和共享渠道,彌補在部分領域的人才短板,尤其需要彌補信息技術領域高端人才的匱乏。但話說回來,我國仍然需要樹立堅定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個自信,避免陷入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當中,仍然需要堅持不懈地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勇毅前行,努力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五、結語
21 世紀全球化加深背景下世界各國在各行業領域都緊密聯系在了一起,而知識技術作為其中極為重要的內容,知識產權的轉讓與許可作為其中的關鍵環節,都啟示著我國學界和實務界需要在這些方面深耕下去。與此同時,更多地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仍然十分重要,本文中所主張的產業類型化對司法裁判的影響,尤其是在全球SEP 糾紛當中占據較大比例的信息技術產業的類型化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產業本身的類型化特征能夠反映或影響我國法制建設的實踐和完善方向,因而需要我國站在全球知識產權技術轉讓與許可的大背景和知識產權總體發展的視閾之下,作出一定程度上的適應性調整和全局應對。但也如前所述,對SEP 帶來的影響給予過度夸張的解讀或關注也是危險的,只有通過對知識產權領域內各種制度展開本質化考察和研究,結合國際發展趨勢和現狀,抓住主要矛盾和關鍵問題,共同營造可持續發展的、互利共贏的國際市場環境,形成完善合理的、科學規律的法治體系,多措并舉,才能真正在整體上促進國家科技水平提高和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助力中國知識產權事業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