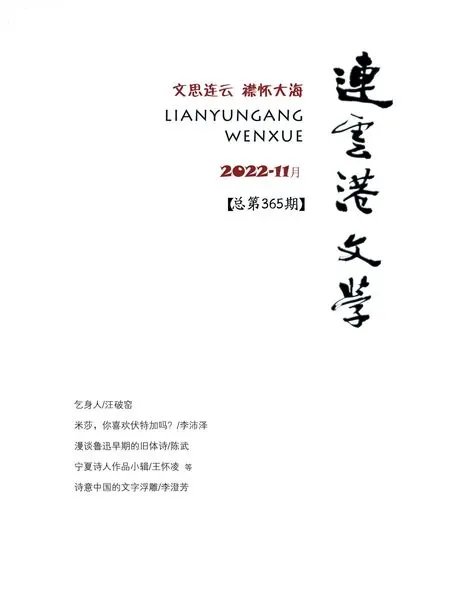蟲鳴填補著夜的孤寂(組詩)
畢俊厚
母親的莊稼
村莊寂寂無聲。這是一個午后
黑壓壓的云層滾至頭頂。悶熱的空氣
樹葉懶散地,一動不動
房檐底,納涼的狗,吐出六月長長的舌苔
如果不是誰家的驢,嚎叫一嗓子
缺少生機的村莊,就會被誤以為
曠古的村落,復活在某段時光的隘口
灼熱持續著。母親頭頂一襲藍圍巾
似乎要將噴涌而來的熱浪隔開。但是
鐵鍬順從了母親的意愿
從一只手挪移到另一只手
像是兩個士兵的交接儀式
村莊外的田野,列隊的莊稼
一副潰敗的模樣。大旱之下
一個村莊的精氣在收斂。
我的母親,鄭重地操起鐵鍬
以微不足道的力量,為萎靡不振的莊稼
注入振作的清醒劑
自然的律法,如晾曬在遠古石頭上的經文
母親的憂傷,深藏于一粒糧食的內部
莊稼的意志,從來未曾減損
它們以種子的形式,延續、繁衍
多么像人類,維系著堅貞的血統
當稚嫩的芽瓣,穿透厚重的泥土
就像一縷希望的火焰
打在母親灰暗的臉頰,一瞬間的光彩
讓母親受用終生。讓龜裂的土地
在豐收的遠景圖中,鍍上厚厚一層
金黃的,精神之銅釉
山那邊
拂曉時分,山那邊,仿佛是被什么
用力掰開一條縫隙。緩緩地,流瀉出
微弱的光陰。山這邊,一眼望不到頭的
莊稼地,就被微弱的光,涂上一層
深綠色的釉。已經整整一個夜晚了
父親和母親沒有合攏過一次眼皮
他們分別守在地的北頭和南頭。像是
隔著地球的南極和北極
他們一個在引水入渠。一個在探測
星輝均勻地灑在流動的水面上
地太旱了。滲透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他們樂于享受這個過程。就像當年
他們哺育懷里吃奶的孩子
享受微笑的過程。但是,整個夜晚
是孤寂的。蟲鳴聲卻無意填補了夜的孤寂
在宏闊的莊稼地里,冷不丁
從地北頭就會時不時冒出一嗓子
地南頭就會隨聲附和一嗓子
像極了一對閃著透明翅膀的蛐蛐
保持了高度的默契,隔著海一樣的
綠波,唱情歌。而渠水無止境地流淌著
成為夜晚的和聲。天上的星星越積越密
清爽的風,彌散著植物大口吐出的香氣
莊稼的葉面上,掛滿晶瑩的露珠
在窄窄的田壟上,兩條弓一樣的影子
緩緩蠕動,很快,就融在一起
成為時光的一部分
聽蟬
蟬鳴聲是一種意外。母親
卻樂于接受這樣的意外。
在短暫的安寧過后
母親耳郭里的蟬群,再一次蜂擁。
稀薄的月光,像一層水霧
漂浮在植物的葉面
凝結出乳白色的暈釉。
這時候,母親會走到院子的墻角里
槐樹旁。那些幽微的聲音
仿佛是某枚葉片發出來的
像召喚,又像催眠曲。
那時,蟬鳴會形成合唱
一波推動著一波
讓母親陷入沉思。
其實,母親的耳鳴癥由來已久
——父親走后,空曠的院落
綠波浮動過后,大片凝脂的月光
仿佛深夜中的良鄉。
月光下,樹影交錯
幻覺中的蟬鳴聲,無法排遣的傷感
此起彼伏地一遍遍壓著顫抖的樹葉
蕩漾
母親不懂蕩漾。常常圍著藏藍色頭巾
行走在鄉間田野。柔風從八面吹過
稻谷的波浪,是另一種蕩漾
我很少拿蕩漾打比方。就像
平靜的湖面,丟進一串石子
石子卻沒能留住攤開的漣漪
而現在,我奢侈地認為,母親荒蕪已久的
院落,那日漸躥高的雜草
搖曳著召喚般的綠意
我所知道的蕩漾,可能還有以下幾種
月明星稀,母親挑著滿滿的星輝
井水蕩漾,時光從窄縫中悄然流瀉
夜幕微啟,灶膛映照著疲憊的眼神
扶搖而上的炊煙,蕩漾成一串串白色的蓮花
那時,母親在簡單的幸福中,得到莫大的滿足
如果讓我繼續描述。駝著腰身的母親
就會扶正滿院的向日葵
金色的光澤,蕩漾著豐收的意象
而那一片白的頭頂,像一株孤零零的蘆葦
時常移動在季節交替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