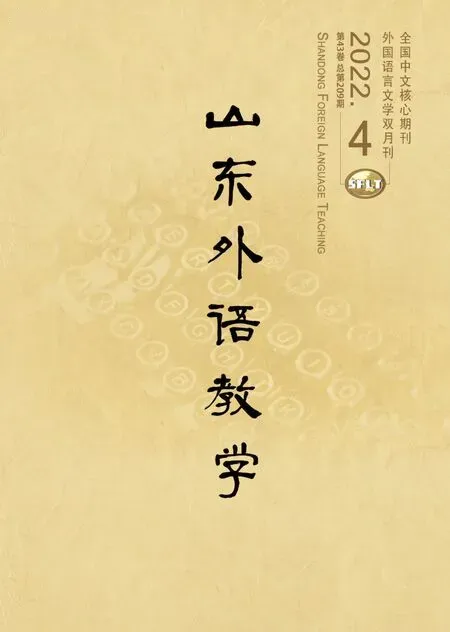尤多拉·韋爾蒂《樂觀者的女兒》的共同體書寫
荊興梅
(蘇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6)
1.引言
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 1909-2001)是美國南方作家,但她并不囿于南方夢和怪誕性等書寫程式。她的長篇小說有《樂觀者的女兒》(TheOptimist’sDaughter, 1972)、《三角洲婚禮》(DeltaWedding, 1946)、《失敗的戰爭》(LosingBattles, 1970)等;短篇小說集有《綠簾》(ACurtainofGreen, 1941)、《大網》(TheWideNet, 1943)、《金蘋果》(TheGoldenApples, 1956)等。她以《樂觀者的女兒》獲得普利策獎,因短篇小說榮膺6次歐·亨利獎。韋爾蒂的創作洋溢著美國南方文化,卻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融合異域文化共同審視轉型期的社會問題。《樂觀者的女兒》中的主人公們喜讀狄更斯和丁尼生等作家的作品,而他們與19世紀作家卡萊爾和莫里斯等志趣相同,都寄希望于共同體來消弭轉型焦慮,這一點已經得到學者們的解讀。本文在細察該小說文本線索的基礎上,證明它與共同體意識契合,從而打破韋爾蒂研究的地方主義限制,尋求廣闊靈動的世界主義內涵。
就文化研究中的共同體而言,其概念往往與轉型焦慮密不可分。其一,當歷史發生重大改變之際,尤其是農業文明式微、工業文明興起之時,共同體意識隨之分崩離析,現代性焦慮應運而生。關于這一點,穆勒(John Mill)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都曾論述過。其二,共同體和社會截然不同,前者代表有機和美好的一面,后者卻充斥著機械性。比如威廉斯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Keywords:AVo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 1975)中認為共同體比社會更具親近感;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在《共同體與社會》(CommunityandSociety, 1957)中強調共同體比社會更加生機勃勃;馬克思(Karl Marx)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heGermanIdeology,1845)中運用“全人共同體”(the community of complete individuals)理念來闡明:共同體能培育出完整和自由的人,而社會則不一定(轉引自殷企平,2016:71-72)。其三,共同體盡管具有想象的性質,但激勵有識之士不斷改良社會,推動人類擺脫焦慮、趨向完美之境。在《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Communities, 1983)中,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共同體具有烏托邦色彩。然而,一代又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前赴后繼、鍥而不舍,希冀遠離階級對立的資本主義制度、走向自由大同的世界主義。
2.現代化轉型中共同體的形塑
2.1 農耕時代的鄉村共同體
《樂觀者的女兒》首先展示了一幅農耕經濟的時代畫卷,它風光旖旎、溫情脈脈,以勢不可擋的力量打開讀者的心扉,令人對社會轉型前的南方共同體頗為向往。這一場域設置在西弗吉尼亞州,那是勞雷爾母親貝基的“老家”。她在這里度過結婚前的所有歲月,嫁到密西西比后又頻頻回去小住,不僅讓貝基一輩子魂牽夢縈,還使她的丈夫和女兒流連忘返。換言之,它對置身其中的常駐者和暫住者都產生吸引力,把他們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老家”一派田園風光,奠定了心智培育與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老家的房子蓋在可以說是世界最高屋頂的頂層。外邊,芬芳碧綠的露天草地上放著幾把搖椅。坐在搖椅上可以看到那條繞著山腳流過的小河。只有當你順著盤旋的山路快走到山腳的時候,才能聽到河水的流動聲。那聲音就像滿教室被施了魔法的小學生在給他們的老師背書。”(韋爾蒂,2013:128)①小說家喬治·艾略特認為,當自我處于忘我狀態,對他者的一切感同身受,就成了心智健全、擁有美德之人(Eliot, 1984:349)。這種物我相忘、怡然自得的狀態,人們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得,寄情于山水就是一種。大自然具有神奇功效,能激發人們的審美與哲思,提升想象力和創造力,從而達到心智培育的目的。這一點早已被華茲華斯等英國浪漫派詩人們所驗證。而美國南方人跟土地和大自然休戚與共,還要追溯到17世紀南方邊疆的拓荒時代。這片地域緊靠大西洋和墨西哥灣,它氣候溫和濕潤、陽光充足、物產豐富,最早吸引了蘇格蘭、愛爾蘭、德國的移民來開疆拓土,后來匯聚了大量英國殖民者來追逐財富夢。移民們在南方安家立業、生生不息,他們的心智受到當地自然水土的啟迪,將英國習俗和禮儀本土化,形成南方紳士和南方淑女的集體文化。
《樂觀者的女兒》中“老家”的生活方式古樸簡單、渾然天成,體現了前工業社會自給自足的景象。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將社會分為三個階段,即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其中前工業社會以傳統主義和土地資源為核心(1997:138)。這一時期的人們還未領略現代機械文明帶來的便利,但日常生活卻盡顯它詩意和滿足的一面,正如貝基告訴勞雷爾的那樣:“我經常騎著塞利姆去學校。走七英里路翻過那座九里山,然后再走七英里才能到家。為了讓時間過得快點兒,我就騎在馬背上背書——毫不費勁就記住了,親愛的。”(128)貝基騎在馬背上悠然自得地讀書,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國性靈派文人袁枚的詩句:“牧童騎黃牛,歌聲振林樾。”這種田園牧歌的氣息沁人心脾,成為美國南方民眾的向心力。馬既是那個時代代步的交通工具,也是南方畜牧業中的重要物種。除了飼養業,南方農業經濟還倚重于棉花、玉米、水稻、煙草、靛青、蔗糖等。棉花一直是南方的基礎農作物,其產出量從1793年開始突飛猛進,因為艾利·惠特納(Eli Whitney)在這一年發明了軋棉機。南方棉花出口到美國境內境外的很多地區,當地的人們則紡紗織布,用手工制作棉布衣服、鞋襪和其他用品,男女老幼一年四季的穿戴毫無后顧之憂。《樂觀者的女兒》就出現了類似情形,貝基對舊時代深情回味:“我平生擁有的最美的上衣是自己做的,料子是媽媽親手紡的,用商陸的漿果染成濃艷的紅薔薇色。”她還用嚴肅的口吻宣稱:“像這樣讓人滿意的衣服,我以后絕對穿不到了。”(127)實際上,并非那件衣服本身讓貝基癡迷,而是它折射的美好時代讓她流連忘返。親手為他人紡織和縫制衣物,是彼此理解和信任的媒介,即使多年后斗轉星移、物是人非,記憶里依然充滿共同的情感。
貝基“老家”的人們詩意棲居,呈現出鄉村共同體的理想境界。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小說中的共同體》一書中指出:雷蒙德·威廉斯心目中的共同體無階級性(classless),它最適宜植根于遠離城鎮的鄉村(remote villages),所以他崇尚以哈代為代表的文學家們;而并不十分認同簡·奧斯丁和亨利·詹姆斯等作家,因為他們是士紳階層的代言人,不能夠表現真正的共同體(effective community)(Miller, 2015:3)。韋爾蒂曾被冠以“農業文學家”(literary agrarian)的標簽。比如學者格萊特朗德就強調,韋爾蒂對農村生活和大自然一往情深,崇尚傳統意義上的倫理觀和價值觀(Gretlund,1994:56)。盡管韋爾蒂本人并不接受“農業文學家”的頭銜,但她確實將許多故事和人物設置在鄉村地區,呈現家族和鄉鄰們的生命景觀,以此探索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樂觀者的女兒》中的“老家”奉行天然的情感結構和公共話語:“‘小伙子們’——總共有六個——為妹妹騎的小馬裝好鞍,然后跟她騎馬上了路。蘋果樹下,他們躺在毛毯和馬鞍上給她彈五弦琴。小伙子們給她講了很多故事,她都哭了,全是關于只有她和他們認識的人的故事。她如果沒哭,便會忍不住哈哈大笑。”(129)山居生活締造出親密無間的公共領域,人們在故事、音樂、眼淚、笑聲中共享人生,在相互關心和幫扶中趨向至善。這里沒有警察和法院等規訓機構,外來者只須拉響河岸邊柱子上的鐵鐘,便會有小船應聲前來迎接入村。鐵鐘也是人際溝通與合作的關鍵樞紐,任何緊急情況都靠它通風報信,援助和扶持一般會及時抵達。可見,山村踐行寬容友善(kindness)和齊心協力(mutuality)的交往習俗,與威廉斯倡導的共同體理念殊途同歸。
韋爾蒂既推崇世外桃源和農耕時代,又洞察到它在社會進程中的局限性,這是她抗拒“農業文學家”稱號的原因所在。她的長篇小說《三角洲婚禮》刻畫了眾聲喧嘩的費爾柴爾德(Fairchild)大家族,營造出頗具典型性的南方莊園生活(Manning, 1985:15)。它盛行精英主義和排外主義,欠缺開放性和創造性,致使很多人受到族群過度庇護,變得庸碌一生。《樂觀者的女兒》對“老家”的落后與閉塞也直言不諱:貝基的父親突發穿孔性闌尾炎,她歷經千辛萬苦帶他來到巴爾的摩醫院,卻為時已晚;她的母親猝然死去,當時身邊無人相伴,那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鐵鐘也未能發揮作用。韋爾蒂習慣將視覺藝術用于小說創作,認為攝影讓人去捕捉彌足珍貴的瞬間,寫作也同樣可以做到。她追隨貝基的回顧性視角,向世人展現遠離塵囂的南方神話,正是努力抓取飛逝的歷史瞬間,因為社會巨變的號角已經吹響。
2.2 現代化進程中的轉型焦慮
美國南方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莫過于南北戰爭,它徹底改變了南方的政治經濟和生活方式,令這一地區逐步走上現代化轉型之路。這場戰爭讓南方深陷傷痛,以至于一百多年后其子孫仍然銘記于心:“許多弗吉尼亞人和南卡羅萊那人在說到‘戰爭’的時候,還是指的南北戰爭,雖然已經發生過兩次可怕的世界大戰,他們好像還是無動于衷。”(湯因比,1986:91)1877年,海斯總統下令不再對南方實行軍隊管制,南北雙方達成妥協從而結束戰后重建。亨利·格雷迪(Henry Grady)以此為分界線,在1886年首創“新南方”一詞,提倡新南方信條來進行社會建設,呼吁農業的南方融入工業的北方。“新南方”的藍圖雖已構想,但舊南方的田園牧歌已經消逝,新南方的理想圖景尚未實現,南部地區依然百廢待興。實際上,南方的現代化之旅漫長而艱辛,遠遠滯后于美國其他區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型。在這一過程中,消費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風日盛,它們形塑著民眾的價值體系,也引領著他們的日常行為和命運走向。
韋爾蒂親身見證了這場歷史變遷,對鄉村共同體的遠去深懷感觸,對物質主義思潮不無擔憂。新南方倡導務實保守做派,糅合新興商業主義和傳統農業主義于一體。但到了1920年代,它打消了對北方工業文明的警覺,金錢主義勢頭越發明顯起來。而此時正值韋爾蒂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時期,她思索美國夢和消費主義等社會現象,為她日后書寫轉型焦慮主題奠定了基礎。她于1936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旅行推銷員之死》(DeathofaTravelingSalesman),描繪了進步浪潮中的小人物鮑曼。為了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存活,他不得不在疾病和寒冷中疲于奔命,最終凄慘地死去。這真實再現了新南方的商業化語境:眾多旅行推銷員開著貨車奔波在小鎮和村落,為大城市的總經銷商出售產品(黃虛峰,2007:166)。當社會崇尚物質主義,人們卻飽嘗文化貧瘠和精神失落之苦,就構成了卡萊爾所詬病的“現金聯結”形態,即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遭遇物化和異化,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系(Carlyle, 1927:195)。《樂觀者的女兒》以勞雷爾的年輕繼母費伊為主線,營造了一個物欲橫流的偽共同體,與滕尼斯視域中生機勃勃的真正共同體形成反差。這個偽共同體的成員們行事純屬利益驅動。年輕的費伊來自南方下層階級,幾乎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只能以婚姻為跳板獲取社會地位和舒適生活。而年逾古稀的麥凱爾瓦是南方貴族的后代,擁有書香門第之余,還是頗有名望的法官和政治家。如果說他對嬌妻寵愛有加,那么她對他只有索取和冷漠:在新奧爾良醫院,她咒罵病重的丈夫不帶他參加狂歡節,他術后不治身亡至少部分歸咎于她的虐待;在密西西比家中,她要求為他安排最昂貴的葬儀,并非出于深情厚意,而是通過購買行為產生炫耀性消費(Rozier, 2015:144)。費伊的同盟軍包括她父母家人、戴爾澤爾全家等群體,他們物以類聚、聲勢不小。費伊娘家人浩浩蕩蕩,不請自來地出現在麥凱爾瓦的葬禮上,個個性情粗俗、拜物成性。戴爾澤爾是麥凱爾瓦在新奧爾良醫院的室友,他一門老小都嗜好消費,對彼此則缺乏關愛和寬容,卻都與費伊一拍即合。可見,用金錢聯結的人際關系大同小異,無不以犧牲情感和德行為代價。
這個偽共同體追逐不勞而獲的財富,盡顯享樂主義風氣。殷企平指出:“討論財富問題,就是討論文化問題。”(2013:41)而卡萊爾和阿諾德等人“都對財富問題發表了深刻的見解,都對社會快速轉型過程中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脫節的現象表達了深深的憂慮”(2013:44)。《樂觀者的女兒》與此不謀而合,其財富議題圍繞房子展開,折射出美國南方文化變遷帶給韋爾蒂的危機意識,尤其是她對物質與精神失衡的考量。勞雷爾父母留下的房子承載著愛的記憶,一家三口的笑聲和讀書聲仿佛聲聲在耳。然而根據遺產繼承法,麥凱爾瓦的遺孀費伊一躍成為它的主人。費伊只看到它的實用層面和市場價值,完全無視其中的情感記憶和文化內涵。她對屋子里豐富的藏書毫無興趣,忌憚貝基與當地女性們的姐妹情誼,也敵視門前那些貝基傳下來的園藝成果。她占盡房前屋內的空間和物件,甚至不肯放過廚房里的木制小面板(breadboard)。這塊面板由勞雷爾摯愛的丈夫在陣亡前制作,由她深愛的母親使用并烹制美味佳肴,對勞雷爾來說意義非同小可。而費伊對烹飪一竅不通,對廚房里的器具“她只叫得出‘油炸鍋’這一個”,“她連怎樣把雞蛋的蛋白和蛋黃分開都不太會做”(99-100)。羅明斯認為,廚藝是當時南方女性展示自身價值的媒介,她們的秩序、忠誠、凝聚力在其中一覽無余(Romines, 1992:259)。費伊游離在勞動和奉獻的世界觀之外,卻對財富坐享其成,是功利型和物質型人群的生動展演。這類機會主義者在社會轉型時尤其狂妄,也活躍在南方作家群的小說里,比如福克納《喧嘩與騷動》(TheSoundandtheFury, 1929)中的杰生,麥卡勒斯《傷心咖啡館之歌》(TheBalladoftheSadCafé, 1943)中的李蒙,都因缺乏歷史擔當而進入不了有機而美好的共同體。
面對滾滾向前的南方歷史洪流,韋爾蒂始終秉持鮮明的道德立場。她在訪談中評價費伊“是道德敗壞之人”(Welty, 1984:227),足見她對精神文化的重視。這種理念也關照到她的真實世界中,變成她以知識分子身份處事的原則。她繼承了父母在杰克遜市中心的房子,后來無償捐獻給密西西比州政府,因為她認為房子屬于文學、文化和藝術,應該服務于大眾,而不是歸她一己所有。韋爾蒂是在呼喚新型共同體,身體力行地解構偽共同體,以此應對轉型焦慮引發的社會眾生相。
2.3 工業化背景下的共同體構想
韋爾蒂思索社會轉型之際的困境與出路,呼應了南方文藝復興運動的文化訴求。眾所周知,英國于19世紀早期和中期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不均衡的現象甚囂塵上,于是“英國狀況大辯論”(The Condition of English Debate)應運而生。其結果是建立了一套公共話語,呼吁人們重視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并想象工業化情境中如何建構共同體。卡萊爾、阿諾德、羅斯金、莫里斯等文化學者都參與其中,提出種種社會救贖之道。狄更斯、蓋斯凱爾、艾略特、哈代等作家也創作出一系列“英國狀況小說”或“英國工業小說”,形成蔚為壯觀的文學盛景。美國南方文藝復興運動也是一場大規模的文化反思和辯論,從1920年代開始一直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很多南方青年北上尋夢或歐洲留學,接觸到廣闊的現代主義思潮,得以用批判性眼光來審視南方現實,一大群“南方新現實主義作家”蓬勃而出。他們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共同體概念,但都立足于當下來回眸農耕時代,希冀在工業主義語境中建立和諧社會,與哈代等英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殊途同歸。無論是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還是波特的“米蘭達系列”,都以雄辯的文風建構精神大廈。韋爾蒂也是這支隊伍中的主力,她與卡萊爾等英國文人所見略同,采用工作福音、藝術福音、深度會話等策略,來構想美好生活和新型共同體,《樂觀者的女兒》就是這樣的典型個案。
這部小說視工作為精神支柱,認為它是人與自身、他人、世界產生文化認同的根基,與卡萊爾的“工作福音”理念異曲同工。卡萊爾所處的年代正逢工具理性當道,他提倡以工作福音來取代現金福音,激勵人們將工作當作幸福的源泉,以此抵御拜金主義的侵襲(唐立新,2017:160-161)。《樂觀者的女兒》中的勞雷爾正是經由工作治愈個體創傷,突破了外部環境的物化壁壘。勞雷爾痛失丈夫和母親之后不久,父親就娶了費伊,老夫少妻的格局引發街談巷議。勞雷爾的受傷心理與其說來自父親對年輕女人的獵奇,毋寧說源于費伊的投機行徑。于是勞雷爾離開了家鄉這塊傷心地,投入到芝加哥的工作中去療傷。小說沒有鋪陳她的紡織品設計事業多么成功,但開篇就讓她以知性高雅的中產階級女性形象出場:“勞雷爾·麥凱爾瓦·漢德是個四十五歲左右的女人,身材纖細,看上去十分文靜,頭發還很黑。她的衣服無論剪裁還是質料都很別致……”(3)。工作給予勞雷爾的踏實感一目了然,透露出她穩定的心理和經濟狀況。這印證了卡萊爾的論斷:工作是自我完善的必經之途,唯有如此靈魂和軀體才能趨于和諧(轉引自唐立新,2017:161)。勞雷爾因安葬父親再次回到家鄉,對故土的熱愛之情溢于言表。她的閨蜜們以及她父母的朋友們都主動前來,噓寒問暖、忙前忙后,大家齊心協力地完成了喪事。這種同舟共濟的工作倫理充溢著共同體情懷,她因深度溝通而緩解了喪父之痛。在費伊出門旅行后,勞雷爾獨自在父母房子里度過三天時光,她在各個房間里思緒萬千,其中就包括曾帶給她火光和溫暖的縫紉室。她孩提時喜歡坐在縫紉機前,用大人做衣服剩下的碎布拼成星星、花朵、鳥兒、人物等,這無形中培養了她的創造力,令她踏入與縫紉息息相關的紡織品設計行業。園藝、縫紉、烹飪都是締結女性共同體的勞動,比如絎縫節就承載了南方婦女的共同記憶:“縫紉是創造才華和姐妹情誼的物質體現。在絎縫節上,陽光和煦,婦女們帶上自制的點心,來到指定場所一起縫百納被,成為南方農村生活的獨特風景。”(黃虛峰,2007:105)韋爾蒂通過設計和縫紉等勞動意象,以及通力合作等勞動場景,將個體體驗匯入集體經驗,贊頌了工作福音引領的共同體理想,為身處變革中無所適從者提供精神支撐。
羅斯金和莫里斯等人推崇藝術福音,成為應對轉型焦慮、規劃理想生活的另一種共同體實踐模式,而韋爾蒂的藝術主張也與此吻合。塑造藝術型人物堪稱韋爾蒂的一大偏好,既與她出生于書香門第有關,也與她本人的審美情趣有關。《龐德之心》中一身詩意、不愛財富的丹尼爾叔叔,《金蘋果》中逃離世俗卻浪漫依舊的金·麥克萊,《六月演奏會》中教授鋼琴的藝術家艾可哈特小姐,都是韋爾蒂筆下藝術氣質濃郁的經典形象。他們把藝術作為凈化和感召靈魂的棲息地,自覺隔離到人心不古的氛圍之外。《樂觀者的女兒》呈現了一個“藝術之家”,勞雷爾本人、丈夫、父母皆書生意氣濃厚,是重精神、輕物質的典型家庭。其丈夫菲爾是建筑師,不但是設計房子的行家,還喜歡手工制作家庭用品。他在日常工作中獲得的成就感和喜悅感溢于言表:“我在把這些東西攏在一起的過程中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只要有這種熱誠和不倦的努力,用硬紙板也同樣能建造出不同的房屋來”(149)。這印證了羅斯金在《建筑的七盞明燈》(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中的藝術觀:建筑在人類藝術中最值得稱道,它帶給心靈的愉悅和滿足無法估量(2012:3)。將藝術奉為最高境界的莫里斯,也從古建筑中獲得感悟:它是對歷史精神的藝術傳承,能將過去、現在、未來融為一體(Morris, 1936:148)。小說中菲爾的建筑設計自然而然地融勞動、藝術、生活為一體,與羅斯金和莫里斯達成默契。藝術具有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如此強大,致使菲爾對家人傾注滿腔熱愛,更萌生熾熱的愛國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毅然奔赴太平洋戰場。藝術讓人摒棄功利主義思維,主動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靠攏,這在菲爾為國捐軀的壯舉中展露無遺。
韋爾蒂還把讀書視為重要的會話手段,用來形塑健康向上的公共價值觀,并走出狹隘的地方主義,彰顯世界主義文化立場。在美國南方工業化進程中,人們的休閑方式和娛樂品味被消費文化所侵蝕。以麥卡勒斯《婚禮的成員》(TheMemberoftheWedding, 1946)為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美國南方小鎮充斥著精神空虛之人,藍月亮酒吧里烏煙瘴氣、騷亂頻出,連穿軍裝的士兵都在酗酒和獵艷。《樂觀者的女兒》倡導以閱讀來充實大眾的業余時間,以家庭圖書館來充當親人間的公共領域,以此締結情感共鳴和文化歸屬。在勞雷爾家中,讀書是最好的對話和溝通模式:“深夜,她能聽到他們倆交替讀給對方聽的聲音,從不讓沉默將兩人分開或打斷他們,兩人的聲音匯成一個永不停頓的嗓音,在她傾聽時悄然把她籠罩起來……一直讀進她的夢境中。”(53)勞雷爾家圖書館既有《密西西比》和《密西西比法典》,也有《狄更斯全集》《簡愛》《丁尼生詩集》等。它們超越了美國南方的地域界限,參與異質文化的對話與交流,從而擁有植根地方的世界主義特征。讀書在韋爾蒂眼中是深度會話和深度溝通,它提升家庭和民族的文化素質,打破地方與國家、本土與世界的隔閡,形成多元文化認同與交匯。
3.結語
韋爾蒂的文學書寫植根于美國南方,又對異域文化兼容并蓄,其共同體意識為社會轉型焦慮提供解決之道。她人生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鄉度過,筆端流出的人物和場景也深具南方性,因而常被當作偏安一隅的地域主義作家。然而,她的價值觀卻超越了地理局限,與源自歐洲的共同體思想產生契合,形成極具開放意蘊的審美現代性。韋爾蒂關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焦慮,構想共同體來緩解文化危機。《樂觀者的女兒》告訴人們:農耕時代穩固的鄉村共同體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工業化背景下流動的共同體。不得不說,韋爾蒂具有“在居住中旅行”的全球化意識,這是她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不凡之處。
注釋:
①引文出自尤多拉·韋爾蒂:《樂觀者的女兒》,楊向榮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以下出自該著引文僅標明頁碼,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