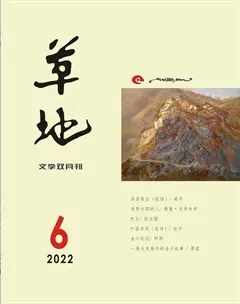吹貝
“小螺號,嘀嘀嘀吹,海鷗聽了展翅飛。小螺號,嘀嘀嘀吹,浪花聽了笑微微。小螺號,嘀嘀嘀吹,聲聲喚船歸啰……”幾乎每個70后甚至80后的童年,都是被《小螺號》這首兒歌吹亮。我至今還能在這首反復哼唱的兒歌記憶里,找回自己的天真與活潑。當時,只知道小螺號是一種樂器,可以吹出動聽音樂,而且來自大海。大海,對于生于深山峽谷的我而言,有著強烈的殺傷力,那是幾乎可以沖破大腦皮層的執著向往。
后來,終于去了大海,卻發現海灘上被海水卷來的海螺,不是每一個都可以吹出嘀嘀嘀或者嗚嗚嗚的美妙童音。最多能證實小螺號是海螺的一種。來到成都求學以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觀了成都永陵博物館,永陵地宮棺床上的石刻“二十四伎樂”給我極大的沖擊力,尤其是手持螺口、兩唇緊貼吹嘴的吹貝伎,讓我對童年愛不釋手的小螺號有了全新認識。
在永陵地宮棺床上,誕生于五代前蜀期間的吹貝伎,其貌似海螺的貝大有來頭,據說源自印度,早在中國北魏時期就盛行于宮廷,大唐時期更是宮廷樂隊常用的唇簧氣鳴樂器。
古代的貝,也是佛教的法器
東漢人許慎在《說文解字》稱:“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從此可知,貝是大海里的動物,而且曾作為貨幣(貨貝)通用于民間。
從骨刻文到象形字“貝”,可見“貝”是貝類動物的貝殼,后來泛指螺的貝殼。螺貝,就因海螺殼制而得名,也稱“螺”“海螺”等名。古人磨去螺殼尾端作吹口,螺腔為共鳴器,用雙唇為簧吹奏,貝或者螺貝、海螺就成為可以吹奏的樂器。
古代的螺(或稱貝),也是佛教的法器。用于法器的螺,也稱法螺。螺,漢語稱為貝、梵貝、螺號、法螺、玉螺等,藏語稱為東嘎、統嘎、董嘎爾等,今人作為普通樂器使用時常常稱為螺號或者海螺,一般只有用于佛教儀式時才稱為法螺。法螺,還是藏傳佛教的“八瑞相”之一,喇嘛寺必備的法器。 螺,這種佛家樂器起源于天竺(今印度),在南北朝時期隨著佛經一同傳入中國,并在北魏時期就常用于宮廷演奏。現今,位于山西大同堪稱皇家風范佛教藝術寶庫的云岡石窟,就雕刻有北魏時期的吹貝樂伎(又稱吹螺樂伎)形像。歷經北魏東魏的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卷五就記述了神龜元年(公元518年),胡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去向西域取經的故事。惠生是比玄奘(唐僧)還要早一些西行取經的高僧,說惠生初入烏場國(譯為烏萇國,今古印度國名,地理位置相當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斯瓦特縣)就看到了令人震撼的“吹貝”禮佛儀式,“國王精食,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已后,始治國事。”取經歸來的洛陽,很快成為一個佛寺林立、梵音裊裊的佛教圣地。然而因為兵變,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洛陽城內外的上千座佛寺在戰火中被毀大半。公元547年,楊衒之因公重返洛陽,目睹了洛陽崇佛的興衰,眼前是: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楊衒之之所以奮筆疾書《洛陽伽藍記》,正是因為他這年的觸景生情,以讓后人牢記洛陽佛寺盛衰這段歷史,“伽藍”是梵語“僧伽藍摩”的簡稱,意思就是佛寺。
在隋唐時期的十部樂中,第九部和第十部樂中已經使用法螺作為宮廷樂隊演奏配器,散見于西涼、龜茲、天竺、扶南、高麗諸樂。據《文獻通考·樂考十二》:“貝之為物,其大可容數升,蠡之大者也。南蠻之國取而吹之,所以節樂也。
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
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瑤池。
云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
相傳李白這首名叫《舍利弗》的詩,提到的法蠡,就是法螺。有唐詩研究專家稱,此詩是否為偽作存疑。有人還因此將此詩的作者,安排給了隋代的無名氏。無名氏,就是說不知道此詩作者是誰。但是,《舊唐書·音樂志》載:“貝,蠡也,容可數升,并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說明當時的大唐人愛把用于佛教音樂的貝(即法螺)稱為“法蠡”。而從此詩風格和大唐宮廷樂舞風格看,我以為《舍利弗》更像是出自李白的飄逸五言詩。因為酷愛音樂也親道近佛的唐玄宗李隆基,喜歡廣納外域音樂,甚至親自教梨園弟子教正曲法,壯大宮廷樂隊,時常在宮中命人吹法螺,在長安供奉翰林的李白就因此常被召之即來作詩附和。事實上,唐玄宗作曲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一首大唐法曲。此曲,改編自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進獻的印度《婆羅門曲》,并且直接吸收了印度風味的音調。
作為當時世界上國力最強的大唐,不論是李世民的貞觀盛世還是李隆基的開元盛世,皆有萬朝來拜進獻國禮的氣象,推崇佛教文化的太宗、玄宗,自然收到法螺等重要國禮。即使因安史之亂而大傷元氣的唐德宗貞元年間,也有南方驃國(今緬甸境內)所獻樂器,該國獻給德宗的玉螺以及樂曲,大都與佛教有關。白居易曾在《驃國樂》詩中提到玉螺這種佛教法器:“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踴。”
白居易這首詩很長,起句“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則以唱童謠般的歌聲說明玉螺,實為海螺。“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纊不塞為爾聽”,寫的是德宗的威儀。緊接著的“玉螺一吹椎髻聳”,是說充當吹螺樂伎的雍羌之子(一作弟)舒難陀兩唇緊貼螺口吹嘴,一吹出玉螺之聲,發髻就聳立起來,盡管形容稍顯夸張,但也把吹奏者用力鳴器的神態刻畫得栩栩如生。銅鼓一響,“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更是令星宿搖、龍蛇動。白居易是擅長以詩寫樂器的高手,不論是《琵琶行》還是《驃國樂》,總是如此傳神,總是如此夸張。只是此詩最后幾句“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不嘆。貞元之民茍無病,驃樂不來君亦圣。
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話鋒陡轉,歌頌的是德宗的見多識廣,感覺是在洗涮驃國人所進獻的樂器平淡無奇。白居易最后一句“不如聞此芻蕘言”,用典于《詩經·大雅·板》:“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啥意思?就是說所謂的玉螺等驃國樂器,如割草的芻,采薪的蕘,這些大唐普通百姓都知道。
唐詩的貝,多是裂開的經文
正因為多個大唐皇帝對外域音樂文化的廣泛吸納,中外音樂交融的景象遍布朝野,大唐詩人們也是大開眼界,各種樂器詩層出不窮。
其中,寫貝或者寫螺的詩,雖然不如笙簫、笛篪那么多,也沒有白居易把琵琶寫成千古絕響的吹貝詩,但也留下了這種音樂文化交流的厚重印跡。
最對我的口味,與貝有關的詩,是有著“詩囚”之稱的孟郊,寫的《贈文應上人》(一作贈高僧),看似漫不經心,卻勾勒出一個清新的畫面:棲遲青山巔,高靜身所便。
不踐有命草,但飲無聲泉。
齋性空轉寂,學情深更專。
經文開貝葉,衣制垂秋蓮。
厭此俗人群,暫來還卻旋。
與賈島齊名,被蘇軾點贊為“郊寒島瘦”的孟郊,屬于中唐時期的重要詩人,詩風追求復古思潮的杰出代表。現存詩歌不多,僅有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詩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此詩中的“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極具畫面感,至今仍覺膾炙人口。孟郊屬于大器晚成的詩人,性格孤僻,命運坎坷,兩試進士而不中,46歲奉母之命第三次應試才考中進士。然而仕途多舛,晚年喪子之痛,加上生活貧困,孟郊的詩因此多是充滿中下層文人窮愁困苦的情緒,反映現實生活,追討貧富不公。另一首代表作《寒地百姓吟》,有一句“寒者愿為蛾,燒死彼華膏”,可以說,孟郊是繼杜甫之后又一個用詩歌揭露社會貧富不均、苦樂懸殊矛盾的詩歌戰士。
孟郊寫詩,喜歡摳字眼,他的《送盧郎中汀》“一生空吟詩,不覺成白頭”,就述說了自己對詩的癡迷和專情。而在寫貝的《贈文應上人》這首詩,依舊可見孟郊的白描功底。 “經文開貝葉,衣制垂秋蓮”,短短十個字,就線描出一幅得道高僧醉心于誦經念佛的生動畫面。此刻,刻在貝葉上的經文到底是什么經,讓人浮想聯翩。“不踐有命草,但飲無聲泉”,則是借助高僧的恬靜生活,生發自己貧困生活遭遇的共鳴。
孟郊此詩中提到的“貝”,屬于貝葉經。而從印度流傳于大唐被稱為法螺的法器“貝”,不僅游走于宮廷,成為皇帝妃子們享樂的吹奏樂器,而且廣泛運用于佛教文化極其鼎盛的大唐寺院。
嗚嗚嗚……在寺院里吹出的法螺之聲,格外空闊而莊嚴。《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說:“若加持螺,諸高處望,大聲吹之,四生之眾生,聞螺聲滅諸重罪,能受身舍己,等生天上。”其實,法螺作為佛教高僧舉行宗教儀式時吹奏的一種唇振氣鳴樂器,由來已久。傳說釋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轉法輪時,帝釋天等曾將一支右旋白法螺獻給佛祖,從此右旋白海螺即作為吉祥圓滿的象征在佛教中廣為應用。楊炫之《洛陽伽藍記》還載:“烏場國有早晚吹法螺以禮佛的習俗。”北魏時期的洛陽,受此影響,一度梵音繚繞,成為佛教圣地。而在唐高宗李治時代,大唐藍谷沙門慧祥所著《廣清涼傳》,則是一本關于五臺山傳承印度大乘佛教主要經典《華嚴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的最早專著,此書記錄五臺山大孚靈鷲寺啟建法會時,即以法螺、箜篌、琵琶齊奏。從《洛陽伽藍記》到《廣清涼傳》相互印證,可見用于佛寺法會的大唐樂器眾多,不僅有法螺,還有箜篌與琵琶。法螺,隨印度傳入中國,迄今不論是藏傳佛教還是漢傳佛教,甚至在中國的蒙古族、滿族、納西族、傣族等民族均廣泛采用。那些從貝殼上裂開的經文,在華夏大地召集內心不安的人,讓貝成為很多人安靜內心的至寶。而在信仰者的心中,聞聽吹貝之音,眾生皆可消除罪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渴望在寺院聽貝之音,這種信仰,在唐詩中的《題法華寺五言二十韻》可以精準找到唐人的印記。此詩,出自當過宰相的大唐詩人李紳之手筆。此詩最后幾句,寫出了唐人在寺院里誦經念佛,垂聽吹貝之音的場景:“貝葉千花藏,檀林萬寶篇。坐嚴獅子迅,幢飾網珠懸。極樂知無礙,分明應有緣。還將意功德,留偈法王前。”李紳與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也是新樂府運動的參與者。他最著名的詩句,是《憫農》詩二首其二:“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句“粒粒皆辛苦”,淺顯易懂,直擊人心,傳達了李紳心系天下蒼生的情懷,雖有說教的味道,但也是意蘊深遠的格言。這也是李紳親近佛教文化時常出沒佛門,而透射出的“利益眾生”的佛家善緣思想。
然而,人生如夢,萬法皆空,一尊還酹江月。對于侍奉過唐高宗李治、武則天、唐中宗李顯的三朝元老沈佺期來說,更是不堪回首的夢。他18歲考中進士,就一飛沖天成為皇帝秘書,進入唐王朝的最高權力圈子,跟隨皇帝出巡做一些應制詩文,以歌時世。后來一度官至中書舍人,貴為太子少詹事,連太子家務事都可管理。可是沈佺期仍然遭遇過被人彈劾貪污甚至眾人紛紛落井下石這種揪心事,被排擠下放,無人求情幫扶。沈佺期曾在《被彈》一詩中,用“萬鑠當眾怒,千謗無片實。庶以白黑讒,顯此涇渭質。”來表達自己無處伸冤的苦楚。擔任太子少詹事時,沈佺期就做了一個夢,這個夢也跟傳說中的貝葉經有關。為此,他還專門寫了一首詩,叫《奉和圣制同皇太子游慈恩寺應制》:肅肅蓮花界,熒熒貝葉宮。
金人來夢里,白馬出城中。
涌塔初從地,焚香欲遍空。
天歌應春籥,非是為春風。
沈佺期陪唐中宗時期的太子游慈恩寺,看見法器聽見梵音卻走了神。在莊嚴肅穆的佛門圣地,金碧輝煌的菩薩面前,沈佺期做了一個夢,夢見金人來侵擾大唐邊疆,他騎著白馬出城迎戰。這個夢,緣起于沈佺期是一個典型的佛教徒,大唐時期的眾多塔寺,他都一個一個虔誠燒過香,求過菩薩。在沈佺期看來,這個夢來自天上的神靈諭示,而且是菩薩被他的誠心打動的結果。《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盡管沈佺期明知是夢,但他找到現實遭遇帶不來的寄托,也就是佛教說的“以假為真”。顯然,慈恩寺中的法器“貝”之音,又一次裂開經文,打開了沈佺期一度內心陰寒的敞亮之門。
在唐詩中,寫“貝”的詩,也有苦兮兮的作品,即杜甫在500字超級長詩《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中的貶官感慨:“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弦。”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同是宰相房琯門下的嚴武與杜甫相繼被貶為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刺史和華州司功參軍,杜甫的詩友賈至這一年也被貶為岳州(今湖南岳陽市)司馬。三人原本是唐肅宗李亨的御前近臣,突然遠離絲竹管弦遍地的長安,都非常郁悶。可是杜甫還沒有心情寫這種郁悶,因為安史之亂帶來的戰亂正愈演愈烈,他得先寫觸目驚心的“三吏三別”。到了第二年辭官去秦州(今甘肅天水市)遠游,閑下來了,杜甫為了發展和鞏固與嚴武、賈至的友情,才作了《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此詩對嚴武、賈至的往昔友情表達五味雜陳,有敘舊、懷念、感傷、勉勵多種情分。“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弦”,則是他們一起在宮廷賞樂的懷念與感傷,因為皇帝身邊像貝的文采一樣美麗的織錦不會停下來,而哥們三個一起聽過的琴弦已經斷了。杜甫除了傳遞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哀怨,還表明自己因仕途失意而欲歸隱山林的心跡。如此的美麗貝錦和斷裂琴弦,形成巨大心理反差,看得出杜甫此刻真的心灰意冷,看淡名利了。
永陵的貝,絲綢之路的結晶
貝,這種響徹大唐宮廷和寺院的嗚嗚之聲,又是何時流傳到成都?前蜀皇帝王建死后留下的永陵石刻“二十四伎樂”,其中的吹貝伎固然是唐五代時期法器“貝”在成都留下的結晶,但在此前后均有來自印度的法器“貝”走來的痕跡。我仔細打量著永陵石刻吹貝伎,眼前只有凝固的貝音,模糊的貝殼。惟有唐詩,可以解密。
在唐玄宗時代,有一個能書梵字兼通梵音的成都人,叫苑咸。歐陽修撰寫的《新唐書·藝文志》,以及清朝人編寫的《全唐詩》皆注,云:苑咸,成都人。大唐詩人王維曾在唐玄宗天寶五載(公元746年)或六載擔任庫部員外郎時,作詩贊美過時任司經校書中書舍人的苑咸。詩名很長,是《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為之贈》: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為郎典石渠。
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
楚詞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辨魯魚。
故舊相望在三事,愿君莫厭承明廬。
王維詩名提到的“苑舍人”,即苑咸。苑咸,工于詩,思想上崇奉佛教,且佛學造詣精深,更重要的是很會為人處世,先后得到兩任宰相抬愛。仕途之路上,苑咸前期受到著名宰相張九齡的賞識,后期又與關涉大唐政治盛衰的關鍵人物李林甫關系很鐵,一度被視為右相李林甫的心腹。文學之路上,因為身居高位,苑咸常與盛唐大詩人王維、盧象、崔國輔、鄭審酬唱詩歌,關系頗為親密。王維戲贈苑咸的此詩提到的“貝葉經”,素有“佛教熊貓”之稱。這種寫在貝樹葉子上的經文,即貝葉經,多為用梵文書寫的佛教經典,還有一部分為古印度梵文文獻,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出生于成都,走紅于長安的苑咸,如何成長為一個能書梵文兼通梵音的高人?
在天寶六載前后,苑咸寫了一首《酬王維》,看似譏笑王維年老官卑,表達有援手之意,實際上也傳遞了自己書梵字通梵音的心得。
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
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
為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推間氣賢。
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
可是,王維并不買這個人情,倒不是他不懂事,腦殼木。
同樣精通佛學,人稱“詩佛”的王維,早就習慣了過自己亦官亦隱參禪悟理的日子。佛門中有一部《維摩詰經》,是維摩詰向弟子們講學的書,王維很是仰慕維摩詰,所以自己名為維,字摩詰,號摩詰居士,正是向維摩詰致敬。面對苑咸的好意,王維也懂,但不能直接拒絕,畢竟苑咸是禁絕請托人情的右相李林甫之親信,他也惹不起權傾朝野的這個宰相,于是就回贈了苑咸一首《重酬苑郎中》表示婉拒:“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慚未報主人恩。草木盡能酬雨露,榮枯安敢問乾坤。仙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斷掃門。揚子解嘲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
說起李林甫,我曾因為創作杜甫蹤跡史詩歌傳記《秋風破》而研究杜甫詩歌期間,內心非常憎恨此等小人。因為杜甫幾次應試求官“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都在唐玄宗面前以“野無遺賢”為由把杜甫拒之官門外。但是,后來研究成都人苑咸,尤其是苑咸之孫苑論于唐憲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撰寫的《苑咸墓志》,又推翻了后人對李林甫嫉妒人才的固化認識。2002年在洛陽出土的《苑咸墓志》(全名為《唐故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安陸郡太守苑公墓志銘并序》,題“遺孫朝議郎前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論撰”)就說:“天寶中,有若韋臨汝斌、齊太常浣、楊司空綰數公,頗為之名矣。公與之游,有忘形之深,則德行可知也。每接曲江,論文章體要,亦嘗代為之文。洎王維、盧象、崔國輔、鄭審,偏相屬和,當時文士,望風不暇,則文學可知也。右相李林甫在臺座廿余年,百工稱職,四海會同。公嘗左右,實有補焉,則政事可知也。”苑論,是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癸酉科狀元及第,同科進士三十二人中還有柳宗元、劉禹錫等后來的詩壇名家,但此時李林甫已經去世多年,他毫無必要討好前朝宰相李林甫,這段涉及李林甫的為官用人一面描述可以說比較客觀。
苑咸之后,宋人歐陽修、宋祁所撰的《新唐書》,在“南蠻傳”章節提到有“貝”等緬甸(古驃國)法器路過成都。書中稱:“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驃國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大抵皆夷狄之器,其聲曲不隸于有司,故無足采云……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絳粉。”也就是說,白居易后來在長安所寫《驃國樂》一詩,提及驃國獻給唐德宗的玉螺,正是歐陽修《新唐書》談到路過成都的法器“貝”。驃國人來獻樂,路過成都,為什么會允許韋皋“復譜次其聲”?因為韋皋時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唐德宗御前紅人,外放成都鍛煉高達二十一年頻頻被加官進爵的南康郡王。驃國人欲進京師長安,必先過韋皋這一關。韋皋的確事事為主子著想,在蜀地任職二十一年,不惜聲名以加重征收賦稅來確保按月向唐德宗進奉錢財,維系德宗多年委以重任的恩典。這一次,哪怕是外國人給主子敬獻器樂和樂曲,韋皋也是事必躬親,詳細整理、記錄了驃國樂曲。對驃國樂舞和樂器感到新鮮奇異的韋皋,甚至還命畫工畫下了驃國的舞姿和樂器,八百里加急送往德宗宮廷,以便德宗提前掌握驃國音樂,并在驃國使者悉利移城主舒難陀在長安正式獻禮時以顯大唐國威。如此膽大心細的韋皋,自然也把來自緬甸的國樂留給他所治下的成都。
由此可見,前蜀皇帝王建在成都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獲封西平王、蜀王,以及后來自己建國稱帝,那些在馬背上指點江山在酒杯里對酒當歌的日子,都有螺可吹,有貝可賞,有吹貝伎可樂蜀宮。當然,王建到成都寺廟里聽吹貝伎吹法器“貝”,則必須嚴肅一點。貝也好,包括笙、簫等大唐樂器,在蜀地繁榮,除了韋皋留樂之功,還跟史載成都是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的起點有關聯。驃國人必須經過成都,走蜀道去長安獻國樂,也是因為走這條絲綢老路更順溜,天府之國的蜀人樂舞細胞發達,順便還可以切磋切磋手藝,停腳歇一歇。永陵的貝,也可以說是絲綢之路上音樂文化交流的結晶。而“貝”這種也稱法器的樂器,早已在成都蔚然成風,還可從杜甫“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云”這些詩句中找到氛圍或影子,因為先于王建入川的杜甫對成都音樂繁盛的描述,是他親耳所聞親眼所見。
回頭再看凝固在永陵石像上的吹貝伎,她固然無法再發出大唐或者五代前蜀時期的嗚嗚嗚的貝之聲。但是,我似乎還可以從唐詩里的玉螺或者法蠡想象貝的神秘之音。要不然,就再一次像童年一樣,脫口而出一首《小螺號》,唱響螺貝的大唐法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