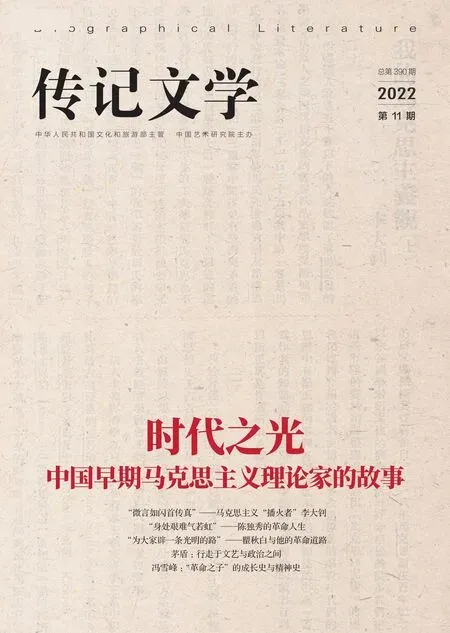消解權威與制造真實
——論朱利安·巴恩斯的實驗傳記
楊亞楠 梁慶標
小說家轉向傳記寫作,用小說文體對歷史、傳記寫作進行拆解或顛覆,是英國當代文壇的重要現象。朱利安·巴恩斯是其中一個典型,其兩部實驗傳記《福樓拜的鸚鵡》(1984 年)與《時間的噪音》(2016 年)堪稱代表。《福樓拜的鸚鵡》主要記述虛構人物布雷斯韋特對真實作家福樓拜進行追憶和“追蹤”的過程,虛構人物和傳主的人生相互分解又相互融合。《時間的噪音》記述了蘇聯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的三個重要時空點:“在電梯旁”“在汽車里”“在飛機上”,重心在其政治遭際下的藝術生涯上,但是虛構與回憶錄同時進行,是作者對傳記或歷史真實性尺度的切實思考。同時,巴恩斯上述傳記中的自傳成分與其自傳《沒什么好怕的》(2008 年)也達到了很大程度的契合,實驗傳記中的宗教、死亡、藝術等觀念的建構與自傳形成了對話模式。
漢密爾頓將《福樓拜的鸚鵡》定義為“惡搞傳記”,稱巴恩斯那令人著迷的以一種半嘲弄半嚴肅的筆調完成的《福樓拜的鸚鵡》吸引了法國解構主義者,一定程度上在對傳主進行諷刺[1]。這表明巴恩斯的實驗傳記超出了傳統傳記的倫理限制,并且在后現代文學語境中維護了作家的游戲式、創造性主體位置。這其實是20 世紀以來西方傳記文學變革的體現,伍爾夫、毛姆、伯吉斯等作家都高度重視傳記寫作,在賦予傳記魅力的同時也形成一股巨大沖擊力,將傳記的真實性推到了風口浪尖,尤其是在強調史實性的傳記中加入想象元素。比如伍爾夫的《奧蘭多》表明現代派傳記向傳統傳記發出了挑戰,她為真實的薇塔·薩克維爾·韋斯特作傳,卻虛構了幾百年間不斷復活的百變傳主“奧蘭多”,以虛構人物演繹真實人生。與之相應,朱利安·巴恩斯是傳記實驗的后起之秀,他運用思想實驗和高超的藝術技巧對傳記真實、權威觀念進行消解,進而建構了更具主觀性的真實理念,對其后的傳記寫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值得深入分析。
消解權威:巴恩斯的傳記敘事實驗
漢密爾頓視巴恩斯為20 世紀后期以來傳記“新方向”中的一員,強調他對傳統頌體、實錄傳記的反思和新傳記理念的建構,即譴責、審視、解構并重建過去某個人的生活[2]。巴恩斯拋棄了凸顯偉人典范、追求客觀全面等經典傳記的特征,轉而剖析傳主的不同自我,且有意增添想象與虛構成分,傳記所代表的歷史真實與解釋權威在此時被解構,這尤其體現在他對“大師”福樓拜與肖斯塔科維奇等形象的重新審視與塑造之中。
追憶福樓拜的傳記甚多,但傳記家各自的寫作姿態不盡相同。李健吾的《福樓拜評傳》更多是對福樓拜作品進行評論解讀,以個人情感填充單薄的生平記述,難掩仰慕之情;左拉的《法國六文豪傳》以福樓拜逝世為緣起將其分為“作家”和“人”進行追述,字里行間盡是崇拜之感;特羅亞的《不朽作家福樓拜》更似傳統形式的傳記,以時間順序記述福樓拜的生平,大量引用書信和回憶錄以塑造其作家身份,較為客觀真實。而巴恩斯在作傳形式上更為跳脫,其年表、文學評論、敘述視角任意轉換等作傳技巧都與傳統傳記格格不入,其獨特性主要體現在有意使傳主“降格”,拆解身為作家的偉大形象,這是其傳記實驗的突出表現之一。作為同時代好友,左拉在《法國六文豪傳》中對福樓拜的形象有如下描述:“居斯塔夫·福樓拜身材高大,天庭飽滿,長長的髭須遮擋著有力的下顎,對我們來說這是思想家和作家的出色形象。”[3]巴恩斯卻寫道:“福樓拜是一個巨人:大家都這么說。他像一個身材高大魁梧的高盧人的酋長超過所有人。然而他只有六英尺高。”[4]“六英尺高”只是一個普通法國人的身高。巴恩斯還提到,布雷斯韋特參觀主宮醫院博物館時,驚訝于青年福樓拜到了中年就變成了“大腹便便”的小市民,普通身高與“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形象顯然有意在顛覆讀者的閱讀期待,而巴恩斯極盡諷刺、刻意制造與傳統認知的沖突以消解其“巨人”形象。
葬禮上的“棺材事件”是有關福樓拜的傳記都會敘述的插曲,但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也顯示出傳記家觀念上的不同。作為見證者的左拉如此目擊了“棺材事件”:“當人們將棺材下到墓穴時,棺材太大,是個巨人的棺材,怎樣也放不進去。”[5]這一窘境之后,“留下我們的‘老人’在那里,斜斜地放進泥土里。我的心都碎了”[6]。左拉以棺材作為隱喻維護福樓拜的“巨人”形象,對此感到悲挽和痛惜。特羅亞在此事的記述上進行了更有意味的補充,“笨手笨腳”還“一邊罵罵咧咧”[7]的墓工致使棺材卡住,以及親友敷衍和不敬的行為,可真是“既滑稽又悲愴”[8]。生前孤高、冷峻的“不朽作家”身后卻只能任人擺布,極具戲劇性。而李健吾親臨墓地時也表示:“這不是憂郁的,這是殘忍的,殘忍的,殘忍的。”[9]巴恩斯則將“棺材事件”歸罪于身為“出名吝嗇的種族”[10]的諾曼掘墓人的偷工減料,但也是對這位諾曼底人福樓拜自身的暗諷,而“警戒隊的士兵使《包法利夫人》書中的最后一行發出滑稽可笑的光彩”[11]一句,則嘲諷了福樓拜獲得原本反對的榮譽稱號這一事件,“文學巨匠”以這樣尷尬的方式辭世實屬諷刺。相比之下,巴恩斯好似把“棺材事件”當作“笑談”來譏諷社會與人生對福樓拜的嘲弄,如此諷刺并不是攻擊和詆毀福樓拜,而是借拆解其“巨人”形象以質疑和挑戰頌揚式傳記之真,以消解既有標準傳記中確立的“真相”。
巴恩斯的創造性還體現在敘述角度的轉變上。巴赫金將音樂領域的概念“復調”、“多聲部”運用到文學批評實踐中,強調作品中多種聲音和意識存在的復雜性。就《福樓拜的鸚鵡》來看,首先是以敘事主人公“我”為第一視角,隨即轉向福樓拜本人及福樓拜作品的評論者,甚至給予福樓拜的情人高萊女士第一人稱“我”出場的特權,作者巴恩斯本人也忍不住從背后站出來發聲,各發聲主體獨立存在又相互對話,旨在從不同敘述視角建構福樓拜身份的多元性。《時間的噪音》的作傳視角也極具創造性,作者以第三人稱塑造肖斯塔科維奇,但行文卻又是以傳主自我回憶錄的形式進行,借此使其展開自我審視,虛構的聲音與傳主的聲音形成了交互對話。這種“復調”視角打破了傳統傳記的單一視角形式,致力于構建一種多角度敘述的作傳模式,凸顯了傳記中的敘述多主體性狀態。
奈德爾在談到傳記實驗時指出:“閱讀當代傳記可以發現構造人物生平的方式:不是依據時間或歷史,而是依據模式或空間。”[12]《福樓拜的鸚鵡》就具有碎片化敘事特征,如“福樓拜的動物寓言集”部分用動物來表現福樓拜性格的多面;“指控種種”歷數了文學評論家對福樓拜的指控;年表、試題、詞典等高妙的拼貼戲仿,則試圖將福樓拜的“惡習和美德”一網打盡。另外,巴恩斯傳記實驗的亮點更在于對“戲仿”技藝的巧妙運用,“戲仿似乎為審視現在與過去提供了一個視點,是藝術家能夠從話語內部和話語對話,卻又不完全同化。”[13]《時間的噪音》之標題取自俄羅斯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回憶錄《時代的喧囂》,與表達曼氏強烈抗議的“喧囂”不同,戲仿而來的“噪音”在肖斯塔科維奇時代有了新的內涵,“噪音”被視為肖斯塔科維奇隱忍求生的作曲生涯,這更表明肖斯塔科維奇的處境更加艱難,其性格值得同情,當“自我保護的本能早已讓位于美學時”[14],卑微求生的懦夫也具有了英雄的另類色彩,巴恩斯一面憐憫、一面深受這種“藝術至上”觀念的感染,并以對照戲仿的方式予以凸顯。
巴恩斯亦以對自傳的否定強化對傳記文體的懷疑,即否定了《沒什么好怕的》一書的自傳屬性:“這不是我的自傳,也不是對我父母的探討,也不是家庭秘密的揭露。”[15]并且所有的回憶都有相同的基調:似乎是如此,但是不能確定。作者在此刻意制造記憶與真實的沖突,事實上就質疑了菲利普·勒熱訥所強調的自傳作者保證所述之事絕對真實的“自傳契約”,表明傳統文類難以作為文體的評判標準,傳記很難也不應當被如此拘束,事實的開放性與文體的混雜性當受到高度重視,這實際是他進行傳記戲仿、混溶的主要意圖。引申而言,化身傳記家的文學家巴恩斯也可被視為當代傳記中的“噪音”,其實驗傳記是較于傳統傳記的噪音,是作為一種異質思想對文類權威的消解,而且也因此贏得了傳記家與批評家的高度重視。
重構傳主與制造真實
巴恩斯在實驗傳記中進行了大膽激進的探索,但一系列的作傳實驗都是為消解單一、絕對的歷史真實與文類權威,而并非走向絕對虛無,事實上他從對傳統傳記的反叛又延伸到對傳主身份的重構之中。莫洛亞認為:“傳記不僅僅是個‘和歷史有關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倫理問題和美學問題’。”[16]傳記要求倫理意識和審美意識的融匯,它并非簡單地羅列事實,而是以一定的社會觀念來處理和解釋事實,并賦予這一過程以藝術性。
巴恩斯從消解傳統真實觀出發,但從未放棄對更為復雜多元的“真實”的覓尋。首先是文本之外的身體力行,其傳記寫作引鑒了福樓拜的多部作品、回憶錄、信件以及各類文獻,其目的是有據可依。他也實地走訪了魯昂以充實自己的旅行見聞并收集福樓拜的逸聞趣事,作品中化身“歷史偵探”的布雷斯韋特也從未停止對福樓拜進行搜證,試圖最大程度地呈現福樓拜的多元形象。《時間的噪音》也參照了很多經典文本及對作曲家兒女的采訪錄等,并將個體置于宏大的歷史語境下,竭力在虛構的過程中無限向真實靠攏。其次是在文本之內對真實的追尋,《福樓拜的鸚鵡》中以“鸚鵡”為象征之物展開“尋真之旅”,這種對真實“鸚鵡”的追尋欲求“表現為一種對真相的執著的渴望”[17]。巴恩斯認為:“我們必須相信百分之四十三的客觀真實總比百分之四十一的客觀真實好。”[18]也就是說,他也并未放棄對相對意義上的歷史真實的探求,對“人物的描繪方式支持了敘述者對歷史事實的解釋”[19],或者說,他要呈現的更多是傳統認為的真實事件中的矛盾、斷裂之處,而這恰恰是更高意義上的真實,借以剖析人們在真實面前的各種姿態。
《福樓拜的鸚鵡》中就有諸多模糊或者相互矛盾的描寫。巴恩斯談及福樓拜對鐵路的態度是“他憎恨這種發明”[20],但鐵路無疑為其戀情提供了便利,所以“鐵路對居斯塔夫來說是有價值的:他不用多大麻煩就可以往返芒斯特”[21]。鐵路一定程度上是資產階級的隱喻,讀者也大多來自這個階級,然而巴恩斯卻認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夢想也是可笑的,這表明他同時憎恨著兩個階級。談及福樓拜與高萊女士的關系時,巴恩斯寫道:“她曾竭力誘使居斯塔夫與她結婚。”[22]然后,又以高萊女士的口吻回應道:“我不需要居斯塔夫走進我的生活中來。”[23]傳記不斷同時為讀者描述出充滿矛盾沖突的多面福樓拜,似乎很難為其定性。也就是說,巴恩斯并不追求最終定論,其筆下的福樓拜自始至終都是矛盾混合體,意在強調傳記應該達到具有張力的多重自我的人物描述,這更多也反映在人們對傳主的不同態度之中。
巴恩斯擅長以這種多元化聲音的建構來重構傳主身份。首先,在《福樓拜的鸚鵡》中,多種敘述聲音的存在揭開了福樓拜不確定的面紗,追尋者布雷斯韋特、情人高萊以及文學評論家等多種敘述角度,及“年表”“詞典”“動物寓言集”等多種敘述模塊,看似無比豐富翔實卻內含沖突,始終沒有建構出一個整體的福樓拜形象,使其更加真偽難辨。其次,《時間的噪音》中的藝術拼盤建構出了肖斯塔科維奇的意識變化,如莎士比亞戲劇,普希金、契訶夫的名言語錄等,都以藝術隱喻表現個體的真實心境,但零散的拼貼材料沒有給出最終的解釋意義,而是追索人物的意識流動來表現客觀世界。巴恩斯在《時間的噪音》的“作者按”中寫道:“關于自己的生活,肖斯塔科維奇有多重敘述。”[24]而肖斯塔科維奇去世后也被東西方陣營各取所需,并無確定的身份定格,不同的主體追尋不同的“真相”。巴恩斯呈現了福樓拜撲朔迷離的形象,且在肖斯塔科維奇“英雄”和“懦夫”的身份中周旋,因為“任何線索都不會有一個終端,猶如無法徹底展開的蛛絲”[25]。人物處于一種不斷變化、游離的身份狀態之中,這種與官方傳主身份定位的斷裂就意在建構一種具有個體差異性和認知主體性的“真實觀”。
巴恩斯擯除宏大敘事,盡可能謹慎、細微地探察歷史,聚焦真實的結果卻又是“曖昧”的:“也許它就是它們中間的一個。”[26]這表明缺席又在場是真相的最終宿命。“拖網里滿了,傳記作家把拖網拉起來,挑選、扔回大海、貯藏、切片以及出售,等等。然而,想一想他沒有捕捉到的:總是大大超過這些已捕獲到的。”[27]所以“真相”不能在檔案和傳記中找到“標準答案”。在巴恩斯的敘事中,作為傳記第一倫理的“真實”被重新定義,語言層面的指涉已經不能訴出真正的真實,“真實”是一種主觀立場與“詩性智慧”的復合體。巴恩斯的傳記反復敘說“歷史真實”是“人的真實”,“人類的內心和情感始終是他作品關注的對象”[28]。他在傳記寫作中極為關注個體的倫理困境和道德抉擇,這一潛在世界無比復雜,往往呈現出建構者、解讀者自身的意識投射。他在《沒什么好怕的》中寫道:“人們是靠記憶,而不是靠真相生活的。”[29]記憶機制的不穩定表明“真相”具有主觀性:“當那些模糊的情景果然變得清晰可見時,我們想象這是我們自己使這一切變成這樣的。”[30]英國小說家拜厄特也認為:“客觀性是一個早被炸毀而且解構了的概念。”[31]類似地,巴恩斯以傳記為標本來重新審視真實與生命,傳記實驗的表象之下是對個體生命復雜性、主客關系的關切與闡發,尤其是作為眾生之中的獨特個體,他時不時在文本之內“暴露”自己,實際是在以他者為鏡像,有意建構從屬于自身的“主體性”。
巴恩斯實驗傳記的“主體性”
從現代傳記理論來看,“作傳之時,內容與形式的調整是為其在文本中建構自傳身份服務”[32]。也就是說,傳記家都在或隱或現地投射自身的主體性,傳主成為傳記家表現自己心理或者精神的載體。從這一角度看就不難理解,福樓拜和肖斯塔科維奇在巴恩斯筆下得到再度塑造,并與傳記家達到了精神上的某種契合。
在風趣又隨性的技巧實驗背后,其實有一副憂慮的巴恩斯面孔,即宗教信仰的倒塌及對死亡的恐懼所帶來的生存焦慮。巴恩斯或布雷斯韋特為何追尋福樓拜的鸚鵡呢?在福樓拜的小說《一顆淳樸的心》中,一只鸚鵡成為費莉西泰生命最后唯一的“神”,但在福樓拜死后,當被視為“神”的鸚鵡出現了幾十只時,即鸚鵡被大量復制而非原件時,所謂唯一的“上帝”就變得模糊甚至不存在了。福樓拜在小說中對基督教史進行了戲仿,而巴恩斯借助這種戲仿間接地否認了上帝的權威性。二戰后,殘酷的戰爭和失望的現實使宗教救贖頻頻失信,巴恩斯敏銳地感受到了這種焦慮并想要告訴讀者:“沒有上帝,沒有天堂,沒有來世。”[33]其小說《10?章世界史》[34]也展示了宗教的荒誕世界,解構了基督教世界對美好天堂的允諾;《倫敦郊區》[35]中對死亡的恐懼亦暗示了宗教救贖的瓦解,消解了“上帝”在人間的權威;《時間的噪音》同樣是在戲仿這個主題:上帝是不存在的,人不會被救贖也終究會死去,肖斯塔科維奇也只能靜待死亡而不是等待上帝眷顧。上帝的祛魅化消除了人類存在的神學意義,由此“對死亡的恐懼取代了對上帝的恐懼”[36]。
如何面對放棄宗教之后的死亡恐懼所帶來的生存問題,成為巴恩斯作傳的契機。巴恩斯在《沒什么好怕的》中對死亡表示“虛位以待”[37]而在他看來,福樓拜“凝視墓穴”也由來甚早,從孩子式的好奇到青年的冷靜再到中年的躲避,然而,“‘凝視墓穴’并沒有為福樓拜帶來心靈的安寧,帶來的只有衰弱的神經”[38]。大作家也不曾想到自己的“墓穴”如此草率,左拉羨慕的所謂中風“好死”在巴恩斯眼中卻不以為然,因為他一直懷疑“死的結果”和“死的過程”哪個更讓人恐懼。見證了親人們的死亡喚起了巴恩斯對死亡的恐懼,他認為上帝被取締之后的死亡“不論多么遙遠,都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提上了議事日程”[39]。肖斯塔科維奇和福樓拜是兩種不同的“死亡”形式,巴恩斯沒有偏袒哪一方,因為“死亡自有其道,它很固執,不會讓我們從我們自己謀劃的方式解決”[40]。“墓穴”是不可靠的,生死難以自己把握,巴恩斯對待“死亡”如同對待“真相”一樣充滿懷疑。
那么,“如何提防死亡”[41]又成為巴恩斯試圖擺脫恐懼的一大問題。福樓拜和肖斯塔科維奇選擇了以藝術抵抗社會與死亡,巴恩斯自己也不禁感嘆:“我們創造藝術,是為了挑釁死亡嗎?是為了超越死亡,將它置于相應的所在?你可以奪去我的身體,你可以將我頭顱內隱藏了所有理性和想象力的黏濕物體帶來,但你不能帶走我已然用腦子創造出來的一切。”[42]顯然藝術成為其生存信仰,“填補這可怕的‘虛空’并直面死亡恐懼”[43]。肖斯塔科維奇對暴力控制的屈服“不僅是死亡的沉思,而且——當然是私下里——嘲諷和鞭撻虛假期望和藝術糟粕”[44];當福樓拜指責高萊只有“對藝術的愛”而沒有對藝術的信仰時,巴恩斯這樣解釋道:“福樓拜使用這一表述時,意指為藝術獻身,而不是自命不凡地崇拜藝術……”[45]這兩位執著于文學與藝術的傳主,為巴恩斯提供了生存的指引,類似于替代性“宗教”或“救贖”。《倫敦郊區》中克里斯的經歷基本反映了巴恩斯的藝術觀念,藝術成為少年克里斯克服死亡恐懼的信仰,受生活影響他已不再祈求從藝術中獲得真理,并在小說結尾處接受翻譯工作時卻感到“慵懶的快樂”,表明在考慮藝術和生存關系時,意識到了藝術之于生活的療救功能。巴恩斯通過傳記和自傳性小說確定了自己作家的身份,通過辯護想象虛構、主體性在傳記中的合理性,既肯定了藝術這一最具意義的存在方式,同時維護了作者在傳記寫作中的創造性角色。在后現代語境中,“作者”身份不斷受到質疑,羅蘭·巴特甚至直接宣布了作者的“死亡”以消解作者存在的意義,但巴恩斯反其道而行地確立作者身份的存在論意義,并不滿地指出:“評論家總是悄悄地把作家殺死。”[46]其傳記中大量的敘事空白和無從尋找的真相,甚至自傳《沒什么好怕的》末尾的“the end”的戲謔表達,都以開放式結構文本并交由讀者評判,從而將讀者眾生這一主體也引入其傳記寫作的交互對話場域,模糊了傳記的單一權威,實則也是打破文體邊界的努力,以促進傳記的創新。
傳記的新轉向要求傳記不僅描述經驗的事實,還需要注意內心的事實,由事實層面上升至哲學意義層面,這就需要帶有特定理念的有意虛構的一定介入。巴恩斯在《時間的噪音》的“后記”中講道:“小說能夠前往傳記和歷史去不了的地方,寫小說的一個長處就是我可以揣摩并描寫人物的心理。”[47]在巴恩斯這里,借助小說更能接近傳記的內在真實,如在《福樓拜的鸚鵡》中,小說線索與傳記線索相互作用,為福樓拜作傳的同時,滲透其間的是敘述者對個人生活的自我探尋,且據此對傳主生平進行填平和想象。而在《時間的噪音》中,作者塑造了客觀傳主“肖斯塔科維奇”和主觀回憶的“肖斯塔科維奇”,看似一個人,實則又是兩個,以“自敘者”肖斯塔克科維奇對“傳主”肖斯塔科維奇進行追述,傳記家的地位被小說敘述者篡奪,就形成了真實與虛構的拉扯。戴維·洛奇在談到非虛構小說時講:“在非虛構小說……的叫法里,小說技巧會使人激動、緊張、激發人的情感……但對讀者來說,保證故事是‘真實的’又給它增添了吸引力,這是任何小說所不能比擬的。”[48]所以小說和傳記并非勢不兩立,而應相互結合與促動,使主客體能夠合力創造,傳記為小說創作提供了更多素材,其文本內容不再是純虛構的,實驗傳記也對傳統傳記構成了挑戰并使傳記達到更高的藝術形式。同時,實驗傳記的挑戰性又對傳統傳記的真實觀與描述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會使傳記創作更為謹慎,也更加具有創造性,達到在“美與真”、“主體與客體”之間更好的平衡,完成對無限接近的“真相”的指涉。
概而言之,巴恩斯通過跨界于傳記并大膽展開敘事實驗,改變了讀者對傳統傳記的認知,這表達了他對個人敘述和歷史文本真實性的懷疑,但是又在消解、顛覆中實現了自我投射與重構,賦予了傳記深層次的主體性、交互性與存在論意義。也就是說,傳記文體成為他傳達自身生命理念的途徑,并建構了“后真相時代”獨特的個體真實觀。雖然因為與傳統傳記構成張力而導致各種質疑,但巴恩斯的傳記實驗無疑亦推動了“傳記的黃金時代”[49]的發展與繁榮,吸引了更多小說家轉向傳記這一“非虛構寫作”領域,亦堪稱對傳記的某種創新與優化。
注釋:
[1][2]Nigel Hamilton,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1.p.219.
[3][5][6][法]左拉著,鄭克魯譯:《法國六文豪傳》,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 年版,第211 頁,第187 頁,第187 頁。
[7][8][法]亨利·特羅亞著,羅新璋譯:《不朽作家福樓拜》,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年版,第469 頁,第469 頁。
[9]李健吾:《福樓拜評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424 頁。
[4][10][11][20][21][22][23][26][27][30][46][英]朱利安·巴恩斯著,湯永寬譯:《福樓拜的鸚鵡》,譯林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9 頁,第85 頁,第85 頁,第134 頁,第136 頁,第125 頁,第178 頁,第250 頁,第37 頁,第125 頁,第200 頁。
[12]Ira Bruce Nadel,Biography: Fiction,Fact andForm,The Macmillan Press,1984,p.183.
[13][加]琳達·哈琴著,李楊、李鋒譯:《后現代主義詩學:歷史·理論·小說》,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 頁。
[14][俄]曼德爾施塔姆著,劉文飛譯:《時代的喧囂》,敦煌文藝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2 頁。
[15][29][33][36][37][38][39][40][41][42][44][45][英]朱利安·巴恩斯著,郭國良譯:《沒什么好怕的》,譯林出版社2019 年版,第37 頁,第272 頁,第22 頁,第82 頁,第132 頁,第114 頁,第22 頁,第22 頁,第49 頁,第77 頁,第157 頁,第90 頁。
[16]André Maurois.Aspects of Biogra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p.5.
[17][43]黃莉莉:《朱利安·巴恩斯的歷史書寫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51 頁,第173 頁。
[18][英]朱利安·巴恩斯著,林本椿、宋東升譯:《10?章世界史》,譯林出版社2021 年版,第228 頁。
[19]Patrik Mí?a.Biography in Fiction by Julian Barnes.Masaryk University Press,2013,p.65.
[24][47][英]朱利安·巴恩斯著,嚴蓓雯譯:《時間的噪音》,譯林出版社2018 年版,第189 頁,第239 頁。
[25][31][英]A.S.拜厄特著,楊向榮譯:《傳記作家的傳記:一部小說》,南海出版公司2016 年版,第165 頁,第97 頁。
[28]Patrick McGrath,“Julian Bar nes.” inBomb.21(Fall.1987),p.21.
[32]梁慶標:《傳記家的報復:新近西方傳記研究譯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210 頁。
[34][英]朱利安·巴恩斯著,林本椿、宋東升譯:《10?章世界史》,譯林出版社2021 年版。
[35][英]朱利安·巴恩斯著,軼群、安妮譯:《倫敦郊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0 年版。
[48][英]戴維·洛奇著,王峻巖等譯:《小說的藝術》,作家出版社1998 年版,第226 頁。
[49]Nigel Hamilton.How Do Biogra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