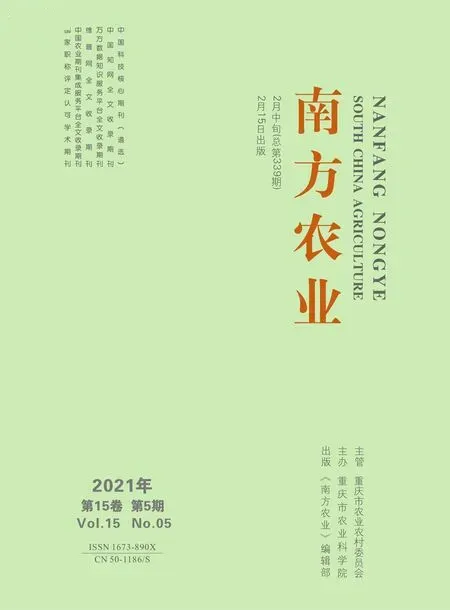關于青稞起源的研究現狀
李 健
(甘孜藏族自治州農業科學研究所,四川康定 626000)
青藏高原被譽為“世界第三極”,區內生態環境多樣、復雜,特別是高寒、低壓、強輻射、缺氧、凍土等極端環境,孕育了豐富而特別的物種資源,是世界重要的基因資源庫。研究青稞起源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了解青稞的起源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研究青稞與近東大麥野生種、栽培種以及西藏野生大麥之間的遺傳差異,探索在青藏高原極端氣候條件下青稞的適應性進化情況,從而為極端條件下的糧食生產提供相應參考。
關于青稞起源的研究工作開始于20 世紀20 年代,研究人員利用各種方法探討了青稞的起源,一種觀點認為青稞起源于西藏二棱野生大麥,另一種觀點認為野生二棱大麥起源于“新月沃地”并馴化為栽培種,隨后向東傳播,進入藏區并最終馴化為裸粒大麥青稞。
1 西藏起源學說
20 世紀20 年代末,蘇聯研究人員瓦維洛夫從世界各地收集了16 000 份左右的大麥種質,經過系統研究提出了作物起源中心的概念。瓦維洛夫認為,近東、中國西部地區以及埃塞俄比亞是大麥的3 個起源中心[1]。
1938 年,瑞典研究人員從四川省道孚縣收集到的小麥種質中發現了野生六棱大麥(Hordeum agriocrithonAberg)。徐廷文等的研究認為,青稞起源于藏區原始野生二棱大麥(Hordeum spontaneumC.Koch),之后產生鈍稃大麥、芒稃大麥、瓶型大麥、野生六棱大麥,野生六棱大麥又分化出野生六棱裸粒,最后野生六棱裸粒馴化為栽培六棱裸粒,即青稞[2]。
Morrel 等以來自“新月沃地”的野生大麥種質,中亞的野生大麥種質以及亞洲、歐洲、美洲的大麥栽培種為研究對象,對大麥的18 個基因位點進行重測序分析,結果表明,東、西方大麥分屬不同的類群,出現轉換的東、西方大麥種質就來自于伊朗的扎格羅斯山脈[3]。同時,東方野生大麥與西方野生大麥都具有獨特的單倍型,東方栽培大麥具有的單倍型只存在于中亞的野生大麥。因此,“新月沃地”可能并不是栽培大麥的唯一馴化中心。
Ren 等選擇83 份野生大麥種質(45 份來自亞洲西南,18 份來自中亞,20 份來自西藏)和20 份中國栽培大麥,對上述種質的HTL、Nam-1 基因進行序列變異分析[4]。根據Nam-1 基因的序列多態性進行系統發育樹分析,來自亞洲西南的野生大麥與中亞野生大麥聚為一類,絕大多數的中國栽培大麥與西藏野生大麥聚為一類。根據HTL 基因的序列多態性進行系統發育樹分析,所有中國栽培大麥與西藏野生大麥聚為一類,而亞洲西南的野生大麥與中亞野生大麥聚為一類。中國栽培大麥所具有的單倍型與西藏野生大麥獨有的單倍型一致,而來自“新月沃地”的野生大麥所獨有的單倍型沒有在中國栽培大麥中發現。因此,青稞很可能是由西藏野生大麥馴化而來,西藏是青稞的馴化中心。
2012 年,戴飛等選取了75 份來近東野生大麥,75份西藏野生大麥,68 份栽培大麥,采用芯片技術對該研究群體進行了全基因組掃描,分析結果顯示,西藏野生大麥與中國栽培大麥被聚為一類,近東野生大麥單獨聚為另一類[5]。群體結構分析的結果也顯示,西藏野生大麥與近東野生大麥分屬不同的類群。基于基因芯片分析,該研究認為西藏野生大麥與近東野生大麥在276 萬年前出現分化。該研究發現,西藏六棱裸粒栽培大麥與西藏野生大麥聚為一類,同時與其他野生大麥沒有共同祖先。因此,可以證明西藏青稞(西藏裸粒六棱大麥)是在青藏高原及其毗鄰地區由西藏野生大麥馴化而成。
西藏野生大麥的發現和相關遺傳學的研究能夠支持青稞西藏起源學說,但是該學說存在的缺陷是西藏野生大麥的自然群落至今沒有被發現,所發現的西藏野生大麥幾乎都是伴生于栽培大麥或栽培小麥。
2 近東起源學說
1848 年,Koch 在“新月沃地”發現了野生二棱大麥,隨后發現在該地域廣泛分布野生大麥群落,因此該地區被公認為大麥的起源中心。相關的考古研究發現,在新石器時代,大麥已經被馴化為栽培大麥并成為人類的主要食物來源[6]。由于在世界其他地區的考古研究中沒有發現年代更為久遠的栽培大麥碳化粒,部分學者認為“新月沃地”是大麥唯一的馴化中心。隨著人類活動,栽培大麥向東、西兩個方向傳播,其他地區發現的野生大麥是伴隨栽培大麥的傳播而傳播的[7]。
20 世紀80 年代左右,在甘肅省民樂縣東灰山遺址發現了公元前3 000 年左右的青稞、粟和小麥的遺跡。2014 年,蘭州大學對西藏東北部的考古研究發現,公元前5 500 年,西藏東北部就存在以農耕文明為主的人類活動,在海拔低于2 500 m 的人類遺址中,粟是主要的糧食作物。大麥的碳化粒在處于海拔2 500 m 以上的人類遺址中被發現,且與大麥碳化粒一同發現的還有小麥的碳化粒,這些碳化粒的年代約為公元前3 800 年[8]。在海拔3 100 m 的西藏昌都卡若遺址發現了起源于中國的粟的遺跡,在貢嘎縣昌果溝遺址發現了青稞的遺跡,該遺跡與粟和小麥的遺跡共存[9]。目前,在青藏高原還沒有發現更早的青稞遺跡,所有遺址的考古證據表明在青藏高原東北部的黃土高原上可能有農耕文明的存在,粟是主要的糧食作物,小麥、青稞可能是從西亞傳入,經黃土高原與粟交匯,再由人類活動帶入青藏高原。
曾興權等選擇了177份大麥種質進行全基因組測序,其中包含來自于西藏的69 份青稞地方品種,35 份青稞育成品種,10 份西藏野生大麥以及部分歐洲、美洲、東非、東亞的大麥野生種和栽培種[10]。根據SNP 突變位點,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的系統發育樹顯示,野生大麥與栽培大麥被聚為不同的類群,栽培大麥又分為兩個亞類,一類主要由東亞、中亞大麥栽培種和西藏青稞品種組成,另一類主要由西亞、中亞、非洲和歐洲大麥組成。基于全基因組測序數據,對野生大麥、西方大麥、東方大麥和青稞進行遺傳多樣性分析發現,野生大麥的低頻等位基因的占比最高,青稞低頻等位基因的占比最低,青稞連鎖不平衡率顯著高于西方大麥和野生大麥。因此,青稞的低遺傳多樣性表明青稞不是由西藏野生大麥馴化而來的,西藏也不是大麥的馴化中心。青稞與南亞大麥的親緣關系高于其與中亞大麥的親緣關系,因此該研究認為青稞可能不是從西藏東北部傳入西藏的,而是經印度、尼泊爾傳入西藏南部的。
六棱性狀和碎穗性被認為是大麥馴化的主要性狀,Pourkheirandish 等選擇了454 份大麥種質,其中包括來自青藏高原的青稞種質,檢測這些種質Vrs1、Btr1 和Btr23個基因的序列多態性,分析這3 個基因序列多態性發現,西藏不是大麥的馴化中心[6]。
上述研究所選西藏野生大麥的數量有限,且不能解釋為什么青稞所包含的單倍型只能在西藏野生青稞中發現而沒有在西亞的野生大麥或栽培大麥中發現。因此,青稞的近東起源學說也存在一定的漏洞。
3 結語
綜合利用植物分類學、考古學、分子遺傳學等眾多技術手段,各國學者對青稞的起源進行了深入研究。由于西藏起源學說和近東起源學說都存在一定的漏洞,因此青稞的起源仍存在爭議。由于青藏高原與大麥起源中心、大麥主要栽培地區的自然環境存在顯著差異;從公元前3 500 年至今,青藏高原地區也可能是全球唯一將大麥持續作為主要糧食作物進行人工選擇的地區。因此,差異顯著的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很可能導致青稞與近東、中亞、西歐、東非、北美的大麥種質存在較顯著的遺傳差異。這些遺傳差異不僅可以用于解析青稞的起源,也可以為大麥抗旱、抗寒、抗倒伏、生育期調控、品質性狀調控等方面的基礎研究提供重要的啟示和參考。這些關乎青稞高產、穩產、優質等重要性狀的基礎研究成果最終會為高產、優質青稞新品種的選育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和技術支持,從而推動以原始創新為主要動力的高質量青稞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