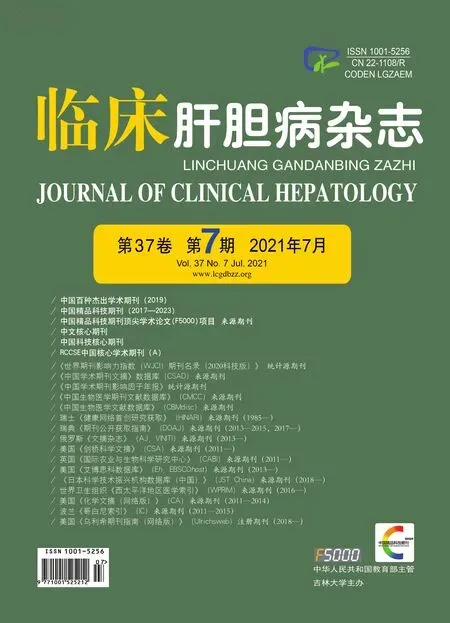慢性HBV感染重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臨床與基礎研究的現狀及展望
蔣麗娜,李 瑋,趙景民
解放軍總醫院 第五醫學中心,北京 100039
慢性HBV感染(chronic HBV infection,CBI)是指HBsAg和/或HBV DNA陽性6個月以上,HBV持續感染引起的慢性肝臟炎癥性疾病即慢性乙型肝炎(CHB),包括HBeAg陽性CHB和HBeAg陰性CHB[1-2]。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一組與胰島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和遺傳易感密切相關的代謝應激性肝損傷疾病,病理組織學改變與酒精性肝病(ALD)相似,但患者無過量飲酒史,包括非酒精性單純性脂肪肝(NAFL)伴或不伴輕度小葉內炎癥或匯管區炎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其相關肝硬化和肝細胞癌(HCC)[3-7]。2019年Eslam教授、George教授及Sanya教授等國際脂肪肝專家小組建議將NAFLD更名為代謝相關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MAFLD)[8],但尚未被正式采納,本文仍采用NAFLD 命名和定義。CBI和NAFLD是世界范圍內慢性肝病常見的兩大病因,CHB重疊NAFLD愈加普遍,已成為肝病臨床和基礎領域關注的熱點及難點問題。目前CBI重疊NAFLD(concomitant CBI and NAFLD,Co-CBI&NAFLD)尚無統一的定義,本文中Co-CBI&NAFLD是指慢性HBV感染前或持續感染中存在或發生不同臨床病理類型NAFLD,包括CHB重疊NAFLD(concomitant CHB and NAFLD,Co-CHB&NAFLD)。本文就Co-CBI&NAFLD的流行病學、自然史、可能的發病機制、病理特征及臨床診療現狀予以述評。
1 Co-CBI&NAFLD流行病學
全球約有2.57億CBI患者,中國CBI患者約7000萬,而NAFLD在西方國家患病率超過30%,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多數國家NAFLD患病率>25%,據估計,Co-CHB&NAFLD患病率為25%~30%[9-10]。源自韓國的全球最大宗(83 339例)CBI社區人群長期隨訪研究[11]結果顯示,NAFLD發病率為41.7/1000人年,但不同規模研究人群或隊列的亞洲CHB患者中NAFLD的患病率報道差異較大,為14%~67%[12-15],其中韓國51.2%,伊朗42.4%,土耳其34.3%,中國臺灣約為43.9%。一項針對北美CHB患者的研究[16]發現,2000年—2005年與2011年—2015年,CHB患者中NAFLD的患病率從1.6%穩步上升至6.8%。源自法國的一個前瞻性隊列研究[17]顯示21%CHB患者合并NAFLD。中國宓余強教授團隊和朱月永教授團隊報道了由肝穿刺病理證實的Co-CBI&NAFLD發生率為30.9%~41.7%[18-21];在中國香港,以受控衰減參數(controlled attenuation parameter,CAP)>248 dB/m為標準,CHB患者中NAFLD發病率47.8%(1134/2370)[22]。現有的全球Co-CBI&NAFLD流行病學資料多數為單中心、回顧性隊列研究數據,且NAFLD診斷與評價主要基于B型超聲、CAP衰減指數等檢測手段,肝穿刺病理證實的Co-CBI&NAFLD研究隊列相對較少,中國尚缺乏基于多地區、大樣本、前瞻性、長期隨訪CBI人群的NAFLD流行病學資料。
2 Co-CBI&NAFLD自然史
Co-CBI&NAFLD自然史尚不清楚。Joo 等[11]對來自韓國的單一體檢中心的83 339例(HBsAg陽性3926例、HBsAg陰性79 413例)社區成年人群進行了長達12年的前瞻性隨訪隊列研究,Cox回歸模型分析顯示,484 736.1人年隨訪期間有20 200例發生NAFLD(NAFLD發病率41.7/1000人年),調整年齡、性別、隨訪時間、吸煙、飲酒、定期鍛煉、教育水平、體脂指數后,HBsAg陽性與陰性人群校正危險比(aHR)為0.83(95%CI:0.73~0.94),NAFLD發病率在HBsAg陽性人群較陰性人群低;引入HBV感染和混雜因素(包括IR和代謝因素穩態模型評估)作為時間依賴暴露因素后,HBsAg陽性和NAFLD發生風險降低的關系有所減弱,但仍然存在。源自中國香港的1013例(HBsAg陽性91例、HBsAg陰性922例)社區人群的斷面研究[23]中,HBsAg陽性人群中NAFLD患病率為13.5%(95%CI:6.4%~20.6%),HBsAg陰性人群NAFLD患病率為28.3%(95%CI:25.3%~31.2%),質子磁共振波譜分析顯示平均肝臟TG水平在HBsAg陽性和陰性人群中分別為1.3%和2.1%。但在CBI人群中,血清HBV DNA載量、病毒基因型、e抗原狀態與NAFLD發生無相關性。
雖然CBI患者NAFLD發病率較低,但NAFLD和CHB可以共同加重肝損傷,增加肝纖維化和HCC的風險。來自中國香港的270例(合并脂肪肝患者107例、非脂肪肝患者163例)CBI患者(HBsAg陽性超過6個月)的隊列研究[24]表明,經過79.9個月的隨訪,11例(合并脂肪肝患者9例、非脂肪肝患者2例)發生HCC。經過多變量的Cox回歸分析發現,并發脂肪肝(HR=7.27,95%CI:1.52~34.76,P=0.013)、年齡、肝硬化、還有APOC3 rs2854116 TC/CC基因型(HR=3.93,95%CI:1.30~11.84,P=0.013)是預測HCC發展的獨立因素。另一項來自中國香港的558例NAFLD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隊列研究[25],經過6.2年隨訪后,血清抗-HBc陽性的NAFLD患者更易發展為進展期肝纖維化或HCC(6.5% vs 2.2%,P=0.039)。
3 Co-CBI&NAFLD的發病機制
Co-CBI&NAFLD的發病機制尚未闡明。HBV感染可能影響肝臟脂質代謝,促進肝細胞內脂質沉積。Kim等[26]通過HepG2細胞系及小鼠模型研究發現,HBx通過增強肝臟X受體和LXR反應元件作用,促進固醇調節原件結合蛋白1(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1,SREBP-1)和脂肪酸合成酶上調,進而增加脂質的胞內沉積。HBx可能通過肝細胞核因子3β(hepatocyte nulear factor 3β,HNF3β)、重組人CCAAT增強子結合蛋白α(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α,C/EBPα)、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 α,PPARα)激活肝臟脂肪酸結合蛋白1(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1,FABP1)啟動子,FABP1在細胞內脂肪酸運輸和利用中起重要作用,促進肝臟脂質堆積[27]。而NAFLD可能通過破壞HBV復制和增加HBV感染細胞的凋亡來促進HBsAg與HBV DNA的清除[28]。在NAFLD和HepG2.2.15細胞介導的硬脂酸誘導的脂肪變性HBV轉基因小鼠中,TLR4/MyD88信號通路被激活,HBV復制被抑制[29]。
Co-CBI&NAFLD對肝纖維化、肝硬化和HCC促進作用的潛在機制尚不清楚。可能的機制是:(1)NAFLD相關的脂毒性可以通過內質網應激和線粒體呼吸鏈產生過量的活性氧,導致DNA和其他生物大分子的氧化損傷,這也是Co-CBI&NAFLD進一步發展成HCC的一個關鍵過程。安威教授團隊[30]系列研究顯示,線粒體在NAFLD發病中起重要作用,認為NAFLD可視為“線粒體病”范疇。(2)NAFLD介導的HBV感染中炎癥損傷和纖維化的加重。譬如,NASH中受損肝細胞釋放的危險相關分子模式,以及炎性細胞因子(如IL-1、IL-6、TNFα、CCL2和CCL5)可以導致肝星狀細胞的激活和增殖,繼而發生肝纖維化或最終的肝硬化[28]。(3)NAFLD中瘦素水平升高和脂聯素水平降低,脂源性細胞因子的改變促進肝纖維化的進展[31]。
4 Co-CHB&NAFLD的病理學特征及組織學評價
Co-CBI&NAFLD肝組織學改變往往表現為兩種肝病的病變混雜,給肝活檢組織學評價帶來一定困難,但有經驗的病理醫師通過仔細檢查,多數CHB和NAFLD各自的病變特點可以鑒別。NAFLD特征性病變包括肝細胞大泡或大小泡混合型脂變,呈小葉中央區帶、匯管區周圍、全小葉及無區帶型分布;脂變區域可夾雜肝細胞氣球樣變(ballooning);可出現脂質肉芽腫、巨型線粒體肝細胞、糖原核肝細胞,而CHB可見毛玻璃樣肝細胞;NASH引起的肝小葉內炎癥壞死主要呈點灶狀壞死,壞死區是以淋巴細胞為主的混合性炎細胞浸潤。CHB通常表現為活動性淋巴細胞浸潤性界面炎(interface hepatitis),NASH通常缺乏或輕度混合性炎細胞浸潤性界面炎,小葉內及小葉界板處融合性壞死、橋接壞死通常為活動性CHB病變特征,上述病變NASH極少出現。成人型NASH肝纖維化往往見于小葉中央區帶肝細胞周和竇周纖維化(chicken-wire fibrosis),而CHB多以匯管區周圍纖維化及橋接纖維化為主要形式。此外,匯管區淋巴細胞聚集性浸潤,乃至濾泡樣結構形成是CHB病變特點,成人型NASH匯管區炎癥通常缺乏。
Co-CHB&NAFLD的組織學評價國內外尚無專門的評分系統,建議選擇Ishak評分系統[32]、Metavir評分系統[33]、我國CHB肝組織學評分系統[34]聯合NASH-CRN評分系統[35]或FLIP/SAF評分系統[36],進行病理組織學評價。近年來,魏來教授團隊[37]采用二次諧波/雙光子激發熒光法對NASH穿刺肝組織切片(無需染色)進行多組織學參數自動定量檢測,并建立了qFIBS定量評價模型。Zhuang等[38]利用上述技術對Co-CHB&NAFLD的肝細胞脂變進行了自動定量檢測嘗試。
5 Co-CBI&NAFLD的無創診斷
超聲雖然是臨床診斷脂肪肝最常用的方法,但其對脂肪肝診斷的敏感性低,特異性也有待提高[39]。CAP能準確區分輕度肝細胞脂變與中-重度肝細胞脂變,近年來對于脂肪肝的診斷價值已被廣泛認可[4]。范建高教授團隊[40]發現CAP對于脂肪肝的診斷準確性優于超聲,但是其與超聲相比易高估肝脂肪變程度。陸倫根教授團隊[41]多中心隊列研究結果顯示,FibroTouch對肝臟脂變及纖維化程度有較好的診斷效能,適用于NAFLD患者的臨床評估和監測。常見診斷脂肪肝的血清學診斷模型中,脂肪肝指數、肝脂肪變性指數臨床診斷效能較佳,但在CHB重疊脂肪肝中研究尚少[3]。
近年來,利用血液中CK-18 M30、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21(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1,FGF-21)、IL-1Ra、色素上皮衍生因子(pigment epithelium-derived factor,PEDF)、骨保護素(osteoprotegerin,OPG)、miRNAs、活性氧等相關標志物對診斷CHB重疊或合并NASH均呈現出可接受的特異性和敏感性[42-45],但上述指標在臨床上尚未進入準入或普遍應用,且診斷閾值待進一步確定。Co-CHB&NAFLD顯著/進展期肝纖維化及肝硬化的預測,GGT/PLT比值(GPR)的AUC似乎高于APRI和FIB-4[46]。瞬時彈性成像技術(transient elastography,TE)在進展期肝纖維化及肝硬化診斷方面優于GPR,使用GRP和TE的兩步法檢測可進一步優化Co-CHB&NAFLD患者肝硬化的評估效果[47]。Shen等[48]發現中重度肝細胞脂變可增加無顯著肝纖維化CHB患者的肝硬度值(LSM)。Xu等[49]發現CAP增加了CHB顯著纖維化的假陽性率,其建立的模型公式Fibro-NAFLD可提高LSM對于Co-CHB&NAFLD顯著肝纖維化的診斷效能。
6 Co-CHB&NAFLD的抗病毒治療
現有的研究表明,NAFLD與代謝綜合征密切相關,代謝綜合征是CBI患者晚期纖維化和肝硬化的獨立危險因素[50],然而HBV DNA載量與NAFLD發病率呈負相關[51]。因此,目前對于Co-CHB&NAFLD啟動抗病毒治療的指征仍尚待進一步明確。
根據中國《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1],無論是否重疊NAFLD,CHB肝硬化均推薦進行抗病毒治療;而對于非肝硬化的Co-CHB&NAFLD患者,需要綜合評估以確定治療方案。為此,孫劍教授團隊提出相關臨床管理建議:當Co-CHB&NAFLD患者無其他肝損傷原因ALT>5×ULN或HBV DNA >2000 IU/ml時可考慮試驗性抗病毒治療,經治療HBV DNA陰轉后根據ALT下降與否,選擇繼續抗病毒治療或按NAFLD管理;當Co-CHB&NAFLD患者ALT為1~5×ULN且HBV DNA≤2000 IU/ml時,先按NAFLD管理3~6個月,再根據ALT水平選擇治療策略。該策略進一步細化了Co-CHB&NAFLD抗病毒治療的時機、路線圖及管理策略,值得臨床參考。
對于Co-CHB&NAFLD患者的抗病毒療效,趙景民教授團隊和魯鳳民教授團隊對兒童Co-CHB&NAFLD患者開展了相關研究[52]。在抗病毒治療的第96周,重疊或不重疊NAFLD的CHB患者在HBV DNA低于檢測下限的比例、HBeAg陰轉及AST和ALT復常方面均無顯著差異,但發現NAFLD是HBsAg轉陰的獨立預測因子(aHR=3.245,95%CI:1.288~8.176),Co-CHB&NAFLD兒童患者HBsAg陰轉率均高于無NAFLD的CHB兒童患者。有研究[53]顯示肝細胞脂變是恩替卡韋治療失敗的獨立因素。在伴有肝脂肪變的CHB患者中,HBV DNA清除率較低。還有研究[54]表明Co-CHB&NAFLD患者抗病毒治療的遠期完全病毒學抑制率(HBV DNA<20~100 IU/ml)和/或生化應答率(女性ALT≤25 U/L,男性ALT≤35 U/L)無明顯影響。顯然,目前重疊NAFLD對CHB患者抗病毒療效的影響尚存有爭議,需要進行多中心、大樣本、隨機對照前瞻性臨床隊列研究,結合臨床真實世界研究,以期為Co-CHB&NAFLD抗病毒治療時機選擇、療效預測、治療方案優化等提供高等級的循證醫學依據。
7 總結與展望
Co-CBI&NAFLD兩者的相互影響作用尚未明確,現有研究[55-59]顯示NAFLD對CHB患者的抗病毒療效影響不大,單純CHB組和合并癥組的病毒抑制情況區別并不明顯,但可能增加HBsAg血清學轉換率[60];Co-CHB &NAFLD較單純CHB肝纖維化進展呈加快趨勢,尤其合并代謝綜合征會進一步促進CHB患者肝硬化及HCC的發生;Co-CBI&NAFLD組織學上兩者病變并存,各自特征性病變鑒別困難。
未來Co-CBI&NAFLD臨床與基礎研究有機結合,將明確其疾病演變的各關鍵環節,闡明其自然史;隨著相關新技術的轉化與應用,建立高特異性和高靈敏性的無創診斷技術,并確定其診斷閾值,解決Co-CBI&NAFLD重點人群篩查、監測及隨訪等臨床問題;隨著高等循證醫學證據的增加,Co-CHB&NAFLD抗病毒治療時機選擇、療效預測及治療方案優化,尤其是抗病毒與脂肪肝干預綜合策略的應用,將顯著降低相關終末期肝病的發生率和病死率,相關Co-CBI&NAFLD診療指南或共識將會隨著證據的積累應運而生;隨著Co-CBI&NAFLD相互影響作用機制的逐漸闡明,將為臨床疾病管理,乃至新藥研發、新型治療策略的制訂提供科學依據。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蔣麗娜、李瑋負責文獻檢索、數據分析及初稿撰寫工作;趙景民負責述評總體設計、主要述評觀點撰寫、修改及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