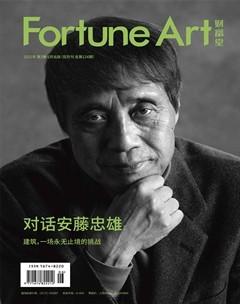不是句號,是問號?
邱敏

在上海,我們每年能接觸到經(jīng)典老大師展覽機會不少,從數(shù)量、品質(zhì)到展覽規(guī)格都可圈可點。當(dāng)然這主要歸功于對外文化交流的開放性和藝術(shù)機構(gòu)自身的專業(yè)性,除此之外,門票回報、網(wǎng)紅效應(yīng)、傳播力度、潛在賦能,讓藝術(shù)機構(gòu)在選擇大師展覽進場時,相互之間有種血拼到底的暗暗較勁。
在2021年西岸美術(shù)館舉辦的這場康定斯基的個展之前,該館的《時間的形態(tài)》一展中,已經(jīng)有兩件康定斯基的作品做了一個熱身。當(dāng)然,康定斯基在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史上的重要性沒有任何學(xué)術(shù)懸念,但若論及這個展覽對上海本地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意義,還是非常有咀嚼口感的。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既有北方的“理性繪畫”,也有以西南藝術(shù)為代表的南方繪畫,同時還有廈門達(dá)達(dá)喊出“無物而不是藝術(shù)”,浙江的藝術(shù)家們回應(yīng)“無為而不是藝術(shù)”,觀念藝術(shù)拋棄繪畫本體的時候,上海的藝術(shù)家卻羈留在畫布上,執(zhí)著于形式、色彩、肌理、材料的探索,構(gòu)筑一個抽象畫的世界。所以,康定斯基的個展不僅僅是滿足中產(chǎn)階級的懷舊趣味,它是給上海依然在進行抽象藝術(shù)實踐的藝術(shù)家們打了一針強心劑。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康定斯基如何從印象派走向抽象的結(jié)果,這不只是一個將形式簡單歸納為幾何形體的過程,同時它也向我們昭示康定斯基個人身上自我抗?fàn)幍木窳α浚核仁且粋€嚴(yán)謹(jǐn)?shù)媒醣J氐娜耍瑫r又是一個果斷放棄現(xiàn)實的安穩(wěn),大膽跨界,甚至積極介入革命的人。
多面的康定斯基:展廳中展出的康定斯基的照片,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種放蕩不羈的藝術(shù)家模樣,相反,他西裝革履,架著金絲邊眼鏡,更像一名睿智的律師。這次展覽可惜沒有他工作室的照片,他的工作室井然有序,顏料罐收拾得像商店貨架上的物品。而他作畫時經(jīng)常穿著白色的西裝,作畫的整個過程,手指縫干凈,白色西裝從頭到尾纖塵不染。
康定斯基有一半東方血統(tǒng),其曾祖母是蒙古的公主,他的父親就出生在中國邊境,而他1866年出生于莫斯科。最初在莫斯科大學(xué)學(xué)法律、經(jīng)濟學(xué),26歲留校并成為教授。康定斯基30歲時在俄國旅行,在旅途中,他觀看了大量的民間藝術(shù),也接觸到歐洲的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在一次展覽會上,他看到了莫奈的《干草堆》,他困惑于這些畫就像未完成一樣,沒有細(xì)節(jié)的精細(xì)打磨,但這幅畫緊緊抓住了他。回去之后不久,康定斯基毅然放棄了法學(xué)教授一職,跑去德國慕尼黑學(xué)藝術(shù)。他去慕尼黑開始波西米亞的藝術(shù)家闖蕩生活時,成為妻子的表妹和他離婚,而他在慕尼黑美術(shù)學(xué)院認(rèn)識了一個女孩子,他們一起游歷歐洲,對新藝術(shù)進行大膽探索。當(dāng)時他師從于一位具有象征主義風(fēng)格的老師,康定斯基并不感興趣,他戀戀不忘的是莫奈創(chuàng)作中的自由開放性。康定斯基是一個學(xué)習(xí)能力超強的好手,他順利完成了四年的學(xué)業(yè),并取得了學(xué)位。他另一個愛好是提琴演奏,也近乎專業(yè)水平,古典音樂修養(yǎng)非常好。


革命的康定斯基:1917年俄國革命以后,他回到俄國,積極參加革命,受到重用,參與組建了蘇維埃文化藝術(shù)宮,并擔(dān)任館長。在這次展覽“俄羅斯:間奏歲月”這一板塊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定斯基有幾幅小畫出現(xiàn)了非常清晰的具象形的繪畫,同時有幾幅迷你版的抽象作品,似乎覺得他不是那么自在地畫那些抽象形式的作品。很快,他與俄國的左派藝術(shù)運動產(chǎn)生激烈的沖突,他的抽象藝術(shù)得不到理解。康定斯基在回憶錄中提到的清高的俄國人,指的就是那些描繪具有宏大敘事、史詩性的左派藝術(shù)家。或許這可以解釋他又回到了具象的物象以及迷你版抽象藝術(shù)的原因,他嘗試著委曲求全,但發(fā)現(xiàn)這實在有違自己的天性,好在1922年他作為文化親善大使去德國時被滯留到了德國,繼而受聘包豪斯,教授包豪斯藝術(shù)基礎(chǔ)課程,二戰(zhàn)爆發(fā)前期,他又跑到法國去,最后在法國終老。

對音樂的吸納:康定斯基一直在研究為什么作曲家通過有限的曲式,就能創(chuàng)造出那么豐富的交響樂,他希望把點線面和顏色關(guān)系變成基本的內(nèi)容。然后后世畫家就可以用這些內(nèi)容互相配合,像譜寫音樂那樣畫出他們所需要的情感。他致力于賦予幾何形式以情感,借助音樂的抽象性來溝通形、線、色的動感、力度和節(jié)奏性。但這是康定斯基一廂情愿的想法,后來理論家格林伯格倡導(dǎo)的抽象藝術(shù)發(fā)展方向之一,就是剔除康定斯基繪畫中的抒情性和音樂性。
康定斯基的調(diào)色板:這次展覽非常有意思的是展出了康定斯基的調(diào)色板。值得注意的是,這塊調(diào)色板的意義不在于它是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工具展示,它對康定斯基最終在畫面上取消客觀物象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康定斯基一直有一個疑惑,每次畫完畫都發(fā)現(xiàn)他的畫不如調(diào)色板好。但調(diào)色板會成為畫嗎?后來他發(fā)現(xiàn),調(diào)色板比畫好的原因在于,客觀物正在消失。而康定斯基之前的畫受印象派風(fēng)格影響很大,有大量可以辨析的形象存在。他終于意識到客觀物沒有意義,在這種靈感之下,他畫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張抽象畫(《無題》1913年)。

東亞藝術(shù)以及神秘主義的影響:此次展覽有機地打破了歐洲中心主義的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史呈現(xiàn),以一種對話和開放的方式,呈現(xiàn)康定斯基的個人藝術(shù)創(chuàng)作生涯的同時,也揭示出一條20世紀(jì)初期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的發(fā)生所受到的東亞藝術(shù)影響的線索。尤其在展覽入口的展廳,專門展示了康定斯基的日本浮世繪收藏,而結(jié)束展廳以中國青銅器的影響收尾。這個展覽點出了康定斯基所受到的東亞文化影響,但遺漏了一點,就是康定斯基的繪畫中還有一個神秘主義的背景。康定斯基從瓦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中看出一種抒情性的體驗,并將其用在點線面的造型因素之中;同時,他又把點線面看成是一種神性。在康定斯基學(xué)習(xí)法學(xué)的期間,他曾經(jīng)到俄國的鄉(xiāng)村考察東正教的各種教會的狀況,對俄國的神秘主義的民間傳說非常有興趣,他的作品中一直有一個神秘主義的背景,后來有一些學(xué)者將其解釋為“通靈論”,探討其神智學(xué)的傳統(tǒng)淵源。對于康定斯基來說,“點線面”作為一種造型因素,要同時具備抒情性和神性的統(tǒng)一。
無論對抽象藝術(shù)依然持有熱情,還是已經(jīng)放棄繪畫本體的藝術(shù)界人士而言,盡管康定斯基的藝術(shù)成就已經(jīng)蓋棺論定,但它不是一個句號,它向我們提出了諸如東亞文化如何影響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革命,大膽跨界應(yīng)該立足于什么,神秘主義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有聯(lián)系嗎等等問題,而這些依然是我們在2021年藝術(shù)中一直在追問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