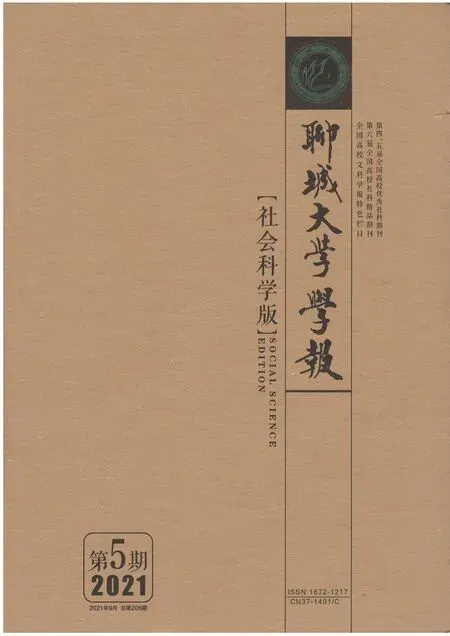藝術形式·民俗物象·群體生計·文化遺產(chǎn):木版年畫研究的四個維度
張兆林
(聊城大學 美術與設計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木版年畫是我國特有的藝術形式,是民眾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生活需求而進行勞作,并獲得相應物質(zhì)收益的復雜文化物象。國內(nèi)外學術界早已關注到木版年畫,而且從多個角度開展了研究工作,產(chǎn)出了一批有相當影響的成果,這為后學繼續(xù)開展相關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通過梳理,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相關的研究成果或從藝術形式,或從民俗物象對木版年畫進行了研究,更多地呈現(xiàn)了作為物態(tài)的藝術形式或作為動態(tài)的民俗物象,但缺乏對藝術生產(chǎn)中藝術行為和生產(chǎn)者的關照,少有對參與木版年畫生產(chǎn)的民眾群體或民眾生計進行專題研究,即使是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語境下的研究也大多如此,導致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存在物的呈現(xiàn)較多,而生產(chǎn)者、生產(chǎn)過程、時代價值呈現(xiàn)較少的現(xiàn)象,“使當下年畫的研究一直處于單一化和平面化狀態(tài),未能真正揭示年畫廣闊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厚的文化魅力”①萬建中等:《民間年畫的技藝表現(xiàn)與民俗志書寫——以朱仙鎮(zhèn)為調(diào)查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4-5頁。。
散布于我國多數(shù)地區(qū)的木版年畫,“它既是美術,又是一種特殊的美術,因此除了其美術功能之外,必須把它放在生產(chǎn)、生活環(huán)境中,發(fā)掘和宣揚其在文化史和文化學上的意義,突現(xiàn)其在人類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生活發(fā)展史中的獨特價值和貢獻。”②張紫晨:《民間美術與民俗文化》,《裝飾》1998年第4期。為了更好地呈現(xiàn)承繼于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木版年畫,筆者選擇以聊城木版年畫為核心對象開展研究工作。“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的聊城木版年畫,是指在現(xiàn)聊城市范圍內(nèi)承繼的木版年畫,包括歷史上曾散布且依然在東昌府區(qū)、陽谷縣、東阿縣、冠縣、臨清、高唐等縣區(qū)零星承繼的木版年畫,是該地域范圍內(nèi)木版年畫的統(tǒng)稱。”③參見張兆林:《從碎片到完整:聊城木版年畫研究的轉(zhuǎn)向》,《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之所以選擇以聊城木版年畫為核心研究對象,筆者主要基于以下幾點的考慮:其一,聊城木版年畫自明初出現(xiàn),其歷經(jīng)清康乾年間的繁盛,至民國時期的衰落式微,后在新中國成立后經(jīng)歷國家意志宣傳的新工具、“文化大革命”期間封建思想的毒草、新世紀文化遺產(chǎn)的多變命運,與我國其他產(chǎn)地的木版年畫嬗變軌跡基本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其二,聊城木版年畫有門神、灶神、財神、戲出年畫等眾多題材,與我國其他類型的木版年畫題材多有交叉,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義;其三,聊城木版年畫可上溯至山西平陽木版年畫,且自明初以來承繼于魯西運河區(qū)域,時值封建社會商品經(jīng)濟萌發(fā)之際,又恰處于南北文化交流之境,及農(nóng)業(yè)文化與商業(yè)文化互促之地,因而具有一定的獨特性。筆者希望通過該既具有普遍性意義,又具有獨特性特征的年畫形式闡釋關于木版年畫研究應關注的四個維度。從藝術本體、民俗物象、群體生計、文化遺產(chǎn)等維度研究木版年畫,實際上就是在堅守自我學科立場的前提下探索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式,采用美術學、歷史學、民俗學甚至經(jīng)濟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并嘗試從藝術學、民俗學、經(jīng)濟學、文化學、藝術人類學等多學科的視角對民眾生活中的木版年畫進行切入肌理的研究。
一、作為藝術形式的木版年畫
木版年畫呈現(xiàn)于民眾面前,多是一種物態(tài)的藝術形式,學術界也給予了該形式充分的關注,但“多是將木版年畫視為單純地民間美術作品,重在論述民間年畫的題材內(nèi)容和藝術形式特征”①梅箐:《民間年畫的產(chǎn)生和傳承》,《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缺少深入的學理分析,缺少對其文化內(nèi)涵的深入研究”②萬建中等:《民間年畫的技藝表現(xiàn)與民俗志書寫——以朱仙鎮(zhèn)為調(diào)查點》,第4頁。。王樹村、薄松年兩位學界前輩是我國年畫研究的執(zhí)牛耳者,王樹村認為“民間年畫,是中國繪畫里特有的一種藝術形式,可以分為三類:一、手工繪制;二、木版彩印;三、彩版套印后手工開臉染衣”③王樹村:《民間年畫六說》,《美術研究》1986年第2期。。就研究對象而言,學者大多將以上三類都囊括其中。因為木版年畫是由木刻雕版印制的年畫,或以木版印刷為主,兼以手繪的年畫,而筆者只是選擇了由木刻雕版印制而無手工敷彩的年畫作為核心研究對象,即王樹村所言第二類中的之一。聊城木版年畫是在晉南木版年畫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只有手工印制的環(huán)節(jié),而無任何其他的手繪輔助,因而其印制效果精美不足,但粗獷有余。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同為山東木版年畫重要組成部分的楊家埠木版年畫,也有手工敷色的環(huán)節(jié),這從另一個方面映射了聊城木版年畫的獨特性。
聊城木版年畫以神像類為主,包括門神、灶神、財神、天地全神、戲出故事、娃娃畫、雜神等,其中門神、灶神是聊城木版年畫中的主要題材。在為數(shù)較少的相關研究成果中,部分學者雖然對聊城木版年畫的題材有所涉及,注重的多是藝術本體及藝術價值的探究,如體裁分類、畫面風格、造型題材、色彩線條等,并由此闡釋木版年畫類民間美術的特點等,但少有對圖像背后文化寓意的挖掘與闡釋。當然,這也是我國木版年畫研究中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相關研究的文本成果也大體可以分為“描述”、“史”和“概論”三類。④王瑛嫻認為,描述型成果“從微觀層面展開,關注年畫的視覺特點或制作工藝,對整個過程尤其是最后的圖像做詳盡論述”;發(fā)展史型成果“重點考察年畫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風格流變或工藝變革,注重結(jié)合時代背景討論年畫的演變”;概論型成果“從宏觀層面旁征博引,幾欲囊括對全國各地年畫的研究,對各地年畫進行橫向?qū)Ρ龋瑩鷳n浮光掠影之嫌”。詳見其文《從“何為年畫”到“年畫為何”——年畫研究的路徑探析》,《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我們不得不承認,近二十年以來關于聊城木版年畫風格特征、藝術價值、發(fā)展脈絡、地方寓意等研究成果(雖然數(shù)量較少),多是后來的研究者對學界前輩及當?shù)匚氖饭ぷ髡哐芯砍晒哪懟螂s燴,“這樣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就是年畫屬于浪漫主義者的想象產(chǎn)物,遮蔽了創(chuàng)作者與使用者關于年畫的創(chuàng)新依據(jù)與生產(chǎn)目的的考究。”⑤榮樹云:《社會轉(zhuǎn)型中楊家埠木版年畫的藝術人類學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藝術研究院,2017年,第32頁。
梳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兼之加以田野考察驗證,就會發(fā)現(xiàn)聊城木版年畫的實用性指向極為明顯,而且這種實用性多表現(xiàn)為對年畫中神靈的恐懼與膜拜,對神靈神通的功利性索求。我們必須認識到,多數(shù)民眾對神靈的膜拜,并非出于發(fā)自內(nèi)心的虔誠,而是基于擺脫現(xiàn)實困境的愿望和對美好未來的渴求,是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現(xiàn)實的幸福和實惠。民眾之所以將年畫請回家貼在墻上或門上,是希望為自己建立一個與神仙世界溝通的渠道,希望通過對著年畫上神靈所舉行的儀式能夠把自己的需求傳遞過去,至于傳遞到哪位神仙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傳遞的儀式和愿望的表達,力求的是“心到神知”。當然,這種功利性的尊重并不僅針對年畫上的諸位神靈,而是針對民眾信仰的所有神靈,且這種功利性的尊重絕非隨意,而是保持著相當?shù)木次窇B(tài)度。這種敬畏信仰的程度與民眾對年畫的需求是成正比的,并且這種敬畏信仰是受當?shù)孛癖娢幕健⑸盍曀住⑸a(chǎn)狀況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二、作為民俗物象的木版年畫
我國各地木版年畫的題材,“在他們告訴我們的以及不告訴我們的東西上,彼此之間卻有明顯的巨大差異。如果我們忽視了圖像、藝術家、圖像的用途和人們看待圖像的態(tài)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千差萬別,就將會面臨風險。”①[英]彼得·伯克:《圖像證史》,楊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2頁。就本文的研究對象而言,筆者認為可以把這種風險理解為,我們可能對相關題材不同民俗背景及寓意的錯誤解讀。為了避免或者減少這種錯誤解讀的可能性,就必須在年畫題材形似的背后,尋找不同區(qū)域民眾在年畫圖像基礎上創(chuàng)生的民俗物象與寄寓的精神內(nèi)蘊。
年畫絕非一種民間藝術形式而已,其之所以能夠傳承數(shù)千年就在于其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且演變成為了一種涵載豐富意蘊的民俗物象。由于木版年畫的生產(chǎn)、銷售、張貼、供奉或欣賞有一定的程式化,也就使得該民俗物象在王朝更替與社會動蕩中保持了相應的穩(wěn)定性。任何一種民俗物象都是其所在區(qū)域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乃至其他各個方面不同程度映射的符碼復合體,是以滿足區(qū)域內(nèi)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為目的。年畫最初的生產(chǎn)是為了滿足民眾辟邪祈福的精神需要,后逐漸又具有了裝飾年節(jié)、倫理教化、增博見聞等功能,隨著其功能的擴展而在全國更大的范圍內(nèi)得以生產(chǎn)、銷售、承繼,成為多數(shù)民眾所接受并喜愛張貼的一種藝術形式。②學界對此少有異議,如張士閃認為傳統(tǒng)木版年畫首先應界定為傳統(tǒng)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民俗事象,后在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演變進程中成為一種社會行業(yè)。參見張士閃《中國傳統(tǒng)木版年畫的民俗特性與人文精神》,《山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一)作為區(qū)域民俗物象的聊城木版年畫
聊城木版年畫是在山西移民攜來的年畫刻印技藝基礎上發(fā)展而成。明初,大批山西移民被政府有組織地遷入聊城地區(qū),構(gòu)成了當?shù)孛癖姷闹黧w,其生計慣習勢必會影響到當?shù)厣鐣姆椒矫婷姊鄹饎π垩芯空J為,洪武年間東昌府移民中山西移民與山東東三府移民之比為20:7,而總移民數(shù)占當?shù)乜側(cè)丝诘?3.4%。詳見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8頁。。山西平陽自兩宋以來就有刻印的傳統(tǒng),刻印已經(jīng)成為平陽民眾改善生活的一種輔助生計。大批的山西民眾遷入聊城地區(qū)后,原本掌握的一些技能又成為其在當?shù)刂\生的重要手段,且當?shù)厥a(chǎn)年畫制作所需的原材料,所以既有部分民眾繼續(xù)從事刻印生計,也有部分民眾憑借刻印手藝從事相關的謀生活計,進而開辟了新的生產(chǎn)領域。“聊城地區(qū)傳統(tǒng)的毛筆業(yè)、雕刻葫蘆、雕版印刷、泥塑和面塑、中堂畫與剪紙等,隨著時間的推移便逐漸產(chǎn)生、發(fā)展和壯大起來,逐漸形成了同木版年畫一樣的產(chǎn)業(yè)。”④楊朝亮:《刻書藏書與聊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頁。雖然聊城木版年畫是從陽谷縣張秋鎮(zhèn)肇始,但張秋鎮(zhèn)的年畫生產(chǎn)主要依靠外力,其既沒有自己的刻版藝人,也沒有自己的印制藝人,而只是組織印制及售賣年畫。從明初至今,聊城當?shù)氐哪戤嬁贪嫠嚾酥饕植荚谝栽靡乜h三奶奶廟村、許堤口村、駱駝山村為中心的一帶村落中,印制藝人也多散居在周邊鄉(xiāng)村,年畫店多開設在周邊運河沿岸的城鎮(zhèn)中。如上所言,當?shù)氐哪戤嬌a(chǎn)自出現(xiàn)之日就帶有了現(xiàn)代商業(yè)分工的色彩,張秋鎮(zhèn)只是作為當?shù)啬景婺戤嬙缙诘纳a(chǎn)銷售地存在,而并未發(fā)展成為區(qū)域性的年畫生產(chǎn)中心。
明末清初,當?shù)氐哪景婺戤嬌a(chǎn)經(jīng)營中心由陽谷縣張秋鎮(zhèn)轉(zhuǎn)移到聊城縣閘口附近的清孝街,且吸引了大量優(yōu)秀的刻版藝人與印制藝人投身此處,“清孝街上刷門神,一溜河涯紙作坊”①東昌俚曲《逛東昌》(光緒末年手抄本)。。清孝街上僅各式年畫店鋪就有數(shù)十家,兼營紙張、顏料的店鋪十余家,此外還有范縣、陽谷、莘縣、東阿、臨清、堂邑、高唐等州縣的年畫商人來此短期租賃鋪面或攤位出售年畫等。齊全的題材與豐沛的貨源吸引了南來北往的商船、張家口的駱駝隊、河北的大車幫、山西的毛驢群等紛紛前來批購,兼有其他年畫產(chǎn)地的年畫商人前來交流,更促進了當?shù)啬景婺戤嫎I(yè)的發(fā)展。同一時期,在附近的臨清、堂邑、高唐、莘縣、東阿等州縣的二十多個鄉(xiāng)鎮(zhèn)形成了數(shù)十個小的年畫生產(chǎn)中心,這標志著在聊城地域內(nèi)形成了一個龐雜的年畫生產(chǎn)系統(tǒng),且聊城木版年畫開始以一個完整的民俗物象出現(xiàn)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上所言,移民攜來的刻版技藝,民眾固有的精神需求,穩(wěn)定有序的民俗生活,甚至當?shù)刎S產(chǎn)的梨木資源,都成為聊城木版年畫生成的重要因素。因而,我們完全可以把聊城木版年畫視為區(qū)域內(nèi)民眾日常生活的自造物,是一種可視有形的民俗物象,對于當?shù)孛袼子^念的傳承與實踐有著獨特的價值。
(二)不同民俗物象之間的勾連
任何一種民俗物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與同一地域內(nèi)的其他民俗物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聊城木版年畫業(yè)作為一種在外來技藝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文化物象,勢必與區(qū)域內(nèi)的其他文化物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如與當?shù)氐拿嫠堋⒛嗨堋⒅乒P業(yè)、剪紙、葫蘆雕刻等,尤其與當?shù)乜虝鴺I(yè)的關聯(lián)最為密切,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當?shù)匕l(fā)達的刻書業(yè)才促進了木版年畫業(yè)的發(fā)展。
刻書業(yè)的繁榮為地方儲備了大量雕刻人才,也促進了相關行業(yè)的發(fā)展,木版年畫業(yè)應是最得其益。清康乾之際是我國木版年畫業(yè)的繁盛時期,聊城木版年畫也不例外,而此時也正是聊城刻書業(yè)最為發(fā)達的時期。清廷對小說的禁毀政策也影響到了當?shù)氐目虝鴺I(yè),使得一些從事刻書版插圖的藝人轉(zhuǎn)向年畫木版的刻制,壯大了當?shù)氐哪戤嬆景婵讨扑嚾岁犖椤<词故墙袢眨數(shù)啬戤嬁贪嫘律α恳捕嗍芙逃诮▏罂套稚绯錾淼睦纤嚾恕"趽?jù)當?shù)貙W者考證,清代刻版藝人徐廣成由刻書版轉(zhuǎn)行刻年畫木版,并成為三奶奶廟刻版藝人的杰出代表。在筆者的田野考察中,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刻版藝人都與刻書業(yè)有著某種淵源,或直接師承于刻書藝人,或?qū)W藝于刻字社等,而且刻版藝人也多以學藝于刻字社或先人從事刻書業(yè)以示技藝正宗。
在聊城木版年畫的有關研究中,存有其與當?shù)乜虝鴺I(yè)出現(xiàn)孰先孰后的爭議,如有學者認為當?shù)啬戤嬁贪嫠嚾巳后w源于刻書業(yè),“他們從為書籍雕刻插圖開始,擴展到年畫印版的創(chuàng)作”③王志剛、金維民主編:《聊城文化通覽》(下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7頁。。也有學者認為,刻書工人是從山西遷入此地的移民中部分掌握木版年畫相關技藝的一些人轉(zhuǎn)行而來,“聊城刻書業(y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木版年畫業(yè)的衍生”④楊朝亮:《刻書藏書與聊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頁。。通過梳理我國印刷史,可以發(fā)現(xiàn)山西平陽的刻書藝人與年畫刻版藝人早在北宋時期就已出現(xiàn),及至明初移民時二者也不可避免地被遷入聊城。此后,雖然兩個藝人群體可能相互從涉彼此的生計,甚至進行技藝的交流,但是并沒有影響各自技藝的傳承,聊城木版年畫業(yè)與刻書業(yè)的發(fā)展使得兩個藝人群體各得其利,又相互影響。無論是書版還是年畫木版刻制都受益于雕版印刷技術的成熟,二者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不過是雕版技術略有不同又密切相關的兩個分支而已。筆者認為,關于聊城木版年畫業(yè)與刻書業(yè)出現(xiàn)孰先孰后的爭論,則間接地證明了二者同源的事實。
由上可知,聊城木版年畫在清康乾年間最終形成了具有廣泛意義上的民俗物象,表現(xiàn)為有一批固定的從業(yè)人員,有一批忠實的接受對象,有一個穩(wěn)定的承繼區(qū)域,有一套嫻熟的生產(chǎn)技術乃至經(jīng)營理念,其生產(chǎn)乃至民眾接受等已經(jīng)成為一種穩(wěn)定態(tài)的民俗物象,并與區(qū)域內(nèi)的其它民俗物象保持著一定的互動。
三、作為群體生計的木版年畫
任何區(qū)域木版年畫的生產(chǎn)均非單純的藝術創(chuàng)作,而是部分藝人群體用以謀食的生計。無論是北方的楊柳青木版年畫、楊家埠木版年畫,還是南方的佛山木版年畫、灘頭木版年畫都是由區(qū)域部分民眾協(xié)作生產(chǎn),供多地民眾主要在年節(jié)使用的民間美術作品,其創(chuàng)作與生產(chǎn)的動機絕不是為了純粹的審美,而是為了滿足生活實用與信仰寄托的需要,是一種物質(zhì)層面與精神層面同步進行的能動性創(chuàng)造行為。年畫藝人在經(jīng)濟利益的刺激下積極地投入到年畫的刻版與印制中,年畫成品因為其所具有的心靈慰藉與精神寄托功能而被更多的民眾所接受,這種內(nèi)外并行的激勵促進了木版年畫業(yè)在各地的發(fā)展與繁榮。
有明以來,在政府的組織下,遷入聊城的大批移民雖得到了分配的土地、農(nóng)具、耕牛等,但是因為受頻仍的自然災害、戰(zhàn)亂等影響,土地所帶來的收益并不盡如人意。隨著人口的繁衍,“土地在男性繼承人之間平均分配保證了他們家庭的生計,也保證了這一家族血脈的延續(xù)。但這種做法也使家庭農(nóng)場的規(guī)模縮小,并組織了財富在一個家庭中連續(xù)兩代或三代的積累;另一方面,它使農(nóng)村社會和經(jīng)濟更容易發(fā)生變動。”①[美]馬若孟:《中國農(nóng)民經(jīng)濟: 河北和山東的農(nóng)民發(fā)展1890-1949》,史建云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1頁。當?shù)孛癖姙榱司徑廪r(nóng)業(yè)歉收對家庭的重要沖擊,就設法通過各種各樣的副業(yè)補充他們的農(nóng)事收入,木版年畫的刻印就是區(qū)域民眾所選擇從事的副業(yè)之一。
就當?shù)孛癖姷娜粘Ia(chǎn)生活而言,聊城木版年畫是作為區(qū)域內(nèi)一個相當大的民眾群體的生計而存在。與其他產(chǎn)地的木版年畫不同,聊城木版年畫有著自己獨特的生產(chǎn)系統(tǒng),是若干獨立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的鏈接,是一個覆蓋較大區(qū)域的生產(chǎn)集合體。我國其他地區(qū)的年畫生產(chǎn),多是家庭成員或師徒在一起從事年畫生產(chǎn),生產(chǎn)地點也多是自家閑置的房屋,在一家一戶之內(nèi)即可完成年畫的生產(chǎn),即使有專門的年畫店也多為前店后坊的生產(chǎn)模式,生產(chǎn)材料來源的半徑及關涉民眾的范圍都相對有限。相較之下,聊城木版年畫的生產(chǎn)系統(tǒng)至少存在著寫樣、刻制、印制、銷售等四個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參與人員眾多,歸屬群體不同,分布范圍較廣,且群體之間有相當?shù)莫毩⑿裕@使其擁有了與其他年畫產(chǎn)地完全不同的生產(chǎn)模式。這個生產(chǎn)模式內(nèi)部業(yè)務是相互合作,但利益又是相互博弈的,遠不如其他年畫產(chǎn)地的年畫藝人群體內(nèi)部之間的關系密切。當?shù)啬戤嫷曛魇悄戤嬌a(chǎn)系統(tǒng)運轉(zhuǎn)的組織者,其將寫樣先生、刻版藝人、印制藝人統(tǒng)籌到年畫生產(chǎn)的不同單元中,而后再將印制的年畫成品予以售賣,從而完成整個生產(chǎn)系統(tǒng)流程。
木版年畫自在聊城區(qū)域內(nèi)出現(xiàn),并由早期的三家發(fā)展到后來的數(shù)十家年畫店,就始終是作為一種群體性生計存在,其盛時從業(yè)人員不下千人。聊城木版年畫生產(chǎn)技藝傳承是維系該生計延續(xù)的根本,在維系及擴大藝人群體的同時,不斷構(gòu)建著群體內(nèi)部的人際關系,更折射著相關行業(yè)發(fā)展及其背后的社會文化狀況。木版年畫作為民間美術形式的一種,同其他民間手工技藝一樣,主要存在家族傳承、師徒傳承、作坊傳承三種方式,此外還應關注其社會傳承。關于木版年畫技藝傳承方式的劃分只是為了研究的方便,在現(xiàn)實傳承中多種方式是相互交叉的,并沒有截然分開的界限。無論哪一種傳承方式,都是教與學的過程,只是有的教與學環(huán)節(jié)或過程比較明顯,有的比較模糊而已,但是教與學的實質(zhì)內(nèi)容都是存在的。如其他民間藝術形式的傳承一樣,聊城木版年畫刻印技藝也沒有成型的教科書,甚至成系列的口訣都少有,傳承過程更多地是靠學徒的耳濡目染,除了學徒對刻印技藝的刻苦追求,更需要其心領神會的頓悟。尤其是在明清時期,多種傳承方式的混雜恰恰是當?shù)啬景婺戤嫎I(yè)繁盛的寫照,因為諸多的農(nóng)家子弟都想通過習得一門手藝謀得生計,以改善家境。由此而言,對作為群體生計的聊城木版年畫進行研究,能夠更好地剖析其在個人生存、區(qū)域社會發(fā)展與國家大勢演進中的多重角色及社會意義。
四、作為非遺項目的木版年畫
在我國28個省市的70多個縣市區(qū)都有木版年畫生產(chǎn)的歷史,甚至現(xiàn)在依然有不少縣市區(qū)的民眾還在從事著規(guī)模不一的木版年畫生產(chǎn)。在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名錄中,就有11個省市的12個縣市區(qū)的木版年畫得以入選,占同批次民間美術類非遺項目的23.5%。待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名錄公布之后,已有13個省18個產(chǎn)地的木版年畫得以入選該名錄。木版年畫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社會公共領域的重要文化產(chǎn)品,而且已經(jīng)成為市場經(jīng)濟中的重要文化商品。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今社會大眾關注木版年畫并非關注年畫本體,而是關注被冠以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稱謂的木版年畫,關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所挖掘出木版年畫自身涵載的文化意蘊及其時代價值。
任何一種木版年畫無論是作為一種民間藝術形式,作為一種活態(tài)的民俗物象,還是作為區(qū)域內(nèi)部分民眾的群體生計,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外界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尤以人文地理環(huán)境的巨大變化為甚。1855年對于聊城木版年畫發(fā)展而言,意義非凡。因為時年六月,黃河在河南蘭考銅瓦廂決口,大量的泥沙導致運河聊城段淤塞,聊城作為運河交通重鎮(zhèn)和水陸交通樞紐的地理優(yōu)勢頓失,當?shù)亟?jīng)濟大不如往昔,到了同治年間,當?shù)氐摹拔魃叹愀餍獦I(yè),本地人謀生為備艱矣”①[清]陳慶藩:《宣統(tǒng)聊城城鄉(xiāng)志》卷一《物產(chǎn)》。。此后,聊城逐漸演變?yōu)橐粋€相對封閉的平原城鎮(zhèn),本地所產(chǎn)木版年畫開始較少銷往外省他地,而是成為了僅供區(qū)域內(nèi)民眾享用的民俗用品。但從另一個層面上理解,人文地理環(huán)境的巨大變化使得當?shù)啬景婺戤嬆軌蛟谝粋€相對封閉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得以傳承,較少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更大程度上維系了其原有的藝術風格和藝術價值。
需要說明的是,聊城木版年畫的體裁與題材少有變化地流傳至今,目前尚能見到或尚在印制的年畫多是清中期流傳下來的樣式。有學者據(jù)此認為是因為當?shù)啬戤嬎嚾巳狈?chuàng)新意識而致,筆者對此并不敢茍同。一種藝術體裁與題材隨著其自身的發(fā)展雖然會有不斷地創(chuàng)新,但是也應該視不同藝術體裁與題材的具體情況而有所區(qū)別對待,因為創(chuàng)新是需要諸多的特定條件,而且一種藝術體裁與題材是否能夠創(chuàng)新并非由個人或群體所能決定,而是包括特定社會個體、區(qū)域社會、國家大勢等在內(nèi)的多種因素共同推動互促的結(jié)果。筆者對于聊城木版年畫體裁與題材少有變化的現(xiàn)象更愿意解讀為,習以成俗的年畫體裁與題材是當?shù)孛癖姽餐瑒?chuàng)造的理想形態(tài),是區(qū)域民眾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審美傾向、工藝技巧的具體體現(xiàn),而且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和傳承性,并與區(qū)域社會的民眾信仰與民俗活動相互依存,反映了當?shù)剞r(nóng)耕社會諸種文化的深厚積淀,符合區(qū)域民眾的審美傾向與心理欲求。對于此類為較大民眾群體參與共同創(chuàng)作的民間藝術形式,其藝術特征、審美風格、情感表達等都為較大民眾群體所影響和制約,而非僅個體年畫藝人所能為之。擁有如此龐大規(guī)模受眾的民間藝術形式,其藝術特征、審美風格、情感表達等所具有的穩(wěn)定性,也已成為其重要藝術價值的核心組成部分。對于在咸豐年間就逐步走入一個封閉區(qū)域社會的聊城而言,當?shù)氐哪景婺戤嬀蛷拇碎_始在一個有限的地域內(nèi)承繼,較少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即使抗戰(zhàn)時期冀魯豫邊區(qū)的年畫改造涉及到該區(qū)域,但是影響甚小。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國家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新年畫運動,而且以山東楊家埠為核心,但依然并未涉及到該地,故當?shù)啬戤嬻w裁與題材少有變化并非民眾缺乏創(chuàng)新意識,而是區(qū)域社會大環(huán)境變遷等諸多因素造成的。
聊城地域范圍內(nèi)分布且在傳承的木版年畫全部被冠以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而得以進入保護范圍歷時達8年之久,但迄今依然處于非理想的保護狀態(tài)。
保護工作熱鬧和學界喧囂的背后,依然有難以掩映的問題存在。雖然,在木版年畫入選各級非遺名錄之后,也遴選認定了一批相應的傳承人,但是“當前聊城木版年畫傳承人的保護是圍繞少數(shù)刻版藝人、印制藝人開展的,只能說是保護了聊城木版年畫傳承的個別環(huán)節(jié),把年畫技藝分割成了幾個割裂的技術模塊,而且被保護的傳承人并沒有能力使得整個生產(chǎn)系統(tǒng)得以運行,因而筆者從該意義上可以理解為聊城木版年畫的保護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②張兆林:《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集體性項目傳承人保護策略研究——以聊城木版年畫為核心個案》,《文化遺產(chǎn)》2019年第1期。。這種尷尬的狀態(tài)并非只是在聊城木版年畫的保護中出現(xiàn),因為“非遺名錄的申報采取了通過各級行政機構(gòu)、自下而上層層申報的方式,所以在申報過程中很難達成跨區(qū)域、跨民族的聯(lián)合申報,這就使得一些非遺項目在進入名錄之后似乎變成了某一地區(qū)的‘特產(chǎn)’,從而傷害到了孕育和保存有同樣文化事項的其他地區(qū)人民的情感和權(quán)益”①王霄冰、胡玉福:《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作的規(guī)范化與標準體系的建立》,《文化遺產(chǎn)》2017年第5期。。作為一種群體性生計的木版年畫,參與人員牽涉面較廣,而只有極少數(shù)人進入四級傳承人保護范圍的現(xiàn)狀,很有可能會間接導致文化的階層化,如補助資金、學習交流等對代表性傳承人的政策傾斜,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部分非代表性傳承人積極性,影響了其他藝人群體傳承的主動性,使“非遺”傳承的可持續(xù)性面臨著新的困境。
現(xiàn)有將聊城木版年畫視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的研究成果,多是套路式的理論推演或空洞式的保護想象,少有批判性的創(chuàng)設或啟發(fā)性的反思。從理性研究的角度而言,即使新世紀國家開展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作以來,聊城木版年畫所謂的復蘇繁榮也不過是一場文化保護工作造就的假象,多是部分文化精英選擇文化符號的人為再現(xiàn)與民間精神的時代解讀而已,其與木版年畫本身的社會價值實現(xiàn)相差甚遠,并沒有實現(xiàn)木版年畫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質(zhì)性再現(xiàn),民眾對待年畫的態(tài)度也由精神慰藉與年節(jié)象征轉(zhuǎn)為記憶懷舊與個性裝飾,當?shù)氐哪景婺戤嬕呀?jīng)從區(qū)域民眾的群體生計發(fā)展為少數(shù)年畫藝人承繼及部分學者珍視的文化遺產(chǎn),或個別部門標榜政績的一個點綴,而其真正的文化價值、民俗寓意等卻少有人問津。
余 論
藝術形式、民俗物象、群體生計、文化遺產(chǎn)已經(jīng)成為學界研究木版年畫保護的主要維度,其在為我們提供相應文化物象更為詳實訊息的同時,也讓世人看到了一個更為靈動復合的生活藝術世界。如明清以來,聊城木版年畫不僅是一種單純的藝術形式,還是一種混合的民俗物象,其更是區(qū)域內(nèi)民眾的一種群體生計,及至今日其已成為政府積極保護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就現(xiàn)實狀況而言,聊城木版年畫是一個集藝術形式、民俗物象、群體生計為一體的集約式文化物象,這也是其入選當今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的重要原因。當前學者關于聊城木版年畫的研究仁智互現(xiàn),探索了不同的研究維度,而由此產(chǎn)出的研究成果也為世人提供了其不同的側(cè)面,這為我們研究其他地域的木版年畫提供了借鑒,也可以由此觸發(fā)我們來思考當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運動現(xiàn)象之下更深層次的東西,尤其是物與人的關系,從而實現(xiàn)學術研究領域的“見人見物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