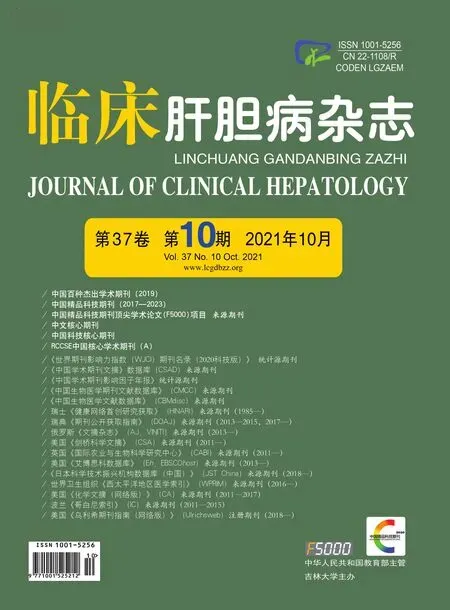黑色素瘤缺乏因子2在肝臟疾病中的作用機制及臨床意義
樂瀅玉, 張榮臻, 王挺帥, 陳寧芳, 毛德文
1 廣西中醫藥大學 研究生院, 南寧 530222; 2 廣西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a.肝病一區, b.脾胃一區, 南寧 530023
固有免疫應答是機體抵抗病原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線,在宿主識別、抵抗病原體感染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免疫系統除了抵御病原體之外,對源自組織或細胞損傷的相關信號亦能作出應答。目前研究認為[1],固有免疫系統細胞識別受體存在兩種模式:病原相關分子模式 (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 和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免疫細胞通過病原體源性信號的識別激活稱為PAMP,宿主源性信號的識別激活通常被稱為DAMP,而以上信號均由模式識別受體(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識別介導。根據其細胞定位的差異,PRRs分為膜結合型PRR和胞漿型PRR。膜結合型PRR包括Toll樣受體(TLR)和C型凝集素受體(CLR),而胞漿型PRR包括NOD樣受體(NLR)、視黃酸誘導基因-I樣受體(RIG-I樣受體)和黑色素瘤缺乏因子2 (absentinmelanoma 2,AIM2)樣受體(AIM2-like receptors,ALR)[2]。這些受體的配體特異性及其信號級聯反應的特征相對較好。其中,NLR和ALR是唯一能夠誘導炎癥小體組裝和活化的受體,而炎癥小體可以激活炎性caspases并導致炎性細胞因子(如IL-1β和IL-18)分泌,以及誘導細胞凋亡。炎性細胞因子的產生和細胞焦亡對肝臟具有重要的生物學效應,包括炎癥級聯反應的放大[3]。雖然以往對炎癥小體活化在肝臟疾病中的作用已有較多報道[4-7],但其多數研究集中于NLR相關的炎癥小體,尤其是NLRP3(NLR家族,含3個吡啶結構域)炎癥小體。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炎性小體AIM2在肝臟疾病中的作用機理及其臨床意義已日趨成為當下研究的熱點,本文就AIM2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HBV感染、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細胞癌(HCC)等肝臟疾病發病機制中的重要性進行歸納和探討,以期為其臨床治療提供新的思路和參考。
1 AIM2生物學特征
AIM2是細胞質雙鏈DNA(dsDNA)感應蛋白,可識別在細胞擾動和病原體侵襲期間釋放的雙鏈dsDNA,并觸發炎性體級聯反應的激活,在天然免疫防御中發揮重要作用。炎性體的激活會導致炎性細胞因子(IL-1β,IL-18)的成熟釋放,誘導細胞焦亡,啟動固有免疫應答。AIM2在結構上由兩個主要結構域組成:N末端pyrin結構域(PYD)和C末端HIN結構域。HIN結構域是寡核苷酸/寡糖結合的結構域,能夠與核酸、寡糖和蛋白質識別,并與胞質溶膠中的dsDNA結合,參與DNA復制、重組、修復及端粒保持等過程。PYD是死亡結構域折疊家族的成員,其在進化上高度保守,參與蛋白質間的相互作用和下游信號的傳遞,普遍存在于細胞凋亡和炎癥相關的蛋白質中。
目前,控制AIM2激活初始步驟的結構機制尚存在爭論,其主要存在兩種假說。假說一:在缺失dsDNA的情況下,HIN和PYD結構域彼此相互作用,從而使蛋白質保持自動抑制狀態[8]。結合域HIN是由帶正電的HIN結構域殘基和dsDNA糖磷酸主鏈之間的靜電相互作用介導[9],從而使PYD從HIN域中釋放出來,并與下游適配器發生相互作用。假說二:PYD的作用并非始終保持自動抑制狀態,當細胞濃度高達近10 000倍時,AIM2可以發生自組裝,促使PYD與接頭蛋白ASC (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RD) 結合,從而驅動AIM2炎性小體形成[10]。
ASC是由PYD和CARD組成的二元結構,而多個ASC分子的聚集會導致大片ASC斑點形成,并由于CARD-CARD相互作用而募集Pro-caspase-1分子。Pro-caspase-1分子自動裂解產生一個p20和p10亞基,兩個p20和兩個p10亞基形成一個活性異四聚體(活性caspase-1)[11]。活性caspase-1具有雙重功能:其一,裂解pro-IL-1β和pro-IL-18 并促進IL-1β和IL-18細胞因子的成熟和分泌;其二,加工修飾GSDMD蛋白并釋放N端片段[12],與質膜相互作用并促使膜孔的形成,從而誘導IL-1β、IL-18的成熟和釋放,并誘導炎性細胞凋亡和釋放細胞內容物[13]。
2 AIM2炎性小體的調節
值得注意的是,炎性小體肆意的激活會導致慢性炎癥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炎性小體的微調穩態在疾病的發生發展中至關重要。ASC的翻譯后修飾在炎性體的激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磷酸化、泛素化,其可調控AIM2炎性體的活化和降解[14-15]。此外,誘餌蛋白也可以通過干擾炎癥小體的組裝或限制配體的可用性從而參與炎癥小體的調控,此過程中PYD-only蛋白(POP)和CARD-only蛋白(COP)發揮著關鍵作用。目前,在人類中已經發現3種POPs(分別為POP1、POP2和POP3),其中POP3含有HIN-200 PYD特異性序列基序,并與AIM2的PYD具有高度同源性。研究[16]表明,POP3能夠通過與ASC競爭AIM2中的PYD結合位點來破壞ALR/AIM2炎性體復合物的組裝,進而抑制炎性小體活化和形成。COP的作用機制與POP類似,通過抑制 CARD-CARD相互作用參與調節。迄今為止,人們發現的3種COPs(CARD16、CARD17和CARD18)均編碼于人類基因組的caspase-1位點,其與caspase-1的CARD結構域高度同源,并通過阻止caspase-1向炎癥小體的招募而發揮作用。
HIN-200蛋白p202是ALR家族的另一種誘餌蛋白,其因缺少PYD結構,僅由兩個HIN域組成,又稱為“HIN-only蛋白”,可以抑制小鼠的AIM2炎性體而無法募集ASC。一個HIN結構域(HIN-1)與dsDNA相互作用,而另一個HIN結構域(HIN-2)與AIM2的HIN有較強的親和力[17-18]。因此,p202抑制AIM2可能存在兩種機制。機制一:p202可能與自身的HIN-1競爭DNA,從而限制自身對AIM2的可用性,同時還可能會抑制其他胞質DNA傳感器。機制二:p202直接與AIM2相互作用。研究[18]表明,HIN-2與AIM2的HIN發生物理相互作用,從而防止ASC聚集和caspase-1的募集。
3 AIM2在肝臟疾病中的作用
3.1 AIM2與NAFLD、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 近年來,隨著人們飲食結構的改變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NAFLD的患病率不斷升高。目前,全球發病率高達25.2%,亞洲發病率約為27%,其中至少有10%將會發展為肝硬化或HCC,從而使NAFLD成為終末期肝病的主要原因之一[19]。NASH是NAFLD更為嚴重和具有臨床意義的階段,臨床表現為肝細胞損傷、脂肪變性和炎癥,可能發展為終末期肝病和HCC。迄今為止,NASH具體的分子機制尚未完全明晰,但炎性活化和IL-1β釋放似乎在其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TLR4和TLR9通過髓樣分化初級反應基因88(MyD88)的激活和通過炎癥小體激活產生的IL-1β導致脂肪性肝炎。目前,有關探討AIM2在NAFLD小鼠模型中的意義的研究較少,其真實世界的人體研究更是缺乏。在一項關于NASH的蛋氨酸-膽堿缺乏癥小鼠模型的研究[20]發現,NASH與AIM2表達上調以及NLRP3炎性小體激活有關。NASH中炎癥小體基因的上調和IL-1β mRNA的誘導是依賴于髓系分化因子88(MyD88)信號傳導的調節。在NASH中MyD88的缺陷會削減AIM2、NLRP3、pro-IL-1β mRNA以及IL-1β蛋白水平的上調。此外,NASH中TLR9配體高遷移率族蛋白1(HMGB1)的水平也明顯升高。HMGB1是一種高度保守的核非組蛋白,其通過激活TLR家族的各個成員(TLR2、TLR4和TLR9)在受損細胞中發揮內源性危險信號的作用[21]。因此,在NAFLD中HMGB1-TLR軸可能是AIM2上調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項研究[22]表明,長期高脂飲食的雄性小鼠中AIM2炎性小體成分的mRNA表達水平升高,并誘發雄性小鼠NASH的發生發展。Gong等[23]發現,AIM2基因敲除(AIM2-/-)小鼠與野生型(WT)對照相比空腹血糖和胰島素水平升高,并且AIM2-/-小鼠在腹腔進行葡萄糖耐量試驗后出現葡萄糖耐受不良現象。經RNA測序顯示,p202的IFN誘導型基因Ifi202b表達顯著上調,并在AIM2-/-小鼠的性腺白色脂肪組織中炎癥信號升高。因此,證明了p202在介導AIM2-/-小鼠脂肪形成和炎癥增加中起關鍵作用。AIM2和p202可用作治療人類肥胖癥和相關代謝綜合征的潛在藥物靶標。
3.2 AIM2與HBV感染 HBV感染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慢性病毒感染。HBV感染在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行,HBV感染的流行強度因地域不同而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據報道[24],全球慢性HBV感染人數約有2.57億,其中西太平洋地區和非洲地區占比高達68%。亞洲HBV地方性流行程度不盡相同,多數亞洲地區均為中高流行區,少數為低流行區。全球每年約有88.7萬人因HBV感染的相關疾病導致死亡,其中肝硬化占30%,HCC占45%。我國肝硬化和HCC患者中,由HBV所致者分別為77%和84%。
HBV是一種可感染人類肝細胞的非細胞性包膜病毒。它包含一個約3.2 kb的環狀DNA 和部分dsDNA基因組,該基因組在肝細胞核轉化為共價閉合環狀DNA(cccDNA),作為病毒復制的轉錄模板。由于HBV感染導致的肝細胞損傷是通過針對病毒抗原的免疫反應介導的,同時AIM2是觸發炎性體級聯反應的dsDNA受體。因此,AIM2可能是參與HBV相關肝細胞炎癥反應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
龐秀青等[25]探討了AIM2 在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肝臟組織中的表達分布及其與肝組織病變程度的相關性。結果表明,AIM2表達定位于肝實質細胞的胞質內,其在正常肝組織極少表達,但在CHB患者肝組織表達顯著增加,且隨肝臟炎癥的加重而表達增強。患者肝臟組織AIM2積分吸光度值中位數在HBV-慢加急性肝衰竭組為19 772.48,其顯著高于CHB組的4 996.88(Z=5.008,P<0.001);CHB組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的2 296.49(Z=-3.028,P=0.002);患者肝組織AIM2表達水平與肝臟炎癥HAI評分正相關(r=0.707,P<0.001)。Wu等[26]研究了急性乙型肝炎(AHB)和CHB患者不同臨床階段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BMC)中AIM2的表達情況。研究結果表明,與CHB中的表達相比,AHB中AIM2、IL-1β和IL-18的表達更高。在免疫清除期的AHB和CHB患者中,AIM2 mRNA的表達與血清HBV DNA負荷、HBeAg呈顯著負相關,與IL-1β和IL-18呈顯著正相關。因此,AIM2的表達與宿主體內HBV的免疫清除率相關。近期一項研究[27]報道,AHB和CHB患者的PBMC中AIM2樣受體IFI16的表達水平上調。Han等[28]比較了CHB和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肝臟活檢中AIM2蛋白的表達。結果表明,CHB患者中AIM2的表達顯著增加并與HBV DNA負荷高度相關,而并非受血清HBeAg水平的影響。CHB患者中AIM2的表達水平(89.4%)顯著高于慢性丙型肝炎患者(8.7%),并且在CHB患者中,高HBV復制組(HBV DNA≥1×105拷貝/mL)中AIM2的表達顯著高于低HBV復制組(HBV DNA <1×105拷貝/mL),提示高HBV DNA負荷會導致AIM2表達增加。此外,AIM2的表達與CHB相關的炎癥活性高度相關,而與纖維化程度無關[28]。AIM2水平與CHB患者中caspase-1、IL-1β和IL-18的表達呈正相關。在對入侵微生物的先天免疫反應過程中,HBV DNA與AIM2的結合可能導致caspase-1的活化,誘導IL-1β和IL-18的釋放,進而在CHB的發病中起重要作用。此外,AIM2在HBV相關性腎小球腎炎(HBV-GN)中的作用意義也有所報道[29],HBV-GN活檢組織中AIM2表達水平(81.4%)顯著高于慢性腎小球腎炎(4.0%),并且與HBV-GN中HBV DNA負荷、caspase-1和IL-1β表達呈正相關。因此,AIM2炎性體激活可能會導致或加速HBV感染期間的腎臟炎癥的發生。
3.3 AIM2與肝纖維化、肝硬化 肝纖維化是由慢性肝損傷導致組織瘢痕形成和炎癥的過程,可進一步發展為終末期肝硬化和HCC。進行性肝纖維化多由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和NASH等疾病引起,以肝臟中細胞外基質過多沉積為特征。據統計,全球肝纖維化患者約有1%~2%,每年因肝纖維化死亡人數超過100萬人[30-31]。肝星狀細胞在細胞外基質沉積和肝臟纖維形成中發揮核心作用[32]。當發生嚴重的瘢痕形成時,纖維化會進展為肝硬化并引發嚴重的肝功能損害。即使此過程較為緩慢,但一旦發生肝硬化將可能會出現一些危及生命的并發癥,如自發性細菌性腹膜炎、肝性腦病、腹水等。
慢性炎癥在肝纖維化和肝硬化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炎癥小體在肝纖維化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機理也已成為當下研究的熱點,尤其是炎癥小體的活化在肝硬化相關并發癥的炎癥反應中扮演的角色。研究[33-34]表明,肝硬化患者腹水巨噬細胞中caspase-1和AIM2的表達水平顯著高于血液巨噬細胞,AIM2表達水平的上調使得腹水中的巨噬細胞促使dsDNA產生大量的IL-1β和IL-18,而NLRP3、NLRP1和NLRC4的表達沒有明顯差異。最新一項研究[35]表明,布魯菌感染可通過激活NLRP3和AIM2炎性小體誘導肝星狀細胞分泌IL-1β,并且布魯菌感染是依賴于功能性T4SS的存在機制以及caspase-1、NLRP3的參與共同誘導IL-1β分泌。值得注意的是,與布魯菌感染的WT小鼠相比,Aim2-/-小鼠的肝纖維化明顯減少。因此,炎性體NLRP3和AIM2在布魯菌感染期間的肝纖維化調節中起關鍵作用。研究[36]表明,在曼氏血吸蟲感染的小鼠肝臟中,AIM2 mRNA和蛋白表達增加。此外,曼氏血吸蟲的可溶性卵抗原可誘導Huh-7肝癌細胞中AIM2炎性體途徑的激活以及AIM2 mRNA的表達。但是,AIM2激活是否有助于血吸蟲病期間的肝纖維化的形成仍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3.4 AIM2與HCC 原發性肝癌是目前我國第四大常見惡性腫瘤,并且是世界范圍內癌癥相關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病死率在所有腫瘤中排名第二。迄今為止,HCC是最常見的原發性肝癌,約占所有病例的85%~90%[37]。由于該病起病隱匿、病情迅猛、惡性率及病死率高等特點,故給患者的經濟及社會醫療帶來沉重負擔。HCC病因主要包括HCV或HBV感染、酗酒、NASH,其中高達84%HCC患者是由HBV感染所致。通常慢性肝臟炎癥伴隨著HCC發生發展的整個過程,因此,由炎性小體介導參與肝癌發病的機制已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重點。
馬小敏等[38]開展了一項關于AIM2對HCC作用效應以及其分子機制的研究,結果表明:與正常肝組織相比,AIM2在肝癌組織中mRNA及蛋白的相對表達水平明顯下調,且其表達水平與腫瘤體積、大小、臨床分期和病理分級等疾病相關的臨床指標呈顯著性負相關。體外過表達AIM2能夠促進AIM2-ASC-Caspase-1炎癥小體復合物的形成,并通過炎癥小體的活化,抑制mTORC1信號通路的活化,而進一步發揮抑癌效應;相反,抑制AIM2的表達則可促進肝癌細胞的惡化。上述結果也與陳洪濤等[39]、Chen等[40]的體外實驗結果相符。因此,通過上調AIM2的表達以及開發靶向mTORC1信號通路的藥物為AIM2缺失表達相關HCC的治療提供了新思路。同作者的其他研究表明[41],肝癌細胞中AIM2的外源性過表達降低了移植腫瘤的生長,并伴隨著mTOR-S6K1途徑的減少。在體外,AIM2表達抑制HCC細胞系的增殖和集落形成。但是,Chen等[40]的研究結果并非如此,他們認為HIM細胞系中的AIM2過表達或沉默不影響細胞增殖。Martínez-Cardona等[42]使用二乙基亞硝胺(DEN)構建大鼠動物模型,研究了AIM2對肝癌發生發展的影響。令人驚訝的是,該模型中AIM2或caspase-1/11基因失活可防止HCC的發展。尤其是在肝癌發生的早期階段,AIM2缺乏似乎顯得尤為重要。DEN給藥48 h后,AIM2-/-小鼠肝臟的急性肝細胞損傷、炎癥和增殖標志物的表達均得到改善。AIM2缺乏也與肝臟中caspase-1激活和IL-1β生成的減少有關,這表明AIM2在DEN誘導的肝臟損傷中有助于炎癥小體的激活。AIM2蛋白和mRNA在肝Kupffer細胞中高表達,并在AIM2刺激下產生大量的IL-1β。值得注意的是,當從DEN處理的小鼠肝臟中分離出Kupffer細胞時,IL-1β的產生仍進一步增加,其提示了致癌性肝損傷可能對細胞中的AIM2激活起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AIM2在HCC中的利與弊均有所報道。AIM2在這些研究中截然不同的作用看似格格不入,其實反映的是AIM2在不同疾病階段(晚期HCC vs早期HCC)或不同細胞類型(HCC細胞vs非實質肝免疫細胞)中作用的差異。因此,AIM2可能根據腫瘤的類型(鱗狀細胞癌、結直腸癌、HCC)、疾病的病因、被激活的細胞類型、疾病的階段和炎癥小體的參與而發揮不同的作用,但尚需更多的研究進一步論證和探討。
4 小結與展望
AIM2作為一種DNA敏感型炎性小體,不僅在固有免疫應答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在不同肝臟疾病的發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AIM2僅在部分肝臟疾病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機制得以闡述,但仍未完全明晰,有待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以明確更多的功能和機理。并且,AIM2在其他肝臟疾病的表達機制及臨床意義的相關研究少有報道,尚需對該領域進一步深入探索,以期為肝臟疾病的臨床防治提供新的策略和實驗支撐。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樂瀅玉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撰寫文章;毛德文負責研究選題,指導文章撰寫;張榮臻、陳寧芳負責設計論文框架,起草論文;樂瀅玉、毛德文、王挺帥負責修訂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