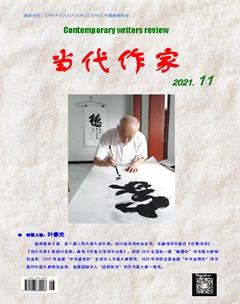風雪求學路
王斌
那一年,十四五歲的我開始上初中,要到離家七華里外的城四家子學校讀書,每天步行往返得走兩個多鐘頭。那時騎自行車的人還不多,農村很多地方沒有公交車,多數人出行還是靠馬車和走路。因我家兄弟多,家境貧困,一輛自行車一百多塊錢根本就買不起。那時北方的冬天零下平均都在攝氏20度以上,寒風凜冽,刺骨難耐,滴水成冰。我們七顆樹屯有男女生十八名同學,都懷著學點知識改變命運的夢想,每天三五成群興高采烈地迎著呼嘯的北風一步一步地向遠方的校園走去……
早上上學時,啟明星還掛在屋檐上,我便從熱乎乎的被窩里爬起來,母親已經把早餐和午飯做好,再三叮囑多吃,吃飽了暖和,并把飯盒裝得滿滿的。說是飯,其實是用玉米面做的餅子,菜是“葷”的,大多時候是麻雀炒咸菜,也時有一些燉菜,還算是“小康生活”。那時我的穿戴還算“時髦”,除了母親煤油燈下一針一線做的能防風御寒的棉衣棉褲外,還有父親親手縫制的羊皮襖、羊皮套袖、羊皮帽子,名副其實的一身“洋貨”。更使我難忘的,還有一頂平時舍不得戴的,也是父親為我精心制做的至今沒有申請“專利”的雪白的鵝皮帽子,我小心翼翼的收藏了很多年。腳蹬一雙蓄滿了烏拉草的烏拉鞋,面戴一副白色口罩,由于呼出的熱氣遇冷放熱,凝華成小冰晶掛在了眉捷和額頭,進入校園猛然間根本就無法辯認出男生女生,著實成了“圣誕老人”,不時引來同學們一片哄堂大笑。
那時學校的教室是干打壘土坯房,非常簡陋,夏天通風涼爽,冬天教室內還是很溫暖的。學校沒有經費買煤,同學們就你拾一筐玉米囊,我拾一筐牛糞生火取暖。說起拾牛糞還有一個令人難忘的讓人能把大牙笑掉的笑話:那是冬季的一個早晨,因為我們要在上學的路上拾牛糞,比往日起的更早一些,看不清是干牛糞還是濕牛糞,隔夜的會結凍成砣砣,誰知道這該死的牛比我們起的還早,居然抓上了還有余熱的牛屎,真不知所措,真叫人翻胃,還好,一付手悶子保護了差點被玷污了的那雙青春小手。
我們學校的學生先不說學習有多好,特別是象我們這些離校較遠的農村學生,能夠每天不遲到,不早退,不曠課就算是“三好學生”了。一個冬天不知道要下幾場膝蓋深的鵝毛大雪,也不知道一場大雪要多久才會融化。那一刻,偉人毛澤東宏偉壯觀的詩句在我的眼前展現出了一幅更加壯麗雄渾的圖景:“漫天皆白,雪里行軍情更迫”。“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那厚厚的皚皚的白雪,猶如在地上織成了一床潔白的毛毯,鋪滿了道路,鋪滿了草地,走上去覺得就象踏在松軟的沙灘上,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腳踩的深度不同,發出的聲音也不相同。我們逢雪天走路都要小心翼翼,都要緊盯著那熟悉且又隱約的通向遠方學校的路徑直走去,不敢偏離,因為在那寬擴的草甸子上,有很多人挖甘草藥材時留下的深坑,不小心就會掉進去變成北極熊,那可就知音難覓了。回頭望去,那一串串腳印好似一支校園歌曲的五線譜,一首人生浪漫進行曲。
遇到雪天,同學們都會主動帶上鐵鍬或掃帚和老師一起打掃操場上的積雪。這時也是同學們最開心的時刻,滾雪球,堆雪人,打雪仗……。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個淘氣的同學按照班花的模樣堆了一個雪人,不料引來了一場“群毆”,大家用自制的“手榴彈”一刻不停的向對方猛烈“攻擊”,“彈片橫飛”,“雪洗戰袍”,男女混戰,亂作一團。嬌柔的女同學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那時的我已情竇初開,青春荷爾蒙逐漸釋放,時不時會偷偷向那個天生一張白晰的瓜子臉,紅潤的嘴唇,一雙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烏黑發亮梳著兩條齊腰大辮子嬌美漂亮的班花瞄上幾眼,此時的我心太軟,手自然也沒有下得那么很,那么重,還好,老師的制止終結了一場“雪腥”大戰,那一刻我們都很開心。
遺憾的是,我們七顆樹屯這“十八名羅漢”“雪戰”到底的只有劉春和、鄒海、徐盛良我們這四位男同學。
那一年,我們在以“黃帥”、“張鐵生”為學習榜樣的浪潮中初中“畢業”了。
那一年,我們又開始了徒步走向十六華里外的德順中學高中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