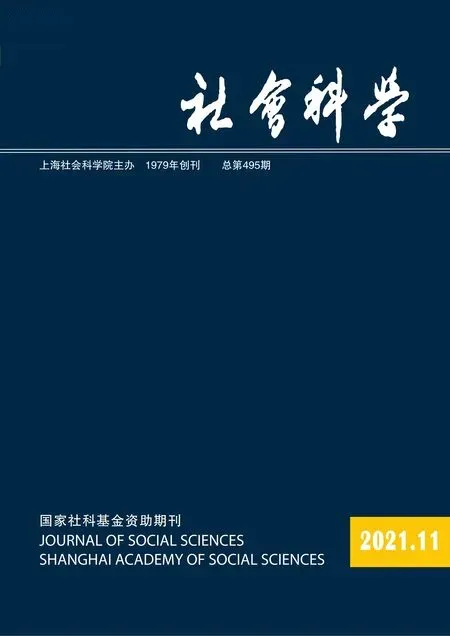明代生員的輿論自覺與社會意義*
展 龍
明代學校之盛,為唐宋以來所不及,學校數量空前,生員數目可觀,(1)涉及明代生員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日本學者夫馬進《明末民變和生員:江南都市輿論形式和生員的作用》(《地域社會的視點論文集》,1982年),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郭培貴《明史選舉志考論》(中華書局2006年版),尹選波《明代學校生員政治活動述論》(《求是學刊》1999年第4期),范金民《鼎革與變遷:明清之際江南士人行為方式的轉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趙毅、武霞《明代基層士人中的藍袍大王——傳統士人精神的背叛者》(《西南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等,所論多集中在明代生員科舉教育、社會生活、經濟特權、政治出路、行為方式等方面,而關于生員輿論問題論者尚少。“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2)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1頁。由于深受儒學熏染,明代生員的思想觀念和價值理念大致趨同,且未出封建正統思想的范疇,因此生員這一特殊社會群體具有強烈的文化認同感和社會凝聚力。明代中后期,學宮敗敝,大批生員無處肄業,只好脫離學校,放棄仕途,轉而遁入學風相對自由、開放、多元的民間書院、私塾和會社,并以“文化人”的身份,發揮著傳統士人獨具的文化功能;或淪落民間,游離于士林學界,徘徊在市井村落,并以“游民”的身份,切身體驗著如同普通民眾一般的生活艱辛和人生愁苦。如此,書院、私塾以及更為廣闊的民間社會,成為多數生員安頓心靈、尋求慰藉、踐履價值的普遍路徑。亦如此,生員群體最易在復雜時勢的刺激下,在有識之士的導引下,在廣大民眾的推助下,更加自覺地介入輿論活動,參與對社會政治的激憤斥責和激情評斷,蔚為伸張大義、洞觀輿情、監督政治、澄清世風的社會力量,成為活躍于民間社會最富激情、最具活力的輿論清流,并以異樣的情緒效能、輿論力量不斷影響著明代復雜多變的輿論生態和價值秩序。
一、生員輿論自覺的生成境域
明代生員別稱秀才、茂才、庠生、青衿相公等,大體包括地方儒學生員和國子監貢生兩類。(3)陳寶良:《明代學校生員的別稱與種類》,《中州學刊》2003年第2期。其中,地方儒學生員可分為府、州、縣的廩膳生(廩生(4)展龍:《明代廩生釋論》,《社會科學輯刊》2015年第2期。)、增廣生(增生)和附學生(附生),都司學、衛學的軍生、武生及宗學的宗學生等;國子監貢生則分為歲貢生、選貢生、恩貢生、納貢生等。按照學業狀況,明代生員又有閑居生員、在讀生員、充吏生員、黜退生員和肄業生員之別。明代生員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擁有一定的政治前途,更重要的是他們與下層民眾接觸廣泛,聯系密切,且常以道統的維護者和踐行者自居,積極關注朝政、點評時事、品核人物,發出集體意見和情緒,此即生員輿論。明代生員之所以能夠形成群體性輿論,蓋因其意識到自身的集體能量和廣泛影響,并擁有共同的理想目標和價值取向,而其群體輿論得以形成的現實契機則在于:一旦有突發政治事件或社會問題,極易引起生員關注并結成群體,從而引發輿論,“如今之諸生,動輒呼朋引類,搖唇鼓舌,持官府長短,自謂以是非為己任,不思正言猶戒出位,而況橫議”。(5)陸文衡:《嗇庵隨筆》卷三,吳江陸同壽1897年刻本,第4頁。
明廷養育生員,旨在“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6)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上》,第21頁。但是,若生員讀書不專,心思不定,擾亂綱紀,明廷便會嚴加禁止。洪武十五年(1382),明廷頒國子監學規及禁例十二條,鐫立臥碑,置明倫堂之左,(7)張廷玉等:《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686頁。警醒生員言行,嚴控生員輿論,規定:天下利病,諸人皆可直言,惟不許生員輕易言論,“軍民一切利病,并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即使生員遭遇冤抑,也只許“將實情自下而上陳告,毋得越訴”,除非府、州、縣及布政司、按察司不為受理,或聽斷不公,“仍前冤枉者,然后許赴京申訴”。此類禁例,旨在嚴禁生員議論國事,干預地方司法,“如有不遵,并以違制論”,輕則跪誦碑文,重則追奪廩膳,罷黜為民,發配充軍,甚而有殺身之禍。(8)申時行等:萬歷《明會典》卷七八《學校·儒學》,載《續修四庫全書》,第790冊,第412-413頁。明廷雖然標榜廣開言路,“直言毋隱”,(9)《明太祖實錄》卷一五,甲辰年五月戊午,(中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1962年,第198頁。但對生員的政治活動和日常言論卻嚴加管控,試圖將其塑造為不問世事、安分守己的青袍書生。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御史趙言等上書,建議明廷嚴禁生員“妄言”,認為:“學校之設,本以作養人材,窮理正心,期有實效。今天下生員,多不遵師訓,出位妄言,非希進用,則挾私讎,甚失朝廷教養之意,宜令有司嚴加禁止。”(10)《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六,洪武十五年七月乙卯,第2290頁。緣此,明廷長期施行學規禁例,并對生員言論有特別規定:“有奇材欲陳便民利國之術者,許與教官詳議可否,同列姓名,然后上達。若其言有可取,仍命題考試文字,中式者不次擢用。如是,則可以杜絕妄言,激勵士風矣。”(11)《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六,洪武十五年七月乙卯,第2290-2291頁。至嘉靖十七年(1538),進而詔禁“各處游民及罷黜生員潛居京師建言希用者”。(12)《明世宗實錄》卷二一八,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丙子,(中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1962年,第4466頁。當然,明代也規定:若生員“學優才贍,深明治體”,且年及三十,愿意出仕者,也準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詞”,并呈報本學教官加以考察,“如是真才實學,不待選舉,即行錄用”。(13)申時行等:萬歷《明會典》卷七八《學校·儒學》,第412頁。
學生議政,淵源有自,“我國大學生之救國運動,始于漢,盛于宋,而復興于現代,史跡昭然”。(14)黃現璠:《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緒論》,載《民國叢書》第五編,第63冊,第1頁。其中,漢代太學生的“清議運動”、宋代太學生的“救國運動”等,皆是學生參與政治、公議時政之先例。明初生員不許言事,但洪武而后漸有改觀,一些生員不顧禁忌,違規言政,并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大體上,政治清明時,生員輿論相對沉寂,情態較為溫和;而權臣當道、小人恣虐、人心浮薄、政局動蕩、天下離亂時,生員輿論便會驟然升騰,異常活躍,即使朝廷嚴加禁止,生員也依然沖破學規,挺身而出,縱議時勢,慷慨持論,這在明后期表現得尤為突出。如天啟年間,禮科給事中熊奮渭上疏:“頃閱江西按臣生員被撻鼓噪一疏,益藩閹尉趙成等辱毆章縫之士,諸生張紹伊等鼓眾雄行,逼迫府官,徒步學宮。”(15)《明熹宗實錄》卷四二,天啟三年十二月壬寅,(中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1962年,第2200頁。崇禎時,各地生員多次以“臣”之口吻進言思宗,縱論時政。如崇禎十一年(1638)三月,晉江諸生蔡鼎根據“西游”見聞,進奏“云中邊守”情況,以為:“云中頻年饑荒,士馬艱食,較宣尤甚,巢丕昌、孔有德之徒,奸謀相引,豈可不早杜耶?”(16)《崇禎實錄》卷一一,崇禎十一年三月甲戌,(中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1962年,第322-323頁。十三年(1640)十一月,監生涂仲吉因黃道周忤旨被罷,疏言思宗:“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憤廬,稽古著書,晨夜不輟,孤蹤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純忠,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17)《崇禎實錄》卷一三,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壬辰,第390-391頁。但此疏被“通政司格之”,于是又有生員指責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次上書請求寬免黃道周,結果觸怒龍顏,“下獄杖之論戍”。(18)《崇禎實錄》卷一三,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壬辰,第391頁。十六年(1643)六月,桐城生員蔣臣議行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錢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19)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九《蔣臣奏行鈔法》,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51頁。為緩解財政壓力,思宗采納了蔣臣建議,設立鈔局,監造紙幣。次年(1644)三月,陳州生員張鑻于中左門進言“三策”,“首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大臣輔之”。(20)《崇禎實錄》卷一七,崇禎十七年三月己丑,第529頁。以上生員言論雖非“官話”,但其關心政治的熱情與建設性意見,同樣成為突破言路之禁的一股清流,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末民間社會輿論的政治取向和現實情懷,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當然,明廷禁止生員言事,有其合理理由:一是生員本業是讀書問學,若貿然議政,便是“有戾規矩”。(21)《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五月庚午,第2279頁。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陜西保安縣歲貢生員任時上所撰《參兩貞明圖》,禮部認為“其說不經”,詔法司訊治,并罷黜為民。(22)《明世宗實錄》卷三一四,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壬子,第5885頁。二是生員大多年輕氣盛,學識有限,一旦聽聞時勢,便激情難抑,輕率言事,只會適得其反。三是較之賢士名流,生員人微言輕,其言論既難左右地方事務,更難影響國家大政。四是生員乃國之未來,其行檢惟以養恬、養靜、守道、守身為第一要義,“我朝建立臥牌,諸人俱許言事,惟生員不許言事,蓋以養其廉恥,堅其德性,欲其異日有待而為,為國家效實用耳”。(23)馮琦:《宗伯集》卷五七《為遵奉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載《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冊,第7頁。在此情況下,明代生員言事是否合法,取決于政治需要和皇帝好惡。如嘉靖十二年(1533)正月,蒲州生員秦鏜“請奉皇考于太廟”,此有違世宗意愿,以致“以妖言論死”。(24)談遷:《國榷》卷五五,嘉靖十二年正月甲子,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3478頁。隆慶元年(1567)九月,因穆宗干預,兩京鄉試時,南京監生中式者僅數人,較舊額少了四分之三,揭曉后,考試官王希烈、孫鋋等至國子監拜謁文廟,遭到監生下第者數百人喧噪杜門。(25)《明穆宗實錄》卷一二,隆慶元年九月甲戌,第341頁。天啟七年(1627)十月,監生胡煥猷彈劾大學士黃立極等,熹宗“意不深罪之也,得以贖論”。(26)茅元儀:《掌記》卷四,載《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10冊,第387頁。明代生員的輿論行為雖障礙重重,但也并非全然無望,很多時候,生員也會力爭言事機會。如弘治十一年(1498)三月,生員汪瑢奏言,閣臣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妒賢嫉能,排抑勝己,急宜斥退”,迫于輿論壓力,劉、李疏言乞罷,孝宗不許,下瑢詔獄,劉健等上疏力救,方得釋放。(27)焦竑:《國朝獻征錄》卷一四《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靖劉公健墓志銘》,載《明代傳記叢刊》,第109冊,第465頁。蓋因如此,有人便開始質疑明初“生員不得言事”的禁例,晚明馮夢禎曾言:“高帝興言路,稱至廣矣。顧獨嚴于諸生,而臥碑之設廩廩然,何耶?豈罪其妄發耶?然其中豈無通經學古、留心世故而其言不可廢者,奈何以諸生錮耶……吾友賀君伯闇,諸生也,而有《救荒八議》。余讀之,或不無激言偏詞,而議論斐然,稱國華矣,豈徒為諸生重而已哉,奈何廢之?”(28)馮夢禎:《快雪堂集》卷一《賀伯闇救荒八議序》,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4冊,第53頁。馮氏所言,道出了晚明生員的心聲,誠謂:“夫言路之關于治亂,甚巨也。自古天下將治,言路先開;天下將亂,言路先塞。”(29)馮夢禎:《快雪堂集》卷一《李方麓待御抒衷疏草序》,第52頁。時人周亮工也對生員“不得干議朝政”的規定不以為然,認為“夫士生今日,既不得稍伸其議于當世,而猶動有傾危之慮”,(30)周亮工:《賴古堂集》卷一六《倪母朱太夫人七十序》,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400冊,第464頁。并為生員言事找理由:“伏讀欽定條約,生員罵詈官長者有禁,而從容跪稟,不激不亢者,未嘗禁也;鼓噪聚眾者有禁,而依期升散,不約而集者,未嘗禁也;言涉利害假公濟私者有禁,而事干學校,情關狐兔者,未嘗禁也。況未達之士,與已達之士,均當奉祖宗之憲章,寒素之士與貴介之士,均當受府縣之約束,未有此獨嚴而彼獨寬者也。”(31)佚名:《民抄董宦事實》,載《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第248頁。
明代生員輿論的生成傳播始終伴隨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的變動而不斷變化,而君主專制統治的政治體制及復雜多變的政治環境,構成生員輿論生成、傳播的總體政治空間。明代生員輿論是民間輿論的重要部分,明廷對此嚴加管控,側面反映了明代朝野輿論之間,基于某種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的差異,二者既始終存在某種關聯性和一致性,也時常存在一定的排他性和矛盾性。這一點在明代后期表現得尤為突出,甚至出現了“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的“怪事”。(32)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八《東林學案》,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30頁。可以說,明代生員輿論的生成境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輿論生態的演進軌跡。
二、生員輿論訴求的表達路徑
中國古代學生輿論是特定時局影響下的歷史產物,表現形式因時而異,既有漢代諸生抨擊時弊的危言深論,也有宋代諸生伏闕清議的振奮之辭。至明,君主專制空前加強,宋代“不殺大臣言官”(33)王明清:《揮麈錄·后錄》卷一《太祖誓不殺大臣言官》,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69頁。的歷史畫面有所改變,但深受儒學熏染的生員群體,依然秉循道統旨歸,勇敢承擔了明代民間社會輿論的制造者、傳播者和監督者的歷史使命。他們作為遠離權力中心的下層士人,很少有機會直接參與朝政,只好以清議、上書、謠諺、詩文等獨特的話語方式,表達政治態度,抒發政治情懷,客觀上成為政治體制之外另一股具有輿論監督功能的社會力量,不僅可以對違法、瀆職、貪墨的官員進行批判,且可以在皇帝言行有違禮制時上書直諫,制約皇權。他們無畏權勢,勇于擔當,敢于直言,與肩負監察重任的言官群體一道,共同勾畫出一幅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獨特歷史畫卷。
清議是傳統士人參與政治的一種獨特方式,即通過發表集體言論,表達對社會現象、政治形勢、當代人物的一種價值評斷,形成以“公論”影響時局的輿論風潮。清議首先突出一個“清”,即議事的基調符合儒家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這一評判沒有明確固定的界限標準,主要依賴清議者“志于道”(34)蔡節:《論語集說》卷四,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94冊,第602頁。“守于義”(35)張獻翼:《讀易紀聞》卷二,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26冊,第474頁。的內在道德志趣;清議所“議”內容雖不全與政治相關,但生員多以“臣子”自居,認為關注時政、針砭時弊,是激濁揚清的正道,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清議最多的還是政治問題, 他們以公共批評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對準時代的主題”,(36)林語堂:《中國新聞輿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一定程度上成為國家政治與公眾話語彼此互動的重要橋梁。
明代生員清議持續時間較為漫長且相當活躍,這與明代獨特的政治體制、嚴密的監察制度、復雜的輿論生態、多變的社會政局等時代因素休戚相關,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突發事件引發了生員關注現實的輿論熱情。更為重要的是,明代空前繁盛的官辦學校和日益勃興的書院教育為生員清議提供了輿論場域。漢代設立太學以來,特別是唐宋實行科舉制度以后,生員群體成為清議的發起者和主力軍,他們與士大夫聯合起來,互相標榜,互相照應,批評權臣奸佞,表彰清官廉吏,澄清世風士氣,對當時的社會起到了激濁揚清的重要作用。同樣,在明中后期,官辦學校徹底變為科舉制度的附庸,多數生員不再選擇學校肄業,轉而進入悄然勃興的民間書院,潛心問學,談學論道,陳論時政,臧否人物。也正因如此,此期對書院輿論嚴加禁止,甚至不惜禁毀書院,如嘉靖年間,按照御史游居敬的建議,明廷禁毀王守仁及門人所創書院,“戒在學生徒勿遠出從游”,并令“書院不奉明旨,令有司改毀”,尤其是那些“陽倡道學,陰懷邪術之人”,(37)余繼登:《皇明典故紀聞》卷一七,載《續修四庫全書》,第428冊,第251頁。更須嚴加禁約,不許循襲。此后,雖罷各地私辦書院,但“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至嘉靖以降,“凡撫臺蒞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38)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四《書院》,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08頁。萬歷七年(1579),首輔張居正擬旨,禁毀天下書院,“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凡先后毀應天等府書院六十四處”。(39)龍文彬:《明會要》卷二六《學校下·書院》,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417頁。之后,魏黨擅權,欲滅東林,再次掀起 “禁講”浪潮,“凡有倡建書院,不論省直州縣,立時改毀”。(40)《明熹宗實錄》卷五八,天啟五年四月己亥,第2705頁。
明代生員清議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41)楊伯峻:《論語譯注·季氏篇第十六》,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4頁。政治清明,治國有道,庶民安居,則言論宴然;反之,則人心惶惑,士風激厲,物議沸騰。可以說,清議已是對無序社會、衰敗政治的一種補救,“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42)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一三《清議》,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478頁。“其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一皆蕩滌”。(43)李延壽:《南史》卷一《宋武帝本紀》,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4頁。當然,清議的發起者與被議者往往從不同立場的辯難逐漸演變為道德層面的相互批駁,雙方不惜拉攏同道,網羅同志,長期以往,便會演變為激烈的政治斗爭,激起一波波輿論聲浪,“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書牘交于道路,請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44)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第23頁。由于專制權力不可能受制于社會輿論,因而既使是最顯公道、最得人心的清議,也難以真正緩解社會矛盾、矯正政治偏頗、撫慰民眾怨憤,或許明代生員的清議行為,至多是其排解郁悶、發泄激憤、申述情愫、安慰自我的無奈之舉罷了!與此相聯系,生員個人的輿論能量也較為有限,于是他們時常聯名言事,以期以集體的輿論合力引起官方的高度重視。僅以嘉靖朝為例,潞州儒學生員孫濡等聯名致仕官員李炫、坊都里老郭琦等,請“改州為府”。(45)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一三《改建潞州府治及添設兵備憲臣疏》,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4冊,第616頁。蒼梧縣學生員黎黻、嚴肅等聯名呈奏:“欲于縣之側,照依南寧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46)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三○《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3頁。生員夏時霖等與其父廷章僑居長樂鄉,曾“率其鄉人以堤議狀上公”。(47)萬衣:《萬子迂談》卷五《新筑黃梅縣長樂鄉堤碑記》,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9冊,第107頁。順天府生員陳珵男、陳大紳等奏張鶴齡等奸惡諸事,詞連致仕大學士張孚敬。世宗詔“以延齡等事與孚敬無預,勿問”。(48)《明世宗實錄》卷二百六,嘉靖十六年十一月癸卯,第4303頁。如此,生員的集體公論無疑成了“公眾利益的呼號”,(49)劉建明:《社會輿論原理》,華夏出版社 2002年版,第261頁。不僅引發了廣大民眾的普遍關注和集體共鳴,而且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不平則鳴、不吐不快、不公則忿的良好輿論氛圍。

謠諺源自民間,經口耳相傳遠播四方,形成輿論,“搖筆端以造歌謠,而撼官府”,(61)郭子章:《蠙衣生蜀草》卷九《學約》,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4冊,第699頁。“秀才最難結,一有不合,造謠言,投揭帖,最可恨”。(62)夢覺道人、西湖浪子:《三刻拍案驚奇》,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頁。關于明代生員造歌謠、投揭帖等輿論形式,日本學者夫馬進認為這是明季生員士變的常見方式;(63)[日]夫馬進:《明末反地方官士變》,《東方學報》,第52冊(1980年3月),第595-622頁;《“明末反地方官士變”補論》,《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第4號(1981年3月),第19-33頁。巫仁恕稱之為明清城市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64)巫仁恕:《明清城市群眾集體行動模式的影響與延續》,載《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337頁。陳寶良則認為士變是“一種對朝廷已有規例的反叛行為,多以激進的聚眾鬧事為表現特色”。(65)陳寶良:《明代生員與地方社會:以政治參與為例》,《明史研究》第八輯,2003年。實際上,歌謠、揭帖等是生員輿論的含蓄方式,也是生員針砭時弊、臧否人物的重要工具,具有更強的政治性和針對性。如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子嗣修高中榜眼,后三子懋修又中狀元,這種現象引起生員不滿,“有無名子揭詩于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探花郎。’后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66)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上《焚塵寄·科名》,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年版,第269頁。又《吳縣志》載:劉瑊為官清正,歸居鄉里,不聞外事,惟喜博覽,手不釋卷,(67)《吳縣志》卷六六上,民國二十二年(1933)鉛印版,第2冊,第96頁。但卻遭到生員匿名諷刺,原因何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一語道破:“劉(瑊)居鄉無修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恣。值其家延僧誦經,先有夜粘對于門云:‘陰府中羅剎夜叉,個個都愁兇鬼到;陽臺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賀惡人亡。’”(68)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六《蘇州謔語》,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67頁。可知劉氏的名聲并不好。同樣,山西督學憲臣袁繼咸,為巡按御史張可振糾劾,生員傅山等上《辨誣公揭》,替袁繼咸鳴冤。(69)傅山:《傅山全書》卷三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603頁。南太學諸生為驅逐阮大鋮,而作《留都防亂公揭》。(70)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二七《黃梨洲先生事略》,載《續修四庫全書》,第538冊,第603頁。萬歷福建巡撫趙可懷曾彈劾提學副使鄒迪光“狂肆”,內言:“一生員夜粘揭于臣門,臣稍懲之,迪光嫌其礙己,遂拂然去,各官留之堅不可挽。越一日忽自回,舉動乖張,殊非師范。”(71)《明神宗實錄》卷一五三,萬歷十二年九月庚子,第2840頁。對于此類揭帖、歌謠,若非出于公心、出自公論,明廷也嚴加禁止,理由是揭帖常是“含沙射影之謀”,謠諺也多是“浮文詭語”乃至“邪說”“異說”。(72)馮琦:《宗伯集》卷五七《為遵奉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第12-13頁。
此外,明代生員輿論的表達方式還有飛語、戲曲、俚語等,“今天下士風薄惡,日益月甚。自臣所親見者言之,署丞銜知府而刊飛語,生員毀提學而編戲文,舉人構怨于曹郎,輒刻《貧女嘆》;尚書積憾于巡按,乃著《猛虎篇》。其他或為民謠,或稱俚語,誕妄不根,更相傳報”。(73)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二《繩薄俗以正風紀疏》,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9冊,第149頁。終明一世,明令禁止傳播謠諺、俚語的情況極少,而清代禁毀小說、戲曲、民歌、榜文、告諭等不勝枚舉。僅此而言,較之清代,明代輿論的生成環境與傳播條件尚較寬松,大體呈前期沉寂、中期勃興、后期活躍的輿論態勢。(74)展龍:《明代社會輿論的歷史意蘊及啟示》,《山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9期。
三、生員輿論監督的社會功能
輿論作為公眾意見的表達,其產生及發揮作用的前提是輿論的公開性,因為個人意見上升為公眾意見的過程,必然經過意見的公開傳播以使民眾接受、討論和凝聚;而已經形成的公共輿論,想要有更廣泛的影響力和傳播度,就須進行更大范圍的傳播。古人言“公道在學校”,(75)王以旂:《王襄敏公集》卷三《贈大京兆黻庵柴公考績序》,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8冊,第85頁。生員作為學校的主體和士階層的一部分,具有得天獨厚的輿論優勢,“在最常涉入各類型城市集體行動事件的幾類人中,士階層,即生員階層占領導與參與人的比重最大,而且生員參與集體行動的類型非常多元”。(76)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頁。明代生員輿論的公共性在利益取向上貼近廣大民眾,涉及公共利益,“他們和城市中等階級反對派的較貧分子及平民反對派有較大的聯系,并和鄉村的農民分子以及一些破產的中小地主也有一定的關聯,于是他們在城市平民的呼應下,較能站在斗爭的前列”。(77)傅衣凌:《明代后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載《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110頁。同樣,明代生員的輿論功能也具有鮮明的批判性、建議性和監督性特點。
(一)批判性輿論功能
明代生員是最富激情、最具力量的輿論動員者和參與者,他們掀起的輿論行動,多是出于對社會不公、觸及切身利益的反抗,以期通過充滿激情的口誅筆伐、搖旗吶喊,維護公眾利益,發泄內心憤懣,甚至不惜生命,挺身而起,竭力抗爭。
明初,朱元璋重法繩下,生員稍有過失,即被懲罰,對此生員心存怨憤。洪武二十七年(1394),監生趙麟鋌而走險,張貼無名帖,抗議國子監虐待生員。趙麟的行為激怒了太祖,被殺示眾。(78)尹選波:《明代學校生員政治活動述論》,《求是學刊》1999年第4期。三十年(1397),太祖又在奉天門訓話監生,強調:“今后學規嚴緊,若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煙瘴地面。”(79)黃佐:《南雍志》卷一○《謨訓考下》,載《續修四庫全書》,第749冊,第288頁。成化十九年(1483),蘇州府儒學生趙汴等二十人以罵太監王敬坐罪。當時,王敬與千戶王臣等以購書為名,向南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錄《子平遺集》等書,生員“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迫遣至驲中亂箠之”,于是趙汴等罵曰:“汝輩擾害百姓不已,又欲害吾儒生耶?”王敬還京訴于憲宗,“以諸生不遵禮法,恣肆放誕為詞”,處罰諸生杖罪。(80)《明憲宗實錄》卷二四六,成化十九年十一月丁未,第4167-4168頁。雖然趙汴等人也因“不遵禮法,恣肆放誕”坐罪,然而其敢于反抗的精神名于一時,為人稱譽。正德年間,劉瑾用事,中外憤怨,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實名“指斥瑾罪惡數事”,有人謄寫賣之,為劉瑾邏卒捕得,下獄拷訊,不知其由。(81)陳洪謨纂,盛冬鈴點校:《繼世紀聞》卷三,載《元明筆記史料叢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7頁。隆慶五年(1571),浙江處州同知江應昴笞辱生員朱正色父朱昹,生員馮椿等呼引諸生數十人,訴于分守參議方岳,方岳不理,椿等遂群毆岳,鼓噪而出,事聞得旨:“生徒聚毆上官,大壞法紀令,撫按官竟其獄無事姑息。”于是,椿等十二人充軍,正色等三十二人各黜為民。(82)《明穆宗實錄》卷五四,隆慶五年二月癸卯,第1345頁。晚明市民反抗礦監稅使的斗爭,也曾得到生員的奔走聲援。萬歷中,礦稅日興,究其原因:一是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余萬;二是朝鮮用兵,費帑金七百余萬;三是播州用兵,費帑金二三百萬;四是營建乾清、坤寧兩宮和皇極、建極、中極三殿,以致國庫大虧。為了緩解財政危機,神宗自萬歷二十四年(1596)始,命中官王亮、王忠、王虎、曹金、劉忠、趙欽、張忠、魯坤、李鳳、李敬、楊榮、高淮、潘相、高寀、陳奉等赴各地擔任礦監稅使,掠奪財富。(83)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五《宦官傳二·陳增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805-7806頁。他們受命于皇帝,握有特權,橫行各地,“隨奏隨準,星火促行”,(84)《明神宗實錄》卷三三一,萬歷二十七年二月丁丑,第6133頁。“大珰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天下蕭然,生靈涂炭矣”,(85)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五《宦官傳二·陳增傳》,第7806頁。“諸稅監益驕,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激變”。(86)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三五《萬歷中礦稅之害》,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797頁。在此情況下,地方生員掀起了反對礦監稅使的斗爭。如萬歷二十八年(1600)四月,趙州生員人等“抗擾開采”。(87)《明神宗實錄》卷三四六,萬歷二十八年四月甲申,第6449頁。此后,在武昌反對稅使陳奉的斗爭中,當地生員沈希孟、張奕業、沈機等赴撫按衙門控訴稅使,群情激憤,蜂擁而至。當時,稅監陳奉“播虐全楚”,沈希孟等一時激憤,以致被“拏問”。(88)《明神宗實錄》卷三四九,萬歷二十八年七月戊午,第6544頁。聞此,朝野嘩然,紛紛救助,“免逮諸生……以收士子之心”,(89)《明神宗實錄》卷三四九,萬歷二十八年七月乙丑,第6549頁。“乞皇上特令暫釋,其陳奉并孟學等亟賜逮系,以雪楚人之憤”,(90)《明神宗實錄》卷三四九,萬歷二十八年七月丁卯,第6551頁。后經撫按“曲為解諭,眾勢稍緩”。(91)文秉:《定陵注略》卷五《軍民激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第696頁。萬歷四十四年(1616)“民抄董宦”案,也是生員輿論鼓動的結果,他們“傳札而起,三月十四日鳴于府,十五日鳴于庠”,(92)佚名:《民抄董宦事實》,載《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第228頁。要求懲治奸惡,并暗中傳播檄札,鼓動民眾,很多士民紛紛加入,追從生員反對苛政暴斂,控訴稅使惡行。
天啟中,魏忠賢專權,生員言事者驟多。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激起反對閹黨的輿論高潮,東林黨也因此遭到殘酷迫害。在各地護衛東林志士、反對閹黨亂政的運動中,生員群體前赴后繼,大聲疾呼,發出了封建社會晚期最為強勁、最富激情的輿論呼聲。它不僅推揚了東林賢者的“清白”之舉,也踐履了生員群體的“清議”之志,“由是深山窮谷,雖黃童、白叟、婦人、女子,皆知東林為賢。販夫豎子或相消讓,輒曰:‘汝東林賢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至今農夫野老相傳,以為口實,猶諜諜不休焉”。(93)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高攀龍傳》,載《明代傳記叢刊》,第5冊,第152頁。如天啟七年(1627),嘉興縣貢生錢嘉徵上《劾逆珰疏》,參魏忠賢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無圣;七濫爵;八掩邊功;九朘民;十通關節。”(94)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五《宦官傳二·魏忠賢傳》,第7824頁。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于上”。(95)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賢亂政》,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64頁。
(二)建議性輿論功能
明初禁止生員言“軍民利病之事”,但實際上,生員條陳時弊常有發生,如洪武二十五年,詔求諳熟歷數者,山東生員周敬心上疏論及時政數事,他以“德”開篇,建議太祖治國,應仿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以求天下承平,國祚綿長;又徑言連年征戰,“役過煩,賦斂過厚”,民不堪負,黎民失于教化,法度失于嚴苛;最后鑒于太祖“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建議其厚德而寬刑。(96)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三九《周敬心傳》,第3998-3999頁。此疏直陳時弊,言辭激切,毫無諱忌,對明初弊政言之甚詳,斥之有理。太祖雖心存不悅,卻也默然接受,給予“報聞”。(97)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三九《周敬心傳》,第3999頁。此后,隨著生員輿論日漸活躍,他們提出的合理建議時常被采納并付諸實踐,在社會公共領域,生員輿論發揮了一定的建議性功能。
一是監督考核。明中期以后,生員聲望日高,甚至與鄉紳同列,每當地方出現紛爭,生員便會出面調停,維護鄉里利益。顧炎武在儒生陳梅墓志銘中寫道:“陳君視余年長以倍,于縣中耆舊名德,以及田賦水利一切民生利病無不通曉……里中凡有繇役爭訟之事,君未嘗不為之調劑,或片言立解。當天啟之末,縣之豪宦縱其仆干魚肉鄉民,而獨于君之居里無所及。至今民間有不平之事,輒相向太息,以為陳君在,當不令我至此也。”(98)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六補遺《常熟陳君墓志銘》,第160-161頁。如果鄉里能有如陳梅這樣德才兼具的生員,既可幫助官府管理地方事務,又能從中調解民間爭訟,甚至可以制止豪強禍亂鄰里,實乃一方之幸。此外,在地方官員考核中,生員的意見有時也是考核的重要依據。僅以宣德史實為例,都御史顧佐曾言:“布政、按察二司暨巡按監察御史,往往偏信鄉都里老、甲長、學校生員等之言,定為去留。”(99)《明宣宗實錄》卷九四,宣德七年八月壬子,第2139頁。如宣德八年(1433)二月,陜西鳳翔知府韓福為官廉潔,將以母憂去官,生員、耆民等九百八十余人訴于巡按御史倪杰、按察副使郭振,“乞為奏留”,宣宗允之,命起復還任,(100)《明宣宗實錄》卷九九,宣德八年二月庚寅,第2220頁。十年(1435)七月,起復舊任。陜西岷州衛經歷許罍丁憂去職,生員劉牧等百三人各保許罍“蒞事公勤,修舉學校,民甚懷之”,乞留職任事,巡撫官以聞,英宗以岷州地處邊陲,許罍“能得下情,可嘉也”,特從所請,以慰人望。(101)《明英宗實錄》卷七,宣德十年秋七月甲戌,第130頁。可以看出,明代地方官府和監察御史在考核官員、巡按地方時,不親身查訪,僅按生員等民間輿論,就決定了地方官員的去留。其間,雖然生員不乏“小人”,“假公濟私,圖報恩復仇”,(102)《明宣宗實錄》卷九四,宣德七年八月壬子,第2139頁。但從側面也反映了生員輿論的重要性。地方官員不得不重視生員的建議,有人為確保考課過關、獲得升遷,甚至不惜討好生員。
二是報災救災。如宣德四年(1429)八月,臨洮衛儒學生員張敘鑒于國家預備倉存在“典守者以粟給民,不以時征還官,或侵盜為己用”等問題,建議有司“查究原儲糧數,及未還官者征收入倉”,如此,才能使“國有蓄積,民無饑餒”。對此建議,宣宗從之。(103)《明宣宗實錄》卷五七,宣德四年八月丙申,第1367頁。正統五年(1440 )六月,監生王玙上言:途經鞏昌府寧遠、伏羌二縣,“見民俱食樹皮草根,有婦餓死澗傍”,(104)《明英宗實錄》卷六八,正統五年六月甲午,第1317頁。請朝廷救濟民難,“速發倉廩賑貸,流移者招撫而驗口給之”。英宗命行在戶部“即移文賑恤”,并對無視災情的官員予以處治,“有司坐視民患者,另行處治”。成化二十一年(1485)四月,監生虎臣上奏:近年來陜西饑荒頻仍,“蓋因官司貪縱殘暴,不恤民艱,賦役不均,賑濟無法,剝下奉上,私便身圖;藩憲失于覺察,巡撫溺于因循,臺省不以告,朝廷未之聞,隱忍蒙蔽,以至于此”。不僅如此,當時河南和山西也有災害發生,若不救濟,“逃移死亡者日眾”。(105)《明憲宗實錄》卷二六四,成化二十一年四月癸丑,第4471-4472頁。為緩解民困,虎臣請求朝廷通過設法勸分、官倉預借、支官銀糴買、官民納粟等途徑籌集糧食,經“多方區畫,得糧數百萬石”,量撥被災地方供給賑濟。(106)《明憲宗實錄》卷二六四,成化二十一年四月癸丑,第4472頁。在此過程中,生員時常提出建設性意見,既可幫助地方官府防災救災,又能代表廣大民意。如虎臣提出的“三賦役”,即是緩解民困之良策,“比及三年豐收之后,定立三等賦役文冊,一里之中貲產富余者為上戶,家道充足者為中戶,衣食不給者為下戶,明置板榜三面懸諸申明亭,諭眾知悉,凡有糧差依此科泒。仍敕憲臣榜行天下,如此則官司知懼,賦役惟均,民庶安生,災變不作”,被認定“實為便民”。(107)《明憲宗實錄》卷二六四,成化二十一年四月癸丑,第4472-4473頁。
三是建言獻策。明代生員積極參與地方事務,踐行“臣子”義務,并通過議論國事,直抒己見,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建設性意見。如族表、祭祀鄉賢、孝子、節婦等,生員均可參與,“有未舉者,諸生商榷舉之;舉之未正者,商榷請廢之”。(108)海瑞:《海瑞集》上編《教約》,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8頁。正因如此,明朝重視利用生員言論檢核地方官員,而地方官員也希冀借助生員的評議獲得遷轉晉升的機會。明中后期,生員群體突破學校界限,結社為盟,通過“使性”“清議”等輿論活動參與朝政,干預科考,“當時南北風氣,皆鋟私所作制舉業,以詡詡自矜,而揚越吳楚籍甚。其中魁然雄鳴者,執牛耳以麾一方之人文,莫不翕然奔之若狂,謂之操選政者,無慮若漢末之清議,魏晉之中正,不入此不得為名士也”。(109)黃宗會:《縮齋文集》,《王元趾先生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136頁。如嘉靖十六年(1537),“應天府進試錄,考官評語失書名,諸生答策多譏時政”。(110)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三《儒林傳二·吳悌傳》,第7280頁。隆慶五年(1571),劉元卿參加會試,“對策極陳時弊,主者不敢錄”。(111)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三《儒林傳二·劉元卿傳》,第7292頁。天啟四年(1624),艾南英參加鄉試,“對策亦有譏刺語”。(112)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傳四·艾南英傳》,第7402頁。天順年間,國子監祭酒邢讓因擅自挪用生員伙食費被逮治,監生李錦“率眾抗章,白其非辜”。(113)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一·李錦傳》,第7231頁。正德年間,淮王府的旗校與生員發生沖突,提學官李夢陽查明真相,鞭打旗校。這惹怒了王府,淮王派人進京告狀。明廷派大理寺卿燕忠前往處理,燕忠不問事情原委,貿然將李夢陽投入大獄,引起生員憤懣,奔走相告,為夢陽伸冤,“諸生萬余為訟冤”。(114)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六《文苑傳二·李夢陽傳》,第7347頁。至晚明,生員言事,蔚為風潮。如崇禎九年(1636)三月,黃安縣學生鄒黃遵旨具奏,薦舉倪元璐;(115)談遷:《國榷》卷九五,崇禎九年三月乙丑,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733頁。十一年(1638)三月,晉江諸生蔡鼎言及關外諸堡的增減;(116)談遷:《國榷》卷九六,崇禎十一年三月甲戌,第5803頁。十三年(1640)七月,浙江平陽諸生楊允中敷陳王道;(117)談遷:《國榷》卷九七,崇禎十三年九月辛巳,第5875頁。十一月,監生涂仲吉上奏“黃道周通籍二十載……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118)談遷:《國榷》卷九七,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壬辰,第5881頁。上述生員所奏,成為明廷洞察輿情、應對危機、緩和矛盾的重要依據。雖然在此過程中,生員頗有好議喜亂、聚眾鬧事之勢,“以猖狂為氣節,以結黨為豪舉”,(119)《明神宗實錄》卷五二四,萬歷四十二年九月戊寅,第9878頁。但多數還是地方官員欺壓所致,如萬歷三十一年(1603)三月,常熟生員孫汝炬因為抗拒點名,遭到知府周一梧撲責, 孫汝炬煽眾鼓噪,“一唱群和,拋磚揮拳,窘辱守令”,(120)《明神宗實錄》卷三八二,萬歷三十一年二月壬午,第7193-7194頁。這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明生員群體力量已逐漸壯大,并與地方權力之間形成緊張而復雜的關系。
(三)監督性輿論功能
明中期以后,生員成為不可小覷的輿論群體,在那個“自由奔放”(121)方志遠:《“山人”與晚明政局》,《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的時代,生員的集體意識日益增強,生員輿論的政治監督功能日漸凸顯,甚至面對朝廷權勢,生員輿論的監督作用也顯而易見。如正統年間,祭酒李時勉請改建國學,英宗命太監王振巡視,因時勉接待不周,王振懷恨在心。后時勉砍除彝倫堂前的樹枝,王振妄言時勉擅自伐樹,矯旨將其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鑒等枷于國子監前,“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余人詣闕乞免,生員石大用更是“上章愿以身代”。當時,“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庭”,王振聽聞,“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慚”。(122)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六三《李時勉傳》,第4422-4423頁。在生員輿論的壓力下,王振只好作出妥協,釋放李時勉等人。
明代生員的輿論力量在于其群體抗爭的方式,“方其成群而呼,有司畏之如虎;一遇孤弱,有司置之若棄。方其诪張為幻,則藩臬之長,降階稱公稱兄,甚至柄文者與諸生媾而和矣。一旦勢去則門隸得,而爾汝家仆可以僇辱”。(123)丁元薦:《尊拙堂文集》卷一《國是隱憂疏》,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0冊,第658頁。于此,黃宗羲在講述明末生員陳確事跡時亦云:“崇禎末,昌邑不飾簠簋,昌邑橫甚,莫之敢指。先生號于眾曰:‘吾邑之人何罪,而使一人橫行于上乎?’同舍生集著數百人,走訴行御史臺。繡斧不聽,沓吏坐先生以罔上。同舍生龂龂不退,沓吏始敗。”(124)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十冊《南雷詩文集上·陳乾初先生墓志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頁。同一事情,陳翼《乾初府君行略》載:“先君子(陳確)以命中之技,值貪尹歸虐,輟所業攻之。當事庇貪尹,欲罪首事者,文移褫革,學憲執不許……諸與貪尹比者,百方恐嚇,先君子屹不為動。邑眾庠生,感先君子義,群聚不散,當事者心惕,卒解其事。未幾,風聞輦轂,當事與貪尹竟中考功去,先君子亦不以此自喜。”(125)陳確:《陳確集》首卷《乾初府君行略》,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3頁。貪官污吏枉法虐民,官官相護,陳確憤慨不平,“乃率諸生首發其罪,上書諸臺司”。(126)吳蕃昌:《月隱先生遺集》卷下外編附錄,載《叢書集成續編》,第188冊,第367頁。官府為打壓生員,欲“罪首事者”,取消陳確鄉試資格,且“幾蹈不測”,但他不以為意,依然“為斯民請命”,直到眾生 “聚而不散”,當地官員心生畏懼,不得不作出讓步,“卒解其事”,貪尹等最終被免職。從該事件,可見明代生員輿論群體力量之一斑,他們的輿論行為對于監督地方事務,糾劾不法官員,端正社會風氣,推揚擔當精神,無疑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當然囿于時代,明代生員輿論也有一定局限性,“明代生員的政治活動,其性質是十分復雜的。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還有荒唐的”。(127)尹選波:《明代學校生員政治活動述論》,《求是學刊》1999年第4期。明初生員多能遵守學規,“篤志圣賢,潛心古訓”,(128)《明太祖實錄》卷二一八,洪武二十五年六月癸亥,第3205頁。然即使如此,生員輿論也有違規之時,太祖就說:“近聞天下學校生員多驕惰縱肆,凌慢師長,宜重禁之。”(129)《明太祖實錄》卷二一八,洪武二十五年六月癸亥,第3204頁。正統年間,山東按察司僉事薛瑄也言:“各處儒學生員多有屢犯刑憲,全無忌憚……刁頑無恥,終難教養。”(130)《明英宗實錄》卷五二,正統四年閏二月乙酉,第994-995頁。至中后期,隨著禮法秩序的日益松散,世風不古,人心薄惡,士風丕變,“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于軍民之家,渾住于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131)黃宗羲:《明文海》卷四八《論太學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65頁。嘉靖年間,吏部尚書廖紀上疏反思了明代士風之變:明初,“士風淳樸,絕無巧偽,勉修職業,不務虛名,故事治民安,國家賴之”;然正德以來,士風浮競,“士多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圖捷徑;或因官非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托養病致仕……人怠于修職,巧于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132)《明世宗實錄》卷五五,嘉靖四年九月乙亥,第1342頁。士人只圖虛名,不求務實,只言近利,不顧遠功,“急功利,喜夸詐,于學者最為戾習。士風如此,世道將何賴”。(133)徐三重:《牖景錄》卷下,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06冊,第123頁。受此影響,晚明生員追名逐利,內心乖張,已無士人之節,幾成社會一害,“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134)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第22-23頁。至萬歷時,生員習氣日壞,“一人有事,群起扛幫,或挾制上司,或侵損小戶,或包攬錢糧,或揑造歌謡,揭官保官,肆行無忌,法紀蕩然”。 鑒于此,時人建議整飭生員言行,“提學官巡歷地方,宜嚴行查訪,或被人告發及自犯發覺事有的據者,即行拏問,為首者依律治罪,其余酌量革降,若生員有事,止許家人抱告,聽有司從公剖斷,如有安靜守己,讀書修行者,亟示優異”。(135)馮琦:《宗伯集》卷五七《為遵奉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第7頁。
在此情況下,生員輿論很難再有公正之理,監督之效也大打折扣,甚而成為生員要挾官府、橫行霸道的工具,“士風日頹,法紀陵夷,以猖狂為氣節,以結黨為豪舉。事關一人乃倡通學,而聚蛟雷之聲;事關本學乃聯各學,而成鴟張之勢,把持官府,武斷鄉曲”。(136)《明神宗實錄》卷五二四,萬歷四十二年九月戊寅,第9878頁。當時,還出現了生員集體罷學的“卷堂”現象,而其表達不滿而撰寫的文章,是為“卷堂文”。卷堂文除了敘述事情原委,表達意見外,還是學生罷課的號令書。時人有言:“余少及見邑庠先生笞責諸生,無敢抗逆者。蓋自嘉靖壬子、甲寅以后,而此風浸衰矣。浙省學使屠坪石公持正方嚴,訪諸生行誼,不委之,廣文多所詢察,務得其人,以行賞罰,諸生一時皆不敢失禮逾法。自后大都務寬,遂至肆無忌憚。分巡以代巡命考校諸生,不容唱名序坐,呼朋引類,莫敢誰何。不五年,而諸生罵父母正官矣,又罵祖父母官矣。罵不已,群攻府通判,而卷堂文出矣。”(137)李樂:《見聞雜記》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頁。可知明末生員處在一種極不安分的狀態,“諸生事不得直,即做卷堂文”,朝廷對此也頗為頭疼:“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138)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第22頁。有時,生員的集體輿論行為會形成“把持官府”“挾制官長”的格局,甚至某些集體行動還帶有一定暴力色彩,“生員每每聚黨橫行,大干法紀”,(139)《明熹宗實錄》卷六,天啟元年二月甲子,第307頁。這在晚明時期尤為突出。以萬歷朝為例,四年(1576)二月,荊州府學生員許仕彥等辱江陵令李應辰,應褫,并劾教授曾貴臣及訓導劉璠。(140)《明神宗實錄》卷四七,萬歷四年二月壬午,第1070頁。同月,黃梅縣舉人瞿九思、生員周谷等毆傷本縣知縣張維翰。(141)《明神宗實錄》卷四七,萬歷四年二月甲申,第1073頁。七月,婺源縣民程任卿鼓煽生員汪時等十五名,“聚黨脅迫官吏,逼求申豁,幾于作亂”。(142)《明神宗實錄》卷七七,萬歷六年七月丁巳,第1654-1655頁。湖廣學政董其昌“不徇請囑”,為勢家所怨,遂教唆生員數百人“毀其公署”。(143)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傳四·董其昌傳》,第7395-7396頁。這次學潮,生員為勢家所利用,武力鬧事,受到懲治。
結 語
明代生員所具有的學識和能力,使其超脫于一般的平民百姓,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特權。但與鄉紳相比,不論是財富、聲望還是影響力都遠遠不如后者。生員群體之所以能周旋于中央朝廷和地方有司之間,同時又溝通官府和平民百姓,成為社會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主要緣于兩點:一是社會輿論,二是群體力量。二者相互結合,形成輿論活動,構成明代市民運動的組成部分,代表了當時最活躍、最激進的群體性輿論力量,“在隱約之中提出帶有素樸的民主政治的要求和人身自由的愿望”。(144)傅衣凌:《明代后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封建運動》,載《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第110頁。明代生員的價值觀念生成于儒學境域,經由理學的固化和心學的沖擊,對于內心的價值標準有了獨到識見,對于國家權力的異化趨向有了敏感體認,對于現實問題和人間百態有了是非評斷。可以說,他們的輿論話語和輿論行動,代表了公理和良知,決定著人心和民意,這或許就是當時的“社會口碑”,就是當時的“輿論風標”,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濁揚清、懲惡揚善的作用。生員群體以“臣子”自居,心系國事乃天經地義,雖有學規制約,但明代生員群體發表輿論意見、監督地方事務的熱情一如既往,從未泯滅。當然,明代生員輿論行為在發揮“正能量”的同時,在復雜多變的歷史變局中,也時常表現出“不端”“放肆”等“負能量”,這在生員輿論最為活躍的明后期表現得尤為突出。當時,隨著禮法秩序的日益松散,“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見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遇尊長乘騎不下者”。(145)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五《建業風俗記》,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頁。處此境地,很多生員不再“篤志圣賢,潛心古訓”,(146)《明太祖實錄》卷二一八,洪武二十五年六月癸亥,第3205頁。轉而厭棄學業,驕慢浮薄,蔑禮玩法,流言惡評,如“以童生而毆辱郡守,以生員而攻訐有司。誹毀官長,連珠遍布于街衢;報復仇嫌,歌謠遂鋟于梓木”;(147)《明穆宗實錄》卷二四,隆慶二年九月壬戌,第656頁。如“近日秀才不惟才高氣傲,才不高者,亦氣傲。小試不利,便罵督學;場屋不中,便罵試官,全不返己進修”,(148)李樂:《見聞雜記》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9頁。甚至出現了生員“剽竊邪說”“炫奇立異”“糾眾扛幫”“罵詈官長”的怪象。(149)張居正:《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人才疏》,載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第一冊,荊楚書社1987年版,第175頁。這些“雜亂不雅”的輿論行為,是晚明士紳階層日益分化的明證,(150)陳寶良的《明代生員層的經濟特權及其貧困化》云:“明代生員層無疑是紳士層中的一員,但生員層日趨貧困化的事實,顯然又可證明晚明紳士層的上、下層正在日益分化。晚明大量的以生員層為主體的‘學變’(或稱‘士變’)的出現,此即其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2期)然“大都意氣所激,而未嘗有窮兇極惡存乎其間”。(151)范金民:《鼎革與變遷:明清之際江南士人行為方式的轉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晚明生員的輿論行為雖多了幾分意氣,但也集中表現出突破禁例、申述意愿的激情和真情,在那個輿論專制的時代顯得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