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庫切的閱讀史

J.M.庫切
一
“如今還有這樣的作家嗎?”
一九九五年,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爵士辭世時,布羅茨基追憶他們曾經做過的一個游戲。在倫敦皇家咖啡館,到訪英國的布羅茨基與斯彭德夫婦聚會,餐敘時哲學家以賽亞·伯林與他們同席。他們列出一份“本世紀最偉大作家”的名單: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穆齊爾、福克納、貝克特。但這份名單只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為止,八十高齡滿頭銀發的斯彭德問布羅茨基:“如今還有這樣的作家嗎?”“約翰·庫切或許算一個,”布羅茨基回答說,“一位南非作家,或許只有他有權在貝克特之后繼續寫小說。”斯彭德問:“他的名字怎么拼寫?”“我找到一張紙,寫上庫切的名字,并加上《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這是布羅茨基發表于《紐約客》的祭文《悼斯蒂芬·斯彭德》中的敘述。
二○二一年盛夏,我在布羅茨基散文集《悲傷與理智》里讀到這個細節。此刻作為生活于現在時的讀者,我已成一個中介,某種見證。
越過時間的蒼茫云煙,同時可以看見存在與逝去者,看見他們的情感凝結和精神聯通。
二○○三年十月,J. M.庫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霍拉斯·恩達爾(Horace Engdal)宣布庫切獲得文學獎的消息時說:“我們都確信他在文學方面所做貢獻的持久價值。我不是指書的數量,而是種類,以及非常高的水準。我認為,作為一名作家,他將繼續被人討論和分析,我們認為應該將他納入我們的文學遺產。”(J. C.坎尼米耶《J. M.庫切傳》,王敬慧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瑞典文學院在正式報告中說:
庫切的小說以結構精致,對話雋永,思辨深邃為特色。然而,他是一個有道德原則的懷疑論者,對當下的西方文明中淺薄的道德感和殘酷的理性主義給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誠實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礎,使自己遠離俗麗而毫無價值的戲劇化的解悟和懺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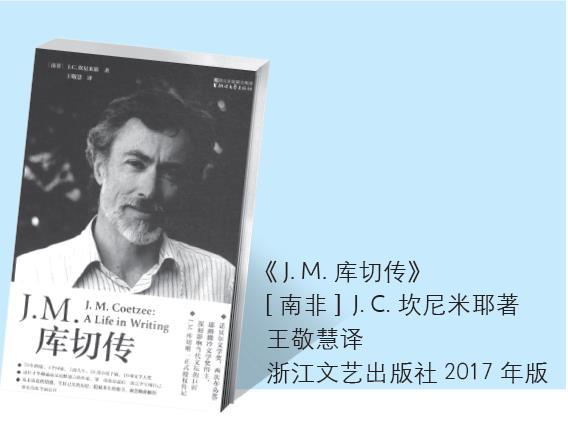
我對瑞典文學院不陌生。曾有三年,我在隆冬之季前往那個晝短夜長的北歐之國,一幢位于斯德哥爾摩老城的城堡般的建筑,昔日是證券交易中心,后來成為瑞典文學院所在的大樓。天光幽暗時刻城市街頭映射著璀璨燈光,隨處可見門廊前徹夜不息的燭焰。踩著石階上樓,或乘老舊逼仄的電梯升降,可進入這幢大樓的任何一處。我進入過瑞典文學院的會議廳,那里圍著一張長桌擺放著十八張宮廷式座椅,有著十八位院士的瑞典文學院只有十五位院士參與日常工作,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就由其中部分院士組成。諾貝爾文學獎對南非作家J. M.庫切的加冕是一個作家所能享有的最高榮耀:
庫切的作品是豐富多彩的文學財富。這里沒有兩部作品采用相同創作手法。然而,他以眾多作品呈示了一個反復建構的模式:在盤旋下降的命運是其人物拯救靈魂之必要途徑。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擊、沉淪落魄乃至被剝奪了外在尊嚴之后,總是能夠奇跡般地獲得重新站起來的力量。
此刻我想到布羅茨基。他可以是庫切杰出的知己。擁有非凡的知己應該是一個人的慰藉。
或許是對精神知己心存感激,庫切在二○○二年出版的小說《青春》中寫到他對布羅茨基的關切。夢想成為詩人的青年庫切遷徙倫敦過著居無所定的漂流者生活,在忙碌的謀生間隙,唯一的盼頭就是回到他的房間,打開收音機收聽BBC的第三套節目。在“詩人和詩歌”系列節目里,他聽到布羅茨基的消息。詩人在冰封的北方阿爾汗格爾斯克半島服苦役。當庫切在自己溫暖的寓所里,喝著咖啡,一點點咬著有葡萄干和果仁的甜品的時候,有一個和他同齡的人,整天在鋸圓木,小心地保護自己長了凍瘡的手指,用破布補靴子,靠魚頭和圓白菜湯活著。

庫切的《青春》敘事,盡顯他在漂流的困頓中對詩人的摯愛。“僅僅在從廣播中聽到的詩歌的基礎上,他了解了布羅茨基,徹徹底底地了解了他。這就是詩歌的力量。詩歌就是真實。但是布羅茨基對于在倫敦的他只能是一無所知。怎樣才能告訴這個凍壞了的人,他和他在一起,在他的身邊,日復一日,天天如此?”
精神聯通就是這樣產生的,在宇宙之間,兩個相距遙遠的人,心靈穿越時空相互貼近。
二○二一年十月五日午夜,我重新閱讀庫切的《青春》,在第十一章找到這個細節。很多次讀到這個細節時我都會被這樣的敘事振動心弦—約瑟夫·布羅茨基“從顛簸在歐洲黑暗的海洋中的孤筏上將……詩句釋放到了空氣之中”,詩句隨著電波迅速傳到了庫切的房間里。“他同時代詩人的詩句,再一次告訴他詩歌可以是什么樣子的,因而他自己可以是什么樣子的,使他因為和他們居住在同一個地球上而充滿了歡樂。”
二
閱讀和聆聽。同屬于精神事務。
《好故事:關于真實、虛構與心理治療的對談》,是小說家庫切與英國心理學家阿拉貝拉·庫爾茨的對話,它的中文版于二○二一年六月問世。這一次庫切放棄他所擅長的虛構文體,也舍掉他造詣精深的理論言說,進入陌生的心理和精神學領域,與精神病理專家探尋他所關切的問題。“虛構與真實”“創傷與記憶”“創造的激情與隱秘的生物基因”“書寫與治愈”……他們如同臨床醫生,一次次剖析這些重要命題。這是一次極具專業性的討論,普通讀者需要具備某種心理學知識才可以進入對談的文本,才可以理解話題所及的要義。
仿佛置身現場聆聽這對話。我尤為感觸的是庫切對閱讀的鑒識。
“死的閱讀與活的閱讀。”這是庫切的劃分方式。“有一種死讀書,也有一種活讀書。死讀書,那些詞語在書頁中從來不會產生意義,這是許多孩子的閱讀體驗,如他們自己所說,那些孩子從未養成愛上閱讀的習慣。通過死讀書,死記硬背的方式來學習,也不是不可能,但這本身是一種苦悶的、索然無味的體驗。”
對閱讀的鑒識當然不是為孩子,它的觀念適宜任何的成年人。庫切繼續分析道:
活的閱讀,會像一種神奇魔力一下子把你擊中。它包括用你自己的方式走進去,聆聽書頁里發出的聲音,那是對方的聲音,沉浸在這聲音里,你可以從外部對你自己說話(你的自我)。于是,這個過程就成為一種對話,盡管它只是內心的對話。這是作家的技藝,這種技藝現在已無處可學,雖然還能被撿起來:創造一個形象(一個會說話的幻影),提供一個入口,讓讀者沉浸于這幻想之中。(《好故事:關于真實、虛構與心理治療的對談》)
閱讀是精神活動,它是我們內心的生活。閱讀也是對人的心靈和智識的開掘。
就像寫作對人的心理隱患的治愈,閱讀對人的精神暗疾具有療治功效。
這樣的體會是我所有的,我的個人經驗是:好作家是慰藉,好故事是靈藥。
我們都是受益于閱讀的人。受益于閱讀,也即被人類文明之光映照。
世間眾多智性蒙昧的心靈經由這文明之光的映照而覺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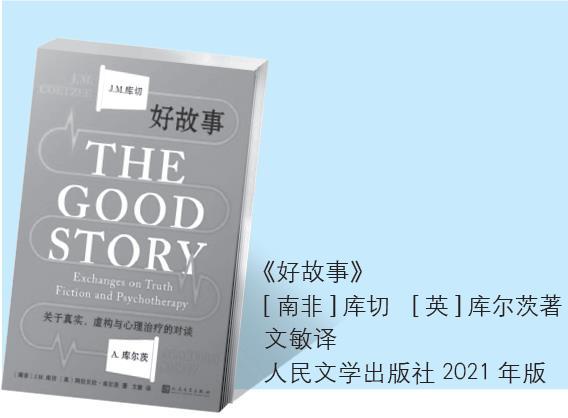
如同心理學家阿拉貝爾·庫爾茨在《好故事:關于真實、虛構與心理治療的對談》中言及她讀《夏日》時的體會:“我們不能完全通過他人來了解我們自身—我們通過感受他人的方式,我們自身亦在與他人的關系中,這也是他人感受我們的方式。”
三
庫切是可以帶來心靈慰藉的作家,對他的閱讀也是我們對精神暗疾的治愈。
一個身在幽暗中的人。一個書寫幽暗的人。我與庫切在共同的精神背景遇見,幽暗是我們共同的經驗。一個是卑微如塵埃者,一個是燦若星辰的文學巨匠。然而我們在精神疆域中產生交集和互聯。庫切早年在南非城鎮度過,當時他的國家有著最野蠻的社會制度—種族隔離。他見證并親歷了很多暴行。青年時期庫切旅居英美,為謀生也為個人的藝術理想,過著飄零的生活。
作為前工業時代的礦工,昔日的漂流者,如今的自由寫作人,我與庫切有著甚深的契合度。因為出生并成長于礦區,幽暗是浸染我身心的顏色。青年時期遷徙京城,有過多年的漂流者生涯。我所閱歷和親證的黑暗已不再限于外省礦區和漂流生涯,它是更廣大世界的某種境況。作為時代的觀察者,生活的體驗者,這是我從前的自我鑒識。作為一個寫作者,過去和現在都有著紛繁的失敗經驗。我與庫切相似的心靈體驗還有對失敗與挫折的體察,對憂郁與孤獨的感知,以及對外部世界的疏離,這是我們共有的精神基因。
“他的每一次敘述都始于并且執著于人物向下沉降的命運,如同一份追蹤地下生活的報告。仿佛只有在這幽暗冷漠的國度,才會見證我們時代的隔離,以及它那些荒蕪靈魂的悲喜劇……”這段文字出現在許志強為庫切撰寫的《夏日》中文版序言里,被我用黑色碳素筆劃過虛線反復記憶。這些話語如同密林中的幽徑被我發現,沿路而行抵達某處隱秘之境,那是小說家庫切的精神疆域。
《夏日》我有三本,其中兩本分別置于我在兩座城市居室的書架上,這么做是為方便閱讀。因為經常乘坐高鐵旅行,穿梭于北京和長春,前者是我的工作場,后者是我的庇護所。庫切在很多時候是映照我的精神光譜,我需要他在內心的陪護。虛實相間,迷離人生,一個偉大小說家的自我史。一場充滿文學快感的小說游戲。最初讀到的《夏日》是在二○一二年冬天買的。其時我剛辭職,結束持續十年的新聞職業,我決心侍奉個人的文學寫作志業。我認為那個冬天遇到《夏日》對我是個安慰。我是偶爾的機緣看到這本書的介紹,當時我與這位作家并無多少交集。只是看見過他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在當年的《書城》雜志上看到過他的一些零散的小說文本。還有就是在多麗絲·萊辛獲諾貝爾文學獎時,我從北京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趙白生先生那里約過庫切寫萊辛的文稿,印象中請趙先生與庫切確認過刊發的版權。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傍晚,我回到京郊寓所,在書架上找出我在二○一二年買到的《夏日》,令我驚奇的是,書中在不同紙頁間夾了三個淺藍色鐵夾,鐵夾夾著我寫下來的數十頁閱讀筆記。這是少有的認真閱讀,當時我只是喜歡這部小說,喜歡它的敘事格調,緩慢而精致,極具個人化。很有些迷戀小說敘事呈現出來的作家的形象,隱忍而內斂。
我不知道對《夏日》的喜愛,是我對庫切充滿個人敬意的閱讀之旅的開啟。
如今我是雙城生活的人,有十年的時間往返于北京和長春。在兩座城市居所的書案上都有藍色地球儀,閑暇時我會旋轉地球儀,尋找自己想要旅行的國家,查詢想要抵達的地方。中國北京—南非約翰內斯堡—澳大利亞堪培拉,從地球儀可見空間相隔的距離。然而我是領受杰出作家慰藉的人,也是被好故事治愈的人。此刻我站在這里就是一個精神標本。一種異族文化,同時也是普世文明,這是庫切所能代表的。他還代表一個杰出小說家應有的精湛技藝,代表一個人文學者的遼闊深邃而多元的精神維度。
《夏日》無疑是一個好故事。充滿游戲與諷喻的氣息—庫切死后,有人想要寫作庫切的傳記,重訪他的生前友好,他的情人、表姐、同事,也尋找庫切舊日的筆記,傳記作者試圖從他獲取的這些材料拼接出庫切的人生實況和精神圖景。這是《夏日》的敘事脈絡,小說結構采用的口述實錄使這部虛構文本顯示出真切效果。這本書打開就被吸引,其時我開始往返于兩座城市,旅程中我需要在隨身的雙肩包放幾本書,《夏日》是我的選擇之一,我想看到當代在世而被稱為“一個偉大作家”的狀態,他的寫作與生活境況。
睿智而誠實,機鋒遍布又情感真摯。這是《夏日》顯示的令我親近的文本氣質。
小說里的主人公—青年庫切—仿佛一個幽靈般的存在,游離于世界邊緣。庫切是一個與外部世界疏離的人,疏離而藝術精湛,這是令我尊敬的作家的品質。有同類品質的作家都是我喜歡的,比如普魯斯特、塞繆爾·貝克特、詹姆斯·喬伊斯、羅伯·格里耶。有這樣的偏好當然也是因為我當時正處于失業的困頓中,辭職之后全心侍奉自由的文學寫作理想,然而寫出來的作品無人問津,飽受拒絕和冷遇。這樣的個人境況使我對庫切書寫的困境有切實體會。許志強先生在《夏日》中文版序言中談到閱讀庫切的體會,讓我感同身受:
……破裂,沉入生命冰涼的殘渣。庫切帶著這種感覺去描寫事物,講述自身的故事,體味他那種孤獨的命運,恰恰因為這個就是他的命運,去尋找他破裂的生活中值得一寫的東西。他用質樸細膩的語言敘述,平穩的筆觸帶著層積遞進的效果,因其尖銳的敘述有時誠實得讓人心里打戰。
四
隱逸而勇毅,仁慈又堅韌。這是我欣賞的人的精神氣質,也是庫切的性格特征。
一九七○年一月一日,即將邁入三十歲的庫切身穿外套,腳蹬棉靴,把自己深鎖在他位于紐約州布法羅市帕克大街二十四號地下室的住所里。他在新年許愿中發誓,如果寫不到一千字,自己就絕不出來。后來他決心堅持每天寫作,直到完成一部小說的草稿。這是庫切寫作《幽暗之地》的時刻,此后他寫作的恒心和毅力從未減退。
這個細節令我記憶深刻,也帶給我最初感動。或許很多寫作者寫作生涯的開始都是如此。
個人的決心與意志和紀律的集合,締造一個寫作者的杰出業績。
庫切重要著作的中文版在圖書市場都能找到,這些年他的虛構和非虛構文本多有出版,不同版本也多有上市。《幽暗之地》是我讀過《夏日》之后看到的庫切著作的第二本。《幽暗之地》是一本有關殘忍的書,揭示了各種形式的征服中的殘忍。“黑暗”或者“幽暗”,這種光線是我熟識的,它應該是我與庫切的共同精神背景。出生于礦區所體察到的黑暗,自然相異于南非社會的黑暗,然而形態不同,精神內核卻一致。

《幽暗之地》分為兩章,越南計劃/雅各·庫切之講述。小說涉及作家對越戰的記憶敘事。軍人出征前的慷慨悲歌和戰爭結束后的慘烈與傷痛,這些景象都可以從電視媒介中看到。《幽暗之地》敘述的越戰當然是不同的。二○一七年我應邀到美國訪問,在洛杉磯有機會到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故居參觀,在那里看到過越戰的全程實況記錄。
出現在庫切小說里的作家形象令我感到親近,在他的敘事情境中出現的父親形象也帶給我親近感。在《夏日》里如是,《幽暗之地》也如是。這個父親會讓我想到自己的父親—一位前半生有著軍旅生涯,穿越血雨腥風幸存下來的老兵,轉業到礦區后過著平民生活。
閱讀過《夏日》和《幽暗之地》,我開始尋找庫切著作的中文版。《男孩》《青春》《鐵器時代》《兇年紀事》《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恥》《彼得堡的大師》。
對一位作家的接受和熱愛,源自我們心靈的選擇,它是內心的契合與印證。
我在閱讀過的庫切著作的書頁里留下個人隨想的筆記:
寫作作為祈禱的方式。閱讀庫切時我想起卡夫卡在他日記里的話。庫切寫出的文本是對卡夫卡的信念的印證。他的小說《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靈感來源于對卡夫卡文學世界的洞察。杰出的寫作是對人類精神的質詢,是對自我的探測。杰出的寫作是與神明的對話,它與時間同構,在時間之內呈現超越人的肉身的永恒性。藝術和匠心。在小說的文本里,它不能只是一些事物的輪廓,一些故事或者情節的概述,它在結構上如同精美的建筑,布局對稱,構造嚴密,在敘事上如同自然涌流的江河,它的延展和推進自然又精妙。是的,只有精妙可體現藝術的匠心。好的小說在整體上就是完美的,每個構成整體的部件都是完美的。
杰出作家的存在是一種現實,然而使杰出作家顯現和呈示在世人面前也需要他者的努力。比如傳記作家和譯者。在不同文明與不同文化之間,在不同語言之間,要使杰出者真正與他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讀者相會更需要傳記作家和譯者的持久努力。因此每個英雄的誕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取決于其所在的環境,取決于環繞在他周圍的鑒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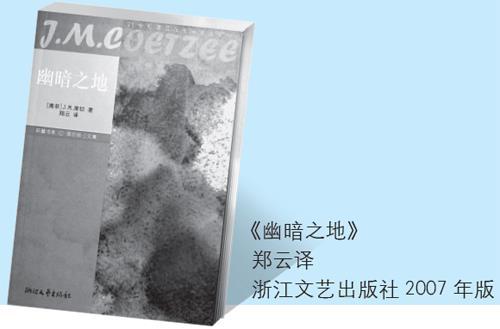
庫切的寫作并非沒有受到過冷遇和拒絕。他的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完成后被多家出版機構拒絕。“《幽暗之地》最初的被拒反映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南非出版界的糟糕品位,但它也將庫切放入了一份著名的長長的名單之中。這個名單包括所有曾經費盡努力想將自己的第一本書出版的知名作家們。”(夏榆《我們比想象中更自由,也更軟弱》,《新京報》2017年11月18日)好的作家遇到知己是必然的,只是需要機緣。“讀過幾頁《幽暗之地》之后,我感到震驚和興奮,在我看來,這是那一代南非英語寫作的巨大突破,”庫切在開普敦大學做講師的同事喬納森·克魯評論道,“《幽暗之地》標志著南非后現代小說創作的開始。”
庫切是幸運的。依靠精湛的寫作技藝,他贏得光榮和贊譽,也贏得世人普遍的尊敬。
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持自然是庫切的光環之一。然而很長時間庫切卻自我命名為“黑暗之子”,他是白種人卻長期生活在施行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社會的動蕩、人性的混亂和掙扎是他人生經驗的一部分,也是他書寫的重要的題材和主題。
庫切對家族史的關注和書寫,只是他對國家記憶書寫的一部分。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個人對國家現實的思考甚至批評,在庫切的小說里隨處可見。他經常將個人與一個國家并置。
在《夏日》里隨處可見主人公與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可見他對國家現實的反省式審察。
他的小說更像藝術精湛的政治寓言—
在這個世界上,你還能上哪兒去找一個把自己藏起來不受玷污的地方?難道跑到白雪覆蓋的瑞典,遠離千山萬水從報章上了解他的同胞和他們最新的惡作劇,能讓他感覺好些?
怎樣逃離污穢:這不是一個新問題。這是一個該死的老掉牙的問題—它不放過你,給你留下惡心的化膿傷口,良心的自責。(《夏日》,文敏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
五
這一次,我是那個被閱讀治愈的標本。
“你自己也應該去做心理治療。”她嘴里噴著煙對他說。
……事實上他做夢也不會想到要去做心理治療。心理治療的目的是讓人幸福。這樣做有什么用?幸福的人太乏味。最好還是接受不幸福的重負,試圖將它轉變成有價值的東西,詩歌或音樂或繪畫:這是他的信念。(《青春》,王家湘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
這是有關精神疾患治療的對話。渴望成為詩人的青年庫切周旋于跟女友錯亂的情欲之中。庫切在《青春》里寫到的情感糾纏帶來心靈的鏖戰與折磨。
“他在證明著一點,每個人是一座孤島……”我反復閱讀過青年庫切的獨白:“能夠治好他的東西,如果來到的話,那將會是愛情。他也許不相信上帝,但是他確實相信愛情和愛情的力量。那個他所愛的人,命中注定的人,將會立刻透過他呈現出的怪的,甚至單調的外表,看到他內心燃燒著的烈火。同時,單調和樣子怪是他為了有朝一日出現在光明之中—愛之光,藝術之光—所必須經過的煉獄的一個部分。因為他將會成為一個藝術家,這是早就已經確定了的。如果目前他必須是微賤可笑的,那是因為藝術家的命運就是要忍受微賤和嘲笑,直到他顯示出真正的能力,譏笑和嘲弄的人不再作聲的那一天。”(同上)
“庫切,迄今為止,在我欣賞的作家中,無疑是最好的導師,小說家職業的典范,他是值得終生閱讀的作家。”二○二一年九月三日,我在《青春》的扉頁留下這樣的題記。杰出作家都有他們的精神傳承。庫切的“外省場景生活”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的誕生受到列夫·托爾斯泰《童年》《少年》《青年》的影響;對庫切產生重要影響的還有作家塞繆爾·貝克特,更早還有卡夫卡,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春》中庫切再次引入對他的精神產生深刻影響的詩人埃茲拉·龐德與T.S.艾略特,他們也是他人生的榜樣,是他在困頓中的慰藉和醫治他精神暗疾的靈藥—
埃茲拉·龐德一生多數時間都遭受迫害:被迫背井離鄉,后來又被禁閉,然后第二次被驅逐出祖國。然而,雖然被打上瘋子的標簽,龐德卻證明自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龐德聽從了自己的保護神,將一生獻給了藝術。艾略特也是,雖然艾略特的痛苦更多是屬于個人性質的。艾略特和龐德過著悲哀的、有時是恥辱的生活……(《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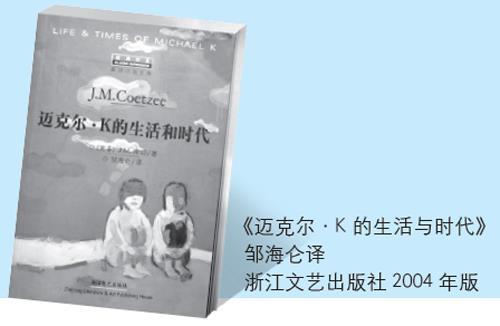
詩人龐德和艾略特對庫切的精神影響之深,使他后來寫出《何謂經典》的演講辭。在演講中庫切向艾略特和龐德致敬。演講稿出現在他的文論集《內心生活》。
“恥辱”,這是我在庫切的言說中看到他頻繁使用的一個詞語。如同幽暗和失敗的詞語一樣,屬于他貼身的詞語。閱讀必須在更為開闊的背景下才更為有效。再讀《青春》時我已研讀過T. S.艾略特的詩集《四個四重奏》,反復閱讀過傳記《不完美的一生:T. S.艾略特傳》,那是一個偉大詩人同樣杰出的傳記,在此之后重讀《青春》就更懂庫切表達的深義:
和龐德和艾略特一樣,他必須準備好忍受生活為他儲備的一切,即使這意味著背井離鄉,微賤的勞作和誹謗。如果他不能夠通過藝術的最高測驗,如果最后證明他不具備這份神圣的天賦,那么他也必須準備好忍受這個結果:歷史的無情裁定。生存的命運,不管他所有的今天和未來的痛苦,都是次要的。許多人受到感召,很少人為神所選中。每一個大詩人的周圍都有大群的次要詩人,就像圍著獅子嗡嗡飛的蚊蟲。(同上)
在無數由失敗帶來的幽暗時刻,閱讀《青春》帶給我心靈的慰藉。庫切使我看清世態炎涼,看清人性的真相。
洞悉從事藝術創造即為某種獻祭,亙古如是。
六
“他一直是我的老師,是種族隔離最黑暗的日子里道德的指南針。”
在世間的贊譽中,庫切的學生安妮·蘭茲曼(Anne Landsman)對庫切的評價別有意味。
無疑,庫切的存在提供了文學的尺度。他的寫作業績顯現出杰出小說家的職業維度。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南非開普敦三百周年基金會將一九九五年度獎頒給庫切,以表彰他終生為文學所做的貢獻。同年他獲得紐約斯基德莫爾學院頒給他的名譽博士學位。這是更早到來的榮耀,庫切逐漸被他生活的環境,也被世人所知曉。頒獎儀式上,致辭人羅伯特·博伊斯(Rober Boyers)教授說:“J. M.庫切是一位小說家、政治思想家、評論家、理論家、語言學家和權力解剖學家。您的作品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生動而內斂,既有風格又有知識分子的勇氣。您的創作來自南非的經歷,帶著特有的壓力與執著,您已經找到了一種方法談論特定歷史所發揮的力量,同時又不局限于單一的時間或國家,您仔細地觀察壓迫、殘酷和不公正,并教會讀者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試圖表達自由的困難。”
“你屬于我熱愛的那個世界。”這是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為加西亞·馬爾克斯頒獎時的贊譽。我以為這樣的話語也適合庫切。尋找能找到的庫切著作的所有中文版,這是我這些年做的事情。我愿意成為與庫切精神相契的閱讀者,然而我反對將這種精神的共振稱為“擁躉”,或者如時下的流行詞“粉絲”。在我看來失去個人精神立場的擁躉無意義更無價值。
打開一本書的同時也是在打開一個世界,那里如同森林浩瀚,如同海洋深邃。
閱讀不是娛樂也非游戲。我們帶著自己內心的疑難和精神詰問。
閱讀的過程是求證和釋疑。比如:什么是真的文學?以創造為業的作家(藝術家)如何自處?作家與他的國家的關系,與他的族群的關系,作家與公共事務的關系,作家的精神立場和道德原則何為?這都是重要的命題。曾經有人說過:“大眾的喧嘩與狂歡之處,并不是一個真實的文學現場。”

庫切讓我們看到真正的文學是怎樣的品質,杰出作家是怎樣的樣貌。
早年庫切寫過一部夭折的小說《焚書之火》,他詳細考察過南非的某些嚴苛的法規和制度,他關心的是那些制度會怎樣影響自己的寫作生涯。庫切批評南非政府那些監管中心愚蠢至極。他在小說《等待野蠻人》中寫道:“所有的事情都相互關聯,當國家的正義秩序坍塌的時候,它在人民心里也就土崩瓦解了。”
作為作家的庫切如豐饒之海。使我在更廣闊的思想視域得以觀看庫切的是兩本傳記,《J. M.庫切傳》和《用人生寫作的J. M.庫切:與時間面對面》。前者是由J.C.坎尼米耶撰寫的一部六百多頁的巨著,后者是由大衛·阿特維爾撰寫,聚焦于庫切的手稿以及寫作秘辛,兩部傳記側重點不同可以互為參照。它們都在敘述一個杰出作家是如何煉成的。這是優異的傳記對杰出作家的精彩呈現。
庫切身材消瘦,但很精神。過早花白的胡子,戴著角質眼鏡,低沉的聲音,有著沉默寡言的風范和清心寡欲的外觀。多年來他用沉默和拒絕對公眾談論自己來保護自己不受外界的入侵。他的私人生活,不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南非國內,都處于公共領域之外。當他罕見地出現在社交場合時,他寧愿站在一個角落里,僅同一個人說話。庫切是一個有著僧侶般自律和奉獻精神的人,他很少接受媒介訪問:“我的抵制不僅僅是保護一種幽靈般的全能。寫作不是自由的表達。寫作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對話:要喚醒自我中的和音,然后與之言說。”
我愿意將庫切的肖像定格在這幅畫境中。
“約翰·庫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位偉大作家,同時也是世界上偉大的教師中的一員。在典范和見證的傳統下,他教導我們怎樣閱讀一本偉大的書。他教我們更清晰地認出人類靈魂,他課內外的言論都是我畢生難忘的回憶,一直在我耳邊不斷回響。”庫切的學生喬納森·李爾的評價楔入我心。《J. M.庫切傳》放置于我臥室的書架之上,在隨時能看見的位置。這是更為深入和遼闊的書寫,在全球的語境之下對庫切的講述。它讓我們看到一個杰出作家的品質和風貌,看到他的精神和靈魂的質地,他的文學傳承和寫作技藝的淬煉,看到他的胸襟和非凡的氣宇,也看到他對公共事務的熱忱與介入。這是我們能看得見的壯闊的人性的海洋。
與時間面對面,這是庫切得以沉潛文學志業的緣由。庫切的手稿上都仔細地標注了寫作日期和修改時間。在寫作過程中必定有頻繁的修改,對手寫稿和打印件一字一筆地校正,在電腦上逐詞逐句地重新錄入,每部作品有十幾個版本的草稿都是家常便飯。
榮耀和贊美成為庫切生活的一部分。“他一直堅持自我的自由,他也沒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南非作家,而是一個在世界范圍內的寫作者,他所效忠的是小說的話語,而不是南非的政治話語。他的作品已被描述為嚴肅、復雜和輝煌的,是智慧、道德與審美的結合體。帶著決然與寬恕,庫切帶給讀者的是理解的冷靜慰藉。您勇敢而不妥協的寫作豐富了我們,也給我們帶來挑戰,迫使我們面對自己和我們所在世界的真相。”然而我記在筆記里的庫切在《青春》里對他的內心在困境中鏖戰的描寫,那是更為痛徹的體驗。
讀著這樣的敘事,你就知道一個杰出作家是如何煉成。
那是煉獄中的淬煉。
“經驗”,這是他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很想用的一個詞。藝術家必須嘗試一切經驗,從最高尚的到最有失身份的。正如藝術家命中注定要經歷最極致的創造的快樂,他也必須準備好承擔生活中的一切不幸、悲慘和恥辱。
……他必須坐下來寫作,這是唯一的辦法。但是不到合適的時候他無法開始寫作。無論他如何一絲不茍地做好自己的準備,擦干凈桌子,把臺燈放置好,在一張白紙的一側畫一道線留出頁邊空白。
……他怎么知道寫這些詩的人沒有多年面對白紙,和他一樣坐立不安地總也不能滿意?他們坐立不安,但終于振作起來,盡最大努力寫出了想要寫的東西,寄了出去,忍受著退稿的屈辱,或忍受看到他們筆下流出物以其全部的貧瘠呈現出令人沮喪的出版物中的屈辱。(《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