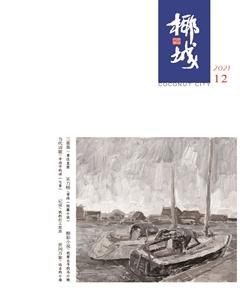舊跡
每一陣落花飄零,都會讓有情天地顫栗一次;每一場無端回首,都會讓世事無常加深一層。
人一旦有了春心,有了愛意,身邊萬物瞬間就會變得慈悲起來。就連山河、大地,如此宏大的意象,也被喚醒,變得溫潤靈性,含情脈脈,并開始幫我們銘記下這段心路歷程。
愛過,就有回想可倚;走過,就有舊跡可循。
從明月寺到鰲溪梁,原本是一條最普通不過的鄉野山路。那條路既有拾級而上的陡峭天梯,也有通往密林的羊腸小道,還要轉過幾個山梁,踩過幾條田埂,路過三兩戶人家的房前屋后,看到一所小白鴿一般靜靜泊在山灣處的白房子,就到了一個姑娘的家。
我把初戀交給了那里。此后,那條路就變成了我夢的一部分、魂的一部分,夢魂之間,霧鎖煙迷,幾多清晰,更幾多模糊。
歲月倥傯。幾十年之后,即使我無數次真真切切地重回到那條路上,卻再也找不到當時年少那份青澀稚嫩、懵懵懂懂的感覺,一切都變得似是而非,反而平添了幾分心迷亂和意躊躇,滿眼只余下時光悠悠、白云蒼狗。
記得當時年紀小,
你愛談天我愛笑 ,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樹下,
風在林梢鳥兒在叫,
我們不知怎樣睡著了,
夢里花落知多少。
這首名叫《本事》的歌謠,雖然字句單純,卻印證了這世間不只是我一個人有這樣敏感的情感體驗,究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夢里花落”:每一陣落花飄零,都會讓有情天地戰栗一次;每一場無端回首,都會讓世事無常加深一層。
看小百花越劇團排演的越劇《陸游與唐婉》,更是喚起了斷腸之感。遠歸的陸游,孑然一身,重游沈園,見人去樓空,往昔不再,乃唏噓長吟《沈園二首》: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
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
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
時過境遷,見證過他們年輕時光的沈園,如今連可供回憶的“舊跡”都不是了,而是變成了荒草掩映的“遺蹤”,只用來哀悼和憑吊,在無盡感傷中泫然淚下。“懷舊”一次,往往誘發了內心的又一次悲鳴,付出的靈魂成本實在太高了。
《紅樓夢》“題帕”的橋段中,黛玉咯血寫出了“湘江舊跡已模糊”,頗值得玩味。寶玉贈帕,寓意“橫也絲(諧音“思”)來豎也絲”,黛玉“聞弦歌而知雅意”,秒懂寶玉的良苦用心。同時,不送新帕送舊帕,暗指“新朋不如舊友”,黛玉對此中真意心領神會,難免就會“神癡”,魂不守舍。
黛玉提到的“湘江舊跡”,指的是“斑竹”,也叫“淚竹”,源于一個更美更雅的典故。湖南省寧遠縣九嶷山上的竹子,稱作斑竹,這竹子身上總是點點墨跡,累累斑痕。相傳,“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史記·五帝本紀》)。他的兩個妃子娥皇、女英未能隨他同去,二妃聞之,由北至南,奔喪而來,沿途撫竹痛哭,淚水灑在竹上成了累累斑痕,過后竹上的淚痕不能褪去,便盡成了斑斑淚痕,因稱此竹為“斑竹”。由于此竹的斑痕是娥皇、女英二妃的淚水染成的,后來二妃在過湘水的時候淹死在湘江,二人的魂靈變成了湘水之神,稱為湘妃、湘夫人,故又稱此竹為 “湘妃竹”“淚竹”。
“淚竹”,如此通人性,就像一冊竹簡,記錄著一部“苦情史”,實在是刻骨銘心啊!竹子上的斑痕早已成為“舊跡”,但是,那些斑斑點點里面,曾經轟轟烈烈的過去,一直還在動蕩不息,有情人見此,會睹物思人,觸景生情,怎能平靜,怎不喟嘆!在這方面,舒婷那首短詩《思念》,寫得不動聲色,卻有剜心之痛:
一幅色彩繽紛但缺乏線條的掛圖,
一題清純然而無解的代數,
一具獨弦琴,撥動檐雨的念珠,
一雙達不到彼岸的槳櫓。
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
夕陽一般遙遙地注目。
也許藏有一個重洋,
但流出來,只是兩顆淚珠。
呵,在心的遠景里,
在靈魂的深處。
外表看似風平浪靜,內心卻在恣意翻卷,“也許藏有一個重洋,但流出來,只是兩顆淚珠”,這該有多么巨大而深沉的魔力?
“舊跡”是一個時空概念,猶如草蛇灰線,飄飄忽忽,實在難以琢磨。一提到“舊跡”,就會惹出一大攤“心病”,不說也罷。但因它涉及人作為高級動物的共性,提升了人類普遍的情感,豐富了我們內心的認知,我才時常回望,畢竟那里有我過去愛過、悲傷過的線索,或可稱作“我們愛恨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