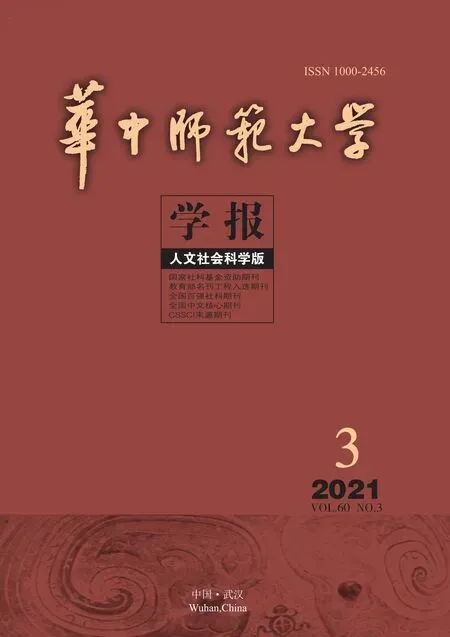日本新保守主義的歷史演變
孫巖帝
(重慶工商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0067)
時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西方陣營在冷戰對峙中走向強勢,“新保守主義”幾近同時發軔于日美英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由此開啟了世界范圍的政治右傾化進程。就日本而言,中曾根康弘、小澤一郎、安倍晉三無疑是日本新保守主義演變延長線上具有指標性意義的三位政治強人。他們不但先后扮演了日本新保守主義的“奠基人”、“理論旗手”、“踐行者”等關鍵角色,而且在日本政治右傾化中次第發揮了“啟動”、“推進”、“提速”等重要作用。迄今為止,關于三人新保守主義的“個案”研究已有所涉獵,但有關日本新保守主義的長時段和整體性探討尚無人問津。因此,就40年來日本新保守主義的演變進行大跨度系統梳理,不僅有助于彌補該課題宏觀研究之不足,而且對把脈今后日本政治走向和中日關系走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一、中曾根康弘與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發軔
中曾根康弘(1918—2019),生于群馬縣一富商家庭。1941年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后進入內務省工作,1942年加入海軍服役并獲副六級勛章。日本戰敗之初在警界基層任職,1947年當選眾議院議員開啟政治家生涯,歷任自民黨干事長、防衛廳長官、通產大臣等要職,直至1982年登上自民黨總裁和內閣總理大臣寶座。中曾根是一位能言善辯、思維敏捷、作風硬朗、戰略視野寬、理論素養高、敢于突破“禁區”的戰后日本政治史上屈指可數的保守派政治家。他經常以非主流的關鍵少數縱橫捭闔于派閥之間,也因一再對田中角榮等政治恩師反戈一擊而被冠以“風向雞”(即“墻頭草”)綽號①。中曾根雖因這般政治操守而飽受詬病,然其跨越大正、昭和、平成、令和“四朝”的百歲人生尤其是漫長政治生涯,卻為當代日本留下了影響巨大而又深遠的政治遺產。
1.中曾根康弘開啟了“日本新保守主義時代”
首先,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義產生背景復雜。中曾根援引司馬遼太郎的名著《坡上的云》說:自己的新保守主義是在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一直盯著的‘坡上的云’”(即歐美先進國家目標)隨著經濟高速發展而消散,“許多日本人感到惘然若失,無所適從”②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旨在為日本民族提供一朵新的“坡上的云”——實現政治軍事“大國夢”。其實,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產生背景十分復雜: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災難頻仍的自然生存環境,極易催生強烈的危機意識和養成內向保守的民族性格;根深蒂固的神國觀念和天皇“萬世一系”思想,極易誘生“民族群體向某一特定目標趨進的心性”③;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演變和“軍事強國”邁進,在中曾根等保守派政治家看來“理所當然”;日本保守勢力不愿面對也不甘接受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現實,圖謀重走戰前并不普通的“普通國家”老路;當年美國占領當局鏟除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和思想流毒的虎頭蛇尾,為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產生提供了保守政治家群體和精神支柱④;日美同盟的“主從關系”結構,為日本保守勢力的政治軍事大國化訴求提供了口實;國際社會曾一味就日本“經濟奇跡”送上謬贊,卻未及時對其新保守主義政治軍事野心保持應有的警惕。
其次,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義政治意味濃厚。他曾就“新保守主義”的內涵闡釋道:“保衛日本美麗的大自然和日本國土”,“保衛日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價值”,“保護自由的市場經濟”,“保護日本民族在大化改革和明治維新時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和積極的民族氣魄”,“這就是我所說的保守主義”⑤。金融泡沫破滅后,中曾根又就新保守主義的內涵補充說:保守主義乃是一種既“全面繼承歷史傳統文化”,又“以自由民主為基礎堅持不懈地進行改革”的“反激進主義的政治理念”⑥。只要縱橫比較便不難發現,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既與之前的日本傳統保守主義不同,也與幾近同時產生的美英兩國的新保守主義有別。吉田茂所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是以再現“經濟大國”輝煌為目標,以“重經濟,輕軍備”為表征的“經濟中心主義”;而濫觴于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是以重塑“政治大國”和“軍事強國”為目標,以“重政治,輕經濟”為表征的“政治中心主義”,實質在為“向戰前回歸”提供理論依據和精神動力。英美兩國的新保守主義,是集中體現于經濟領域即以建立“福祉國家”為訴求的民主主義;而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系主要體現在政治、軍事和外交領域即以實現政治軍事“大國夢”為目標的民族主義。
再次,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義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政治遺產除反映在《新的保守理論》(1978年)等50余部著作中,還體現于出任首相期間(1982年至1987年)推行的一系列內外政策上。前者主要就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進行了理論闡述,后者則將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化為現行政策加以踐行。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口號,力主“修憲”,動議開發核武器,突破防衛費不超過GNP1%限額,首開首相八一五“公職”參拜靖國神社惡例,強化日美同盟等,既系其新保守主義的主要內容,也是日本政治右傾化啟動的重要標志。當然,作為戰后日本政壇鮮有出其右者的政治家,他留給當代日本最大、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遺產,當屬“新保守主義”的推出和“日本新保守主義時代”⑦的開啟。
2.中曾根康弘新保守主義的闡述與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啟動
首先,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吹響了“戰后政治總決算”號角。如果說1978年《新的保守理論》一書出版意味著中曾根新保守主義開始醞釀,那么1983年極具沖擊力和挑戰性的“戰后政治總決算”口號的拋出則標志著其新保守主義正式出籠。該口號的核心內容有三。一是成為“國際國家”即“政治大國”。中曾根認為,經濟大國日本應該“為人類的和平、繁榮做出積極貢獻”⑧,而欲實現這一“期待和要求”⑨即“成為真正的國際國家”⑩,就必須著手“戰后政治”總清算和“增加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二是重新培植“民族自尊心”。他指出,崇洋媚美使日本政要喪失了制定國家長遠戰略的“覺悟和努力”,也導致日本民族失去了自尊心和獨立自主精神,故需清算“戰后政治”所造成的這一“弊端”。三是建設國防國家。他宣稱,日本應成為美國對抗蘇聯“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突破防衛開支不超過GNP1%的限制,實際在為回歸“軍事強國”創造條件。
其次,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拋出了“修憲”政治訴求。1947年生效的《日本國憲法》,因第九條否定擁有國防軍和放棄國家交戰權而被譽為“和平憲法”。戰后以來,日本保守勢力對這部給國家和東亞地區帶來和平發展“紅利”的憲法必欲鏟除而后快,因之“修憲”便成為中曾根新保守主義的政治訴求之一。出任首相前,中曾根經常指責“和平憲法”是“強制憲法”、“麥克阿瑟憲法”,成為“促進修改憲法的頭號熱心人”。組閣期間,中曾根一面表明“自己是改憲論者”、“修憲”“是本人的一貫理念”,一面又宣稱在“修憲”問題上“一個議員和一個總理的立場不同”,意在說明暫不將“修憲”提上政治議程只是出于長期執政考量。卸任首相后,中曾根重新打出“修憲”大旗,除繼續兜售美國“強加論”、憲法“缺陷論”外,還強調“日本擁有必要的自衛力量并不違背憲法第九條之規定”,推動日本早日成為所謂“正常國家”。
再次,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充斥著錯誤歷史觀。一是“英靈史觀”。由于懷揣“二百數十萬純真的英靈”是“為了保衛祖國和東洋和平”而戰死,“國民應該感謝為國家而倒下的人們”等錯誤認知,那些逞兇肆虐、斃命于侵略戰場的“皇軍”將士在中曾根眼中就成了“應該感謝”的“英靈”,而這些“英靈”生前所進行的戰爭也就不是什么“侵略戰爭”了。二是“自虐史觀”。中曾根不但將日本進步人士“反復使用‘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等言詞”稱為“自虐”,而且對戰后將“大東亞戰爭”改稱“太平洋戰爭”感到“不可思議”,甚至主張通過戰爭翻案來恢復民族自信,實是企圖用“皇國史觀”重新武裝日本國民尤其下一代的頭腦。三是“新天皇中心觀”。中曾根宣稱,自己之所以最崇拜天皇,是因為“天皇是歷史的、傳統的、權威的存在”,是一個“一無所有又取之不盡”的神圣存在,實際在為恢復天皇的實質國家元首地位鼓與吹。
最后,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啟動了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曾根康弘不但通過拋出上述政治理念將戰后日本從“傳統保守主義時代”推向“新保守主義時代”,而且通過突破一個個“禁區”——著手“戰后政治總決算”(1983年)、首開首相八一五“公職”參拜靖國神社的惡例(1985年)、突破防衛費不超過GNP1%的限額(1987年)等,率先啟動了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其結果,一是導致日本政治軍事大國化加快。在中曾根政治理念的引領下,后續日本內閣經常打著為世界做“貢獻”的旗號,要么一再向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目標發起沖鋒,用海部俊樹首相的話說就是:日本欲“為國際和平做貢獻”,唯有“入常”;要么掀起“修憲”濁浪和海外派兵(1991年),用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話說就是:憲法第九條是美國給日本鑲上的“令人不舒服的假牙”,誓言拔除。二是“戰爭翻案”風越刮越烈。在中曾根錯誤史觀影響下,在其參拜靖國神社行動的“率先垂范”下,日本右翼學者兜售的“自衛戰爭論”、“解放戰爭論”、“美英同罪論”、“南京大屠殺虛構論”、“東京審判復仇論”等種種戰爭翻案謬說甚囂塵上,以至在中曾根主政期間匯聚成一股洶涌的戰爭翻案逆流。作為中曾根“戰后政治總決算”的一部分,日本右翼知識精英“戰后學術總決算”的極端危害性同樣不容忽視。
綜上表明,中曾根新保守主義的精神實質是“向戰前回歸”,即以重溫戰前政治軍事“大國夢”為訴求。他不僅在思想理論層面豎起新保守主義大旗,而且在政治實踐方面啟動了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曾根康弘能夠成為日本新保守主義的“奠基人”和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啟動者”,除緣于他本人以理論見長、思想深邃外,既與其執政期間日本經濟高速增長、軍事實力迅速增強、右翼勢力重新抬頭等國內背景息息相關,也同日美同盟不斷強化、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等國際因素密不可分。對中曾根在日本新保守主義演變及日本政治右傾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需做出準確的評估。
二、小澤一郎與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系統化
小澤一郎(1942— ),生于巖手縣一政治世家,先后畢業于慶應義塾大學和日本大學。1969年當選眾議院議員后,歷任自民黨干事長、新進黨干事長、民主黨代表以及自治大臣、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等黨政要職,但始終未能登上首相寶座。小澤一郎能夠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政治家,既同其鮮明另類的從政風格和導演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政治大劇”密不可分,更與其將發軔于中曾根的日本新保守主義系統化、理論化為“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兩大政治理念息息相關。換言之,小澤一郎不但以罕見的理論素養成為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理論旗手”,而且以卓越的政治才能一度使“保守兩黨制”政黨政治格局初步形成和“普通國家”戰略目標部分獲得實現,成為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承前啟后的關鍵政治人物。
1.“保守兩黨制”:政黨政治制度的頂層設計及其執著嘗試
1993年小澤一郎推出《日本改造計劃》一書,就日本政黨政治模式和國家戰略調整方向進行了頂層設計,這就是影響巨大而又深遠的“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新保守主義兩大政治理念的推出。與此同時,小澤還是一位“知行合一”即注重將理念付諸實踐的政治家。可以說,無論其臺前縱橫捭闔還是幕后政治運作,無不旨在實現“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兩大政治夙愿。
首先,小澤一郎闡明了構建“保守兩黨制”的必要性。小澤認為,所謂“保守兩黨制”系指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結構中,兩個資產階級政黨通過總統選舉或議會選舉輪流坐莊,以維護資本家集團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換言之,“保守兩黨制”的內涵是:兩大保守政黨不分伯仲、勢均力敵;兩大保守政黨均代表資產階級利益,輪流執政;兩個政黨通過政見闡釋獲取選票,贏得議會或總統選舉;勝者上臺行使國家權力,敗者在野監督權力運行。鑒于美國總統能夠從若干政策選項中選擇最佳方案實施,而日本首相僅能發揮“主持儀式的神父的作用”,小澤確信美英兩國的“保守兩黨制”不但能夠避免決策失誤,而且有助于達成民主治國初衷,遂將之確定為日本政黨制度改革的目標。
其次,小澤一郎闡釋了構建“保守兩黨制”的迫切性。小澤矢志構建“保守兩黨制”的基本考量有四:一是,“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單肺國家”現實,妨礙了日本盡國際義務和做國際貢獻;在現行制度下日本政府只能“制定出被動的、短期的、局部的政策”,無法推行“主體的、綜合的、長期的、機動而首尾一貫的政策”;為不給國際社會添麻煩,必須賦予首相決斷權和領導力。二是,當下日本之所以陷入困局,主要緣于議會民主精神未獲貫徹,政府決策和實施機制未能建立;唯有構建“保守兩黨制”,才能根本擺脫目前困境。三是,明治維新和戰后改革之所以都能取得成功,原因之一便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原敬、吉田茂四位政治強人“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實現這一目標的權力意識”,小澤一郎渴望成為“第五位”杰出政治家。四是,海灣戰爭暴露出國會束縛內閣手腳、首相決策力和領導力欠缺等弊端;唯有進行議會和政黨制度改革,才能維持“經濟大國”地位進而實現“政治大國”目標。
再次,小澤一郎重點闡述了“保守兩黨制”的主要內容和運作模式。一是,為確保政府決策的正確性和連續性,構建理念相近、勢均力敵的“保守兩黨制”政黨政治架構勢在必行。小澤堅信,唯有“保守兩黨制”才能“使最高領導者承擔責任和能夠決定政策”,進而克服“五五年體制”下的“保革對立”所帶來的政府決策遲緩、行政效率低等各種弊端。二是,為確保政府施政高效迅捷,著手執政黨與內閣一體化改革事不宜遲。小澤認為,唯有黨的政策機構內閣機關化,黨的領導人內閣成員化,充實首相身邊的秘書官和智囊人員等,才能避免戰前因內閣權力分散所導致的悲劇,也才能改變戰后以來“權力分散于‘官’的世界中”之現狀,從而賦予內閣會議決策權和確保首相切實發揮政治領導作用。三是,鑒于中選區制使“政權輪替”和“改革成為不可能”,主張用小選區比例代表制取而代之。
最后,小澤一郎一度使“保守兩黨制”變為現實。1993年,小澤一郎在推出《日本改造計劃》一書的同時,不但率44名自民黨籍國會議員另組新生黨,而且一手導演了“八黨聯合政權”即細川內閣的誕生,宣告持續38年的“五五年體制”壽終正寢,日本政壇向“保守兩黨制”邁出重要一步。然而,小澤一郎的“保守兩黨制”政治實踐旋因先驅新黨和社會黨“轉向”而初嘗苦果。1994年底,小澤的新生黨又聯合九個在野黨成立新進黨,并在翌年大選中一舉成為國會第一大在野黨,日本政壇再現“保守兩黨制”曙光。1997年底,隨著新進黨因《宗教法人法》風波被迫解散,小澤的“保守兩黨制”愿景再度化為泡影。1998年初,小澤一郎又建自由黨,并先后運作誕生了“自自政權”(自由黨、自民黨)、“自自公政權”(再加公明黨),但旋因政策分歧而退出聯合政權。就在“保守兩黨制”屢遭挫折之際,崛起中的理念接近的民主黨又讓小澤一郎看到希望。2003年10月,小澤義無反顧率自由黨加入民主黨并出任副黨首(2006年4月出任黨首)。在擅長選戰又掌握對手(自民黨)內情的小澤一郎的高超指揮下,民主黨先后在2003年、2004年、2007年的眾參兩院選舉中屢創佳績,再次成為國會第一大在野黨,讓日本朝野再度看到“保守兩黨制”的曙光。就在小澤率民主黨向奪權目標發起沖鋒之際,2009年3月曝光的政治獻金丑聞給小澤和民主黨帶來重創。小澤遂將黨首一職讓位給鳩山由紀夫,自己退任干事長繼續組織和領導選戰。結果在2009年8月的眾議院大選中,民主黨一舉奪得308個席位而擊敗自民黨組閣,至此日本政壇不僅誕生了第一個由單一政黨執政的非自民黨政權,而且呈現兩大保守政黨民主黨與自民黨對峙的政黨政治格局,標志著小澤一郎的“保守兩黨制”政治訴求初步獲得實現。然而,小澤一郎不但與首相寶座擦肩而過,而且由于逐漸被邊緣化而不得不從民主黨游離出來。隨著民主黨走向衰落和自民黨一黨獨大局面再現,日本政黨政治與小澤一郎的“保守兩黨制”漸行漸遠。
2.“普通國家論”:國家戰略目標的重新設定及其現實追求
首先,小澤一郎就“普通國家論”的內涵進行了闡釋。小澤認為,必須改變日本“經濟巨人、政治侏儒”這一“不正常”的國家形象,努力建設成為該做就堅決去做的國家和在地球環保方面開展合作的國家;只要為國際社會尤其是國際安全做出貢獻,日本就能成為一個可以自主決定內外政策的“正常國家”或“普通國家”。為此,小澤一郎一面主張承認侵略歷史以便早日“入常”,一面又宣稱不存在“侵略戰爭”與“正義戰爭”之別;一面主張對華對美開展等距離外交,一面又強調以日美關系為外交基軸。可見,小澤一郎渴望成為的“普通國家”并不普通,而是一個意欲重披“鎧甲”的政治軍事大國。
其次,小澤一郎就“普通國家論”提出的依據進行了闡述。一是,日本欲做出“國際貢獻”,就必須先成為“國際國家”;擬成為“國際國家”,就必須先恢復成“普通國家”。二是,日本既應借鑒威尼斯靠經商、外交和海軍力量稱霸地中海并“維持了千年繁榮”之成功歷史經驗,也需汲取迦太基僅用金錢招募雇傭軍而被落后于自己的羅馬軍團滅亡之慘痛歷史教訓,做一個威尼斯式的“普通國家”。三是,只有內政與外交相互配合,才能發揮各自的政策效應,也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普通國家”。四是,唯有糾正對“吉田主義”的錯誤認知,改變國防依賴他國的狀況,讓日本成為一個有目標追求的國家,使日本國民“成為國際社會中正常的‘普通國民’”,日本才能成為健全的“普通國家”或“正常國家”。
再次,小澤一郎就“普通國家論”的主要內容和實現路徑進行了說明。一是,“借船出海”。小澤認為,盡管“修憲”訴求不宜動搖,但強化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應該選擇的道路”,也是“普通國家”戰略目標實現的路徑之一。二是,推進聯合國外交。小澤認為,應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和敦促聯合國改革,使之成為日本“普通國家”化的重要推手。三是,修改“和平憲法”。小澤主張,通過在憲法第九條中增加不妨礙自衛隊“維和”之“第三款”、在憲法之外另訂一部“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解除“和平憲法”對日本“普通國家”化的束縛。四是,改變防衛戰略,積蓄軍事力量。小澤建議,用“和平創出戰略”取代“專守防衛戰略”,使日本“自衛隊不僅能夠對付純軍事的威脅,而且能夠從事軍事以外的各種活動”。五是,推行“價值觀外交”。小澤認為,只要積極參與“世界新秩序的創建”,繼續以日美關系為外交基軸,“明確顯示重視亞太地區的外交姿態”,日本就能從“單肺國家”回歸為“普通國家”。
最后,小澤一郎將“普通國家論”政治理念付諸實踐。一是,奉行矛盾性或兩面性的對華外交政策。小澤非常清楚,日本擬成為“普通國家”尤其是達到“入常”目的,必須獲得常任理事國中國的理解;而欲獲鄰邦中國的理解,就必須清除歷史觀沖突這一嚴重障礙。然而,小澤一郎一面主張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該反省就反省”,一面又宣稱“對戰爭中的殺人行為給予價值判斷是錯誤的”。類似的兩面性或矛盾性言論在小澤的外交話語體系中并不鮮見。二是,強推“普通國家”化相關法案。在小澤一郎嫻熟老道的政治運作下,日本國會通過了“有事三法案”等,致使“和平憲法”名存實亡。三是,強化日美同盟和聯合國外交。為換取美國對日本“普通國家”化的支持,小澤不但支持橋本內閣修改了《周邊事態法》等法案(1997年),而且迫使小淵內閣接受了有助于推進“普通國家”化的若干條件(1998年)。2002年4月6日,小澤一郎在福岡市發表演說稱,“(日本)只要愿意,馬上就可以用核電站的钚制造出幾千枚核彈頭”,公然向“無核三原則”發起挑戰。隨后,他又推動國會通過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等法案,為日本“普通國家”化提供了“法理”依據。
總之,在日本新保守主義演變的歷史延長線上,小澤一郎可謂承上啟下的關鍵政治人物。他不僅將發軔于中曾根的日本新保守主義理論化、系統化為“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兩大政治理念,使之成為世紀之交日本新老保守勢力共同遵循的指導思想和日本歷屆內閣政黨制度改革及國家戰略調整不變的政治訴求,而且將這兩大政治理念付諸實踐并部分獲得實現,強有力推進了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
三、安倍晉三與日本新保守主義的踐行
安倍晉三(1954— ),生于東京一政治豪門家庭。1993年當選眾議院議員伊始,就經受了自民黨首度淪為在野黨的政治洗禮。后雖然在政治上“經歷過重大挫折”,但憑借個人的政治才能及祖輩和父輩留下的人脈,繼擔任自民黨干事長、內閣官房長官等黨政要職后,僅用13年時間就登上了自民黨總裁和首相寶座(2006年),并雙雙創下連續在位時間最長(7年又8個月)和史上累計在任時間最長(8年又8個月)的政治紀錄。尤須指出的是,盡管祖父安倍寬戰時因反對東條英機而被視為有骨氣的政治家、父親安倍晉太郎戰后擔任過自民黨干事長、外務大臣等要職,但安倍晉三最崇拜的卻是出任過戰時東條內閣商工大臣及戰后日本首相的外祖父岸信介。正因為當年的甲級戰犯嫌疑人岸信介是最令其“感到驕傲”的“嚴肅的政治家”,正因為岸信介留下的“修改憲法這把火是不能熄滅的”政治遺訓被其牢記,安倍的“政治DNA更多地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成為日本新保守主義演變延長線上和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的第三位關鍵政治人物,也就不令人費解了。
1.安倍晉三的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
首先,“美麗的國家”是安倍晉三新保守主義的目標追求。2006年9月29日,安倍首相在首次國會施政演說中就“美麗的國家”之內涵闡釋道:“美麗的國家”應該是重視文化、傳統、歷史、自然的國家;以自由社會為根本的凜然的國家;持續有能量的國家;對世界具有領導力的國家。一句話,就是“令全世界的人都憧憬和尊敬、讓孩童一代都感到自信和自豪的‘美麗的國家’”。從其中“凜然的國家”、“有能量的國家”、“具有領導力的國家”等用詞來看,安倍擬締造的“美麗的國家”并不“美麗”,而是一個政治軍事大國化的危險國家。
其次,“修憲”是安倍晉三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夙愿。其“修憲”目標有二:一是,刪除“和平憲法”第九條,建立國防軍,恢復國家交戰權,使日本成為“普通國家”;二是,補充“積極的和平主義”政策條款,為世界做出軍事“貢獻”,為“入常”提供政治資本。其“修憲”動力除源于外祖父政治遺訓的鞭策,還緣于五個因素的共同推動。一是,緣于“經濟大國”地位的重新確立。安倍對“經濟巨人、政治侏儒”國際形象不滿,更對剝奪了國家交戰權和擁有國防軍權利的憲法第九條耿耿于懷,必欲鏟除而后快。二是,緣于日本經濟復蘇乏力。隨著經濟泡沫破滅尤其是中日經濟總量發生歷史性逆轉,日本朝野滋生出焦躁、憂慮、不自信、不適應等復雜心態,安倍首相試圖通過“修憲”提振民族精神,進而重振大國雄風。三是,緣于美國的默認和縱容。為發揮同盟國日本在遏制中國崛起中的作用,美國當局對日本國內的“修憲”逆流采取了放任乃至縱容態度,這是對安倍的莫大支持。四是,緣于擴張主義歷史傳統。“海外雄飛”是日本右翼思想意識中不變的主題。在安倍看來,解除“和平憲法”桎梏是走向“普通國家”的關鍵和重現戰前“輝煌”的前提。五是,緣于安倍本人的政治謀略。他深知,通過振興經濟贏得選票短期內難以奏效,唯有祭起“修憲”大旗才能迅速樹立“偉人”形象,進而實現長期執政。
再次,右翼史觀是安倍晉三新保守主義的思想基礎。安倍史觀有三個鮮明特征:一是,荒謬性。安倍經常拿美國阿靈頓公墓與靖國神社做類比,聲稱“一國領導人對殉國者表示尊崇之念,是哪國都有的行為”,顯然在為自己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徑辯護,也混淆了兩處設施的性質和功能。如果說阿靈頓國家公墓主要是為祭奠在南北內戰和反法西斯戰爭中陣亡的將士以及為國家做出杰出貢獻的人而設置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那么靖國神社則是戰時鼓動國民參軍參戰的侵略擴張工具和戰后毒害下一代的軍國主義教育基地,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恰如日本學者高橋哲哉所言:“靖國神社只厚待戰死軍人,這是由超越‘文化論’的國家政治意志決定的。”安倍還質疑東京審判并為戰犯鳴冤叫屈說,“東京審判是由盟國戰勝方單方面做出的裁決”,“所謂被稱為甲級戰犯的諸位,是在東京審判中被認定為戰犯的,按照國內法不是戰犯”。類似不分善惡、不明是非的荒謬言論,在安倍的話語體系中屢見不鮮。二是,矛盾性。安倍一面承認日本是聯合國和國際法院“關于侵略定義之決議”的簽字國,一面又聲稱“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乃至國際上沒有定論”;一面肯定戰后民主制度并表示“今后也絕不打算改變”,一面又力主擺脫“戰后體制”束縛與“和平憲法”桎梏。凡此,旨在貫徹其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三是,雙標性。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安倍對當年的侵略對象國采取了因國而異的雙重標準和因應對策。諸如,2007年,當其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謬論同時遭到亞洲鄰國批判和美國國會“決議”譴責時,安倍對來自鄰國的批評置若罔聞,卻一再向美媒和布什總統表示對慰安婦的遭遇“感到有責任”、“從心底表示同情”和“抱歉”;2014年初,當美國政府對其“公職”參拜靖國神社表示“失望”后,安倍立即派胞弟岸信夫(副外相)和親信谷內正太郎(安保局長)赴美解釋,卻對來自鄰國的譴責和抗議充耳不聞。這是日本右翼勢力欺軟怕硬秉性的反映。安倍史觀成為其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思想認識基礎,不但助推了日本國內的“戰爭翻案”暗流,而且加速了日本“向戰前回歸”的進程。對日本國內的這一動向,需做好應對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2.安倍晉三的新保守主義政治實踐
第一,“公職”參拜靖國神社。在供奉于靖國神社的246萬余尊亡靈中,不但戰死于對外侵略戰爭者多達2438477名(占99.4%),而且其中立有14名甲級戰犯和一千多名乙、丙級戰犯的靈位。繼中曾根首相首開八一五“公職”參拜靖國神社惡例、小泉首相首開任內每年“公職”參拜靖國神社惡例之后,安倍首相亦悍然于2013年12月26日走進靖國神社參拜戰犯亡靈,用行動表明自己的歷史修正主義立場。安倍選擇此時此刻參拜的考量有三:一是,感到首相“公職”參拜靖國神社的國內條件已經成熟。因為當時在20多歲的日本年輕人中,“贊成安倍參拜靖國神社”者多達60%。二是,居心叵測、包藏禍心。他特意選在毛澤東120周年誕辰日參拜靖國神社,旨在激起中國人民憤慨及引發中國社會強烈反彈,從而為“修憲”和政治軍事大國化尋找借口。三是,時值節日假期,心存僥幸。安倍自以為選在圣誕節假日參拜,不會引來美國當局譴責和干涉。然而,其參拜行徑立即遭到國內外強烈譴責:日本正義人士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安倍的參拜“暴舉”;中國政府和人民理所當然進行了譴責,但并未出現日本右翼勢力期盼的社會動蕩和失控局面;美國也不像他們想象的那么“遲鈍”,其駐日使館在安倍參拜數小時后迅速發聲,明確向日方表示“失望”。
第二,修改《教育基本法》。鑒于明治初年頒布的《教育敕語》淪為日本政府“忠君愛國”教育和發動侵略戰爭的工具,戰后初期美國占領當局遂以《教育基本法》取而代之。然而隨著日本政治右傾化提速,安倍內閣首先對《教育基本法》開刀,以實施“擁有大國化自覺的國民教育”,培養年輕人的“愛國心”。2006年底日本國會強行通過的新《教育基本法》,將培養“愛國心”和“集體主義精神”塞進其中,日本學校道德教育被“引上歧途”。前述60%的日本年輕人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表明,其所謂“愛國心”教育已然收到“實效”。《教育基本法》的修改,還使嚴重失實的右翼教科書大行其道。2015年,推卸九一八事變責任、否定“南京大屠殺”史實、質疑“東京審判”合法性的右翼《新歷史教科書》被文部省審定為“合格”,便是新《教育基本法》推波助瀾的結果。
第三,強推“密保法”。2013年12月6日,一部《特定秘密保護法》在安倍內閣和自民黨的力推下由國會通過。這部涉及外交、防衛、反恐、防間諜內容的“密保法”明確規定:國家公務員及相關人員泄漏或者有意搜集日本軍事秘密的,均被視為犯罪行為,最高可判處死刑。其影響在于:這部“密保法”不但類似戰前的《治安維持法》直接針對日本國民,還包括對在日華僑和朝鮮人的監視;不但限制了國民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且強化了首相的權力和放寬了對自衛隊的限制;不但加快了日本政治大國化進程,而且為向軍事強國演變做了政策鋪墊。
第四,“解禁集體自衛權”。為了實現包括外祖父在內的新老保守勢力的軍事大國化夙愿,安倍內閣利用美國政府的縱容和支持,終于在2014年7月1日強行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內閣決議案”,提出日本在遭受武力攻擊或者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國家在遭受武力攻擊時,可以行使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武力。然而,恰如前首相吉田茂曾準確理解的那樣:“(憲法)第九條第二項否認一切軍備與國家交戰權的結果,是放棄了以自衛權之名發動的戰爭以及交戰權。”在吉田首相看來,不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是憲法第九條的題中應有之義。而現如今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實質是在扭曲吉田茂的憲法解讀尤其是否定第九條對國防體制和武裝力量的明確規定。其后果是:架空“和平憲法”,為最終完成“修憲”埋下伏筆;為強軍和武器出口大開方便之門,使日本成為地區乃至世界的新禍源;在使日本成為美國對外戰爭幫兇的同時,也會使存在歷史恩怨的美國最終成為日本復仇的目標。用安倍的話說就是,要“把日本從戰后歷史中奪回來”。
第五,推進“修憲”進程。為完成外祖父的“修憲”遺愿和自民黨的“制憲”立黨使命,安倍內閣不遺余力加快“修憲”步伐。包括:采取升級防衛廳為防衛省、解禁集體自衛權、頒布“密保法”等迂回戰略解構“和平憲法”,使“憲法”第九條失去約束力;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朝鮮半島危機論”,為“修憲”制造借口;持續兜售現行憲法“強加論”和“過時論”、制定自主憲法“權利論”和“需要論”,為“修憲”造勢。安倍內閣最初采取的是“明文修憲”方式,例如自民黨《憲法修正草案》刪除憲法第九條“不保有戰力”關鍵字句等;后轉而奉行“解釋修憲”戰略,并打出“積極的和平主義”旗號作掩護。2013年7月29日副首相麻生太郎在東京發表的如下演講,一語道破了安倍內閣“解釋修憲”的本質:“(德國)魏瑪憲法在不知不覺中就變成了納粹憲法。如果我們學習(這一)手段怎么樣?”公然號召日本國民學習納粹當年的做法,用“憲法解釋”方式“在不知不覺中”將“和平憲法”修改為“納粹憲法”。小堀桂一郎等右翼學者與安倍政府遙相呼應,鼓噪必須制定“與明治時期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有內在繼承性的自主憲法”,“必須排除抵抗,修改憲法第九條”,要“找回失去的日本”,要解決“憲法第九條與核武裝”問題等等,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勢。
第六,加快“強軍”步伐。安倍政府實現了安保政策的兩次“躍進”:一是,在2012年至2014年的兩年中連續射出安保“三箭”——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頒布新《防衛計劃大綱》等文件,為整體提升軍力和實現防衛政策調整奠定了基礎;二是,在2014年至2016年的兩年間又連續射出新安保“三箭”——改變武器出口方針、解禁集體自衛權、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表明日本防衛政策發生重大轉變和安倍政府在軍事大國化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受到右翼勢力的一致歡迎。
第七,強化“日美同盟”。當初締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1978年),旨在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隨著蘇聯解體,該“指針”本來失去了存在的依據,但日美兩國卻將“指針”矛頭轉向崛起中的中國。1997年9月完成修訂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將日美軍事合作的范圍擴大到所謂“周邊事態”。安倍“梅開二度”后,經兩國防長先后四次緊鑼密鼓地磋商,又于2014年10月完成了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進一步修訂。此次修訂的目的在于:一是,“借船出海”、相互利用。美方希望日本能夠在自己推行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發揮關鍵作用和擔負更多的職責;而日方則旨在利用日美同盟實現海外派兵和完成“修憲”。二是,“聯美遏華”,即借助美軍力量應對中日島爭,增強兩國在第一島鏈對抗中國的實力。《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一再修訂即日美同盟的不斷強化,實現了日本軍事大國戰略與美國維護世界霸權戰略的“無縫”對接,也推動了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
第八,推行圍堵中國的“價值觀外交”。冷戰結束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與日本經濟長期低迷所形成的鮮明對照,尤其是中日兩國經濟總量發生歷史性逆轉的嚴酷現實,給日本人尤其是右翼政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由此所產生的焦躁情緒和挫折感進一步強化了其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島國危機意識。恰如日本學者南博指出:“每當日本面臨重大變故,日本社會就會產生強烈的‘自國意識’,有關日本民族性的‘日本人論’也會成為熱門話題。”作為日本最高首腦、日本新保守主義的踏實踐行者和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強力推進者,安倍晉三當然不會坐視這一態勢持續下去。在本國經濟復蘇乏力、正常競爭難以奏效的情況下,安倍便試圖用“價值觀外交”、“主見性外交”、“戰略性外交”,取代以往對東亞鄰國的所謂“服從外交”、“被動外交”、“屈辱外交”,以構筑圍堵中國包圍圈進而遏制中國崛起勢頭。
總之,作為戰后在位時間最長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既是日本新保守主義的踐行者,也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提速者。這一方面與美國“重返亞太”等國際背景相關聯,也與其“政治DNA”即外祖父岸信介的言傳身教密不可分,更與其以行動力見長即少說多做的執政風格息息相關。右翼大佬們送上的“不愧是岸信介的后代”(中曾根康弘)、其對華強硬立場將成為“歷史證言”(岡崎久彥)、是“了結戰后政治恩怨的人”(中西輝正)等謬贊,以及安倍本人或身穿迷彩服登上“731”編號戰機,或穿上96號球衣在公眾場合亮相(“和平憲法”第96條就“修憲”程序做出規定),或在日本天皇即位儀式上振臂三呼“天皇陛下萬歲”等行徑,均足以反映這一點。安倍晉三雖然理論建樹不多,但在踐行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方面尚無出其右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安倍晉三在日本新保守主義演變延長線上的地位尤其是在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覷。因為對政治家來說,“理念”化為“政策”最終成為“現實”乃題中應有之義。
四、結論
通過對日本新保守主義及政治右傾化演變軌跡的系統梳理,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日本新保守主義既主要體現于中曾根康弘、小澤一郎、安倍晉三先后推出的《新的保守理論》《日本改造計劃》《致美麗的國家》三部代表性著作中,也反映在三位政治強人提出的政策主張里;既與以重建“經濟大國”為目標的日本傳統保守主義不同,也同以建立“福祉國家”為主要訴求的美英兩國的新保守主義有別。對三位政治強人分別扮演的日本新保守主義“奠基人”、“理論旗手”和“踐行者”角色,以及先后對日本政治右傾化發揮的“啟動”、“推進”和“提速”作用,只有置于世紀之交40余年的日本政治史中觀察和評估才能更準確一些。
第二,作為日本新保守主義政治思潮的現實反映,日本政治右傾化不但已演變成為一股洶涌的政治逆流,而且呈難以遏止之態勢;不但導致日本內政和外交全面右傾化,而且滲透到國民意識層面;不但協助美國“重返亞太”打破地區“均勢”,而且向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發起一次又一次沖鋒。對日本政治右傾化給日本政局走向、中日關系走勢和亞太地區格局變化帶來的深遠影響,只有放在戰后70余年的日本史和東亞史中觀察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第三,日本新保守主義思潮的蔓延和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加劇,是日本新保守主義政治家推動和不覺悟國民盲從的結果,只是身為國家“舵手”和民族“領航員”的三位政治強人起了引領作用而已。換言之,如果說日本社會黨“幾乎一夜之間就完全拋棄了左派制定的黨綱”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標志之一,那么日本國民對右翼政客參拜靖國神社行徑的寬容則可視為日本社會右傾化的重要體現。因此,對日本社會總體右傾化與日本新保守主義思潮蔓延、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快的因果關聯性無須回避。
第四,日美同盟既是日本新保守主義產生和日本政治右傾化提速的助推因素之一,也是阻止日本“向戰前回歸”的強有力制約因素。40多年來,基辛格一再向周恩來做出的鄭重承諾以及再三向世人發出的忠告——“美日軍事同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牽制日本……如果東京重新回到擴張主義老路的話,美國將撤銷對日本的核保護傘”,“中曾根掌權意味著日本暴力的國家主義抬頭,美國將盡最大努力遏制這一動向”,日本若成為“普通國家”“推行獨斷且具有攻擊性的外交政策,將成為地區隱患”等,便足以表明這一點。因此,認清美日同盟的“主從關系”實質,有助于評估美國因素對日本新保守主義政治思潮及其政治右傾化的“雙刃劍”作用。
注釋
③孫立祥:《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34頁。
④粟屋憲太郎:《東京審判秘史》,里寅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第94頁。
⑥董立延:《融合傳統與改革的保守主義哲學——評中曾根康弘新著〈保守的遺言〉》,《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7月5日,第13版。
⑦內田健三:《現代日本の保守政治》,東京:巖波書店,1959年,第131頁。
⑧王希亮:《論80年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史觀的泛濫同新保守主義的關聯》,《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
⑩日本外務省:《外交靑書》,東京:大蔵省印書局,1984年,第3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