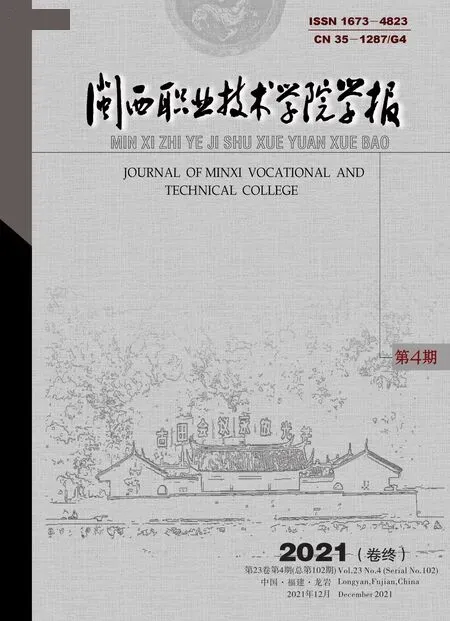論何凱旋小說的民間性特征
——以《江山圖畫》為例
任 雨
(牡丹江師范學院 文學院, 黑龍江 牡丹江 157000)
出生于黑龍江密山的何凱旋,是黑龍江本土作家群的中堅力量,著有長篇小說《昔日重現》《都市陽光》《江山圖畫》,話劇《紅蒿白草》《夢想山巒》《1945 年以后……》,先后獲東北文學獎、黑龍江省精品工程獎、黑龍江省文藝大獎,哈爾濱天鵝文藝大獎和第十六屆、第十九屆田漢戲劇獎,首屆“大益文學雙年獎”最佳小說獎等。2009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江山圖畫》以黑龍江省六大山脈之一的完達山為故事發生地,敘述農場兩戶人家日常的生活,呈現苦難與溫情、傳統與現代文明碰撞中的民間風貌,是一部書寫黑龍江民間生活的小說。 何凱旋在小說中不采用傳統的敘事手法,而是從個人和家族的生存本相微觀敘事,打破以往固有的農村與政治、 農村與城市或對立或融合的模式,還原最為真實平凡的東北民間世俗生活。
文學理論中的民間概念是一個多維度的復雜概念, 這一概念被人們廣泛關注和討論源于20 世紀90年代,由陳思和首先提出。 他在《新文學整體觀續編》一書中認為,“當代大學里的民間概念,包含兩個層面意思: 第一是指根據民間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度向, 即來自中國傳統農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來自現代經濟社會的世俗文化的方式來觀察生活、 表達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學創作視界;第二是指作家雖然站在知識分子的傳統立場上說話, 但所表現的卻是民間自在的生活狀態和民間審美趣味。 作家注意到民間這一客體世界的存在,并采取尊重的平等態度而不是霸權態度,使這些文學創作充滿民間的意味”[1]。本文從文學理論中的民間概念出發,探究小說《江山圖畫》在內容、藝術手法上所表現出的民間性特征,以及作家民間立場的表達。
一、多重包容的民間生活狀態
完達山是一個美丑并存、善惡共生的民間世界,有著無限的包容性。在這種空間背景下,何凱旋不但洞察到民間世界的劣性與野性, 而且捕捉到民間存在的美好品質,構建的民間世界既有愚昧、自私、野蠻、算計等劣根性,又有樸實、善良、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美好品德。
何凱旋在小說中借助一個生長于這片土地少年的視角觀照人物的生存狀態,摒棄“輕易站出來指手畫腳完成他們自有規律的習慣”[2], 保持一種客觀尊重的態度,既不歌頌人的善良與美好,也不掩蓋人的丑陋與骯臟。當人受到現實生存困境的制約,金錢的欲望被挑起時,“小聰明”的劣性與野性一同迸發。小說中的爹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人: 算計到雨天公路上有錢可賺,開車拉著“我”帶上繩子駛向公路,有償拖拽陷進水坑的油罐車,趁機加錢;幫三楊母親送葬誤工后爹蠻橫地搶來他家的新牛車拉化肥;因國順丟失“我”家的馬,爹搶占三楊一家的新房子作為補償。 三楊一家則更是像民間的痞子,無賴、自私:三楊總以他母親的由頭向“我”家理所當然地借東西, 國順不靠自己勞動經常偷魚偷馬, 楊香向“我”家賣魚、吃酸菜時耍賴與胡攪蠻纏,他們在“我”家馬被人牽走時表現出看戲的冷漠。 面對普通民眾長久以來所形成的狡黠、算計等性格弱點,作家并沒有刻意回避,而是以民間的自有法則進行審視。除此之外, 何凱旋還在小說中表現民間神秘的神靈觀念和愚昧的迷信。 神秘的神靈觀念廣泛存在于民間社會,伴隨自發性的信仰崇拜,成為一些人的精神支撐。三楊母親去世時手里緊握一炷香向著青銅佛像;三楊燒香祈求女兒生產順利以獲取自我安心; 完達山農場的人們認為人死后要扎夠七天的白麻布, 燒三炷香都升起就會大吉大利,烏鴉是報喪的不祥之物。何凱旋用這些表現民間生存狀態中的封建與迷信。
何凱旋在展現民間糟粕和人性惡的同時, 著重突出完達山農場民間生活的美好元素。 爹是一個勤懇務實的普通農民,精通各種勞作技術,帶領“我們”一家開荒種麥子,每天都忙于養馬、砍柴、耕地、播種、追肥等各種勞作,總是一副忙碌堅毅的樣子,用自己的雙手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腳踏實地而又安分守已。爹沉默寡言的外表下有一顆溫暖的心,“我”同母異父的哥哥小鍵呆了短短幾天就要回城里時,爹非常細心地準備了錢給他。在三楊母親去世時,雖然爹總是與三楊一家產生矛盾, 他主動出力幫三楊安葬他母親。 小說還描寫了國順奮不顧身沖進火海砍樹阻擋火勢蔓延的勇敢行為、三楊孝順母親、楊香努力過日子等,展現民間人們的美好品質。
作家通過人性的張力使民間成為自由、包容、充滿無限可能的象征。一方面,作家以“我”的視角進行敘事,兒童的所言所思總是單純無所顧忌,加強了“我”面對善惡事件的主觀色彩。 “我”的媽媽桃兒原來并不屬于完達山農場,因未婚先孕執意生下孩子被發配到這里,由于生長背景的不同,媽媽有著與民間觀念相沖突的道德準則,像是一個“說教者”。她認為楊香與國順住在一起是傷風敗俗的事情, 爹耍聰明趕走三楊家的新車在“我”看來是非常厲害的事,但媽媽卻輕蔑地說“像賊一樣,一點道理也不講”[3],并經常教育“我”和姐姐。但長期的民間生活,使媽媽逐漸認同了民間的生存哲學。三楊與“我”媽媽評理爹趕走他家的新車時,“我”媽媽以這是幫他母親送葬耽誤農事的補償為由打發了三楊, 馬軍與姐姐戀愛時的親密舉動同樣并沒有遭到“我”媽媽的制止與訓斥。另一方面,何凱旋運用全知視角進行敘事,對民間的價值觀給予充分的尊重。翟木匠與擠奶工公開調情,三楊在其母親剛下完葬就與寡婦鄭喜鳳在一起,這些原本會受到排斥與唾棄的事情, 通過作家的民間立場描寫,使人的生命有了率性鮮活的感覺。在何凱旋的筆下,民間是一代人、一方土地的真實縮影,民間生活狀態自在包容。
二、日常生活敘事的民間審美趣味
日常生活敘事以普通民眾的悲歡離合為書寫對象,還原日常生活,解析小人物的世俗欲望與生存,“成為觀察時代轉型和人性變遷的舞臺”[4]。 在《江山圖畫》中,作家將視點放置到對民間日常生活的關注上,敘寫的是一幅不受外界渲染、生動活潑的民間日常影像,純粹而富有生命活力。與部分知識分子拒絕和改寫日常生活的寫作姿態不同, 何凱旋認為樸素的東西更有力量。他在小說中強烈關注現實生活,用簡約樸實的話語, 試圖將民間日常生活的繁雜與瑣碎真實記錄下來, 忠誠于寫實手法, 鐘情于世俗生活,作品富有煙火氣息,富有民間審美趣味。
小說細致描摹農耕場景, 表現具體可感的百姓日常生活。何凱旋出生于密山農場,從小見聞農場的點點滴滴,親身經歷農場的生產勞作,受到童年經驗和歷史文化的熏陶, 在創作時將自己對農場日常生活的個人記憶融進小說, 對民間圖景進行再現式還原。農業生產作為農村重復的慣常行為,成為作家日常生活敘事的對象。 作家將筆觸延伸到農民所生存的世界,細致描摹農耕場景,嫻熟地再現底層人民的生活面貌, 表現民間自給自足的生存本相。 小說以“我”和爹買馬準備開荒為起始,以莊稼生長的不同時間段展開情節的敘述,將人物的日常勞作活動貫穿全文。“我”和爹在自家園子前開辟一塊荒地,從用斧子砍樹開荒到耕地播種,從給麥子追肥到收割晾曬,展開一系列的農業勞作,“媽媽和姐姐, 她們倆站在牽引架后面掛著的播種機上面, 用棍子攪拌著播種箱里的種子,麥種通過一排膠皮管流進壟溝里面”[3]。小說高度還原化的細節描寫,生動展現“我”家播種時的勞動場景,在日常生活的真實再現中完成文本的架構。何凱旋不僅實錄傳統的原始勞作方式,而且契合小說的故事時間, 將農業活動融入機械現代化的發展浪潮,展現當時農村農耕發展二元融合的現狀。小說再現耕種、收割等場景時,出現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現代農具的身影,呈現勞作場景的時代特色,突出時代浪潮中農村的選擇與順應。 何凱旋有意打破傳統文學對民間或苦難或理想的兩極書寫趨勢,將農耕場景拘囿在散發著淡藍色光芒的完達山脈,既滿足詩意的民間風貌,又肯定勞作自給自足的價值。
“日常生活中活動的人是鮮活的生命個體,生活的簡單與復雜、平凡與豐富……就是一塊值得去發現和言說的領域。 ”[5]除了田野勞動,夫妻拌嘴、鄰居紛爭、婚喪嫁娶成為被敘述的主體,何凱旋在瑣碎雜事的敘述中為讀者展現原生態的生活。 他以平視的姿態貼近民間的普通民眾,把那些看似無味的日常瑣事當作敘事的主體加以展現,使生活本身產生意義。小說圍繞兩戶人家的日常生活、情感糾葛展開敘述,以細致的描摹揭開生活的面具。 小說安排“我”家開荒種地、三楊以他媽媽為由頭向“我”家強要東西、國順偷魚受傷但屢次不改、三楊母親安葬、“我”同母異父哥哥來訪、姐姐與周軍無疾而終的愛情、“我”媽媽與爹先弄院子還是先弄門而爭執等瑣事,將民間的百態生活娓娓道來。在小說中,何凱旋不刻意書寫那些苦悶無助、無所適從的世俗情境,而是賦予人物個體意識的覺醒,每個人都在詮釋自己對生活的態度,日常生活成為個體自由意志的表達。何凱旋將藝術技巧與自己對現實的握力相結合,去飾求真,展現普通民眾真實生動的生存狀態,塑造更加鮮活靈動的民間世界。
三、質樸親切的民間意味
方言、 俗語作為這片土地的先輩們創造出來的語言,被生長于這片土地的民眾所接受吸納,成為融入血脈的第一語言。當作家回首故鄉進行創作時,方言成為其文學獨特的外在表現, 金宇橙的上海滬話寫作,劉玉堂的沂蒙小說語言,遲子建和韓少功等人對地域文學的書寫, 構成了區別于他人的地域創作風格。何凱旋作為一位土生土長的黑龍江作家,有著濃厚的地域文化底蘊,不斷踐行文學“須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他的脈搏,表現在文學上”的原則[6]。 在《江山圖畫》中他不避俗,運用大量東北方言和具有民間特色的語言表現民間生活, 鍛造質樸親切和地域鮮明的美學特征。
《江山圖畫》大量使用“壟臺”“火墻”“玉米樓”“障子”“窩棚”等具有地方生活化的方言,構建寧靜祥和的東北民間生活圖景: 在散發著純凈淡藍色光芒的完達山腳下, 兩戶人家的身影總是穿梭在被耙過的荒地、新背起的壟臺上;夜晚他們則順著風化石的道路走回家,或睡在玉米樓上,或躺在叫火烤熱的炕頭。小說以農場為故事空間展開敘述,在刻畫人民勞動場景時,大量使用“镢頭”“鐮刀”“笤帚”“鎬頭”“簸箕”“鍘草”等詞語,反映人民的生產生活情狀,增加細節的真實感。 同時,使用“瞅著”“光說”“招呼”“叫喚”“吱聲”等詞,生動傳達出農場民眾的日常生活狀態。 此外,小說還記錄東北民間的風俗習慣,描寫“我”和姐姐以及楊香玩抓“嘎拉哈”的游戲,用特有的日常游戲忠實反映東北民族的歷史文化。“嘎拉哈”又叫羊拐,是東北“舊十怪”之一,多見于婦女和孩童之間的游戲,代表著勇敢、財富和吉祥,是東北地域文化之一。 何凱旋運用質樸親切的黑土語言探索民間世界,小說的語言與故事呈現有機結合,更好地塑造文學意義上的民間空間。
《江山圖畫》的“土氣息、泥滋味”不僅體現在方言上,而且體現在在通俗化意象上。何凱旋在牢牢把握小說故事情景氛圍的基礎上, 圍繞故事的民間性特征選取農村常見的、 與農民息息相關的動物作為恰當的意象,渲染小說的民間意味,使小說兼具文學性與大眾化色彩。自在的魚、勤勞的牛、仁義的狗、柔順的馬等動物意象在小說中頻繁出現, 這些動物不僅以物的形式存在,而且具有人性化的特征,隱含內在深意。 魚的意象反復出現在男歡女愛的故事情節中,是男女愛情的象征與性關系的表現。在描寫三楊與鄭喜鳳的性愛時, 連用九次魚表現鄭喜鳳的情態和三楊的內心活動。 馬軍與“我”姐姐確定愛情關系時,送了姐姐一個魚形的耳墜作為禮物,當這段愛情走向崩潰后,魚也早已死在姐姐的兜里。牛與狗則在小說中高度擬人化,成為人性的象征。下雨天爹準備靠拖陷進泥里的油罐車趁機“打劫”時,特寫了雨中橫沖直撞的牛,將鐵鏈拽得嘩嘩響,然后寫道“爹也是這樣, 他身上的那種東西也在不斷地涌動不斷地沖撞,不斷地需要一種方式解脫”[3]。爹作為北大荒農民的代表,像頭牛一樣始終保持勤勞樸實、任勞任怨的秉性,但在雨水的刺激中,爹的內心欲望與野性一同爆發,這時的牛被賦予野性與力量象征意義。小說中的狗意象也是如此,映射出三楊的性格特征。在三楊媽媽死后,狗一直陪在她身邊,在下葬時也趴在棺材上面, 但在棺材快被埋住的最后一刻狗改變了主意,瘋狂逃離。 三楊因母親去世悲傷哭泣,一安葬好母親就與鄭喜鳳歡好, 狗的行為正好與三楊的表現相呼應。馬是整部小說的另一條線索,柔順的母馬則與楊香的處境和命運相關聯:馬懷孕,楊香也懷孕;馬因懷孕而不用下地,楊香因懷孕逃避勞作;母馬與楊香差不多同時生產, 一匹小馬出生, 一個孩子去世;最后,一匹母馬死亡,一個女人活著。通過設置馬這個意象,含蓄地預示楊香的悲劇命運,增強作品的感染力。 作品中烏鴉的意象也被賦予告知災難死亡來臨的能力,烘托悲涼的氛圍。
四、結語
《江山圖畫》真實再現了20 世紀90 年代東北農村的現實生活狀態,濃墨重彩的山村風景、通曉人性的動物牲畜、庸凡的人物群像、自由自在的生存狀態共同組成了這一方江山的圖畫。在這方極具包容性的民間大地,何凱旋以尊重的、客觀化的敘事立場,用平淡樸實的話語演繹著小人物的命運浮沉和生存哲學,肯定民間的價值與魅力。同時,何凱旋把質樸親切的黑土語言完美地融入小說之中,對民間日常生活等進行記錄描寫,形成極具黑土情懷、泥土氣息的美學風格,增強了小說的通俗感和藝術魅力。這種民間性特征是何凱旋一貫的創作風格,體現在他的多部作品中,《紅蒿白草——我的家園》演繹一個家庭三代人的命運與生存哲學,《三匹馬》展現民間小人物頑強的生存意志。 自在的生存狀態、客觀化的敘事立場、質樸親切的黑土語言構成獨具魅力的民間審美趣味,獨特的創作風格使何凱旋成為民間文學的一方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