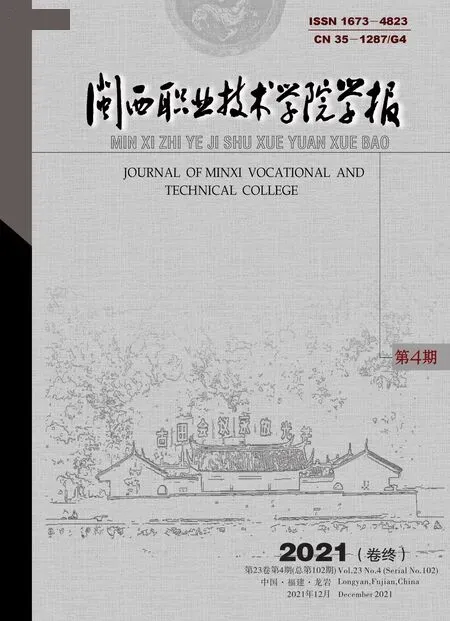承繼共同正犯責任范圍之消極說的建構
王 杰,馬嘉陽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刑事司法學院, 武漢 430070)
承繼的共同犯罪, 是指先行為人已經實施一部分犯罪實行行為,在實行行為尚未完全終了時,后行為人以共同犯罪的意思參與實行行為或者提供幫助。[1]承繼的共同正犯,則是指先行為人已經實施了一部分實行行為之后, 后行為人以共同實行的意思參與實行犯罪的情況[2]。對于承繼共同正犯的探討應當置于承繼的共同犯罪之下,并以共犯理論為依托。
如何認定承繼共同正犯的責任范圍是承繼共同正犯中關涉后行為人刑事責任承擔的重要問題。 其不僅是共同犯罪的理論問題, 也反映了一個國家在平衡人權保障與社會防衛過程中的價值取向, 對于公平正義的實現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前關于承繼共同正犯責任范圍的學說主要有積極說、 消極說和中間說。本文在共同犯罪基本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積極說、 消極說和中間說的觀點, 試圖立足于消極說,合理構建承繼共同正犯的責任范圍。
一、承繼共同正犯責任范圍的相關學說
在理論上, 關于承繼共同正犯的責任范圍主要存在三種不同的學說。
(一)積極說
積極說,也被稱為肯定說、積極利用說、完全承繼說等[3]。該說的代表性學者有西原春夫、福田平、貝林、威爾策爾等。 積極說認為,后行為人承繼先行為人的全部行為,對整個犯罪過程承擔責任。 換言之,對于后行為人未參加的,但由先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后行為人也要承擔責任。
積極說的觀點不僅違背了責任主義, 與現今普遍主張的因果共犯論相抵觸, 其也會加重對后行為人的處罰。 例如,甲已經實施了強奸的行為,乙中途得知情況后再加入,那么,如果肯定后行為人需要對先前的行為負責,那么甲、乙二人均應當按照輪奸處理。 然而,這樣解決的問題在于:后行為人加入實施之前,其僅對前行為造成的結果存在認識。如果因為具有認識就應當承擔責任, 則對于后行為人的處罰過重。
在肯定責任承擔的基礎上, 有學者認為應當在一定的限度內肯定承繼的觀點, 即所謂的限制肯定說。 該說內部又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是積極利用說;二是整體評價說。
1.積極利用說
積極利用說認為, 限于能認定后行為人積極利用了先行事實的場合, 才能認定存在為共同正犯性奠定基礎的相互利用相互補充之關系, 進而才能成立承繼的共同正犯[4]。 正如有學者所說,不能僅僅以利用的意思作為承繼的共犯的認定標準, 因為利用的意思只是后行為人主觀方面的表現, 其與動機很難區別開來。即使是在單純的一罪中,既可以說后行為人積極利用了先行為人的行為, 也可以說先行為人的行為只不過是后行為人犯罪的契機而已[5]。所以,“利用”行為并不能成為刑法譴責的對象。 行為人對先行為人造成的損害結果或者不法狀態沒有任何的過錯,僅僅是客觀上的“利用”而已。 換言之,先行為人造成的結果和純粹的自然力量造成的結果沒有什么區別。 例如,甲先將被害人打傷,乙與甲交談并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后,拿走被害人的錢包;被害人由于自然原因(或者自己跌倒)而陷入重傷,經過的路人A 拿走被害人的錢包。 上述兩種情形唯一的區別是前者的后行為人在主觀上知曉了先行為人已經造成的狀態。從行為的角度來看,后行為人都僅僅實施了拿走錢包的行為,因此,僅僅因為主觀上對于先行事實的認識就將先行行為的結果歸于后行為人,是與責任主義相違背的。
2.整體評價說
整體評價說認為, 當后行為人對先行為人造成的狀態加以利用時, 就可以將這種狀態融入后行為人的實行行為,并予以整體性評價。 例如,在搶劫的場合中,雖然被害人受傷的狀態并非后行為人所致,但如果后行為人拿走財物的行為是利用了前行為人制造的狀態, 那么就可以將壓制的狀態與拿走財物的行為進行整體性評價, 從而將后行為人的行為評價為搶劫罪。然而,這樣的解釋與前述的積極利用說沒有什么差異,其仍然對“利用”的意思進行了刑法意義上的苛責。
(二)中間說
中間說認為, 后行為人僅在一定的范圍內對先行為予以承繼。 典型的是在后行為人對先行為人已經造成的狀態加以利用時,就可以肯定承繼[3]。 該說的代表者有大冢仁、大谷實等。學界普遍支持以因果共犯論為基礎的消極說或中間說。中間說要求的“一定范圍內”指的是“后行為人將先行為人的行為作為實現該犯罪的手段加以利用”[3]。 這一學說仍然沒有徹底說明后行為人為何要對其利用行為承擔責任,甚至據此可以作出如此推論: 只要后行為人知悉先行為人已經造成的結果, 就應當對先行為承擔一定的責任。值得考慮的是,中間說和前述的積極利用說均強調后行為人的“利用”意思,這兩種表述不存在實質性的區別。
(三)消極說
消極說立足于因果共犯論, 認為后行為人僅對參與后的行為、結果以及因果關系承擔責任,對其參與前已經發生的行為不承擔任何責任。 該說的支持者有山口厚、曾根威彥、前田雅英、金德霍伊澤爾等[6-8]。根據德國主流學說,若有共同正犯在犯罪既遂之前承繼地參加進來, 不得將加入者進入前所實現的結果歸屬到后來的參加者身上。[8]在理論上還存在二分說[4],即區分共同正犯與承繼的幫助犯。 但是二分說否認所謂的承繼的共同正犯的概念, 而僅承認承繼的幫助。這樣的二分說是存在疑問的。正犯與幫助犯是犯罪參與形態的一種分類,可以說,正犯與幫助犯是相并列的概念。既然存在承繼的幫助犯,那么也應當存在承繼的正犯。從發揮作用的角度講,正犯在犯罪中的作用往往大于幫助犯, 既然作用較小的幫助都可以存在承繼, 為什么作用大的正犯就不能存在承繼?
本文贊成消極說的觀點,同時承認承繼的幫助,并且從法益質與量的變化上把握后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以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后行為人應當對基于因果關系實施的行為負責,但無需對前行為負責。不可否認的是, 在一些情形下后行為人確實利用了先行為人造成的狀態, 但是只有后行為人已經認識到損害結果的進一步惡化, 且該結果的惡化與后行為人的行為具有因果關系時才應當對此負責。
二、消極說的合理性論證
(一)契合共同犯罪的本質學說
在承繼的共同正犯中, 采取消極說的觀點能夠契合共同犯罪的本質學說。 關于共同犯罪的本質學說主要存在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其中,犯罪共同說又可以分為完全犯罪共同說和部分犯罪共同說。 當前,完全犯罪共同說已經被否定,部分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成為共同犯罪本質學說爭論的交點。 然而,不管采取哪種學說,就承繼共同正犯的判斷結果而言,應當是相同的。根據部分犯罪共同說的觀點,當不同的犯罪之間具有重合的性質時,在重合的范圍內能夠成立共同犯罪。 [9]在承繼的共同正犯中, 先行為人與后行為人重合的范圍是后行為人的參與部分。因此,后行為人也僅對其參與后的行為承擔責任。根據行為共同說的觀點,不要求具有共同的犯罪意思聯絡,而僅具有行為的共同性時,就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在承繼的共同正犯中,只要行為人之間在實行行為的部分具有共同性即可認定承繼共同正犯的成立。因此,后行為人僅在故意的范圍內對犯罪承擔責任。
(二)符合責任主義原則的要求
在承繼的共同正犯中, 采取消極說的觀點能夠符合責任主義原則的要求。“沒有責任就沒有犯罪…沒有故意與過失,即使造成了嚴重的法益侵害,也不可能成立犯罪”[10]一方面,消極說的觀點并不違反共同犯罪中“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原則。“部分實行全部責任” 的原則建立在具有犯罪意思聯絡的共同犯罪的基礎上,因此,行為人承擔的全部責任應限制在其參與后所造成的危害結果的范圍內。 例如,甲、乙兩人按照預定計劃共謀實施盜竊, 但甲并未在約定的時間前往犯罪現場, 最終由乙單獨完成了犯罪計劃。 在這一過程中,甲僅參與了共謀行為,但仍應對乙造成的結果負責。再如,甲、乙共謀實施搶劫,在搶劫行為完成后,乙對被害人實施強奸,甲應當對乙的結果負責。 上述兩種情形的共同特點在于被害人的損害均是由甲已經實施的行為造成的, 即使甲并未實施構成要件要求的實行行為, 但至少甲的行為為之提供了方便。在承繼共同正犯的場合中,后行為人對先行為人的行為僅是一種事后知曉, 而非事前預謀,從這一角度看,兩者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部分實行全部責任”與消極說并不矛盾。 另一方面,責任主義要求行為人具有責任能力、故意、過失與期待可能性,且僅能就行為人實施的行為予以非難。[2]在承繼的共同正犯中, 后行為人對先行為人及其造成的狀態僅具有主觀上的認識, 并不具有犯罪意義上的故意與過失, 因而并不能就前行為對后行為人予以刑法上的苛責。
(三)避免產生主觀歸罪的問題
在承繼的共同正犯中, 采取消極說的觀點能夠避免產生主觀歸罪的問題。 后行為人對于先行為的知悉,根據知悉時間的不同,可以分為事前知悉與事后知悉,兩者具有很大的差異。 事前知悉是“共謀”;而事后知悉并不構成共謀。換言之,即使后行為人在主觀方面具有可譴責性, 也僅能就其實施的行為負責。 例如,就搶劫行為而言,行為人如果參與事前的謀劃,其便為之后的犯罪實施作出了貢獻。 然而,就知悉本身這一主觀認識而言, 事后的知悉與一般民眾的知悉沒有任何區別,在承繼的場合中,后行為人的可譴責性在于后行為人在已經認識到了既有損害結果或者危險的情形下,進一步實施了危害行為。因此,真正應當受到譴責的不是知悉的主觀認識狀態,而是知悉后又實施的不法行為。 共同犯罪最重要的特點在于行為人之間存在雙向的意思聯絡, 并且在雙向意思聯絡下實施了實行行為。 但是在承繼的共同犯罪中, 先行為人與后行為人在犯罪開始時并不存在雙向的意思聯絡, 而是在犯罪行為已經實施了一部分后,才產生了雙向的意思聯絡,此后的行為才應當是二人共同應當負責的行為,或者說,后行為人加入后的過程才應當作為共同犯罪來看待。因此,如果僅僅因為后行為人在主觀方面的知悉就將先行為歸屬于后行為人,可能出現主觀歸罪的問題。而消極說將重點放在后行為人實施的參與行為上, 因而能夠避免出現主觀歸罪的問題。
三、承繼共同正犯責任范圍的建構
(一)承繼共同正犯責任范圍的理論建構
承繼共同正犯責任范圍的建構應當以法益保護為中心,根據被侵害法益數量,分析被侵害法益在后行為加入后是否惡化。在此前提下,應當堅持因果共犯論,如果行為和結果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那么不能僅因為后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犯罪故意, 在客觀上實施了加入行為, 就將不具有因果關系的結果也歸屬于后行為人。[11]詳言之,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承繼共同正犯責任的范圍進行建構。
首先,分析犯罪行為侵害的法益是否單一。任何一個侵害的法益都需要解釋,[12]被侵害法益是否單一的判斷應根據刑法規范的目的進行解釋。 如果是單一法益遭受侵害,后行為人加入犯罪后,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被侵害法益的量繼續增加;二是在自然因果流的推動下而侵害另一法益, 且該種法益的侵害在行為人的預料之內, 即侵害的法益發生了質的變化。第一種情況中,應當承認后行為與前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 因此后行為人不需要對前行為已經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 而僅需要對其加入后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在該種情況中,由于后行為人已經明確認識到先行為人已經實施的行為、造成的損害結果,其繼續參與實施實行行為并不會影響共同正犯的成立。第二種情況中,后行為人造成的另一種法益侵害與已經造成的法益侵害之間具有自然的因果流, 因此, 即使被侵害的法益發生了“質”的變化,后行為人也應當對這種結果承擔責任。與第一種情況相同的是, 后行為人無需對先行為人已經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
其次,若侵害的法益是多個法益,則需要考慮各個法益被侵害的先后順序。一般而言,數個被侵害的法益之間具有一定的先后順序,即使不存在,在分析時也可以根據犯罪行為的性質進行假定。 該種情況下,應首先分析被侵害的法益是否會發生“質”或者“量”的變化。這種“質”或者“量”的變化并非單純、抽象的判斷,而是看后行為人是否對其繼續施加作用。后行為人施加作用的效果具有兩種情況: 一是后行為人對最先遭受侵害的法益繼續施加侵害,那么,無論其是否親自實施侵害第二個法益、 第三個法益的行為……其都應當對之后的結果負責。 二是后行為人對已經發生的法益侵害不再施加任何影響, 僅僅是繼續實施尚未完成的法律規定的動作。 在該種情形下,后行為人與先行為人構成承繼的共同正犯,先行為人應當對整個犯罪負責, 因為整個犯罪的完成是在其參與下順利結束的; 后行為人僅對其施加影響的行為負責,所以單純評價其實施的行為即可。對于后行為人而言, 如果有相應的罪名則按照此罪名處理,若無相應的罪名,可以按照承繼的幫助處理,即按照幫助犯的處罰原則。
最后, 先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是否已經完成對于后行為人責任的承擔亦會產生影響。 犯罪行為是否已經完成,應當根據具體的犯罪情形來確定。 例如,搶劫罪的完成必須是實施暴力、 威脅或者其他手段取得財物,如果財物尚未取得,整個犯罪行為就沒有完成。在先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已經完成的場合中,對于后行為人的加入,不宜認定為共同正犯。根據后行為人在整個犯罪過程中所發揮的具體作用的大小,也只能認為是承繼的幫助犯,甚至不能認為是犯罪。因為整個犯罪已經完結, 如果將后行為人根本沒有起到任何實質性作用的加入行為作為共犯處罰,將會違反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 在先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尚未結束, 而后行為人加入被評價為共同正犯的情況下, 也并不意味著后行為人需要與先行為人承擔同等的責任。
(二)承繼共同正犯責任范圍的案例檢視
關于承繼共同正犯的責任范圍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的爭議。 日本大審院曾采取積極說的態度。 ①在2012 年日本的一判決中,對于承繼共同正犯責任范圍的態度發生了變化。②[3]對于該案,一審、二審法院均肯定后行為人對全部的損害結果承擔責任,但是最高裁判所依職權否定了這一決判決。 最高裁判所認為, 被告人的共謀以及基于共謀的行為與已經由A、B 等人造成的傷害結果之間不具有結果關系,不應當承擔傷害罪共同正犯的責任。 適當的理解是在被告人共謀參與后, 只有對被害人傷害結果的發生具有因果關系時,才負傷害罪共同正犯的責任。原判決認為被告人利用了先行為人制造的被害人難以逃走或者抵抗困難的狀態,以便自己實施暴行。但是即使存在這樣的事實, 被害人難以逃走或者抵抗困難的狀態只不過是被告人共謀參與后的動機或者說契機而已, 不能成為被告人對其共謀參與前的傷害結果負刑事責任的理由, 不影響上述關于傷害罪共同正犯成立范圍的判斷。[5]在上述案件的整個犯罪過程中,被害人僅有身體法益遭受損害,而這一法益的損害僅存在“量”的變化。因此,后行為人無需對已經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 即使后行為人認識到被害人不利狀況的存在,但正如上述判決所述,不能因為后行為人僅有犯罪的動機和契機就讓后行為人對前行為負責,這違反了責任主義原則。
但不可否認的是, 由于后行為人已經認識到了被害人的狀況, 后行為人對于其實施的進一步的侵害行為可能造成的損害后果當然應當承擔責任。 在此基礎上,當被侵害的法益發生了“質”的變化,行為和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時, 后行為人也應當對其行為負責,即對加重的結果承擔故意或過失的責任。有學者會對此提出反駁: 若先行為人將被害人非法拘禁22 個小時,后行為人以共犯意思加入后將被害人繼續非法拘禁2 小時, 后行為人難道無需對非法拘禁罪負責嗎? 再如,若先行為人已經盜竊了2 800元,后行為人以共犯意思加入后盜竊200 元,后行為人又是否構成盜竊罪?本文的觀點是,后行為人僅對其參與后的行為負責, 因而上述的后行為人僅對非法拘禁的2 個小時和盜竊的200 元負責。毫無疑問,二者都實施了實行行為, 均成立非法拘禁罪和盜竊罪的承繼的共同正犯, 但歸責問題應嚴格遵循責任主義原則,后行為人僅能對其實施的行為負責,即使先、 后行為人的行為合力導致被害人的法益受到了嚴重侵害,但這并不意味著無人對其負責,先行為人無疑要對整個犯罪過程負責。
對于侵害單一法益的情形不妨作以下設想:
案例一:甲對某住宅進行盜竊,盜竊過程中見好友乙從旁邊經過,甲向好友乙說明情況后,乙提出為其望風,最終甲順利盜竊財物2 萬元。
案例二:甲以傷害的故意對X 進行毆打,毆打一段時間后, 甲向好友乙說明情況, 二人一同毆打X,致使 X 重傷。
案例三:甲以傷害的故意對X 進行毆打,毆打一段時間后, 甲向好友乙說明情況, 二人一同毆打X,致使 X 死亡。
在案例一中, 共同正犯要求后行為人實施實行行為,但在該類情形下,乙并沒有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未支配犯罪事實,沒有以其行為造成被侵害法益“量”的加重或“質”的變化,因而乙成立的是承繼的幫助犯, 與先行為人構成盜竊罪的共同犯罪。 案例二中,乙中途加入,與甲一同對被害人進行毆打,造成被侵害法益“量”的加重。 由于X 的重傷與乙的毆打行為存在因果關系,故可以進行歸責,但這并不意味著乙要對甲的先行為負責。在案例三中,由于乙應當預見到其毆打行為可能造成X 的死亡,且傷害與死亡之間具有自然的因果流, 因而乙也需要對傷害致死的結果承擔責任。 后行為人在已經認識到的情況下繼續實施了侵害行為, 后行為人的行為并非單純的認識或者利用, 而是在認識到的基礎上實施侵害,其僅對之后的結果負責。
對于侵害單一法益的承繼共犯正犯可以這樣歸結:后行為人加入并實施犯罪的實行行為后,對其所造成的被侵害法益“量”的加重以及可能造成的“質”的變化,后行為人均應當承擔責任。 但是,當行為人的傷害行為與死亡結果不存在因果關系時, 則應當排除歸責,即僅對一般的傷害行為承擔責任。
較為復雜的是復合犯,復合犯的特點在于,犯罪的完成一般需要行為人先后完成兩個動作[13],并且侵犯不同的法益,例如搶劫、敲詐勒索、綁架等。
案例四: 甲以搶劫的故意致使被害人X 重傷后, 被害人倒地不起無法反抗, 甲向好友乙說明情況,乙以共犯的意思直接拿走財物3 000 元。
案例五: 甲以搶劫的故意致使被害人X 輕傷后,被害人仍在反抗,甲向好友乙說明情況,乙以共犯的意思與甲共同對被害人X 實施傷害后,乙直接拿走財物3 000 元。
案例六:甲以詐騙的故意使被害人X 產生錯誤認識,甲向好友乙說明情況,乙以共犯的意思獲得了X 的匯款 20 萬元。
在復合犯中, 主要問題在于當先行為人已經將一個行為實施完畢, 后行為人中途加入并對先行為人造成的狀態加以利用時, 如何確定后行為人的責任范圍。 在案例四中,甲已經造成了X 的重傷,在該種情況下,乙對之予以利用。由于乙并沒有對被害人的身體法益造成量的增加, 因而其僅對拿走財物的實行行為承擔責任, 在與甲的重合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即應當以盜竊罪論。 在案例五中,由于乙繼續對X 實施傷害行為,X 身體法益的受損存在量的增加,因而乙需要對傷害和拿走財物的行為負責,即成立搶劫的承繼的共同正犯,以搶劫罪論處。[14]在案例六中,甲的欺騙行為已經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被害人交付財物與甲得到財物的之間不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被害人交付財物是因為甲的欺騙,乙并未對之前的行為施加任何的作用, 因而乙僅成立詐騙罪的幫助犯,不宜以正犯論處。[15]
對于侵害多個法益的承繼共犯正犯可以這樣歸結:后行為人加入并實施犯罪的實行行為后,表面上看后行為人的確利用了先行為人已經造成的狀態,但僅僅對其行為繼續造成的“量”的加重以及可能造成的“質”的變化承擔責任。但是,當后行為人并沒有對已經被侵害的法益造成量的增加時, 則僅對由其實行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承擔責任。如前所述,承擔責任的根據并不在于之前的結果, 而在于后行為人在已經認識到之前的結果的情況下而繼續實施加害行為。 另外,還可能出現一種情形,即后行為人確實利用了先行為人造成的狀態, 但是并沒有造成被害法益量的增加而是侵犯了另一法益; 在另一法益沒有與之相對應的犯罪時,可以以幫助犯論處。
注釋:
① 大判昭和 13 年 1938 年 1 月 18 日刑集 17 卷 839 頁。
② 該案中,先行為人X、Y 在其他地方對被害人A、B 實施暴力之后, 又將被害人帶往另一地點并在途中將此事告知了 Z。 在到達另一地點后,X、Y 繼續對 A、B 實施暴力,而在Z 到達現場之前A、B 已經受傷。 Z 在到達本案現場之后,雖認識到A、B 因受到X、Y 的暴力而已經處于難以逃走或者抵抗的狀態,仍與X、Y 共謀并繼續對A、B 實施暴力,并且Z 在共謀參與之后實施的暴力比X、Y 此前實施的暴力強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