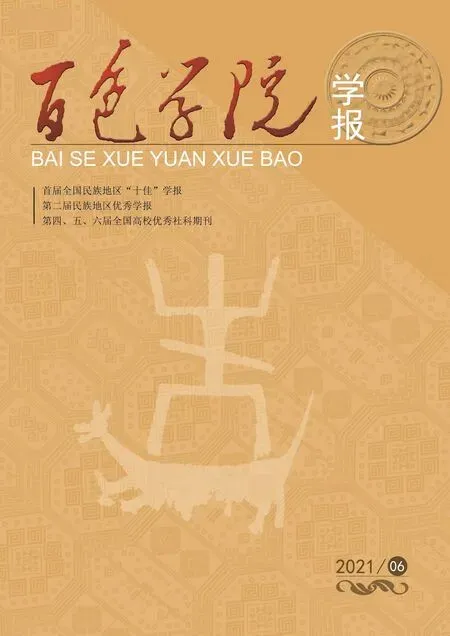八江語言路 濃濃古道情
——中國民族語言學家孫宏開先生之茶馬古道語言文化專訪
龍國貽(問),孫宏開(答)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081)
龍國貽:孫先生,您好!眾所周知,茶馬古道是我國歷史上內地和邊疆地區進行茶馬貿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線,歷經漢、晉、隋、唐、宋、元、明、清,不僅是中國西南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西部國際貿易古通道。您花費了很多時間精力,研究茶馬古道的語言和文化,成績斐然。現在很多學者對這些語言和文化都很感興趣,尤其北京大學的陳保亞先生更是給這條古道直接命名為“茶馬古道”,做了很多深入研究。
孫宏開:不僅陳保亞,還有孔江平等幾個人,他們在茶馬古道做了好長時間的調研,不僅做藏羌彝族走廊研究,還從云南出發、經成都、最后到西藏,實地走過這條線路,這也是茶馬古道中間的一段。我過去所說的茶馬古道主要還是指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民族走廊。有位領導把費孝通所提的藏彝走廊改成藏羌彝走廊,因為藏羌彝走廊中間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羌語支的問題。我在其中發現了幾種新的語言,除了原來的羌語、嘉絨語和普米語之外,又發現9種語言,并將西夏語文獻語言也納入其中。因為西夏實際上是黨項羌在唐宋期間從這一帶往寧夏、內蒙古額濟納旗遷徙的一個古老民族,后來在銀川成立了西夏王國,建國190多年。西夏王國在宋朝時期非常重要,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重要階段。實際上黨項就是羌語支的一個部落。當時李紹明的文章[1]之中就談到這一帶的部落有二三十個,現在留下來的語言有12種,這些人都歸入了藏族。
1978年以后,國家又展開了一次民族識別的大調查,期間一共發了4個文件,前面3個文件要求進一步做好民族識別工作。當時要求識別一批民族,但后來除了基諾族以外,沒有公布確定新的民族。費孝通1978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叫作《關于我國的民族識別問題》①費孝通1978年9月1日在全國政協民族組會議上發言,題為《關于我國的民族識別問題》,后刊登于《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文章第四部分講到,從甘肅的白馬經過康定往南一直到西藏的察隅、包括門巴、珞巴和僜人,當時要識別一大批民族的。黃光學和施聯朱出版過一本關于我國的民族識別問題的書,講了56個民族的來源。
龍國貽:您說的是《中國的民族識別》嗎?這本書2005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孫宏開:對,這本書有一個附錄,就是國家民委負責人答記者問。
龍國貽:費孝通先生講話稿的背景,您可以談談嗎?尤其是第四部分。您曾經提過,費先生文章前三個部分主要介紹20世紀50年代以來民族識別的遺留問題,核心思想都在第四部分。
孫宏開:當時國際上興起民族解放運動,成立了很多國家。那時中央主管民族工作的統戰部副部長江平有一個講話,談到亞非拉的民族要解放,我們國內也有很多民族要識別。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編纂5種叢書和大百科全書。這是費先生當時講話的大背景,在第四部分他就講到,從甘肅經過四川,以康定為中心,一直到藏南地區,包括察隅和僜人,有一大批民族要識別,很多連名字都確定了。我們這一代學者1976—1982年調查了好多新的語言,當時費先生認為有獨立語言的應該都是獨立民族。中印自衛反擊戰以后,周恩來總理宣布識別了門巴和珞巴。“文革”期間我們民族所做了很多工作,組織了西藏社會歷史考察隊,我們的語言組就去了察隅、墨脫、山南等地進行調查。當時就是有一個民族識別工作的大背景。現在你們想了解哪方面?
龍國貽:我們想請您談談語言方面的問題。
孫宏開:語言方面就是我們這一代學者當時做了大量調查,你看看我的《八江流域的藏緬語》[2],這本書是當時我調查的一個記錄,調查發現了很多羌語支語言,另外在西藏又發現了門巴、珞巴、僜巴講的達讓語、格曼語、義都語這些語言。藏南地區大概有十多個民族部落講獨立語言,如果把中印邊界的問題解決了,這些民族部落怎么辦,是否要進行民族識別?
龍國貽:在您看來,我們的民族識別,還有一些遺留問題需要妥善解決?
孫宏開:是的。黃光學和施聯朱的那本書雖然得了好幾個獎項,我印象中獲得國家民委的獎、國家社科基金的獎,等等。這本書后續還是有些問題,關于民族識別的遺留問題就寫了不少。
龍國貽:書中寫到的有些工作后來沒有動靜了?
孫宏開:后來都沒有做了。但是我們的語言識別工作一直在進行。我在香港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國家、民族、族群、語言——讀〈中國的“少數民族”知多少?中國的語言知多少?〉有感》[3],其中講到四者的差別,“國家”這個概念很明確,現在聯合國承認190多個國家。“民族”實際上是國家認定的一個族群單位,“族群”是自然形成的一個歷史的共同體,“族群”只要不被國家承認,就不能成為一個“民族”,反之,國家承認的就是“民族”。我們國家一直就是這種情況,通過這種方式來區別“民族”和“族群”。“語言”也是自然形成的,反而跟“族群”差不多可以劃等號。因為這涉及我國一個很重要的語文政策問題,所以我把這篇文章復印了好幾份,交給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的領導。具體到羌語支,還不僅僅是羌語支,比如到了瀾滄江就有柔若語,到了怒江有怒蘇語、阿儂語等等,再往西到了雅魯藏布江邊上語言就更多了。
龍國貽:您長期深入云貴川藏等地,在調查記錄30多種漢藏語系語言的基礎上,新發現了15種少數民族語言。能跟我們說說您在語言識別上的標準嗎?
孫宏開:學術上的語言識別跟國家層面的民族識別不太一樣,我們是根據語言事實來識別。一些族群所說的話,劃歸不到其他任何一個語言里去,那么就得承認它是一個獨立的語言。比如僜人所說的話,如果非要強行劃入藏語,那整個就亂套了。語言識別必須依據語言事實來判定,純粹從語言學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秉持科學精神,探尋語言事實。我的判定標準還是比較嚴格的,判斷一個新的語言還是非常謹慎的。比如,爾蘇語我劃分了3個方言。好些學者把這3個方言分作3個語言。爾蘇語3個方言差別的確非常大,互相不能通話,但是我們不能把互相能不能通話作為區分語言和方言的標準。有的語言不同方言之間就是不能通話,比如:藏語的3個方言之間就不能通話,羌語的12個土語之間也不能通話。按照美國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的標準,不能通話的都算作是獨立的語言,那怎么行呢?關于語言識別和民族識別的關系,我在《語言識別與民族》一文中談到中國語言的復雜情況,還談到語言識別的必要性,語言識別和民族識別的關系,以及語言識別的標準。[4]
龍國貽:是否能通話這樣的劃分語言標準實在太松,而且摻雜了很多主觀因素,相互是否能通話、是否能聽懂,這跟很多因素都有關系。您多次去怒江調查語言,能否跟我們談談有關情況?
孫宏開:我第一次去怒江調查是在1960年,最后一次去怒江是前幾年的語保工程調查,算起來前前后后在怒江一共調查了十幾次,那里所有的語言我都調查過,而且都是我識別出來的,這些獨立的語言已經是學界共識。每次去怒江都是有任務的,有的是國家分配的任務,有的是所里交代的任務,有的是在配合別人的研究任務,還有的是國外的課題需要調查,就這樣來來回回去了十幾次。你剛剛也說了,我花費了很多時間精力,研究茶馬古道的語言和文化。
茶馬古道的語言和文化的確很值得研究。茶馬古道最早是費孝通先生提出來的,大約是在1991年或者1992年,在民族文化宮開一個茶馬古道會議,那次我也去了。后來陳保亞開始研究茶馬古道,他過去插隊落戶到云南,后來考上云南大學,之后一路走到北京,所以他有情結,一直在認真研究茶馬古道。有一條古道,是從昆明往西,通過寶山騰沖到緬甸,一直到印度。還有一條古道,云南的茶葉往西藏運的時候走的那條古道,過去條件更加艱苦一點。陳保亞、木霽弘、孔江平等人開著車沿著這條路調查了一遍,還有一次王士元也被請到四川的羌族地區做茶馬古道的調查。他們有他們的研究視角,主要探討茶馬古道的歷史過程,陳保亞最早發現并且提出“茶馬古道”這個名字。
龍國貽:孫先生,您和陳保亞老師就茶馬古道的問題有過深入的交流嗎?
孫宏開:有一次我們一起在全國政協開會,他們想要沿著茶馬古道做一些考察,當時王延中所長、陳保亞和我都在,還有歷史所一個中青年專家。我發言之后,陳保亞就問我要手機號碼,說以后找時間一起聊聊。當時我就講茶馬古道上的一些敏感問題,因為當時全國政協提出來,他們可能更多地關心一些敏感問題。記得當時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民族識別和語言識別問題等,當時的會議是內部討論,我就把我的研究成果都說出來,供全國政協參考。
有幾篇文章建議你們去看看,比如《再論西南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及其相關問題》[5]一文,起初刊登在四川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上,后來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語言學科和民族學科兩個學科從不同角度都轉載了。我這篇文章就講到費孝通關于民族識別問題,后來他的觀念變化可能有一個歷史過程,文章里有些問題我沒有寫得太直白,有些問題涉及那個歷史時期個別機構和個人的不當做法,類似文章我寫過幾篇。
龍國貽:還有一個問題,復旦金力團隊在《自然》雜志發表《語言譜系證據支持漢藏語系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起源于中國北方》之后在語言學界反響很大,您曾經跟我提過,這篇文章意義重大。關于漢藏分化的時間和歷史背景,您早些年就一直在關注,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觀點,有些零碎的論述散落在早年的文章和著述中。您能具體談談嗎?
孫宏開:是的。我一直想弄清楚,漢和藏緬分化的時間和歷史背景,這個問題我還沒有專門發文章討論,但是觀點很早就已經形成了。最早羌和漢還沒有分化開來,《史記·本紀》中記載“禹興于西羌”①“禹興西羌”是目前學術界呼聲最高的觀點。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禹興于西羌”是能追溯到的最早文獻記載。南朝·宋裴《集解》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語:“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西羌’是也。”唐代學者張守節《正義》解釋說:“禹生于茂州汶川縣,本冉駹國,皆西羌。”。如果夏禹真是羌人,那就說明當時漢族可能是被羌人統治,在夏朝之前也許羌人很厲害,統治著中原。但是到商朝的時候,漢人就成了統治階級。甲骨文中講到羌人被俘虜以后當奴隸,甚至于陪葬,說明那時候的羌人已經是被統治階級。再到周朝和秦朝,羌人的地位更進一步下降。秦朝把羌人往西趕到山里頭去,那些羌人就四處逃竄,那時候漢族在中原就占有絕對統治地位了。
我一直在思考和考察這個過程,但是這個話一直沒有直接說出來。我之所以要到甘肅多次參加馬家窯文化考察,他們從馬家窯文化往南遷徙,一直到四川、云南,甚至西藏,這些問題我一直在考察,但是現在身體條件不允許再深入研究下去。
龍國貽:這一段沒有任何證據,只是一種猜想。漢人和苗瑤的關系,也值得研究。
孫宏開:你仔細看看翁獨健的《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6],這本書談到這些問題。我有篇文章發表在《暨南大學學報》[7],就講到苗瑤的祖先、侗臺的祖先、漢人的祖先可能分化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寫過一些這方面的文章,原本想把這類文章結集出版,從歷史考古、甚至包括古代傳說、再到語言學的研究,梳理整個漢藏內部的關系。但現在已經沒有精力去做了。2019年王志安在北京搞彩陶展覽,問我能不能去?我說我現在病了去不了了。
龍國貽:您這一病,很多研究擱置下來,實在太遺憾了。我印象中王志安是畫家、書法家,還專門研究馬家窯文化。我看過他寫的《馬家窯彩陶文化探源》和《馬家窯彩陶紋飾破譯》等著作。
孫宏開:他還主編了一個刊物《馬家窯文化源流》,我曾經兩次參加他們在嘉峪關組織的學術會議。甘肅的辛店文化彩陶、馬家窯文化彩陶,創造者都是羌人。這部分羌人后來往南遷建立了秦朝,再往南遷就形成了現在說羌語支語言的許多部落,更進一步往南遷就形成了印度尼泊爾的藏緬語族語言的一些族群,我在《再論西南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中都有論述,那是一篇2萬多字的長文。
我還寫過一篇文章登在《西北民族研究》[8],講絲綢之路上的語言接觸和文化擴散。那還是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當時我就感覺到甘肅是一個節點,可能一部分羌人從甘肅往西翻山越嶺到西藏定居,后來成為藏族。藏族的形成實際很晚,唐代才逐漸發展起來。四川西部的族群,比如黨項之類都早于藏,松贊干布統一西藏的時候,這些族群已經在四川定居很久了,這些都有歷史記載。李紹明的《唐代西山諸羌考略》就提到20多個羌的部落:東女、黨項、嘉良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羌”人等。但是這些部落跟現在羌語支多數都對不上,只有少數能對得上。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羌”人——基于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的視角》[9]發表在一個學報上。很多文章都是正好趕上人家約稿,我就給了對方。
龍國貽:好幾年前,有一次到您家中拜訪,您說過自己中年時期的工作狀態,基于對漢藏語長期深入的調查研究,有太多的思想和內容要討論,以至于您最多產的時候一兩個星期就寫出一篇大文章。正是因為您成果很多、約稿太多又年代久遠,導致您很多重要文章很難找到。您的《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10]國內知道和參考的人不多,但是在國外影響很大,據說有日本學者坐飛機到中國來買刊發這篇文章的雜志,西田龍雄和馬蒂索夫都曾經引用這篇文章。
孫宏開:小龍,我正好有一個重要的學術思想跟你討論,本來是想專門寫成一篇文章,現在身體情況不允許了。我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在西南地區從事藏緬語族語言調查的經歷,使我形成了一個學術思想,是關于中國八江流域藏緬語的分布問題。這個學術思想集中體現在我的專著《八江流域的藏緬語》中,這本書被列入社科院的學部委員文集叢書,原本他們想要整理我的論文結集出版。你說的那篇國外學者專程來找的文章是我1983年發表的,文章很長,原文大概有二十六七萬字,后來拓展整理成42萬字的專著《八江流域的藏緬語》。1983年那篇文章的確很重要。實際上費孝通先生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的《關于我國的民族識別問題》,文中主體思想是根據我這篇長文章的學術思想來的。
龍國貽:這個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費孝通先生文中也沒有提過,您能詳細說說嗎?
孫宏開:《再論西南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中,我也講到跟費孝通先生的關系。我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語言識別工作緊密結合,那段時間剛剛調查了白馬語和羌語支語言,1976年到西藏去做門巴、珞巴、僜巴調查的時候,費孝通先生還沒有恢復研究工作。“文革”時期,我經常去所里①“所里”的“所”指的是孫宏開和費孝通當時所在的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常常能見到費先生。那段時間我跟費孝通先生這些資深的民族學家的關系比較密切,他那時還是我們民族所的副所長。
1976年我正好去西藏調查察隅、門隅、珞隅、達旺的語言,發現了好多新的語言,后來1978年又受四川民族研究所和四川民委的邀請參加白馬的民族識別工作,后又受邀參加西番的民族識別工作,并調查他們的語言。費先生經常來我這里了解這方面的消息,聽說這些以后他非常高興,后來他寫了那篇發言稿,文中的第四部分那段話就談到,以康定為中心,向北到甘肅的白馬地區,向南到印度邊境的察隅地區,有一條民族走廊。這條民族走廊他后來命名為藏彝走廊,也就是現在的藏羌彝走廊,實際上是藏緬語族,主要是羌語支語言分布的地區:西藏的全部、四川的西部、云南的西北部和甘肅的南部。這條走廊實際上就是藏緬語的分布。費先生在全國政協作報告的時候,有那篇文章的油印稿,他當即就送給我了。油印稿有一個腳注,說明這篇文章的材料來自于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學的一些年輕科研人員調查回來跟他講的一些情況,后來文章正式在《中國社會科學》刊發的時候,這個注腳取消掉了,所以也就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油印稿我一直存在家里。
龍國貽:據我所知,您1956年就開始在這個地區進行調查,“文革”時期也基本沒有間斷,是否可以認為《八江流域的藏緬語》反映了您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后期調查的整個過程?這本書還被評為中國社科院老干局的優秀成果二等獎。
孫宏開:我原來寫了“六江”流域的文章,后來改寫為“八江”流域的文章,原來是想要把它們整理成文集的,后來各種原因就寫成了這本專著。剛剛跟你說了,我有個重要的學術思想要討論,也是一個基本的學說:整個藏緬語族語言是在4000多年前形成了以后向南遷徙的。
《再論西南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中,我把藏緬語族語言分為10個語支:藏語支、喜馬拉雅語支、那嘎-波多語支、庫基-欽語支、米佐語支、克倫語支、緬語支、彝語支、景頗語支、羌語支,其中5個語支分布在中國,5個語支分布在喜馬拉雅南麓。大部分在印度和緬甸接壤的山區,尤其是緬甸,整個緬甸大部分是藏緬語族語言,尤以緬語支語言居多;一部分在喜馬拉雅南麓雅魯藏布江下游印度境內的恒河流域。整個藏緬語原來在中國,從古氐羌分化出去,它的遷徙路線有多條,整個藏羌彝走廊就是往緬甸、印度遷徙。在中國,有幾十種藏緬語族語言,后來有人說印度有100多個藏緬語族語言,對于印度有100多個藏緬語族語言這個數據,我持保留態度,甚至還有美國學者提出印度有好幾百個語言,實際沒有那么多。這個遷徙是陸陸續續在進行,現在藏緬語的分布就是在八江流域,也就是整個橫斷山脈。橫斷山脈跟河流之間有許多縱橫交錯的馬道,不同歷史時期都有很多文獻記載,過去的交通運輸、商品交換、漢武帝開發西南等等,我最近一段時間一直在看不同時期的相關文獻,但很難將這個思想匯總成一個文件給你。
最近我看到一些文章提到甘肅南部也就是隴南地區到四川的通道,這個是北邊的茶馬古道。它實際是商品交換的一種道路,當然這種商品交換不僅限于茶和馬,還有絲綢等其他一些商品,這種商品交換是歷史上形成的。我發現:從甘肅南部的白馬語(包括藏語),到四川羌族的語言,再往南羌語支的12種語言①羌語支語言全部分布在我國境內,包括12種現行語言和一種文獻語言(西夏語),其中木雅語古稱“彌藥”語,爾龔語又叫道孚語、扎語又叫扎壩或扎巴語,貴瓊語又叫魚通語,爾蘇語又叫栗蘇語或多續語。羌語支本身可以分為北支和南支,前者受藏語支的影響大,后者受彝語支的影響大。有些學者認為嘉絨語應屬藏語支,還有些學者認為西夏語應屬彝語支。(包括羌語、普米語、木雅語、嘉絨語、爾龔語、扎語、卻隅語、貴瓊語、爾蘇語、納木依語、史興語、拉烏戎語,分布在甘孜、阿壩、涼山和云南的麗江地區),然后一直到云南怒江的語言,這條線路就是一條民族走廊。
龍國貽:簡言之,藏羌彝走廊實際就講羌語支語言,然后從中國內地逐漸遷徙到喜馬拉雅南麓的9個國家,即尼泊爾、不丹、印度、緬甸、泰國、孟加拉、老撾、越南和巴基斯坦。這些藏緬語族語言有哪些共性?
孫宏開:他們的共性主要體現在同源詞和語法范疇上。藏緬語族語言有一批同源詞,幾乎都是核心詞,數量不好說。馬提索夫整理出來好幾百個同源詞,其中二三百同源詞我可以確定,這些同源詞語音上有對應關系,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藏緬語族語言還有一些共同的語法范疇。原始藏緬語有很多重要的語法現象,特別是形態變化,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文章中都討論過,比如《我國部分藏緬語中名詞的人稱領屬范疇》[11]《我國藏緬語動詞的人稱范疇》[12]《藏緬語動詞的互動范疇》[13]《論藏緬語中動詞的命令式》[14]《論藏緬語語法結構類型的歷史演變》[15]《論藏緬語動詞的使動語法范疇》[16],漢語也有動詞的使動范疇,王力先生的同源詞族就提到這個問題。討論藏緬語語法范疇的文章,那時候我陸續寫了十幾篇,還涉及量詞問題、語法范疇的簡化問題,等等。當年論證這些語法范疇,主要還是研究國內的藏緬語,后來才陸續搜集到國外的藏緬語材料。另外,藏緬語族語言的語音系統方面雖然差距較大,但它們音系格局的一致性和演變脈絡也是非常清晰的。
龍國貽:孫先生,關于茶馬古道這個概念,大家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樣。您能簡單說說嗎?
孫宏開: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到茶馬古道,僅僅是指到西藏的茶葉交換這條線路,這個觀點跟陳保亞等先生的看法類似。所以,他們多次從云南沿著川藏走廊去考察,一路上也做了記錄、拍了很多照片。在我看來,整個西南地區就是所謂的茶馬古道。我剛剛為什么要說這條走廊呢?實際上就是整個藏緬語族語言從甘青向南遷徙到四川、云南,再由云南的西部騰沖那一帶到西藏、到緬甸,再從緬甸的曼德勒到印度、到喜馬拉雅山脈。當然,另外還有一些走廊可能是從新疆往南遷徙、從西藏往南遷徙,遷徙的路線就是八江流域,也就是橫斷山脈中間的那八條江。最東邊是白龍江(嘉陵江上游),再往西就是岷江,再往西是大渡河,大渡河往西就到了金沙江的上游(我調查的像云南和四川的木里地區,一些藏緬語族語言就是羌語支語言都在這一段古道上),再往西就到了瀾滄江,再往西就到了怒江,再往西就到了雅魯藏布江。所謂的八江就是八條江,我那本《八江流域的藏緬語》實際就是調查八江流域語言的一個記錄過程。岷江往東南能到古城文縣,還有一條陰平古道,是三國時期的鄧艾將軍開辟的,從甘肅文縣一直到四川平武縣。①《三國志》記載:三國時,司馬昭命鐘會、鄧艾領兵伐蜀。被蜀漢大將姜維堵在劍門關以北,久攻不下,鄧艾則回軍景谷道,到達陰平郡,走數百里險要小道,到達江油關,蜀漢守將馬邈開關投降。鄧艾軍長驅南下,攻克綿竹,直抵成都。蜀后主劉禪投降,滅了蜀國。從此留下了陰平古道的歷史遺跡。陰平古道起于陰平郡,即今甘肅隴南文縣的鵠衣壩(文縣老城所在地),途徑文縣縣城,翻越青川縣境的摩天嶺,經唐家河、陰平山、馬轉關、靖軍山,到達平武縣的江油關(今南壩鎮),全長265公里。
龍國貽:這個學術記錄很重要,國內好像沒有人具體做。
孫宏開:這樣的學術記錄都沒有人去做。所里的創新工程課題研究茶馬古道,由于各種條件限制,可能沒有辦法做大量實際的民族調查和語言調查。詳細的調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從學術生涯開始,1956年做藏緬語族語言調查的時候算起,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最后田野調查基本上結束,之后也就很少再做具體語言的記錄了,有的時候就是走馬觀花看一看。實際上我整個學術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就放在了藏緬語族語言的實地調查,最后整理成《八江流域的藏緬語》,它實際上是一個田野調查記錄,幾十年的記錄形成的一本書。有些語言的概況在別的地方發表了,比如:獨龍語簡志,怒語簡志,門巴、珞巴、僜巴的調查,這些我就沒有收到這本書里去,如果都要收入的話,篇幅就更長了。
龍國貽:所以說,費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是從地域這個角度來看,您的八江流域是從河流這個角度來看,陳保亞先生的茶馬古道是從交通這個角度來看。
孫宏開:對,就是這個意思,算是一個概括吧。其實也可以從山脈這個角度來看,那就是橫斷山脈。我說的八江流域,江的兩邊總是要有路,否則人們無法行走、無法通行,那八江是指大江,中間還有縱橫交錯的很多小的支流。我的文章中都有具體的描述,比如說,獨龍江就是恩梅開江、邁立開江的一個支流,到下游就是怒江下游。印度的恒河流域分布著大量的藏緬語,實際上就是雅魯藏布江的下游,所以《八江流域的藏緬語》就是講藏緬語族語言的分布及其由北向南遷徙,一直到印度、孟加拉國。這個遷徙過程,綿延了幾千年,一直到西夏還在北遷、蒙古還在南征,所以整個過程包括了人類遷徙、商品交換、甚至于發生戰爭等各種過程。
龍國貽:孫先生,以您目前的身體情況,您還堅持這么長時間講述茶馬古道的概念、語言識別和民族識別、漢藏分化的時間和歷史背景、藏緬族群的分布形成和遷徙等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不僅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非凡,而且這樣的治學精神也鼓舞鞭策著我們不負韶華、不懈奮斗,沿著先生們開拓的道路努力前行。八江流域的語言和文化讓您傾注了幾十年的心血,茶馬古道不僅是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更是您的治學坦途。關于漢藏語尤其是藏緬語,我們還有太多的問題要向您請教,后續還要請您做一部基于語言學研究的口述史。非常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