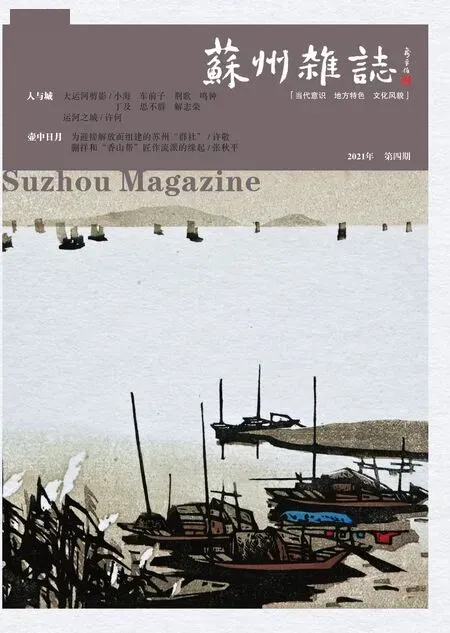一方風(fēng)物
王茵芬
場(chǎng)院
往日村莊里家家戶(hù)戶(hù)有場(chǎng)院,用青磚鋪就,像一方厚實(shí)粗糙的老土布,在日常里接納各種生命,鳥(niǎo)飛上去,陽(yáng)光在它的翅膀上追逐,土布不再是塊土布,變成一張金屬唱片。麥子熟了,稻子黃了,場(chǎng)院堆滿(mǎn)糧食和柴草;秋收時(shí)節(jié),黃豆、玉米、芝麻、高粱等農(nóng)作物都會(huì)陸續(xù)來(lái)訪;冬來(lái),腌制咸菜和蘿卜干的光景,場(chǎng)院最起碼被它們占據(jù)幾個(gè)日頭,接著是芒草、枯枝落葉等柴禾的天地。
有關(guān)場(chǎng)院的記憶早已繞成一個(gè)線團(tuán),一旦拉出線頭,就會(huì)越拽越長(zhǎng),顏色泛著麥秸的黃和青苔的蒼綠。那些散落的時(shí)間,失散的親人,遺忘的事件和物件,全都爭(zhēng)先恐后地趕上來(lái),與我重逢。
我的奶奶永遠(yuǎn)住在這個(gè)記憶的線團(tuán)里。常出現(xiàn)的場(chǎng)景是在阡陌縱橫的田野上,奶奶拄著楝木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在我的前面,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通往小鎮(zhèn)。奶奶在一個(gè)針織廠里做搖線工,我在小學(xué)讀書(shū)。
偶爾,奶奶帶我去娘家看望她的母親。奶奶屁股一側(cè)的骨頭生了東西,動(dòng)過(guò)兩次手術(shù),一條腿走久后會(huì)隱隱酸痛。我們便在路過(guò)的人家場(chǎng)院邊歇腳,找一塊石板坐下。那是個(gè)夏日傍晚,場(chǎng)院上曬著一地欲黃未黃的草。我知道,這些草曬干后,就要用稻柴捆成一個(gè)個(gè)草干團(tuán),藏在茅舍里,是給羊儲(chǔ)備過(guò)冬的糧草。一個(gè)大男孩在不緊不慢地收攏著場(chǎng)院上的干草。男孩朝我們看過(guò)來(lái),他的眼睛很大,在夕陽(yáng)里,目光尤其干凈明亮。我和奶奶的身上披了一層余暉,相互依偎。一場(chǎng)草,被男孩堆在一起,它們被男孩的手輕輕地摩挲著,就像奶奶的手撫摸著我的頭發(fā)。就這樣,我們坐在暖色里。
奶奶的母親,我叫她老太太,八十多歲,滿(mǎn)頭銀發(fā)向后梳成一個(gè)髻,一張滿(mǎn)是皺褶的臉,有點(diǎn)扁,牙齒落光了,嘴癟癟的。每到臘月,老太太會(huì)來(lái)我家住個(gè)十來(lái)天。奶奶總慢篤篤地說(shuō),老太太不是來(lái)吃閑飯的,好多活等著她做呢。
老太太像我家的一張被屁股磨得光滑柔順的草繩板凳,樸素憨厚,默不作聲。和她說(shuō)話,大多時(shí)候報(bào)以微笑。想不起來(lái)她和我說(shuō)過(guò)幾句話。記得那年夏天,人們都在為可能發(fā)生的地震做準(zhǔn)備。老太太特地到我們家來(lái),和奶奶一起做麥面餅。麥面餅是用面粉做的,有咸的,有甜的,薄薄的,圓圓的,一張張貼在鐵鍋上烙,烙到外皮有點(diǎn)焦黃,硬中帶松脆。按往常,餅子烙得少,菜油自然多些,麥餅更香。這次的餅太多,只在鍋壁上抹上一薄層油。待餅子烙熟后,用夾子夾起來(lái),放進(jìn)竹匾里攤開(kāi),等它們涼了,裝進(jìn)一只大壇子里,用麥秸編的蓋子,蓋嚴(yán)實(shí),再包上塑料薄膜。說(shuō)是一旦發(fā)生地震,沒(méi)啥吃,就可以啃麥面餅。當(dāng)然,還得儲(chǔ)存井水,把井水灌在塑料桶或甕內(nèi)。我父親把壇子和水甕分別搬到場(chǎng)院上的草棚里,草棚是臨時(shí)搭建的,原本是生產(chǎn)隊(duì)的瓜棚。我當(dāng)時(shí)總喜歡跟在大人身后,感覺(jué)很有趣,忘記了地震的可怖。老太太在磚場(chǎng)上,安詳?shù)刈谀菑埐堇K板凳上折疊麥秸草把。她微笑著和我說(shuō),晚上住草棚里吧,床上張了蚊帳。我學(xué)她平和的模樣,慢慢地?fù)u頭,其實(shí)是怕夜晚會(huì)不會(huì)有蛇游進(jìn)去。
那次的地震警報(bào)持續(xù)了大約半個(gè)月。直到有天深夜打雷刮風(fēng)下暴雨,感覺(jué)到房屋有點(diǎn)晃動(dòng),但沒(méi)出現(xiàn)倒塌事故,大家的心才安定下來(lái)。那會(huì)兒,老太太和奶奶一直住草棚,母女難得有這么長(zhǎng)時(shí)間生活在一起,每天都樂(lè)呵呵的,真有點(diǎn)因禍得福。
到了這年仲秋,母親把我養(yǎng)的一只老湖羊牽到場(chǎng)院中間,讓它臥在一塊草席上,準(zhǔn)備剪羊毛。那天的陽(yáng)光特別干凈耀眼,照得老湖羊懶洋洋地閉上了眼,母親把一只布袋套在它的頭上。她利索地使用著剪刀,有順序地從羊肚開(kāi)始剪,“咔擦咔擦”,動(dòng)作慢騰騰的,生怕刀尖劃破羊的皮肉,把白凈的羊毛順手堆放在草席上。當(dāng)時(shí),我只覺(jué)得那一地羊毛仿佛一堆麥秸在燃燒,整個(gè)場(chǎng)院被映得黃燦燦的,宛如一塊巨大的面包。
場(chǎng)院,讓我看見(jiàn)了生命的接納和孕育。
菜地
場(chǎng)院前的一塊菜地,被父母侍弄了大半生,是他們多年的“菜籃子”。父母各有分工,父親干的是體力活,翻地、澆水、施肥、除蟲(chóng)、搭棚,母親的活輕一點(diǎn),播種、栽苗、除草、摘菜。
當(dāng)山芋藤活潑潑滿(mǎn)地跑時(shí),雜草也不甘示弱,瘋長(zhǎng)著,母親頭戴遮陽(yáng)帽,穿一身花花綠綠的衣服,蹲在一片濃綠里。她的背越來(lái)越駝了。那些野草有的注定開(kāi)出花來(lái),有的照例結(jié)籽。陽(yáng)光一寸一寸踩過(guò)山芋藤蔓,土里的山芋在長(zhǎng)個(gè)兒。母親的影子在這片菜地上移動(dòng),像一個(gè)“瓜”字。
記得那次回家,母親悄悄把我叫到房間,從舊木箱底下摸出一個(gè)布包,這塊布是二十多年前我買(mǎi)給她的一方手帕。給過(guò)她皮夾的,她嫌用起來(lái)麻煩。打開(kāi)手帕,幾張不同面值的鈔票,最多三四百元錢(qián)。她把一張五十元的鈔票塞進(jìn)我手里,讓我買(mǎi)一只收音機(jī),說(shuō)是去菜地里帶在身邊,聽(tīng)聽(tīng)老戲。我看著母親的憨樣,忍不住笑了,把錢(qián)還給她。今天,母親又拿出二十元錢(qián),要買(mǎi)一條絲巾,秋天了,外面的風(fēng)太涼。我每年買(mǎi)圍巾給她的,它們都被她遺忘在哪個(gè)角落了。以前的事,她記得特別清楚,總記不得當(dāng)下的事。
母親十多年前得過(guò)抑郁癥,現(xiàn)在時(shí)而清醒,時(shí)而糊涂。她幾乎每天把自己的幾雙鞋子抱出來(lái)曬太陽(yáng)。她忘記自己老了。這樣也好。
母親把雜草曬在家門(mén)前的場(chǎng)地上。我喜歡青草被陽(yáng)光踩過(guò)后散發(fā)出的香味,俯身嗅著,想起母親以前常說(shuō)的一句話,人,有時(shí)候還不如一棵草。
場(chǎng)院西邊搭著一架絲瓜棚。秋陽(yáng)下,葉子顯得蒼老,一些花朵卻開(kāi)得有力,綠蔭里的小絲瓜在長(zhǎng),長(zhǎng)不大,就要老的,老在深秋里。
菜地里多了一棵木蘭樹(shù)。如果沒(méi)有躲在椏杈間的鳥(niǎo)窩引起我的注意,或許不會(huì)在意一棵葉子泛黃的樹(shù)。未曾見(jiàn)過(guò)這棵樹(shù)開(kāi)花的樣子。它筆挺地站在那里,主干修長(zhǎng),枝條疏朗。母親告訴我,三年前的早春,父親去小鎮(zhèn)路上,發(fā)現(xiàn)這棵樹(shù)歪倒在廢墟里。原本瘦弱的它遭遇硬物撞擊,并擠壓,根部幾乎裸露,是主人遺棄了它,抑或無(wú)處安置它,不得而知。父親彎下僵硬的腰,扶起它,抱在懷里。他像收養(yǎng)一個(gè)受傷的棄兒,將樹(shù)種在菜地,用木棍和繩子固定主干,好讓它挺直了往上生長(zhǎng)。
泥土的氣息喚醒了木蘭樹(shù)。它身上的傷痛被沃土治愈,在父親期望的目光里一個(gè)勁地長(zhǎng)高,長(zhǎng)大。
鳥(niǎo)窩非常精致。這該是哪種鳥(niǎo)安的家?聽(tīng)父親說(shuō),有靈性的鳥(niǎo)喜與人親近、共處,把窩搭在家門(mén)前向陽(yáng)的樹(shù)上,這也說(shuō)明家園的風(fēng)水好。
菜地不大,一棵樹(shù)的生命卻是這般遼闊,可以讓鳥(niǎo)兒棲息,搭窩,繁衍生息。
父親拎著一把鐵鍬走上來(lái),說(shuō),掘幾個(gè)蘿卜給我。他步子遲緩,腰明顯彎了。內(nèi)心不禁一陣酸楚,這些年,我忽略的僅僅是一棵樹(shù)嗎?一時(shí)無(wú)語(yǔ),連“哦”這個(gè)字也哽在喉嚨里了。自然的秩序,這樣了然,頓生惆悵之意。
幾十年來(lái),父母種了一茬又一茬的蔬菜,菜地依然年輕,而他們老了,“老得像一個(gè)影子”。
河灘小徑
菜地邊的河灘小徑,窄而短,兩根扁擔(dān)的長(zhǎng)度,我走了半生。
一個(gè)盛夏的午間,來(lái)到小徑,和兩旁雜草歡喜相逢。首先和我打招呼的益母草,有點(diǎn)清瘦,穿著紫紅碎花袍子;一個(gè)少年般的大葉紫蘇微笑著,站在幾個(gè)頑皮的車(chē)前草身旁;一群蓼草向我舞動(dòng)起柔姿,串串粉紅花穗像姑娘的辮子;刺莧和蒲公英在風(fēng)中歌唱;馬齒莧有點(diǎn)害羞,露著半邊臉;艾草在稍遠(yuǎn)的河岸,像少年的伙伴們,天真無(wú)邪,走向青春。
河灘頭的梔子花開(kāi)得靜美,花不再是那時(shí)的花。當(dāng)年的我在河邊蹲著,水里搖搖晃晃的影子有點(diǎn)瘦弱,像岸上那棵結(jié)著青毛桃的小桃樹(shù),在貧瘠的土地上成長(zhǎng)。河灘石長(zhǎng)得難看,也就四五級(jí),蹲著的一塊平實(shí)多了,下面還有一塊長(zhǎng)著青苔,靜靜地臥在河里。一群小魚(yú)游了過(guò)來(lái),我試圖赤腳踏進(jìn)下面的石板,“啪”一屁股跌坐在上面的石上,嚇得縮成一團(tuán),不敢哭,只能坐著,坐在疼痛里,等自己長(zhǎng)大。
兩岸的各種樹(shù)們長(zhǎng)得茂密,如同一個(gè)綠棚,搭在原本很窄的河面上。河灘的風(fēng)清涼里夾著些許水腥味。岸邊老楓楊樹(shù)上鳥(niǎo)鳴和夏蟬叫得歡。東南風(fēng)吹著樹(shù)下的草花,一年蓬野性十足,卻又不失窈窕,而一種頂著紫色花冠的馬刺薊草顯得拙樸,它們本來(lái)是被風(fēng)播撒在這一帶的,和從前鄉(xiāng)間女孩一樣,土氣中透出清秀,自然生長(zhǎng)著。每種植物都是有名字的,它們的形狀、色彩、味道和品質(zhì)都包含在名字里。
忽而,一只白鷺飛過(guò),被風(fēng)追趕著,停歇在合歡樹(shù)的枝頭,合歡花紛紛飄落,鋪在淺綠色的水波上,像一塊花布,散發(fā)出絲絲縷縷的香氣,隨之而來(lái)的,是靜謐和安寧。生命延續(xù)繁殖,滋濡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往往有著治愈人心的力量。
就這么一條小徑,依然為我保留著塵世的純真和素樸。或許,這是屬于父母輩和我這樣一代人的一種草木情懷了。
父親拿著一把鐮刀走上來(lái),要割些樸樹(shù)的枝葉,問(wèn)及何用,父親心事重重的樣子,說(shuō)話聲很低,你大伯想趁活著聞聞家鄉(xiāng)的味道。
幾年前,八十多歲的大伯中風(fēng)癱瘓了。他幼年父母因病雙亡,由我奶奶撫養(yǎng),少時(shí)離家去上海做學(xué)徒,成家后定居北方一個(gè)小城。
大伯半輩子駐扎西北修鐵路,修到遠(yuǎn)方,遠(yuǎn)到戈壁灘。1970年代,作為一名工程師赴坦桑尼亞援建坦贊鐵路,沿線環(huán)境惡劣,大伯險(xiǎn)些獻(xiàn)出寶貴的生命,回不了祖國(guó)。他可以用腳步丈量漫長(zhǎng)的鐵路線,而故鄉(xiāng)于他,唯有用心抵達(dá)。
奶奶在世時(shí),大伯每年寄家書(shū)和錢(qián)物。我給奶奶念過(guò)許多封信,開(kāi)頭的稱(chēng)呼始終是“母親大人膝下、賢弟”。那時(shí),覺(jué)得大伯真迂腐。奶奶也每年給大伯寄一些自家的風(fēng)干食物,比如山芋干、毛豆莢干、柿餅……除了這些,還寄曬干的草木。
這些年,大伯每次打我父親電話,一開(kāi)口就訴苦:“我回不去了。”哽咽著,繼而,像一個(gè)孩子,嗚嗚大哭。稍許平靜后問(wèn):“我小時(shí)候種的樸樹(shù)在不在啊?”
那棵樸樹(shù)在河岸的最西邊,高大挺拔,樹(shù)冠婆娑,已有75年樹(shù)齡,是大伯12歲離開(kāi)家鄉(xiāng)時(shí)栽種的,他希望讓這棵樸樹(shù)替他扎根在這塊血脈之地,還因樸樹(shù)生命力頑強(qiáng),象征著一種樸實(shí)的品格,他要自己長(zhǎng)成一棵樸樹(shù)。
每年,父親都會(huì)在樹(shù)身上采摘一些葉子、剪若干細(xì)枝條,曬干后,用塑料袋包得整整齊齊,去郵局寄給大伯。
我年少時(shí),大伯每次回轉(zhuǎn)故里,總帶著他的相機(jī),給我們拍照,也常看見(jiàn)他站在樸樹(shù)下,把照相機(jī)按在一個(gè)三腳架子上,然后聽(tīng)到“咔嚓”一聲。后來(lái)我才知道大伯在給自己拍照。
現(xiàn)在,大伯和父親都老了,又相隔千里,無(wú)法團(tuán)聚,唯有小徑和樸樹(shù)能讓他們的兩顆心靠在一起,相互安慰。河灘小徑,在我們的生命里不斷延伸、擴(ku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