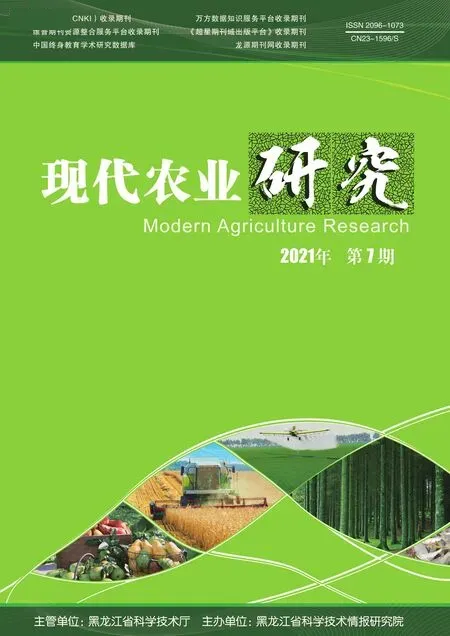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問題研究及規則指引
鄒欣微
(江西財經大學 江西,南昌 330000)
1 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的立法情況
1985年實施的《繼承法》首次闡明了承包經營收益的可繼承性,但是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問題上表述不明,并未明確“繼續承包”是基于繼承關系產生的遺產權屬變更還是按照發包時簽訂的承包合同發生的土地承包方當事人的身份繼受,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繼承編中并未延續這一條文。
2003年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依據土地是否適宜從事農業生產,將承包的土地劃分成兩種類型,分別對應了兩種不同的承包方式:“家庭承包”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并指出了承包收益可以繼承。
2005年發布的《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解釋》中指出承包方的繼承人請求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林地、四荒地的應予支持,但并未提及可“繼續承包”是否等同于繼承,并且規定繼承人需要提出繼續承包的請求。從以上法律規范可以看出承包收益可以繼承,但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能否繼承的問題上法律規定的較為模糊,需要進一步探討和明確。
2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能否繼承
相關立法的不確定為學界留下了很大的討論空間,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地”的可繼承性得到普遍認可,但在家庭承包土地的承包經營權繼承問題上存在兩種相反的主張:繼承否定說以及繼承肯定說,兩種學說都各有其論據和內在邏輯。
繼承否定說依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屬性、保障功能以及繼承后果得出其不具有可繼承性,理由如下:第一,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極強的身份專屬性,這種身份專屬性表現在權利分配和權利流轉上,這種獲得發包資格、流轉資格的權利為“成員權”,具有人身性,是一種特殊的用益物權,不能作為遺產進行繼承。第二,草地、耕地、林地等農業用地是農民開展農業勞動、獲得家庭收入、維持生存需要的根本保障,允許繼承則可能導致一人擁有多份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重復享有與此種權利的設立初衷背道相馳。第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會在一塊土地上創設出若干個不同權利主體的承包經營權,且每一權利主體能支配經營的土地面積有限,土地的細碎化會阻礙農業活動的開展,不利于農業生產經營集中化、穩定化、規模化的實現。
部分學者在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屬性和財產屬性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對公平原則的貫徹提出“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肯定說”,其理由如下:第一,《民法典》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納入物權編并歸屬于用益物權,作為用益物權的承包經營權是絕對的,需要被賦予更多的保障制度以維護其完整性,理應在權屬人死亡后由繼承人繼承。第二,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天然涵蓋的土地經營權進行流轉是獲取財產收益的主要來源,其財產屬性相較于身份屬性有更強的外在表現。作為一項完整的財產權,法律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同樣應當允許其繼承。第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國家賦予農村居民的一種私有福利,因為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的社會保障功能就完全否認其作為農民自身權益的繼承性顯然是不公平的。
繼承肯定說忽視了流轉過程中對受讓主體、流轉條件、流轉程序的限制要求,且流轉與繼承產生的法律后果以及社會效果不盡相同,沒有實質關聯與可比性。繼承否定說則無視法律的特殊規定全盤否定了家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
家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主體為農戶,只有在發生“絕戶”的情況下才會有繼承問題的探討空間,有權繼承承包人遺產的繼承人一定為戶外成員。若繼承人不是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則其可以享有其他集體組織管轄土地的承包資格并分得一塊農業用地,若繼承人為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則其同樣會享有作為城市居民的保障。允許繼承會造成權利的重復分配,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人身專屬性相沖突,因此家庭承包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根據其性質不適合作為遺產,原則上不能繼承,但《農村土地承包法》、《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解釋》中作出了例外規定:林地承包人死亡,其繼承人經過請求可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筆者認為“繼續承包”即為對林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之所以這樣表述是因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其特殊性,不能完全依照遺產繼承的方式對同一順位繼承人的戶籍情況以及農業生產能力不做區分均等繼承。筆者認為在滿足一定條件時林地的承包經營權可以繼承,除林地外的其他家庭承包的土地不具有可繼承性,筆者將該種觀點稱為“限制繼承說”。
3 繼承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規則指引
3.1 戶內成員部分死亡不發生繼承問題
《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6條指出“承包方為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民法典》第330條闡明家庭承包是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的基礎,“農戶是家庭承包經營權的實際權利主體”這一觀點有現行法律規范作為理論基礎,也有“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這一原則作為制度支持,理應得到認可。農戶內的部分家庭成員死亡并不會導致權利主體完全消亡,作為準共有的財產權利份額在剩余的戶內成員之間自然擴張,該種權利的擴張并不屬于承包權的轉移,剩余成員依據承包合同繼續享有承包經營權,不存在繼承的法律效果。
3.2 戶內成員全部死亡依據承包土地的性質確定繼承效果
基于法律的特別規定,當承包土地為林地或以其他方式獲得的四荒地(承包主體為農戶)時,戶內成員全部死亡發生承包經營權轉移的繼承效果。林地和四荒地具有合同簽訂期限長、投入與回報間隔時間久、前期投資大等特殊性,若不允許對該類土地的繼承會降低承包的積極性,引起不必要的紛爭。
林地具有區別于其他家庭承包土地的特征,但作為家庭承包方式的一種其同樣具有強烈的身份屬性,這就導致了林地的承包經營權不能像其他物權一樣完全按照繼承法的相關規定進行遺產分配,目前林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主體范圍尚未明確。有學者指出林地承包經營權只能由歸屬于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繼承人繼承,隸屬于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或隸屬于城市的繼承人不享有繼承權,這種觀點雖然符合承包經營權權利主體的身份要求,但是卻違背了繼承法律規范的平等繼承原則,顯然是不合理的。筆者認為不應在林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問題上依據繼承人所屬的組織不同作出區別對待,但是可以通過訂立相關規則避免與承包經營權的身份屬性發生沖突。例如當集體經濟組織內的繼承人請求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林地時,其可優先取得承包經營權,其他繼承人可在預期所得繼承收益范圍內獲得折價補償金;當不存在隸屬于同一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繼承人或者沒有繼承人提出繼續承包請求的,應當要求于一定期限內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獲得的流轉收益由繼承人享有。
除林地外其他家庭承包經營權不能繼承,當承包農戶全部死亡,承包方主體的缺失導致承包合同無法繼續履行隨即產生合同終止的法律效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收回承包地,繼承人可獲得該土地的承包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