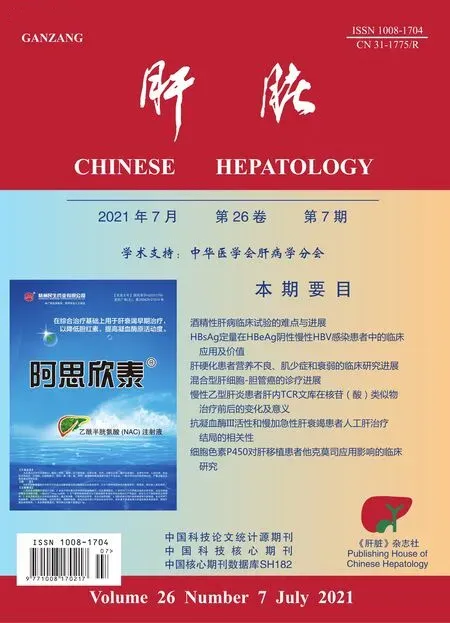混合型肝細胞-膽管癌的診療進展
殷霖霖 趙思 張秀華 季國忠
混合型肝細胞-膽管癌(Combined hepatocellular cholangiocarcinoma,cHCC-CC )是一種罕見的原發性肝癌,其僅占原發性肝癌的0.4%~14.2%,其特點是兼具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和肝內膽管癌 (intrahepatic cholangio carcinoma, ICC)的組織學特征[1]。混合型肝細胞-膽管癌(cHCC-CC)就其細胞起源來說,仍然存在爭議,大多數研究者認為,cHCC-CC腫瘤細胞來自具有肝細胞和膽管細胞分化潛能的肝祖細胞(HPC)[2]。其診斷較困難,很難術前通過影像學或血清學指標明確診斷。同時cHCC-CC的預后較差,目前一致認為其預后介于HCC或ICC之間或比兩者都差。本文結合目前混合型肝細胞-膽管癌診療方面的最新研究進展,希望能為未來cHCC-CC的診斷和治療提供參考。
一、分類和分子學改變
依據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分類,cHCC-CC被分為兩種不同的亞型:一種是經典亞型,它典型的特點具有HCC和ICC混合組織的移行區;另一種是具有干細胞特征的亞型,由三種不同的變體組成:(1)“典型”型,成熟肝細胞被HPC樣細胞包圍;(2)“中間細胞”型,其由病理組織學和免疫組織化學介于肝細胞和膽管細胞之間的中間型細胞構成;(3)“膽管細胞”型,由形態類似于HPC的小細胞,排列成管狀或索狀吻合結構模式。最新的2019年WHO分類將“膽管細胞”型從cHCC-CC亞型中去除,將其歸于肝內膽管癌類別中[3]。
cHCC-CC的分子學機制尚未完全闡明,但目前已經發現 3p和14q染色體的雜合性(LOH)丟失、TP53失活、TGF-β激活、KRAS突變、TERT啟動子、Wnt途徑(CTNNB1 /β-catenin)和細胞周期基因以及染色質調節因子的改變(ARID1A和ARID2)已經參與了其發生、發展[4]。
二、診斷
cHCC-CC往往術前診斷困難,易誤診為ICC或HCC,通常手術切除后才能明確診斷。但常規的實驗室、影像學檢查及組織學活檢仍是初步篩查和診斷cHCC-CC的主要方法。
(一) 實驗室檢查 實驗室檢查指標主要為AFP和CA-199。CA-199和AFP通常各自在ICC和HCC患者中顯著升高。而cHCC-CC同時存在HCC及ICC兩種腫瘤細胞,同樣發現CA-199及AFP在cHCC-CC患者中升高,但cHCC-CC的AFP水平往往低于HCC,明顯高于ICC患者, 而CA19-9水平反過來比ICC低,但比單純HCC高得多[5]。除此以外,Wakizaka等[6]還發現,維生素K缺乏或拮抗劑-II誘導的蛋白質(PIVKA-II)在50.0%的cHCC-CC患者中升高,其升高水平與HCC相似,但明顯高于ICC患者。因此,在患者AFP和CA-199同時升高并伴有PIVKA-II升高時,我們要注意篩查cHCC-CC的存在。
(二) 影像學檢查 除了腫瘤指標常規篩查外,cHCC-CC的診斷主要依靠影像學證據。相關研究表明,相比于增強CT或MR,對比劑增強超聲(CEUS)將cHCC-CC誤診為其他病理類型的概率最高(48%),但是其比CT與MR能更好地檢出惡性病變[7]。而在CT和MR的診斷CHCC-CC的表現上也是欠佳的,因為腫瘤的放射學特征與腫瘤內的主要組織學成分相關,肝細胞占優勢的病灶更類似HCC表現,膽管細胞占優勢的,更類似ICC表現[8-9]。因此,影像學檢查應更適用于惡性肝臟腫瘤檢出,而不是明確區分病理類型。
(三)其他方法 考慮到單純影像學或腫瘤指標診斷cHCC-CC的不足,Yang等[10]將腫瘤標志物與超聲結合起來共同診斷,其區分cHCC-CC的敏感性、特異性、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準確性分別為40.0%、89.9%、58.3%、80.9%、76.9%;而Jiang等[11]將MR與血清學指標結合起來識別cHCC-CC,其靈敏度為76%,特異度為88%。而Liu等[12]創新地應用機器學習來輔助CT/MR對cHCC-CC和非cHCC-CC的識別,并取得良好的區分性能。
通過以上檢查,如果對cHCC-CC高度懷疑,應行穿刺活檢來進一步診斷。為了達到診斷標準,樣本必須顯示肝細胞和膽管細胞分化的明確證據,所以術前活檢的診斷準確性取決于采樣面積。正是因為這種組織學上的特殊性,僅對穿刺細胞檢查存在局限性,因此,手術切除標本的活檢仍是診斷的金標準。
三、治療
(一)手術切除 手術切除仍是治療cHCC-CC的主要方法,但大多數患者發現時,已經錯過了手術時機。成功的手術主要取決于兩個參數:達到R0切除的同時保留更多的肝實質[4]。cHCC-CC常表現出兩種腫瘤的特點,有與肝細胞癌類似的肝靜脈和門靜脈的侵犯,也包含肝內膽管癌的肝門淋巴結的浸潤。Takamichi等[13]也認為,淋巴結是cHCC-CC的第二常見復發部位,如果術前診斷出cHCC-CC,則在進行肝切除術時有必要行淋巴結清掃。但淋巴結清掃是否能改善cHCC-CC預后仍存在爭議。在肝硬化與非肝硬化患者比較中,合并肝硬化患者術前肝功能較差,HBV感染的頻率較高,且腫瘤尺寸較小,較少采取大切除,其腫瘤復發率及復發相關死亡率與非肝硬化患者相當,但肝功能不全相關死亡在肝硬化組更常見,以及肝硬化患者的5年總生存率也較低[14]。 同時最近一項研究表明,相比于年輕患者,老年cHCC-CC患者的手術切除一樣有效,與年輕患者有相當的總生存期(OS)和無病生存期(DFS)[15]。雖然手術切除是根治的主要手段,但cHCC-CC惡性程度高,手術切除后5年生存率較低,平均約為30%,且復發率高,超過一半以上患者復發[1]。
(二)肝移植 米蘭標準為肝移植最常用的標準:單個腫瘤直徑≤5 cm;多發腫瘤少于3個,最大直徑≤3 cm。肝移植是對于不可手術切除肝癌患者的唯一可治愈方法。但在cHCC-CC的肝移植治療上存在明顯爭議,部分研究認為,肝移植對于cHCC-CC的療效與HCC相當,且生存率高于手術切除的患者,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案,但也有研究表明,cHCC-CC患者的肝移植效果比HCC患者差,且對比單純手術切除沒有優勢,應被當作肝移植的相對禁忌[16]。肝移植在cHCC-CC患者中有爭議的結果表明,肝移植應該只在特定的人群中考慮,因此需要明確導致肝移植后預后較差的相關危險因素。 Antwi等[17]研究表明,對局部區域療法有反應的cHCC-CC患者肝移值后3年總體生存率明顯高于無反應者(92% VS 43%)。同時相關研究認為,ICU住院時間長、腫瘤大小>3 cm、癌性淋巴管增多、淋巴結轉移、肉眼可見的門靜脈癌栓、高齡、晚期腫瘤和低血小板等為cHCC-CC患者肝移植后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16,18-19]。總之,亟需制定相關的cHCC-CC患者的肝移植納入標準,從而為那些實實在在能從肝移值中獲益的cHCC-CC患者提供幫助。
(三)局部治療 局部治療主要包括:經動脈放射栓塞(TARE)、化學栓塞(TACE)、肝動脈灌注化療、局部消融治療。主要用于不可切除的cHCC-CC的姑息或其降級治療。
Badar等[20]利用Yttrium-90放射栓塞治療cHCC-CC, 研究結果顯示,患者有70%的客觀緩解率(ORR),其中位OS為15.2個月,與HCC患者比較,兩者之間的ORR及中位OS無明顯差異。此外,Chan等[21]的研究同樣支持Yttrium-90放射栓塞治療,認為對于無法切除的cHCC-CC患者來說,TARE是一種安全且有前途的治療。
TACE適用于不能切除的肝癌患者,它已被證明可以提高這些患者的存活率[22]。Kim等[22]研究顯示,TACE對于延長不能切除的cHCC-CC患者的生存是有效的,且TACE術后患者生存期明顯取決于腫瘤大小、腫瘤血運、Child-Pugh分級和門靜脈有無侵犯。 Seong等[23]將復發性cHCC-CC依據影像學表現分為整體強化組(CT/MRI上表現為強化占腫瘤體積的50%以上)以及外周強化組(僅顯示周邊強化),研究發現,TACE治療對整體強化組的客觀緩解率明顯高于外周強化組(36%比0%),同時整體強化組也顯現出較高的中位OS(52.8個月比12.4個月)。 Park等[24]研究也表明,TACE對多血管的cHCC-CC患者具有更好的療效。
對于肝功脈灌注化療在cHCC-CC中應用的研究較少,數據有限。一項小樣本研究比較了TACE、TARE、灌注化療治療cHCC-CC的療效,發現灌注化療有更高的治療緩解率(66%),而TACE、TARE的緩解率分別為20%和50%[25]。對于消融治療,由于cHCC-CC的低發生率,故缺乏相關報道,但依據對HCC和ICC的經驗推斷,不能手術的相對較小的cHCC-CC(<4 cm)有可能采用局部消融治療[26]。
(四)系統療法 目前用于cHCC-CC系統性治療的藥物主要包括吉西他濱、5-氟尿嘧啶(5-FU)、順鉑、奧沙利鉑、索拉非尼、貝伐單抗等。Kim等[27]研究發現,索拉非尼組與細胞毒性化療組(吉西他濱+順鉑、氟尿嘧啶+順鉑、氟尿嘧啶或吉西他濱單藥療法)在治療cHCC-CC的療效上無明顯差異(中位OS,10.7比10.6個月,P= 0.34),同時他們研究還發現,無論腫瘤主要組織學類型是HCC還是ICC,索拉非尼或細胞毒性藥物化療在治療上都是有效的,而在多變量分析中,發現不含鉑的化療方案與較差的OS相關。但Satoshi等認為[28],對于不能切除的cHCC-CC,含鉑聯合方案(如吉西他濱/順鉑、氟尿嘧啶/順鉑)是優于索拉非尼單藥化療的。在一項單中心研究中,他們也支持含鉑方案(吉西他濱聯合順鉑)比不含鉑方案(吉西他濱聯合五氟尿嘧啶)在cHCC-CC治療上有優勢,認為其有更好的整體緩解率和疾病控制率[29]。在包含貝伐單抗的治療方案的研究中,接受吉西他濱+貝伐單抗或順鉑+貝伐單抗治療的3例患者,cHCC-CC得到控制[30],同時奧沙利鉑加貝伐單抗與吉西他濱+奧沙利鉑及吉西他濱+順鉑相比,療效沒有明顯差異[31]。綜上,含鉑的化療方案在治療cHCC-CC上可能更有優勢,索拉非尼的療效存在爭議,而靶向藥物貝伐單抗的療效在少部分病例中顯現,但仍需大規模前瞻性研究去證實。
隨著基因組學的發展以及它們在轉化研究中的整合,分子靶向治療將成為治療cHCC-CC的有效潛在途徑。可能提供治療靶點的分子通路包括p53、PI3K-AKT-mTOR、MAPK和Notch-Hedgehog通路[32]。 同時針對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TLA-4)、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PD-1)或程序性細胞死亡配體1(PD-L1)的免疫位點抑制劑的有效性也已在臨床前或臨床試驗中得到證實[4]。這些在未來都將可能為cHCC-CC提供更多潛在的治療選擇。
四、總結與展望
cHCC-CC的癥狀不典型,很難在疾病早期及時發現。同時cHCC-CC難以在術前明確診斷。傳統的腫瘤指標和影像學方法更適用于惡性肝臟腫瘤的檢出,而不是區分病理類型,但多種方法的聯合應用以及人工智能的輔助診斷在對cHCC-CC識別方面取得初步成效。鑒于cHCC-CC不易發現及不易診斷的特性,建議高危患者應定期體檢篩查。
治療上手術切除仍是首要選擇,鑒于肝移植是否值得應用于cHCC-CC患者尚存在爭議,有必要制定一套cHCC-CC患者肝移植的納入標準,來進一步將有限的供肝發揮到最大效應。而對于不可切除的cHCC-CC患者,局部治療和全身系統治療顯現出令人樂觀的前景,尤其基因學及靶向治療的發展,有望為不可切除的cHCC-CC患者提供新的治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