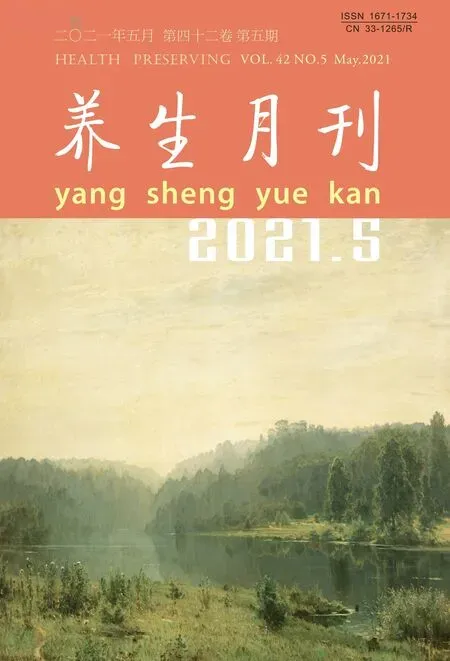絲瓜之趣
劉世河
近日造訪一老友,一進書房便立刻被他墻上的一幅墨寶所吸引。那是一幅畫著絲瓜的小寫意,兩條彎彎的藤蔓時隱時現在幾片肥碩的葉片中,葉下懸吊著幾根長短不一的絲瓜,其中有一根最有趣,于藤蔓頂端的一片葉子背后探出小腦袋來,剛剛成形的樣子,很嫩,還有點微胖,嬰兒肥的那種,煞是可愛。空白處的題詩更有味道,瀟灑飄逸的行草,恰是我喜歡的元代名儒郝經《詠絲瓜》中的兩句:“狂花野蔓滿疏籬,恨煞絲瓜結子希。”
畫寫物外形,詩傳畫中意,二者珠聯璧合、相映成趣。我禁不住連聲大贊:“好畫、好畫!”贊嘆之余,我也觸景生情,想念起老家院子里的那架絲瓜來。每年夏天,絲瓜秧都郁郁蔥蔥地瘋長,遮天蔽日的不但豐盈了餐桌,還是我們家消暑納涼的絕妙之地。
母親說:“絲瓜是個寶,結起來就沒完沒了。”意思是絲瓜這種植物十分高產,只需三兩棵,結出的絲瓜就足夠一家人吃的。每年春天,母親都會在院子的西墻根兒下點上幾顆種子,不消幾日種子便破土萌芽了。老家魯北平原,土地肥沃,絲瓜苗長得特別快。等苗兒長到幾十公分高的時候,母親就開始忙活著刨坑栽桿,繩捆索綁地搭建絲瓜架了。一進五月門兒,絲瓜藤便爬滿了整個架子,隨后絲瓜花也開了,密密麻麻的,滿架都是。花的蒂部就是一根細小的絲瓜,周身長著許多淺綠色的絨毛,每到清晨,絨毛上面總頂著一些細碎的露珠,晶瑩的露珠與黃的花朵、綠的葉子交相輝映,整個絲瓜架就像一座冰雕玉琢的小城堡,美輪美奐。
每到午后,爺爺就會將那張小方桌搬到絲瓜架下喝茶。那個年代鄉下人喝茶純為解渴,極少有人去品。爺爺卻不一樣,首先他用的那套茶具就十分雅致,小巧玲瓏的青花細瓷,而村里其他人家多是一把高高胖胖的粗瓷大提壺。我稀罕那精致的小杯,便常常在絲瓜架下膩著爺爺。爺爺一邊喝茶一邊就沒少給灌輸諸如“水為茶之母,器為茶之父”等等這樣的茶識,至今依然記憶猶新,而且這些年來我這個“不可一日無茶”的喜好,定也是得了爺爺真傳的。
絲瓜是怎么爬上架子的呢?我曾經很好奇,有一次扒開葉子一看,不由一怔,原來絲瓜有“腳”,它的莖上有一根卷須,絲瓜就是用這根卷須纏著架子向上攀爬的,而且絕不是胡亂地爬。它的每一片綠葉,每一個花朵,結出的每一個瓜,都按著它自己的章法有序生長。季羨林先生也曾對絲瓜的這個無聲的“章法”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徘徊在絲瓜下面,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參禪。”最后他終于悟到“原來這絲瓜是有思想的,它能考慮問題,而且還有行動”可他又無法同絲瓜對話,難以求證,于是感慨道:“這真是一個沉默的奇跡。”
喜歡絲瓜的文人墨客,歷史上也有不少。魏明帝曹睿的《種瓜篇》:“種瓜東井上,冉冉自逾垣,瓜葛相結連,蔓延自登緣。”描繪了絲瓜登墻爬屋,上架攀緣的自由自在;宋代杜北山的《詠絲瓜》“數日雨晴為草長,絲瓜沿上瓦墻生。”則寫出了絲瓜黃花綠葉,垂棚滿架的詩情畫意;近代的白石老人對絲瓜更是偏愛有加,不但畫它,也愛種它。他筆下的《絲瓜蜜蜂圖》,氣韻之靈動,實乃妙趣天成。
絲瓜的生命力很強,一直到晚秋,葉子都落光了,裸露的瓜秧還依然纏繞在架子上,頗似一張剪紙。架子上還會有幾根已經干癟的老絲瓜,是故意留的。一是留種子,其次,瓜瓤可用來清洗碗碟,亦可用其洗面擦身,效果極佳。絲瓜還可用來入藥,《本草綱目》中記載:“絲瓜,嫩時去皮,可烹可曝,點茶充蔬。老則大如杵,筋絡纏紐如織成,經霜乃枯,滌釜器,故村人呼為洗鍋羅瓜。內有隔,子在隔中,狀如栝蔞子,黑色而扁。其花苞及嫩葉卷須,皆可食也。”《陸川本草》中也有:“生津止渴,解暑除煩”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