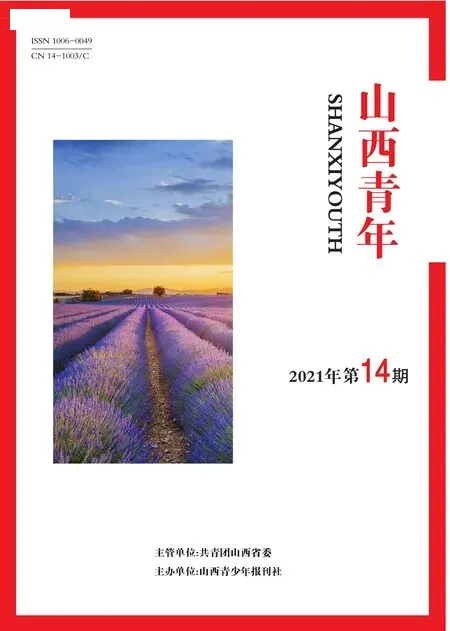布爾迪厄文學場域視角下的莫言小說英譯研究
李小冰
(河南工程學院國際教育學院,河南 鄭州 451191)
莫言小說在成功摘取諾貝爾文學獎后,引起了西方對中國文學的關注,莫言小說不同語言的譯本也受到了文學界前所未有的關注,其中葛浩文的英譯本對世界文壇的影響最大。本文運用皮埃爾· 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考察莫言小說英譯所處的文學場域,以及翻譯實踐在文學場域中推動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作用,以期對中國文學“走出去”有所啟示和幫助。
一、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理論
布爾迪厄是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其理論體系的構成可以簡述為三部分:場域、慣習和資本。布爾迪厄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把“場域”界定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這就使其與傳統的社會學在研究對象的層面上有所區別。在他看來,所謂的“場域”是指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整個社會是由一系列場域組成的,這些場域是獨立的,也是相互聯系的。因此,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不應該是單純的個體,也不僅僅是一種理想的抽象社會。
布爾迪厄在運用社會學理論審視文學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創立文學場域理論。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理論不限用于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從新聞傳播的層面上解讀文學問題,從史學角度審視文學問題,他的文學場域理論都具有指導意義。他認為文學作品價值的生產者不僅僅是作者本身,它的價值體現主要依靠作為信仰空間的文學場域對文學生產者的影響程度和認可程度。[1]作者的創作活動賦予了文學作品一定的價值,但這種價值的體現卻依賴于一定的場域——信仰空間。信仰空間是一個復雜的構成:一是構成信仰空間組成的復雜,二是這些構成信仰空間的組成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復雜的。因此,為了充分揭示文學作品的價值,在“場域”這一網絡式的構成中,各構成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影響都是我們分析其文學場域的重要內容。
二、葛浩文英譯的莫言小說
(一)葛浩文英譯的莫言小說
對于莫言小說的葛浩文英譯版本,之所以我們運用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理論審視,其理由如下:首先,譯者系統地翻譯了莫言的諸多小說作品,如自傳體小說《變》以及《紅高粱家族》《生死疲勞》《酒國》《檀香刑》等十余部小說。在大量的翻譯實踐里,譯者精準地把握了莫言小說創作的精髓。其次,葛浩文英譯的莫言小說成為翻譯界探討的重點。在翻譯界的學術研究中,葛浩文英譯本已經成為探討研究翻譯問題的典范。再次,葛浩文“結合語義、語境及讀者審美體驗等因素,運用文化意象闡釋法、明示法及置換法等靈活多樣的翻譯策略,再現源語傳達的意義、方式及風格,達到文化傳真的效果。”[2]民俗文化和習語的翻譯是文學翻譯的難點,為了使國外的讀者能夠理解小說中特有的文化內涵,葛浩文運用以文章意象闡釋法為核心的多種方法對其進行了個性化的處理。從翻譯方法的角度講,多種翻譯方法的運用也是構建一個新文學場域的手段。
(二)英譯中文學場域的構建
葛浩文翻譯的眾多中國當代小說中,《紅高粱家族》是最具影響力和最暢銷的作品。《紅高粱家族》英文版在國外大受歡迎,不但使其成了莫言的代表作,同時也成了其海外作品的標桿。從某種程度上看,翻譯是對小說的再創作。因而,這樣的再創作行為同樣可以接受文學場域理論的指導。正如上述所言,文學場域是一個“網絡”。在這個“網絡”之中,其構成要素之間是相互影響的,在小說的傳播過程中,文學場域這個網絡可以理解為:一是以原小說文本為存在核心的網絡;另一是以翻譯后的小說文本為核心的文學場域。這兩個文學場域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兩者之間的聯系由翻譯者構建;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因翻譯者與原文作者及譯文讀者之間的差異構成。因而,探討文學場域問題,既能拓展我們對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理論的理解,又能引導我們反思文學翻譯中存在的問題。
三、布爾迪厄文學場域視角下的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
(一)文學場域的構建
文學場域的構建是小說英譯的關鍵。首先,加注釋是最常見的構建新文學場域的方法。例如,《酒國》英譯本中葛浩文對于“白匪”的注釋是:Kuomingtang,white bandits[3].有研究者對此這樣評價:“用加注的方式翻譯了原義,既滿足了讀者的好奇心又忠實于原義的描寫。”[4]在這里,“加注”就是一種構建新文學場域的方式。因為面對英語讀者而言,他們或許能夠理解“匪”的含義,但當它被“白”所修飾之后,他們就很難理解“白匪”的確切含義。但是這樣的詞語又不能不出現在譯文里,所以加注。翻譯的方法有許多,但并非所有的方法都是構建文學場域的方式。“增”的翻譯方法是一種典型的構建文學場域的方法。就如上邊這則案例而言,加注就是如此。與此相同,還可以在原文添加語詞,也可以起到加注的作用。
其次,形式的保留也是構建新文學場域的一種方法。因為語言上的差異,中國的章回小說翻譯是一個難點。于是葛浩文采取了保留小說形式的方法來努力構建一個新的文學場域。《生死疲勞》原文中的標題形式均為對偶句,在翻譯時,譯者不僅注意了信息的轉述,而且保留了原文中對偶句的形式。以第四十三章的標題為例:“黃合作烙餅泄憤怒 狗小四飲酒抒惆悵”。葛浩文的譯文為:Angered,Huang Hezuo Bakes Flat Bread Drunk,Dog Four Displays Melancholy.[5]英語中沒有這樣的對偶句式,而譯者保留原著中的對偶形式的文體,不僅是內容上的傳遞,也是一種特有文化形式的傳遞。因此,從單純的一次翻譯而言,這樣的形式保留是構建新文學場域的實踐;從長遠的翻譯過程來講,這樣的形式保留式的翻譯也是通過文化的傳播,再構新文學場域的過程,因為閱讀這一文本后,讀者再見到類似翻譯的時候,就不會對此感到陌生了。
再次,直譯相結合也是在傳播中構建新文學場域的方法。從某種程度上講,翻譯是一種文化傳播的方式。直譯不僅保留了中國文化的語言特點,而且可以依賴傳播語境實現構建新文學場域的目的。在對《檀香刑》中“爹”與“公爹”進行英譯時,葛浩文沒有按照慣例將其翻譯成“father”(父親)和“father-in-law”(岳父),而是創新性地音譯成了“dieh”和“gongdieh”[6]。這種翻譯手法除了反映原文的語言特點外,譯者還把本民族的文化傳遞給不同文化的讀者,給讀者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體驗。在翻譯“中國工農紅軍”時,葛浩文采取了直譯的方式:China’s peasants,workers,and soldiers。通過對“紅軍”組成成分的逐一翻譯,英語讀者可以很容易地知曉“紅軍”的性質。換而言之,這種對“紅軍”組成成分的逐一說明,其實質就是在從不同的層面構建一個新的“網絡”:一是構建與“中國工農紅軍”這一名詞相聯系的網絡;二是構建與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相聯系的網絡。前者是顯性網絡,后者是隱性網絡,兩個不同網絡的整合則是讀者明確小說文本內涵的具體過程。
(二)文學場域的影響
翻譯中文學場域構建的影響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總結:首先,從翻譯的角度講,構建一個新的文學場域可以拓展翻譯作品的影響。因為,在這樣的新場域里,讀者更容易理解原著小說的文學價值和文學意義。其次,從文化傳播的層面上分析,依賴翻譯構建一個新的文學場域,它的影響是長遠的。從暫時的角度講,新文學場域的構建是譯文讀者理解本篇小說的關鍵,從長遠的層面上說,任何一次翻譯中的新文學場域的構建都為下一次文化傳播中的場域構建奠定了客觀的基礎。再次,翻譯與文化交流的整合。在翻譯中構建新文學場域,其實質是為文化交流做準備。在許多小說作品里,相同意義上的語詞均會有重復出現的機會。例如上邊提到的如“白匪”“中國工農紅軍”等中國特有詞語的翻譯,它們不僅出現在莫言的小說里,也可能出現在其他作者的創作中。當譯文的讀者從莫言的小說理解到“白匪”這樣的詞語之后,他們再一次在其他作品里遇到同樣的詞語的時候,他們就能很容易地理解。也就是說,雖然這里探討的對象是莫言小說的翻譯,但這種新文學場域給予文化交流的影響卻不僅限于如此。
(三)構建文學場域中需要關注的問題
構建一個新文學的場域是翻譯中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為了構建一個新的文學場域,翻譯者需要通過多種翻譯方法的綜合運用來實踐。其次,在翻譯中構建一個新的文學場域要有長遠的意識。一次翻譯中構建的文學場域可能會成為日后其他翻譯所需要構建場域的基礎。因此,翻譯中的新文學場域需要不同的翻譯者共同努力,需要在文化的交流中去構建。而且隨著文化交流的深入,新場域的構建也會不斷地更新。
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理論對翻譯實踐有著重要的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講,構建文學場域的實質就是組建一個不同文化之間的網絡,然后運用這樣的網絡去實現不同文化間的交流。為此,結合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的實踐對此進行了審視與說明,并希望這樣的拋磚引玉之舉,引起更多文學翻譯者對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理論的關注,在文學場域中從跨文化對話的角度關注多元文化的研究,從而使中國文學在成為世界文學閱讀和流通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