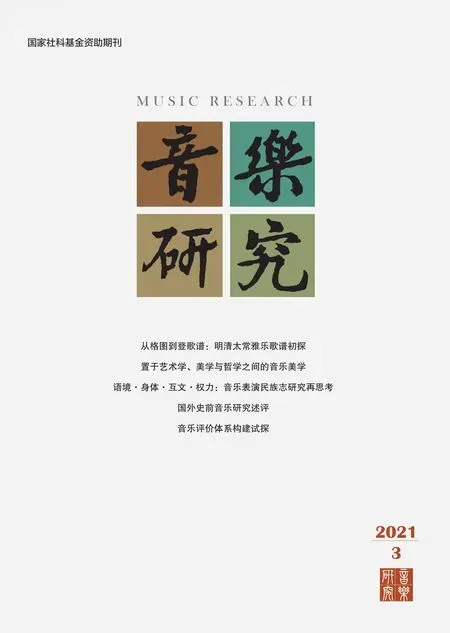西方“波普音樂”研究的歷史嬗變
文◎郝苗苗
波普音樂,譯自西方術語popular music/pop music①國內多譯為流行音樂,但由于國內學術視野中的流行音樂與西方“popular music/pop music”并非同等內涵,所以本文仍采用音譯,稱其為“波普音樂”。Pop music在狹義層面又特指20 世紀中葉盛行于歐美青年中的音樂類型,但在廣義層面和民間評價中依然指示受眾甚廣的popular music。。在國內音樂學界,郭昕②郭昕《音樂學術視野中的流行音樂研究》,《音樂研究》2013 年第5 期,第80—101 頁。和趙樸③趙樸《流行音樂分析的學術發展歷程》,《黃鐘》2019 年第3 期,第53—61 頁。曾分別撰文譯介西方學界關于波普音樂的一些研究情況,對我國的音樂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西方學界,波普音樂的內涵處于流變之中,而相關研究也經歷了比較曲折的發展歷程。鑒于此,本文以西文數據庫JSTOR 和ProQuest 為例,追溯波普音樂研究的源頭,剖析其發展脈絡,以及不同社會動因對西方波普音樂研究發展的影響;解析其復雜內涵的生成過程,以及不同歷史階段波普音樂研究的主要理論方法;并以高頻引用文獻為例,剖析當下波普音樂研究在西方的主要論域,以期為中國波普音樂研究提供一定啟示。
一、波普音樂研究在西方的萌芽(1855—1950)
波普音樂是popular music 的音譯。1855年的《舊時代的波普音樂》④W Chappell. Popular music of the Old Times.London: Cramer, Seals. 1855.一書最早使用了該術語。這是一部英國民間音樂集成,涵蓋了從游吟詩人旋律到民間歌謠舞曲的收集、整理與描述。其中關于popular music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該術語在誕生之初更多用于指示盛行于普通百姓之中的民眾音樂。又如1876 年編撰的《斯坦納和巴雷特音樂術語詞典》⑤Stainer and Barrett's Dictionary of Musical Terms.Novello, 1876.,則將民族音樂的概念與popular music 相等同:“民族音樂,是一個特定國家/民族所特有的民眾音樂(popular music)。”
19 世紀中后期,出現了關于popular music 研究的最早文獻《某些類型的音樂與波普音樂》⑥F. Corder. “Some Kinds of Music. VS. Popular Music.” The Musical Times and Singing Class Circular, Vol.30, 1889, pp.143-144.和《波普音樂》⑦H. Lunn. “Popular Music.” The Musical Times and Singing Class Circular, Vol. 19, 1878, pp.660-661.,分別由倫敦大學作曲技術教授弗雷德里克·科德和音樂學者亨利·倫恩撰寫。前文試圖從調性安排、旋律創作等層面,探求受眾歡迎的音樂技術特征,但在綜合分析了眾多古典器樂聲樂作品及民間曲調之后,作者指出音樂流行的原因如謎之難解。值得關注的是,文中也有指出,當時的音樂創作中已存在為了受眾更多而蓄意制造這一情況。后文并未界定何為波普音樂,但卻呈示出在當時的社會認知中,已將音樂分為好的和壞的,且大家習慣性地將未受過教育的人進行娛樂的波普音樂視作一種低劣藝術。這種認識也并非偶然,在此階段中,面對工業革命后機器文明和拜金主義對社會的沖擊,以馬修·阿諾德為代表的英國文化與文學研究者,在提出文化二重功能的同時,也已對平民文化的價值進行了否定——將“混亂”視作平民中盛行的文化之本質。⑧M.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1867.
可以說,此時的波普音樂已有了多重含義,擁有大量追隨者的音樂可算作波普音樂(即便是古典作品),沒文化的平民百姓中盛行的娛樂音樂也是波普音樂。值得一提的是,前述二文的出現,也說明了西方關于波普音樂的研究,最早出現的領域并非眾多國內學者所說的法蘭克福學派,而是音樂學領域。
20 世紀上半葉,利維斯繼承了阿諾德的思想,并認定工業革命導致文化最終分裂為兩種:一種是少數人的精英文化,是被思考和被解說的最好的價值和標準化身,是好的文化;另外一種就是波普文化,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不假思索而消費的商業性文化,是壞的文化。波普音樂也不可避免地被涵蓋于后者之中。與此同時,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主導的社會學者,開始將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區別看待,認定“民間文化是人們自己的文化、一種自然產生的文化”,但卻將涵蓋了波普音樂在內的大眾文化,視作是被資本主義構建的商品性文化,認定其是資產階級把信息強加給聽眾的途徑。阿多諾更是嚴正批判了波普音樂的標準化創作,否定了其美學價值和藝術個性;⑨T. Adorno. “on Popular Music.” in On Record: Rock,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Edited by S. Firth and A. Goodwin,New York: Routledge,1990. pp.21-24, 199-132, 310-314.他關于波普音樂的認知,延續了前述英國文化研究傳統所指出的“商業性文化”之一般意義,又增加了缺少個性的、被動聆聽的、遵循特定標準生產的音樂產品之特定內涵。
整體而言,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英國文化與文學研究傳統,以及法蘭克福學派對波普音樂的判定,終使其被視作一種沒有藝術個性的“低級趣味”,并將其概念限定在與民間文化、古典音樂相對而言的第三類音樂——音樂工業下的標準化產品。如1948 年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出版物中,也將“波普音樂”與音樂印刷、創作發行直接關聯。⑩Library of Congress 1948, ML 112.這種對波普音樂價值的否定與批判,對西方學術界尤其是音樂學研究影響深遠,使得在后續的三十多年中,罕有學者對波普音樂展開深入探討。正如學者蒂姆·庫利所言:“(長期以來)音樂學者對波普音樂的研究有著集體不適……”?P. Manuel. “From the Editor.” Ethnomusicology,Vol.51,2007, pp.1-3.
盡管如此,這一階段依然有個別音樂學者持不同的見解:斯佩思在《波普歌曲中的生活現實》?S. Spaeth. The facts of life in popular song.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34.中,追溯了美國波普音樂中的民間與古典音樂傳統,指出波普音樂是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生活的真實寫照,認為它呈現著每一代人的倫理、習慣和性格;西班牙學者薩拉扎也提出了“波普音樂是一種影響”?A. Salazar. Music in our time. New York:W.W.Norton.1946.。這些不追風、不盲從的學術見解,為當時的學術界打開了觀察波普音樂的另一扇天窗。
二、波普音樂研究在西方的崛起(1950—1980)
20 世紀50 年代,西方社會進入經濟文化轉型期,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很多令人費解的現象,音樂領域則涌現出流派各異、風格怪誕的波普音樂,因此時的波普音樂只以青年群體為目標受眾,被貼上了“青年文化”的標簽。音樂學界較早關注到這一現象,并于1953 年召開以“音樂在青年和成人教育中的作用與地位”為題的國際會議,會議指出:“波普音樂是一種能夠激發人民想象力的個性作品,但只浮于表面,缺少深根,通常是曇花一現……”?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ole and Place of Music in the Education of Youth and Adults, Brussels, 1953.這種判定代表著當時很多學者對波普音樂的認知——認定年齡所致的代際差異,導致了這種離經叛道的音樂涌現,它只能一時控制公眾的注意,隨后便會消逝。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波普音樂不僅沒有消逝,青年聽眾的狂熱反而使波普樂隊(如披頭士樂隊)從西方一國蔓延到了世界各地。這種情況再度引發了學者的特別關注,其中,一些學者繼續對波普音樂嗤之以鼻,也有學者開始反思。法國符號學者羅蘭·巴特,開始致力于厘清其文本和實踐中那些“表里不一的東西”的隱含作用,而引發了西方學界對波普音樂的重新審視,一些學者陸續進入波普音樂研究領域。這一階段較具代表性的文獻有《內戰前商業之于波普音樂的影響》?J. Stone.“ The Merchant and the Muse: Commerci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Popular Music before the Civil War.”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30, No. 1, 1956, pp.1-17.和《波普歌曲中的求偶對白》?D. Horton.“ The Dialogue of Courtship in Popular So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62, 1957,pp.569-578.。前者剖析了商業環境對美國人音樂品味及才能的影響,揭示了音樂出版業的市場特質、定價政策等因素對波普音樂的形塑;后者以唱詞文本為分析對象,解讀了波普歌曲的意涵及其在引導青少年社會交往中的作用。
20 世紀60 年代以后,始有民族音樂學者進入波普音樂研究領域,坎提克在《盲人與象:波普音樂領域的研究者們》?R. Cantrick.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Scholars on popular music.” Ethnomusicology, Vol.9, 1965,p.100.中,批判了否定波普音樂價值的學說,指出波普音樂雖存在問題,但有積極意義,倡導以跨學科視野予以研究。文化人類學者米德所描述的“整個世界處于一種前所未有的狀態中,青少年與其年長者隔著一條深溝相互張望”?〔美〕瑪格麗特·米德《代溝》,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年版,第83 頁。,則基本上代表了該時期文化研究領域對波普音樂的解讀方式——“世代分析模式”?C. Reich.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New York:Penguin, 1967.。此外,霍爾和沃內爾的《波普藝術》,開辟了波普文化系統研究的先河,它駁斥了法蘭克福學派貶低波普文化的觀點,指出“這種青少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社會轉型的真實反映,是一種由一代人中的部分甚至全部人共享的符號與意義”?S. Hall&P. Whannel. The popular Arts. Pantheon Books,1964, p.276.,并發現波普音樂中政治抵抗的可能性。然而,書中關于波普音樂的認識依然矛盾:“波普音樂,最糟糕的不是它的粗俗或道德墮落,而是,簡而言之,大部分波普音樂并不好”;書的最后一章卻又如此寫道:“撰寫該章時,我們已認識到披頭士樂隊及其音樂風格是一種嶄新的景觀。”顯然,此時的文化學者,對波普音樂的價值判定開始舉棋不定,他們確實打算重新審視波普音樂的價值,但終究沒能說得明白。
有趣的是三年之后,披頭士樂隊開始親自為波普音樂的藝術價值代言,以身體力行的音樂創作(第八張專輯《佩珀軍士寂寞的心俱樂部樂隊》),向全世界言說了波普音樂的美學價值——精致的管弦樂配器和重唱藝術,觸動人心的自傳性歌詞及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錄音技術層面對多聲道的探索。他們在贏得市場受眾的同時,也極大地扭轉了學者對波普音樂的認知,波普音樂的正面評述也隨之頻繁見于報刊。美國知名時政雜志《紐約客》指出:“披頭士將波普音樂帶入了新天地”,使之“從一種娛樂消遣變成了一種藝術”。[21]L. Ross. “Talk story about the Beatles’ thirteenth and latest record album, Sgt. Pepper’s Lonely-Hearts Club Band.” The New Yorker. June 24, 1967, p.22.作為權力機構代言人的英國《泰晤士報》,也發布:“披頭士樂隊重振了波普音樂的前景與希望”[22]W Mann. “The original Times review of Sergeant Pepper’s Lonely-Hearts Club Band.” Music Critic, May 29,1967.。美國歷史學者羅森斯通更是敏銳地指出:“60 年代初,沒人認真地看待波普音樂……但時至今日,關于波普音樂的看法已發生戲劇性改變……”[23]“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The music of Protes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82,1969, pp.131-144.
與此同時,歐美社會學領域關于青年群體波普文化的研究日益成熟。伯明翰學派代表霍爾、杰弗遜等,已將法國符號學和人類學的結構主義,發展成波普文化分析的主要理論;進而批判過往社會文化學研究中,將年齡差異作為文化類型差異之主要決定因素(“世代分析模式”)的缺陷——缺少考察青年文化的歷史特殊性:“強調代溝……我們在其中看不到任何歷史特殊性的概念,這些特殊形式為什么發生在特定歷史階段,也未能說明”[24]D.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Methuen & Co. Ltd,1979, p.73.;亦由此將社會文化學者關于波普音樂的研究導向“結構分析”模式——將青年文化置于社會階級結構中進行研究,探求社會結構尤其是階級、地位等因素,對青年文化形成,以及社會結構矛盾的影響。具有代表性的文獻有:赫伯迪格的《亞文化:風格的意義》[25]同注[24]。,科恩的《民間魔鬼與道德恐慌》[26]S. Cohen.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1972.。前者闡釋了亞文化通過“風格”來間接抵抗霸權文化的方式及其生成過程,文章將音樂作為構成亞文化風格的元素之一,認為亞屬階層成員以構建一種階層劃分和教育體系之外的身份認同為目的,是對主流社會的象征性抵抗;后者則重點揭示了被標簽化的摩登一族和搖滾青年,與主流社會道德恐慌之間的深層關聯。此外,《女性與亞文化》[27]A. McRobbie, J. Garber. Girl and Subculture. London: Palgrave, 1976.一書,解析了處于社會從屬地位的女性樂迷的亞文化建構方式及意義,進而修正了當時波普文化研究對象中的“女性缺位”傾向。與此同時,萊恩和弗里斯繼續挑戰了赫伯迪格的理論:前者關注音樂文本構建聽眾群體的方式,認為朋克音樂體裁的出現是亞文化行為的前提條件;后者則指出音樂只是進行其他行為的背景,而非標識反對之空間。[28]S. Frith. Sound Effects:Youth,Leis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och 'n' Roll. London: Constable, 1983.可以說,女權主義視角及對青年群體波普文化研究的多角度批判,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當時學界更多聚焦于階級分析視角下的波普音樂研究,視野與方法變得日益多元化。
整體而言,這一階段波普音樂研究開始在西方學界崛起,但在這一階段的早期,主要參與者依然是社會文化學者。正是在這些學者的探討反思聲中,在見證了波普音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歐美大陸的氣勢之后,西方音樂學界排斥波普音樂的防線開始坍塌,音樂學者也隨之加入研究行列,但他們的關注焦點,與社會文化學者仍有著很大不同。
宏觀而言,70 年代出現在西方音樂學界的波普音樂研究,主要是由西方正統音樂學者率先參與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美國音樂學者懷爾德的《美國波普音樂:偉大的革新者們1900—1950》[29]A. Wilder. American Popular S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英國學者梅勒斯的《披頭士樂隊過往》[30]W. Mellers. Twilight of The Gods. Viking, 1973.、《波普風格的起源:20 世紀波普音樂的緣起》[31]P. Mere.Origins of the Popular Style: The Antecedents of Twentieth-Century Popular Music,1989, pp. 213-286.及《波普音樂的和聲理論》[32]P. Winkler. “Toward a Theory of Popular harmony.”Theory Only, 1978(4). pp.3-26.等。這些著述的共性特征,均是對音樂本體開展分析,但所選取的樂手及代表作卻存在很大差異。例如,《美國波普音樂》論及的樂手涵蓋柏林、格什溫、羅杰斯等,而《波普風格的起源》則聚焦于藍調和格雷泰姆。這些成果的出現,推動著西方音樂學界對波普音樂研究的接納與認可。時至1981 年,國際波普音樂研究協會(IASPM)成立,劍橋大學出版社也創辦專門刊載波普音樂成果的期刊《波普音樂研究》,這些行動都在一定程度上宣示著西方音樂學界對該研究領域的正式接納。而學者們關于波普音樂范疇的差異性論述,也引發了80 年代初期西方學界關于波普音樂的新爭論:到底什么音樂和誰的音樂才是“波普音樂”?德尼索夫指出:“波普音樂就像獨角獸,每個人都知道它該是什么樣子,但從來沒有人見過它……”[33]S. Denisoff. Solid Gold: The Popular Record Industry,N.J.: Transaction Books,1975瓊斯[34]G. Jones. “Definitions of Popular Music: Recycled.”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1977、塔格[35]P. Tagg. “Analyzing Popular Music: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opular Music. 1982 (2), pp.37-67.和查爾斯[36]C. Hamm. “Some Thoughts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pularity in Music.” Popular Music Perspectives 1982 (2),pp.3-15等學者,從傳播途徑、銷售規模、表演方式甚至作為審美對象本身的特點等不同層面,探討了波普音樂的界定方式,但卻又先后被其他學者所駁斥。盡管如此,大量社會學者堅持傾向于將商業屬性或者說是唱片的銷售數量及電臺轉播次數作為波普音樂的主要判定方式。這種界定方式,加之科技進步,逐漸使波普音樂的批量生產和全球流通成為可能;繼而間接導致了具有商業曝光度的波普音樂的制作、存儲、分銷及推廣的網絡體系研究,成為80 年代西方波普音樂研究的焦點之一。其中,代表性的文獻有《音樂背后的金錢》[37]M. Eliot. The Money behind the Music, New York:Franklin Watts.1989.《節奏布魯斯之死》[38]N. George. The Death of Rhythm and Blues. 1988。在這股研究熱潮中,最受關注的莫過于對音樂工業的產品代表——世界音樂(World Music)的關注。世界音樂的混生性,帶給聽眾新奇與刺激,但其碎片化與失位感,也激發了學者的更多探討,《科技空間、波普音樂、加拿大媒體》[39]J. Berland. “Technological space, Popular music,Canadian mediations.” Cultural Studies, 1988 (2):3, pp.343-358.《那些小國家的音樂工業》[40]R. Wallis and M. Krister. The Music Industry in Small Countries. New York: Pendragon. 1984.等都是相關重要研究。其中,很多學者認定全球音樂文化已在音樂工業的運作下,走向了同質化的凄涼結局。
但這種偏見很快被80 年代末出現的民族音樂學者的研究所打破。在1989 年的著述《隱藏的音樂人——英國城的音樂制造》中,芬尼根基于田野考察工作,記述了英國米爾頓·凱恩斯鎮草根音樂人的音樂創作與表演實踐,轉述了其向不同樂手和粉絲群體(從古典音樂到朋克音樂,從教堂唱詩到重金屬樂隊)[41]R. Finnegan. The Hidden Musicians: Music-Making in an English Tow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所提出的關于音樂使用方式、表演過程和意義的問題,并從音樂學習、創造性、表演機構和組織支持等層面,對不同音樂風格開展了比較研究,剖析了音樂審美的復雜性(無法從音樂的審美趣味明確區分出階層/年齡/社群歸屬),最后提出:音樂為人們的活動和關系提供了一種語境,人們選擇音樂作為個人/集體身份和價值的一種表達,因為音樂允許人們在時間和空間上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有意義的建構。
《隱藏的音樂人——英國城的音樂制造》是波普音樂研究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本著述。它基于腳踏實地的田野工作,聚焦于對普通人的波普音樂體驗過程,挑戰了阿多諾將波普音樂視作資本主義工業強加給人們的文化結論,以及社會學者將波普音樂視作與主流社會對抗的“抵抗的亞文化”之主導觀念,突破了西方正統音樂學者對波普音樂的研究方法,也證明了民族音樂學視野下開展波普音樂研究的重大價值。
緊隨之后,又出現了幾部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田野工作基礎上的波普音樂研究成果,如利普希茨的《集體記憶與美國波普文化》[42]G. Lipsitz. Time Passages: 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0.、科恩的《利物浦的搖滾文化》[43]S. Cohen. Rock Culture in Liverpool: Popular Music in the Ma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等,但學者們也并非沒有困惑,最令大家感到苦惱的是,家門口的波普音樂,并不是西方民族音樂學特有的研究對象——他者/異文化,那么,如何界定我者與他者的關系,如何證明自身研究的客觀性,變得麻煩重重。然而,很快,民族音樂學者就在學術反思與研究實踐中,對“他者”給出了新的界定:“他者,不是作為一個自我封閉或獨立的研究對象,而是作為對象,只能在其與研究者的關系中定義。”[44]L.Grenier and J. Gilbault. “ Authority revisited:the ‘other’ in anthropology and popular music studies.”Ethnomusicology, Vol.34,1990, pp.381-397.這種界定方式的適時調整,也為西方民族音樂學視野下波普音樂研究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20 世紀50—80 年代,在勢不可擋的波普音樂浪潮中,在關于波普音樂界定及其價值意義的不斷追問中,學者們漸趨明了波普的相對性,波普音樂的可變性與復雜性,認識到自身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在跨學科視野下開展波普音樂研究的必要性。
三、西方波普音樂研究的反思與重構(1990—)
20 世紀90 年代以后,反思與批判精神占據西方學界的主流。90 年代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米德爾頓的《波普音樂理論導論》[45]R. Middleton. Popular Music i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該成果以傳播學、社會學交叉研究的獨特視角切入,探討了技術、文化、地理、政治等因素調整和形塑波普音樂的方式,并針對當時的研究現狀開展了三重反思:研究資料方面多依賴雜志、唱片公司和電臺的數據,開展研究的資料來源不可靠,因為這類資料會受到行業操縱;[46]R. Middleton. Studying Popular Music.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研究對象過多聚焦于個別明星和少數專業樂手,對商品交換研究的極端依賴,導致多數學者忽視了波普音樂在本質上是一種生活方式或文化實踐形式;在研究方法方面,認識到“波普音樂根本不能像藝術音樂那樣被分析,將西方音樂傳統方法應用于波普音樂會導致誤解誤讀”[47]同注[46],第328 頁。。塔格和尼格斯也明確指出西方學界波普音樂研究存在的重大學術漏洞:“研究波普音樂的音樂學家仍然傾向于忽視社會背景……”[48]P. Tagg, K. Negus. “The primary text: back to square one?” IASPM UK Newsletter, 1991, R. C., p.3.科恩更是直言:“直到現在,我們依然不清楚音樂家們如何做出關于音樂的選擇,他們到底如何界定自身的社會角色及處理其矛盾……”[49]S. Cohen. “Ethnography and Popular Music Studies.” Popular Music. Vol.12. 1993, p.127.此外,國際音樂學學會(ISM)第16 屆會議的圓桌論壇,大家也認識到音樂學領域缺少對波普音樂及其聽眾群體的研究。[50]P. Brett. “Round Table VIII: Cultural Politics.” Acta Musicological, Vol.69,1997, pp.45-52.
這些反思促使研究者開始借助跨學科的視野開展更為深入的研究,并推動波普音樂研究的蓬勃發展,其內涵也得到進一步拓展。較之80 年代西方學者傾向于以商業屬性和轉播次數為基礎的定義,卡斯薩賓提出的波普音樂意指“無所不在的音樂”[51]A. Kassabian. “Popular.” in Key Terms in Popular Music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113.理念也被廣泛接納,而這種界定方式使波普音樂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泛化,從以商業屬性為基礎而制作的音樂,到百姓日常生活中頻繁接觸的音樂(如超市音樂、電子游戲配樂等),抑或經過現代轉型后受眾廣泛的新傳統音樂,甚至為提升工作效率而創作的音樂,都納入了研究視野。
縱觀新千年前后的西方波普音樂研究文獻,方法論的多元化、跨學科化及個性化是其突出特征。由于文獻眾多,難以一下子概括出當下研究的更多共性特質及主要缺陷,但若從具體研究視角而言,當下西方波普音樂研究存在四大主要論域。
(一)傳播受眾理論視野下的波普音樂研究
受眾理論主要聚焦于群體的接受問題,它承襲了社會文化學者關注波普音樂接受群體的傳統(如前述阿多諾的被動聆聽理論,20 世紀50 年代對樂迷青少年群體的關注,60—70 年代轉為對青年亞文化的聚焦,整體而言,之前對樂迷的論述多處于否定狀態),著重闡述聽眾群體在參與音樂活動時對音樂的接納、理解和使用。時至20 世紀90 年代,學者們更加關注的是(較之一般人)特定音樂體裁的聽眾群體的自發性與創造性。特隆德滿[52]M. Trondman. “Rock Tastes -On Rock as Symbolic Capital.” in Popular Music Research. Nordicom, 1990.等學者,借用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探討了波普音樂的聽眾是如何基于音樂體驗中的象征性來將自身與他人相區隔。李維斯[53]L.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Routledge.1992.和簡森[54]同注[53]。等學者聚焦于音樂“粉絲”,分析了“粉絲”的身份創造功能,對波普音樂進行主導的可能性,以及對表演意義促成的影響——“通過成為“粉絲”,為自身建構了同一身份,并在此過程中進入了借由自身而創造的文化活動領地,這是潛在的、與沉重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中令人不滿的情況進行對抗的力量源泉。”[55]同注[53],第3 頁。錢伯斯[56]I.Chambers. Migrancy, Culture, Identity. Routledge.1994.與科恩[57]S. Cohen. “Sounding out the City:Music and the Sensuous Production of Pla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5, Vol. 20, pp. 433-446.等學者,則更多關注作為商品的波普音樂的消費與轉化,認識到觀眾在音樂消費過程中,可以將其用作個人身份的標識、對抗性的表征,甚至音樂生產的源頭,揭示了聽眾在音樂消費和體驗過程中變被動為主動的轉化過程,從而形成了波普音樂研究中的積極受眾研究。
(二)西方正統音樂學視野下的波普音樂研究
西方正統音樂學以音樂本體分析為首要研究方法。新千年前后,這種方法在波普音樂研究中依然延續,從中不難看出,正統音樂學者依然期待波普音樂有自成一派的創作技術與審美。相關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論文集《波普音樂的文本分析方法》[58]R. Middleton. Read pop: Approaches to Textual Analysis in Popular Mus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其中,有借助比較研究法對波普音樂與其他題材進行區分的研究,也有不同研究者借助獨創形態分析法對布朗、斯普林斯汀等人代表作品技術特征的探索。阿蘭·摩爾在波普音樂文本分析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代表性著述有《搖滾樂中的降七級音》《和聲類型》《主要文本——搖滾音樂學的思考》[59]A. Moore. “The so called ‘lattened Seventh in Rock’.” Popular Music, 1995. pp. 285-202;Rock: The Primary Text: Developing a Musicology of Rock. Ashgate, 2001.。前兩篇文章分析了搖滾使用的各類降七級音與和聲模式;后者則突破了音樂分析的一般關注要素,基于不同體裁及亞類音樂文本的比較,建立了一套適用于搖滾分析的特有體系,關注了對搖滾樂分析的基本要素:音色、記譜、樂器法、節奏組織、樂句結構、即興方式的差異等,為當代波普音樂的形態分析提供了啟示。
(三)符號學視野下的波普音樂研究
符號學視野下的波普音樂研究,于20世紀70 年代末期在西方學界興起,在赫伯迪格和塔格等學者的影響下,波普音樂逐漸被視作當代社會中符號表意活動的集合。90 年代后,學者們認識到傳統符號學研究無法闡釋當代波普音樂的復雜性,進而著手建構適應當代波普音樂研究的符號學理論。該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表演儀式:論波普音樂的價值》[60]S. Frith. Performing Rites:On the Value of Popular Mus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波普音樂、社會抗議與其符號意涵》[61]D. Martinelli. “Popular Music, Social Protest and Their Semiotic Implication.” New Sound, 2013, Vol. 42,p.42.和《波普音樂符號學:主流波普音樂與搖滾音樂中的孤獨主題》[62]M. Elicker. Semiotics of Popular Music : The Theme of Loneliness in Mainstream Pop and Rock Songs. Tubingen:Gunter Narr Verlag.1997.。《表演儀式》從符號學視野闡述了波普音樂的文化價值:“交流性是波普音樂的本質,這種交流與一般交流有所不同,它是一種關于價值、理解、認同、商榷進而化解分歧與隔閡的交流,涉及交流雙方之身份認同和外部世界的構建與重構”,并指出:“儀式化的表演和傾聽是波普音樂實現其文化功能的交流形式和文化策略。”此成果的誕生,也將學者們的視野引向了關注波普音樂的文本/符號如何與人發生互動從而產生意義。此外,奧希斯等學者,還探討了波普音樂專輯封面符號資源的展示方式及內涵。[63]M. Ochs.1000 Rock Covers. Cologne: Taschen, 1996.
(四)民族音樂學及其他跨學科視野下的波普音樂研究
民族音樂學以田野工作及在此基礎上撰寫的音樂民族志為開展研究的方法之本。1995 年,美國民族音樂學會設立波普音樂學研究部之后,波普音樂研究在民族音樂學領域呈現井噴之勢。學者在田野工作的基礎上,從不同路徑闡釋著波普音樂的創作、表演及體驗。從借助皮爾斯符號學探討波普音樂在地化問題的《雅加達的朋克音樂生活》,到借助生態學理論分析淡水河主題歌曲創作變遷的《臺灣淡水河之歌》[64]N. Guy. “Flowing down Taiwan's Tamsui River:Towards an Ecomusicology of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 Ethnomusicology, 2009,Vol. 53,pp.218-248.,再到借助音響存時分析法闡釋新傳統音樂中審美與認同問題的《土耳其“改編的傳統音樂”之美學研究》[65]E. Bates. “The Aesthetics of Arranged Traditional Music in Turkey.”Ethnomusicology, 2010, Vol. 54 . pp. 81-105.,體現了民族音樂學者關于波普音樂研究方法論個性化的表征。
與此同時,新千年前后新媒介和新技術的出現,顛覆性地改變了樂迷群體消費和體驗波普音樂的方式,很多學者也嘗試借助跨學科的視野對波普音樂進行多樣化的研究。從對波普音樂的網絡傳播下載對音樂產業的影響,[66]K. Mcleod. “The Rise of Internet Distribution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Major Label Music Monopoly.”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 2005, Vol. 28, pp.521-532. 因版面有限,請恕文獻不過多例舉。到數字技術下的波普音樂創作及倫理研究;[67]T. Warner. Pop Music-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Ashagte,2003.從特定波普體裁史學研究,到波普音樂對社會性權力的解構與建構;[68]P. Collins. From Black Power to Hip Hop: Racism,Nationalism, and Feminism.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均橫跨多個社會文化學科與視角。而學者從跨學科視野所開展的波普音樂研究也示明了,波普音樂是一種復雜的音樂文化現象,把落腳點放在問題意識上,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呈現出的不同圖景,更有助于我們獲得客觀、全面的認知。
結 語
筆者以波普音樂研究在西方的發展變遷為研究對象,厘清了其內涵的歷時性變化、方法論的變遷,揭示了不同社會動因對西方波普音樂研究造成的影響及當下的主要論域。從中可以看出,每個時期、每種類型的波普音樂,只有局內人才懂得它的價值,無需局外人對其價值高低進行評判。倘若身處局外,則永遠難以真正理解它的意義。愿此文可以帶給國內學術同行以啟迪,也愿我們打開視野,去關注、體驗和研究當代社會生活中被人們體驗著、傳播著、活生生的波普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