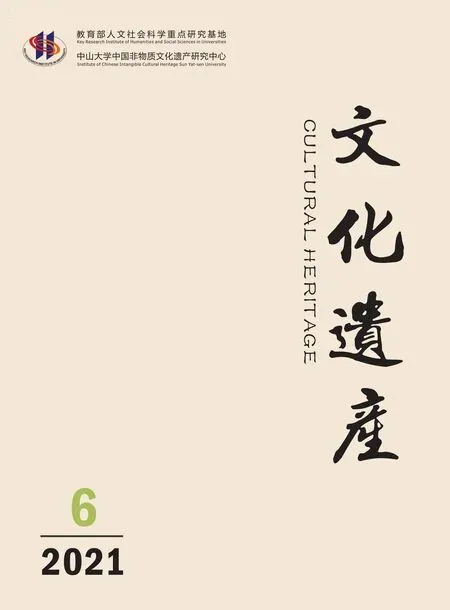活化歷史: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的學理建設思考*
高小康
一、 非遺研究:發現歷史的“缺口”
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發生和應用起自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遴選第一批“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和2003年頒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非遺保護不同于以往歷史遺產考古與保護工作特有的高度專業性。從《公約》的指導和各國的實踐來看,具體的保護工作包括建檔記錄、傳承教育、傳承人保護、社會傳播等多方面公眾性的文化活動。因為非遺保護觀念的創新性和特殊性,這種文化保護活動不僅僅是具體的工作實踐,而且需要在非遺保護的進程中不斷進行理論觀念和實踐方面的科學研究。
我國自加入《公約》以來,在非遺保護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如今教育部把非遺保護增列為本科教育專業就是推進非遺教育與研究的一個重要措施。作為本科教育的非遺保護專業需要有更高層次的學術研究形成專業的學理基礎,但由于非遺保護觀念自身的創新性和學術內涵的復雜性,這方面的學理研究目前還是個需要開拓的新領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1年頒布《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可以視為非遺保護的前奏。這是20世紀后期對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生態危機進行反撥的一種文化政治主張,倫理根據是當代世界不同群體、不同傳統文化生存與發展權利的公平性。但隨著非遺保護實踐的進展,保護文化多樣性不再僅僅是政治立場和姿態,實際上正在成為人類克服文化生態危機、尋求健康發展的科學路徑探索。因此需要對這種文化實踐的價值和目的進行學理探討,從政治訴求進入到科學研究層次,使非遺保護成為促進人類文化生態健康發展的有效實踐。
在教育部本科專業設置中,非遺保護專業是屬于藝術學大類的學科范圍。這顯然是因為非遺項目的文化形態多與藝術相關,在具體項目的保護實踐方面需要較多藝術學方面專業知識的原因。作為文化保護專業教育,提供保護知識、專業技能是沒有問題的。但高等院校本科教育的目的并不僅僅限于提供現成的知識和技能,更要提供在知識傳授背后支撐知識的學理基礎教育,幫助學生深化思考、開拓視野,培養創新思維和創造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一個新的文化研究和保護實踐的概念,非遺保護的理論基礎、文化價值及其實踐的可操作性等方面都是處于探索中的新觀念、新實踐、新問題,需要在非遺保護進程中不斷研究。基于這種狀況,應當認識到非遺保護專業不僅限于文化保護實踐層面的專業學習,還應當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的學理研究作為專業學術基礎。
從深層次的學理基礎上講,非遺保護的根本問題不在于具體被保護項目的藝術特征和價值的分析判斷,而在于非遺保護對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關系的重新認識,即從文化傳統內在的社會整合性、歷史延續性、生態多樣性和發展活力的視域,認識非遺對社會發展的普遍價值。從這個學理層面來說,非遺研究是一種歷史研究,或者說是文化史學的學理研究。
然而非遺的歷史研究又不同于傳統史學研究。中國傳統史學所追求的研究成果是“實錄”,即真實、客觀地記錄事實。西方的歷史研究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就是“敘述已發生的事”。(1)亞里斯多德、賀拉斯:《詩學·詩藝》,羅念生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9頁。總而言之,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歷史書寫都是記錄、敘述發生過的“事實”,即特定的人在特定時空中曾經發生的行為及其結果。歷史的記錄編纂和佐證歷史的史料考證都是以歷史事實的客觀性為前提的。但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過去留下的遺產所關涉的歷史卻與傳統史學所研究的歷史不同——它不是客觀存在的物質性“事實”,而是影響事實發生的“非物質”因素——規則、技能、習俗、意象、情感、信仰等等。這都是存在于“事實”背后,充滿矛盾、缺失、虛構和不確定性的社會記憶內容。從傳統史學對歷史真實性或客觀性的要求來看,這都是不可靠因而不具有歷史價值的東西。
然而走向近代的史學研究越來越發現,純粹客觀、真實的記錄和史料本身并不一定能夠成為對人類對自身的理解和發展有意義的知識。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的那句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就是認為僅憑編年和史料這些客觀資料的真實性并不能構成真正有意義的歷史。他用筆記本和保存在首飾匣里的干花瓣比喻關于歷史事實的編年和史料:
我們每個人在筆記本中記下我們的私事的日期和其他事項(編年史)或把綢帶和干花瓣放在首飾匣中……但是我們知道,歷史存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它的資料就在我們自己的胸中。因為,只有在我們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種熔爐,使確鑿的東西變為真實的東西……(2)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3-14頁。
他所說的“確鑿”是指像干花瓣那樣客觀存在的事實,而“真實”則特指深藏于“自己的胸中”,與干花瓣相聯系的蘊涵個人心靈體驗的特定瞬間事件記憶。如果說傳統史學關注的是事實的“確鑿”,那么非遺的史學研究所側重的就是記憶的“真實”,或者說心靈真實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非遺史學不同于傳統史學的一個基本特征在于研究對象的變化,即從確認客觀的“事實”轉換到喚起內心的記憶。
傳統史學歷來相信歷史記載的可靠性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所謂“信史”“實錄”便是對歷史著作最高的褒獎。然而如果參照克羅齊的比喻就會發現問題——札記的可靠性(編年)和干花瓣的真實性(史料)都具備了,但如果關于事件當時情境的記憶卻淡忘了,那么無論多么可靠的歷史敘述和事實證據還有什么意義?
對于傳統史學來說有確鑿的事實而無真實的記憶似乎是個悖論——有了事實記錄當然也就有了記憶,或者反過來說有記憶才會有關于過去的記錄。但這種“理所當然”的推論忽略了史學中的空缺問題:有的歷史是不被記錄的。美國社會學家芮德菲爾德提出了一種“一個文明兩種傳統”的理論:
在一個文明中存在著具有反思性的少數人的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和不具有反思性的多數人的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大傳統通過學校或宗廟培育,小傳統則在未受教育的村民社區中自行發展。(3)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70.
這兩個傳統同屬于一個社會,但卻包含著不同的歷史記憶。傳統的歷史書寫即“正史”所記錄和研究的是“大傳統”,而“小傳統”是在沒受過教育的村民社會中通過口傳、習俗等非文字方式傳承,因而很少在“正史”中出現,也就是說是不被作為歷史記錄的。中國正統史學是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如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以及先秦典籍中對“黃帝四面”“夔一足”等傳說的理性化闡釋等等,都可以看出主流文化對經過官方或文人合理化闡釋、整理的正統敘述之外的歷史所持的懷疑態度。
然而“一個文明兩種傳統”顯示出了正統歷史在小傳統記憶方面的缺失。這正是自18世紀維柯、赫爾德以來對民間記憶作為族群傳統的歷史觀在近代歷史研究中日益凸顯的新史學研究方向。
兩種傳統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差異非常明顯——大傳統是書寫的,而小傳統是口傳心授的。在一個文明的發展過程中這兩個不同的傳統可能形成集體記憶的斷裂。比利時口述歷史學者范西納在研究“口述傳統的動態過程”時注意到記憶的斷裂,他稱為“浮動缺口”(the floating gap):
起源敘述,集體敘述和個人敘述都是同一過程不同階段的不同表現。當把這些敘述整體組合在一起時,通常整體會出現三個層次。近代時期的信息越往前越逐漸減少,而在較早的時期,由于有些不確定,人們會發現信息要么有中斷,要么僅僅剩下一個或幾個名字。我把敘述上的斷層稱之為“浮動缺口”……一些人類學家已經用這些階段來代表社會中的不同功能。第一個是神話,對應著恒久的過去;第二個是一個重復的(周期性的)中間階段;第三個是線性時間……歷史意識只在兩個層次上運作:創世的時間和和最近的時間。由于時間計算的限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Generationenfolge)而變化,我把這個斷層稱為一個浮動缺口。(4)范西納:《作為歷史的口頭傳說》,鄭曉霞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第17-18頁。
范西納所說的“浮動缺口”出現在口述歷史的三階段演進中——第一個階段是久遠的神話時代,第二階段是周期性重復的中間階段,第三階段是當下的線性連續時間。范西納認為歷史意識只存在于創世時代的神話組織和當下經驗的連續性中,而二者之間是會隨著代際序列(Generationenfolge)浮動變化的“缺口”。這三個階段對應的是早期口述歷史、中期“周期性重復”的歷史再到當代經驗這三種歷史時期,但在神話時代之后的中間時期是循環重復的“靜態模式”,在口述歷史中成為斷層。
范西納研究的是非洲土著歷史,在神話與當代之間似乎是個空白。而在傳統的軸心文明中,這個中間時期正是“大傳統”形成的主流歷史時期,口述歷史因其不雅馴而被主流文化遮蔽,成為集體記憶的“缺口”。如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所說:
歷史通常始于傳統中止的那一刻——始于社會記憶淡化和分崩離析的那一刻。(5)哈布瓦赫:《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埃爾、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余傳玲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7頁。
他所說的“歷史”就是指正統的或者說作為大傳統文化傳承內容的歷史書寫,而“傳統中止”的“傳統”是指正史之前的集體記憶傳統。正統歷史書寫開始就意味著此前集體記憶傳統的“淡化和分崩離析”。一個文明因此而分裂為兩個傳統——主流歷史書寫的大傳統與“淡化和分崩離析”的集體記憶小傳統。
然而反思的、理性的大傳統歷史知識只是文明的顯性表象。隱沒在歷史表象背后的集體記憶中隱含著文明底層的生命動力。班固曾引孔子“禮失而求諸野”,認為諸子等民間雜說可補正統文化“禮”之遺,說明民間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傳承延續具有互補之用。范西納所謂“歷史意識只在兩個層次上運作”,可以理解為在主流文化“大傳統”的歷史書寫中,作為集體記憶的口述歷史是缺失的,“小傳統”被遮蔽,因此形成了歷史意識的“浮動缺口”。非遺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正是從這個“浮動缺口”進入,重新發現被遮蔽的集體記憶,構建大小傳統整合的“更大傳統”的歷史研究。
二、書寫的歷史與鮮活的記憶
傳統意義上的史學所研究的基本內容在于敘述,即歷史書寫。歷史敘述的表層是對事件的敘述,深層是敘述的邏輯——關于事件的因果關系梳理與闡釋;使敘述邏輯及其闡釋得以成立的根據是關于事件的證據即史料。
然而在德國學者卡西爾看來,歷史作為插入人和過去之間的符號系統,不僅僅是證據和敘述;更重要的是這個符號體系背后隱藏的東西:
如果我們知道了編年史順序上的一切事實,我們可能會對歷史有一個一般的框架和輪廓,但我們不會懂得它的真正生命力。而理解人類的生命力乃是歷史知識的一般主題和最終目的。(6)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233頁。
對于編年史背后生命力的發現,卡西爾強調了赫爾德歷史觀的意義:
在歷史哲學的近代奠基者之中,赫爾德最清晰地洞察到了歷史過程的這一面。他的著作不只是對過去的回憶,而是使過去復活起來……正如歌德在一封信中所說的,他在赫爾德的歷史敘述中所發現的并不僅僅只是“人類的表皮外殼”。使他極度欽佩的乃是赫爾德的“清掃法——不僅僅只是從垃圾中淘出金子,而是使垃圾本身再生為活的作物。正是這種“再生”,這種過去的新生,標志出偉大的歷史學家的特征。(7)卡西爾:《人論》,第225頁。
此后,法國史學家米什萊也強調了歷史研究要使過去復活的觀點:“‘讓往昔復活’,這正是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之一。”(8)哈斯克爾:《歷史及其圖像》,孔令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378頁。歷史怎樣才會“復活”呢?米什萊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大革命之后很久,有位年輕人向上了年紀的梅蘭·德·蒂翁維爾(Merlin de Thionville)請教,如何才能讓自己去恨羅伯斯庇爾。這位老先生好像對他的舉動很遺憾,但接著猛然一振,“羅伯斯庇爾,”他說,“羅伯斯庇爾,只要你見過他的綠眼睛,你也會像我那樣恨他。”(9)哈斯克爾:《歷史及其圖像》,706頁。
在這段敘述中,歷史從事件變成了記憶中的現場——大革命時代的創傷通過羅伯斯庇爾的“綠眼睛”所留下的恐怖記憶再度觸動心靈而復活了。
稍晚于米什萊的荷蘭史學家赫伊津哈接過了米什萊“讓往昔復活”的觀點,他認為復活歷史的要素是“歷史思考中的審美元素”,(10)哈斯克爾:《歷史及其圖像》,第705頁。即包含著生動畫面和激情的歷史情境。在他看來,人們不是從研究文獻中而是從圖像的感知中了解歷史的。他在《中世紀的衰落》一書中對中世紀史研究的創新性在于,把歷史研究的重點從證據學轉移到圖像學,通過對藝術作品的圖像學分析、對當時社會公眾生活的儀式、風俗和激情的再現來重構歷史的生動情境。他在研究公眾活動場景時特別指出:
要想完全理解那個時期人們生活的話,就必須牢記這些極富感情色彩的公眾活動……現在的讀者,在研究那些基于官方資料的中世紀歷史時,是永遠無法充分認識到那時人們的情緒是多么易于激動。雖然官方的資料可能是最可靠的來源,但這些資料缺少一個內容,那就是無法充分地表達出王侯和老百姓皆有的熾熱的激情。(11)赫伊津哈:《中世紀的衰落》,劉軍等譯,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5-11頁。
在這段敘述中,赫伊津哈所關注的那些比官方資料更重要的“極富感情色彩的公眾活動”,正是歷史書寫背后的非物質文化層面。
實際上,早于赫伊津哈的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已體現出從社會生活習俗視野研究歷史的特點:“雇傭兵隊長和人文主義者的簡筆肖像,敘述簡練的復仇和惡作劇之類的軼事趣聞,表明詩人和歷史學家對待諸如風景、榮譽或者死亡之類各種題材的態度的引文等等。惡行,狂歡,英勇的壯舉、對榮譽的渴求,這些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全景中的組成部分。無數來到意大利的旅游者擠滿了佛羅倫薩、錫耶納和威尼斯的大街小巷,充滿他們想象的正是這些場景和事件。”(12)貢布里希:《理想與偶像》,范景中等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第50頁。
從鮮活的社會生活場景去感受和理解歷史,這種“復活”歷史的研究意圖是近代從事實的研究轉向風尚、習俗研究的一種趨勢。作為歷史內核的集體記憶研究也從客觀性延伸到心靈性。哈布瓦赫在研究集體記憶時,特別關注到那些不同于實證史料的非物質性記憶,如夢境,心靈體驗等等。他在研究基督教傳統時注意到宗教歷史的兩個傳承維度:教義取向(dogmatic)與神秘取向(mystic),“有時是前者占優勢,有時是后者占優勢,而且最終宗教產生于這兩者的妥協。”(13)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0頁。他把神秘主義和教義主義之間的關系稱作“鮮活的記憶和多少變為成規的傳統之間的關系”。(14)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第181頁。教義主義以教義經典的保存和闡釋為根據,屬于基督教社會的“大傳統”傳承。這種傳統多少變為固化成規的傳統,逐漸失去了宗教精神在后代社會持續傳承的內在活力。神秘主義者則是在心靈中自由地體驗宗教以構建自己所感知的直觀形象,通過自己的神秘直覺解釋經文,以從中發現與當下興趣相關的新的意義。
在哈布瓦赫看來神秘主義并不比教會傳統更精確地接近真實的過去。神秘主義的記憶對經義的解釋難以被主流經學所承認,更難以被史料所證明。然而它體現的是當時的人從圣經所獲得的心靈體驗,那種獨特的直覺屬于他們所處的時代,體現了當下的宗教精神需要,因此被稱為“鮮活的記憶”。對后代史學來說,這種神秘主義體現了每個時期人們的特定體驗。如中世紀的神秘主義所體現的就是中世紀人們對基督教信仰的記憶和心靈體驗。由此而形成了關于一代代人的心靈體驗歷史,這就是“鮮活的記憶”。
作為心靈體驗的集體記憶之所以能夠被傳承認同,就在于它是“鮮活的”,它是被直觀地看到、感知到的。被視為虛幻的宗教體驗,在建構特定社會的文化共識和情感認同方面卻又是實在的。通過“鮮活的記憶”所構建的心靈史是族群認同的歷史。這種心靈史的價值不在于考據意義上的客觀真實性,而在于它體現了某個文化群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心靈體驗和情感認同的凝聚過程。
從非遺保護的視角來看,包括宗教體驗在內的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其歷史性就在于集體記憶活化所形成的文化認同持續建構的過程。形形色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內涵,歸根結底都凝聚于集體記憶所蘊涵的情感共鳴和社會共識上,通過這種文化精神的凝聚力在現代世界形成了各種文化傳統的社群性、民族性認同。“鮮活的記憶”生產著想象的歷史,從而形塑起一個族群、一種文明的精神傳統——如美國學者安德森所說的“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安德森把現代民族共同體稱作“想象的”,是因為在他看來,現代民族共同體“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聯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15)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頁。這就是說,作為共同體精神內涵的民族文化傳統是一種使群體成員“相互聯結的意象”,即通過傳播交流而感知到的集體記憶表象。從這個意義上講,“想象的共同體”就是在社群歷史中持續存在和發展的活的歷史共同體表象,是社群歷史的活力和持續性的證明。
三、非遺保護的生態條件:后全球化文明
非遺學科的學理研究應當與非遺保護和傳承的操作相結合,需要把非遺學的學理思維邏輯和研究成果與非遺保護實踐打通,通過學理性的研究和深度思維解決真正要保護的文化內涵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實現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初衷。
非遺保護不僅僅是從知識與藝術價值角度認知、評價和保護文化遺產的活動,更重要的是與20世紀后期文化政治的全球化趨勢相關:冷戰結束后世界經濟、文化的全球化傳播與發展造成了全球文化的同質化危機。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提出承認文化多樣性,確保屬于多元的、不同的和發展的文化特性的個人和群體之間的和睦關系和共處。在宣言的基礎上開始的非遺保護關注的重點是多元文化政策,即為了抵制文化霸權而保護和發展處于弱勢的文化,尤其是對處于瀕危狀態的少數族群文化遺產進行搶救。美國人類學家薩林斯描述過一些人類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關于愛斯基摩文化即將消亡的警告:
移民到大陸上的甘貝爾村民“已不再是愛斯基摩人,不再是保有一種他們自己文化傳統的民族了。”這是那個時代人類學的一般見識,也同樣是預見家鄉社區最終要被涵化(acculturation)的補充性看法。(16)薩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銘銘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119頁。
這種關于土著文化和鄉土文化即將消亡的警告正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運動的認識和觀念背景。問題的重點還不是這些傳統文明正在消亡中,而是在于挽救這些文化遺產是否可能?在19世紀進化論和歷史主義觀念影響下,學者們多相信歷史進化的必然性和線性。按照線性的歷史進化論,傳統文明進入現代社會之后面臨的是不可避免的被拋棄的命運:“阿基里斯能夠同火藥和鉛彈并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并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繆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17)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頁。愛斯基摩人的雪橇、獵鯨生活當然會隨著整個族群向南遷移而消失,所以“不再是愛斯基摩人”了。在這個文化背景下對土著和少數族裔文化的保護似乎多在考慮如何建檔記錄和數字化,如何建立保存鄉土文化殘余形態的生態博物館等等,似乎是在對即將消失的文化進行某種臨終關懷式的保護、博物館化的保存和紀念性的追思。
薩林斯卻提出了與臨終關懷不同的相反觀點:“愛斯基摩人還在那里,并且還是愛斯基摩人……愛斯基摩人既變化得多,而同時又變化得非常少。”(18)薩林斯:《甜蜜的悲哀》,第119-120頁。他認為,那些原本屬于遠離現代文明的土著文化在與世界交往的過程中正在經歷著“現代性的本土化”過程:
最近幾個世紀以來,與被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所統一的同時,世界也被土著社會對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適應重新分化了。在某種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質性與地方的差異性是同步發展的,后者無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這樣的名義下做出的對前者的反應。因此,這種新的星球性組織才被我們描述為:“一個由不同文化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這是一種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組成的世界文化體系……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間……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現代性的本土化。(19)薩林斯:《甜蜜的悲哀》,第123-124頁。
薩林斯在20世紀末說當代多元文化的發展是走向“現代性的本土化”,似乎還難以令人信服。但自從非遺保護公約頒布以來,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意識卻在發生著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變化——逐漸從臨終關懷轉向“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組成的世界文化體系”建設。
傳統文化保護意識的這種變化意味著同質性的全球化正在轉向本土化的多樣性發展。但真正實現這種文化發展意識的轉向,需要非遺保護觀念在學理層次上的發展和深化:
首先是對“保護”這個概念的重新解釋——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概念是對物質性對象的固化保護,而非遺保護從物質性對象轉向非物質文化形態,保護的方式也從固化保護轉向活態保護,即通過介入參與使物質性對象成為具有意義的活動。
其次是從“遺產”的遺存觀念轉向傳承觀念——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一般意義上的遺產不同:它不是前代遺存之物,而是代代相承的社會生活內涵。
再次是歷史觀的演變——從線性歷史進化論所呈現的“現代性”當下對“本土性”過去的否定轉向“現代性的本土化”,即傳統文化對現代文化的吸收和再生。
總體上說,非遺保護的內容從尋求過去遺存的“本真性”拓展到發現和培育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活力,意味著當代社會文化生態的多樣性演化。非遺保護的學理研究中,如何認識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文化環境中的存在、傳承與發展狀況,重點就在于對當代世界文化環境中各種地方、族群社會的傳統文化如何繼續傳承發展的文化生態根據。
19世紀法國學者丹納是主張“研究歷史就是復活歷史”的史學家之一。他“復活”歷史的方法就是找到歷史生成的基本要素,發現其間的關系。他提出的文化傳統生成的基本要素是:種族、環境和時代。(20)泰納:《英國文學史》序言,楊烈譯,《西方文論選》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第236頁。
丹納所說的三要素可以抽象為社會、空間和時間,這是文化產生發展最基本的生態要素。可以說他是在20世紀文化生態學創立之前就開始從文化生態視角研究歷史的學者。依據對特定種族生活方式、環境影響和歷史傳承積累的分析,他從物化形態的藝術品和史料中解讀出鮮活的生活和生命歷程。他這種研究方法受到了赫爾德和溫克爾曼關于文化史、民俗史和藝術史研究的影響。對于今天我們解讀歷史的文本仍然有重要意義。
但在今天的非遺歷史研究中,丹納的文化生態史三要素觀念面臨著重大挑戰,就是文化生態在當代的蛻變問題。
如果把人類征服、改造自然以獲取生活資源的能力達到爆炸性水平的工業文明視為人類社會生態的一個頂峰,那么從工業文明到后工業化時代,人類社會的文化生態則發生了顛覆性的演變。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文化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提出了“內爆”(implosion)的概念:從身體在空間的延伸轉向中樞神經系統向全球的延伸,(21)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0頁。即智能空間的發展在逐步取代地理環境。到21世紀初,美國社會學家卡斯特提出當代城市社會中“流動空間與地方的張力與結合”(22)卡斯特:《21世紀的都市社會學》,劉益誠譯,《國外城市規劃》(京)2006年第5期。,意味著當代文化生態正在經歷著根本性的轉換。
新的文化生態正在建構新的歷史關系——這正是非遺歷史研究所要面對的新問題。簡單地說,就是從丹納的“族群/環境/傳承”生態三要素轉換為“跨域群體/流動場景/智能傳播”這些新生態要素的歷史性演化——與特定文化傳承相關的群體從傳統的社區群體擴展到網絡社交群,傳統社群所依附的自然環境轉換為跨域生活的流動場景,族群共同體的歷史傳承被智能化分形化傳播網絡切割和改造。(23)參考高小康《社群,媒介與場景:非遺活化三要素》,《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1年第1期。
從丹納的歷史文化三要素到當代新生態要素,這種轉換的歷史背景是全球化轉向后全球化文明的時代文化特征。20世紀后期,以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義強調的是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對抗,或者說是“為承認而斗爭”(24)霍耐特:《為承認而斗爭》,胡繼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頁。。但生態多樣性存在的基礎不是對抗而是多樣性的共生。從雅斯貝斯把全球文化發展史區分為三大軸心文明至今,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是不同文明日益走向全球性聯系,走向麥克盧漢所說的“地球村”。但同時全球的文化形態及其生態界限又在不斷分化中:從文明類型到民族國家,地域族群,社區,代溝,粉絲圈……一層層分化和裂變。當代生態系統的復雜性不僅在于多樣性,更重要的是隨著信息傳播的發展而產生的多維和多質性演化。從芝加哥學派的區位空間生態到移動互聯時代的信息生態之間是一個世紀文化生態發展演化的歷史——從“全球分裂”到全球分形(fractal),即趨向不規則多維化自組織發展的文化新生態。
這種文化新生態的意義一方面在于對小生態自足性的保護防止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剝奪;另一方面通過大的生態關聯來消解斷層線對抗的危機——每一個特定的文化生態群落既需要保持自己的群體歸屬感和內在活力,同時又要構建與整個生態環境的相互性開放關系,即全球沖突下的文化互滲與互享關系。這是非遺保護的總體生態背景——后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新生態:在全球沖突背景下通過文化多樣性保護與互享重構人類文化共同體發展的理論愿景與實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