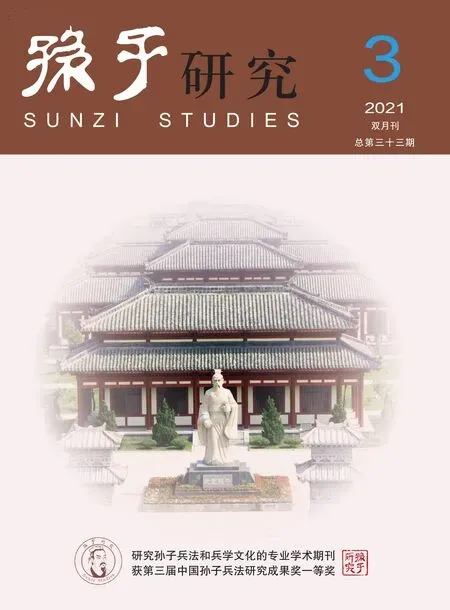先秦兵家軍事倫理思想探要
——兼辨傳統和當代軍事倫理思想的關系
張 申
軍事倫理學在我國作為倫理學研究領域中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分支并被應用于實踐及學術研究,至今已走過了30 余年的發展歷程。總體來看,大多數學者認為它的對象和基本問題就是軍事道德問題,然而究竟在什么范圍、何種意義以及在何種價值取向上研究軍事道德,一直未有定論。此外,在對其研究對象的具體認識和學科體系的構建過程中,學者對軍事倫理和“國防倫理”“軍人倫理”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理解上和軍事倫理與軍事法、軍事保障等區別和聯系等問題上也一直未能明確其概念和范圍。同時,隨著相關研究的不斷展開,近年來出現許多冠以“軍事倫理”之名但實際上超脫了軍事倫理研究的范疇,雜糅進許多牽強附會之說,亟須為之正名。
一、軍事倫理之真正內涵
研究軍事倫理學,首先要弄清它的研究對象。軍事倫理學相較于倫理學其他分支的應用和研究,其區別在于深入人類社會戰爭現象、軍事活動以及相關環境,體現了人類倫理文化的一個獨特視野。〔1〕顧智明等指出軍事倫理學是研究軍事道德的本質及其起源、發展和社會作用的學科。〔2〕趙楓也持這種觀點,認為軍事倫理學就是對軍事道德相關問題的研究,但要注意軍事道德和一般社會道德的區別。〔3〕而王聯斌則從“武德”角度對軍事倫理學的意義進行了發微,他解釋道,中國軍事文化古老而文明,中國是崇尚道德的國度,故在軍事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就融入了禮儀之邦的文明。〔4〕武者,止戈為武,武是停止干戈、消停戰事的實力。德,以仁、義為核心理念,以上、止、正為行為操守的言行舉止。所以,其表述雖然看似是以“武德”這個比較獨特的視角,但其論皆本仁義而重德,實亦未脫道德概念之范圍。國內倫理學界普遍認為倫理學的本質是關于道德問題的科學,是道德思想觀點的系統化、理論化。或者說,倫理學是以人類的道德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而軍事倫理學同時跨越軍事學和倫理學,是一個二者交叉兼容的新學科。
雖然倫理學和軍事倫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都是與道德相關,但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中國古代傳統軍事倫理思想尤其是先秦兵家的傳統軍事倫理思想時,不能以當今對于道德定義的理解簡單地帶入到先秦時人的思想中去。在研究和考察時,不僅需要注意古今異同,還需要辯證地看待這種區別和繼承的關系。因為在中國倫理學史上,道德既可以看作一個整體概念,又可以說是兩個獨立的概念。道是指行為上應該遵循的原則,德則代表了實際所體現的行為原則。而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時,道德不僅代表行為原則而且也有其具體運用。張岱年認為道德不僅是思想觀念,而且必須有其實際的行為。若只有空言徒事談論,行言不一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德。且就倫理而言,自古以來不僅有倫理思想,更有倫理實際,倫理實際就是社會的道德風尚和個人品德風范的綜合。〔5〕張岱年指出,倫理學又可稱為道德學,主要是研究道德原則和規范的學說,如《論語·述而》:“至于道,據于德,依于人,游于藝。”道指代行為應該遵守的原則,德則是道在實際的體現,其他諸子最先亦是道、德分稱而后合為一詞,釋義又有與儒家不同者。說明在先秦時,道與德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是有內涵差異的兩個命題,同樣在軍事倫理學相關問題的研究中亦須注意。
蘇秦說齊宣曰:“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后。”(《戰國策·齊策一》)可見諸國地方守御之兵,都已征發出去充作戰斗軍隊了。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全國皆兵的時期,怕莫若此時了。戰爭一方面倒逼了道德的發展,但戰爭對道德的發展同樣有阻礙的作用。雖然戰國時期有著軍事倫理發展的時代和歷史背景,兵家也有執行道德倫理的權利,但戰爭至此時已發展到了關乎國家危亡的劇烈程度,所以勝利才是作為一名將帥最基本的追求。同樣,哪怕是一名最普通的士卒,最強烈的愿望也是追逐勝利,因為只有戰勝殺敵才能獲得土地、財富和奴隸,“庶人之有爵祿”〔6〕。對勝利的追求在戰國時代已可稱得上是“上下同欲”。當上下同欲時,就形成了勢不可當的歷史大勢。換句話來說,或換個角度來看,世諺有云“成王敗寇”,最通俗來說,戰勝者就是合法的,失敗者就是非法的,戰勝一方可以繼續執行他的理論實踐及其思想,而若戰敗,不僅使國家危亡,而且其理論、其思想更會隨波湮沒。所以,道德在勝利面前,起碼在戰國而言,是“不值一提”的。
那么戰國時代的戰爭是否有倫理道德的約束呢?抑或是戰國兵家最重倫理呢?起碼在戰時,人們的認識里應該是沒有的,《漢書·藝文志》曰:“兵家者,王官之武備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韓子亦云:“戰陣之間,不厭詐偽。〔7〕”首先,軍事戰爭首重勝敗,尤其是在春秋“泓水之戰”后,兵不厭詐的理論早已深入人心,宋襄公“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和“不鼓不成列”的“道德式”戰爭不僅成為后人的嬉笑談資,“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于古為義,于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8〕,眉山蘇先生古史評之亦以為可笑之甚,而且標志著自商、周以來以“成列而鼓”為主的“禮義之兵”退出歷史舞臺,意味著西周軍禮和古典軍事倫理的實際終結,昭示著新型的以“詭詐奇謀”為主導的作戰方式的崛起。其次,“義戰”性質的戰爭逐漸變為“率獸食人”的野蠻兼并。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孟子認為春秋時期就已經沒有了合乎于義的戰爭,但春秋時各國尚且要“尊王攘夷”,起碼在政治上還需借助于周天子的大義和名義,奉行的是合諸侯、朝天子的爭霸戰爭,尚且有宋襄公這種愚蠢的仁義戰爭。而進入戰國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9〕,戰爭形式也變為以兼并和統一為目的,不僅在實際上打破了周天子名義統治下的禮法制度和政治體制,而且也徹底摧毀了在舊體制和禮法保護下存在的道德體系。此外,兵家最事功利。兵家最重實際,故從不諱言利,尉繚認為軍隊務要“發能中利,動則有功”,所以兵家看待問題的出發點都是“視利害,辨安危”,選賢任能也要“不時日而事利”。在看待“利”這個問題上,孫武與尉繚高度一致,武子所說的“以利動”,也是指從事戰爭應當以利害關系為最高標準,有利則打,無利則止,一切以利益大小為轉移。“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這些都是兵家的用兵原則。事利思想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因為它從根本上劃清了與《司馬法》為代表的舊“軍禮”的界限。〔10〕
由此來看,起碼在戰國兵家的戰爭觀中,倫理道德還尚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到了全社會都重視道德的今天,戰爭也是道德難以觸及的盲區,更遑論數千年前。而在近年來的軍事倫理學相關研究中,倫理學似乎有成為“萬能”的趨勢,其表現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無論中外,言必稱軍事倫理,如《荷馬史詩的軍事倫理思想》《伯利克里的軍事倫理思想》《黑格爾軍事倫理思想論析》等;第二,無論古今人物,皆言其軍事倫理思想,如孔子、老子、孟子、荀子、管子、諸葛亮和孫中山等人軍事倫理思想的研究論文;第三,不論古今兵書,必言其軍事倫理思想,如論述《六韜》《商君書》《呂氏春秋》《司馬法》《尉繚子》等兵書的軍事倫理思想,以上皆為王聯斌一人所著。夸張的是,軍事倫理思想的相關研究論文雖然較少,但王聯斌一人所發表的論文就占據了將近總量的一半,而且絕大多數都由同一期刊所發表,且這一期刊連續數年每期必有王聯斌的軍事倫理思想研究的文章,甚至在一期就有不止一篇。
二、軍事倫理學內涵探要
明確界定軍事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建構其學科體系的關鍵和基礎,直接關系到它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創設、發展和實際應用前景。目前已形成的共識是認為現代軍事倫理學在我國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屬于應用倫理學范疇。現代軍事倫理學是研究涉及軍事領域道德相關問題的專門學科,不僅涉及軍人主體自身的道德建設問題,還廣泛地研究戰爭與和平、熱核戰爭與常規戰爭、軍隊建設、國防教育,以及利益集團、政府以至世界范圍內的許多與軍事有關的道德問題。〔11〕在對軍事倫理學研究對象的具體認識和學科體系的構建過程中,對“軍事倫理”“軍人倫理”“國防倫理”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理解,至今尚有分歧,主要有三種觀點。
首先,什么是倫理?戰國時人對倫理的理解與今人有何不同?老子認為道為萬物本原,將德看作是天地間萬物的本性。由此看來,道德是指體現在個人行為中的普遍的道德原則,更多地意味著個人的德行。倫理一詞見載于《禮記·樂記》,“樂者,通倫理者也”〔12〕,鄭玄注曰:“倫,類也。理,分也。”“倫”多代表人跟人之間的關系,形成了“人倫”;“理”的本意為治玉,后來引申作分理意。二字連用時,后來常指人們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所遵循的準則。所以說倫理更多代表了社會倫理,龐樸根據出土的郭店楚簡,也認為古代儒家思想有個體道德和社會倫理兩部分,道德趨向于主觀的個體道德,更多代表了實際的道德行為;倫理則意味著對客觀社會關系的調整,有較多的理論趨向。〔13〕以此來看,就倫理本身而言,其實就包含了個體與個體、社會關系調整兩層含義。
有學者認為倫理即道德即先秦之軍禮,并通過對《司馬法》內容的考察后認為其所言軍禮雖然兼指法與道德,但其實還是更多的指道德而言。他還就此指出,《司馬法》亦有將禮與法通用的跡象,所謂司馬之“法”,也可稱之為司馬之“禮”。〔14〕其實這種說法雖然看似無誤,但還需斟酌,因為軍禮有軍法之意,但禮并不同于軍法。《左傳》載“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楊伯峻注曰:“軍禮猶言軍法也。”〔15〕軍禮尚有“禮儀”之意,“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漢書·周亞夫傳》);軍禮還有軍事典禮的意義,在周代一年四季的軍事操練,春季的叫作振旅,夏曰茇舍,秋曰治兵,冬稱大閱,這些都被稱作“軍禮”。〔16〕軍禮亦有師旅操演、征伐之禮的含義,作為周代“五禮”之一的軍禮,其存在的主要意義就是“以軍禮同邦國”〔17〕,即以大師之禮征伐那些不馴服的諸侯。所以軍禮雖然與軍法關系密切,也具有一定軍法的意義,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軍事法。此外,周代軍禮產生時就與一般意義上的禮制存在較大差異,必須加以區分而不能隨意混淆,所以對于軍事倫理思想的考察和研究,就要先弄清軍禮、禮和倫理之間的辯證關系。
周代立國之初,為配合和維護宗周統治的“封藩建衛”等政治制度,以周公旦為代表的統治者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全面革新,將上古至殷商的禮樂進行大規模的整理、改造,創建了一整套具體可操作的禮樂制度,包括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均納入“禮”的范疇〔18〕。“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史記·周本紀》)使其成為系統化的國家典章制度和具有實踐可能的行為規范,并形成了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禮樂文化,即禮樂成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領域的重要文化結構,并在其統轄范圍內全面推行禮樂之治。
禮樂文化及其制度不僅規定了個體的權利和義務,也調整了當時宗法制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關系,是“祀”在政治上全面且系統的制度化。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反映在軍事領域,則在以禮樂文化為指導的制度框架下形成了相輔相成、互為保障的軍禮,并以軍禮為指導,形成了相應的符合其時代特色的軍事道德。因為軍隊道德建設離不開一定的道德環境,道德環境能夠形成道德群體效應、輿論效應和示范效應,而軍事倫理學的創新和學科建設,則直接源于軍事主體的道德實踐,服從并服務于軍事主體的道德實踐。〔19〕道德環境的形成仰賴政治上的安定和統一,大一統中央政權統治力的強弱直接關系并影響道德環境穩定,進而影響并關系到軍事領域禮制建設。換句話說,軍事倫理的應用和教育具體表現為倫理道德規范的理論確立和實踐遵行,其前提是政治制度的統一和穩定,軍事倫理本身可以看作是具有強制性的道德規范, 是“道德”成文了的法,也是道德律令。在統一中央政權走向沒落并解體的過程中,軍事倫理同樣在逐步瓦解,其解體的時間的過程稍后于政治體制,但軍事倫理之建立亦在政治制度重新確立之后,以為新的軍事倫理規范必須直至大一統政治制度建立之后方能重新確立,并以國家的強制力來保證實施,亦是該政體意識形態在軍事領域上的反映。
春秋時期,雖然有人認為當時的禮樂制度已經開始崩壞,但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在政治上依然具有較強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相應地,反映在軍事領域,則突出表現為西周軍禮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得以延續,如在軍事上對尊貴身份的尊重以及重視其作為軍事統帥的影響力。上博簡《曹沫之陳》載:“人使士,我使夫大夫;人使夫大夫,我使將軍;人使將軍,我君身進。 此戰之顯道。〔20〕”“人使將軍,我君身進”,其含義并非要求君主必須以身作則、身先士卒,而是重在強調分封制下國君本身的權威,因為在時人看來身份愈貴重,其作為將帥的影響力愈大,所以曹沫認為國君最好能作為直接將兵的統帥,因為只有國君親自領兵作戰,才能保證軍隊的和諧。〔21〕此外,在秉承周禮的宗法制下,貴重的身份和地位不僅為本國人尊崇,也為其他諸國所尊崇,這是周天子政治影響力尚存和政治體制尚能維系的體現,也是周禮在軍事領域仍然發揮作用的具體實踐。如鄢陵之戰時晉國將軍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且對楚使“三肅使者而退”。晉國將軍韓厥以“不可以再辱國君”為由,停止了對鄭成公的追擊;同時,郤至以“傷國君有刑”,亦停止追擊鄭成公。這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仍然是典型的重視血緣關系的宗法社會,在軍事領域仍然是尊奉周禮并以軍禮來指導戰爭實踐。《左傳·成公二年》楚救齊,“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昭公二十三年吳楚爭,楚“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皆是其證。
軍禮不僅是周禮在軍事領域的反映和實踐,同時也是政治體制的保障。《呂氏春秋》言:“古圣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22〕且軍隊代表的是國家的威嚴,而威嚴就是國家的力量,“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所以“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周天子令行諸侯,就是因為有強大武力作為后盾以確保其政令得以在全天下貫徹執行。西周時期有兩支常備軍,一曰宗周六師,屯駐于都城鎬京;一曰成周八師,戍守成周。實際上,西周立國之初,周室為了有效遏制諸侯勢力,設立了以宗法制為核心的各項等級森嚴的制度。當然,如果宗法制度沒有強大武力作為保障政策執行的支撐的話,那么“周禮”所規定的一切便會成為一紙空文,“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23〕。因此,為了保持對下和對外的軍事威懾,周王室便常備宗周六師、成周八師,來應對諸侯以及邊患問題。春秋時期,周天子直接控制的軍事力量持續衰弱,故五霸迭興。“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諸國互相征伐后勝者即為霸主,而維持霸主地位同樣要依靠強大軍事實力進行威懾甚至戰爭。“五霸”尊勤君王、攘斥外夷,歸根到底還是霸主利用強大軍事實力來約束各國尊崇周王的權力并維護周王朝的宗法制度。而進入戰國后,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等事件和戰爭形勢由爭霸轉為兼并統一為標志,不僅表明周天子統治力的實際性衰弱,而且昭示了西周以來禮的秩序已全面崩潰,進入到“戰國相攻,大伐有德”的兼并時代,而軍事道德的建設又離不開穩定政治統治下有序的道德環境,所以在戰國特殊歷史條件下,并無軍事倫理生存和發展的土壤。
西周以來的禮制和軍禮秩序在進入戰國后全面崩潰,時人對于統治方法的爭論也日趨激烈,即“王霸之辨”。王道和霸道在本質上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政道,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平方略。當時概以仁義治天下為王道,以武力結諸侯為霸道,故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稱美三代,認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而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則主霸道而貶王道。秦國在商君主持變法行“霸道”后迅速崛起,法家思想和霸術則在秦國開始政治實踐并獲得階段性勝利,結果就是最終秦掃六合而四海一,表明了這是一個霸道戰勝王道的戰國時代。而儒家王道思想理論終戰國一世也未能成為任何一國的政治實踐。雖然歷代政權實行的一系列國家政策的內在指導思想是內法外儒,“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但自漢武帝時儒學定于一尊后,王道政治至少獲得了外在與形式上的“正統”地位。同時,孝武卓然罷黜百家也標志著戰國以來用來約束社會各階層的禮制崩壞后,倫理的重新法制化。法儒二家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不斷地結合、互濟,儒家為專制統治披罩了一層倫理勸導的仁德外衣,法家也為表面上的仁德統治提供了法律保障,故《中華文化史》指出:“政治事功與倫理勸導是中華文化所講求的并行不悖的兩大核心內容。”〔24〕在政治倫理重新確立后,軍事倫理也在政治倫理的指導下形成,又因政治倫理的延續性,所以兩千年來中國傳統軍事倫理思想均是在儒家政治倫理的框架下繼承和發展的。
也有學者認為,武德就是從武、用武的德行,指的是軍旅生活中的一切道德現象及其與軍旅生活相關的道德活動、品質和意識以及價值觀念的總和,武德思想及實踐是其兩大主要構成部分,亦稱軍事倫理思想。但經考先秦文獻,雖然該詞原義及內涵較為豐富,但是否有指代軍事倫理之義則值得商榷。“武德”一詞,最早見于《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莊王言:“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武之有七德,既是古人對戰爭本質的深刻認識,也是對戰爭目的和作用的總結和企盼。春秋時人認為,正義之戰爭應是禁止強暴、消弭戰爭、保持強大、鞏固功業、安定百姓、調和大眾、豐富財物,古人稱其為七德〔25〕,其中禁暴和戢兵是對戰爭正義性質的定義,保大、定功與安民是王者之軍的理想追求,而和眾并豐財則不僅既是王兵所追求的目的,而且是仁義之兵的前提和保障。
和眾、豐財之所以是興軍伐亂的前提準備,是因為王兵能使士大夫不離其官府、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非霸國“臣妾人之子女、利人之財貨”的掠奪之兵。春秋以來,隨著列國改革的不斷深入,如齊國“相地而衰征”、晉國“作爰田”、魯國“初稅畝”、鄭國“使田有封洫”、魏國“盡地力之教”和秦國“廢井田、開阡陌”等,以至戰國時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已開始成為社會主要矛盾,而社會生產又是人口繁衍、物資供應、親睦百姓、財政充裕和國家富強的基礎和條件。〔26〕“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漢書·食貨志》),故在農業為主的戰國社會,保障民眾生存和基本生活的目的歸根到底是要維持農業生產和再生產,是緩和社會矛盾和維護統治秩序的必要手段。同時,戰國時因列國間連年征戰,劉向云“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和尉繚言“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就是當時最現實之寫照,這就更加劇和擴大了原有社會矛盾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如此,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和持續時間更久,對后勤保障的要求也就隨之提高,孫武“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和尉繚“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皆有詳論。統治階級為了穩定社會秩序、減輕民眾損失和促進國力提升,建立與社會和時代背景相適應的保障措施已迫在眉睫,當國者吸取那些亡國之君的教訓,業已知安撫百姓對于鞏固統治和緩和社會矛盾的重要性。戰爭的不斷發展倒逼了社會保障思想的萌芽、發展和實踐,而社會保障的實踐又為戰爭的進一步加劇創造了條件,由此可見保障和軍事二者互為促進。
普遍社會保障是軍事倫理思想形成和實踐的先決條件,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也認同這種現實。“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27〕孔子回答子貢問政的話,可以說基本反映了儒家治政的思想。自古人皆有一死,但民無信則不立,故三者中依次可去兵去食,但民以食為天,民無食不成兵,所以說在孔子看來,社會保障是軍事戰爭進行的前提。而孟子在面對梁惠王“何以利吾國”詢問中亦給予了“王何必曰利”的斥責。《史記》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史記·管晏列傳》),雖說禮、義、廉、恥的倫理如果不大加宣揚,國家就會滅亡,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28〕,在民眾衣食尚不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與之談禮節榮辱是不現實也是行不通的。
對于倫理學中道德評價標準的問題,至戰國時發展成關于道德行為與物質利益的關系問題的爭辯,即著名的“義利之辨”。雖然至戰國時儒家學派已有較為完整的義利學說并發展成了系統的思想體系,但終戰國之世儒家思想也未有其思想理念之政治實踐,亦未被諸國統治者所接納。由此可見,儒家等學派的治政思想雖然更為符合國家社會的道德價值取向,但這些往往側重于和平時期的治理,是通過理想的理論操作并依靠大一統政權的統治力來確保實施的。而兵家則不同,兵家非常注重功利,主張不為無利之事,一切行為皆以利益為中心并且貫穿著其軍事行為的全過程。〔29〕兵家是戰國百家中最講究現實實際的一家學派,其一切行為和手段都圍繞著一個清晰的戰爭目的,那就是成勝立功。兵家是一種實用學說,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和可操作性,戰國兵家的一大特點是軍國兼治。特別是在大爭之世的戰國,兵家更清楚軍隊在國家政權的角色和職能,對內維護統治者,對外實行軍事擴張,故從兵家的軍事倫理價值取向上看,戰爭的最高價值形態是“國家”和“民眾”的利益,也就是以保大、定功、安民為最高價值取向,“兵”是和眾、豐財的手段,禁暴、戢兵是“兵”的目的。在這一過程中,戰國兵家不僅不諱于言利,而且還重利。
以《孫子十三篇》成書為標志,“兵以詐立”思想的提出昭示著兵家重利思想的形成并開始應用于軍事實踐。先秦兵家視兵為生死存亡之道,生死存亡的現實要求,使兵家大膽揚棄了“仁義勝甲兵”的軍事倫理思想,強調主要利用武力的對抗,以獲取最大的戰爭功利。〔30〕孫子以利為本的軍事理論,其所說的本并非本體之“本”,而是根本之“本”,也就是認為“利”為戰爭之根本價值。而強烈的關乎利害得失的憂患意識,就是其軍事倫理思想的出發點與歸宿。〔31〕《九地篇》《火攻篇》均可見“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的論述,其中以《火攻篇》最具代表性:“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此安國全軍之道也。”〔32〕戰爭可看作是國家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矛盾總爆發,其用兵目的是要達成利益的再分配,故兵書為利而生,因利行兵,由兵求利〔33〕,杜牧注解《孫子兵法》時亦云“計算利害是軍事之根本”〔34〕。在《尉繚子》一書《戰威》和《武議》兩篇中,也重復并著重論述了“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同《制談》篇“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表達的意思一樣,這些都是尉繚以實際之利來指導軍事行為的一種功利態度,帶有極強的功利色彩。吳起也認為軍事謀劃的目的就是為了趨利避害,即“謀者,所以違害就利”〔35〕,而且吳子也將“爭利”作為戰爭的起因和目的之一,“吳起殺妻”的行為更能直觀具體地體現他功利之心態。《六韜》“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表達的同樣也是重利的價值觀,又借姜太公之口指出“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將以利為先看作是人的本性之一。兵家的功利價值觀,首先體現為以求利作為一切軍事行動的直接目的,同時還體現為以利益的多少和有無作為指導軍事行動的標準。有鑒于此,有學者指出周禮傳統與時代的脫節,在軍事領域最為明顯地體現出來,這就促使軍事思想向著功利化的方向轉變,兵家也因此成為先秦最早提出并實踐功利主義思想的學派。〔36〕
春秋以來尤其是進入戰國時代以后,各種社會關系急劇變化,新出現的許多新問題亟須解決,百家爭鳴學術局面的形成正是動蕩和急劇變革的時代特征在思想界的反映。在原來維系社會秩序的禮制和軍禮崩潰后,對于功利和道德的關系及其評價標準等問題,也逐漸被各學術流派所重視,代表各階層、階級和政治力量的主張和理論學說互相碰撞和詰難,形成了涉及思想政治文化領域的“義利之辨”,并且這種論辯的矛盾性在戰國兵書中的反映更加明顯。如吳起之為人,“貪而好色”“節廉而自喜名”,但為拜魯將“欲就名”而殺其妻,可見在其心中名利甚至大于所愛,后又在與魏武侯問對時大談仁德,云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險。……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不僅是兵家現實性的表現,也是對于在道德標準尚沒有統一評判標準時矛盾性在思想上的顯現。
而這種矛盾性在尉繚軍事思想上表現得更加明顯。首先在戰爭觀方面,《尉繚子·武議》云“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令上》又云“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如果單看這些,那么《尉繚子》所體現的戰爭觀是合乎儒家所倡導的道德標準體系的,但其又主張軍隊行止要“發能中利,動則有功”,舉賢任能的標準也是“事利”,好像又回到了法家的重利思想中去。其次在對待交戰國民眾的態度方面,尉繚一方面提倡在戰略上要“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要注重社會保障的執行,“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一方面在實際戰術上又無所不用其極,“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 ,各逼地形,而攻要塞”〔37〕。此外,在對待士卒的態度方面,尉繚一邊力倡“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在軍隊中營造親如父子兄弟之情,“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一邊又施行峻法嚴刑來約束部下,認為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要使士卒畏懼將帥,“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尉繚于其兵書《尉繚子》中詳述了督責士卒之法令,其中有誅殺之法〔38〕,以致宋明時人多有批評其書者,指出“督責諸令刻深儼秦法”〔39〕,《周氏涉筆》亦曰“《尉繚子》言兵,理法兼盡,然于諸令,督責部伍刻矣”〔40〕。
從傳世戰國兵書著述來看,即使是最具實踐性的兵家,對道德的評價標準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衡量尺度。當周代的禮樂統治秩序逐漸崩壞后,原有的制度規則對涵蓋政治、軍事、文化和地理等范圍內的“天下”“四海之內”中所有的社會關系失去約束,戰爭因此而興并加劇了這一破壞的過程。與這一時期相似的歷史循環如中唐以后,在儒學遭遇危急后原制度秩序漸次崩壞,章炳麟評其曰“中唐以來,禮崩樂壞,狂狡有作,自己制則,而事不稽古”〔41〕。非大一統時期或歷史割據時期,軍事及政治立法權下移,軍法、行政法多具有臨時性和復雜多變性,而且是將帥、割據者個性化的體現,帶有將帥個人主觀色彩,本質上講是唯心的、是沒有物質基礎的。就軍事倫理而言,在戰國時期并沒有形成實際上被各方公認的、具有約束性質意義上的統一標準,戰國兵家軍事倫理多因將帥而異,復雜、多變又具有臨時性,且很多道德評價標準尚停留在理論階段而無法付諸實施,也有一些因與成文之軍法存在沖突而不具有約束性。如《六韜》對將帥德的要求提出了“五材十過”的標準,“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孫武在其兵書首篇即說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吳子則指出為將者要具有“五慎”的品德,即“理、備、果、戒、約”;《司馬法》在道德教育的內容和目的問題上指出軍事道德教育的內容是禮、仁、信、義、勇、智六德〔42〕,“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自古之政也”。而《孫臏兵法》對于為將道德要求,學者們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孫臏將帥道德修養理論是“以義、仁、信、智、忠、敢、勇為綱”〔43〕,也有人認為孫臏的武德修養要求是“信義德智”者〔44〕,還有人認為“忠、信、敢、智、勇”是其武德之要求〔45〕。無論如何,在“戰國相攻,大伐有德”的現實條件和“禮崩樂壞”的歷史條件下,當時天下范圍內的確沒有一個統一的道德評判標準。直到漢朝武帝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在新的政治指導思想下重新認識德與法的關系并確立新的、統一的道德評價標準,進而肯定道德教育在軍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對后世產生了深刻影響。細化到軍事倫理思想層面,這一過程可看作是漢朝統治者從認同儒學倫理價值觀到確立儒學倫理為正統的轉變過程。
三、傳統軍事倫理思想的真正內涵
常言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對于先秦兵家的評價,有人認為孫武、孫臏是先秦集兵家之大成者〔46〕,有人認為《六韜》是先秦集兵家大成之作者〔47〕,還有人認為尉繚乃是之者〔48〕,甚至評價尉繚是先秦兵學的最后一位大師〔49〕。若從對先秦軍禮和武德軍事思想繼承和發展的角度來看,尉繚無疑才是戰國兵家中的“集大成”者。繚書中也提到了“武德”的概念,并明確指出了順應戰國時代大勢的武德內涵——“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尉繚之論禁暴,“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對戰爭性質進行了道德層面的定義;其論戢兵,在利益收支的角度對戰爭進行了分析,指出“戰再勝,當一敗”,告誡統治者和將帥要以慎重的態度來審視戰爭的破壞性;其論保大,提倡以威服天下而非力交,盡量避免實質上的殺傷,“國車不出于閫,組甲不出于橐,而威服天下矣”;其論定功,在戰國初期就預判了“分久必合”的時代發展走向,并以大一統為兵家的歷史使命和責任,“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其論安民,認為是治政的最終目標,“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其論和眾,調和四民大眾,勸諫統治者“今良民十萬而聯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力圖改變“千金不死,百金不刑”的階級分化現狀,認為制度乃為政之要,“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繚書《原官》章就是尉繚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對為政者進行了約束和限制,并對“臣下”和“主上”以及四民之職責進一步明確;其論豐財,亦不出其農戰的軍事思想,“夫在蕓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積蓄”,指出“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是最理想的豐財狀態,并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儲蓄思想。〔50〕
繚書卒章有“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句,當代學者對“殺”字釋義的爭論,在對過去學者意見延續的同時,也進行了橫向和縱向的拓展。概括說來,除原有“誅殺”“殘殺”的釋義之外,又有了“甘愿犧牲和戰死”、裁減和減省、克敵和殺敵等觀點。〔51〕明人歸有光輯評、文震孟等參訂的《諸子匯函》即認為尉繚所言殺士卒乃誅殺己方士卒,此說極具代表性,并以此責斥繚書立意“慘刻太甚”〔52〕,但若結合本篇上下文句、成書的歷史背景以及當時的戰爭情況來看,明顯與尉子的本意相去甚遠。通過考察尉繚所生活的時代背景、戰爭中人員戰損情況與后勤保障等,認為此處“殺”字應理解為“對敵方士卒的殺傷”。正確理解該書《兵令下》篇中殺士卒“殺”字的寓意,對進一步研究這部先秦優秀兵書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殺”字本意的考察,不僅是研究《尉繚子·兵令下》篇的前提,更是研究考察整部兵書乃至魏惠王時期魏國以及整個戰國中期社會的軍事、政治的基礎。
管仲相齊桓,齊因而成五霸之首。孔子贊稱管子:“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論語·憲問》)子貢、子路等因管仲起初助公子糾爭位于齊桓不成又轉而相齊桓為不仁,并非議之,孔子對此非但不以為然,而且連稱其仁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并贊其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朱熹注“不以兵車”曰:“言不假威力也。”這與孟子所謂的“以力假仁者霸”的霸道正相反,但是在孔子眼中,管仲之“不忠”于公子糾相較其有功于國泰民安,二者高下立判。因管子相齊助齊桓尊王攘夷功不可沒,因此可知管子相齊實有王道之風,故孔子贊之。〔53〕
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國藩在給部屬彭玉麟的信中說:“鄙意克城打仗,總以能多殺賊為貴,遠如九江、安慶之役,近如金柱關之捷,誅戮最多,賊中至今膽寒,去歲春夏間,所克地方未甚殺賊,當時頗切隱憂,來書深恨未能痛剿,實與鄙見相符。〔54〕”他要部將士卒對敵人不要存在憐憫之心并充滿 “恨 ”意,不能因殺人過多而生有悔意。他與部將言“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此賊之多擄多殺,流毒南紀;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雖使周孔生今,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咸豐三年(1853),曾國藩在與張亮基的信中說:“只以時事孔,茍利于國,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為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于將歇。〔55〕” 將“茍利于國,或益于民”作為他所作所為和湘軍軍事行為的最高價值目標,將其作為衡量軍人價值大小、軍事行為正當與失當的根本標準,與我國傳統的用兵在于“安國保民 ”思想一脈相承。周濤也認為“克城以多殺為妥”亦不影響其仁民愛民的軍事人道主義。〔56〕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指出:“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57〕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再如1942年4月13日毛澤東召集“魯藝”的一些教師座談,談到打仗時,我們正在追擊敵人,這時我們身邊的同志受傷了,倒在地上了,我們到底應該停下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還是應該繼續追擊敵人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我們認為還是應該追擊敵人,把敵人消滅,完成戰斗任務以后,再回來照顧受傷的同志。〔58〕毛澤東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明確提出了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軍事道德行為評價標準,并充分肯定了它的人道主義價值。這種軍事行為,既體現了消滅敵人與保存自己的辯證關系,又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道德要求,因而是一種“善”的行為。〔59〕
由此可見,軍事戰爭中的“多殺”,并不能一定代表“非仁”,更不能影響戰爭正義的性質。西方中世紀的正義戰爭大體要滿足三個條件:戰爭要由一個法定的權威人士來宣布, 戰爭必須以正義事業為目的,戰爭必須出于正義的基督徒的態度或動機。西方歷史上連宗教社會都要討論戰爭的性質問題。基督教一方面竭力反對戰爭,一方面也不得不對戰爭正義與否的性質作出規定,而西方當代對正義戰爭的定義也基本以此為基礎。〔60〕毛澤東提出了區分戰爭性質的三個具體標準——戰爭的政治目的、階級本質和歷史作用,并且指出要正確區分戰爭的性質,就必須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客觀實際出發,把戰爭進行綜合分析。毛澤東同時指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作為一對矛盾范疇,兩者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又相互對立。但矛盾雙方的性質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在一定條件下,正義戰爭可以轉化為非正義戰爭,非正義戰爭可以轉化為正義戰爭。以戰國為例,雖然秦國不斷發動戰爭并以首級記功,山東六國號之為“虎狼”,秦國的軍事行為看似“不仁”,看似是嚴重違背了軍事倫理思想,但列寧指出:“決定戰爭的性質的是戰爭所繼續的是什么政策、戰爭是由哪一個階級進行的、是為了什么目的進行的。〔61〕” 就戰國歷史和戰爭實際而言,秦國代表的是新興軍功地主階級,進行的是結束分裂的大一統戰爭。再結合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則顯見其是符合中國傳統軍事倫理思想評價標準的。
結語
朱熹注“不以兵車”曰:“言不假威力也。”〔62〕這看似與孟子所反對的“以力假仁者霸”的霸道背道而馳,但孟子對于齊伐燕亦云“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總之,戰爭是否正義,輔君用戰是否有功,最根本的判別標準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 “吊民伐罪”〔63〕。雖然兵家重利重殺,但不能就否定其沒軍事有倫理,其倫理在大義,儒家亦大之。在戰國之時,減少一次、數次戰爭的傷亡是小仁,用暴力手段摧毀舊秩序以及結束數百年的分裂則是大仁,是孔子亦大之的仁。但需要注意的是,霸道和王道是兩種均以治平為目的的政道,亂世用霸而治世則用王。治世仁及黎庶,在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軍事倫理的約束指導下提倡的是仁義之兵、大齊之兵,“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此為“小仁”。而在禮樂制度已經崩壞不能形成約束時的亂世,則重在澤被后世,故三代王者亦行之,“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64〕,此乃“大仁”。所以在正義戰爭性質不變的前提下,不論是以霸道還是王道思想指導下的軍事戰爭,其本質上都是符合軍事倫理思想的內在要求的。
【注釋】
〔1〕翁世平、孫君、天羽:《中國軍事倫理學研究綜述》,載《道德與文明》2006年第1 期。
〔2〕顧智明:《中國軍事倫理文化史》,海潮出版社1997年版,第2 頁。
〔3〕趙楓:《中國軍事倫理思想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 頁。
〔4〕王聯斌:《中華武德通史》,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版,第1 頁。
〔5〕張岱年:《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 頁。
〔6〕(漢)桓寬:《鹽鐵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5 頁。
〔7〕(戰國)韓非著,秦惠彬校點:《韓非子》,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 頁。
〔8〕(漢)劉安著,(漢)許慎注,陳廣忠校點:《國學典藏 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12 頁。
〔9〕(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555 頁。
〔10〕黃樸民:《大寫的歷史 被忽略的歷史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6年版,第56 頁。
〔11〕夏偉東:《目前軍事倫理學研究主要理論觀點綜述》,載《軍事倫理學研究》,藍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1 頁。
〔12〕陳澔注:《禮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 頁。
〔13〕鄭淑媛等:《倫理學導引》,東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 頁。
〔14〕王聯斌:《〈司馬法〉的軍事倫理思想》,《軍事歷史研究》1993年第1 期。
〔1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903 頁。
〔16〕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選》第2 冊,第502~503 頁。
〔17〕(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黃侃句讀:《周禮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 頁。
〔18〕薛藝兵:《論禮樂文化》,《文藝研究》1997年第2 期。
〔19〕孫君:《先秦時期軍事倫理與軍事法制發展關系探要》,《遼寧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 期。
〔20〕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圖版見其書第91~156 頁,釋文考釋見其書第241~285 頁)
〔21〕王青:《上博簡〈曹沫之陳〉的軍事思想》,《軍事歷史研究》2016年第2 期。
〔22〕(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徐小蠻標點:《呂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 頁。
〔23〕王立民譯評:《孟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 頁。
〔24〕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 頁。
〔25〕熊武一、周家法等:《軍事大辭海》,長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5 頁。
〔26〕王文濤:《論漢代的社會保障思想》,《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 期。
〔27〕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1072 頁。
〔28〕(唐)房玄齡注,(明)劉績補注,劉曉藝校點:《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 頁。
〔29〕李桂生:《兵家管理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 頁。
〔30〕許青春:《先秦兵家義利觀》,載《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 期。
〔31〕陳二林:《論〈孫子兵法〉的“利本”思想》,載《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 期。
〔32〕孫武著,吳九龍注釋:《孫子校釋》,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232 頁。
〔33〕呂菊:《〈孫子兵法〉功利觀辨析》,載《重慶郵電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 期。
〔34〕楊丙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1 頁。
〔35〕《中國軍事史》編寫組:《武經七書注譯》,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428 頁。
〔36〕趙志超:《先秦法家與兵家關系研究》,中國人民大學2019年博士論文。
〔37〕(戰國)尉繚:《尉繚子》,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5 頁。
〔38〕張申:《〈尉繚子·兵令下〉“殺”字解》,載《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3 期。
〔39〕(明)阮漢聞:《〈尉繚子〉標釋》,明天啟三年刻本。
〔40〕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 十通第十種》,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第876 頁。
〔41〕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徐復點校:《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170 頁。
〔42〕趙楓:《〈司馬法〉軍事倫理思想初探》,載《道德與文明》1992年第3 期。
〔43〕胡東原,張德湘:《孫臏軍事倫理思想研究》,載《學海》2008年第4 期。
〔44〕趙娜:《孫臏對孫武軍事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濱州學院學報》2013年第5 期。
〔45〕王聯斌:《孫臏的軍事倫理思想》,《軍事歷史研究》1994年第2 期。
〔46〕楊仲林、蔡聰美:《先秦為政理論與實踐》,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 頁。
〔47〕王慧:《古代兵書》,黃山書社2013年版,第50 頁。(張大可、何乃光主編,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亦持此觀點,詳見該書第41 頁。)
〔48〕唐濤、周名成:《名著鑒賞辭典》,遠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6 頁。
〔49〕曉垣:《中華名流大典》第2 卷,中國人口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6 頁。
〔50〕王贏:《“儲蓄”最早并非指金錢》,《人才資源開發》2015年第17 期。
〔51〕張申:《〈尉繚子·兵令下〉“殺”字釋義爭論述評》,《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
〔52〕歸有光輯評:《諸子匯函》,明天啟六年刊本。
〔53〕楊少涵:《論荀子隆禮重法的軍事倫理思想——從孔孟荀評管子論王霸說開去》,《蘭州學刊》2007年第5 期。
〔54〕(清)曾國藩:《兵鑒:曾國藩治兵籌策錄》,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 頁。
〔55〕曾國藩著,溫林編:《曾國藩全集·書信》,京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4 頁。
〔56〕周濤:《曾國藩軍事倫理思想初探》,《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年第6 期。
〔57〕《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445 頁。
〔58〕艾克恩編纂:《延安文藝運動紀盛1937.1—1948.3》,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 頁。
〔59〕鄒生才:《毛澤東軍事倫理思想論要》,《河池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7年第4 期。
〔60〕夏偉東、胡德榮:《軍事倫理學的意義》,載《道德與文明》1990年第2 期。
〔6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列寧全集》第25 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 頁。
〔62〕(宋)朱熹撰,張茂澤整理:《四書集注:大學 中庸 論語》,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 頁。
〔63〕王聯斌:《孟子的軍事倫理思想》,《軍事歷史研究》1993年第4 期。
〔64〕李零譯注:《司馬法譯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