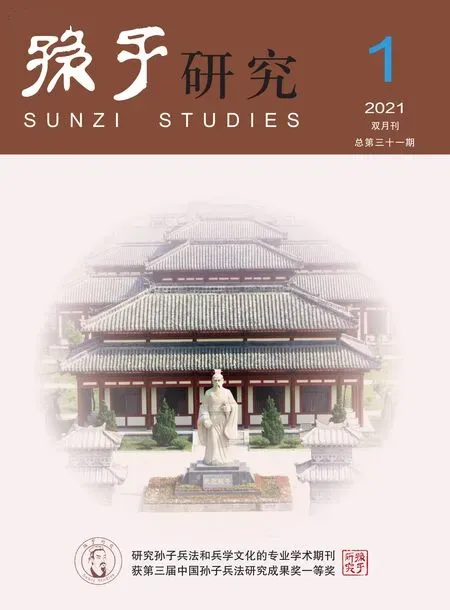“蔡侯以吳子”及孫武伐楚入郢考論
吳名崗
公元前506(魯定公四年)年,吳王闔廬伐楚“入郢”,幾乎滅了稱霸百年的楚國,是春秋時期的重大事件。早在六年前:
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
(《史記·吳太伯世家》)[1]
伍子胥同意了孫武的意見,并與之一起諫諍闔廬,闔廬暫時放棄了攻楚入郢的打算。六年后,應蔡、唐請求,吳軍才在孫武的謀劃和闔廬的指揮下與楚軍大戰柏舉,打敗楚相子常,攻入楚都郢城。蔡昭侯申不僅是伐楚的發起者,而且是重要的組織和實施者,但最終也是這次伐楚入郢的受害者。
周武王平定天下后,封其弟“叔度于蔡”,蔡國在今河南上蔡一帶。叔度因參與武庚作亂,被周公流放。后其子姬胡改邪歸正,“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復封胡于蔡”(《管蔡世家》)[2]。蔡國是姬姓諸侯,在晉楚爭霸的春秋時期,本屬晉國一方,但蔡國緊靠楚國,不得不與楚國交好,夾在晉楚之間,十分艱難。蔡昭侯居新蔡,遷都下蔡,公元前518年到491年執政,在位28年,與楚平王、楚昭王、晉頃公、晉定公,齊景公,魯昭公、魯定公,吳王闔廬、夫差等同時代。
1955年5月,安徽壽縣治淮民工在壽縣城西門內北側取土加固城墻時,發現了蔡昭侯墓,發掘出土了車、馬、兵器等大量珍貴文物,有青銅劍、箭簇、鼎、鐘、鬲、豆、方壺、鑒、盤、尊與編鐘等。經整理后共584 件,其中青銅器486 件,包括佩劍一柄,其中有銘文的尊、盤等多件,玉器51 件,金飾12 件,骨器28 件。這些文物分藏于國家博物館、安徽省博物館和壽縣博物館。在觀看這些文物時,不僅讓我們聯想到蔡昭侯所主導的吳、蔡等伐楚入郢之戰之慘烈,也讓我們見證了蔡昭侯與吳王闔廬、孫武等伐楚入郢時的青銅劍、箭簇等真實兵器,沉入了對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的思考。
一、因“一佩一裘”引發的一場大戰
蔡昭侯的隨葬品中有51 件玉器,這應是他生前佩戴、使用之物,可見他對玉器之喜愛。君子愛玉,無可厚非,但蔡昭侯因為一件佩玉而引發了一場大戰,卻是其始料所不及的。
(一)蔡昭侯因無法送楚相子常佩玉和裘服而被留楚三年
蔡昭侯為訪問楚國,精心準備了兩件禮物送給楚昭王。“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左傳·定公三年》)[3]蔡昭侯把與自己相同的一件玉佩和一襲裘服獻給楚昭王,精美的玉佩和漂亮的裘服讓楚昭王很高興,楚王設宴款待蔡侯。宰相子常參加宴會作陪,看到昭王和蔡侯穿著一樣的裘服,佩戴著相同的美玉,自己非常羨慕。會后,子常示意蔡侯隨從,希望蔡國也送他一套與昭王相同的禮品。蔡昭侯知道后,一是自己再沒有第三套相贈,二是把相同的禮品贈送國王和宰相是不符合禮法的,所以沒有把自己的一佩一裘送子常。因此,子常把蔡昭侯強留在楚國達三年之久。
訪楚的唐成公與蔡昭侯遭遇相同,因沒有第三匹骕骦馬送子常而被留在了楚國。實在沒有辦法,后來唐侯的部下竟把國君灌醉,偷出唐侯的骕骦馬送給子常,才被放回唐國。蔡國人見唐國成功,也照葫蘆畫瓢,弄出蔡侯的一佩一裘送給了子常。子常收到一佩一裘后,對蔡侯的隨從說:“蔡君在楚國待了這么久,是因為楚國沒有準備好送給蔡國的禮品。明日,如果負責這項工作的官員再拿不出給蔡君的禮品,我就處死他們。”這才放了蔡昭侯。
蔡昭侯在回蔡的路上經過漢水時,把一塊美玉沉入江心。他發誓說:“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左傳·定公三年》)[4]意思是:我不報此仇,再渡漢江,就和這江水一樣一去不返!
(二)晉侯等十八國諸侯伐楚至召陵,不戰而返
蔡昭侯回國后,立即找盟主晉國,要求伐楚。“蔡侯入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左傳·定公三年》)[5]作為盟主的晉定公,一方面報告周天子,一方面組織各諸侯國伐楚。公元前506年春天,晉、魯、蔡、衛等18 國諸侯率領大軍集結到楚國邊境的召陵,周王室派劉文公作為代表參加伐楚。魯國的孔子在其《春秋》中是這樣記載這次軍事行動的: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春秋·定公四年》[6]
這是當時除秦、越外的幾乎所諸侯有國家,而且除齊國外,都是國君親自率領軍隊參加。但也有例外,緊靠楚國的沈國拒絕參加這次伐楚。于是,聯軍司令晉國的范獻子令蔡軍攻沈。“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春秋·定公四年》)[7]這次蔡滅沈,也為楚滅蔡埋下了禍根。沈,在今河南汝南東。
正當聯軍將要對楚開戰之際,“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辭蔡侯。”(《左傳·定公四年》)[8]晉國的荀寅是這次伐楚聯軍的副總司令,他借機向蔡昭侯索賄,蔡侯不給,于是荀寅就公開說了不該伐楚、應辭蔡侯而撤兵的所謂理由。荀寅的這些說辭,如果是在各國未出兵前,在晉定公未決策前,那也罷了。十八國諸侯聯軍已經來到楚國,蔡國聽命已經滅掉了沈國,荀寅這個時候說出這樣的話,誰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范獻子和荀寅是同伙,荀寅索賄應是其授意,所以荀寅說出這些話后,范獻子就決定退兵了。
十八國諸侯大軍千辛萬苦一趟,就這樣撤兵了。這次伐楚雖然未戰,但王室的劉文公和杞國的國君都死于這次軍事行動。許國因靠近楚國,害怕楚國報復,在十八國諸侯聯軍撤兵后,“遷于容城”(《春秋·定公四年》)[9]。
秋,“楚人圍蔡”,蔡國面臨危亡。這時的蔡昭侯可以說是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萬般無奈,他只好求救于吳國。吳國肯出兵嗎?單單一個吳國能與強大的楚國相抗衡嗎?
(三)孫武曰“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作為敵國和鄰國,吳國對楚國及蔡國的情況當然是關心的,對兩國的情況也了如指掌。十八國諸侯撤軍之后,蔡國被楚國圍困之際,吳王闔廬也正考慮借機攻楚入郢。
九年,吳王闔廬請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史記·吳太伯世家》[10]
唐是離楚國郢都比蔡國更近的國家,今湖北省隨州市隨縣唐縣鎮是春秋唐國故地,有骕骦亭。“得唐蔡乃可”是伐楚入郢的戰略問題,因為得唐、蔡至少有如下好處:
1.出師有名。因唐、蔡而伐楚是對楚相子常貪腐無道的懲罰,是子常扣押唐成公、蔡昭侯于楚國三年所引起的。因蔡伐楚名正言順,從道義上增強了吳國的力量。“道”是在戰爭中能否取勝的首要條件,如果吳國無故侵楚,在道義上就難以得到國內外的支持。現在楚國令尹子常無道,因索賄而遭唐、蔡人的怨恨,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憤,因此才有十八國諸侯侵楚到召陵。諸侯不戰而退,吳國應唐、蔡兩國之邀伐楚就是正義之舉,是為天下人伐無道。吳國秉持正義,成了天下敢于抗衡無道強楚的英雄,攻楚入郢就成了一場正義戰爭。
2.增強了吳國的軍事實力。唐、蔡不僅向吳國提供了實力可觀的軍隊,而且可以在后勤保障方面向遠征強楚的吳軍提供后勤保障。唐、蔡是更靠近楚都郢的鄰國。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蔡在今河南新蔡一帶,唐國在今湖北省隨縣,離襄樊很近。
3.得唐、蔡有伐楚的地理優勢。唐是比蔡小的國家,不在一個層級上。蔡是十二諸侯之一,唐則不見于《春秋》,連小邾國都不如。孫武所以把“唐”放在“蔡”前,正是看中了它比蔡更靠近郢都的地理優勢,而吳軍正是經蔡、唐而伐楚的。唐本是楚的屬國,對楚國各個方面都很熟悉,可以向吳軍提供各方面的幫助。
4.削弱了楚軍的士氣。楚國人本來對令尹子常的貪賄聚財就非常不滿,現在因為他向鄰國國君索要佩玉、裘服、駿馬而引起戰爭,楚國士兵打仗只是為了令尹的個人貪財索賄而賣命,士氣自然不會高,并且會有怨言,這就無形中削弱了楚軍的士氣和戰斗力。吳因唐、蔡伐楚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瓦解楚軍的作用。
5.協調了吳國與諸侯國的關系。在諸侯紛爭的春秋時期,任何一國的強大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高度關注和警覺,因為“鄰之厚,君之薄也”。吳國攻楚自然會引起各國的注意,甚至有“諸侯乘其敝而起”的危險。現在吳國因唐、蔡而伐楚,是做了十八國諸侯要做而沒有做成的事,是替天下人鳴不平,所以各國都樂意看到吳國伐楚為他們出氣,而不與吳為敵。
對于孫武和伍子胥的“必得唐、蔡乃可”的謀略,闔廬自然能心領神會,會認為這是天賜良機,是攻楚入郢的好機會。所以,蔡昭侯求吳攻楚的計劃進行得很順利,可謂一拍即合。
《左傳》載:“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郗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11]《左傳》這是說蔡侯借吳兵以伐楚,實際上吳國也是借蔡以伐楚。蔡、唐與吳相互為用,結為一體,這就為擊敗楚國奠定了基礎。
二、“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柏舉之戰是蔡、吳、唐伐楚入郢的關鍵之戰,《春秋》《左傳》《史記》等從不同的角度記載了這場大戰。
孔子的《春秋》從全局著眼,正面記載了柏舉之戰: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12]
以現代新聞的要求來看,五W 俱全,十分清楚,并且還特別交代了柏舉之戰是蔡昭侯主導的:“蔡侯以吳子”是吳王為蔡侯所用之意。杜預的注說:“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13]“及”說明是蔡、吳聯軍主動進攻楚軍。“敗績”是大敗。“楚囊瓦出奔鄭”,不但寫出了楚軍主帥子常的下場,而且有指明囊瓦罪責之意。
《春秋》沒有寫“唐”,但是唐國是參加了柏舉之戰的。為什么不寫唐呢?唐是小國,它的軍隊沒有單獨成軍,唐軍交給了吳國指揮,所以《春秋》中無唐。從《春秋》和《史記》的記載看,蔡在柏舉之戰中,部隊應是獨立的。從春秋時期的戰爭和《左傳》對柏舉之戰的記載看,三國聯軍應分為三軍:夫概一軍,蔡一軍,夫差一軍,蔡侯和吳王在中軍。不然,孔子不會那樣寫。
(一)“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
《左傳》對柏舉之戰記載比較具體。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后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14]
蔡國是個沿淮國家,行船是吳軍的長處。據此,吳軍選擇了沿淮而上的進軍路線。“舍舟于淮汭”既是對吳軍沿淮西進的記載,也是關于孫武用計的記述。因吳軍“舍舟于淮汭”這個看來再正常不過的行為,卻藏著孫武的分兵之計。孫武在其兵法中說:“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孫子兵法·虛實篇》)楚將左司馬戌偵知吳軍“舍舟于淮汭”,他要毀舟切斷吳軍的退路,企圖把吳軍徹底殲滅于楚地,其計策不可謂不狠毒。但是,此計至少犯了兩條致命的錯誤:一是分散了楚軍兵力,二是逼迫吳軍死戰。這對當前的楚軍都是大忌。司馬戌向蔡國方向的淮汭進軍后,留下與蔡、吳、唐聯軍對抗的就只有令唐、蔡人恨之入骨的楚相子常了。這個貪腐無底線的囊瓦,不僅傷害了蔡、唐兩國,其實也被楚國百姓所憎恨,所以他的部下史皇當面對他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在戰場上,司馬戌要求子常“沿漢而與之上下”,是讓囊瓦堅守漢江等待其回軍共殲吳軍,但吳軍這時在漢水以東與楚軍相持是等待戰機。
自私自利的人最容易被“利”所誘惑,也就最容易犯錯誤。還沒等到孫武用計引誘子常上鉤,子常就為了爭功而聽從部下之計,不等司馬戌回師,就毀約渡過漢江與蔡、吳、唐聯軍開戰,結果三戰三敗,以至于“知不可,欲奔”。一支主帥都想逃跑的楚軍,其戰斗力是可以想見的。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15]
《左傳》的這段記載,如下要點須特別注意:
1.三國聯軍的總指揮是吳王闔廬而非孫武,這有夫概“晨請于闔廬”為證。后世的蘇洵等人要孫武為聯軍入郢后的暴行負責,是不知道誰是蔡、吳、唐聯軍大權的執掌者。后世把柏舉之戰的功績歸于孫武,主要是闔廬聽從孫武之計而取得的。
2.夫概違命私戰,有罪無功。在戰場上,有君主在,夫概王沒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權利,他是公開違抗命令。他雖然擊敗了子常之卒,但子常的失敗早成定局。如果依從孫武的謀劃,密切觀察,抓住最佳時機攻楚,吳軍的犧牲會更小,勝利會更大。
3.《左傳》雖然沒有提到蔡軍,但蔡軍在柏舉之戰中一定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史記·管蔡世家》說:
蔡昭侯使其子為質于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廬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16]
蔡國人對子常之痛恨,子常是知道的。他也知道自己扣留蔡昭侯三年是何等的無道,所以他對蔡人對他的恨之入骨內心非常恐懼。在柏舉之戰前,他就“欲奔”,柏舉之戰一打,他的部下就散了,他本人則“奔鄭”。所以,可以想見,蔡軍在柏舉之戰中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三、吳軍入郢及“子期、子蒲滅唐”
(一)吳軍入郢
吳夫概不待命而攻擊楚軍子常的主力后,楚軍潰敗,吳王闔廬隨即下令全軍進攻。至清發江,吳軍故意放過部分楚軍,半濟而擊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庸澨而從之,五戰及郢。”(《左傳·定公四年》)[17]按照杜預的注解,“敗諸庸澨”因“奔食,食者走不陣,故不在戰數”。所以,所謂“五戰及郢”,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再加柏舉之戰、清發之戰共五戰,其他不成陣的小戰則不計。
柏舉之戰后,吳王闔廬本應依照軍令處罰夫概、整頓軍紀,但是夫概是闔廬的同母弟,擊楚又取得了勝利,所以就沒有追究夫概的責任。夫概自以為有功,更加恣意而為。因此,蔡、吳、唐聯軍在柏舉之戰后就陷入了失控狀態,吳王闔廬之命已不被遵守,孫武之謀已無人執行。各支部隊各行其是,不但出現了太子與夫概爭宮,而且導致了夫概自行歸吳,自稱為王。柏舉之戰后的混亂和失敗,都是吳王闔廬不執行軍紀,不對夫概進行懲處所導致的。
《淮南子·兵略訓》說:“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19]“君臣乖心”是指夫概和吳王闔廬背離,吳軍失去團結。在這樣的情況下,孫武的謀略再好,也無法讓吳軍應敵。《兵略訓》極可能是伍子胥的后代伍被所著,他對柏舉之戰是了解的。總之,柏舉之戰后,吳軍失去了控制,各支部隊自行其是,如此焉能不敗!
(二)子西、子蒲滅唐
吳王闔廬對聯軍失去控制,對伍子胥、伯嚭也不加約束。蔡、吳、唐軍入郢后,可以說是有仇的報仇,有冤的報冤,各種殺掠復仇行為都有。伍子胥掘墓鞭尸固然令楚人無法接受,唐軍、蔡軍對楚的復仇也讓楚人無法忍受。在楚人看來,唐、蔡這樣的小國,只有服服帖帖的服從楚國之事,那有小國到楚都橫行的道理?所以,各種復仇行為激起了楚人的激烈反抗,而申包胥是楚人誓死抗擊蔡、吳、唐入侵的典型代表。
申包胥逃到秦國去搬救兵。秦國看到吳軍直入郢都,如此厲害,不想出兵救楚。秦伯派使臣對他說:“我知道了,您先到館舍住下,我們商議商議再告訴你。”申包胥說:“吾君現在還在野外逃難,無處安身,我怎么能到館舍住下呢?”他“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20]。申包胥隨秦將子蒲、子虎及戰車500 乘、大軍50000 人救楚,但這已經是“吳入郢”第二年六月的事了。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21]這是楚、秦共擊吳軍所取得的一個重要勝利,也是戰爭的一個轉折點。
唐因國小而不被《春秋》所記載,但《左傳·定公五年》還是為唐國的被滅亡記上了一筆。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左傳·定公五年》[22]
杜預注說:“從吳伐楚故。”[23]子西是楚將,子蒲是秦將。在吳、蔡軍與秦、楚相持之際,子西、子蒲先滅唐,可見唐對這場戰爭之重要。這是因為,唐離楚近,是蔡、吳、唐聯軍的根據地,所以楚才急于滅唐,這也可見楚對唐之仇恨。滅唐對楚是件大事,《史記·楚世家》載:昭王“十年冬,吳王闔廬、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楚昭王滅唐”[24]。唐本來是楚國的屬國,公元前597年(魯宣公十二年),唐惠侯曾跟隨楚莊王與晉軍戰于邲,是楚國欺壓小國太甚,才逼迫他們寧可滅國也要反抗楚國的迫害的。
(三)魯國“歸粟于蔡”
蔡昭侯以吳子伐楚,得到了魯國的支持。《春秋·定公五年》載:“夏,歸粟于蔡。”[25]這是魯國對蔡國的支持,也是對吳軍的支持。《公羊傳》和《谷梁傳》認為,支援蔡國糧食的不僅是魯國,還有其他諸侯國,這也是可能的。
四、蔡國遷州來與孔子居蔡
蔡、吳攻楚入郢之傷痛,十年之后楚人仍痛恨不已。
(一)蔡遷州來
《春秋·哀公元年》載:“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26]這年是蔡昭侯二十五年,楚昭王二十二年。《左傳》的記載是:“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27]
楚、陳、隨、許四國國君率軍圍困了蔡國國都,他們圍繞蔡都修建廣一丈、高二丈的工事一周,晝夜圍困,要求蔡人北遷,把土地讓給楚國。蔡國被迫出降,答應楚國的要求,楚軍等才退去。
第二年,蔡國沒有按照楚國的要求北遷,而是東遷。《春秋·哀公二年》:“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28]此年是蔡昭侯二十七年。《左傳》載:“吳洩庸入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29]遷都是件大事,關系到許多人的利益,很多人不愿遷都,蔡國遷都州來是在吳軍的脅迫下遷徙的。《史記·管蔡世家》載:“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30]
(二)孔子居蔡
孔子在公元前493年來到蔡國,這年是魯哀公二年,蔡昭侯二十六年。《管蔡世家》載:“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吳。”[31]這年“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春秋·哀公二年》)[32]。孔子入蔡在蔡遷州來之前。
孔子在蔡國待了三年。《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后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33]
這就是說,自蔡遷都州來到蔡昭侯被殺這段時間,孔子都在蔡國,他是這段歷史的經歷者和見證者。孔子應該是見過蔡昭侯,他對蔡昭侯從被楚相囊瓦扣留到蔡、吳、唐伐楚的歷史事實一定是清楚的。除了蔡昭侯,孔子也一定見到了其他柏舉之戰的參加者。所以,有關柏舉之戰及其以后的戰事和變局,孔子是清楚的,他在《春秋》中的有關記載是絕對真實可信的。
州來是今天的何地?《辭源》的說法是:“州來:古地名。春秋時楚邑。后屬吳。魯哀公二年,吳王夫差遷蔡昭侯于此,改稱下蔡。故址在安徽壽縣。”[34]1955年在壽縣發現并發掘了蔡昭侯墓,證實《春秋》《史記》所記州來在壽縣,因為蔡侯墓不會離他的都城太遠。
蔡昭侯墓出土的部分青銅器有銘文,蔡侯申尊有銘文23 行95 字,記載了公元前518年蔡昭侯為大孟姬作媵嫁之事,有“敬配吳王”之語。從這些出土文物看,蔡與吳既有共同抗楚的盟友關系,又有親戚關系,這從蔡遷州來可以看出其關系之非同一般。蔡昭侯過于依賴吳國,也導致了他的被弒。唐、胡、頓都是因反楚而滅亡的小國。楚國的無道,迫使那些本來追隨自己的小國無奈反楚的教訓,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蔡昭侯以吳王闔廬、伍子胥、孫武伐楚入郢已經過去了2526年,戰時使用的箭簇仍在,蔡昭侯的佩劍仍在,孔子的《春秋》仍在,歷史的真實是不容懷疑的。這場戰爭留給了后人太多的思考:楚國的衰敗,蔡國的滅亡,吳國的興盛和迅速亡國……這些問題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而現實之殘酷并不亞于春秋時期。
【注釋】
[1] 司馬遷:《史記》第五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66 頁。
[2] 司馬遷:《史記》第五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565 頁。
[3]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4-1615 頁。
[4]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5 頁。
[5]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5 頁。
[6] 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2 頁。
[7] 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2 頁。
[8]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9 頁。
[9] 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 頁。
[10] 司馬遷:《史記》第五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66 頁。
[11]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8 頁。
[12] 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 頁。
[13]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8 頁。
[14]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8 頁。
[15]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8-1629 頁。
[16] 司馬遷:《史記》第五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568-1569 頁。
[17]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9 頁。
[18]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9 頁。
[19]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下冊,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088 頁。
[20]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 頁。
[21]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8 頁。
[22]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8 頁。
[23]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9 頁。
[24] 司馬遷:《史記》第五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715-1716 頁。
[25] 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7 頁。
[26] 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6 頁。
[27]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6 頁。
[28] 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9 頁。
[29] 左丘明:《左傳》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2 頁。
[30] 司馬遷:《史記》第五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569 頁。
[31]司馬遷:《史記》第五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569 頁。
[32] 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9 頁。
[33] 司馬遷:《史記》第六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928-1930 頁。
[34]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辭源》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95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