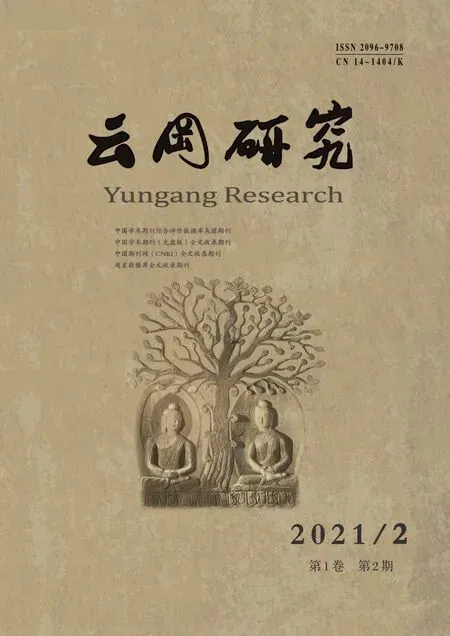考古學建構下的印度佛教史——拉爾斯·福格林《印度佛教考古史》評介
湯移平
(1.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2.江西財經大學旅游與城市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2)
一
印度早期佛教研究主要建立在語言學和歷史文獻學的方法上,直接從梵、巴、漢、藏、中亞語言的原始文獻,以及其它的碑刻銘文中,進行文本的校勘解讀。自19世紀以來,隨著科學考古學的誕生,學者們對印度佛教古跡遺址進行了全面地調查和發掘。研究表明,綜合運用考古材料,多角度地思考和解讀,往往能夠展現更為豐富的歷史圖景。
拉爾斯·福格林(Lars Fogelin)是美國亞利桑那(Arizona)大學人類學學院的考古學教授,他早年曾對印度奧里薩(Orissa)邦托特拉康達(Thotlakonda)佛教遺址進行過深入調查。福格林的研究方向主要為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科學哲學在考古學上的應用,他擅長利用考古學的方法探索宗教的不同層面,以此審視寺院制度和僧侶生活。福格林認為,文獻學與考古學之間有許多需要對話的地方,佛教文獻為印度佛教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證據和見解,但考古學材料有其自身的特點,佛教考古史需要對考古學證據和文獻學證據給以同樣的關注。
《印度佛教考古史》(An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是對印度佛教考古的全面考察,作者的目的,不僅是要尋找佛教的歷史脈絡,還要為宗教考古提供一個范例,即重新詮釋印度佛教的發展歷史,重新定位考古學在佛教研究中的作用,探索宗教考古的理論與方法。福格林對印度佛教考古史的撰寫,采用的是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他主要通過實物遺存,探討僧侶和信眾的關系。
《印度佛教考古史》共八章,福格林按時間順序進行了闡述。第一章為導言,考古和印度佛教史;第二章為宗教的物質性(Material);第三章為從佛陀至阿育王,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00年;第四章為僧侶(Sangha)與信眾(Laity),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第五章為大乘佛教的起源、佛像以及寺院隱居(Isolation),公元100年至公元600年;第六章為佛教信眾與宗教融合(Syncretism),公元第一個千年;第七章為寺院佛教的鞏固(Consolidation)和崩塌(Collapse),公元600年至公元1400年;第八章為結論。
二
僧侶與信眾的關系貫穿于福格林的整個研究,福格林結合考古發現,從“關系”的角度,對印度佛教考古史進行了獨特的闡釋。
公元前6世紀—前4世紀,佛教遺存十分有限,考古學難以增加人們對該時期佛教的理解。福格林認為,根據羅賓·科寧漢(Robin Coningham)在藍毗尼(Lumbini)發現的樹祠(Tree-shrine),佛教朝圣可能在孔雀王朝之前就已經開始,并盛行于公元前3世紀。而公元前1世紀的孔迪維特(Kondivte)石窟,以及更早的貝拉特(Bairat)、洛馬斯·里希(Lomas Rishi)、蘇達瑪(Sudama)等早期遺址表明,很可能在公元前3世紀,佛教徒就已經在木材或茅草建造的圓形小屋中沿塔繞行,且有舉行集體儀式的大廳與之毗鄰。
公元前2世紀之前,考古材料只允許對佛教活動作一般性地推測,自公元前2世紀開始,佛教建筑、碑銘、圖像等資料開始大量出現。從考古遺存來看,這時期的佛教機構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朝圣中心(Buddhist Pilgrimage),即僧侶和信眾共同朝拜的佛塔建筑群,如桑奇(Sanchi)、巴爾胡特(Bharhut)、阿瑪拉瓦蒂(Amaravati)、康那伽納霍利(Kanaganahalli)等大型佛塔朝圣中心;第二類是佛教寺院,如西印度石窟,以及安得拉(Andhra)邦和奧里薩(Orissa)邦的佛教寺院。
通過朝圣中心和佛教寺院的比較,福格林認為,自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僧侶和信眾的儀式活動開始出現分歧。因為此時的僧侶嚴重依賴國王、行會、信眾的支持和捐助,他們在寺院建造公共禮拜大廳,或者改變佛塔的形態,使之看起來更加威壓和壯觀,旨在確立他們對信眾的權威,以及佛陀合法繼承人的地位。此時的僧侶大大減少了隱居生活,轉而專注于建立他們在信眾中的權威。不過根據該時期朝圣中心的布局可知,信眾并未默許僧侶作為佛陀合法繼承人的地位。
為強化對信眾的權威,僧侶不得不在政治、經濟和精神上與信眾交往,這使得寺院生活越來越社區化,某種程度上,僧侶失去了隱居苦行和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只能在寺院創造多種建筑空間,以滿足個人修行和群體活動的需求,如供個人使用的僧房和群體禮拜的大廳。不過信眾并未默認僧侶地位的合法性,他們選擇了獨特的禮拜方式,強調自己與佛陀的關系。當僧侶開始禮拜佛陀的象征符號時,信眾仍一如既往地朝拜佛塔。福格林認為,信眾保留了佛教的最初形式,并抵制著僧侶改變佛教儀式的行為。
在19世紀的佛教文獻研究中,早期僧侶一直被描繪成孤獨的苦行者,他們在信眾的支持和捐助下,沉浸在超脫世俗的思考之中。福格林指出,根據考古學、碑銘學、圖像學等研究,早期僧侶對隱居苦行(Seclusion)的興趣并不高,遠非文獻學研究的那樣,而禁欲苦行也并非從一開始就有,它們是后來形成的。
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僧侶極力尋求領導整個佛教群體,為此他們在寺院設立公共禮拜大廳。在西印度石窟內,他們控制佛塔的外形,使之看起來更加高大,以此增強對信眾的權威。根據茱莉亞·肖(Julia Shaw)在桑奇山的調查,僧侶積極地參與社會實踐,如加強寺院周邊農業和灌溉設施的建設。僧侶為了自己的利益,通過各種手段,將佛陀遺產的繼承合法化,并因此積累大量財富。
從公元2世紀開始,除最富有的信眾以外,僧侶開始退出與普通信眾的常規接觸。他們退回到寺院里,依靠大額捐助和寺院生意營生。福格林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僧侶創造了一種新的佛教形式,即大乘佛教,這使得苦行隱居合法化。
三
大乘佛教的興衰是僧侶和信眾關系的外在體現,福格林從政治、教義、儀式、建筑、象征意義等方面揭示了大乘佛教起源、發展和演變的內在動因。
自公元元年之后,佛教寺院逐漸成為自給自足的機構,公元500年,寺院儼然成為強大的政治和經濟機構,他們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福格林認為,這種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使得僧侶可以減少與信眾的日常接觸,他們不再以宗教人士的身份與信眾互動,而是以地主的身份與他們來往。以前僧侶必須在隱居和生存之間平衡,現在他們可以自由地將自己隔離在僧房里,過著苦行禁欲的隱居生活,將自己沉浸在以佛陀為中心的內觀中。從寺院布局也可以看出,僧人與信眾的活動分區越來越明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佛教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如大乘佛教的興起、佛像的創制、苦行的產生等。以前佛陀被塑造成信眾崇拜的樣子,現在他則被描繪成孤獨的隱居者形象,因為大乘經典強調內在的佛性,以及獨處和冥想的價值。總之,寺院經濟的發展為僧侶隱居提供了條件。
考古證據表明,公元2—6世紀,僧侶在個人隱居和群體隱居之間找到了新的平衡。由于積累了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僧侶逐漸脫離了與信眾的日常接觸,不過他們并未選擇個人隱居,而是選擇群體隱居,并致力于佛教經典的創作。福格林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關于禁欲苦行的佛教文獻大都出現于這個時期,而在早期的考古、碑銘或圖像中,卻沒有相關的證據,因為這些文獻并非佛陀或早期佛教的真實記載,而是僧侶的后期創造。
盡管在公元第一千年內,印度的政治和宗教環境不斷變化,但信眾的朝拜模式卻依然保持穩定。與寺院佛教相比,信眾佛教更為保守。雖然佛像在朝圣地也有出現,但大多數情況下,信眾依然圍繞著佛塔禮拜,并在庭院里舉行公共儀式。信眾佛教的變化主要是人數,而非禮拜方式。福格林指出,僧侶對信眾的拋棄,是佛教衰落的主要原因。相反,為獲得信眾的支持,早期印度教大量吸收佛教儀式,他們有的還把印度教寺廟改造成佛教寺院的形式。公元1000年前后,寺院僧侶基本上退出了與信眾的日常交往,完全沉浸于苦行隱居。當社會發生變動時,僧侶再也無法獲得信眾的支持,因為他們早已轉向印度教、耆那教等敵對宗教,這直接導致佛教在印度的衰落。福格林認為,公元7—12世紀,寺院僧侶大都專注于經文,佛教也變得越來越學術化。為反對寺院佛教的經學轉向,部分僧侶逐漸離開寺院,在社會邊緣過著流浪苦行的生活。至公元15世紀,佛教痕跡僅存于印度教、耆那教、伊斯蘭教或其他宗教的活動中。
四
福格林的《印度佛教考古史》在研究方法上,與歐洲和南亞的考古學者有著明顯的區別,福格林以人類學為導向,他關注的是僧侶和信眾的行為,這與關注古代社會各方面細節的歷史學導向有著很大不同。
歐洲和南亞的考古學被認為是歷史學的一部分,但在美國,考古學卻是人類學的分支學科,這源于美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當人們從古代遺址中發現文化遺存的時候,總會很自然地把這些遺存與印地安人祖先聯系起來,這種學術上的聯系,最終造就了美國考古學的人類學傳統。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其主要任務是設法從人的角度解釋物質文化,這種以人類學為導向的研究,將物質文化視為人類適應其環境的獨特手段和方式,它探索的是人類文化的性質及其發展演變規律。
作為一名美國考古學家,福格林不但重視人類學關于實踐、物質性和符號學的最新見解,而且還堅持利用馬克思、韋伯(Weber)、迪爾凱姆(Durkheim)、特納(Turner)等人的理論和方法。福格林認為,印度佛教自開始便充滿了矛盾和分歧,其中最主要的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和群體主義(Communalism),印度佛教史就是研究佛教徒如何利用、解決、包容這些矛盾和分歧。要解決相互矛盾的宗教實踐和信仰,就需要利用多種理論和方法。當然,福格林的人類學傾向并未影響他對佛教遺跡的全面調查,他盡可能地通過考古數據,闡述佛教的發展變化。此外,福格林還充分利用南亞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佛教主張的是超越現實和世俗,長期以來,佛教研究大都集中于文獻和精神層面,忽視了信仰的物質表達。因此從物質的角度研究佛教,必然會產生一種與佛教徒信仰不同的理解,這正是福格林的目標,因為物質遺存是意識形態的具體反映,福格林充分利用佛教考古與發現,通過古跡分布、佛寺布局、佛塔建筑等方面的研究,全面探討了遺存背后的宗教文化內涵。福格林還結合佛教寺院和朝圣中心的建筑特點,對僧侶和信眾的儀式活動進行了相應研究。
五
《印度佛教考古史》通過建筑、圖像、儀式、教義、象征意義等的分析,從考古學視角,對印度佛教進行了新的詮釋,這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尤其是從僧侶和信眾的關系、個人主義和群體主義等問題著手,具有明顯的獨創性,不過亦有可深入的地方。首先,本研究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佛教考古史,福格林以人類學為導向,對僧侶與信眾的關系進行探討,以此呈現佛教歷史的某一層面,但對佛教考古史的梳理,卻有一定的不足。其次,福格林雖然倡導佛教研究的多元融合,但對歷史、考古、建筑、藝術等不同學科之間相互作用的討論明顯單薄。
雖然在闡述對象和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并不影響作者的基本觀點,應該說,本研究對宗教考古具有無可爭辯的價值。